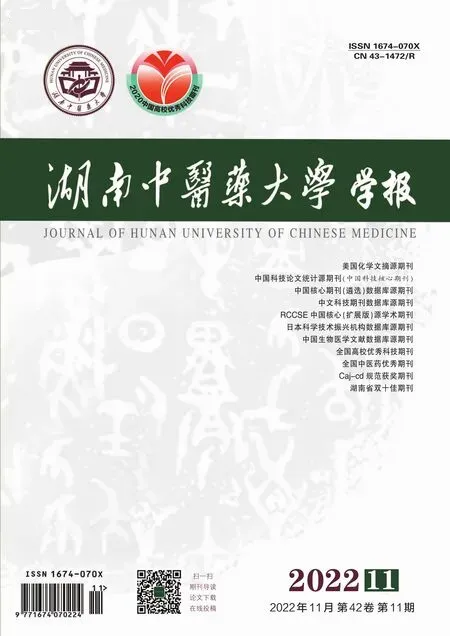孙克伟教授辨治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经验
王石中,苏晓岚,涂雨落,彭 憬,孙克伟
(1.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 410208;2.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 410007)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PBC),又称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是一种自身免疫性以慢性肝内胆汁淤积为特点的肝病。 本病以慢性胆汁淤积、血清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γ-谷氨酰转移酶(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 GGT)升高、血清抗线粒体抗体(anti-mitochondrial antibadies, AMAs)阳性为特征,组织病理学显示非化脓性破坏性胆管炎或“花管病变”和以淋巴细胞浸润为主的小叶间胆管破坏为主要病理特征[1-2]。PBC 发展隐匿,早期可无明显症状,或仅出现皮肤瘙痒,部分患者发现时已出现肝硬化。 PBC 主要表现淤胆等临床相关症状,包括乏力、纳差、黄疸、皮肤瘙痒、腹泻等[3]。 熊去氧胆酸是其一线治疗用药,部分患者可获得生化以及组织学上的改善,但乏力、瘙痒、纳差等症状难以解决[4]。
孙克伟系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一级主任医师,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全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湖南省名中医,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病种研究负责人和首席专家。 孙教授诊疗肝病数十载,临床经验丰富,在多年的诊疗中对PBC 的病因病机、治疗有独到见解,临床疗效佳,现报道如下。
1 病因病机分析
中医古籍中并无PBC 的病名记载,根据其不同的疾病阶段可归属于中医学的“风瘙痒”“泄泻”“黄疸”“积聚”“臌胀”等范畴。 《灵枢·五音五味》曰:“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本病多发于中老年女性患者[1]。 孙教授认为本病是基于患者肝血不足、情志抑郁导致气滞、血瘀、脾虚湿阻,进而形成多证兼夹的综合病症。 依据疾病特点及症状将本病病程分为肝郁期、黄疸期、肝肾虚损期3 期,认为“肝郁脾虚”是本病的关键病机,并贯穿本病始终。
肝郁期为疾病初起期,常以皮肤瘙痒起病,其特点为四肢为甚,时发时止。大都医家认为瘙痒常责之于血虚风燥、风热、血热[5],孙教授则认为本病瘙痒为肝郁所致,因肝气郁结,气机不畅,营卫之气不能远达四末,故发瘙痒,以四肢为甚。 《灵枢·邪客》曰:“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气机疏泄随情志而变,气机畅则瘙痒缓,临床中常见患者皮肤瘙痒时发时止。 《丹溪心法·郁症》言:“盖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不得变化也,此为传化失常。”肝郁犯脾,传化失常,肝郁期除感皮肤瘙痒外,常伴纳差、腹胀、泄泻等脾虚之症。
如未重视、及时控制本病,疾病会在肝郁期的基础上出现黄疸之症。孙教授主张依循“阳黄-阴阳黄-阴黄”[6]的辨证模式论治分析黄疸期。 《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言:“然黄家所得,从湿得之。”有别于寻常阳黄多责之湿热,孙教授则认为本病阳黄当责之于瘀热。 肝郁不解,气血郁遏不通生瘀,久则化火生热,蕴蒸肝胆,精汁疏泄失常,溢于肌表,发为瘀热阳黄。 患者以肤色鲜黄如橘,瘙痒随热而重为主症,也可因瘀热伤阴而出现口干、咽干、目干、大便干结等症;若黄疸的持续时间过长,月余不消,则邪盛正衰,最终导致阳虚寒湿内生。 又或过用苦寒、寒凉药物,如苦寒之药久用,或病轻药重,则损脾败胃,脾阳渐衰,导致寒湿凝滞,转化为阴黄。如“用茵陈之药过剂,乃成阴黄。 ”(《丹溪心法·疸》)患者肤色多暗黄,以乏力、纳差、腹胀、泄泻为甚。 本病主要病机为肝郁脾虚,虚实夹杂,实为“瘀热”,虚为“脾虚”。 病情若处于阳黄向阴黄转化的一个特殊的病理阶段,其病机为瘀热兼脾虚,既具有阳黄与阴黄二者的病因病机和证候的多种特征,但又不能完全归之于阳黄或阴黄,故孙教授提出“阴阳黄”概念病情阶段,此阶段是阳黄向阴黄渐进的中间阶段,患者肤色介于鲜明与暗黄之间,以瘙痒重、纳食差、乏力、腹胀为主症。
久病及肾,疾病进入肝肾虚损期。《诸病源候论·虚劳积聚候》曰:“虚劳之人,阴阳伤损,血气凝涩,不能宣通经络,故积聚于内也。 ”气滞、血瘀、水湿等实邪蕴结,因虚致瘀,乃生积聚。 《金匮翼·痰饮统论》言:“气行即水行,气滞即水滞。”肝脾肾功能失调,水液停于腹中,发为臌胀。 《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云:“其腹胀如水状……腹满者难治。 ”黄疸继发的腹满臌胀,因积聚、水饮、瘀血兼夹难除,治疗难度大。 肝肾虚损期患者以面色黧黑、胁下积块、腹胀大如鼓为主症,且长期卧床,失去自主能力,生存质量差,情志愈发抑郁。
纵观本病,“肝郁脾虚”贯穿疾病始终,并为肝郁期主要病机。 黄疸期肝郁甚则发瘀热阳黄,脾虚甚则成寒湿阴黄,肝郁脾虚兼具则为阴阳黄。 久病及肾,肝脾肾三脏失调则成积聚、臌胀。
2 治法心得
2.1 肝郁期以疏肝理脾、调畅营卫为主
孙教授认为肝郁期治疗需以疏肝理脾、调解营卫为主。方用调和肝脾之四逆散、逍遥散为基础,配伍调畅营卫之品加减。 常用方药:柴胡、当归、白芍、薄荷、桂枝、黄芪、茯苓、白术、鸡内金。 其中当归、白芍养肝血、滋肝体;柴胡、桂枝、薄荷行肝气、助肝用。 薄荷辛凉,入肝经,行肝气,入肺经,黄元御之《玉楸药解》言薄荷“善泻皮毛……治瘾疹瘙痒”,李中梓在《雷公炮制药性解》中言其可“引诸药入营卫”。薄荷配合桂枝宣通肌表,领白芍、当归之润于肌表止痒,再配伍黄芪、白术、茯苓益气健脾,助行卫气。孙教授治疗本病善用鸡内金,《医学衷中参西录·鸡内金解》谓:“鸡内金与白术等分并用,为消化瘀积之药……无论脏腑何处有积,鸡内金皆能消之……加鸡内金于滋补药中,以化其经络之瘀滞而病始可愈。 ”鸡内金可助消食健脾,化积祛瘀,有既病防变之用。 针对瘙痒的治疗,《素问玄机原病式·五运主病》中曰:“微热则痒。 ”若郁生微热,瘙痒甚,可循《内经》之“火郁发之”,可加牡丹皮、栀子、连翘等清发郁热之药;若肝血不足,不荣则痒,则加生地黄、熟地黄、女贞子、墨旱莲助养肝血;若患者纳差、泄泻的脾虚之症为甚,加升麻、党参、茯苓、山药以引元气之升;若胁痛、胀满,加香附、郁金、川芎、厚朴增行气止痛之功;若心烦寐差,加石菖蒲、远志、酸枣仁、柏子仁以安神魂。
2.2 黄疸期首辨阴阳,注重脾胃功能
患者若以黄疸为主症进行就诊, 需先辨阴阳。若患者黄疸色鲜、瘙痒重,孙教授认为此类瘀热引起的阳黄患者需及时运用清热凉血、活血化瘀、利胆退黄的治法,使用经验方赤丹退黄汤加减。 常用方药:赤芍、丹参、茵陈、郁金、枳壳、大黄、豨莶草、葛根、天花粉。黄疸因瘀热而起,故方中重用君药赤芍、丹参,赤芍用量可增至80 g,清热凉血、活血化瘀,清解血分瘀热。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赤芍、丹参中的有效成分具有一定的增强肝脏代谢、保护肝细胞、降低炎症反应、抑制肝胶原纤维合成和沉积、促进胆汁排泄,起到保肝退黄、抗肝纤维化的作用[7-13]。郁金既可凉血活血,配茵陈、地耳草、白花蛇舌草又清热解毒,散瘀退疸为臣。佐以小通草、大黄、枳壳通利化瘀,于大小便中分消瘀热。 瘀热伤阴可出现口干、咽干、目干等症,佐凉润之葛根、天花粉养阴生津。诸药合用,血中瘀能化,热能清,黄疸消,瘙痒因热退而止。若出现发热,偏热胜者,加板蓝根、虎杖、半枝莲等清热解毒;齿衄、鼻衄,皮下现瘀斑等出血倾向者,加生地黄、牡丹皮、水牛角等凉血止血。
若患者发为阴阳黄,肤色介于鲜明与暗黄之间,出现瘙痒重、纳差、乏力、腹胀等症,孙教授常用经验方温阳解毒化瘀方治疗,主于温阳健脾、解毒化瘀,祛湿退黄。 常用方药:附片、赤芍、茵陈、白术、丹参、薏苡仁。 附片大辛大热,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温补脾阳;赤芍味苦微寒,取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之功效,二者寒热并用为君药。 茵陈利胆退黄,为治黄疸之要药;丹参活血化瘀,与茵陈共为臣药,再佐以白术、薏苡仁以燥湿健脾,如此脾阳得运、湿气得泄、瘀热得化。 其中温阳健脾、解毒化瘀法等已列为国家“十一五”“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慢性重型肝炎证候规律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研究”的治则之一[14]。临床中对PBC 黄疸期的患者也具有一定的疗效及指导意义。
若患者发为阴黄,肤色多暗黄,以乏力、纳差、腹胀、泄泻为甚,需温阳化湿退黄。 方用茵陈术附汤加减。整个疾病过程需在辨证论治基础上加附片、白术等温阳健脾类药物干预应对“脾虚”之机。
2.3 肝肾虚损期以滋补肝肾、活血利水、缓消瘀滞为主
孙教授针对具有积聚、臌胀等症的患者常运用滋补肝肾、活血利水、缓消瘀滞之法,方用鳖龙软肝汤合杞菊地黄汤加减。 鳖龙软肝汤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肝纤维化、肝硬化的特色方剂,主要由桃仁、莪术、鳖甲、地龙、茯苓、柴胡、白芍、甘草组成。方中鳖甲色青入肝经,《本草衍句》中言鳖甲可“软肝血之积坚”,其既软坚散瘀,又滋肝肾之阴,是治疗本证之要药;地龙咸寒入肝经,活血通络,配合桃仁、莪术共奏破血祛瘀、消积散聚之功。 现代药理研究显示,鳖甲、莪术可通过抑制炎症反应、阻断转化生长因子信号转导途径、促进肝星状细胞凋亡、抗氧化损伤、抑制肝星状细胞的活化增殖、调控细胞外基质的产生和降解,发挥抗肝纤维化的作用[15-19]。白芍配合杞菊地黄丸中枸杞、熟地黄、山茱萸滋养肝肾之阴,防桃仁、莪术破血过甚;柴胡行气解郁;茯苓配合山药、泽泻益气健脾,与地龙共行活血利水之效;甘草调和诸药。 然滋补碍胃,虫类鳖甲血肉有情之品难化,可加鸡内金、陈皮健脾和胃;若患者腹中如囊裹水,可加大腹皮、猪苓增强利水消臌之效。 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之精不能濡养筋骨,致周身筋骨经脉失荣而痛,可加杜仲、牛膝、菟丝子补肝肾、强筋骨。 盖救病非一日之功,孙教授认为本期用药时间需以“月”为单位,轻量久服,故中药可为丸为散,缓以为功。
3 验案举隅
患者苏某,女,53 岁,2021 年4 月22 日初诊。 诉反复ALT 升高2~3 年, 查肝功能:TBIL 29.1 μmol/L;D-BIL 17.2 μmol/L;ALT 79.2 IU/L;AST 104.4 IU/L;GGT 133 U/L;ALP 144U/L;抗AMA2(+);肝活检结果:中度界板炎症;有肉芽肿形成;考虑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纤维化肝3 级/炎症3 级)。 刻下症:乏力、纳差、皮肤瘙痒,多在四肢,位置不定,长期寐差易醒,舌质淡苔薄,舌下脉络稍迂曲,脉细弦。 体格检查:面色白光白,巩膜无黄染,未见肝掌、蜘蛛痣,肝、脾肋下未触及,腹软,无压痛反跳痛,无移动性浊音。仔细询问病情,患者近年因琐事郁郁寡欢,身心俱疲。西医诊断: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纤维化肝3 级/炎症3 级);中医诊断:积聚,肝郁脾虚证(肝郁期)。治法:疏肝理脾、调畅营卫。处方:逍遥散加减,药用:醋柴胡10 g,白芍15 g,当归15 g,茯苓15 g,白术15 g,薄荷10 g,桂枝10 g,甘草5 g,黄芪15 g,石菖蒲15 g,远志10 g,鸡内金10 g。 水煎服,日1 服,早、晚餐后30 min 温服,共15 服,嘱长期配合熊去氧胆酸口服,200 mg/次,每日3 次;鳖龙软肝片口服,6片/次,每日3 次。
二诊(2021 年5 月10 日):患者诉皮肤仍瘙痒、溲黄、乏力,纳差症减、睡眠质量尚可,大便正常,舌红苔薄黄,舌下脉络稍迂曲,脉弦。 方用“一诊方”去黄芪、桂枝,薄荷用量增至15 g,牡丹皮10 g,栀子10 g。续服10 服。继续配合口服熊去氧胆酸、鳖龙软肝片,服法同前。
三诊(2021 年5 月24 日):复查肝功能 TBIL 23.6 μmol/L;D-BIL 9 μmol/L;ALT 44.8 IU/L;AST 64.4 IU/L;GGT 43 U/L;ALP 114 U/L。 诸症均减,舌红苔薄,舌下脉络稍迂曲,脉弦。 再予“二诊方”去牡丹皮、栀子,加黄芪10 g,续服15 服巩固治疗效果。继续配合口服熊去氧胆酸、鳖龙软肝片,服法同前。患者随访至今,诸症均消,肝功能稳定在正常范围内,肝脏硬度检查10.7~14.4 kPa 之间,病情稳定。
按:患者因七情内伤,情志不遂而起病,初诊时以乏力、纳差、瘙痒、寐差为主症,结合舌脉可辨证为肝郁脾虚证,病情处于肝郁期,结合西医肝活检情况,可辨病为积聚。 情志不遂,肝郁气滞,肝魂动扰,则寐差易醒;脾气虚弱发为纳差、乏力等症;营卫不畅发为瘙痒。方药采用逍遥散加桂枝、黄芪,行疏肝理脾、调畅营卫之效,再配伍石菖蒲、远志安神定志。二诊时患者脾虚已缓、肝魂稍定,但存微热瘙痒,增薄荷用药量宣发微热,牡丹皮、栀子清热泻火。 三诊时患者诸症均减,祛寒凉之牡丹皮、栀子,加黄芪固护脾胃。本案辨治过程,抓住肝郁期患者肝郁脾虚的主要病机,配伍调畅营卫之法,时刻抓住患者病情的寒热变化,灵活加减,病情稳定后注重固护脾胃。 肝活检提示患者存在积聚,长期服用鳖龙软肝片,取缓消瘀滞之功,如此病情稳定,诸症俱消。
4 小结
中医药与熊去氧胆酸合用是目前临床上治疗PBC 的常用方法,但也存在对熊去氧胆酸生化应答不佳的患者,尤其是已经出现肝硬化及肝硬化失代偿者亟须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孙教授在临床上采取中西医结合诊治本病,将其分3 期辨证,强调“肝郁脾虚”基本病机对于本病发生、发展的重要性。治疗上肝郁期主于疏肝理脾、调畅营卫;黄疸期分阳黄、阴黄、阴阳黄而灵活运用清热凉血、解毒化瘀、温阳健脾、祛湿退黄等治法;肝肾虚损期主于滋补肝肾、活血利水、缓消瘀滞。 在疾病各个阶段贯彻既病防变的思想,利用中医药的全局观优势来认识治疗本病,并利用中医药能在多方面、多靶点和多层面对于本病产生积极影响[20],基于临床疗效探索系统、有效的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以解患者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