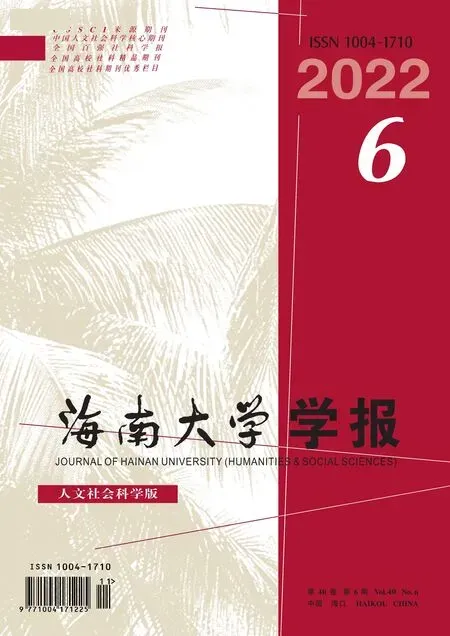王阳明“心气一体”思想论析
黄仕坤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学界不少学者主要从心物二分的角度理解王阳明之“气”,而少有注意气的“心气一体”生生存在意蕴。例如:陈清春将王阳明之“气”分为“物质之气”和“精神之气”[1];方旭东将“同此一气”的“气”,解作“某种精神性的东西”,但又认为王阳明五谷养人等论是主张万物间有“某种统一元素”[2];吴震将王阳明的气化观诠解为“物质实在主义宇宙观”[3];陈立胜将王阳明“良知”释为“精神力量”,并以生物的“一气”为蕴含精神能量的“宇宙质料”[4]。这些诠释或说法,虽然推动了王阳明之“气”的哲学研究,但是在不同程度上,又皆未能完全传达出“气”的“心气一体”存在意蕴。另一方面,上田弘毅指出了王阳明之“气”的“理气一体”,但未能融贯相关文句予以系统阐发,且未论及“气”的心物融通一体之生生存在意蕴[5]420-433;邓克铭认为王阳明“心气合一”而不异质,但亦未贯通相关文句展开讨论,且主要是从实践角度予以分析[6]39-55;杨儒宾论析了陆象山、王阳明等儒哲的“心气一体”思想,并指出由“生理体气”的存在向“心气一体”存在转换的关键是“体证”,但其书中对王阳明之“气”亦未进行系统详细的文本分析[7]325-459。本文之作意在承继上田弘毅、邓克铭和杨儒宾等学者之思,从王阳明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出发,通过相关文句较为系统详细的讨论,明晰王阳明之“气”的“心气一体”生生存在意蕴。
一、心气一体
王阳明主张心即性、性即理,认为万物之理不在心性之外,并将心、性、理收摄于良知。从“心即理”出发,王阳明阐发了“心外无物”之意:良知心性非主客二分的主体,而是生发万物并“与物无对”[8]115的本体,故心物本融通一体而生生。王阳明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8]115,但“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8]119。在此“心物一体”的存在中,不仅人之心、性、理、良知,而且心、性、理、良知发见的眼、耳、鼻、舌、身、意,皆与万物融通一体而生生不已。王阳明的“心即理”与“心外无物”之论,表明“心物一体”的生生存在即是人与万物的真实存在,而既没有现成不变的主体之人,又无现成不变的自然客观之物。正是基于此“万物一体”之意,王阳明阐发了“一气”流行生生的存在思想。
(一)同此一气
王阳明的气化流行思想,其实与“心外无物”的万物一体之意相通。因为心物的融通一体,即呈现为“一气流通”的生生存在。因此,气化流行的实情是“心物一体”的生生存在,所以基于心物二分的思维,将王阳明之“气”理解作精神之气或客观物气等,值得商榷。王阳明曰:
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8]118
天地万物与人本一体化生,并呈现为一气的生生流行,而良知心体即是此一气生生存在得以开显的精窍。如此,也可反过来说,万物存在的实情即是“心气一体”的气化生生流行。因此,心即物即气,三者体用一如,故不可将气与物理解为自然客观的物质存在者。换言之,“同此一气”并非意谓万物皆由亚里士多德式的质料构成,而指万物皆是“心气一体”的生生不息之存在。同理,五谷养人等论并非意指自然客观的事实,而指向万物融通一体呈现的心气一体流行生生存在。相应地,五谷等物与人气息相通的论断,也就并非心物二分的理性认知,而是人对“万物一体”存在的明觉感知。如王阳明曰:
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8]136
良知之“感”是使万物融通为一气化生存在的关键,并使得此气化流行的存在充满光明,而区别于自然客观的物气。这意味着王阳明之“感”,并非主体对客体刺激的反应,而是心与物无对的良知明觉之发见,故“感”不仅是良知明觉之“知”,且能感通万物而一体“生生流行”。王阳明曰:“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8]92良知天理无分于未发已发,故心物体用圆融不二,而此心物圆通存在得以实现的关键即是良知发见之“感”或“知”。从存在结构言,良知天理明觉发见既呈现为意感之知,又呈现为万物的存在;而恰是通过“感”或“知”,良知自知存在的是与非,并使万物融通一气成为光明虚通的生生存在。同时,良知就在感知与物的一体缘生中真实现身,故良知即感知即物生,而且感知与万物是心气一体流行之真实存在的两面。正是基于良知灵明的“感生”性,王阳明将之称作万物一体存在的“发窍之最精处”。因此,“同此一气”“一气流通”及五谷禽兽养人等论,既不同于主体对自然客观世界的知识论断,又不指向心物二分的自然客观存在,而是基于良知明觉即感即物即气的一体存在领会或生命决断,并指向良知自发自知自明的心物融通一体生生的气化存在。①陈立胜论“同此一气”之意区分了两种“一体”:万物由同一生气或质料构成的“一体”,良知与气同步共鸣并由良知的明觉体知呈现的“一体”。其以前者为实在属存在论问题,以后者为意义存在属意义呈现问题,故二者属不同的存在层。不过,“意义”之论实有主体的预设,故会导致存在的分层;而本王阳明“心外无物”之意:良知发见即使万物感通,开显明觉通透而真切笃实的气化存在,故心气一体的存在即真实存在,没有主客之分或意义与实然的区别。参见陈立胜:《王阳明一体之仁的六个面向》,《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12-17页。相较而言,五谷养人等逻辑理性知识,则是人对心物融通一气的存在领会,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
存在的心气一体意味着气不能离心性而生物,而且心性亦不能离实气而悬空。王阳明曰:“‘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8]66从逻辑上说,心气有体用之分而不离,如孟子的性善为本原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则是心性开显而不离的气之用;但从良知的自知自证言,心性与气圆融不二而一时具显,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气即心、性、良知或天理。可见,王阳明转变了“生之谓性”的传统诠释范式:不以材质论物之生与性,而从体用一如角度重新界定“生”,即“生”是本原之“性”的开显,并实化为心气一体之“气”的发用。
另外,虽然王阳明在引文中从人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指点“气”,但“四气”并非限于心灵主体的精神而与物无关。相反,四者是良知心体发见的“意”或“感”,而“意之所在便是物”[8]6,或“感”之所在便是“生”,故从良知的自然发见言,“四气”的本然实情,是心意身物融通一体的流行生生存在。因此,“气”化流行之“生”,必然总是“心物一体”的生生实存;或者万事万物之生,皆是心性本体的开显并呈现为“心气一体”存在的流行。由此,“生”既非单纯的形质之生,又非只是主体精神的发生,且“气”亦无客观质料与主观精神之分;相反,存在之真情实意是心性与万物融通一体的气化流行之“生生”,所以物之生即气之生即心性之生。
(二)良知即气
王阳明将“心气一体”的气化生生存在,又论作良知心体的流行,并进一步诠释为“阴阳”的相生变易,而与《周易》的阴阳观相通。王阳明曰:“《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8]271;“良知即是易”[8]137;“易者,吾心之阴阳动静也”[8]1580。①后两句引文的原文中“易”字有书名号,但按文义应无,故略。这是从体用不二角度认为:《周易》是对心气一体之阴阳消息气化存在的诠释;其中,易道即人的良知心体,并具化为一气化生之阴阳动静。换言之,良知心体发见即呈现为阴静阳动的气化流行存在,而良知心体就在一气的消息变易中显现自身,二者体用一源,所以良知即气。关于此意,王阳明通过诠解周敦颐的阴阳动静观,给出了更详细的论说:
动静者,所遇之时,心之本体固无分于动静也。理无动者也,动即为欲,循理则虽酬酢万变而未尝动也;从欲则虽槁心一念而未尝静也。……太极生生之理,妙用无息,而常体不易。太极之生生,即阴阳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无息者而谓之动,谓之阳之生,非谓动而后生阳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体不易者而谓之静,谓之阴之生,非谓静而后生阴也。……阴阳一气也,一气屈伸而为阴阳;动静一理也,一理隐显而为动静。[8]69-70
“动静”作为“所遇之时”,意味“动静”指向时空中的存在。相对地,“道无方体”[8]23,即良知心体并非时空中的形体存在,故无分于动静或寂然感通。不过,王阳明又将存在生生之“动”,窄化为循私欲的背理之“动”而与循理之“静”相对,以表明万物生化之动循理方是良知天理的自然开显而贞静有常,所以是“动而无动”或“动中有静”[8]70。这良知天理自然发见之真实存在的动静互涵,也就是心物融通一气之生生存在的阴阳相生:阳气之“动”是良知天理之开显而实化生物;阴气之“静”是良知天理开显的万物虚通一体而贞静。同时,前者对应良知明觉发见的即知即生之“感通”,后者对应良知天理开显的万物融通一体之“寂然”。
因此,王阳明又以“妙用无息”和“常体不易”,指点阳气之动与阴气之静。良知或太极作为道,无方无体而无动无静,故其与作为时空存在的阴阳动静并不相同。如此,从逻辑概念言,良知或太极,不仅不直接就是妙用无息的阳生之动,而且与阴静不易之常体也不直接相等同②王阳明于《传习录》曰:“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若说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王阳明全集》,第34页)其又在《答伦彦式》中曰:“心,无动静者也。其静也者,以言其体也;其动也者,以言其用也。……动亦定,静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静,其体也,而复求静根焉,是挠其体也;动,其用也,而惧其易动焉,是废其用也。”(《王阳明全集》,第195页)在《传习录》中,王阳明明确否认将心之动静直接与体用等同,尤其是“静”不直接等同于良知心体,因为心体无分于动静,而动静之分是对时存的区分。其次,《答伦彦式》动静之论看似与《传习录》矛盾,但并非如此。因为“言”字如“谓”字,即“动静”谓述或显见着体用,而非将动静直接等同体用。正因动静为良知定体的体现:“动亦定,静亦定”,而“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王阳明全集》,第18页)。因此王阳明又言静为体,言动为用,反对离开动静别求体用。相反,若动静不循理则皆为私欲,即纯为妄动而无静。因此,虽然阴静并非本体,但阴静对应的万物之“一体”体现着“理”之“一”。。不过,从体用一如的角度言,“妙用无息”的阳气之动和“常体不易”的阴气之静,皆是良知或太极的体现,而后者也只有开显为阴静阳动之相生变易才能显现自身。其中,阳气之动的“妙用无息”,强调良知明觉生发的不测与无限;阴气之静的“常体不易”,意指良知开显之万物的“虚通一体”,即万物本以“虚通一体”的方式存在,故虽生生不息而常体不易。
其次,王阳明又把“妙用无息”的阳气伸发之动称为“神”,将虚寂融通而“常体不易”的阴气凝聚之“静”称作“精”,并明确区分良知天理的“精一”之体,与“精神”相生的气化流行之用。例如王阳明论曰: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气言。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8]67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阴根阳,阳根阴,亦非有二也。[8]68
气凝聚所成之“精”是“精神”之“精”,而非“精一”之“精”,故“精一”之“理”与“精神”之“气”,虽体用一如但有分。因此,“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8]21之“精”“气”“神”,皆不直接指向良知心体,而意指着太极心体的生生之用。如王阳明论“惟精惟一”曰:“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8]244具体而言,太极或良知天理开显而生生,即呈现为心物融通一气的阴屈之精与阳伸之神的消息:气之屈,意指万物存在收摄贞定于良知天理,呈现为心物一体的贞静凝成,故为阴精;气之伸,意指万物本良知天理真实开显,呈现为心物一体之存在的生生,故为阳神。这意味着,阴精之静,是就心物存在地凝成一体而贞定言;阳神之动,是就心物一体之存在的实化创生不测言;而“精”与“神”的和合即呈现为心物融通一气的屈伸聚散或虚实的相生流行。因此,“心气一体”的阴阳相生流行的存在,没有心物二分的形象方所可被人把捉,故只有通过默识体证方能冥契。
接着,王阳明又将气之屈、静、精称为良知天理之“隐”,而将气之伸、动、神称作良知天理之“显”。“心物一体”存在的实化生生即是良知天理之开显,但“心物一体”存在的生生又收摄贞定于天理,故虚静贞正而为阴“精”。天理之显隐与存在之阴阳的对应,表明理之显隐如同存在之精神或动静,皆指向良知天理自然发见的状态,是心气一体之存在的两面。然而,王阳明为何将存在之阴静称作理之隐呢?这其实是从常人的视角发论。具体而言,常人通常只能看见天理实化创生万物之动,并以之为良知的开显,但少有能证悟或通达万物生动缘起的心物虚通一体之贞静,即存在之阴静于常人往往处于蔽隐不显状态,故可将阴之静称作良知天理之隐。相对地,圣人虽未尝无动静,但无间于一体生生存在之动静,即无分于天理的显隐,而只是良知天理的自然发见流行。因此,圣人之存在即有限而无限,如《庄子·田子方》言“目击而道存”[9]703。
最后,阴精阳神作为道化存在的一体两面,并非凝固不变的对立双方,而是不断地相互给出:万物澄明实化生生之阳动,须根于万物虚通一体贞正之阴精,方能不息地实化创生出来;而万物一体虚通之阴精,亦须根阳以实,方得以成为真切笃实之精,否则即是虚而不能实。至虚至实,至实至虚,阴虚阳实互根相生,方使良知天理真实不息地开显为心气一体的生生存在。总而言之,气之流行为“动”为“阳”为“神”,而存在的凝聚一体或虚通一气则为“静”为“阴”为“精”;同时,存在的“一体”之“静”或“一气”之“精”,是“理一”之贞与定的体现,而存在的“生生”之“神”或“流行”之“动”,则为“一理”生生的显现。
(三)精粗一气
王阳明在《稽山承语》中对道、心、性、理、良知、诚、中、极,与气、精、神、隐、显、易等的意蕴和存在关系进行了概括,并基于良知、心、性、理与精、气、神等的体用关系,将“心气一体”的生生存在区分“精”与“粗”。其意在于使人明真实存在得以开显的至精至明之良知心体,进而实做功夫以复归精粗一体的气化生生存在。王阳明曰:
道无形体,万象皆其形体;道无显晦,人所见有显晦。以形体而言,天地一物也;以显晦言,人心其机也。所谓心即理也者,以其充塞氤氲而言谓之气,以其脉络分明而言谓之理,以其流行赋畀而言谓之命,以其禀受一定而言谓之性,以其物无不由而言谓之道,以其妙用不测而言谓之神,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以其主宰而言谓之心,以其无妄而言谓之诚,以其无所倚着而言谓之中,以其无物可加而言谓之极,以其屈伸消息往来而言谓之易,其实则一而已。今夫茫茫堪舆,苍然隤然,其气之最粗者欤!稍精则为日月、星宿、风雨、山川,又稍精则为雷电、鬼怪、草木、花卉,又精而为鸟兽、鱼鳖、昆虫之属;至精而为人,至灵至明而为心。故无万象则无天地,无吾心则无万象矣。故万象者,吾心之所为也;天地者,万象之所为也。天地万象,吾心之糟粕也。要其极致,乃见天地无心,而人为之心。心失其正,则吾亦万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谓之人。[8]1608
“道”无形无象,自然涌现生成万物一体之存在以显现自身,故道无显晦而万化一体。然而,人常由于被物欲晦蔽而心物二分,故不能感知天理自然,造成作为道的天理蔽晦不显。这与前文“理”之“隐”的意涵相呼应。相对地,若人心能感通道则能使道真实地显现自身,并表现为良知天理的自然发见,开显万物一体而精明通透且真切笃实的气化生生存在。因此,心并非主体之心且万物之理亦不在心外;而是心即理且无间于万物或体用。基于此,王阳明就心物一体存在的虚通之阴与实化之阳的氤氲无滞谓之“气”;就心物一体生生存在的条理分明谓之“理”;就心物一体存在流行而贞成赋生谓之“命”;就心物一体存在中万物生生所禀受的定理谓之“性”;就心物一体存在中万物得以生生实化的本根谓之“道”;就心物一体存在之生生的神妙不测谓之“神”;就心物一体存在中万物贞止于天理而凝聚一体谓之“精”;就心物一体生生存在的灵明主宰谓之“心”;就心物一体存在的真切笃实而无妄谓之“诚”;就心物一体存在的不偏不倚谓之“中”;就心物一体存在地贯通天人而至真至善谓之“极”;就心物一体存在的屈伸消息与往来相生谓之“易”。这表明,“气”“理”“命”“性”“道”“神”“精”“心”“诚”“中”“极”“易”等皆本是体用一如的,而诸名之异缘自从不同角度对万物融通的心气一体真实存在进行的不同诠解。
因此,王阳明“粗”“精”“至精”“至灵”之论,并非如物活论或有机哲学般,将万物划分为不同的生命等级,而是从体用角度将万物融通的心气一体存在区分精粗。这还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证明。首先,“故……无吾心则无万象”中的“故”字表明:此“心象一体”之意是由前文的精粗之论导出的结论,并意指万象之粗是作为“精一”的至明心体的发见,故精粗犹如体用,一体不分。相反,如果“万象”之前的文句,论述的是自然有机物气的精细之别,那么难以得出心物(象)一体之论。其次,王阳明在文段开头将万物比喻为道之形体,是以心身关系作譬喻。同样,其在文末亦是将日月、星辰、花草、树木等“天地万象”,认作心的形(身)体而称为“糟粕”或“粗”;并且将良知心体诠作万物存在得以发窍的“灵明”,故心是“极致”,而为比人身更精的真正的“至精”或“精一”。如此,存在之“精粗”犹如“心身”,是王阳明基于道与物的体用关系所发之论,故其认为后者须由前者之“为”方得以开显。
再者,心正为人而心不正则为万象之论,意指:比“万象”更精之“人”,并非从自然物气而论之人,而是能正心以使良知真实发见的心意身物一体之“在”;而只有当人不能正心以致良知,才成为不正的万象,即沉沦为对象化之物而与自然客观物象相类。此论断表明,王阳明亦据良知真实开显的程度,区分存在的精粗:心意不正的对象化存在物为粗,而正心诚意的心气一体存在则为精。不过,相对万物得以开显的良知灵明之精一,无论良知自然发见的存在,还是其被遮蔽而开显的对象物,则皆属粗。最后,王阳明继上引文段曰:“所谓心者,非今一团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灵至明、能作能知者也”[8]1608-1609。“心”不是自然客观物气形成的血肉之心,而是万物存在得以发窍的灵明,所以上引文段所述心与万物的精粗,就并非从自然有机物气的精细发论。由此可见,王阳明是基于体用关系,区分“心气一体”存在的精粗,而与从物质到精神的有机生命的演化序列不同:良知心性是真正的至精至明之体,而万物存在则是心体发用之粗。
不过,王阳明精粗之论,其实亦是从常人的理性视角发论,因为圣人与道同体而无精粗体用之别。王阳明曰:“道无精粗,人之所见有精粗。”[8]22精粗或体用皆是人逻辑理性区分的产物。同样,日月、星辰等万物作为气之“粗”,与人作为气之“精”,亦是王阳明从常人的逻辑理性之“见”进行的区分。然而,王阳明通过将良知灵明诠释为存在的至明“精一”,把常人对气之精粗的理解,收摄入体用的诠释范式中,使气从常人理解的自然物气,转变成了心物融通一体的生生之气。因为,王阳明区分存在的精粗,本意不在突出存在的分别,而旨在为常人指明真实存在得以开显的精窍,使其知功夫下手处而实做功夫,以复显精粗一体而心气同流地生生存在。如朱熹亦言,若人做得功夫纯熟,待“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焉,则亦有以知其浑然一致,而果无内外精粗之可言矣”[10]528。真实存在本无精粗内外之别而浑然一体,但因人私欲之患而分化、蔽隐,故做得功夫方可使良知自然发见;能如此者其心与万物一体生生,皆是至精至明地存在而没有精粗体用之别。因此,不可将王阳明所论气之精粗,理解为自然客观物气的精粗。
综上,王阳明之“气”论通于王阳明“心外无物”之思,故“气”的实情指心意身物融通一体而虚实生生的存在,并呈现为“心气一体”存在的流行。相应地,“同此一气”的论断根源于良知灵明的感通自知,而非心物二分的知识判断。此外,王阳明承继《周易》之旨,将心气一体生生存在,诠释为良知天理流行显现的动静、阴阳、精神、屈伸等的相生变易:“心气一体”存在的实化生生,是良知伸发而神妙不测的阳神之感动;“心气一体”存在的贞正一体,是良知伸发而收摄凝成贞定的阴精之虚静。最后,王阳明基于体用关系将心气一体存在区分精粗:良知心体是万物存在得以开显的至灵至明之精窍;万物或万物融通一体的气化存在则是良知发见之用而为粗。王阳明意在通过存在的精粗之分,指明真实存在发窍之处,以使人做正心诚意的功夫而通达无人己、物我之分的融通一气之生生存在。①“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王阳明全集》,第60页。
二、心气的分裂与复合
习染私欲致使良知不能自然发见,将导致心气二分而使人陷于心物对立的有限存在之域,即人从心气一体清明和善的气化生生存在,堕落为心气断裂而清浊驳杂的恶气存在。因此,如果人要回复心气一体的本然存在,就须时刻切实地做正心、诚意、修身、格物的知行合一功夫以致良知;待人的私欲杂质被剥落而良知得以自然发见,恶气存在即转归善气存在,或者生理私气将重新贯通天地万物之气,成为心气一体生生而无限的气化存在。因此,王阳明认为善恶本是一物,即恶气存在与善气存在,是心物一体存在的不同表现,二者转换的枢机在于能否致良知以去蔽。
(一)心气二分
心性与气虽本一体,但因后天之习的不同,造成心气或离或合,并表现为气的清浊善恶。王阳明曰:“惟性善则同耳。人生初时,善原是同的。但刚的习于善则为刚善,习于恶则为刚恶;柔的习于善则为柔善,习于恶则为柔恶,便日相远了。”[8]135人禀气生而皆有性善在其中,所以性气原本皆善而纯粹。然而,气之阴阳刚柔随后天习行的不同,而各有善恶之分或清浊之别。例如人以刚猛处物而伤物或以阴柔接物而无实,皆是良知被习染私欲所弊而发不得中,故气之动无所贞止而伤物成恶。因此,王阳明曰:“性一而已,仁、义、礼、智,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8]75耳之聪、目之明、心之思与知等,皆是良知心体之发见,故是良知流行之气而为性得以实化之质。人的仁性本同一而至善,所以性发见实化之质与情,亦原无不粹而和畅。然而,常人的气质因被后天习气所染而往不同的方向发展,故常是清浊善恶相驳杂而不复纯然之善。这具体又表现为耳之不聪、目之不明、心之思与知不能智而明等等,结果是四者不仅难以通达万物本性,反而常导致心性的蔽隐而使七情发动过与不及,并最终表现为私欲和客气两大病痛或症状。
私欲与客气两痛作为一病,意味着二者互为表里,是心气二分存在的两面:恰是私欲遮蔽心性导致心气被阻断而呈现为客气。因此,邓艾民将“客气”注解为“受外界影响而生之骄傲、名誉、情欲等”[11]139,是正确的,但仍有可补充的空间。《说文》解“客”为“寄”,段玉裁注之曰“自此托彼曰客”[12]597,故“客气”有寄外而不能自主之意。将此再结合王阳明“心物一体”意旨观之,“客气”应指人不以心主而随生理私欲产生的逐外之气或存在。因此,客气与心气一体的纯粹之气相对,前者是后者因私欲浊化或异化的后果。
心性因私欲遮蔽造成的气之分与浊,并不限于主体之内,而是延伸至存在的整体。因为,作为万物本体之心性的遮蔽,将导致人与万物,皆从原初万物一体的无限性存在,异化为心物二分的有限物存在,并表现为流通天地的心气一体的清明之气,被分裂、浊化为对立的精神之气、生理客气与自然物气等。因此,私欲与客气的产生,不仅表征着人的沉沦,而且喻示着万物存在的对象化,从而使天地人及万物的存在皆失落生机。以此之故,王阳明将私欲与客气,认作良知心性以及真实存在之弊病的症结或症候,是一病之两面。
同时,私欲造成的心气二分存在,作为良知天理与万物生机的蔽隐不显,也就是万物的存在因弊病而不善,所以王阳明又将此心气分立的存在称作“恶”:
夫恶念者,习气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为习气所汩者,由于志之不立也。[8]1031
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8]32
“恶念”由习染产生,故可称作“习气”。本“心外无物”之意,意念之生必有其物。因此,“恶念”作为后天习染造成的习气或私欲客气,并非只是主体的精神活动,而关联着整个没有良知主宰的纯恃私欲发生的存在,故可称之为“恶气存在”。同理,良知自然开显为善念,即呈现真实无妄而精明通透的心物融通一气的生生存在,所以王阳明从体用一如角度称之作“本性”,而亦可谓之作“善气存在”。将二者相较可明:良知心性是否被习染私欲遮蔽,将决定人的整个存在之域的善恶。
私欲对良知心性的遮蔽,首先表现为对良知发见的纯善志意的汩没,从而使之不能诚而立,导致气的生生运化失去主宰。王阳明曰:“夫志,气之帅也,……志不立则气昏。”[8]277志意不能得以诚而立,将使气之生动失去主宰而无所贞定,结果是气之动茫然无收而沉沦为昏恶之气:“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8]33。因此,私欲恶气与志之不立或意之不诚,实为心气二分存在的两面。相对地,若心之志意得以诚而立,那么气将重新获得主宰以循理化生而贯通天人。换言之,良知心体发动为意,意诚即志立,志立则气之伸发生物得以凝摄贞定于天理而虚静不奔忙,故是私欲恶气(客气)被消解,而转归清明纯善的万物融通一体的气化存在。①“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听一毫客气之动,只责此志不立,即客气便消除。”《王阳明全集》,第277页。因此,“‘持其志’则养气在其中,‘无暴其气’则亦持其志矣”[8]24。志立意诚之循理与气养之善,是物我融通之真实存在的一体两面。
王阳明将心气二分的恶气存在归因私欲,是对宋代理学天理与人欲对立思想的承续与发展。“无善无恶”的“至善”,原是就天理或心性而言:“至善者性也”[8]28。不过,在上引相关文段中,王阳明不仅以“理”论“无善无恶”,而且从圣人顺天理之行或存在论之。这缘于圣人的存在,是心物无间而体用精粗浑然一体的生生存在,故虽即好恶而无好无恶或无善无恶。因此,“心气一体”的气化存在的纯然至善,并非主体的日常伦理道德,而是良知天理与万物一体的生生本身。②吴震诠释“无善无恶”言:“‘无善无恶’,不是指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性讨论”,而指良知心体的本然状态,且是“‘人伦之至’的圣人境界”。参见吴震:《〈传习录〉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页。另一方面,人的存在“若着了一分意思”[8]32,即是与物二分的主体因私欲在心而“动气”,或“思而外于良知”而“暴气”[8]209,导致昏恶之气的存在。因此,相对于循理之养气,“暴气”或“动气”与“私欲”,是心气二分存在的两面。同时,就万事万物因“着意”皆将导向“恶”或“恶气”的存在而言,王阳明之“恶”亦并不限于日常伦理道德之域,而指向心物对立或心气分裂的存在。
由此再回观上引文段“理之静”与“气之动”之言,可明二者实为王阳明基于理与欲的对立所发之论,而与前文“理静”与“动欲”之意相应。③董平认为“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与四句教“有善有恶意之动”相通,而“动于气”则纯属“恶”,故二者之意不同。(参见董平:《论王阳明的四句教》,《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9年第2期,第15-24页。)不少学者亦持相似观点。不过,从文段语境看,王阳明此处明显将理气或理欲对举。上田弘毅亦持此看法。(参见小野泽精一等编:《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与人的观念的发展》,第422页。)因此,“气之动”与四句教“意之动”不同,而与“动于气”之意相通,指向不循理的“私意”之动。然而,气之动而有善恶之意却与王龙溪对意动而有善恶的解释相呼应:“若有善有恶,则意动于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参见王畿:《王畿集》,吴震,编辑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因此,“有善有恶气之动”应指“动于气则有善有恶”,即好恶皆不循理而从“躯壳起念”[8]31,所以王阳明认为,这些好恶或善恶皆是“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8]32。此心已不是本然之心,而是随身体的生理私气而动之习心,故此习心之好恶即气动而生之好恶。这意味着理气或心气的二分,如同头脑与躯壳的分裂:顺理而动是依作为存在之头脑的良知起念生存而无善无恶;恃气而动是依从无所主宰的作为生理私气的躯壳起念生行,故好恶在己而有对待之善恶。因此,王阳明将气动而有的善恶皆归入恶的范畴与循理之至善区别,并将前者归为“私意”,以后者为“诚意”[8]32。④陈来对“着意”导致对待善恶或“着意”将造成良知发用滞着之意,皆有深入讨论。(参见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30-240页。)杨国荣亦认为“着意”是执着,会使善恶沦落到习气中。参见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173页。需要指出的是,王阳明“私意”之恶与“诚意”之善,皆关联着物的存在,即善恶总是存在的善恶,故善恶之实情分别指向:心物融通一气的善气存在与心物相分而心气隔断的恶气存在。
另外,恶气存在因私欲习染蒙蔽心性产生,表明善恶在心而不在物或气,即物或气原无清浊善恶之别,而本是心气一体流行生生的和善存在。因为,人心与物本是一体,所以“人之生理,本自和畅,本无不乐,但为客气物欲搅此和畅之气,始有间断不乐。”[8]207良知天理自然流行生发万物一体之存在,所以人的生理并非只是形气,而是良知与物一体同流的气化生生,故晶莹明澈而和畅并有大美至乐。然而,这心物融通的气化存在,将会因私欲之蔽而被截断分化。因此,心气一体的善气存在与心气二分的客气或恶气存在,只是良知心体是否有私欲搅扰或遮蔽的区别而并不决然异质。王阳明论之曰:“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故善恶只是一物。”[8]107至善心体因私欲遮蔽发而不中之“恶”,正是心体发动而“着意”之“恶”,而指向心气或理气断裂二分的恶气存在,为良知自然发见通物一气而和善生生之存在的反面。可见,善恶之气的存在转变的枢机在于能否去蔽以致知①“既去恶念,便是善念,便复心之本体矣。譬如日光,被云来遮蔽,云去,光已复矣。”《王阳明全集》,第109页。。
(二)致良知与心气合一
习染导致气与心分离而浊化、分化、异化,并症结于私欲的背后,其实是致良知的失败。换言之,无论心志之不立、意之不诚及物之不格,还是恶或恶气的产生,皆是人因私欲“客气为患,不肯实致其良知”[8]199,或者说是知行“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8]4。因为私欲习气对正心、诚意、修身、格物等任何致良知功夫的中断,皆将导致良知不能自然发见流行,而使“心气一体”之存在断裂为“心气二分”主客对立的存在。因此,心气的分裂与复合或者善气与恶气之间转变的枢机,是人能否时刻切实地致良知以去弊病。
气之清浊的实情,是后天习染私欲造成的对心性遮蔽的深浅或厚薄,故只要去蔽以使良知透显,则气自然清明和善。例如王阳明曰:“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8]74良知莹彻便是良知明觉自然发见,显现为真诚恻坦不已的心气一体之气化流行,而使良知自然朗现以及气由驳杂转变为清明的枢机,则是正心、诚意、修身、格物或知行合一的致良知功夫。因此,王阳明曰:“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及其成功则一”[8]30-31。现实中普通人的气质常是清浊驳杂的,而唯有圣人得清明之气,即其良知明觉时刻感通天地气息而自然发见流行,故是“生知安行”。相对地,即使气质美者也未达清明之气,只是渣滓少而容易明悟心气一体之存在,故仍须实作“学知利行”的功夫。待中下之人能“知行合一”,则与圣人无异。
王阳明的上智下愚并非智力之别,而是气之清浊或障蔽深浅之分,所以其回答薛侃上智下愚为什么不能移之问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8]34。即使是生知安行的圣人也有智力才能的差别,故上智与下愚转变的关键不在智力的“移”,而是人否能使其心发动纯乎天理,王阳明在“生知安行”的前文论曰:“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8]30由此而言,陈清春将才力的高低与气之清浊合论[1],似忽略了二者的区别:才力是智力才能,区别于良知天理明觉之“智”,而气的清浊则指良知发见是否有私欲之蔽。因此,王阳明强调人应在致知去蔽上用功而不是致力于追求知识才能的增长:“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8]31。
不过,才力作为性之“分两”,喻指其关乎心性的发见实化。王阳明言:“气质犹器也,性犹水也。均之水也,有得一缸者,得一桶者,有得一甕者,局于器也。气质有清浊、厚薄、强弱之不同,然其为性则一也。能扩而充之,器不能拘矣。”[13]243气的清浊、厚薄、强弱、才力等,虽皆会局限心性,但亦是心性得以实化之质,故无碍诸气与心性不分而皆可从体用不二角度称作性。因此,人若能扩充良知心性,那么不仅气质不能拘之,而且气亦会从有限的生理之“器”,转变为与心性一体流行、充周万物的生生之“气”,实现人的参赞化育之功。如是观之,气质之清浊、善恶、强弱及才力高低等等,皆非自然客观而凝固不变之物,而诸气转变或发展的枢机则皆在于是否能知行合一以致良知②“人要随才成就,才是其所能为。如夔之乐,稷之种,是他资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王阳明全集》,第23页。。
从此“知行合一”功夫与真实存在的关系可明:“知”与“行”是“心气一体”生生存在的两面。这本王阳明“心外无物”之意亦可得解。王阳明曰:“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8]75;“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8]222。“知”与“行”,是良知心体自然发见之良能或良用。同时,从“心物一体”观之,良知自然发见为“知”,其知物即感物,使万物开显为融通一体而精明通透的生生存在;良知发见为意念及视听言动等身行,而意念、身行作为良知心体之流行,即是生发万物一体而真切笃实地生生存在。③关于“知行”的存在意涵,参见黄仕坤:《王阳明“知行合一”新论——基于心物一体存在视域的分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8-25页。因此,“知行”皆指向良知流行的“生生”,而并非只是日常伦理道德功夫,只是二者称谓角度不同:“知”强调心气一体存在的纯粹精明;“行”强调心气一体存在的真实化生。相应地,“气”则兼具“知行”,而突显着心物融通存在的一体之精和生生之神,并呈现为阴虚阳实的变易流行。以此之故,“心气一体”存在的复显,须切实地做“知行合一”的功夫。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功夫,又具体落实于正心、诚意、修身、格物等致良知功夫。或者说,每一个功夫,皆须兼及正心、诚意、修身、格物四者,方是真正的知行合一或致良知功夫。例如王阳明曰:“言‘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则必兼举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8]53因此,致知与格物等致良知功夫,实际上是一个功夫系列,故不只是诚意或立志就能实现,还须真正地实现物之格。然而,人的有限与物的无限,或者说心物一体缘生之域的无限性,决定了格物是一个无限过程,即正心、诚意、修身、格物等致良知功夫需要人一生去实现,而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王阳明曰:
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圣人到位天地,育万物,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后儒不明格物之说,见圣人无不知、无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时讲求得尽,岂有此理![8]15-16
“婴儿”之喻,据陈荣捷之注,源出于《老子·第十章》“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并与王阳明念念存天理而“结圣胎”之论相通。[13]40因此,“纯气”并非以物质界定的先天之气,而喻指着未显发、分化的性气一体之纯善本原,故王阳明称作“未发之中”。然而,人初生时的性气一体之纯善,却仅为渊泉而并未自觉且充盈,故须在整个人生历程的生存中切实地持之养之,待其精气日强方能充沛天地而参赞化育。这意味着,王阳明的“纯气”“精气日足”及“啼”“笑”“行”“持”等语,皆是从性气一体圆融的角度立论,而指向人心气一体之“生—存”的展开:包括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在内的整个人之存在,既是致良知之“学”,又是本良知心体生养心气一体存在的致知与格物。以此而观,引文之“知识”,并非心物二分的知识,而是对良知之“知”,且“行”亦非心物二分的人之行,而是本良知的创生之“行”,故圣人无不知无不能。①“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王阳明全集》,第106页。相对地,若从自然气质论诠释这些话语,则与从未发之中上养来等语相矛盾,而无法使后者得到诠解。
其实,王阳明此段气论与本节前文,皆意在阐释同一个道理:心物一体的气化与致知格物等功夫,是一体的两面,所以致知即养气,养气须格物,物格则知至,知至则心、意、身、物融通一体而气化生生,使人与万物真实地存在出来。②邓艾民将此段之论与《王阳明全集·紫阳书院集序》一段合观,略录如下:“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耳矣。”人的日用行为皆是本心而有之学,是致知格物开显的良知之流行,故“精气日足”实为推致良知而展现的“心气一体”之存在。(参见邓艾民:《传习录注疏》,第33页。)相似地,梁启超亦引施氏语注释言:“盖人自堕胎后无息不与物接,此物物之,则在吾心。即此是未发之中,乃所谓天理也。君子只是戒慎恐惧,一心在天理,任他耳听目视手持足行,定盘星一毫不走,方是本原之学。”梁启超:《传习录集评》,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换言之,人若能常推致良知天理于事事物物,便是使良知“日夜滋长,生气日完”[8]36,而待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而正,便是性气养成达至心气一体的生生存在,与圣人无二。如王阳明曰:“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8]127致良知即复其气,气复则清明感通,化转私欲客气为心气一体的纯善之气,达至圣人的存在世界。由此而言,将此段之“气”,单纯理解为自然客观之气质,是值得商榷的。
另外,正心、诚意、修身、格物而无邪思欲望开显的如夜气般清明的圣人之在,也就是良知自然发见与天地万物一体同流的生生存在。如《传习录》记曰:
问:“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昼知夜的。”……“夜来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无睹闻,众窍俱翕,此即良知收敛凝一时。天地既开,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赌闻,众窍俱辟,此即是良知妙用发生时。可见人心与天地一体,故‘上下与天地同流’。”[8]116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意指良知知昼知夜,而良知之知昼即是开显昼,知夜即是开显夜。因为在心物融通的存在中,并无在昼夜之外的主体之人去知作为对象的昼夜,而只是良知与昼夜一体生生,并具体表现为良知的夜来宴息与昼时生僻。不过,这种说法是王阳明从逻辑的区分所发之论,实际上良知的翕辟不分昼夜。因为相对于昼夜作为“动静之时”,良知本体无分于昼夜或动静,故其在万化生动中未尝不寂静,而在寂然之静中亦未尝不感通,所以“一叫便应”[8]116。当然,王阳明特地区分昼夜以论良知之翕辟,意在强调:良知随“时”发用与收摄凝聚,而不因私意滞着,方能实现天地人的一体同流。
与此不同,王阳明有时也将良知随昼夜生发之意,专就夜气而论:“良知在‘夜气’发的,方是本体,以其无物欲之杂也。学者要使事物纷扰之时,常如‘夜气’一般,就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8]116-117。王阳明并非指良知在夜晚的发用,才是心体发见流行的本然,而是意在表明:良知自然发见而开显的无私欲夹杂的存在,就是如夜气般清明的存在,并且良知自然发见而清明地“存在”,即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这意味着良知之知昼与知夜,皆是“知”或“生”同一个“心气一体”的清明气化存在,并具化为良知与天地万物的一体消息盈虚:天地在夜晚翕合之时,良知即自然宴息;天地在白昼开生之时,良知天理明觉即发用创生万物而不息。常人若能如此,就能成为圣人,而开显清明如夜气般的精明通透且真切笃实的存在;但若被私欲烦扰,则与天地良知相隔,所以即使在夜晚无声之时,其气亦昏而不明,而或沦为昏睡之存在,或思不能精明通透,止于迷惘无实的妄气之在①王阳明认为“闲思杂虑”亦为私欲,因为皆从私欲而起。参见《王阳明全集》,第24页。。
总之,心气二分的昏恶存在,缘于习染私欲导致良知不能自然开显。就功夫言,这首先缘于心之志意不能成立,而导致格物等致良知功夫失败。因此,心气一体纯善气化存在与心气二分恶气存在转变的枢机,在于人是否能做得正心、诚意、修身、格物的知行合一之致良知功夫。同时,人若能时刻知行合一而致得良知,则不必持守孟子为常人指点良知萌动处的“夜气”之论:“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说‘夜气’”[8]73。因为常能知行合一而致良知之人,其良知心体自然流行,使事事物物皆是心气一体而清明通透且真切笃实的生生存在,所以夜气或一气同流翕辟之意,已不待说而自显自明②“‘夜气’,是就常人说。学者能用功,则日间有事无事,皆是此气翕聚发生处。圣人则不消说夜气。”《王阳明全集》,第19页。。由此而观,杨儒宾强调“体知”对转化不同气之存在的作用,涉及了存在转生的“知”之面向,但对生物之“行”的面向关注有所不足。
三、结语
王阳明由“心即理”论“心外无物”,又从心物一体论“一气流通”之意。因此,王阳明的气论与心物一体思想相通:心物融通一体呈现为“心气一体”的生生存在,并具化为阴阳、精神、动静、屈伸的消息变易。其中,“气”之阳、神、动、伸,指良知天理开显心物一体的存在并显现为精明通透之生生;“气”之阴、精、静、屈,指良知天理开显的万物存在凝成笃实而虚寂一体。因此,无论心、性、道、理、诚、良知,还是气、精、神、动、静、屈、伸、易等,皆是对心气一体生生存在不同面向的诠解。由此,将王阳明之“气”区分为主体精神与客观物气,或界定为精神与物质的统一,皆未能完全传达“心气一体”之气作为精粗内外浑然一体之生生存在的意蕴。因为,心气一体之“气”是:即心无心,即意无意,即身无身,即物无物的心意身物感通一体而明觉生生之存在。
然而,人生本然的心气一体纯粹和善的气化存在,会因后天习染导向心气二分的清浊驳杂之恶气存在,并症结为私欲、客气两大病痛。私欲与客气或恶气互为表里,是导致心气隔断的真正原因。心气二分的清浊驳杂之恶气存在的产生,正是首先缘于私欲遮蔽良知自然发见的志意,进而导致格物致知的失败,结果造成心气一体存在的分裂、异化。因此,气的清浊或善恶,喻指着私欲障蔽心性之深浅,而既非客观不变之物,又并不决然异质。其中的转变枢机,在于人能否时刻切实地,做得正心、诚意、修身、格物的知行合一之致良知功夫以去蔽。因为,“知”与“行”原是“心气一体”生生存在的两面:“知”是良知明觉开显的心物一体存在之精明通透;“行”是良知开显的万物一体真切笃实存在之生生。因此,良知、气与致良知一体不分:功夫即气,气即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