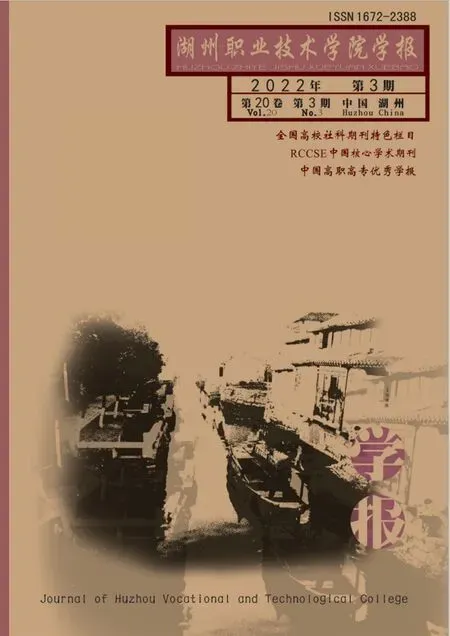论波德莱尔的艺术批评原则
黄 迈 , 禹志云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年)是法国19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同时也被美国文学批评家韦勒克(René Wellek)评价为19世纪最伟大的评论家之一。他将诗人的才华与艺术家的敏锐洞察力运用于艺术批评之中,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在浪漫主义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审美现代性的维度,为现代艺术批评奠定了美学基础。
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波德莱尔给“现代性”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19这一定义充满了辩证的哲理,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肯定了美和艺术既包含暂时的、相对的、变化的因素,又有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因素。正如波德莱尔自己所言:“美永远是、必然是一种双重的构成……构成美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种,或是兼容并蓄……没有它,第一种成分将是不能消化和不能品评的,将不能为人性所接受和吸收。”[1]4-5这段话也是在告诉我们:永恒的、绝对的美必须由暂时的、相对的、时代性的美来表现,当下的过渡性与偶然性中包含着永恒和不变。正是基于此,波德莱尔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美,这种时代性的美能体现出永恒的美。所以,艺术要“捕捉审美现代性,极力发掘现代社会特有的现实的美、瞬间的美、独特的美”[2]52,要通过现代性的美来发掘永恒的美。这便是波德莱尔对于审美现代性的理解(1)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波德莱尔虽然主张表现现代社会的美,但并没有全盘肯定社会的现代化,相反,他还对现代化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持反思与批判的态度。。围绕这一理解,他提出了自己的艺术批评理论,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批评原则,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艺术批评实践之中。
一、波德莱尔艺术批评的党派性原则
在批评立场与批评标准方面,波德莱尔秉持着党派性原则。在19世纪的法国评论界,浪漫派在摆脱了古典主义推崇的客观法则(2)例如三一律、人物形象塑造类型化、理性克制情欲等艺术创作法则。之后,不再相信艺术批评有一个永恒的客观标准。他们转向了另一个极端,为追求“公正”采用折中主义的评论,使艺术批评变为没有任何共同标准的争论,陷入了主观主义的泥沼。
波德莱尔和浪漫派一样,不相信艺术批评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客观标准,但他也绝不认为艺术批评是没有任何标准的主观争论。他觉得艺术批评的立场和标准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一个时代可以有一个时代的临时的艺术批评标准。这一观点正是来自他对于审美现代性的理解,既然艺术的一半是永恒和不变,一半是变化和短暂,艺术是永恒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那么艺术批评就自然可以有临时的、相对的标准。沈语冰教授在《20世纪艺术批评》的导论中探讨波德莱尔的批评理论时就指出:波德莱尔认为,“批评已经不再有一种永远的合理性基础,却可以有一种临时的合理性基础。”[3]28
也就是说,波德莱尔认为,艺术批评没有永恒的批评标准,但不能没有批评立场和标准。他在《批评有什么用?》一文中指出:“公正的批评,是有其存在理由的批评,应该是有所偏袒的,富于激情的,带有政治性的。也就是说,这种批评是根据一种排他性的观点做出的,而这种观点又能打开最广阔的视野。”[4]103这段话,集中体现了波德莱尔艺术批评的党派性原则。这一原则,具体体现在排他性和政治性两个方面。
(一)排他性——艺术批评要有所侧重
波德莱尔艺术批评的党派性原则,首先体现为鲜明的排他性。从波德莱尔的艺术批评实践中可以看出,波德莱尔对于自己喜爱的艺术家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地褒扬,而对于不符合自己的审美理想与艺术批评标准的艺术家,即使这些艺术家在当时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他还是持坚定的批判态度。
波德莱尔对众多的艺术家都有过艺术评论。在同时代所有的画家里面,德拉克洛瓦(Ferdinand Victor Eugène Delacroix)的艺术风格最符合他的艺术批评标准。因为,在波德莱尔看来,美与艺术是具有时代性的,所以,艺术创作也要符合时代的艺术标准。在波德莱尔所处的时代,“浪漫主义是美的最新进、最现时的表现”[4]106。因而,波德莱尔以浪漫主义作为时代的艺术批评标准。与新古典主义强调理性相对立,浪漫主义强调感性,主张艺术要富于创造力,要张扬个性,要充满想象力。德拉克洛瓦的艺术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波德莱尔在对其进行艺术评论时开篇就说道:“浪漫主义和色彩把我直接引向欧仁·德拉克洛瓦。”[4]115德拉克洛瓦的画作也确实如波德莱尔所分析那般,充满了瑰丽的想象力、丰富的创造力以及深沉而又忧郁的激情,《但丁之舟》《自由引导人民》便是最好的印证。
正因如此,波德莱尔非常推崇德拉克洛瓦,根据自己党派性的艺术批评原则,热情地肯定了德拉克洛瓦的艺术创作,并驳斥了其他批评者对德拉克洛瓦的攻击。他指出,德拉克洛瓦在细节上的缺点,对于他在浪漫主义艺术上的伟大成就来说是瑕不掩瑜的。波德莱尔还在《灯塔》一诗中,将德拉克洛瓦与拉斐尔、米开朗琪罗、伦勃朗、鲁本斯等伟大的画家并列在一起,特意用一个小节来描述他的艺术风格。
除了热情赞扬像德拉克洛瓦这样符合自己艺术批评标准的艺术家外,波德莱尔还批判了很多沉迷于再现和模仿,缺乏艺术创作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艺术家,即使这些艺术家在当时备受赞誉。例如新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对于波德莱尔而言安格尔只是对古典人像的完美临摹,他们只是复制者而已”[5]113。
波德莱尔在《论折中主义和怀疑》一文中写道:“一件从排他性的观点出发制作的作品,无论其缺点多么大,总是对与艺术家的性情相类似的性情具有一种巨大的魅力。”[6]277他之所以如此强调排他性,是因为他发现了艺术批评的规律:折中主义的艺术评论没有明确的标准和原则,不能给艺术家任何有益的指导,终将会因为没有方向而被历史所遗忘,只有有所侧重才能成就伟大的艺术批评。
(二)政治性——艺术批评要立场明确
波德莱尔艺术批评的党派性原则,还体现在他的艺术批评是带有政治性的。在《一八四六年的沙龙》的前言中,波德莱尔就明确地表示:这本书献给“在数量和智力上都是多数”的资产者。这说明,波德莱尔的艺术批评是站在资产者的立场上的(3)这里需要指出:波德莱尔只是在艺术批评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因为相较于封建主义的古典艺术批评,他更倾向于资产阶级的新的艺术批评。波德莱尔总体上的政治倾向是一种无政府主义。他反对封建势力的复辟,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也有着尖锐的批判。这一点皮舒瓦和齐格勒所著的《波德莱尔传》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这就是波德莱尔艺术批评的政治性。
波德莱尔之所以强调艺术批评的政治性,并且站在资产者的立场上,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资产阶级的强大力量,预感到资产阶级将成为更加先进的社会治理者,将更能促进艺术的发展。而以“垄断者”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已经腐朽,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艺术的繁荣。波德莱尔对资产者们说:“你们在数量和智力上都是多数,因此,你们就是力量,这是理所当然的。”[6]212还对他们说:“你们是艺术的天然的朋友,因为你们由富有者和博学者组成。”[6]214在当时,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确在努力地促进社会文化与艺术的发展。他们建立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让原本上流社会和贵族们才能获取的知识与艺术能够面向所有的民众开放。
波德莱尔不仅从艺术批评理论上主张艺术批评的政治性,也在艺术批评的实践中遵循艺术批评的政治性原则。从《评〈悲惨世界〉》以及《对同代人的思考》等评论文章中,都可以看到波德莱尔的艺术批评在政治方面的党派性原则。他在《评〈悲惨世界〉》这篇文章中,站在资产阶级的艺术批评立场上,将《悲惨世界》中法国复辟政府的一个爪牙——警察沙威视为绝对的敌人。这不仅仅因为沙威为了维护腐朽的法律而阴魂不散地追捕冉阿让,冷酷无情地将芳汀送进监狱,还可能因为沙威曾作为密探去共和派革命者的街垒中刺探情报,企图扼杀革命。波德莱尔曾参加1848年法国革命的街垒战,与革命者同处一个阵营。这样的经历让他更加厌恶沙威这个人物形象。
虽然,波德莱尔并没有非常鲜明的政治观点,但是,在他的艺术批评中,读者还是可以感受到他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偏袒,是一种对数量和智力上都是多数的资产阶级的偏袒。这种偏袒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喜好,也是一种在艺术批评中谋求更长久发展的表现。
二、波德莱尔艺术批评的诗意性原则
在批评实践方面,波德莱尔主张批评的诗意性原则。波德莱尔在《一八四六年的沙龙》中写道:“最好的批评是那种既有趣又有诗意的批评,而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代数式的批评,以解释一切为名,既没有恨,也没有爱,故意把感情的流露都剥夺净尽。”[6]215波德莱尔强调批评的诗意性,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自己就是艺术创作的主体,在艺术批评中常常会以艺术家的视角看待问题。诗人的才华让他在讨论、鉴别、评判艺术作品或艺术现象时,从批评语言到批评方法都充满诗意性。另一方面,在审美现代性思想的指导下,波德莱尔认为“浪漫主义是美最新进、最现时的表现”。浪漫主义强调自由,强调情感和想象的巨大作用。这导致他不仅要求艺术创作必须充满情感和想象力,还要求艺术批评应该富有激情和诗意。
波德莱尔反对那种针对艺术作品的创作方法进行枯燥分析的艺术批评。在他的批判实践中,秉持诗意性原则,对艺术作品进行富有激情的评论。他的艺术批评不仅是一个批评家对一部艺术作品的品鉴与评点,还是一个艺术家与另一个艺术家的心灵碰撞。具体而言,波德莱尔艺术批评的诗意性原则体现在情感的流露和诗意的隐喻这两个方面。
(一)情感的流露——艺术批评要富于激情
波德莱尔艺术批评的诗意性原则,首先体现在他的艺术批评带着许多情感的流露。这种情感的流露,在波德莱尔的艺术批评实践中是处处可见的。《论〈包法利夫人〉》一文就充满了强烈的情感色彩。当时,福楼拜(Gustave Flauber)因为出版《包法利夫人》而被起诉,理由是破坏了公序良俗。最终,经过律师的努力,福楼拜打赢了官司。波德莱尔的这篇文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波德莱尔在文章中充满激情地痛斥了那些指责福楼拜的批评家们。那些批评家认为,《包法利夫人》一书没有一个人物是能够代表道德,说出作者良心的。还认为,作品的主人公包法利夫人爱玛太过淫荡、伤风败俗。波德莱尔直言他们荒谬至极,提出了与之针锋相对的看法:“作品的逻辑足以表达道德的要求,得出结论是读者的事。”[6]57换言之,波德莱尔认为,文学作品不是道德劝诫书,无须在作品中树立一个道德模范,明智的读者是懂得分辨是非的。通读《论〈包法利夫人〉》,我们可以发现:波德莱尔的情感流露从来都是有增无减,从最开始为福楼拜胜诉而喜悦,到中间为批评家们的诋毁而气愤,到最后赞扬书中的爱玛,始终都满怀激情。这种激情让整篇文章变得生动,读起来有一种快感。而且,波德莱尔的艺术性批评语言充满了感染力,让这种激情的表达更富有诗意。
此外,在《论几位色彩家》《论埃德加·爱伦·坡的生平及其作品》以及《评〈悲惨世界〉》等一些评论文章中,波德莱尔的激情与情感流露都十分明显。因为,波德莱尔不仅作为批评家介绍着艺术家们的作品与风格,而且作为诗人与艺术家们进行着心灵的沟通。尤其是《论埃德加·爱伦·坡的生平及其作品》这篇文章,波德莱尔作为批评主体的欣赏与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他将爱伦·坡(Edgar Allan Poe)视作创造美的天才,称赞爱伦·坡的诗精雕细刻,透明、规则如水晶的首饰;称赞爱伦·坡的艺术风格纯粹而怪诞,紧凑如盔甲的锁扣,自得而细密[6]187。可以说,波德莱尔与爱伦·坡形成了强烈的共鸣。他对爱伦·坡的艺术批评是这两位天才诗人思想碰撞形成的火花。
(二)诗意的隐喻——艺术批评要有形象性
波德莱尔艺术批评的诗意性原则,还体现在他的艺术批评有许多巧妙的隐喻,批评语言形象生动,给人以艺术的美感。波德莱尔的研究者金心亦就曾指出:“波德莱尔除了是一位艺术批评家还是一位诗人,因此,诗意的隐喻在他的批评写作中比比皆是,这是他批评写作修辞的一大特点。”[7]30例如,在《论几位色彩家》一文中,为了向读者说明德刚先生绘画作品带给人的强烈刺激和吸引力,波德莱尔用“最开胃的菜肴”和“加了最辛辣的调料的食品”,来说明德刚画作带给欣赏者的那种野性的快感。本来所有形容词都难以描述清楚的风格与美感,被波德莱尔轻松地表现了出来,让读者有了最切身的体验。同样的,还有一个关于爱伦·坡的例子,波德莱尔在《再论埃得加·爱伦·坡》中写道:“我们经常从那些整夜守着古典美学神圣大门的没有谜语的斯芬克斯们口中听到这种空话,并且还伴着一种夸张的哈欠。”[6]190这处批评用“没有谜语的斯芬克斯们”来隐喻保守的古典主义者们,立刻让人联想到固执又乏味的老生常谈。这样隐喻式的评论形象而又精准,让读者通过文字就能感受到古典主义者们毫无性情、无视自然、充满学究气而显得迂腐的风格。
除此之外,波德莱尔还曾说:“对于一幅画的评述不妨是一首十四行诗或一首哀歌。”[6]215-216在他的诗集《恶之花》中,确实有一首艺术评论式的诗歌,它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灯塔》。波德莱尔在这首诗中使用极具形象性的诗句,分别概括了八位画家画作的美学风格。其中,对于德拉克洛瓦的评述是:
“德拉克洛瓦,堕落天使出没的血湖,
掩映在常绿的枞树的阴影里。
在忧郁的天空下,吹奏乐队过处,
奇怪的乐音像韦伯的闷塞的叹气。”[8]28
后来,波德莱尔在《论1855年万国博览会(美术部分)》中解释了这节诗歌:其中的“堕落天使出现的血湖”是隐喻德拉克洛瓦画作中的鲜艳红色,而“常绿的枞树”是隐喻画作中作为红色陪衬色的绿色,“奇怪的乐音”是隐喻与韦伯的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相和谐的浪漫主义绘画风格。总而言之,波德莱尔以诗歌式的隐喻评述了德拉克洛瓦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形式让艺术评论变得形象又富于诗意。
从波德莱尔的艺术批评实践以及艺术创作实践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他的艺术评论充满了形象性的隐喻。这正是他艺术批评诗意性原则的又一个表现。
三、结 语
在西方艺术批评史中,波德莱尔的艺术批评理论和艺术批评实践是独树一帜的存在。他的艺术批评原则直到今天仍然极具启发性。在艺术批评愈加繁荣且越来越商业化的今天,受到市场经济弊端的影响,许多艺术批评都有商业炒作的嫌疑,为了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丧失了原则和立场。面对这一倾向,坚持艺术批评的党派性原则,将帮助我们“坚守文艺审美和陶冶情操的底线,同时使用好资本运作的商业效应”[9]35,从而让文艺批评的艺术属性与商业属性达到平衡,构建起更加合理的艺术批评的价值体系。此外,在艺术批评中,也要防范过度学术化,表达越来越艰深难懂的现象。遵循艺术批评的诗意性原则,一方面有利于创作者与读者更好地接受批评者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能让艺术批评变得更加生动透彻,避免文艺批评的枯燥乏味与千篇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