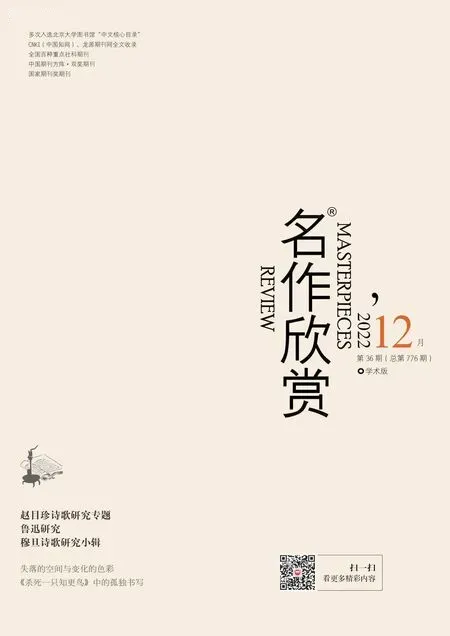失落的空间与变化的色彩
——电影《挪威的森林》空间叙事研究
⊙翟文颖[惠州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0]
电影《挪威的森林》是根据日本现当代作家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挪威的森林》改编而成,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执导,村上春树亲自担任编剧,松山健一、菊地凛子和水原希子等人主演。该片主要讲述了大学生渡边与直子、绿子之间的情感纠葛,2010年12月11日在日本上映,2011年9月16日在中国大陆上映。2011年,该片获得第五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摄影奖,并入围第六十七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挪威的森林》(1987)是村上春树在中国的成名作,20世纪90年代曾在东亚地区掀起‘村上春树现象’。”①因此电影拍摄伊始就受到中国读者广泛关注。然而,《挪威的森林》在中国大陆上映后口碑欠佳,截至2022年9月,在知名电影评论网站“豆瓣电影”中仅获得6.0的评分。②电影与小说在中国受众的冷热两极现象,其背后有多重原因。本文仅从空间叙事角度阐释其电影语言特征,分析其在中国大陆传播遇冷的原因。
空间是电影语言符号中的重要符号要素,电影通过空间叙事表达人物的静态特征,也形象化地讲述人物与世界的关系。电影《挪威的森林》视觉影像符号表现在空间方面有两大特征:一方面空间的拍摄精致却又模糊,表达了失落的叙事空间;另一方面,色彩的选择纯净而醒目,在变化中演绎故事节奏。
一、精致却模糊:失落的空间
陈英雄在对《挪威的森林》改编过程中,对作品的空间进行了个性化处理,具体表现为故事发生地点的精致化拍摄,故事发生空间的模糊化处理。影片注重展示内部空间,多用近景、中近景拍摄有限度的空间内部,故意割舍空间外部与其他空间的关系,造成一种无标识的空间印象,使观众产生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的错觉。空间的“无标识”化,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作品的“全球化”传播,可以代入全球任何一个地方。
影片很少用远景镜头,多用单双人镜头,聚焦于人物的表情和动作。电影开头木月和直子在泳池中彼此凝视依偎的镜头,用画面描述了二人的恋人关系,其场景选用了泳池。泳池是室内泳池,是狭窄而密闭的空间,泳池依然没有远景拍摄,直接进入近景模式,因此也无法猜测这个泳池是东京的泳池,还是北京的泳池,它只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泳池。另一个镜头,同样重复着电影制作者的空间拍摄爱好。渡边和木月两人身穿白色的学生制服,一同穿过足球场。白色的学生制服在镜头的俯拍下,显得两人孤独又渺小,镜头中只有他们白色的制服和他们行走的淡黄色路面,路面被放大,他们就像白色的花盛开在黄色的沙地。
与此同时,镜头聚焦放大空间的同时,却人为割裂了作为背景的空间与其他外部空间的联系,成为单纯的“画布”,成为世界任意角落的一部分。比如,影片开始渡边、木月、直子三人一起游玩的两个场面,一个近似于某个校园的一角,但镜头没有远景,只有类似宿舍的建筑物大门、几辆自行车、人群的谈笑声、鸟叫声。穿着白色制服的渡边和木月是镜头的焦点,醒目、清晰。白色的宿舍楼上,木色的门窗在光线的背阴处,此外再无别的提醒,电影字幕没有提示,电影画外没有声音解释。正如画面显示的,这是“某个”学校的一个角落。拍摄者无意提供更多信息,观众可以想象这是中国的、日本的,或者其他国家的某个校舍旁发生的故事。去掉语言的不同,故事中的年轻人可以是日本人,也可以是中国人。
点清三人关系的旁白之后,三人一起出现在动物园。没有三人走入动物园的情节,只是以动物园一角的红色水鸟作为背景,依然是近景拍摄,没有其他游人的镜头,也没有水鸟之外公园的镜头。此后一组三人在动物园的场景拍摄,是一片草坪,草坪上有几只绵羊。因为镜头没有对动物的近距离拍摄,精确地说,是看到几只近似绵羊的动物在绿色的草地上。几只绵羊犹如绿色地毯上白色的斑点和三个年轻人共同在绿色的草地上。
导演陈英雄喜欢舍弃空间与外空间的关系,去掉空间与空间的联系,聚焦于独一的空间内部,这样的拍摄手法使镜头呈现出精致美,清晰地呈现了人物活动的空间,但关于人物所处空间的外部信息从镜头中无法得出更多的答案。这样的拍摄手法是电影《挪威的森林》空间叙事的重要特点。
电影中给予空间全景镜头的是渡边上戏剧课时,几个参加学潮的学生走进来,教授暂停授课的场面。镜头视点从讲台开始,一一扫向学生和教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镜头没有学生从室外进入室内的镜头,只有学生进入教室后的镜头,镜头虽然详细叙述了教室内部诸要素,但是教室之外所能看到的只是几片从窗外伸过来的绿茵。这样,我们仍然无法得知教室外的空间详情,也无法知晓教室所在具体的地理空间。
电影中渡边和直子重逢后,两人行走在东京的街头,从白天到晚上。白天,他们穿梭在一棵棵苍翠的大树之间,镜头所见是绿色的树叶、高大的树干,就像“挪威的森林”。晚上,他们并肩穿过东京的街道,灯光是模糊的,人群是朦胧的。不管白天黑夜,始终是中近景,焦点始终在渡边和直子,好像世界是不存在的,唯有他们。走着走着,直子问“这里是哪里”,疏离的空间也让人不禁追问“这里是哪里”。电影给人强烈的不确定感、模糊感、后现代感。
影片中去除了与周围关系的空间叙事特点,清除了空间的地方特色,给人随处可见的、全球化的属性,反映了导演陈英雄和编剧也是原作者村上春树的“全球化”的作品特色。片中人物无法明确确定的位置,既是后现代社会青年人内心空间的视觉表达,是作品诉说的主题之一,同时,也是电影制作者故意剔除空间的具体位置标识,想要与读者完成共情。导演去掉故事主题之外非必要的细节,妄图使读者将情绪集中于狭小的空间,达到与作者的共情。
二、纯净而醒目:变化的色彩
“电影空间,是电影利用透视、光影、色彩的变化……创造出包括运动时间在内的四维空间的幻觉”③,色彩是空间叙事的重要语言。陈英雄的电影擅长以色彩进行空间叙事,“通过色彩造型来强化和凸显人物心理变化”④。《挪威的森林》中的色彩叙事有两大特点:一是出现了大片的纯净色,二是不同的纯净色被赋予不同的含义。随着电影情节的推进,色彩不断变化,在变化而纯净的色彩中表现出故事的节奏,为观众带来审美的享受。
在《挪威的森林》中,绿色是导演最爱用的背景色之一。绿色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颜色,绿色一般代表青春、生命、希望等。渡边和直子高中分别后,初次见面的镜头,就用了大面积的绿色。镜头开始先是切入近景,一条鱼在浅浅的、快要干涸的黑色污泥中游动;继而推进中近景,渡边背对镜头,捧着一本书,对面是成片的绿色荷叶。渡边站起身,沿着低矮的亭廊漫步,亭廊尽头是正在观看池塘的直子。镜头所到之处,只有人物侧面及正面的近景,绿色的水草和荷叶幻化为绿色的背景。站在亭廊里的两个人,正值人生的青春年华,他们就像那条搁浅的鱼一样,表面上深处碧叶相连的荷塘,灵魂却被忧愁和孤独困扰,在死亡的阴影中不断地挣扎。
直子住进疗养机构(原著为阿美寮),渡边坐车远远望见阿美寮,小说用详尽的语言对阿美寮进行了描述。电影中既没有阿美寮的名字,也没有阿美寮的全景。电影中阿美寮的镜头,充满了绿色之美。一条山路,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向远处延伸,路的入口处有一个小小的警卫亭,这就是阿美寮的入口。渡边和直子凌晨在阿美寮群山环抱的绿色中奔走,是电影中的经典镜头之一。远处是绿色的山,近处是绿色的草地,远处和近处连成密不透风的绿色屏障,像绿色绒毯将他们包围。直子急速地走着,渡边快步跟随,直子语速急促地讲述她内心的双重不安和痛苦。她和木月精神彼此合一,肉体却无法顺利结合。她不爱渡边,肉体却想要和他结合。
绿色代表生命、活力和希望,进入阿美寮后的绿色,没有空白,没有杂质,镜头从上空切下,没有天空,只有从远处,从高处鸟瞰,被均匀的绿色覆盖的连绵的绿地。屏幕娇翠欲滴的绿色给人带来纯净之美、宁静之美,身体被绿色包围,心灵被绿色安慰。在纯绿色的空间快速前进的直子和渡边、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直子,成为空间中不和谐的元素,由此构成不和谐之律动。这就是生命的孤独和矛盾。生命是美好的、充满活力的,然而,其中却不断跳动着不和谐的旋律,这就是生命的形态。即使剔除了周围所有的不和谐,在其内部却仍然可能出现生命的背反。
从空间读出人与环境的关系,就是读懂了其中的人文历史和文化。电影中涉及直子的部分是绿色,并且多是纯净的大片原色。与此相对,“绿子”虽名为“绿”,在她的镜头中却没有出现过大片绿色背景,多以生活空间场景呈现她和渡边的交往。渡边和绿子首次相遇在学校食堂,背景中有嘈杂的、吃饭的人群。其他场景有绿子家中、医院病房等。背景不再是诗意空间,而是现实空间。直子的“绿色”在影片中不再隐喻生命和希望,从人物的悲剧命运来看,绿色承载着渡边对直子和木月的怀念,绿色是回忆,是永恒的宁静,是美化,是异界。“绿子”和直子的色彩语言不同,叙事空间却具有相同的封闭性特征。这隐喻了影片对青春的追忆和悼念。往事如风,青春易逝,青春的美好和悲伤就如同密封在一个个罐子中,与外界,与社会,与历史割裂,在回忆中,只有他和他的朋友们。
电影中多处使用白色,白色具有特殊的隐喻意义。白色代表着萧瑟和虚无、死亡和纯洁。木月的镜头自不必说,大部分都身着白色学生制服,头戴黑帽,这一方面是因为17岁正是读书的时候,身穿制服也属正常现象。更重要的是,这代表了木月已经随风而逝,仅仅存在于渡边的记忆中。白色代表着过去的回忆、失去的朋友。渡边第一次去阿美寮看望直子,在他小憩时,突然镜头转换,渡边和木月并排嬉笑着走来,他们都身穿白色制服,头戴黑色帽子,睁开眼睛,直子忧郁的脸正注视着睡梦中的渡边。原来这是一个梦,斯人已去矣。直子出场后的服装,也多以白色为主,要么是纯白色,要么是以白色为底色。与此相比,渡边和绿子的服装颜色要丰富得多。白色在影片中有自己的独特含义和使用原则。
初美是影片中又一个女性悲剧形象,就像她的名字一样,代表着青春期最纯净的美好。不幸的是,她爱上了主张“不要同情自己”的永泽君,永泽是和几十个女人有肉体关系的花花公子。电影中她最后出现的镜头,是和渡边坐在汽车后排座位。镜头特写了她精致优美的五官,恬静地眯着眼的微笑,镜头利用光影效果,在昏黄的车窗内,只有她的脸和白色的蕾丝发出和谐的光芒。镜头特写她优雅的脸庞和白色的蕾丝时,舒缓的音乐响起,旁白道:“她两年后割腕自杀了。”白色隐喻了初美的纯净之美,也暗示着她的死亡。
时间随着直子的来信一点点向前推移,不知不觉中,从郁郁葱葱的夏季来到了秋季,镜头中阿美寮的群山从绿色变成了灰色,一根根灰色的野草在风中摇曳,显得说不出的苍凉。直子邀请渡边下雪时去看望她,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渡边从阿美寮回来不久,直子就自杀身亡了。
镜头大部分画面是在野外,白雪皑皑的群山、黑色的树、被雪覆盖的小草,窸窸窣窣的雪划过天空,飘向说话的渡边和直子。他们交谈着,计划着未来;他们躺着,厚厚的雪洁白无瑕,黑色的树伸出枝丫。镜头从近景变为远景,白色的群山中,他们变成黑色的两点,好像消失在雪地,变成一粒尘埃。镜头从他们身上慢慢移向白色的山、黑色的树、远处灰色的天空。镜头再次特写,他们在雪中吻别。渡边离开,雪越下越急,背景已是白茫茫一片,分不清是雪,还是雾。只有直子的脸,在雪中分外清晰。雪已在她头上、身上落了一层,音乐悲伤而缓慢,渡边在雪中攀登的背影显得孤独而坚强。画面最后,是直子流泪的脸,在白色的雪景中,犹如初美宁静的脸在白色的蕾丝上。
直子死后,渡边流浪缅怀直子的场景,以灰色调为主。白色的水浪肆意地冲击着岸边的岩石,犹如渡边无尽的悲哀在心中蔓延,激荡。大全景下,渡边微小的身影在灰色的岩石和白色的巨浪下,显得如此渺小、孤独,却又是整个镜头的灵魂所在。白色的水浪一次次向他冲来,他毅然立在礁石上的身影显得如此绝望,又如此勇毅。镜头一转,渡边和直子出现在绿色的山与草丛间,直子让他永远记住自己。镜头瞬间切回渡边抽搐哭泣的脸。尖锐的音乐中和并锐化了哭泣的声音,无声的哭泣、尖锐的音乐、从四面八方不断涌流的巨浪、灰色的礁石,都强化了屏幕上的悲伤,使观众从视觉、听觉两方面感同身受剧中人物难以治愈的伤痛。
白色和绿色属于过去和回忆,光代表着未来和希望,火红色也是电影的重要色彩。直子生日,渡边带来蛋糕,关闭灯光,点燃生日蜡烛,泛起温暖的烛光。在阿美寮,黑夜来临,病人三三两两坐在一起,中间燃起篝火,他们围坐在一起。篝火旺盛,泛起火红的光,就像生命本身的力量,治愈着各种原因入院疗养的病人。在直子的房间,摆满水果的桌子上有一支蜡烛发出温柔的光,玲子盘腿而坐,用吉他弹奏演唱《挪威的森林》:“有一个女孩,她曾经拥有我,她邀请我去她的房间坐坐,她的房间就像挪威的森林。”渡边和直子面朝玲子,三人围绕在烛光周围。微弱的烛光好像三人生命之光,依偎在一起彼此取暖。就在此时,听着《挪威的森林》,直子突然陷入伤感,这也是直子病情的转折点。火光色是电影中的重要颜色,对其处理进一步强调和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影片最后,电话铃响,绿子从点缀着粉色小花的帘子后面走出,柔和的灯光打在帘子上,绿子身穿温暖的奶黄色毛衣。灯光映衬得房间如此明亮,又如此温馨。这和前一组灰色岩石中渡边哭泣的镜头宛如两个世界。这正是影片中灯光的效果和隐喻含义。灯光象征着光明与未来,有光的地方就没有黑暗,有光的地方就有生命与希望。在“白色”与“绿色”世界回忆的渡边,在“灰色”中绝望的渡边,对身在光中的绿子说:“我现在唯一渴求的就是你。”渡边渴求的不仅是绿子,更是她身上的光。
“色彩对影片艺术再创作的实现必须与影片的叙事时空紧密契合在一起。”⑤电影中的镜头色彩,从白色、黑色、绿色交错,到以绿色为主色调,再到以白色为主色调,最后以灰色为主色调。这样的色彩变迁与渡边的生命状态起伏保持一致,有着深刻的隐喻意义,增加了电影的表现效果,为观众的情感变化和共情效应准备了良好的视觉材料。
三、结语
在小说《挪威的森林》中,主人公渡边周一到周六拧紧发条过日子,以对抗生活的荒诞。小说中主人公用“精确”的日常对抗存在的荒诞,“精确地”计算着抽烟的根数、吃饭的次数,荒诞的是这样的“精确”没有呈现意义,反而袒露出失去了存在意义的贫瘠。⑥电影《挪威的森林》没有完全照搬小说的细节,但其空间叙事却异曲同工地呈现了后现代社会人类存在的荒诞感。
《挪威的森林》中大全景和调度精细的远景长镜头,在空旷且颜色纯净的视觉背景中,一方面营造了高雅的美感,一方面凸显了人物的孤独。陈英雄似乎在大写特写空间之美,观赏中我们知道故事发生具体的空间,仔细思考却不由得发出绿子的经典之问:“你在哪里?”我们也只能像渡边那样回答:“我在不知道哪里的中心。”电影《挪威的森林》中的空间叙事都使用中近景详细叙述,似乎是无比详细的,但所叙述空间的外部特征、外部关系又是极其模糊的。这既是影片空间叙事的特征,也是其悖谬所在。正如片中青年的人生,似乎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但具体所指又是含混不清的。这既是后现代社会对“自我”的极度重视,也是后现代“自我”存在的荒诞和迷失。关注自我,忽略他者,关注细节,忽略关系,这正是陈英雄在空间叙事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社会的回应。
同时,这也是陈英雄的电影无法在中国得到观众认可的原因之一。观众从影片中只能看到“树木”,却无法看到“森林”。中近景加上大片纯色,聚焦于空间内部,使得拍摄画面精美无比,但舍弃了对空间与空间关系的讲述,凭空割裂了空间之间的关系,使观众陷入空间内部叙事的同时,也增加了其故事叙事的割裂感,使电影受众尤其是没有读过原著的人,如堕五里雾中,不知其所云。只有外部空间及空间之间的位置关系,才能定义空间本身,使故事发生的空间具有真实感、具体感。省略外部空间的叙事,只能带来故事情节的割裂感、荒诞感,使人无法流畅感受故事本身发展的脉络,从而产生一定的焦灼。这也许是小说在中国有“村上春树现象”,而电影在网络“豆瓣电影”中评分不高的原因。观众期待品尝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电影的讲述从一个空间内部进入另一个空间内部,始终无法看到故事发生空间的全貌,无法清晰把握镜头与镜头之间必然的、可靠的逻辑关系。对于期待“故事”的受众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电影。
① 翟文颖:《村上春树研究现状述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73页。
② 见网址: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3168086/.
③ 许南明:《电影艺术词典》,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④ 姚沫寒:《陈英雄电影的色彩艺术研究》,河北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页。
⑤ 郭晓冰:《色彩与电影叙事时空的关系解读》,《电影文学》2014年第5期,第150页。
⑥ 翟文颖:《论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中的荒诞性》,《惠州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