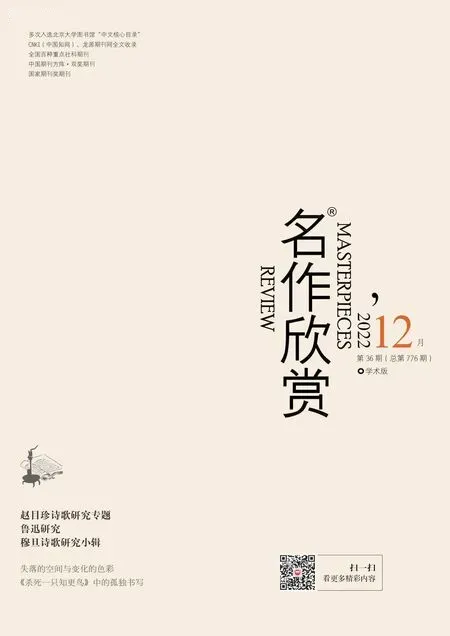写作即经验
——杜威实用主义下《瓦尔登湖》的整体性与实践性
⊙杨惠晰[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19 世纪中叶美国开始了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进程,给当时的美国人带来相应的社会文化问题。梭罗发现其所栖身的康科德镇的人们变成一台台随波逐流的“机器”,“麻木不仁地活着”,将自身困于与自然分离的机器生活和自我的身心分裂状态而无法“汲取生活的全部精髓”,实现生命的完满。为了寻找解决康科德镇困境的方法,梭罗前往瓦尔登湖隐居、身体力行进行实验,并将其探寻过程与结果写成《瓦尔登湖》。可以说,《瓦尔登湖》是梭罗以寻找生存答案的探寻经验为蓝本而完成的作品。
杜威的自然主义经验论可借以观察梭罗的瓦尔登湖经验的目的、过程和结果。杜威认为,无处不在的生命经验之所以能成为具有审美特性的“一个经验(an experience)”,关键在于“被经验的材料走完其历程而达成完满(fulfillment)”。亚历山大将杜威的经验总结为“一个置于自然环境的过程(a process),它由一套社会共有的符号系统调节(a socially shared symbolic system),并试图将世界的含混(ambiguity)带来问题的部分变为确定的(determinate)东西,藉此来主动探索、反映世界的含混”。
亚历山大将经验总结为一个过程,并指出其发生场所及动力、目的机制,他意识到经验能将“含混”变为“确定”,却忽视了杜威所强调的经验这一过程自身拥有的结构性:“因此,不管各种经验在其对象上如何细节不同,它们拥有共同的模式……这种共同模式的要点在于,每个经验都是一个活的生物与它生活的世界的某些部分交互产生的结果。”
在上述基础上,杜威的经验概念可总结为一个拥有某种确定性的模式和结构、发生在现实世界的实践的过程,它不断地受影响并应对来源于外部环境条件变化的不确定,并由处于当下的有机体调节,以此追求一种相对确定的圆满感。梭罗的经验与杜威的经验具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一个过程,都强调人与环境的关系,都追求自我更新和解决困境。
本文以杜威“一个经验”的实用主义美学思想为思路,审视梭罗《瓦尔登湖》的实践经验和书写经验。《瓦尔登湖》的写作呈现了人与环境协作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由人在经验过程中用理性与感性结合的方式与环境进行交互而获得。
换言之,这是一种重建人与自然协作的整体性的实践范式;《瓦尔登湖》的实践性正在于此——梭罗以自身的实践作为行动范式,希望影响读者采取相应的行动,以实现个体和社会的更新。
一、作为行动经验的《瓦尔登湖》的整体性
《瓦尔登湖》是对遭受身心分裂的现代人,如何使其恢复身心合一整体性的方式和结果的探寻。梭罗探究了作为有机体的人如何通过实际行动与自然协作,并最终构建人与自然协作的整体,实现自我完满的实践过程。梭罗发现,康科德人与其周围的环境处于一种支配与顺从的二元对立关系,“人错误地劳作”,他们成了“土地的奴隶”“自身的奴隶监工”,从而失去“真正的完整”,无法与他人保持“最为有利的关系”。人既生存于环境之中又是环境的一部分,和环境的分离意味着问题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梭罗所理解的环境并非像常常被误解的那样单纯指自然,而是也将社会包含其中,即一切客体和事件的世界,毕竟他在瓦尔登湖所居住的地方离其他居民也仅有“一英里”。
诚然,《瓦尔登湖》的确更多着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较少涉及人与他人的关系,但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只有每个人先把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得当,获得“真正的完整”,才能进而和他人建立起“最为有力的关系”。
遭遇人与环境分离的现实困境,《瓦尔登湖》的主体“我”带着探究走入林中,“不是希望隐居”,而是要去“证明”生活到底是“贫乏”还是“崇高”,并将结果“公之于众”:
我想要深深地生活,汲取生活的全部精髓;要顽强地、斯巴达式地生活,用鼻子拱除一切不是生活的东西;要刈出一大片地带,仔细修整;要将生活逼入绝境,降到最低的位置。如果证明生活是贫乏的,那就弄清所有真实的贫乏之处并公之于众;如果它是崇高的,那就在经验里切身体会,并在我下一次的旅行中予以真实的记录。
梭罗反复强调探索生活的前提是去除冗余之物,仅留下生活最基本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经济”章早已指出:食物和遮蔽处是一切生命所需要的,除此之外人类生活必需的还有仅够维持体温的衣服和燃料,如此这般满足必要的需求,“高贵的植物”才能“扎根土地”,进而将茎叶“伸向天空”,开始“生活的冒险”,并最终结出代表植物价值的“果实”;而其他的如财富等都属于奢侈品和不必要之物,只会将人变成“低级的食用植物”,“仅仅生了根并常被摘除了顶部”。
“高贵的植物”象征人,它既是自然的一部分,也与自然相互作用,两者是一个相互协作的整体。其中,“土地”与“天空”虽皆象征自然,却有着不同的功用,前者满足生存必要的需求,后者是植物“冒险”、发展的空间与对象。最终,“果实”象征人实现圆满的自我,正如它是“高贵的植物”“扎根土地”“伸向天空”一系列生长过程的结果,圆满的自我也是人与自然协作的整体的产物。此后,“我”要将获得圆满的自我的方法“公之于众”,从而为建立人与包括社会在内的环境的整体性奠定基石。
现在我们以杜威的“一个经验”鉴照《瓦尔登湖》对整体性探寻的本质和获得方式。杜威指出:“经验是有机体与环境交互的结果、标志与回报,当这种交互进行到极致时,就转化为参与和交流。”在这里,杜威使用了“有机体”与“环境”这两个生物学术语,但并未直接采用其生物学含义,而是对之加以哲学上的改造。
他说道:“当然,存在一个独立于有机体的自然世界,但只有当其直接或间接进入生命功能时才成为环境。有机体自身是更大的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只有当其处于与它的环境的积极联系中时才作为有机体存在。”换言之,有机体和它的环境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仅存在“实践性和时间性”上的、即经验发生之时的区分。当有机体与环境成为一个整体,环境是自我的一部分,自我是环境的组成成分,因此,人与自然协作及其过程的整体是实现自我完满的过程和结果。
《瓦尔登湖》中的主体若要实现自我的完满,就需要与自然协作,构建人与自然统一的整体。首先,《瓦尔登湖》阐明人生存于自然中,是整个生物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身上存在一种不亚于追求精神生活本能的“野性”,它让“我”渴望“吞吃野兽肉”,追求“原始地位和野蛮生活的本能”。所谓“野性”,便是人作为生物的本能。生物的本能也是杜威经验理论探究的起点,“生命是在一个环境(an environment)中进行的;不仅仅是在其中,更是因为它,与它进行交互”。《瓦尔登湖》的主体“我”正是杜威所描述的这样一个生命,它通过生物链参与整个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在物质基础上与自然密不可分。
“野性”是形成人与自然协作整体的基础,而人要真正与自然形成协作整体,还需要感官与头脑的合作:
我的头脑就是手和脚。我感觉自己最好的官能都汇聚其中。本能告诉我,我的头脑是挖掘的器官,正如有些生物使用鼻子和前爪,我将用头脑挖出穿山的路。我想最丰富的矿藏就在此……
“挖掘”的对象是“山”,也就是自然;“挖掘”的目的是“矿藏”,也就是完满的自我;而“挖掘”的方式和工具“就是手和脚”的“头脑”。“头脑”代表着理性,“手”与“脚”代表基于感官的感性,“我的头脑就是手和脚”意味着两者的结合统一;此后,“我用头脑挖出穿山的路”,“穿”意味着“我”完全进入“山”的内部,人与自然经由“头脑”和“山”的协作成为整体,并最终使人得到了“矿藏”。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在这种协作中不可或缺:感性强调感官发现,依赖于个体经验,具有在场性;而理性,特别是普遍理性,为人所共有,具有恒常性。在经验中,知觉是基于“感觉器官和与之相连的动力机制”之上的“复杂而精细的区分能力”,使人建立“经验的上层结构”成为可能。知觉结合做与经受,赋予经验以模式与结构,同时又受做与经受平衡的制约,过多的做或者经受都会“模糊对关系的知觉”。
其中,知觉的对象是“存在于此时此地的,带有伴随着并标志此存在的所有不可重复的特性的单个的事物”,强调感性正是强调个人实践,强调做;同时,理智联系预期要达成的总体来思考做与经受的关系,推动经验构成一个整体,强调理性即是强调成分之间的逻辑构建,强调整体,强调经受。因此,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旨在更好地组织、指导思维和行动,从而建立人与自然协作的整体,发现“矿藏”。正如梭罗在日记里所说的,“我发现当我建造篱墙,测量农场,甚至是采集草药时,这些是知觉与享受的真正方法”。
如此,当作为有机体的“我”结合了理性与感性,与周围环境进行交互形成协作整体,“矿藏”就会被获取,即圆满的自我的获得:
至少我从自己的实验中了解到这些……他会抛下一些东西,会越过一条无形的界限;新的、普遍的、更为自由的规律将会在他周围和心中形成;或者,旧的规律将会被拓展,被以一种更自由的、对他有利的方式进行解释,他将得到允许生活在更高级的生命状态中。
这段话用“整体”的概念可以解释为:跨越“无形的界限”意指旧“整体”的破裂,新的“整体”在“周围和心中”构建,失衡带来的焦虑在做与经受中被解决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平衡得以建立,圆满的自我得以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圆满的自我是阶段性的,有机体将继续与周围环境交互并期待下一次完满的到来,因此,在《瓦尔登湖》的最后“我”离开了瓦尔登湖,走向下一段旅程。
综上所述,《瓦尔登湖》探究了作为有机体的人如何通过实际行动与周围环境协作,并最终构建人与自然协作的整体,实现自我完满的实践过程。在这一点上,他与其同时代的美国哲学家爱默生不同,因为后者虽然同样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但主体在与自然、神的交流中消解,“我成了一只透明的眼球,我荡然无存”,而不是在人与自然的协作中获得了梭罗式的自我的完满。
二、作为写作经验的《瓦尔登湖》的整体性
整体性不仅是《瓦尔登湖》实践行动的主题探寻,也是其经验书写的形式策略,表现为梭罗对作品的结构、章节的安排、意象的选取和悖论的使用等方面的关注。
首先,《瓦尔登湖》全书以季节循环为架构,这也契合杜威实用主义美学强调的人与自然协作的整体性。杜威认为,自然中先验地存在节奏,这对生命和艺术有着重要意义:只有这样,人的生命才能在与自然节奏的联系中得以发展;只有这样,作为艺术形式重要特征的节奏才能成为“材料在经验中朝向自身的顶点发展的运动”。四季轮转是人所能领会到的最基本的自然节奏之一,梭罗将其融入《瓦尔登湖》的形式框架,赋予《瓦尔登湖》书写语境的活力。
其次,《瓦尔登湖》形式的整体性也体现在章节安排上。前文指出,梭罗在文本中将人比作一株植物,它扎根于土地,枝叶伸向天空,并最终结果,事实上,《瓦尔登湖》的章节也呈现出一株植物生长结果的历程。第一章“经济”是探究的出发点,对应植物的种子形态;最终章“结语”呈现整个《瓦尔登湖》探究所得到的结论,是体现植物价值的果实;剩下的章节,是植物在两个阶段间一系列与自然做与经受的生长过程。这些章节都是代表事物或现象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其中有具体的物质环境或行动描写,如“豆子地”“湖”等,有抽象的哲思的抒发,如“更高的规律”“独处”等。
并且,存在由具体的环境走向思想的阐述的规律:“我所生活之地,我为何生活”引出“阅读”“声音”“独处”;“访客”“村庄”“豆子地”“湖”“贝克农庄”引出“更高的规律”“野蛮的邻居”“室内取暖”“以往的居民;冬天的访客”“冬天的动物”、“冬天的湖”引出“春天”。
青辰已经越来越接近地面,箭囊中的箭矢也即将告罄。他知道,如果在他落地之前,不能将地面的这些土狼驱散的话,他将会与那女子一样,陷入土狼的包围圈中。
以杜威的经验理论观之,这种“种子—生长—结果”的植物生长过程可视作需要时间完成、生长性的动态组织,呈现“开端—发展—实现”的经验过程。“经济”章是经验的开端,“结论”章是经验的实现,而位于其中的章节是经验的发展;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经验结构,且整个过程持续地流动。章节的交替是一种做与经受交织的节奏,这种有秩序、有组织的运动赋予《瓦尔登湖》的写作一种内在一体与完满的审美特性,使得《瓦尔登湖》的写作成为具有整体性的“一个经验”。
再次,《瓦尔登湖》形式的整体性也暗含在悖论的使用上,显现了“破除边界—形成整体”的路线。在语言层面,《瓦尔登湖》使用了大量的悖论,“经济”与“结语”两章尤为突出。
艾布拉姆斯将悖论定义为“表面上看起来逻辑自相矛盾或荒谬的陈述,实际上却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解释”。廖昌胤认为,悖论将“互相矛盾的等值因素并存于同一体内”,“旨在突破传统价值观的范式,实现价值观的创新”,“其基本方法是用新的定义来定义现有的定义”,即以已有的概念和观念创造新的概念和观念。
悖论的形式本身具有包含两种事物并将之融为一体构建成新整体的能力。以《瓦尔登湖》中越橘的悖论为例,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这种“破除边界—形成整体”的模式:
果实并不会将自己真正的味道献给购买它们的人,也不会献给为买卖而种植它们的人……如果你想要知道越橘的味道,去问问牧童或山鹑吧。如果你认为自己虽从未采摘过越橘但知道它们的味道,这是犯了常见的错误……在前往市场的马车上,随着果实的粉霜被刮蹭掉,它那芬芳以及精华部分也都消失了,仅仅成为食物。
此悖论中存在的完全对立的等值因素是吃了果实就能知道它的味道和吃了果实也不能知道它的味道,若想理解这段话的意义,需要消解两种等值因素的边界并在两者的基础上阐发一种新的逻辑和观念,“买卖”“采摘”“仅仅成为食物”等提示指引逻辑方向,最终新的整体得以构建,意义得以浮现——康科德镇人认为的“越橘的味道”和“我”所认为的“越橘的味道”相异,后者才是真正的“越橘的味道”,它需要人与自然协作才能获得。
综上所述,《瓦尔登湖》的布局结构、章节安排、意象选取和悖论使用等,都指向或暗含整体性的形式策略,其在作品层面强调作为劳作的写作经验的完整性,在话语层面则倾向于将两种或多种对立的事物融为一体,并在新的整体中获得新的知识和体验。
三、作为一个完整经验的《瓦尔登湖》的实践性
前文以杜威的“一个经验”为透镜,观察分析了《瓦尔登湖》行动主题和形式策略上的整体性,发现其内核归根结底在于克服分离、构建统一整体,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深入讨论整体性所具有的实践价值。
整体性的意义在于其通向确定性。在《瓦尔登湖》的最后,“我”的脚在这里留下“印记”,踩出“十分清晰”的“一条小路”,在瓦尔登湖的生活也变成了“传统和习俗”,带来熟悉感和确定感,使“我”带着“成功”和“信心”开始新的“航行”。这也与“一个经验”强调的整体性带来确定性不谋而合,杜威指出,当经验之为经验时,其不再“被封闭在个人的感受和感官中”,而是“积极且机敏地与世界交流”,甚至达成个体自我与客观世界的“完全渗透”;其也不再“屈从于任意且无序的变化”,而是向有机体提供一种“有节奏的、发展中的唯一的稳定性”。
这种稳定性事实上是一种消除带来含混与威胁的不确定之处、肯定成就感与愉悦感的确定性,而获得这种稳定性的方式在于与世界真切地交流甚至是“完全渗透”,即构建有机体与环境的协作整体。因为通过与环境的抵制、紧张与融合,问题得以解决,有机体得以丰富与发展,其对世界和周围环境的了解更近一步,世界和周围环境再次变得熟悉而安全。
《瓦尔登湖》的实践范式具有可复制性。首先,《瓦尔登湖》源于梭罗本人的亲身经历,在《瓦尔登湖》第一章“经济”的开头,梭罗就指出,《瓦尔登湖》是用第一人称所写。使用第一人称,不仅意味着是“真诚地描述自身的生活”,也暗示着一个具体的人的存在。
其次,人与环境的关系是进行《瓦尔登湖》中的实践条件,而这种条件普遍存在。人与环境的关系是指人通过理性与感性结合的方式与环境协作。这里的环境并不仅仅指自然,而是包括社会在内的一切影响人之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就连《瓦尔登湖》中,“我”也不是仅仅与自然发生关系,而是“独自住在森林里,离周围邻居至少一英里”,“正如我在林中散步时观察鸟和松鼠一样,我在村中散步时观察成人和孩童”。
梭罗虽然要“如一只黎明时的雄鸡,立在栖息之处高声报晓,只要能唤醒我的邻居”,但他不希望任何人重复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生活。这是因为梭罗希望读者复制的是建构人与自然协作整体的行为范式,而这种范式不是只能到瓦尔登湖隐居才能进行,而是只要满足人与环境的关系,每个人都能与自身的环境建立起独特的协作整体。
最后,这种实践范式能够帮助人获得完满的自我,具有重复的意义。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之所以要安排“经济”与“结语”两章,目的便是如此,写作契合经验有着一个有目的的开头和一个有结果的结束的内在结构。自然,经验也在结局发展到圆满,有机体与环境协作的整体得以构建,带来一种满意与确定的感觉。相比于“经济”章的失落,“我”如今是“充满信心的”。
在“结语”章,说明要离开前,“我”大段提及旅行与探索新世界,并将其与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相比,“做发现你内心的新大陆和新世界的哥伦布吧,开辟并非贸易的而是思想的新航线”。在瓦尔登湖生活也是旅行与探索新世界的一部分,无论是实际上的还是思想上的;因为思想上的探索与现实世界的探索是同源的——在探索的过程中,人与新的环境不断以最内在的方式建立新的“整体”,在差异和抵抗中得以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四、结语
将恢复人与环境协作的整体性、寻求确定性知识的经验的形式传递给读者是《瓦尔登湖》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消解确定性的后现代社会,面对发展迅速、变幻莫测的世界,焦虑、抑郁似乎成为人的常态。所以,非常有必要透过杜威的“一个经验”重读《瓦尔登湖》的探究模式,汲取梭罗重建人与环境的完整、人的身体与心灵的完整、获得满足感与确定感的经验。梭罗的实践范式或许能成为解决当代人生存问题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