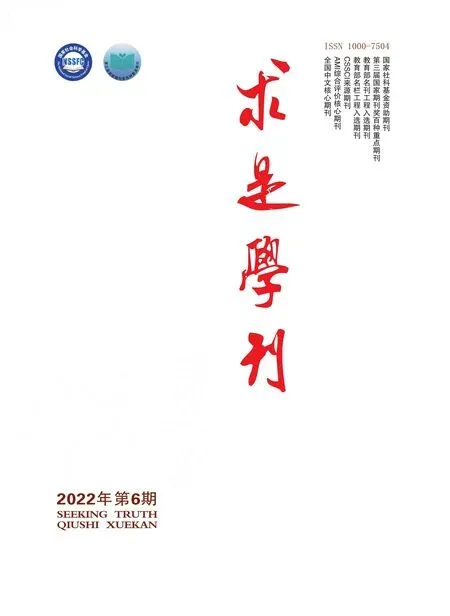“未来的文学”
——解构理论中关于“巴特比表述”的对话与争锋
吴娱玉
在19 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梅尔维尔(1819—1891)于1853 年写的著名短篇小说《抄写员巴特比——一个华尔街的故事》中,主人公巴特比是一个抄写员,他除了抄写之外拒绝做任何事。抄写触及的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语言,西方传统思想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够发出有意义的声音,而动物只能无意义地嚎叫,这说明语言与意义、理性密切相联,没有逻各斯的动物只能快乐或痛苦地嘶吼,发出无意义的“沉默的言语”。在“意义”基础上建构的是再现的艺术体制,再现对象常常是宏大的神话、历史与政治,而庸俗、普通与边缘的部分总是被无视。基于此,作为抄写员的巴特比本该是语言的遵循者、逻各斯的保卫者、英雄的呈现者,但却成为模糊的匿名者、理性的背叛者,他不是英雄般地奋勇抗争,也不是悲剧式地殊死搏斗,而只凭借一句古怪而蹩脚的句式就获得了无可企及的能量。在整部小说中,巴特比一共只说了37 句话,1/3 以上是重复的“我宁愿不”(I would prefer not to)。这种怪异的句式以釜底抽薪的方式疏离了逻各斯:其一,他是一个书写者,在西方思想史中,书写的地位远低于对话,正如柏拉图贬斥书写,认为书写的文字只会重复自己,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意义,“书写是无声的话语(discourse)……它们不知道如何回答问题,不像活生生的话语(discourse)”①Jacques Rancière, The Philosopher and His Poor,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p.40.Discourse 指柏拉图所说的“对话”,是一种口头的交流,与言语(speech)的意义接近,它拥有一个言说者,与书写(writing)的意义相对。。与在场的对谈相比,书写是沉默的言语,是摹仿、拟像,离理念最远。到了解构语境中,书写是比声音更本源的,本源是一种原初踪迹(architrace)。“声音—符号—文字的序次将为文字—踪迹—差异的序次替代。”①陆扬:《德里达的幽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页。而巴特比不停抄写却少有言说,这意味着他离理念更远,离解构更近。其二,他的言说总是拗口怪异、喃喃自语、断断续续、无法表述、不成系统,他的语言没有进入理性秩序,切断了与逻各斯的关联,让语言变得无意义,让思想陷入荒芜。
巴特比句式引起了当代诸多理论家的兴趣,它犹如一个棱镜折射出不同理论家各异的思想成色。德勒兹(1925—1995)在《巴特比,或文学表述》②Gilles Deleuze,“Bartleby,or The Formula”,in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trans by Daniel,W.Smith and Michael A.Greco,London&New York:Verso,1998,pp.68-90.中译文参考了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9—191页。中认为,巴特比古怪的、翻译般的语言制造了一种空虚,让原有的逻辑链条遭遇挫折和断裂;阿甘本(1942— )的《巴特比,或论偶然》接续德勒兹的思想,认为这种不作为是一种悬置、潜能,从而背离原有的逻辑框架,开拓出一个全新的空间,呈现为一种“非实在”(unreal)的拓扑学(topology);朗西埃(1940— )在《德勒兹、巴特比与文学表述》中延展、反思了德勒兹,他将巴特比的表述看作一种沉默的言语,语言中断了与一切表意的确定关系,变成了破碎的、零散的分子,语言不再是意义的传达,而是符号的链接,符号的间隙都被无法辨认、不可通约的空白填满。这些理论家彼此影响,相互对话,针锋相对,形成了一个网状的理论场域,无论是德勒兹的“少数”、阿甘本的“潜能”,还是朗西埃的“沉默”,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消解主体、走向外界的使命寄托给一种脱离理性逻辑,看似含混、呢喃的语言;寄托给一种充满无限潜能的、具有革命性和抵抗力的未来的文学。因此,聚焦于巴特比,就能窥探出解构思想如何击溃理性,如何另辟蹊径,如何应对质疑,进而绘制一幅动态的、多声部的理论地图。
一、断裂:德勒兹论巴特比的逃逸哲学
(一)巴特比句法制造空白
首先,巴特比句法不合常规,制造断裂。巴特比不断重复的“我宁愿不”(I would prefer not to),一般的句式是“I had rather not”。尽管这个句式符合语法,但用法奇怪:第一,用肯定的非谓语动词来代替否定谓语动词,prefer很少被这样使用;第二,to后面本应增加一个成分,这就进入了一个常规的二元结构“我喜欢这个,意味着不喜欢那个”,但巴特比句式to 的后面没有加任何成分,使被否定的内容无法辨别,成为一个空白,拥有无限的空间;第三,巴特比总是用耐心而迟缓的语调不断重复,以呢喃而坚持的语气道出,形成了一个含混不清又异乎寻常的团块。德勒兹认为,“梅尔维尔发明了一种陌生的语言,它在英语下面流动,并带走了英语,这就是外部语言(OUTLANDISH),或者去除疆界的语言(Déterritorialisé)”③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第148页。。如果巴特比断然拒绝,那么,他是反抗者,还能扮演一种社会角色。但他的句式令一切言语行为失去作用,也令巴特比成为一个完全受排斥的人,无法被赋予任何社会位置。诉讼代理人察觉到他意欲让巴特比恢复理智的希望落空了,因为这些希望寄托在预设逻辑之上,巴特比发明了另外一种逻辑,它足以在暗中破坏言语活动的预设。这个句式令词语与事物、词语与行动“脱节”:它割裂了言语活动同一切参照物的联系,让巴特比成为一个没有参照的人。
其次,巴特比句式制造沉默的效果。每当这个句子出现,周围的人都惊愕不已,他们听到的是不可言说本身。而巴特比则陷入沉默,仿佛他已经说出了一切,语言一下子枯竭了。这个句式通过重复不停地自行增殖,每次出现都让人觉得一切又从头开始了,每次都让这个无法确定、无法分辨的区域扩大,每次都让人感觉到疯狂的程度在加深。巴特比是秩序之外的人,他是白痴、疯子,这个句式具有强大的破坏性、传染性,它经过之处一片死寂,令其他人“舌头打结”,文员和诉讼代理人也被感染了。巴特比说出“我宁愿不”时,他就不能书写了。这个句式不仅排斥巴特比不愿做的事,还令他正在做的一切、他理应做的一切变得不可能。这意味着他情愿什么都不选择,胜过选择任何东西——这不是一种渴求虚无的意愿,而是意愿虚无性的增长,他始终在拐弯抹角地制造悬念,跟所有人保持距离。
(二)一个无人称、无主体、反俄狄浦斯的“形象”
在井然有序的理性世界里,不按照秩序行事的人会被排斥甚至流放,疯狂就作为秩序之外的阴影地带,它变成被规训与管制的部分,而巴特比的句式让语言陷入枯竭,失去功效,他成为一个被排斥的边缘人。在这个意义上,巴特比是无主体、无人称的,用德勒兹的话来说是一个“独身者”,他没有参照,没有财产,没有土地,没有个性,没有特殊之处,他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他就是瞬间。德勒兹认为:“I PREFER NOT TO 是巴特比的化学公式或者说炼丹公式,但我们可以从反面来看它:I AM NOT PARTICULAR,‘我没什么特别的’,并将其作为巴特比句式不可或缺的补充。”①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第153—154页。巴特比处于一个最原初的、无法分辨的混沌状态,他没有同第二天性分离,其原始天性揭露了分辨之错漏、理性之空洞、逻各斯之匮乏,展示了一个充满骗局的、自我蒙蔽的世界。作为一个独特者,他脱离了理性框架、认知范畴,他的句式摧毁了语言的普遍规则和逻辑预设,是一种单纯而特殊的语言、一种原始的语言的残余和投影,它将语言带到了沉默的极限。
德勒兹认为巴特比与诉讼代理人之间是一种父与子的关系,诉讼代理人是社会机器中的掌控者,履行父亲的责任,彰显父亲的权威,巴特比是儿子。②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第160页。这意味着西方哲学建立在重视头颅、理性、中心组织、父亲统治、认知主体的基础上,只有父亲的功能分崩离析为一个虚无、不确定的空洞,一个被兄弟姐妹萦绕的区域才能实现。梅尔维尔将人从父亲的职责中解放出来,在独特者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平等的、众声喧哗的兄弟社会。③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第178页。于是,诉讼代理人试图履行父亲的职责时总被不确定的话语打断,这一句式击垮主体的地位,取消父亲的功能,让父亲的雕像变成模糊的肖像,再游移到另一个肖像,直至分化为任何人的肖像,或根本不是人的肖像。当失去了权威与参照,人的成长让位于一种新的未知因素,成为一种非人的、无定形的生命,于是,父与子的俄狄浦斯结构就这样被摧毁了。
(三)“群岛”:一种抵抗的政治
德勒兹认为,有一种能量潜藏在这种否定的逻辑中:“一种超越所有否定的否定态度。”④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第147页。这就是梅尔维尔描绘的美国式的大杂烩——语言脱离逻辑,主体取消结构,呈现出无限繁衍的差异世界,这是一个缺乏中心、缺乏反面也缺乏正面的文学世界。梅尔维尔特有的这种断断续续、词不达意的表达方式,使主体变得摇曳不定,父亲榜样性的话语被撤销,儿子复制、书写的功能失效,这是一种抵抗旧世界的精神分裂。精神分裂与精神分析不同,精神分析是理性逻辑的反面,依然遵循着理性逻辑,但精神分裂却是对原有体制的瓦解。所以,巴特比和诉讼代理人之间不是父子等级关系,不根植于同一的结构体系,而是一种滑移、相邻,一种非血缘、非等级的结合,这意味着他们遵循的原则不是摹仿,而是生成。新的世界是在父亲权威碎裂后的废墟上建立的一种平等的兄弟关系,它遵循结合或毗邻的原则,如同块茎一般非中心、无组织、无限蔓延,彼此邻近却互不占有。德勒兹认为,梅尔维尔的创作是对过程和群岛的肯定。群岛不是拼图,拼图意味着每一片在互相调整后仍能构成一个整体,而群岛“是一堵由可活动的、没有用水泥固定的石块砌成的墙,其中的每个元素都有独立的价值,但这价值又是通过与其他元素的关系体现的:隔离群与漂浮的关系,岛屿与岛屿的间隙,移动的点与曲折的线,因为真理总是有着‘不平整的边缘’”①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第183页。。群岛不是一个头颅,而是一根脊椎,不是均匀的整块,而是无限色块的叠合,哪怕只是白色与白色的叠加,是无限延长、多处接合的拼凑,使认知主体在群岛式透视法中听觉和视觉并用,全景镜头不断推移,正在生成的感觉来代替固定僵化的概念,形成一种全新的、通感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巴特比是整个19 世纪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匿名者、弑父者,是现代的尤利西斯(“我谁都不是”),是大都市中某个被压垮的、机械化的人,同时也被寄予从他身上走出一个未来或新世界的人。可以看出,德勒兹认为巴特比句式是一种谵妄的、游牧的言语,一种解域化的实验运动,蕴含着巨大的抵抗性和政治性。真正的写作是一种逃逸、一种生成,需要背离理性,变成未知。
二、虚无:阿甘本论巴特比的潜能诗学
与德勒兹一样,阿甘本也关注到巴特比句式,他认为巴特比所有的创造源于“无”,这种“无”蕴含着一种潜能,它肯定偶然性,质疑所有先在的规定和预设,蕴含着一种批判和抵抗的能力,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潜能是一种“无”
阿甘本认为抄写员即写字板,他犹如一张白纸,栖居在潜能的深渊。潜能是一种空无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才能产生崭新的力量和反抗的可能。②乔吉奥·阿甘本:《潜能》,王立秋、严和来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第452页。阿甘本援引了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亚里士多德把nous即智识或潜能的思想比作一块上面什么也没有写的写字板——nous 是一块写字板(grammateion),“思想在心灵之中就像在一块没有被现实地书写的写字板上的字一样”③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7页。。心智就是一张没有任何性格特征、没有任何观念的白板,如果思想本身有某种确定形式,如果它已经是某物,就像写字板已经是物,那么,它必然也是可认知的,并因此构成对理智的阻碍,nous 除了是潜能以外没有其他本性,在思想之前是绝对的无。“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所有存在或做……的潜能都永远也是不存在或不做的潜能,没有这种不……的潜能”④乔吉奥·阿甘本:《潜能》,王立秋、严和来等译,第440页。。一切潜能也是非潜能。“正如建筑师甚至在他不实现他建造的潜能的时候也保有这种潜能,也正如西塔拉琴手之所以是西塔拉琴手乃是因为他也能不演奏西塔拉琴那样,思想也作为一种思考与不思考的潜能而存在”⑤乔吉奥·阿甘本:《潜能》,王立秋、严和来等译,第440页。,潜能只有在永远不去做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一旦它变成现实,产生行动,潜能就消失了。巴特比只在不意欲的情况下才有能力,他的潜能并非由于意志缺乏而不能实现,相反,他在每个点上都超出了自己和他人的意志,“我宁愿不”破坏了意愿与能力之间的链接,巴特比以不作为的方式执拗地停留在潜能中。巴特比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在绝对不意欲的情况下有了能力(或没有能力)。“我宁愿不”不是他不想抄写或他不想离开办公室,而是他只是更喜欢“不”,这就是潜能的句式。
阿甘本谈到了德勒兹的分析——巴特比句式的破坏力在于他隐秘的不合语法性:“这个句式‘断开了’词与物,言语与行动,也断开了说话的行动与言词——它把语言和所有的指称割裂开来,这与巴特比的绝对使命,成为一个无指称的人,一个突然出现然后消失,不指示他自己或别的什么的人,是一致的。”①乔吉奥·阿甘本:《潜能》,王立秋、严和来等译,第455页。巴特比句式不肯定也不否定,不接受也不拒绝,这个句式开启了一个是与否、可取与不可取之间的无区分区域,一个存在(或做)的潜能与不存在(或不做)的潜能之间的无差别区域。巴特比的句子结尾的那个“to”有一种回指的特征,它没有直接指向现实的一部分,而是指向它前面的一个语项,而它唯一的意义就出自于前面的那个语项。但这个回指被绝对化,甚至到了失去所有指称的地步,它可以说回转这个句子本身——一个绝对的回指,在自身上打转,不再指向一个真实的物体,也不再指向一个被回指的项。西方思想的惯用逻辑如哈姆雷特一般,把一切问题化约为生存与毁灭(to be and not to be)、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对立。只有巴特比这一个句式如此决定性地悬停在肯定与否定、接受与拒绝、给予与夺取之间,他指出一个超越二者的第三项——“毋宁”或“谁也不更”,坚持无、非存在,将思考模式从存在和非存在中解放出来,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潜能本体论。
有向无环图(DODAG)[13-14]中所有节点以类似于树状的拓扑结构连接,所有路径均指向DODAG的根(Root)节点。其构建过程如下:
(二)潜能是一种“偶然”
科学实验关心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某事发生或不发生,为真或为假,而在梅尔维尔的故事中关心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某事发生且同时不发生,是真的且同时不是真的,只有背离真理、事物的实质或非实质的联系时,巴特比的“我宁愿不”才获得完整的意义。无真理的实验与事物的实际存在或不存在无关,只与它的潜能有关。而潜能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这就退出了真理的条件,并且退出了“所有原理中最强的”矛盾律。在第一哲学中,一个既可能存在又可能不存在的存在,就是一种“偶然”。所谓偶然不是某种非必然或非永恒的东西,而是它的反面在它发生的那个时刻也可能发生。在同一个瞬间,我既能以一种方式行动,又有能力以另一种方式行动或根本不行动。阿甘本援引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家司各特的观点,他认为意志不是决定,而是给了对“……的能力与不……的能力”“……的意志与不……的意志”的构成性的、不可化约的共属的经验,即“有意愿的人会经验到他不意愿的能力”②乔吉奥·阿甘本:《潜能》,王立秋、严和来等译,第465页。。此种意志就像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一样模棱两可,它既有意愿的能力又有不意愿的能力,这两种能力并不相左。巴特比的潜能废除了所有哲学的原则——意志、理由、因果律、必要性,且超越了存在和非存在,他召唤出过去的潜能,在潜能中任何事物都有重新复活的可能。
(三)对话德勒兹:一种新的弥赛亚
阿甘本与德勒兹都探讨了一种不确定的领域,不肯定也不否定,暂停的不作为状态。德勒兹将巴特比看作一种新形式的基督③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第191页。,他废除旧法并开创一种新的指令。阿甘本补充道:“如果巴特比是一个新的弥赛亚的话,那么,他的到来并不是,和耶稣一样,为了救赎过去存在的东西,而是为了拯救过去不存在的东西。”④乔吉奥·阿甘本:《潜能》,王立秋、严和来等译,第476页。在巴特比的世界里,过去发生的和过去没有发生的都回到原初混沌、未分的状态。阿甘本认为:“弥赛亚形象的到来意味着法律的完满和废止。”⑤Giogio Agamben,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an Francisc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30.在弥赛亚中,法律得到了悬置,生命摆脱权力规训,得到复活和救赎。弥赛亚论的核心在于潜在论——“不是”比“是”更根本。弥赛亚式生活的精髓在于“as not”,即“像不是那样”地去生活,这与巴特比尔的“我宁愿不”异曲同工,这种方式拆解规定,悬置律法,消除等级,在不改变形式的情况下暗中破坏它。弥赛亚式的召唤使人从现实身份中抽离出来,它不是简单地否定或消灭法律,而是让它停下来,无法运作,失去作用。弥赛亚创造了一个脱离权力和法律掌握的空间,它不发生冲突,却能停止工作,废弃一切形式,使之回到一种潜能状态,即被去活化、去现实化的状态。需要指出的是,取消的现实不是被废除,而是被保存起来,世界是潜能展开的过程,事物不会消失,而是折入潜能,等待新的显现契机。
弥赛亚不是终点,它是对均质时间、线性序列的瓦解。弥赛亚不是通过一个宏伟的、整体的体统来改变世界,而是通过打断使之停顿,从而产生一个没有预设的方式调整更新。弥赛亚没有目的,它使既有的结构、体制失去效用,却不涉及重新组建。弥赛亚具有强大的恢复能力,它唤醒一个从来不曾有的、未知的世界,所以说弥赛亚时间不是末世时间,而是剩余的时间,每个瞬间都是潜在的终点。每个现在都是对编年的连续时间的打断,人在某个时刻的绽出就可能成为弥赛亚事件。“一种弥赛亚政治也不是‘yet to come’,而是‘come’”①吉奥乔·阿甘本:《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钱立卿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6页。,人们不是生活在弥赛亚降临后的永世中,也不是生活在弥赛亚迟迟未到来的无尽等待中,而是生活在弥赛亚式的召唤中,即弥赛亚随时到来。②吉奥乔·阿甘本:《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钱立卿译,第16页。可以说,阿甘本通过巴特比不作为、不意愿的姿态,打断原有的线性时间序列,呼唤一种新的时间观,从而生发出一种抵抗的潜能。
三、沉默:朗西埃论巴特比的“石化”风格
朗西埃在《德勒兹、巴特比与文学表述》中延续了德勒兹的思路,他认为德勒兹将巴特比句式/表述(formule)呈现出一种不可言说、飘忽不定的言语特点,它击碎了原先的逻辑链条,完成抵抗,走向民主,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沉默:在表意系统崩溃之后
朗西埃认为这部小说不是一个关于贫困书记员古怪与不幸的故事,也不是人类处境的象征,而是“一种表述、一场演出(performance)”③雅克·朗西埃:《词语的肉身:书写的政治》,朱康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5页。,表述宣告了表象体系的破裂。语言不再是表象的工具,不具有再现功能,它们以自身为目的,无限繁殖,野蛮生长。文学要求一种新的法则,与原先模仿、再现的法则对立,这是分子的世界——一个未决定、未个别化、先于表象、先于理性的世界。朗西埃认为德勒兹将文学从表象世界的使命中抽离,让其直面自己破碎的本质,让其从理性逻辑中逃脱,让其呈现一种“火焰般的表达线条”④雅克·朗西埃:《词语的肉身:书写的政治》,朱康等译,第230页。,德勒兹用一种异质联盟取代有机、系统、结构的观念论联盟。最终,这种异质性将“还原为一根抽象的线(ligne),一根线条(trait),以找到自身和别的线条无法辨识的区域,以个别性(l’heccéité),即造物主非人格性的(impersonnalité)方式进入”⑤雅克·朗西埃:《词语的肉身:书写的政治》,朱康等译,第221页。现代文学,形成一种特殊的风格。所以,德勒兹以反再现、反叙述的方式赋予文学生成性,他拒绝塑造典型,告别父亲榜样,模糊人物特征,消解人物性格,形成一个非叙事、非交流、无意义、无深度的“形象”,一个面目模糊的匿名者,将人从组织化、中心化的理性体制中解放出来,进入一个感觉释放、肉体复活的世界。所以说,文学的特殊性不在于他律,也非自律,而是具有一种表演性。
朗西埃期待的未来文学与德勒兹相同,即切断文学表达的确定性,语言不再为叙事、再现、抒情服务,不再困顿于密闭的自我循环系统,而是在外界思想中任意流传,流向那不知名的所在,流向“无人称”且“沉默”的生命。沉默的言语是居无定所的孤儿式言语,逃离了父亲的法则、权威和掌控,它无依无靠,恣意生长,随处游荡,破碎散漫。正如柏拉图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时认为语言自由暗含着不惧权威、不受规训的因子,它挑战了城邦的秩序,破坏了原有的系统,拥有一种实现民主的潜能。⑥柏拉图:《理想国》,张竹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304页。这种游荡的语言是越轨的、非法的,它的出现总是稀奇古怪、无法预料,不符合身份、场合,不挑选时间、语境,它没有原因,漫无目的,不需要讨好谁、教化谁,无法承担意义的重任,让一切确定的、固有的东西都变得飘摇未知,它意味着中断、碎裂、逃逸。沉默的言语不是意义之间的彼此传递与无限衍生,而是符号的毗邻,“意义变成一种‘沉默’的符号与符号的关系”①Jacques Rancière,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19.。这与德勒兹的观点惊人的一致,在《差异与重复》中,德勒兹谈道:“逻各斯碎裂为一个又一个难以理解的符号,每一个符号都讲着一种能力的超越性语言。”②Gilles Deleuze: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Paris:Presses Univesitaires de France,1968,p.190.朗西埃深受意大利政治哲学家维科(1668—1744)的影响,维科在《新科学》中提出言语(speech)源于逻各斯(logos)的演变,而“在希腊,寓言(fable)也被称为神话(mythos),它来自拉丁文的mutus,即沉默(mute)。因此,言语作为一种精神语言诞生于无声的年代”③Giambattista Vico,New Science:Principles of the New Science Concerning the Common Nature of Nations,trans by David Marsh,Harmondsworth:Penguin,2001,p.157.。维科批判了将逻各斯等同于理性的这一常识,他指出逻各斯最早融合在神话和感性之中,诗人无法区分感性与理性、虚构与真实的边界,沉默就是诗歌没有从生活和神话的具象思维中独立出来的状态。
基于此,沉默的言语呈现的是一种被远离理性、杂乱感性、不合规范,进而被遮蔽、被忽略、不可言说的言说,正是这种飘忽性、流浪性构成了艺术的解放,这种艺术不服从任何权力,不规定受众等级,不用单一的模式解释世界,这才是解放的艺术、大众的文学。沉默的言语总是含混不清、肆意蔓延,它挑战着文学的边界和范式,使自亚里士多德确立的再现等级崩溃,阐释文学的范式失效,让诸多不可见的、不被认可的部分进入了文学,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分逐渐模糊。在朗西埃看来,这就是文学艺术走向美学体制的结果,在这一体制下,文学写作就是在重新审视、突破各种界限,力图对既定可见性、可思性、可能性的不断僭越和重新配置。
(二)反思德勒兹:一种新的民主
朗西埃认为:“巴特比通过将‘不愿意’这一执着肉身化(incarnant),宣布了意志向无效意志[volumé de néant]的巨大转变。”④雅克·朗西埃:《语词的肉身:书写的政治》,朱康等译,第231页。德勒兹对巴特比的论述体现了他的延异、游牧思想,期待文学可以一劳永逸地刺穿表象的高墙,通过创造友爱的政治建立一个平等的、自由的世界。然而,朗西埃对德勒兹也有微词,他认为德勒兹描绘了一个伟大的自由的世界的图景:“一个‘过程中(的世界),群岛’,上面住着友爱的个体:‘一堵由自由的[libres]、没有用水泥固定的石块砌成的墙,其中的每个元素都有独立的价值,但这价值又是通过与其他元素的关系体现的。’”⑤雅克·朗西埃:《语词的肉身:书写的政治》,朱康等译,第238页。在朗西埃看来这既是德勒兹制造的最宏大、最强烈的图景之一,也是最奇怪的。因为石块还是建基于父亲的法则之上的,德勒兹将这条道路的尽头描述为一堵墙,一堵由自由的松散的石块集合在一起形成的墙,作为新的友爱的世界秩序的图景。⑥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第183页。但是,父系律法怎能同自由的、分属于各个独立石块的墙所共容?朗西埃认为德勒兹试图借助巴特比的面具摆脱父系律法,开辟众声喧哗、友爱平等的开放之路,但这可能仅仅是德勒兹思想的“愚人节”,它无法承担起反抗父系社会的真正使命,德勒兹从文学走向抵抗的政治是无效的。⑦雅克·朗西埃:《语词的肉身:书写的政治》,朱康等译,第241页。
于是,朗西埃提出了“行动的书写”,他把写作论述指向一种把“沉默的言语”(mute speech)转化为实践行动的期望。他认为,“文学的政治”就是“说出一切、言语过度和某种政治社会状态的关系”⑧雅克·朗西埃:《文学的政治》,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3页。,所以说,“文学必然是政治的,因为通过文学,感性得以重新配置,既定的政治秩序被打乱了,不可见者变得可见,不可听者变得可听,文学的过程是感性重新配置的解放过程,是不断追求平等的民主过程”⑨郑海婷:《论雅克·朗西埃的文学介入观》,《东南学术》2015年第4期,第154页。。朗西埃以福楼拜为例,福楼拜认为“任何东西,任何题材,都可以做成艺术品”①福楼拜:《福楼拜文学书简》,丁世中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第29页。,他以外科医生的手法,客观冷静、不露痕迹地穿梭于各种叙述视角、时态和语境,模糊作者语言与人物语言的界限,混淆了叙述者、隐含作者、小说人物的声音。在他笔下,词语平等,题材自由,人、物、事被平等呈现,没有特权,不设等级,这是一种彻底的民主视角,人物、风景自由显现,他拒绝任何政治介入,不受制于任何“主义”,不从属任何流派,使其作品成为言说自由的民主场域,让沉默的言语获得最大的表达权限,在他的小说里,平平无奇的农家女可以成为小说的主角,普通物件、惯常风景可以被隆重、细致地描写,石头、草地、阳光、雨露等静默之物都获得了一种可见性。可以说,沉默的言语既是平凡之物又是异质之物,朗西埃将石化与抵抗(résistant)联系起来,法语的“抵抗”也具有顽固、不顺从的含义,故沉默且坚固的石头的被动抵抗与人的主动抗争形成互文,因而具有了抵御、解放的色彩。石化风格背离“高贵的艺术”准则,解构诗学的等级,让暗淡的、遮蔽的元素被看见,进而呼唤一种新的未来的文学。可以说,朗西埃看到了德勒兹理想愿景的脆弱性,试图采用一种介入式的书写,批判等级、权威,制造空白、断裂,只有这样不被看见的世界才有机会浮现,真正实现民主、平等与解放。
四、未来的文学:“少数”“悬置”与“沉默”
事实上,文学创作比社会实践更具探索性和先锋性,真正的书写应该大于被书写的事物,它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可以对感性世界进行预先判定和有效修正,先锋的文学也不只是可读的,而是预言着在真实世界中未曾出现的行动逻辑,召唤着人民及庆典的来临。在这一点上,德勒兹、阿甘本、朗西埃殊途同归,他们认为真正的文学是“少数”的、“悬置”的、“沉默”的,这三个词彼此互文,都指向一种蹩脚古怪、言不及义的语言,一种断裂破碎、歧义丛生的写作,并挖掘其中潜藏的巨大颠覆力和革命性,共同指向一种即将来临的、未来的文学。
(一)“少数文学”的先锋性
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少数”并非是一种数目上的多寡,而是没有类型、不建模式、不再现人性,是尚未辨识、正在生成、处于游牧状态的一种无限的多元体,所表达的是一种风格、一种装配;而多数文学表达普遍主体,再现故事情节,“多数”是一种已成型的标准或规范,意味着主导性、优先性、本源性。在这个意义上,少数背离标准和规范,处于边缘,默默抵御着多数的暴政,为了保持作为少数的特性,它不断地选择逃离多数的主导和控制。
少数文学最大的特点是语言解域化,相较于“正确”的言说,巴特比句式词汇贫乏,语法怪异,是无意义的自说自话,如同《变形记》中没有成型的音乐,只有声响,无论是大甲虫的尖叫、妹妹用小提琴拉出刺耳的声响,甚至儿童语言般的呢喃重复,都是一种不合常规的、解域化的语言,在这里,词语以陌生、变形的方式逃离权力的掌控,具有一种革命的能量。少数文学的人物常常缺乏鲜明个性特征,梅尔维尔不去描写反抗社会的英雄,而总是关注在国家、社会机器的钳制之下艰难存活的喘息和哀鸣,他们是挣扎在逃逸线上的异样的、弱小的群体,少数文学的人物都具有精神分裂,展现了人的欲望面对巨大的国家机器和科层体制开拓出的一条逃逸线。父子之间的矛盾也是巴特比的主题之一,它打破理智的秩序,突破家庭等级,摆脱父亲的阴影,逃离社会编码,是一种“反俄狄浦斯”的行为。可以说,巴特比句式从辖域化的秩序中脱离出来,敞开一片多元的、差异的、纯粹强度的生成领域,其欲望书写是对主导性的文化符码体系进行的革命性解码。德勒兹认为,“坚硬线的关键词是‘切分’(coupure),句法是‘我应该……’,存在着界域化与编码化的危险,导致了生命的枯萎与人生的乏味;柔韧线的关键词是破裂(fêlure),句法是‘或者……或者……’,虽具有相对的解域化,也总是存在再域化的危险,出现微—俄狄浦斯情结化、权力的微—构造、微—法西斯主义;逃逸线的关键词是‘断裂’(rupture),句法是‘我情愿不……’(I would prefer not to…),虽具有绝对的解域化,但有可能发生最糟糕、最僵化的节段化,存在着毁灭的极端危险——‘变成消除、摧毁、他者与自身的线’”①可参见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修订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46页。。事实上,真正的文学不应该局限于交流和再现,而是向不确定的意义、多重层域的潜能敞开,文学的先锋性也恰恰是刺破、逃逸、僭越和向着非知、危险敞开与探索。
(二)文学的暂停与不作为
德勒兹认为,巴特比句式打开了在“是”与“不是”之间构成的不可识别的区域,而阿甘本将巴特比句式与怀疑论者的“no more than”(既不是也不是)句式进行对比,这两个句式不谋而合,也就是说,怀疑论者的语言只表述现象,没有意见、观念的渗入。如同信使,仅携带信息而无任何添加,语言从命题、断言转变为一种宣告、记录,把自身维持在“谁也不更”的悬置中。当一名怀疑论者说出no more than 的时候,只是表述性地宣布了一个事件,在对no more than 的猜测中,语言只是它自己。巴特比句式有着相同的逻辑,巴特比句式打开了肯定与否定之间构成的区域,它不指涉任何事物,不做任何判断,是一种暂停的状态,这种暂停即潜能,潜能不肯定,也非否定,不归于存在,也非不存在,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潜能从二元对立、意义与理由中解放出来。
基于此,阿甘本认为巴特比的尝试是一个解构真理的实验,他用偶然性(contingency)来描述存在和非存在。关于过去的真理不是发生或不发生的必然,而是在两种可能性发生之前,这个事件可以发生也可以不发生,每一个潜能的实现意味着其他一些事情的无法实现,这也是巴特比停止抄写的原因:永无休止的抄写也会废止不存在的潜能。巴特比句式即潜能,它可以存在,也可以非存在。过去可能是本应该发生却没有发生或者是本没有发生实际却发生的无差别区域,在这个意义上,过去保持了它的潜能。阿甘本试图在二元对立之外寻找一个失效、悬置、不作为的空间,不作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为一种新的可能留出余地,不作为是实现潜能的手段,不作为为一种新的可能性开启了道路,让存在的事物恢复其潜能,使新的方式成为可能。
(三)文学的“石化”力量
同样,朗西埃也反复强调空白、虚无的价值,当柏拉图认为书写的文字对逻各斯而言只是一种略显苍白的表述,朗西埃却说“被书写的文字就像一幅无声的画,它在自身的躯体上保持着这些运动激发了逻各斯的活力,并把它带向了它的目的地”②雅克·朗西埃:《语词的肉身:书写的政治》,朱康等译,第7页。。基于此,朗西埃认为真正的文学不是“活的言语”而是“沉默的言语”。“活的言语”指意义明确、准确接受、合法传递的语言,比如授教、布道、动员、宣讲,而“沉默的言语”的言说者不合秩序,脱离常规,它处于边缘、少数、无法言说的境地。沉默的言语犹如聋哑的人群,又如无言的石块,借助肢体动态、咿呀作响、历史痕迹进行言说,所以文学不是直接呈现,而是由寓言、缺席、暗示、沉默、不可言说构成一个虚无的空间和一种不可见的空白。维科谈到“任何石块都可以成为语言”③Giambattista Vico,New Science:Principles of the New Science Concerning the Common Nature of Nations,trans by David Marsh,Harmondsworth:Penguin,2001,p.33.,石头无法诉说,但它已然见证,建立在活的语言基础上的文学分为两种,一是遵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法则,二是遵循“文以载道”的他律法则,而未来的文学只有在沉默的言语、在矛盾的冲突中才能生成。未来的文学表述不再现、零碎而非整体、漫溢却无结构,它凭借万事万物发出声音,又将自己隐匿其中,它是石块般的物质生产,而非纯粹的精神追寻。原本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无意义的沉默的言语,在朗西埃看来正因为不被共同体秩序所承认,沉默的言语才有了脱离秩序、四处流浪的可能,这一僭越的特征反而赋予沉默的言语反叛和颠覆的力量。
结语
综上所述,巴特比拒绝命令时使用肯定的非谓语动词来替代否定谓语动词,他从反抗的政治走向一种不作为的政治。反抗的政治立足于它所否定的事物,而不作为的政治不肯定,不否定,制造了一种断裂与空白,开辟出一个模棱两可、无法确认的空间,使原有的逻辑链条、表意体系停顿了,正是这种不作为被解构理论家看作是悖离同一、重现差异的契机,这一思想影响深远,当代著名批评家齐泽克(1949— )就认为巴特比传达出一种全新的政治学理论——“减法政治”。将全部的质的差异转化为纯粹的形式上的最小差异,不作为的形式却是彻底的拒绝。“我宁愿不”可以被称作建设新秩序活动的一种武器,巴特比政治的逻辑就是从某物(something)向空无(nothing)的转移,为新旧事物的更替制造了一个空隙,新事物才有可能取代旧事物。①斯拉沃热·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97页。“减法政治”意味着与反对之物保持距离,暂时撤离,伺机而动。然而,解构思想的温和反抗受到左翼激进思想的质疑,当代理论家哈特(1960— )、奈格里(1933— )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认为,巴特比把脑力或语言都降低到一种纯粹潜能的位置,而他们更需要“创造一种新的社会机体,这种方案需要超越(巴特比的)单纯的拒斥。我们的逃离路径需要的是一种构成性的、能够带来一种新的替代性选择的方案”②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Empire,London,Engl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04.。以革命的视域考察巴特比的反叛就显得微不足道。解构思想并不想延续反抗与否定的思路,这是同一逻辑的两个极端,它试图逃脱这一逻辑,寻找新的可能,理论家寄托于逃逸、潜能和沉默,至于它们是否有效,都交给未来,交给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未来的文学极具先锋性和使命感。这不是理性认知,不是超验想象,而是人与万物相通、秩序化为碎片的场域,也只有在差异、繁复、动态潜能中才能获得一种新的可能。
——透析阿甘本的弥赛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