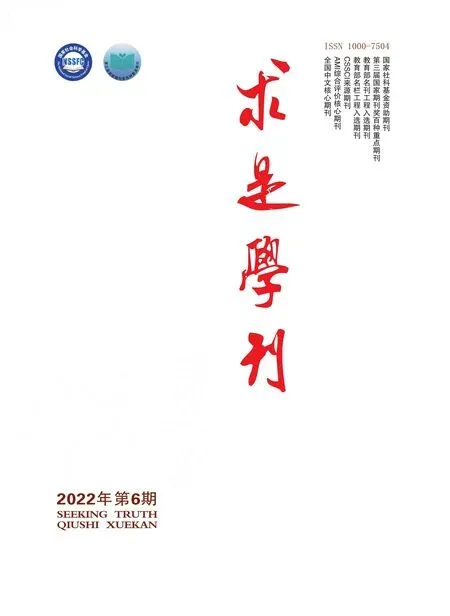中国“反家庭暴力”话语实践变迁及其逻辑
赵树坤,胡艾雄
引言
有研究表明,在1990 年以前的中国,发生于家庭内部具有暴力特征的行为被概括性地描述为家庭生活中的“矛盾”“纠纷”①参见卜卫、张祺:《消除家庭暴力与媒介倡导:研究、见证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59页。,法律中也缺乏关于“家庭暴力”的明确定义。直至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提出了“妇女与暴力”议题,以“家庭暴力”为主题的讨论使此概念得到广泛关注。会后制定并发布的《北京行动纲领》,第一次明确将家庭暴力定性为侵犯人权的行为,并通过其传播逐渐渗入人们的日常认知。在此过程中,“家庭暴力”的概念常与女性遭受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妇女组织的行动对于建构这种联系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反家庭暴力”立法初始过程中,女性视角和倡导占据主导。然而,随着制度化进程的推进,女性视角却逐渐被隐去了。“家庭暴力”被解释为对更广泛受暴主体的侵害,反家暴应当从人权理念和社会性别视角出发,是对所有受害者都应予以解决的问题,以此才能建立平等的新型家庭关系。②参见《〈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及说明》第一条、第二条、第十条,http://iolaw.cssn.cn/flfg_99/mjjyg/201007/t20100709_4607132.shtml。时至今日,《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近七年来,女性无疑依然是家庭暴力最突出的受害群体。反思“反家庭暴力”制度进程中的女性视角和话语的隐退,作为探寻女性免于家庭暴力困境的另一种思路也许是有价值的。
福柯对“话语”的描述与阐释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分析视角:“话语”蕴含的不仅是文本中对概念的描述,更可呈现为词语自身的内容、与词语相关联的其他主题甚至是主体对词语的“反馈”——运用词语进行的叙述。他认为“话语是一种变换主题的概念游戏”①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1页。。在《知识考古学》中,概念、陈述、范畴及其相互作用与变换确定了“话语”的范围及其对人运作模式,因此分析话语可以成为认识并尝试重塑主体的一种可能途径。“陈述”②福柯通过将陈述与命题、句子与语言行为的方式进行比较确定陈述“更纤小、更不具规定性、结构更不严谨”。命题、句子和语言行为受语言形式法则限制,对陈述的研究则要摆脱这种被形式法则定义的模式。陈述是使各种符号存在的功能,这些符号既可以是语言符号,也可以是非语言符号。作为话语的原子,其内容将为作为整体的话语划定范围。“反家庭暴力”立法中的“陈述”,除法律条文外,亦有专家学者对词语概念范围的阐释与探讨,并延伸至法律颁布后适用过程中的判定、取舍。立法“陈述”依据一定规则③福柯认为“陈述”的规则包含:对象、陈述方式、概念和主题四个方面。关于“陈述方式”,罗清在其论文中详细分析并阐释了《反家庭暴力法》诞生过程中民间组织、妇联和国家三类主体形成的不同立法叙事及立法过程和文本的互动,三个主体的叙事交汇、绾合体现一种符合社会需求的“复合性”话语结构,因而本文在此问题上不再赘述。参见罗清:《中国〈反家庭暴力法〉诞生中的三重叙事》,《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1期,第205页。被组织为整体意义上的“反家庭暴力”制度话语。本文拟以“反家庭暴力”制度话语实践为主要分析对象,考察制度“陈述”中体现的表达“对象”之间产生的中断及其发生的转换;透过追问对象中断及其转换背后的逻辑,揭示“反家庭暴力”话语实践变换所体现的性别文化与无意识权力结构。
一、以女性视角为起始的“反家庭暴力”话语实践
1995 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将家庭暴力作为重点议题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纲领》,认为私生活领域的家庭暴力属于性别暴力,并第一次非常明确地将家庭暴力定性为侵犯人权的行为,呼吁各国积极履行制止家庭暴力的国际法责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进行反家庭暴力研究与倡导的公益性机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北京成立。“2000 年6 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陈明侠研究员等人的推动下,一个名为《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的课题项目开始运行。该课题运行三年后,课题组正式被扩展为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以下简称“反家暴网络”),反家暴网络成了一个有全国影响力的公益机构。这个机构整整运行了十年,最终成为中国反家庭暴力非政府组织的民间代表。”④罗清:《中国〈反家庭暴力法〉诞生中的三重叙事》,《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1期,第189—190页。十年间,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于2003 年和2009 年分别向“两会”提交了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专家建议稿。在建议稿的说明中强调“从人权理念和社会性别视角出发”⑤《关于〈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的说明》,中国法学网,http://iolaw.cssn.cn/flfg_99/mjjyg/201007/t20100709_4607147.shtml。以确定立法原则。可见,“家庭暴力”首先是作为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进入公众视野的;在民间代表的推动下,原来被界定为私生活领域的家庭暴力,其本质逐渐被确立为基于性别的系统性暴力。以性别视角解读“反家庭暴力”概念开始进入公共决策和立法实践。
而政府层面的家庭暴力治理,其核心意向同样是伴随着女性议题而被表达出来的。2002 年5 月,国务院发布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 年)》,首次提出“预防和制止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2011年7月,国务院发布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推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立法进程”①《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具体表述为:预防和制止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推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立法进程。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自觉抵制家庭暴力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受家庭暴力侵害妇女的自我保护能力。完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多部门合作机制,以及预防、制止、救助一体化工作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1995—2005 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其中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在中国2.7 亿个家庭里,约30%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实施暴力者有九成是男人。”②于东辉:《〈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建构的思考》,《法学杂志》2007年第4期,第57页。显然,女性是“反家庭暴力”话语实践中的核心主体。
二、“反家庭暴力”制度化进程中的话语变迁
(一)受暴主体陈述上:“女性”的核心地位被“家庭成员”所替代
早在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便将家庭暴力界定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引起一定伤害后果的暴力行为”,但对于家庭成员的范围、构成,并未进行详细的界定。2009 年专家建议稿关注到了以保护女性为起始的“反家暴”行动,将未婚同居者、恋爱者或曾有配偶关系者纳入法律保护范围。该专家建议稿的说明中亦强调家庭暴力中的受暴者多为男性以外的群体,并用妇女权利的各类宣言及行动纲领佐证立法的必要性。专家建议稿中受暴主体范围的扩大,目的正如反家暴网络的推动者陈明侠教授所说:“在讨论家庭暴力概念的时候,应将‘家庭’的概念扩大一些,考虑到‘差异’和‘多元化’的社会现实,才能认识到在一切形式的家庭中防止对妇女的暴力和对妇女剥削的必要性。”③陈明侠、夏吟兰、李明舜等:《家庭暴力防治法基础性建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同时,该专家建议稿说明中的解释也值得注意:“因为这些人之间都有难以割舍的感情,爱恨情仇相互纠葛,其间所发生之暴力问题极为类似,需要相同或类似之保护与防治措施。”④《关于〈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的说明》,中国法学网,http://iolaw.cssn.cn/flfg_99/mjjyg/201007/t20100709_4607147.shtml。一方面,专家建议稿扩大了传统家庭成员的范围;另一方面,其将暴力发生的场域建立在“难以割舍的情感”基础上。由此可见,起草者对“家庭”的广泛定义是“为了保护遭受各种形式的暴力的女性”⑤罗清:《中国〈反家庭暴力法〉诞生中的三重叙事》,《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1期,第191页。;而将“情感”作为家庭维系的主要纽带,这种认知无疑符合人们对女性注重情感的传统印象,但将“情感”作为对受暴女性投入更多关注的证明,这将强化女性因情感而对家庭有更强依附性的判断。有关女性的这种“判断”或“描述”,后文将进一步讨论。
2014年的征求意见稿将家庭暴力的发生范围重新限制于家庭成员之间,并对家庭成员作了狭义解释,“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当然,在征求意见稿的讨论过程中,的确有专家学者仍建议扩大受害者群体范围,例如“对于恋爱同居关系、前配偶等发生的暴力参照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的规定;对于养父和养女之间的性暴力、家政服务关系中的暴力,以及女婿对岳父母、儿媳对公婆的暴力,准予参照家庭成员的暴力执行”或“对比《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建议对家庭成员的保护延伸到家政工、同性家庭的成员和室友”⑥王灵:《〈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座谈会会议综述》,《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5 年第2 期,第62页。。在征求意见稿的座谈会上,部分学者的意见体现了对多元社会关系的回应,对受暴主体认知上的更新。但在征求意见稿的正式文本中,起草者最终克制地对“家庭成员”进行了明确列举。与此前专家建议稿中以“情感”为标准类比家庭的做法不同,征求意见稿中的“家庭”尽量保持了与此前立法表述⑦当时适用的《民法通则》及其解释有关“近亲属”的一般规定,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的一致,从其列举的范围看,界定受暴主体时女性不再是被投注更多关注的对象。
2015 年《反家庭暴力法》正式通过,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被确定为“家庭成员”,但并未做列举。同时,在附则中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相较此前以某种标准来对“家庭成员”进行扩大解释,正式出台的法律规范则更为审慎、克制。这样界定的理由是考虑到家庭暴力的受暴主体应从中国国情、民族传统影响下的社会普遍认知出发,例如夏吟兰教授认为,“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与现行法律的衔接以及公众的接受程度,直接将前配偶以及具有或曾经具有恋爱关系、伴侣关系、同居关系者均纳入家庭成员的范围,既不符合法律概念的抽象概括原则,不符合中国的法律体系逻辑,也难以被公众所理解与接受。可以考虑将他们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视为家庭暴力”①夏吟兰:《家庭暴力概念中的主体范围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5期,第51页。。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也在其对《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的修改意见中回应了部分代表扩大家庭成员范围的提议:“家庭关系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制定本法要把握好公权力介入家庭关系的尺度,要考虑当前社会的普遍认知和接受程度。”②2015 年12 月27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报告。如此,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社会整体对“家庭”的认知基本贯穿了法律体系中对“家庭成员”的界定,始终是基于法律确认的血缘或婚姻关系来确定成员间的关系。而立法进程中所关注到的多元化社会关系,仍然被认定为属于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不纳入家事法领域进行调整。
《反家庭暴力法》最终文本对受暴者主体范围的界定,明显将性别因素隐去,而采用了传统的家庭视角。可以说,该法采取了性别中立的框架,对应着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运用了去性别化的话语,它强调男性和女性一样都会遭受家庭暴力,旨在突破“家庭暴力即针对女性暴力”印象的局限性。当然,有人可以辩称,女性可作为“家庭成员”而得到“保护”。但立法中的性别中立框架会掩盖女性作为家庭暴力主要受害者的社会现实,从而可能影响国家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干涉效果。“反家庭暴力”受暴主体的陈述,经历了从女性、家庭中的女性到家庭成员的变迁,这既可解释为对家庭暴力现象认识逐渐全面的过程,也是立法进程中女性视角逐渐隐退的过程,“家庭”成为法律规范“陈述”的主要对象。
(二)“家庭暴力行为”陈述:由多样到被窄化
2001年4月《婚姻法》修订,首次将“家庭暴力”作为离婚的考量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在同年12月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中将家庭暴力解释为:“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其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都有关于“家庭暴力”的规定,但仅作为概念出现在法律条文中。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仅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虽然该表述明确指向保护对象是“妇女”,但这是该法律以妇女为保护对象的逻辑结果,无法推导出“家庭暴力”定义上的女性视角。同时,这一规定仅在于宣示,缺乏对行为的具体界定与解释,给出的可分析信息太少。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家庭暴力”同样仅作为禁止性规定所列举的行为出现,缺乏对其的具体解释。
2009 年的专家建议稿参照妇女权利国际公约与宣言,采用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原则,将家庭暴力行为确定为:“损害身体、精神、性或财产的行为”③《关于〈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的说明》,中国法学网,http://iolaw.cssn.cn/flfg_99/mjjyg/201007/t20100709_4607147.shtml。,并对行为类型、方式进行了详尽列举,目的在于尽可能广泛地保护遭受各种形式暴力的女性。但2014 年的征求意见稿又沿用了《婚姻法解释(一)》中对“家庭暴力”的表述,将范围限制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在征求意见稿说明中,将家庭暴力行为解释为“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的身体伤害、精神伤害或者身体、精神双重伤害”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相较于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仅保留了身体暴力与精神暴力两种行为类型,将精神暴力纳入家庭暴力范围是其亮点所在,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观念的认识。而关于“性暴力”与“损害财产”的行为,立法机关认为与我国国情尚存在差距,对此两种类型作为家庭暴力社会整体上尚未形成普遍共识。这一立场最终延续到反家庭暴力法最终文本,仅将家庭暴力行为界定为身体暴力与精神暴力。但相较于征求意见稿,反家庭暴力法终稿在“身体、精神”后添加了“等”字,为法律适用预留了裁量空间。同时,对具体行为方式进行列举后的“等”字,亦为其他的暴力形式提供了司法上确认的可能,例如,反家暴领域中已出现具备多种暴力特征的“胁迫控制”(coercive control)模式。②胁迫控制是一种长期的、有计划性的动态行为模式,是伴侣中的一方通过多种方式建立起对另一方系统性支配的行为策略。控制者所使用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辱骂、恐吓、孤立、身体/性暴力、威胁、惩罚、微观管理、跟踪和经济控制。参见吴小沔:《关注亲密伴侣间的权力:胁迫控制研究述评》,《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6期,第45页。
关于“家庭暴力行为”的陈述与前述确定“受暴主体”的逻辑近似。《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暴力行为范围的划定更多基于我国现实国情的考量,以及克制的立法态度。尽管专家建议稿从性别视角出发,在描述“家庭暴力行为”时坚持了性别上权力与控制的特征,但这一特征在后续的立法过程中被消解。尽管性别平等与女性权益保护也许是国家立法机关立法时考虑的因素之一,但从全局把握“家庭暴力”的根本,考虑家庭暴力行为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的影响,始终是立法者最看重的。如果扩大“暴力行为”的范围,有可能破坏“家庭”内的固有规范,进而影响社会原有秩序。这种担心或忧虑进一步反映在法律实施层面。即使法律条文为司法机关补充家庭暴力行为的话语叙事预留了空间,但大多数司法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问题时,仍将社会和谐稳定的判断置于女性视角的保护价值之前,法院很少在判决中认定家庭暴力行为,致使受害者利益未能得到充分的保护。③贺欣:《司法为何淡化家庭暴力》,《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第7页。
(三)“请求-回应”模式主导的“家庭暴力处置措施”陈述
2001年《婚姻法》修订,在离婚相应条款中对“家庭暴力”救助与责任承担进行了明确表述,④参见《婚姻法》第四十三条: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其中关于“家庭暴力处置”,形成了包括居委会、村委会及当事人所在单位的多种处置主体、“受害人请求-相关部门回应”的处置模式。
2009年的专家建议稿基于社会性别理念将立法重点放置于对家庭暴力的预防上,形成预防与早期干预相结合的机制。处置主体以政府为主导,并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并规定设置反家庭暴力委员会作为协调机构。这一构想坚持不仅要通过宣传和倡导来营造对家庭暴力采取“零容忍”的社会氛围,采取综合措施改变传统文化和社会性别刻板印象,还要有专门机构进行统筹协调。专家建议稿中关于证据规则体系的规定,引入“受虐妇女综合征理论(battered women syndrome)”⑤该理论由雷诺尔·沃柯(Lenore Walker)于1979 年提出,以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表现的特殊心理和行为模式的分析来解释其自愿处于一段暴力关系并对施暴者产生依赖现象的原因。但该理论存在对女性固有受害者形象的描绘,即一种感性、柔弱的刻板女性形象,若司法实践中出现强势或理性的受暴女性,就可能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帮助。同样基于女性视角,一方面明确了“受虐妇女综合征”的认定标准,另一方面认定其可作为“减轻受害人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事实情节和证据”⑥《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第八十七、八十八条。。
而征求意见稿则将反家庭暴力认定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处置主体涵盖国家社会中的各层级机构,即所有处置主体都应对受害人的投诉、求助进行及时处置、回应。与专家建议稿中处置主体的主动预防、提前介入的机制不同,这是对先前立法中“请求-回应”处置机制的复归,其原因被明确解释为:“毕竟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具有特殊性,需要明确公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方式。”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换言之,征求意见稿中的“家庭”关系仍被认为是属于私人关系,即便其有一定社会危害性,启动对其处置的机制仍需以“个体请求公权力介入私域”为前提。
这一话语叙事逻辑在《反家庭暴力法》终稿中被更加直白地表述出来,其第1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制定本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处置措施最终守护的是作为整体的“家庭”。而关于处置主体的具体条文表述,虽然也包括了“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但前提却很明确,要求“家庭成员之间应当互相帮助,互相关爱,和睦相处,履行家庭义务”。由此可见,家庭的稳定秩序在于其内部的自我协调,首要的处置责任并不在外部的引导、干预和建构。另外,相较专家建议稿,《反家庭暴力法》终稿具体条文中虽然规定了主要处置方与协助方,但并无统筹合作机构,这使得实践中反家暴各机构间权责不明、流于形式的困境明显。最后,《反家庭暴力法》终稿对家庭暴力行为者的责任认定上,只是对既有法律规范做了援引性规定,如强制报告、告诫令、临时安置、人身安全保护令等制度规定,且都比较原则,将难题留给了实践。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出台的过程,女性视角逐渐被消解,而被取代为一种中立的性别立场;从以性别结构分析家庭暴力产生根源的倡导阶段开场,却以保护“家庭”作为私域的完整性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叙述收场。法律最终预设的是平等的两性权力结构,性别之别被《反家庭暴力法》共同表述为“家庭成员”。而“家庭”的主要角色依旧是女性的“庇护所”,相应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所建立起的不过是“保护女性”的外在机制,作为补充性的角色。同时,在立法文本中也很难看到“女性”或具有“主动性”的权利话语,可以说,制度话语内部的对象转换整体上已经完成。
三、“反家庭暴力”话语实践的对象转换及效果
(一)从“女性”向“家庭”的转换
“反家庭暴力”制度话语的主要转换,即“家庭”替代“女性”,且这种转换看似自然而然,是通过名为“感情”的纽带来完成的。如前所述,专家建议稿的说明所呈现的,将“有难以割舍的感情,爱恨情仇相互纠葛”②《关于〈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的说明》,中国法学网,http://iolaw.cssn.cn/flfg_99/mjjyg/201007/t20100709_4607147.shtml。作为判断“家庭”范围的参照。虽然在后续的立法陈述中没有再看到有关“感情”的表述,但“感情”作为话语中的重要概念仍发挥着它的作用——维护女性的“感情”需要,当然应该保护寄托着女性“感情”的家庭。安妮·K.梅勒(Anne K.Mellor)在《浪漫主义与性别》中将浪漫主义时期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珍惜家庭价值、情感价值作为崇高审美新维度,认为女性“自然”地看重“家庭”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并将其称为“家庭化的崇高”③Anne K.Mellor,Romanticism and Gender,New York:Routledge,1992,p.103.。“感情”之于女性类似于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集体期待”,这种期待成为人们熟悉的环境构造并一再被确认:男性擅长在公共场合运用理性与女性需要在家庭中满足情感,理性与感情的标签正是公共场合与家庭的对立,即男性公共空间与女性私人空间的对立。
在“感情”的问题上,“家庭”与“女性”同构,即“感情”之于“家庭”与“女性”皆不可或缺。自近代以来“家庭”便被视为贯通历史的“自然之物”,特别是近代工业社会中,家庭被视为“没有算计和功利、无私的共同体”①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9页。。在家庭这一共同体中,成员们同甘共苦,共通的“感情”使得家庭成为真正的、超越了个体单位的平等之地,拥有了外界不可介入的私密性与神圣性。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将“感情”破裂作为婚姻关系解除的重要条件,判定“家庭”完整与否的标准,背后的支撑逻辑可以说是相通的。威廉·古德(William Goode)认为,“家庭以共同生活为基础,由至少两个不同性别的成年家庭成员组成,且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劳动分工,进行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即为对方办事),共享物质活动与社会活动”②威廉·J.古德:《家庭》,魏章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3页。。即不同性别在某种“特定领域”中形成的联系及范围便是“家庭”。维系不同性别组成的家庭,守护“爱的共同体”被默认为是社会期待“女性”之“感情”实现的场所,“肯定或否定的‘集体期待’通过它们规定的主观期望,倾向于以永久配置的形式进入身体”③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8页。。因此女性对“感情”的需要逐渐被转化为对“家庭”的需要,守护“女性”向守护“家庭”的置换得以形成。
这种转换也同样反映在实践效果上。根据全国妇联的数据:在中国,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家暴,而女性平均被虐待35 次才会选择报警。换言之,女性面对家暴与面对其他暴力时,行为选择上很难同样的坚决果断,这里有太复杂的情感、亲子等多重家庭因素需要考虑。根据一项针对2017—2020年千份涉及家暴离婚裁判文书的分析报告显示,女性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暴主体(样本中离婚诉讼的受暴女性原告占比94.8%),但能提供有效受暴证据的人少(占比29.8%),而法院将案件多定性为“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而非“受家庭暴力”(占比80%),最终,法院支持离婚的判决低(占比30%)。④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研究团队:《“看不见”、“听不到”的家庭暴力——2017—2020年千份涉家庭暴力离婚判决书分析》,http://www.woman-legalaid.org.cn/news/1708.html,2021年11月25日。
(二)从“暴力”向“和谐”的转换
“反家庭暴力”话语实践中形成了对描述“暴力”行为向实现“和谐关系”的转换。“家庭暴力”是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异常现象”,它代表着两性关系在家庭领域内一种极端对立与冲突的紧张状态。即使“暴力”的形式与部分犯罪行为并无任何不同,但因其发生于“家庭”内部而被认定为私人的、个体间或性别的冲突。而个体的陈述作为私人表达或基于性别的客观差异而无法进入公共话语中。
但是,“反家庭暴力”制度话语属于个体对外公开的表达,是外界认识并介入关于性别陈述的法律依据,这使得有关“暴力”的叙述突破私密性从而成为具有公开性的表达。当急剧的性别“暴力”冲突呈现于公共领域时,其与立法隐去了性别视角、明确表达的重要价值——“和谐”发生着对峙。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一条:“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制定本法。”而制度话语对“和谐”价值的强调显然淡化了作为初始陈述对象的“暴力”。
由于“暴力”和“和谐”的陈述同时发生在“反家庭暴力”整体的话语对象内部,当性别问题、反家庭暴力理念的认识与陈述个体经历的语言交织在一起时,作为话语对象的“暴力”与“和谐”之间的转换产生了一定的相互支持与补充效果:一方面,关于这种行为及家庭内冲突状态的描述破坏着性别主体间原有关于“家庭”形成的共识与传统叙事中和睦友善的家庭秩序;另一方面,“和谐”作为制度话语中守护“家庭”的目标,在调和或消解着“暴力”本身的同时肯定着暴力的客观存在。被置于制度话语中的“暴力”进一步突破着曾经对“私人领域”的限定,具有主体意识的公开表述加入有关暴力的叙述,企图寻求话语新秩序的建立,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同时,“和谐”作为事件发生的总体趋向及立法目的之所在,使得“暴力”终将完成在立法整体话语中话语对象的转换,即从公开的场合逐渐回归私域本身,以实现社会领域的稳定。
我国在“家庭”治理实践中,同样存在着“暴力”与“和谐”的话语转换。早在1994 年2 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在“消除对妇女的暴力”一章中承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消除性别暴力,“家庭”是“经济发展的社会细胞”和抵御“违法犯罪”的场所,同时也在该章节中出现了有关“和谐家庭”的表述。①报告原文为:“多年来我国在城乡广泛开展的五好家庭活动,它将法制、道德、学习科学技术、活跃文化生活、促进家庭经济发展融为一体以优化家庭这一社会细胞,抵制各种违法犯罪。目前,全国评选五好家庭800多万个;此外,各地区评选好母亲、好丈夫,举办家庭文艺表演、家庭运动会等活动,这些促进了家庭的和睦。”到2021 年,我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颁布,这是我国迄今颁布的第四个国际人权行动计划。在其中的“预防和制止针对妇女的一切形式家庭暴力”的语段中,起始的表述是“倡导性别平等、责任共担的新型家庭文化”,换言之,家庭建构是消除对妇女暴力的“前见”。这些实践表明,一方面,家庭内对妇女的“暴力”因素无疑被政府关注到了;另一方面,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单位,应当符合和谐友爱的传统预设。毕竟,要“充分发挥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妇女成为幸福安康家庭的建设者、倡导者”②参见国务院《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发展领域、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六)妇女与家庭建设”,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9/27/content_5639412.htm,2021年9月8日。。可以说,制度话语对象的转换仍在重现着社会生活中原有的逻辑,“私人领域无论何时都可以转化成一个封闭专制的小王国。由于家庭的共同体神话的生命力过于顽强,被殴打至生命垂危的妻子即使求助,但当警察在了解施暴者是其丈夫时,他们也只是沉默而去。当遭受性暴力的孩子终于鼓起勇气开口时,大人们不予理睬或只是称孩子在撒谎而已”③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第50页。。相比要直面并斥责家庭暴力,人们似乎更希望保留家庭和谐美满的神话。
四、“反家庭暴力”话语实践变迁的逻辑
(一)“家庭”内的性别文化逻辑
家庭作为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单元,曾具有稳定的、单一形式和难以撼动的文化基础。追溯至早期儒家性别文化制度,男性贵族通过对公共空间的垄断将女性隔离于公共话语体系之外,并牢牢地限制在家庭之内,但她们仍可“以妻子或者母亲的身份间接地参与公共事务”④付洪泉:《早期儒家文化的性别制度研究》,《求是学刊》2017年7月第4期,第22页。。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中女性跨越私人领域的界限、进入公共空间之前提便是家庭中“身份”的获得。因此,无论是男性为中心的性别机制运行还是女性参与公共政治的需要,“家庭”不可或缺。
费孝通就认为:“婚姻的意义就在建立这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⑤费孝通:《生育制度》,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122页。正是在传统单一、稳定的家庭形式中,家庭里发生的事通过其自我维持的秩序机制,即婚姻家庭伦理便可解决。相应地,“家庭”作为封闭、稳定的单元,其内部长期以来的有效运转致使“不干涉”或“干涉可能导致社会结构不稳定或秩序混乱的后果”成为主流观念。“家庭”作为叙述主体,暴力在其内部机制运行的过程中被替换成如“矛盾”“冲突”等其他的表述,一方行为的后果在家庭内部的陈述中被替换为多方的责任,“暴力”发生的原因与本质在家庭作为主体话语的层面上被消解,自然地实现向“和谐”的转换。
然而,当代社会家庭形式正在走向多元化,例如,某些国家通过同性婚姻法或伴侣法确定同性组成的家庭也是一种家庭形式,传统对于两性家庭结构的运行机制不再能够完全适用。家庭成员的个人主义色彩日益浓厚,家庭作为整体的观念受到挑战,“家庭成员”很难完全被传统的“家庭”整体话语概括和解释,正如涂尔干所说:“家庭的运行取决于社会形态学:家庭共产主义的衰退,换来的是个人主义在家庭中的兴盛。‘家庭成员的个性’越发从家庭整体中脱颖而出。”⑥弗朗索瓦·德·桑格利:《当代家庭社会学》,房萱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页。尽管对家庭的认识、社会的发展都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关于家庭的认知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基础却非轻易就可撼动。性别研究揭露出“家庭”借助性别与年龄进行统治的事实,使得现代制度下最后仅有的一点“共同性”趋向瓦解。很多人抗拒自己被彻底还原成“支离破碎”的个体,作为“爱的共同体”的家庭与自然紧密联系,仿佛处于其中就可以“不受现代生活异化和碎片化的影响”①芮塔·菲尔斯基:《现代性的性别》,陈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1页。。当女权主义者触及这一“神圣领域”,揭露“家庭是披着‘共同性’的外衣而实为压迫和统治的场所时,许多人——男人也好,女人也罢,都为自己曾经所深信不疑的神话幻灭而惊慌失措”②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第49页。。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却仍然是公共领域统治及其理论难以触及或彻底改变的,制度话语对象中的“家庭”或类比家庭的亲密关系仍保持着作为私人领域的完整性。“顶着个人隐私这一‘神圣’光环,家庭得以将公共性干涉与监督拒之门外。丈夫对妻子的暴力以及孩子的虐待,都是私人领域(privatization)确立的专有产物。”③Blumenfeld.E,Susan Mann, Hidden in Household: Women’s Domestic Labor under Capitalism,The Women’s Press,1980,p.293.只有暂时从“爱的共同体”中抽离出来,关注到“家庭”内部被还原为功利主义与经济主义带来的统治与经济压榨之现实,私人“神圣领域”中的暴力与压迫才可能变得清晰可见。
(二)无意识性别权力结构逻辑
1.话语对象内部的无意识性别权力结构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男性统治的“再生产活动由三个主要机构即家庭、教会和学校完成,这三个机构在客观上相互协调,共同作用于无意识的结构。再生产男性统治和男性观念的角色无疑属于家庭;对劳动的性别划分和对这种划分的合法表象的早期体验是在家庭中被规定,这种划分有权利保障并被纳入语言之中”④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1页。。如前所述,“反家庭暴力”制度话语起始于女性视角,“女性”作为主体在其后的陈述中被转换为“家庭”,这种话语对象的转换,背后的性别结构无意识支持同样是鲜明的。
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男女有别”与“生计”是家庭内部已然存在的性别关系。“男女有别”话语指向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角色分工及等级制度,同时也暗含了包括“三从四德”在内的性别伦理。在人类历史阶段的初期,家庭关系和生产关系统一。家庭这一结构形式能够实现劳动力的固定,家庭成员之间存在初级劳动分工,他们相互配合、彼此协作,共同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基础。至近现代社会,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父权制”经济基础便是家庭内部的生产方式。家庭以性别和年龄组合而成,“父权制”决定了年长男性以外的家庭成员从事无偿劳动的事实。这样的机制使得女性在这样的地位与劳动中被“异化”:“由于父权制是从其劳动的性别原理中取得利益的,所以已婚女性形成了共同利害关系特征、超越阶级的‘女性阶级’(women class)。这种阶级的规定,使女性——家务劳动者有着从劳动中自我异化的物质基础,无论是否存在异化感,异化的事实是存在的。”⑤参见Christine Delphy, Close to Home: 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4,chap.2。Delphy谈到,社会学家认为已婚女性的分层由丈夫所属的社会阶层所决定,因为其对家庭抱有依赖性。然而,这种依赖性正说明,无论作为“个体”的女性从事何种工作,其“已婚”的属性决定她们共同具有在父权制的家庭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特征。在家庭内部被异化后的女性当遭受来自“一家之主”的暴力时,其感受到的并不一定是“暴力”,也难以意识到这是被法律禁止的行为,“她”往往将其视为普遍主义的,并且通过占统治地位的实践活动再次肯定这种定义。“现代国家将男性中心观念的所有基本原则都纳入家庭权利,尤其是确定公民身份的规则中”⑥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第124页。。
而“生计”的表达则是在以经济因素圈定家庭内部的范围,并成为女性所受到压迫的物质基础。何殷震通过列举分析我国古代婚姻制度得出“男女之关系,均有经济之关系而生”①夏晓虹:《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9页。的结论,即家庭中不掌握经济或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在婚姻中往往沦为男性的私有财产,而女性作为私有财产的历史事实成为“财富不均衡积累的源泉,并直接导致社会不公的延续和再生”②Lydia H.Liu,Rebecca E.Kaxl and Dorothy Ko,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p.22.。基于对女性无法平等参与社会生产活动原因的分析——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的过程中延续并强化了婚姻家庭中的性别权力结构,“生计”话语是对这种结构产生根源的概括。家庭“这种正式的婚姻文件并非源自性道德的原因或者任何其他感官享乐的考虑。更正确地说,这是为了适应经济方面的考虑”③安德烈·比尔基埃等:《家庭史:遥远的世界、古老的世界(第一卷)》,袁树仁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00页。。刘禾等学者在编译何殷震的著述过程中这样概括其提出的解决进路:“只有女性有能力将其劳动身体回归基本人类劳动的时候,人类才能从被权力与财富工具化的境况中获得自由。”④Lydia H.Liu,Rebecca E.Kaxl and Dorothy Ko,p.25.当规范化的家庭结构已被编织成型,物质与制度的现实,既塑造了女性与历史、现实之间关系的主导观念,也让女性被这些观念所塑造。因此,“生计”也归化为“家庭”内的物质满足或家庭成员间的财富比较。“家庭”及其内部的权力结构成为某种既定的自然秩序。
2.话语实践过程中的无意识性别权力结构
话语的实践过程意味着话语自身适应制度并产生特性的过程,最后也将产生新的“统一、特征和形成规律”⑤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第73—74页。。“反家庭暴力”制度话语在进入实践后产生的“新规律”同样受此前已存在的无意识性别权力结构影响,进一步延续并依据它形成实践层面的话语规则而发挥约束作用。目前,针对法官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中所面临的制度/结构性约束方面的研究,例如伊森·米歇尔森(Ethan Michelson)曾指出:中国法院拒绝首次离婚申请高度制度化的做法造成了对女性的不利影响,并产生了相当多的女性婚姻暴力难民。⑥Ethan Michelson,“Decoupling: Marital Violence and the Struggle to Divorce in China”,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19,Vol.125,No.2,pp.325-381,p.325.再如张剑源认为,家庭暴力难以被认定的原因除去常见的当事人举证不能以外,更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如《反家庭暴力法》条文中有关“家庭暴力”的标准、“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法官人身安全保障不足等司法实践中的共性问题,同时也包括法官对家庭暴力认知偏差等司法实践中的独特性问题”⑦张剑源:《家庭暴力为何难以被认定?——以涉家暴离婚案件为中心的实证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03页。。因为“反家庭暴力”制度话语中性别视角消解,完成话语对象间的转换为其后的司法实践提供着某种判断依据,以如下裁定中的陈述为例:
王某申请再审称……在一审起诉间,詹某又对我进行了殴打,并打砸家里物品。而此次家暴中,幼儿更是受到了严重惊吓,后经陆军总医院精神科专家鉴定,孩子已经产生了心理应激障碍。我在怀孕期间遭受了詹某的打骂,当时寻求了居委会帮助,居委会进行了拍照,并通知了詹某的科室领导。北京110 也多次出警,出警记录可以证明我遭受家庭虐待的事实,但出警记录需要法庭调取,经我多次提出,法庭未应允也未加理睬。
本院经审查认为……二审法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詹某对王某实施了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行为……⑧王某与詹某离婚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8)京民申3099号]。
由此可以看到,原告的叙述具有较为明显的性别因素,女性在家庭的抚育与生育行为都受到暴力的严重影响,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却未进行调查回应,而是严格依据立法文本中的规范进行判断,形成了所谓“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行为”的话语。产生于性别无意识的话语结构内容“再生产”了实践中的陈述:先前实践中形成的某种无涉性别的规则,在新实践中实现着话语的延续。
无意识的性别权力结构影响着“反家庭暴力”制度话语实践,它内在于稳定的社会总体结构,却使得话语呈现“去社会性别”的表达。可见,司法实践并非话语自身的实践,而是产生于社会结构整合下的基本模式在司法上的应用,而且不断按照相同模式生产,在话语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下不断加强。“反家庭暴力”的司法实践经验在每个相关的行动者的陈述中可以呈现某种持久性的构造原则,然而这种一以贯之的话语与个体表述出来的特定内容之间,偶然地也会出现话语与实践的特定距离,同时出现一种具有主体性的陈述经验。
结语
妇女权益是基本人权。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申,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要消除针对妇女的偏见、歧视、暴力,让性别平等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只有致力于社会基本结构和体制的正义建构,性别平等和公正才能真正实现。”①赵树坤:《“以人民为中心”人权理念的话语表达》,《人权法学》2022年第1期,第12页。中国“反家庭暴力”话语实践产生于女性视角下妇女权益的主张,却未能摆脱“传统的女性形象”想象,并逐渐隐去了特定的性别立场,完成于国家层面的《反家庭暴力法》的总体叙述中。制度话语实践中女性视角的退隐与立法陈述中对象的转换,整体符合性别文化逻辑,反映了无意识性别权力结构的内在束缚。要打破这种束缚,真正落实消除对妇女的偏见、歧视和暴力的权利保障实质,对于话语实践而言,依然有极大的努力空间,《反家庭暴力法》不是终点。目前,《妇女权益保障法》正在修订中。观察修法的过程,可以看到,以“全过程民主”为依托,立法者与民间持续进行的话语和沟通,②2022 年6 月1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杨合庆表示,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收到了共有80 960位公众提出300 504条意见,及近100封群众来信。使得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共存的结构之间的缝隙被进一步缩小。当偶然的个体“陈述”真正能与作为整体的话语发生联系时,真正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就可以介入,并对实践甚至是观念产生影响。毫无疑问,这是可以进一步探索并为化解女性遭受家庭暴力困境所合理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