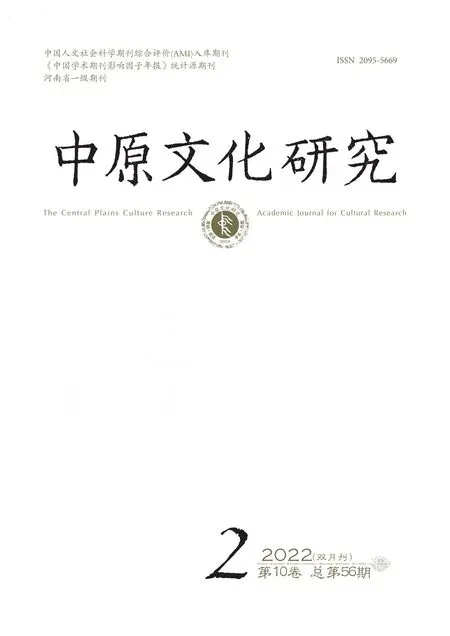由秦律中的“同父”原则看秦汉时期的亲属观念
赵心怡
近年刊布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中有这样一条律文:“廿六年十二月戊寅以来,禁毋敢谓母之后夫叚(假)父,不同父者,毋敢相仁(认)为兄、姊、弟。犯令者耐隶臣妾而毋得相为夫妻,相为夫妻及相与奸者,皆黥为城旦舂。”[1]39该律令属于岳麓秦简中秦律令简的第二部分,开篇明言“廿六年十二月”,可知本条律文产生法律效力即具体施行的时间,当不会早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十二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初并天下”[2]299,虽未提及具体月份,但十二月已是岁末,且尚未改元,故此时之法律可视为秦统一后颁行全国之法令。简文中的“假父”(整理者注为“后父”),语义不甚明晰。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亦有“假父”一词,整理者注为“义父”[3]202,《汉语大词典》亦将“假父”解释为“义父”,并引刘向《说苑》中嫪毐自言“吾乃皇帝假父也”为证,指“非本生之父而拜认为父者”。如此疏通后,律文或可作如下翻译:廿六年十二月戊寅以后,不得称母亲的后夫为假父,不同父之人不能互相认为兄弟姐妹,犯令者耐为隶臣妾,且不得结为夫妻(此处结为夫妻的对象是犯令者还是不同父者暂不确定),若结为夫妻或行通奸之事,皆黥为城旦舂①。
一、法禁恶俗:律文制定背景的考察
从法律颁行的社会基础与缘由来看,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法令或多或少会折射出该时期的社会现实,法家言圣人立法的一个重要原则便是“因时而立”。《商君书锥指·更法》云:“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4]5又在称述周文王、周武王的功绩时,赞其“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4]4,即治国理政的一项原则便是根据当下的时代环境制定与之相应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法”与“礼”有着根本的不同。汉初贾谊便论道:“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5]2252“礼”通过教化的形式将观念内化于心,而“法”则借助赏罚之明来应对具体的行为。若就习俗论之,“礼”可将某些欲形成的风气禁于未发的状态,而“法”则通过绝灭现有的“恶俗”来实现其“禁已然”之功用。因此,不难推知,秦律中对亲属称谓进行界定与规范的缘由,便是当时民间社会中存在认母之后夫为“假父”以及“不同父者,相认为兄、姊、弟”的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该条律文针对的社会现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女子再嫁后,其与前夫所生的子女认母亲后夫为假父;另一类为女子再嫁后,其与前夫所生的子女与母之后夫组建的家庭中其他子女相认为兄、姊、弟。就前者而言,“认父”情境的特殊之处在于,女子再嫁后,其与前夫所生的子女可依据母亲的婚姻关系认定其“父”。自进入父系社会之后,父亲身份的认定便以父系血缘为准,而“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6]1330便成了对久远的“太古之世”的追述。《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年②,其书所载反映了时人对于社会演进的认知,此时已经认为“知母不知父”是仅存于远古时期的情况,又何以会出现秦律中对“母之后夫”认为“父”进行禁绝的现象?因此,可以认定,民间社会的实际情况与律文所见的条令规定存在不合之处。
二、秦及汉初之基层社会重母系血缘再探
“不同父者,相认为兄、姊、弟”的情况,对女方与前夫的子女而言,与之不同父的对象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女子再嫁后,与后夫所生的子女;一类是后夫与其前妻所生子女。因此这则律文针对的社会现象为母亲再嫁组建的家庭中,其子女在认定与己身同辈的家庭亲属时,只依母系血缘或母亲的婚姻关系为准。女子再嫁的情况在秦汉时期并不少见③,而当时社会所见有关兄弟姐妹认定的实例也并非以父系血缘为唯一准则,即使并未结成正式的婚姻关系,同母异父的情况亦不在少数。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云:“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其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媪通,生青。青同母兄卫长子,而姊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为卫氏。字仲卿。长子更字长君。长君母号为卫媪。媪长女卫孺,次女少儿,次女即子夫。后子夫男弟步广皆冒卫氏。”[2]3515卫青因同母异父之姊卫子夫得幸天子而冒姓“卫氏”,足见母系血缘的重要性即使到了汉初,也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不难看出,“同母”在这一时期的亲属观念中成为衡量亲疏远近的直接标准。对此,牟润孙先生则有较为精当的认识:“当夫西汉初年,刘氏帝室及其宗族外家实未尽脱民间本色。叔孙通所定者,仅为朝廷宗庙之仪注。朝谒时,高祖见群臣震恐肃敬,领略为皇帝之尊贵,即已踌躇满志,欣然自得,未遑更进一步,彻底接受儒家所提倡之古代典制,有以整饬其家人宗族,使之成为笃守礼教之贵族。”[7]50从汉初皇室起自民间这一现象便可知当时基层社会中家庭内部对于母系血缘及亲属的重视。因此,不难推定,这一风俗亦当存于秦代社会。
三、秦汉时期的“同父为兄”观念
亲属称谓作为联结称呼人与被称者之间的语言符号,既是亲疏关系的反映,也体现了借之划分亲疏远近的思维与意识。冯汉冀指出:“决定称谓的构成的原则是语言学的和社会学的原则。从语言学来看,亲属称谓是按汉语的句法规则组成的;从社会学看,亲属称谓的语义是由其反映的亲属关系以及所处的语境来决定的。”[8]1“父”“兄”“姊”“弟”一类,都属于核心称谓,即用于称呼与己身关系最为密切的亲属。岳麓秦简律文中提及称“假父”“兄”“姊”“弟”的对象及标准,反映了通过限制亲属称谓的适用范围来划分亲缘关系的意图,亦即操控决定称谓语义的“社会学原则”来实现某种特定亲属观念的确定与推行。就本条律文而言,突出的是“同父”认亲原则,即在血缘上同父才可以认定为兄弟姐妹。
“同父者为兄弟”这一说法也见于传世文献。《汉书·元帝纪》云:“除光禄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产之令。”[5]285-286又《汉书·龚胜传》:“其上子若孙若同产、同产子一人。”[5]3083《汉书·循吏传》:“坐同产有罪劾免。”[5]3627颜师古注曰:“同产,谓兄弟也。”可见,西汉时期“兄弟”与“同产”同义。《汉书·元后传》载:“太后同产唯曼蚤卒,余毕侯矣。”[5]4018张晏注曰:“同父则为同产,不必同母也。”[5]4018故“同产”又指“同父”之人④。因此,在汉代“同父”是为“兄弟”。
综上可知,无论是秦律还是汉代史籍,皆是以“同父”原则为认定“兄弟”的标准。可见,在这一时期的官方意识里,“同父”成为确定亲属范围的一个重要原则。
四、父兄同宗:先秦秦汉文献中的父系宗亲观念
汉代经学家不仅强调“同父”者之间亲属关系的特殊性,又进一步将“同父”原则扩展至“同姓”,强调同姓宗亲之间的亲近关系⑤。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念并非到了汉代才开始出现,先秦时期便有了类似的表述。《国语·晋语》所载司空季子所言“同姓为兄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段史料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关于其解释也存在颇多争议。现将原文抄录如下:
司空季子曰:“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仓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9]237
关于这段记载,论争的焦点主要在于对文段前后表述不一致的解释,司空季子先是叙述了“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其后又说“唯青阳与仓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因此,有学者认为,此为母系社会遗俗之反映,开篇提到的“同姓”即“同生”,指同母所生的兄弟⑥。杨希枚先生以“仓林氏”“夷鼓”为同一人,以此与“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相合⑦。从文本本身来看,后文所指的青阳与仓林氏同为姬姓是由于“得姓”,而前文并没有交代青阳与夷鼓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同为“己姓”,因此简单地以从母姓或是母系血缘来解释则失之牵强⑧。此外,己姓与姬姓当为两个不同的姓,文中在列举十二姓时区分明显,且多次提及分为十二姓,当不存在书写上的误差,若己姓指黄帝所得的姬姓,便不当再和姬姓同时出现在十二姓中。因此,对于这段材料的解读,应当从其他角度加以考虑。杜正胜、陈絜两位学者提出了从氏族演变的角度进行阐释,其视角值得借鉴⑨。按照原文的叙述顺序,梳理可知:黄帝二十五子别为十二姓,青阳、夷鼓同为己姓(姓氏来源未知),十四子得姓,青阳、仓林氏得姬姓,二十五宗分为十二姓。《礼记》曰:“凡言大宗、小宗者皆谓同所出之兄弟所尊也”。大宗、小宗为西周实行宗法制后产生的概念,其共同之处在于对始祖的追认。吕思勉先生指出:“公子不得祢先君,因而别为一宗。为宗法之一义。始来在此国者,后世奉以为祖,为宗法之又一义。”[10]15司空季子此处对“宗”这一概念的运用表明,通过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这一过程,宗亲观念得以强化,继而通过“同父姓”进一步推导出“同姓为兄弟”的说法⑩。因此,先秦时期的“同姓为兄弟”与汉代重视兄弟伦理在同姓宗亲间的推及本质上若合符节,皆是通过“同父”这一原则实现对“兄弟”以及“宗”的认定,而后者又继承了秦律中出现的“同父为兄弟”的观念。可以看出,秦代的立法原则和更为传统久远的宗亲观念之间存在一致性。
事实上,宗亲观念可上溯至西周时期。谢维扬在研究周代家庭观念时指出,这一时期的姻亲在姓氏制度、亲属范围、丧服等级等方面地位均低于父系宗亲,对父系宗亲的推重又集中表现为“亲亲”“尊尊”观念的盛行。宗亲观念不仅包含父系直系宗亲,也将旁系宗亲囊括在内。《礼记》曰:“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郑玄注云:“己上亲父,下亲子,三也。以父亲祖,以子亲孙,五也。以祖亲高祖,以孙亲玄孙,九也。杀,谓亲益疏者,服之则轻。”就礼的观念来看,在世系认定上以“父系”为准,由己身推之,与父之关系越远则丧服越轻。这种礼制与秦律的一致性在于,通过一定的标准将不属于“亲”的对象剔除在外,实际上是基于自然血缘关系对亲属范围的再划分。因此,此处的“法”与“礼”手段本质上并无区别,皆是通过限制亲属范围来实现某种理念的渗透。具言之,这种理念的内涵在于对父系宗亲的重视,即以父系血缘来确定亲疏标准。
结语
自商鞅变法推行分异政策以后,秦代民间社会小家庭的数量逐渐增多,但并未成为主流。在这一实态下,家庭内部确定亲属关系时存在相当数量偏重母系血缘的现象,而岳麓秦简中“不同父者,不得相认为兄、姊、弟”的律文恰是针对这一现象做出的规定。事实上,由于西周、春秋时期“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对于父系原则的推重更多地表现为统治阶级和上层贵族的规范。至战国时代,各国变法迭起,不同阶层的流动更为迅速,在编户齐民的有效统治下,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与控制得以实现。秦代重法,也使得其推重的父系宗亲观念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传至民间。汉代经学家则进一步强调父系宗亲间的亲近关系,并将这一观念逐渐提炼和演绎而日渐理论化。
注释
①关于本条律文中“假父”的专题讨论,还可参看程博丽:《秦代妇女再嫁及相关问题研究——以岳麓秦简为中心的考察》,《简帛研究》2018年第1 期;张以静:《秦汉“叚父”称谓及“不同父者”间的关系试探——以〈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一则令文为中心》,《简帛研究》2019年第1 期;杨振红:《〈岳麓书院藏秦简(伍)〉有关女子重组家庭的法令与嫪毐之乱》,《简牍学研究》第八辑。其中,与本文论题相关的张文和杨文均认为本条关于“假父”的律令或与嫪毐事件有关,但笔者认为,仅以皇室内部的变乱为基点来论定律令制定的原因,难以证实或证伪,因此本文更倾向于认定此条律文的制定,是出于对民间社会类似习俗的规范,其背后的思想动因或存在防范类似嫪毐事件的目的,但更多地与先秦秦汉时期一脉相承的父系宗亲观念相吻合,因此并不是偶然创制,详见后文论述。②此说法由清末学者孙星衍考证提出,他认为《吕氏春秋·序意》所言“维秦八年”应从秦庄襄王灭东周的第二年(公元前248年)起算,即实际时间当为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0年)。参看吕不韦撰,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5 页。③薛洪波通过《张家山汉简》中关于夫死继承的规定“其出为人妻若死,令以此代户”推知当时的民间社会此类现象应较为常见。参看薛洪波:《秦汉家族法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④论证“同产”为“同父”者的相关论文还可参看李亚光:《“同生”同产”考辨》,《东岳论丛》2019年第3 期。而“同产”一词又可又见于《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云:“同产子,同母兄弟也。”杨鸿年先生认同此注,并以秦律中“同居”关系以母系为主的律文证明“同产”应指“同母”兄弟姐妹。参看杨鸿年:《汉魏“同产”浅释》,《法学评论》1984年第1 期。实际上,“同居”一词在出土秦汉律令简文中较为常见,学者或认为“同居”主要依据是否“同财”来判定,如贾丽英:《秦汉律简“同居”考论》,《石家庄学院学报》2013年第2 期;或认为“同居”主要强调“同户籍”,并非一定“同财”,如王辉:《汉律中“同居”及相关问题考订》,《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 期。综上分析来看,判定“同居”的条件主要是“同籍”或“同财”,与是否以母系血缘为准没有太大关系。因此,若据此论证“同产”之义,则论据不够充分。另一方面,“同产”除了作为连坐对象出现于刑律律文中之外,也多见于与继承有关的法令,当用来指代连坐对象的成员时,多与“父母”“妻子”等连称,难以辨清其具体所指,故可从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出发考察其含义。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置后律》:“同产相为后,先以同居,毋同居乃以不同居者,皆先以长者。其或异母,虽长,先以同母者。”参看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60 页。从此条律文可以看出,“同产”和“同居”是两个维度的概念,分别从亲属关系和生活状态的维度划定继承者的地位,这也与本文中所指通过亲属称谓来划分亲疏远近的语境相符合。⑤关于宗亲的概念,《汉语大词典》解释为“同宗亲属”。谢维扬参考摩尔根的叙述后指出,可以通过世系认准的亲属为宗亲,周代文献中便是以父方亲属为宗亲,母方亲属为姻亲。此说较为准确。参看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 页;(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05 页。而《史记·五宗世家》云:“同母者为宗也”。参看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533 页;杨希枚、牟润孙等认为此为汉初母系遗俗尚存,故《史记》载之。参看杨希枚:《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牟润孙:《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5页。事实上,汉代强调“同母”原则亦常见于史书,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及同母昆弟贵。”便是表明在同父兄弟中“同母”者之地位更尊。因此,“宗亲”概念指同母者或可视为同父情形下对“同母”原则的推重,是官方意识形态中仍以是否“同父”为亲属观念确定的根本标准。参看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517 页。⑥钱宗范先生则认为二十五子只有十二姓当是由于除青阳和仓林氏之外,黄帝其他子都归入了母方氏族,故从母姓,而从父姓的情形则标志着父系制的确立。参看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 页。雁侠先生的观点与之类似,认为这一记载实际反映的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过渡阶段,故而既存在从母姓也存在从父姓的情况。参看雁侠:《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7 页。⑦杨希枚认为,“己姓”的“己”为“自己”之意,并以此推断青阳与夷鼓皆是与黄帝同姓,故夷鼓与仓林氏当为同一人。参看杨希枚:《国语黄帝二十五子得姓传说的分析(上篇)》,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 本。⑧徐复观也认为此段材料中提到的姓氏来源并非通过简单的得母姓或得父姓可以解释,他认为远古时的姓氏作为部落的符号,由其统治者所领。参看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 页。⑨杜正胜认为“姓”最初是作为区分异族的标识,是统治阶层的专利。参看杜正胜:《周代封建制度的社会结构——封建与宗法(下篇)》,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 本;后来在这一看法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得“姓”的基础在于“德”,同德才可同姓。参看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190 页。陈絜指出,随着氏族的分化,黄帝的姬姓由其后代的某一支所继承,而其余氏族则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新的氏族名号,亦即姓。参看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0-31 页。⑩司空季子前后叙述用语的差异值得注意,先说“二十五子”后称“二十五宗”。“宗”的概念为后起,反映了叙述者有意将其与早期传说中“与父同姓”的现象相联系。这里的“姬姓”虽无法确定是否源于对父姓的继承,但可以确认的是,青阳与仓林氏二人兄弟的认定是通过“同姓且同父姓”这一条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