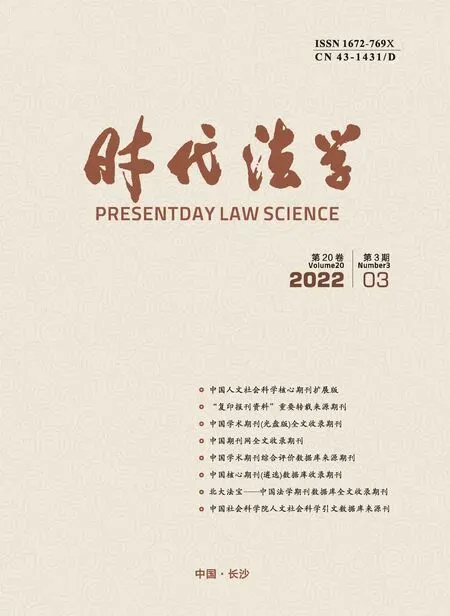自动驾驶汽车适用产品责任的困境与对策*
邓建志,程智婷
(1.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湖南师范大学知识产权中心,湖南师大知识产权运营有限公司,湖南 长沙 410081)
一、问题提出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1)[英]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M].宋兆霖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人工智能作为21世纪最前沿、最尖端的技术,犹如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生活带来方便与快捷的同时,亦打破了原有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给现有产品责任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
自动驾驶汽车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在汽车领域的具体应用,对人类的社会生活有着颠覆性的影响。自动驾驶汽车也因此被誉为“人工智能应用之母(themotherofallAIprojects)”(2)RobDavies,AlexHern. Applechief: DriverlessCarVentureis“TheMotherofAllProjects”[N].theGuardian,13Jun,2017.。目前,理论层面与现实层面的自动驾驶汽车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具言之:在理论层面上,自动驾驶汽车可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合理规划交通运输的路径,提升交通运输的便捷性与效率度。根据自动驾驶汽车制造企业的报告:“全球每年有12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其中94%的交通事故是由于人为失误造成。”(3)新华网.美媒:美称30年内靠自动驾驶技术消灭交通事故[EB/OL].(2016-10-08)[2021-08-17].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0/08/c_129313009.htm.基于此背景,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研发工作,承担着减少因人为原因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使命,以实现在拯救上百万生命的同时,解放司机劳动力的目标(4)杨延超.机器人法:构建人类未来新秩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也就是说,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日臻完善,因驾驶技能、疲劳驾驶、情绪波动等人为失误造成的交通事故将会逐渐减少,给人类交通出行带来“畅通无阻”的便捷(5)章军辉,陈大鹏,李庆.自动驾驶技术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科学技术与工程,2020,20(9):3394-3403.。但在现实层面上,无论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将会完善与发展到什么程度,其都难以完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近期,国内外自动驾驶汽车领域发生了两起引发社会公众关注与热议的事件,即2021年8月12日,一辆启用“NOP”领航辅助系统的蔚来汽车,因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驾驶员身亡;同年8月17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NHTSA)对特斯拉自动辅助驾驶系统“Autopilot”展开正式的安全调查(6)杨忠阳.“自动驾驶”出事,谁背锅[N].经济日报,2021-08-19(006).。自动驾驶汽车侵权事件的频频发生,让社会公众不得不再度关注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性问题,与自动驾驶汽车相关的侵权责任也成为司法实践中不可回避的法律问题。
自动驾驶汽车领域井喷式的技术发展,将会对现有的侵权责任体系带来新的挑战。为抢占自动驾驶汽车发展的制高点,美、英、德等国家先后针对自动驾驶汽车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案,旨在从法律层面规范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各国对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多持支持的态度,如2021年5月28日,德国正式通过自动驾驶汽车法案,将允许具备L4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在全国范围内的公共道路以及指定区域内行驶(7)德国联邦议院通过自动驾驶汽车法案,将在2022年允许自动驾驶汽车上路[J].金属功能材料,2021,28(3):72.;同年7月29日,北京市允许自动驾驶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进行测试(8)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无人车可以上高速了!北京开放首个自动驾驶高速测试场景[EB/OL].(2021-07-29)[2021-09-28].http://www.gov.cn/xinwen/2021-07/29/content_5628230.htm.。基于各国政策对使用自动驾驶汽车的支持,伴随着自动驾驶汽车而来的风险也将日益增长,可以预测大约在未来的5~10年里,传统交通事故将会逐渐淡化,交通责任也将会迭代为产品质量责任(9)新华网.美媒:美称30年内靠自动驾驶技术消灭交通事故[EB/OL].(2016-10-08)[2021-08-17].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0/08/c_129313009.htm.。但是面对这类新问题,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等关于产品责任的相关规定,在适用自动驾驶汽车时均存在明显不足。基于此,本文拟在分析自动驾驶汽车法律地位的基础上,重点分析自动驾驶汽车适用产品责任的现实困境,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与建议,力求初步构建自动驾驶汽车的产品责任体系。
二、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
明晰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是确定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前提条件。自动驾驶汽车作为传统汽车与人工智能技术高度融合的产物,随着近几年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业界对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做出了大胆的预测,如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预测:“2020年至2025年,自动驾驶汽车将实现部分自动化或有条件自动化”(10)赵晨熙.谁在混淆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概念[N].法治日报,2021-08-31(007).;高通中国董事长提出:“未来5年内,自动驾驶汽车将发展到L4级”(11)腾讯网.L4级自动驾驶何时到来?高通高管给出答案[EB/OL].(2021-09-05)[2022-01-25].https://new.qq.com/rain/a/20210905A015XZ00.;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表示:“中国到2030年,有望实现L5级别自动驾驶水平汽车的量产”(12)人民网.产业观察:我国智慧出行生态加速推进 自动驾驶催生产业新机遇[EB/OL].(2021-05-12)[2022-01-25].http://finance.people.com.cn/GB/n1/2021/0512/c1004-32101119.html.。由此可见,在不久的未来,自动驾驶汽车将能够独立于人类的干预,自主作出决策并执行决策,逐步具备高度拟人化的智能属性。据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自动驾驶汽车法律地位的讨论,主要有:公司法人说(13)张玉洁.论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人权利及其风险规制[J].东方法学,2017,(6):56-66.、电子人说(14)EuropeanParliament. Robots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 MEPscallforEU-wideliabilityrules[EB/OL].(2017-02-16)[2021-09-08].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170210IPR61808/robots-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meps-call-for-eu-wide-liability-rules.、拟制人格说(15)杨清望,张磊.论人工智能的拟制法律人格[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6):91-97.、有限人格说(16)袁曾.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审视[J].东方法学,2017,(5):50-57.、工具性人格说(17)许中缘.论智能机器人的工具性人格[J].法学评论,2018,36(5):153-164.、一般客体说(18)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35(5):128-136.等。可以看出,对自动驾驶汽车法律地位的讨论,主要可以分为客体说与主体说两大类。若法律将自动驾驶汽车认定为法律客体,那么当自动驾驶汽车发生侵权纠纷时,一般应当由生产者或者使用者承担侵权责任;若法律赋予自动驾驶汽车独立的主体地位,那么其将有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会对责任的归属产生直接影响。简而言之,自动驾驶汽车法律地位的争议性,将会给自动驾驶汽车侵权损害的司法审判造成困惑,难以统一自动驾驶汽车侵权损害的审判标准。因此,在设计适用自动驾驶汽车的产品责任体系时,应当先明晰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
现阶段产品责任规则的设置应当以自动驾驶汽车是法律客体为前提。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SEA)将自动驾驶汽车分为L0~L5六个等级(19)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J3016_201806:道路机动车驾驶自动化系统相关术语的分类和定义[EB/OL].(2018-06-15)[2021-09-08].https://www.sae.org/standards/contentj3016_201806/.。虽然当下不少车企对外宣传自动驾驶技术已经达到“高级自动驾驶”“全自动无人驾驶”“高性能自动驾驶”等极具技术感和未来感的水平,可以表现出超越传统汽车的深度学习与自主决策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市面上量产汽车的自动驾驶技术,仍多处于L2级或者以下的辅助驾驶级别,与L3级有条件自动驾驶水平要求的条件相差甚远,更是未到达“可排除人类干预,独自行驶车辆”的完全自动驾驶水平(20)胡立彪.推广自动驾驶技术要稳些再稳些[N].中国质量报,2021-08-31(007).。换而言之,现有“自动驾驶汽车”仍处于人类控制的范围,是算法程序运算后所得的机械认知,尚未达到人类的智慧水平(21)张力,李倩.高度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侵权责任构造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8,(8):35-43+156.,还不具备可拥有法律人格的独立性,在法律层面仍属于“产品”的范畴。或许终有一天,自动驾驶汽车将拥有媲美人类大脑的智慧,让现有法律制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就眼下来说这仍属天方夜谭的想法,因为目前自动驾驶汽车还存在一道道难以跨越的技术鸿沟,事实上截至到现在,自动驾驶汽车尚未超出蠕虫的智能程度(22)模拟蠕虫的大脑是国际科学项目“开发蠕虫”(OpenWorm)的研究课题,他们希望人工复制在秀丽隐杆线虫大脑中发现的203个神经元。相比之下,人类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参见:“开放蠕虫”项目官网. OpenWorm is an open source project dedicated to creating the first virtual organism in a computer[EB/OL].(2018-06-15)[2021-09-08].http://openworm.org.。虽然技术研究与理论探讨可以大胆、超前,但是法律制度的设置还是需保持谨慎与客观的态度。因此在设计自动驾驶汽车的产品责任规则时,应当将自动驾驶汽车作为法律客体进行调整与规范。
三、自动驾驶汽车适用产品责任的现实困境
产品责任向来对新技术都有很强的调整适应性,自动驾驶汽车引发的侵权问题仍可以适用产品责任(23)John Villasenor. Products Liability and Driverless Cars: Issuesand Guiding Principles for Legislation[J]. Intelligent Vehicles,2014:15.,但是由于自动驾驶汽车具有一定高度的智能属性,这使得其与传统产品有一定的区别(24)魏益华,于艾思.法经济学视阈下人工智能产品责任归责原则[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60(2):110-118+221.,同时这也给自动驾驶汽车适用现行产品责任带来了现实困境。
(一)现有产品责任的主体范围难以确定自动驾驶汽车侵权的责任人
侵权责任主体范围是确定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基础要件。依照《民法典》第1203条、1204条的相关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和运输者、仓储者等根据自身的“过错”,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产品责任。由于自动驾驶汽车需要多方主体共同研制开发,如系统的设计者、汽车的生产者、导航服务的提供者等,任何一个环节的瑕疵均有可能引发产品责任,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将使产品责任的侵权主体范围扩大。在认定自动驾驶汽车所涉及的产品责任时,除传统的汽车生产者外,还有两类主体值得引起注意:一是自动驾驶系统的设计者。自动驾驶汽车的自动运行得益于自动驾驶系统的不断升级与完善,然而自动驾驶系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分析性程序、算法程序等构成,传统汽车的生产者难以对其进行控制。也就是说,对于自动驾驶系统的设计者而言,若其在程序设计中出现差错,将有可能导致自动驾驶汽车侵权纠纷的发生,对此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是导航服务的提供者。自动驾驶系统以核心算法为运行基础,通过对导航服务提供的海量数据进行筛选、分析与深度学习后,才可独立控制机动车的运行。一方面,自动驾驶系统本身的抗干扰性十分有限,若导航服务的提供者未提供准确、有效的信息,将会对自动驾驶系统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在开放的互联网环境下,还存在多种可能引发误差产生的因素,诸如出现黑客、病毒等对系统进行攻击,雨水、强光、路途颠簸等外界环境对系统的运行产生影响,以及雷达读数、惯性测量等存在不准确性,这类因导航服务提供者形成误差的情况,均将影响自动驾驶汽车的正常行驶,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由此可见,若导航服务的提供者没有尽到其相应的义务,而导致自动驾驶汽车无法正常运行,引起产品侵权纠纷的,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综上所述,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将会扩大侵权责任主体的范围。
(二)现有产品责任的标准难以认定自动驾驶汽车的缺陷
侵权责任标准是确定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核心要素。根据《产品质量法》第46条的规定,产品缺陷的类型具体包括:设计缺陷、制造缺陷、警告和指导缺陷;而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主要包括:不合理危险标准与技术性标准。鉴于自动驾驶汽车基于其拥有的自主学习能力,将会在车辆使用过程中形成一套“与预先设立算法和程序不同,并具有不确定性、不透明性因素”的推理规制(25)景荻.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9.;加之,自动驾驶汽车存在“既要解放人类双手,又让人类时刻准备接管”的矛盾现状(26)杨洁.论智能汽车产品缺陷认定及其责任承担[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2(6):107-114+154.,这将会增加自动驾驶汽车缺陷认定的难度。
自动驾驶汽车将使产品责任的缺陷认定变得更为复杂。虽然在现有的理论层面,可以将产品的缺陷具体分为设计缺陷、制造缺陷、警告和指导缺陷三种类型(27)通常,产品缺陷被认为包括设计缺陷、制造缺陷、警告和指导缺陷三种类型。具体而言,(1)设计缺陷。设计缺陷是基于产品生产时对设计利弊的权衡。识别设计缺陷的测试是“合理的替代设计”,也即可以通过替代设计避免可预见的伤害,则可以认定该产品存在设计缺陷。由于自动驾驶汽车的运行完全依赖自动驾驶系统,一旦自动驾驶系统出现设计缺陷,将直接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2)制造缺陷。在制造产品的过程中,若偏离了预期的设计,该产品就会被认定为存在制造缺陷。自动驾驶汽车不仅存在自动驾驶系统上的制造缺陷,还存在各类汽车零件上的制造缺陷。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自动驾驶功能与自动驾驶系统紧密相关,所以因自动驾驶系统存在制造缺陷而引发交通事故的概率,将远大于因各类汽车零件存在制造缺陷而产生的交通事故。(3)警告和指导缺陷。如果通过提供合理的指示或者警告,就可以避免或者减少产品造成的可预见危害,则可以证明该产品存在警告和指导缺陷。由于自动驾驶汽车属于高新技术产品,大量用户可能不会意识也不会辨别风险的存在,若在使用的过程中没有合理的警告或者指导,很容易造成用户在人身或者财产方面的损失。也就是说,在判断产品是否存在警告和指导缺陷时,不仅要考虑是否需要警告或者指导,而且还有考虑警告与指导是否合适。参见:[美] 瑞恩·卡洛,迈克尔·弗鲁姆金,加伊恩·克尔.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对话[M].陈吉栋,董惠敏,杭颖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37.;但是在实务操作中,鉴于自动驾驶汽车是前沿技术产品,不仅其自身存在一定程度的专业性、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28)翟强,程洪,黄瑞,詹慧琴,赵洋,李骏.智能汽车中人工智能算法应用及其安全综述[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20,49(4):490-498+510.,而且司法实践中也缺乏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审判经验,所以这将增加自动驾驶汽车的缺陷认定难度,难以判断其是否存在缺陷,以及其具体存在何种缺陷。一方面,在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认识层面,均没有对“不合理危险”标准形成统一的认识。由于我国法律没有准确界定“不合理危险”标准的内涵,在司法实践中,通常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认定。但是自动驾驶汽车作为新兴技术产品,不仅在设计上具备极强的专业性,而且其运行的工作原理也十分复杂,仅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这将难以准确、公平地判断自动驾驶汽车是否存在缺陷,以及自动驾驶汽车存在何种缺陷,不仅会加重法官的日常审判压力,而且还可能导致事故无法合理归因于设计或制造的缺陷。另一方面,在国家和行业的标准层面,缺乏与自动驾驶汽车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相关的技术性标准。自动驾驶汽车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范例,虽然在技术上已经日渐成熟,但是还没有被全面投入到市场中使用,各个国家乃至我国的部分城市对自动驾驶汽车还处于测试、试行、探索等阶段中。目前,我国尚未制定规范自动驾驶汽车的国家标准,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所以难以根据技术性标准认定自动驾驶汽车的缺陷,尤其是系统层面的缺陷认定。可见,缺乏统一的不合理危险标准和技术性标准,将会加大认定自动驾驶汽车是否存在缺陷以及存在何种缺陷的难度。
(三)现有产品责任的抗辩事由难以调整自动驾驶汽车的侵权行为
风险抗辩事由是确定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重要内容。依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的相关规定,产品责任的风险抗辩事由包括:(1)产品未流通的;(2)产品流通时缺陷不存在的;(3)产品流通时缺陷尚不能被发现的(又称为“发展风险抗辩”)。与传统汽车适用风险抗辩事由相比,各界较为关注自动驾驶汽车能否有效适用现有的风险抗辩事由,以及如何完善现有的风险抗辩制度等重要议题。
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行为难以适用现有的风险抗辩事由。首先,自动驾驶汽车适用“发展风险抗辩”存在较大争议。关于这一问题,目前理论与实践层面主要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主流观点。一是肯定说。学者们主张:“从平衡人工智能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权利义务关系,实现二者之间的实质公平与正义,鼓励自动驾驶技术革新等视角来看,应当给予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以合理和恰当的宽容”(29)胡元聪.我国人工智能产品责任之发展风险抗辩制度构建研究[J].湖湘论坛,2020,33(1):70-89.。二是否定说。学者们认为:“从技术的前沿性,产品的安全相关性以及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等角度来看,应当排除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者适用发展风险抗辩事由”(30)韩旭至.自动驾驶事故的侵权责任构造——兼论自动驾驶的三层保险结构[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2):90-103.。可想而知,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未对“自动驾驶汽车能否适用发展风险抗辩”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之前,将难以统一该类案件的司法裁判依据,甚至会引发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的“恐慌”,进而采取最为保守的自动驾驶汽车生产、研发方式,导致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受到阻碍和影响。其次,即便采取肯定说的观点,在发生侵权纠纷时,给予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主张风险抗辩事由的权利,但若未根据自动驾驶汽车的自身特点完善现有的风险抗辩制度,亦有可能被生产者将风险抗辩事由用作一切行为的“免死金牌”,进而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31)司晓,曹建峰.论人工智能的民事责任:以自动驾驶汽车和智能机器人为切入点[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35(5):166-173.。由此可知,现有产品责任的风险抗辩制度,难以公平、合理地调整自动驾驶汽车的侵权行为,需尽快明晰可有效适用于自动驾驶汽车的风险抗辩制度。
四、自动驾驶汽车适用产品责任的解决对策
(一)扩大产品责任的主体范围
一是将自动驾驶系统的设计者纳入到产品责任主体范围。自动驾驶汽车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高科技产品,其具有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的特性,这均离不开程序设计者不断地研究与开发。若在自动驾驶系统的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出现了过错,这将直接影响自动驾驶汽车的产品质量,进而引发产品侵权纠纷。可见,在自动驾驶汽车产品侵权责任中,自动驾驶系统设计者的行为,可能会对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的判断产生影响,故应当将其纳入到产品责任的主体范畴内。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实践中,往往存在程序设计者与汽车生产者互为同一主体的情形,因此在具体认定侵权主体责任承担这一问题时,应当首先明晰程序设计者和汽车生产者的身份,在此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也就是说,当自动驾驶汽车的设计者与生产者为同一主体时,应该由生产者承担全部的产品侵权责任;当自动驾驶汽车的设计者与生产者各为不同当主体时,应当分步骤进行分析,先确定产品的缺陷类型,再根据缺陷类型确定具体承担责任的主体。即若是因为自动驾驶系统的程序设计、数据采集、规划决策等软件存在缺陷导致侵权的,则应当由自动驾驶系统的程序设计者承担相应责任;若是因为自动驾驶系统或汽车的零部件、传感器、控制器等硬件存在缺陷导致侵权的,则应当由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者承担相应责任。
二是扩大侵权责任的第三人范围。自动驾驶汽车的独立运行,离不开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定位系统等算法程序之间的协同合作,离不开对海量数据的筛选、分析与深度学习,更离不开互动、开放的互联网环境。正因如此,外部环境中存在诸多影响车辆独立运行的因素,将会导致自动驾驶汽车侵权纠纷的发生,除了产品自身存在缺陷的原因外,第三人的行为也可能会造成侵权纠纷的发生。基于自动驾驶汽车运行需依赖“先进的算法程序、海量的数据资料、开放的互联网环境”等技术背景,这便在法律层面上,给自动驾驶汽车侵权纠纷产生的原因具备一定特殊性埋下了“伏笔”,诸如互联网环境下的黑客入侵系统、病毒破坏程序、病毒篡改或者窃取数据资料等,都有可能导致自动驾驶汽车侵权纠纷的发生。当自动驾驶汽车被第三人恶意入侵时,自动驾驶汽车原有的系统、程序、数据等都将被破坏,其将无法按照原先设计的程序进行正常的工作,这将有可能会对他人的人身、财产等造成损害,由此造成的自动驾驶汽车侵权纠纷,应当由入侵系统、破坏程序、篡改数据等的第三方侵权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32)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35(5):128-136.。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解决自动驾驶汽车带来的问题,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1204条规定的第三人责任,同时将承担侵权责任的第三人范围由运输者、仓储者扩展到黑客、病毒传输者。
(二)统一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
技术性标准是判断自动驾驶汽车缺陷的首要认定标准。技术性标准作为一种强制性标准,一般是指生产标准,即只有当自动驾驶汽车的产品质量满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时,才能认定其不存在缺陷。由于信息存在不对称性,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水平,难以与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高低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所以为了避免阻碍人工智能技术以及自动驾驶汽车产业的发展,在制定生产标准时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应当综合考虑当前技术的发展水平,制定与技术发展水平相契合的生产标准。在具体适用该标准时,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不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则应当认定其存在缺陷;但是,如果自动驾驶汽车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时,则仍有必要进一步判断自动驾驶汽车是否存在其他不合理的危险。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导致自动驾驶汽车缺陷的因素比较复杂,二是技术性标准本身可能也没有跟上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步伐,而存在滞后或者不够周全的情形。
“不合理安全”标准是判断自动驾驶汽车缺陷的重要认定标准。“不合理安全”标准一般是指安全标准,比国家、行业层面的生产标准更为严格,即只有当自动驾驶汽车避免了“能够且应当避免的危险”时,才能认定该自动驾驶汽车不存在缺陷;反之,自动驾驶汽车将因未能避免“能够且应当避免的危险”而被认定为存在缺陷。鉴于自动驾驶汽车具备一定智能程度的自主决策与深度学习能力,即便其满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也仍有存在缺陷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对其是否具有“不合理的危险”作进一步的审查。在判断自动驾驶汽车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危险”时,为克服“消费者期待”标准存在主观片面性的问题,可以在使用“消费者期待”标准判断缺陷的同时,辅之以客观的“风险—效用”分析方法,这将有助于作出更准确、更恰当的判断。即在判断自动驾驶汽车是否存在合理的危险时,应当综合各项因素进行考虑,包括但不限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智能化程度、消费者对使用自动驾驶汽车的合理期待、自动驾驶汽车投入市场流通的时间等因素(33)徐海涛.汽车产品责任纠纷案件的审判实践与学理评析[J].法律适用,2017(23):66-74.。总体而言,在认定自动驾驶汽车是否存在缺陷时,应当同时满足上述两个要求,即只有当自动驾驶汽车既满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又同时不具有“不合理的危险”的情况下,才可以认定该自动驾驶汽车不存在缺陷。
(三)明晰产品责任的抗辩事由
自动驾驶汽车可适用完善后的风险抗辩制度。在政策科学领域,法律亦是一项公共政策(34)吴汉东.知识产权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虽然现代化的产品责任逐渐朝着严格责任的趋势发展,但是风险抗辩制度并不是对严格责任的排斥或者限制,而是作为产品责任的一项辅助机制(35)贺琛.我国产品责任法中发展风险抗辩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34(3):135-144.,以发挥其“均衡”各方合法权益的公共政策作用。质言之,为避免生产者因无法承担未知的风险而阻碍技术的发展与创新(36)梁亚,王嶂,赵存耀.论产品缺陷类型对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影响——《侵权责任法》第41条生产者责任之解释与批判[J].法律适用,2012,(1):37-41.,法律应当明晰自动驾驶汽车责任主体适用抗辩事由的条件。一方面,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者不能以“技术中立”为理由主张抗辩,因为适用该原则进行抗辩,既不利于自动驾驶汽车安全秩序的维护,同时也有碍于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37)杜明强,冷传莉.论无人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8(2):129-139.;另一方面,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者可以依据《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主张免责。其中,关于“发展风险抗辩”适用的问题,从激励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自适性特点的角度来看(38)彭建,何珊,蔡哲鹏.论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的发展风险抗辩[A]. 2021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组委会.《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21年第5卷 总第53卷)——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法治论坛文集[C].2021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组委会:上海市法学会,2021:10.,支持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者适用“发展风险抗辩”,将有助于降低生产者承担高度危险责任,促进自动驾驶汽车产业发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开发风险抗辩仅适用于存在设计缺陷的情形(39)彭建,何珊,蔡哲鹏.论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的发展风险抗辩[A].2021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组委会.《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21年第5卷 总第53卷)——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法治论坛文集[C].2021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组委会:上海市法学会,2021:10.。
严格限定自动驾驶汽车的风险抗辩适用。针对自动驾驶汽车这一新兴技术产品的高危险性,适用抗辩事由应当拥有更严格的要求(40)高完成.自动驾驶汽车致损事故的产品责任适用困境及对策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6):115-121.,即生产者应当拥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基于自动驾驶汽车依赖的自动驾驶系统具有自适应性、不可预测性、难以理解性等方面的特点,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当包括事前预防、事中监测与事后跟踪等方面的内容。具言之:一是事前预防。在将自动驾驶汽车投放至市场之前,生产者不仅应当加强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测试,并且不可以在宣传、销售等过程中过度夸大自动驾驶汽车的级别与功能;二是事中监测。在自动驾驶汽车的使用过程中,生产者应当定期维护和升级产品软件,预防病毒、黑客等对系统进行攻击;三是事后跟踪。对于已经进入市场流通而科学技术尚未发现缺陷的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须严格履行跟踪、观察等注意义务,一旦发现自动驾驶汽车存在缺陷的,应当及时发出警告和召回,如果因为没有及时发出警告和召回而导致损害发生的,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产品责任。
(四)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
加快完善与自动驾驶汽车相关的保险制度。保险制度与侵权责任息息相关(41)韩旭至.自动驾驶事故的侵权责任构造——兼论自动驾驶的三层保险结构[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2):90-103.,这尤其体现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中。鉴于证明自动驾驶汽车的产品质量,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司法负担,而保险制度相对诉讼制度而言,更节约社会资本,更有助于人身、财产安全的保障,保险制度必将成为自动驾驶汽车企业运营中必备的经营成本(42)杨延超.机器人法:构建人类未来新秩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因此有必要引入与自动驾驶汽车相关的保险制度。目前,多国法律对自动驾驶汽车设置了购买保险的规定,诸如英国将自动驾驶汽车纳入到车辆保险的范畴(43)搜狐网.英国公布自动驾驶汽车新保险法规——以乘客为重[EB/OL]. (2017-02-24)[2021-09-08].https://m.sohu.com/a/127115562_579461.;美国要求进行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的车辆,需要购买500万美元的保险或等额保函(44)NHTSA.Federal Automated Vehicles Policy: Accelerating the Next Revolutionin Roadway Safety [EB/OL].(2016-09-08)[2021-09-08].https://www.nhtsa.gov/sites/nhtsa.gov/files/documents/av_policy_guidance_pdf.;荷兰规定自动驾驶汽车上路行驶需提供额外的保险(45)Nynke E Vellinga.From the Testing to the De-ployment of Self-Driving Cars: Legal Challen-ges to Policy makers on the Road Ahead[J].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2017(6):847-863.;我国北京、上海等地亦规定自动驾驶汽车进行道路测试需要提供500万元人民币的保险或等额保函(46)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EB/OL].(2020-11-12)[2021-09-08].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102/W020210203384556285539.pdf;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公安局、市交通委关于印发《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EB/OL]. (2019-09-10)[2021-09-08].http://www.sheitc.sh.gov.cn/cyfz/20190910/0020-683620.html.。由此可见,为自动驾驶汽车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已是各国统一认可的做法。但是自动驾驶汽车作为新兴的出行交通工具,与传统汽车相比具有其自身特殊之处,一是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者与使用者均有可能导致侵权事件的发生,并且导致自动驾驶汽车侵权的主体将逐渐由使用者向生产者转移(47)冯洁语.人工智能技术与责任法的变迁——以自动驾驶技术为考察[J].比较法研究,2018,(2):143-155.;二是自动驾驶汽车侵权造成的损害金额通常较为昂贵,仅由自动驾驶汽车使用者购置的交强险,难以对受害人进行完全赔付,因此从“降低自动驾驶汽车行业发展风险,分散自动驾驶汽车侵权损害,合理维护生产者、使用者及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等角度来看,可以引入产品责任险、商业保险等多类险种(48)牛彬彬.动态系统论视角下自动驾驶侵权损害赔偿体系之建构[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3):89-100.,并加强各险种之间的衔接与配合,形成以交强险为主,辅之以产品责任险与商业保险的自动驾驶汽车行业保险体系。
积极推动自动驾驶汽车行业协会基金的设立。自动驾驶汽车产品侵权责任的救济,不能仅依靠产品责任与保险制度,社会自发的自动驾驶汽车行业协会也可以在损害救济中担当重要角色(49)胡元聪.人工智能产品发展风险抗辩后的损害救济分摊机制研究[J].政法论丛,2020,(3):121-130.。技术创新源于社会,同样也由社会共同受益,风险也应当由社会分享共担。社会层面可通过设立自动驾驶汽车行业协会,来解决救济补偿的问题。一方面,自动驾驶汽车在技术研发阶段,需要协会基金的支持。自动驾驶汽车行业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新产业,虽然“自动驾驶汽车”这一名词已经频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目前尚未成功研制拥有完全独立决策能力、充满科幻色彩的“自动驾驶汽车”。“闭门造车”式的研发不仅难以满足技术创新的需求,而且还会增加技术研究的成本,浪费智力劳动的投入,但如果能由自动驾驶汽车行业协会汇总技术研发痛点,进行信息交流共享,从源头解决可能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产品缺陷,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自动驾驶汽车在因产品缺陷引发侵权纠纷时,也需要协会基金的支持。无论是自动驾驶汽车因发生侵权行为,进行损害赔偿;还是自动驾驶汽车为避免侵权行为发生,进行日常维护与追踪,都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行业协会可通过提前缴纳风险准备金的方式,分摊自动驾驶汽车的侵权风险,以维护消费者及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共同促进自动驾驶技术的创新发展。
五、结语
科技进步意味着拥抱不确定性,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技术高速发展与法律设置滞后之间的冲突将会日益明显,自动驾驶汽车给现有产品责任带来的挑战也将日益增加,为此产品责任体系应当根据现实需求作出适当调整。首先,应当明确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客体地位;其次,在分析自动驾驶汽车适用产品责任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扩大产品责任的主体范围、统一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明晰产品责任的抗辩事由、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等对策与建议,以均衡鼓励科学技术创新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之间的关系,促进自动驾驶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