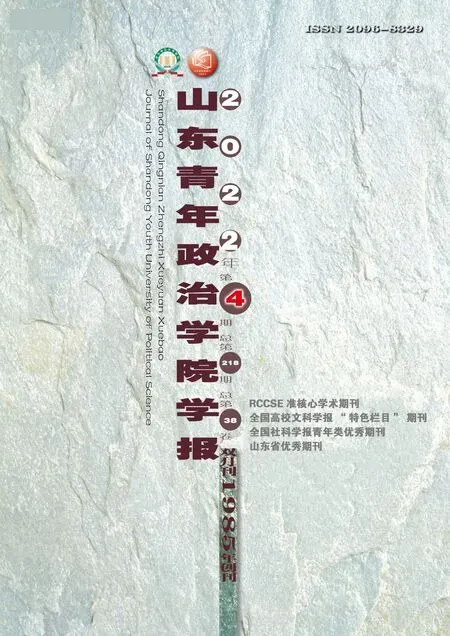诗性颖秀,江南草长
——曹嵩长篇小说《青涩年华》的叙事与修辞艺术
张 灵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综合学院,山东 威海 264504)
曹嵩的长篇小说《青涩年华》以近四十万字的篇幅讲述了一个怀揣文学梦想、高考屡次失利的农家子弟在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急剧转型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寻求人生出路和梦想实现的二十几年的人生历程,笔触所及囊括了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的众多层面的生活场景,展示了一个农家青年在人生的关键阶段里领受到的生活与生存的艰难困苦与精神心理上的酸甜苦辣。作品除了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以外,在艺术上也颇具自己的特色,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探索和审美个性,值得我们予以梳理、总结。
一、清新的“生活流”,轻松的“阅读感”
《青涩年华》是一部本色的小说,作者谦逊地退到了故事的背后,让故事随着主人公的人生轨迹汩汩流淌、峰回路转地自然呈现,只是在不得已的地方作者才以画外音的方式作必要的交待,因此这部小说完全符合大部分小说读者所喜欢、期盼的形式品质——让小说的阅读成为“快乐的阅读”。而之所以这样,一方面与作者自己的文学经验的积累有关,另一方面应该也与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青涩年华》封面勒口的作者简介就呼应了通篇的故事走向,这部小说正如丁帆先生所言,是“一部介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流年岁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1]。可以说,作者胸中太多的等待书写的饱含鲜活的生活汁液的素材和他对“自传体”文体形式的选择,决定了《青涩年华》的叙述方式和基本特征,使作品在总体上体现出精谨、细腻、清纯、质朴的工笔画特色,当顺着主人公的人生故事一路读下去的时候,小说描写的世界就像夹岸的风景一般源源不断地迎着读者扑面而来。就此,也可以说这是一部清新的“生活流”作品。
“生活流”小说是一种本色写法的小说,在21世纪的今天,“生活流”写法虽然不再是常见的整体构筑作品的艺术选择,但它确能体现小说创作的基本功和小说构成的基本元素。小说这种叙事文体是不能完全没有“生活流”的内容,即鲜活的社会生活的,因为鲜活的社会生活是小说甚至一切文学作品最基本的构成材料。读罢《青涩年华》,作品艺术上的“生活流”特色叫人有种“他乡遇故人”的新奇,而回味作品的内容则令人感到与其说是作者选择了这样的写法,倒可能不如说是这些丰富生动的生活内容推动他写成或者无视他的个人意志而生成了这样的作品风格。
我们不用去通过作品中那些枝叶繁茂的大大小小的故事情节来说明问题,单看梁月鹏高考第三次失利之后参加农村劳动时的场景,就会见识到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熟悉,那些生动的场面走到作品之中似乎是不需要任何艺术的加工的,那些生活内容叫人觉得熟悉又生动,其中的用词也似乎无需雕琢却简洁准确,显示出了“生活流”作品的典型特征。
我们看一个生活场面,这是梁月鹏在高考补习班的情况:“接下来,梁月洲又送钱给梁月鹏,使梁月鹏渡过了又一个经济难关。隆冬到了,下起了大雪。补习七班里,大多数学生穿得比较单薄,但他们仍在认真地上晚自习,咳嗽声,鼻塞的呼啦声,打喷嚏声,此起彼伏。一个女生打了一个雷鸣般的喷嚏,引起哄堂大笑。梁月鹏在做作业,忽然想起什么,犹犹豫豫地站起身。原来这是元旦前夕,教学楼上的教室里隐约传来庆祝元旦的欢笑声和歌声!”[2]不能说这里的描写有多新奇,但这些笔墨不可谓不充满了现实生活的声音与气息。
古典文学专家余恕诚先生曾这样谈到杜甫的《赠卫八处士》:“这首诗却似乎写得毫不费力,乍看去似乎不觉沉郁顿挫……诗顺着时间的线索……写得层次井然,确实类似古诗那样质朴而平易近人。”[3]这一段文字,恰巧可以用来说明“生活流”作品的特征,这里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来说明《青涩年华》的基本叙述特征。
这段分析中说到“乍看去似乎不觉沉郁顿挫”,言外之意,抛开表面,其实充满了人生的顿挫曲折之感和生命的飘摇沉郁之叹,它们是由诗所描写的内容自然传达的。当我们将《青涩年华》一气读下,它的主人公及其所连带、裹挟的众多人物的人生故事、生存状态也不禁叫人感慨万千。所以说《青涩年华》之所以具有那样的总体风格,对作者来说,首先应该是一种生活的馈赠,没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的积累,“生活流”小说是不好支撑起来的。
二、浓厚的电影化色彩,突出的视觉化叙述
《青涩年华》自觉、巧妙、大量地吸收与发挥了电影艺术的一些表现手法与艺术元素,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进一步成就了作品的“生活流”特色,这特别体现在对生活内容的选择、剪裁与切换之中,这些手法使作品形成了强烈的节奏感、直观化、视觉化效果,这无疑也增加了作品阅读的快感,使它的文本不因生活的沉重、黯淡而变得苦情、消沉,整个作品散发出“暮春三月、江南草长”[4]般的清新蓬勃的气息。
小说的电影化、视觉化特色与这部自传体色彩浓厚的作品之作者本身或者说作品的主人公的经历尤为契合。小说主人公梁月鹏从少年时期起就迷恋文学特别是电影剧本的写作,即使是高考复读期间对此爱好也是欲罢不能。梁月鹏曾对他大哥说:“我很讲究蒙太奇结构,电影剧本和故事会里的故事不一样,电影剧本是一节一节向前走的,节与节之间省略了我们知道的东西。”[5]尽管说所有的文学写作都存在一个剪裁与省略的问题,但电影或从事电影剧本创作的人对此会有着更为明确、自觉的认识。小说人物梁月鹏关于电影的这个看法,显然也是《青涩年华》作者曹嵩一贯的见解,他在小说中对电影的这些惯用技巧作了精妙的发挥。
我们不妨以例说明。这是梁月鹏在高考复读期间的暗恋故事:“王继红还没有下自习,她趴在自己的位置静静地做作业。窗玻璃外,梁月鹏张望的脸,很快移去。走廊里,梁月鹏在徘徊。他走到窗前站定,伸头往窗内看。王继红端坐着做作业,目不斜视。窗玻璃外,梁月鹏张望的脸。王继红做完了作业,开始收拾书本。梁月鹏蓦地缩回头,在走廊里徘徊起来,又转身躲到一廊柱后。王继红捧着装书的小皮包出来了,向前面走去。梁月鹏倚着廊柱看着。王继红走远了。梁月鹏走了出来,远远地跟着……”[6]关于梁月鹏紧张胆怯又渴望表白的暗恋心理,作者是通过一个个镜头的不断切换、剪辑来呈现的,作者自己没有站出来直接刻画这种心理和情绪的波动,而是把这些内容交给了不断切换的画面。
梁月鹏被清溪县公安局拘留,通知给了家里:“母亲安好却楞楞地坐在堂屋内,眼睛红肿,面容憔悴。” “父亲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加荷包蛋,递给梁月鹏妈道:‘都两顿没吃了,趁热吃了。’月国妻子笑了笑道:‘还是老两口子亲,饭都递到手上。’”[7]镜头直接切换到了这里。这一跳跃省略了前面的情况,反而突出了此事给家庭尤其给母亲带来的影响。
如果说剪辑、蒙太奇式安排是这部小说的一个情节安排的特点的话,镜头化、视觉化则是《青涩年华》的一个更加擅长和作了充分发挥的艺术技巧。
梁月鹏在公路站打工劳动的间隙,走进值班室,“伸手拿起桌上电话机旁的《江汉省清溪县电话号码簿》翻看起来,他藏青色上衣的背部结上了白色的盐霜”[8]。最后一句对于情节的交代并无直接的意义,但作为叙事的一笔,却自然、巧妙地显示出梁月鹏此时此刻的处境和形象,镜头感非常强烈。
梁月鹏一个电话约来了张副书记。这一次会面前后,梁月鹏和张书记的心理和结果变化急剧,但作者只以镜头直观展示:张书记来的时候,车停下来,先是一个小青年从副驾驶座位下来,接着打开后排车门让张书记下来。但把梁月鹏带走的时候,张书记却坐到了副驾驶座位。小汽车在县政府大院停下,“张副书记对男青年说:‘你带小梁去楼上值班室等一下,我去一下就过来。’说完转身离去。梁月鹏想对张副书记打声招呼,但见张副书记已走去,只能欲言又止”。到了值班室,里面有一个值班的老者,“老者又友好地把风扇的风向移向梁月鹏和男青年,梁月鹏看到了这一点,脸上升起了幸福的神情”。但接着出现的是警察,把梁月鹏带走了。这整个事件前后,作者全是以镜头说话,不作任何解说,也不刻画人物心理,但这一切一般小说所要讲述的内容都通过镜头语言和画面呈现了,读起来还让人感到轻松并耐人寻味。
作者常采取“清水洗尘”的质朴手法,短短一段文字,事情或情节的微观过程得以视觉化呈现,不长的文字,却用了几个句号,使表达没有多余的辞费,但人物的心理情绪和环境气氛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三、结构助词“地”的超常使用与“反复”“镶嵌”等手法的运用
与“镜头化”“视觉化”密切相关,还应该单独予以关注的是《青涩年华》的一个也许自觉也许只是出自艺术直觉的修辞创造或对修辞手法的创造性运用:《青涩年华》大量、突出地使用了以结构助词“地”为形式特征和词缀的状语形式来叙事,作者敏感到“地”这一状语的形式标志可以轻巧、有力地改变词语的表达效果,使一个句子变得更加具有表现性,或者说使一个记叙、描述变得更加视觉化、镜头化。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
梁月鹏被收押以后,警察又赶到桥梁工地的工棚搜查梁月鹏的东西,看看有什么犯罪证据。正值夜晚,工人们已经在休息。“警察到处搜了起来。梁月国他们都醒了,坐了起来,只有服从地看着……”显然“服从”首先是一个动词,常用为谓语,动词是它最常见的用法,但这里作者通过一个“地”就把它纳入了一个状语的位置框架,从而行使起状语的作用,既生动呈现了梁月国们“看”的情态,更简洁有力地表现了他们面对警察的心理,丰富的内容得以直白、准确和分寸恰当地展现。
梁月鹏婚后依然没钱,要买本书也得向贾铁馨要或者向其他人借钱。一天他在书摊上见到两本书,急着要买回来,只好找人借钱,“梁月鹏一人在店里,他有心事地来到‘衣篱’边,拨开一件衣服,把头探向张华那边,喊道:‘张华,张华。’……”“有心事地……”又是一个状语妙用。“地”作为一个语法标志,它以潜在的语法功能创造出一个表现性表达,又将人物心理的描写形象化、镜头化了。关于“地”的功能的发挥小说中还有很多例子,不必逐一列举了。
这里我们再来看看作者对另一种艺术手法“反复”的使用。“反复”作为修辞手法经常出现在诗歌中,但小说中出现也是由来已久的,别的不说,早在新文学的开创时期,冰心女士就在她的著名小说《超人》中使用过:“月光如水,从窗纱外泻将下来,他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极力的想摒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其中“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这一串意象和文字在作品中出现过两次。[9]在《青涩年华》中,作者多次成功地运用了“反复”这一手法,如梁月鹏在陷入人生的低谷时,小说里不止一次出现:“母亲深情的声音似乎又在耳畔响起:‘月鹏,粑粑摊在小锅里,大锅里有粥,我下田了。’”这种反复如同电影里的主旋律在回响,在给主人公以温暖和鼓励。
“扶着铁皮的梁月鹏眼睛一闭,同时身子一颤。铁皮脱落。……扶着铁皮的梁月鹏眼睛又一闭,同时身子一颤。铁皮脱落。……扶着铁皮的梁月鹏眼睛又一闭,同时身子一颤!铁皮脱落。扶铁皮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哈哈大笑起来,有两个姑娘笑弯了腰……”[10]这是梁月鹏打工的场景,既是写实,也是描写内容的“反复”,传达出工作的单调乏味和令人灰心的状况。
至于小说后半部反复写到吴小花脸上的痤疮和两颊绯红,更是一种艺术表达的伏笔安排。
在梁月鹏吴小花找工作那段日子里,“当夜,夜光中,依稀可见睡在一头的梁月鹏和吴小花都闭着眼,都在不住地咽唾沫,他俩都睡不着……”[11]这个“当夜”的镜头也反复出现过多次,以相似的镜头表达主人公同样的处境与心境。
“走在银铃集团滨海分公司偌大的厂区里,拉杆箱轱辘在地上滚动所发出的‘咕噜噜噜噜’的声音更加响亮动人!”这个拉杆箱在街道上咕噜噜滚动的镜头和声音多次出现在作品中,他是人物命运和生存状态的反映,某种意义上梁月鹏和吴小花乃至更多的年轻人,很多年总是终日奔走在陌生的城市或乡村,在寻觅中惶惶如丧家之犬!
另一个反复出现的镜头,如同拉杆箱,也同样是一个令人有锥心之痛的人生征象:无论是谈恋爱、求职、求人办事、求客户,等待人家的回应,总是一再反复写到梁月鹏打接电话的情形,如:“梁月鹏拿着手机,继续查找通讯录,拨号,然后把手机贴在耳朵上,紧张地谛听着,并干咳一声,清了一下嗓子,准备对话。”[12]这个镜头生动刻画了梁月鹏惶惶不可终日的求生状态,其实也是这个喧嚣时代,我们很多人,很多弱势甚至只是低势(——因为这个时代特殊的社会潮流与运行方式,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有多少人能说自己不是弱势或不是在某件事情上处在仰仗于人的弱势、低势之中呢!)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不断经历的典型的生命时刻的表现,一个渴望、祈求他人的典型生存流程——“行为公式”“行为形式”——的反映。
另外,小说灵活运用了文体“镶嵌”的艺术手法,在作品中多次镶嵌了主人公梁月鹏的作品。比如,梁月鹏在高考复读的艰苦生活中,孤独地唱出想念妈妈的歌,小说就嵌入了他写的歌词。这样的镶嵌,既与作品对人物个性的设定吻合——他热爱文学、具有文学才华,另一方面有助于塑造人物、表现人物的情感。其他的普通书信、情诗、情书等等“镶嵌”的作用和好处是同样的。小说还插入电影厂文学部编辑的稿件处理信、梁月鹏剧本的“准扉页”,甚至法院判决书、法律条文、课堂的板书内容、名片的版面、工作记录、离婚协议书、夜空绽放的礼花标语,等等,这些内容以独特的形式在小说中起到了塑造人物、描写与烘托环境、体现人物心理情绪等等的丰富作用,也使小说在形式表象上具有了更为丰富的“镜头化”表现或形式性内容,增加了小说的表现力、新颖性和趣味性。
四、“颊上三毛”与颖异的灵感
故事的情节、人物的行为,对这些外在的、大的方面作镜头化描写、交待是小说和影视的基本艺术手段,也不一定有很大难度。对小说来说,在镜头化或非镜头化的心理刻画等方面,最为可贵的是一些细微的笔触,就像一颗大树上的一个枝杈或一片树叶,对于大树来说微乎其微、无关紧要,同样在叙事艺术中,这样的一枝一叶或许也算不上故事情节或人物行为必不可少的一节,但有了它们,就会让读者顿时眼前一亮或感到作品一下子生气勃然、生机再次焕发。这种笔触的胜处与顾恺之人物画艺术的奥秘或许隐隐相通:“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13]如同这里的画像,颊上三毛似无关眉目鼻口,但却令人物形象更加活灵活现。《青涩年华》里这样的小镜头、小笔墨不少,它们也显示了作者对生活和人物内心情感心理的谙熟。
如,在梁月鹏被释放前后有两个小镜头,也很能说明问题:“警察走了,小窗子关了,梁月鹏把被子和两件换洗内衣放在地上,不禁蹲靠着墙,低头饮泣起来。”[14]这是接到家人送来的衣物后的一个镜头。“‘请问,在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一个一个打他们,为什么单单到我就不打了呢?’帅哥警察说:‘你斯斯文文的我打你干吗?’梁月鹏满意的神情。”[15]这是他被释放后的一个镜头。梁月鹏为什么饮泣、为什么满意了,作者并没有具体交代,而只是给了镜头。这样的镜头从大的情节的角度来说也是可以阙如的。
研究生毕业后艰难地找到一份工作,一年之后却不得不离开并搬迁还未温热的家:“搬家汽车启动,开走。驾驶室内,吴小花依依不舍地流下了眼泪,梁月鹏递了一张手帕纸给吴小花。搬家汽车拐弯驶去,上了马路,进入茫茫车流中。”[16]这种看似随意的一笔,暗含着命运播迁、生计无措的灰暗心情和辛酸。这些叙事的大情节之外的细微一笔,带给小说的是生命的不绝的气息,也正是这些细微之处给冰冷的社会叙事灌注了生气。其实,这是一部小说常规构思以外、情节设计以外而随着作者的内心体验与想象在写作时即兴而得的东西,也恰是陆游所说“妙手偶得之”的东西,它们是一部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生命力的源泉所在。当然这些精彩细节的捕获乃是作家对所描写的生活经过“艰苦的‘格物’过程达到‘物格’之境,洞悉人心,通达世情”[17]之后取得的。
另有一些笔墨看似细枝末节,或与叙事无关的闲笔,却极大增强了小说的生命力。如为了梁月鹏的工作,大姐夫找到他当年的战友家,想请有一定职权的战友关照,但战友既不愿帮忙而且对他们也不怎么讲交情礼貌,对他们带来的两只母鸡不屑一顾、毫不领情:“大姐夫看了看梁月鹏,说:‘那走吧。’梁月鹏站起身来,看了看地板上的鸡,大姐夫对战友说:‘这两只老母鸡丢这了。’战友看了看地板上的鸡,明显反感道:‘不要不要,我们没人宰,你看已经拉了。’”在一番推让后,“战友生气道:‘你何富国你叫我怎么说呢?这样拖泥带水的干什么呀你?’梁月鹏拉了拉大姐夫道:‘我们走吧。’”[18]这点细节和插曲,不仅有力地反映了梁月鹏寻求出路的艰难,也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生动、刺心的描述、记录。
总而言之,《青涩年华》是一部以现实主义为基本特征,包含扎实深厚的社会生活内容,又吸收、融合、发挥了电影、诗歌等的叙述、修辞手法,从而具有自己的鲜明艺术特色和思想价值的长篇力作,值得肯定和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