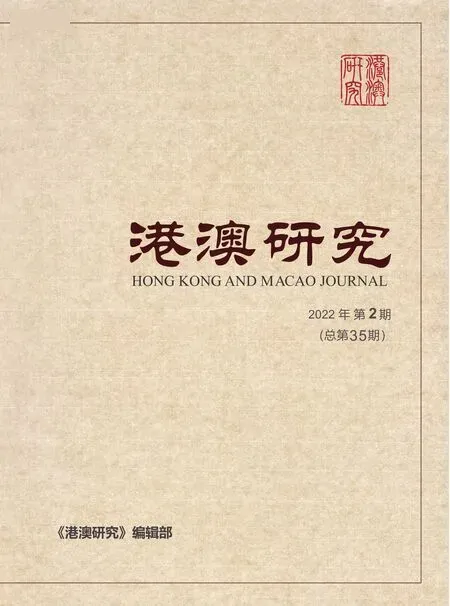香港回归25 年来对外交往的成就与未来展望
伍俐斌 赵 希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对外交往的法理基础
从国际法上讲,无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外交权完全属于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地方政府或联邦成员单位不得分享,这是关系到国家统一的主权问题,世界各国毫无例外;①王远美:《“一国两制”对我国国家结构形式的影响》,《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同时,一国地方政府或联邦成员单位又往往被依法授权享有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在经济、科技、文化、贸易等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的有限权力——对外事务权(外事权)。②广义的对外事务概念是指包括但不限于外交事务的所有对外事项,狭义的对外事务概念仅指外交事务之外的其他对外事项;有学者将对外事务权与外事权相区分,以将特别行政区享有的对外事务权与内地地方政府享有的外事权相区分,但另有学者认为这种区分并无必要,因为二者在权力性质、来源等方面完全相同,对特别行政区和内地地方政府而言,唯一不同的是权力范围不同。参见饶戈平:《香港特区对外事务权的法律性质和地位》,饶戈平主编:《燕园论道看港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姚魏:《从菲律宾人质事件看香港对外事务权》,《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12期;周露露:《国家外交权与香港对外事务权关系浅析》,饶戈平主编:《燕园论道看港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页。回归前,随着香港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英国逐步在事实上承认和允许香港享有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的自主权。①参见肖蔚云主编:《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95—398页。回归后,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3 条规定,②《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3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香港设立机构处理外交事务。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香港依法正式享有了广泛的对外事务权。那么,香港作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为什么被赋予广泛的对外事务权呢,其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一)香港特区被授予广泛对外事务权的原因
首先,香港特区被授予广泛的对外事务权,是出于对香港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尊重和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的要求。③饶戈平:《香港特区对外事务权的法律性质和地位》,饶戈平主编:《燕园论道看港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页。广泛的对外联系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必要条件。回归前香港已经是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同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官方、半官方关系,在经济、贸易等领域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订了多项协议,以单独关税区名义参加了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以地区经济体名义参加了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正是由于香港同许多国家和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和贸易交往,赋予回归后的香港更广泛的对外事务权才更有利于这种交流与合作关系的保持和发展。④参见《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就提请审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协议文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4年28期。总之,香港特区被授予广泛的对外事务权,是香港本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际社会许多成员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需要,更是中国确保香港回归后繁荣稳定的需要。⑤参见饶戈平、李赞:《国际条约在香港的适用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其次,香港特区拥有广泛的对外事务权是由其在中国国内法中的地位决定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超过中国内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甚至超过一些联邦国家的州。正是由于香港特区在如此广泛的领域中拥有自行管理和立法的权力,且香港的社会制度与内地不同,为确保香港特区能够继续保持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交往,因此有必要赋予其相应的对外交往权,包括缔结协定的权力。⑥参见邓中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对外缔约权及有关问题》,《法学评论》1993年第2期。
(二)香港特区对外事务权的法律依据
综合而言,关于香港特区对外事务权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三种学术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宪法、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共同构成香港特区对外事务权的法律依据。这种观点似乎是多数学者的观点。虽然这部分学者主要从香港特区所享有的对外缔约权来论述有关的法律依据问题,但缔约权是最重要的对外交往权力之一,据此可推断香港特区缔约权以外的其他对外事务权的法律依据也将是宪法、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⑦参见袁古洁、丘志乔:《香港、澳门回归后的部分缔约权及条约适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葛勇平:《香港国际法主体地位及其缔约权限的理论与实践》,《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5期;曾华群:《港外经济协定的实践及其法律依据》,《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张磊:《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缔结国际条约的法律权力——以修订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为视角》,《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9期。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英联合声明》是香港特区对外事务权的法律依据。这种观点主要来自西方学者。罗德·穆什卡(Roda Mushkat)认为某些领土实体如根据条约确立的“自治实体(autonomous entities)”或所谓“国际化领土(internationalized territories)”虽不符合国家的构成标准,但根据国际法仍可获得独立的法律人格,一个典型例子是根据《但泽自由条约》,但泽在1920—1939 年期间被视为由国际法原则和规则调整的具有法律人格的自由市(free cities)。①Roda Mushkat,“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Legal Person”,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6,Issue 1,1992,pp.109-110.有鉴于此,罗德·穆什卡(Roda Mushkat)认为香港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而不是国内法确立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国际法调整的、具有客观法律人格的国际实体。②Roda Mushkat,“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Legal Person”,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6,Issue 1,1992,p.110.埃里克·约翰逊(Eric Johnson)认为香港是《中英联合声明》创设的类似于中世纪时期的“自由市(free cities)”。③Eric Johnson,“Hong Kong after 1997:A Free City?”,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40,1997,pp.402-404.根据埃里克·约翰逊的定义,“自由市”通常由条约而非国内法常设,具有参与国际关系的能力,它不属于某个国家的组成部分,也不属于某个国家的自治领土。④Eric Johnson,“Hong Kong after 1997:A Free City?”,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40,1997,p.396.布莱恩·Z·塔玛纳哈(Brian Z.Tamanaha)也认为香港是一个受国际法调整的自治实体。⑤Brian Z.Tamanaha,“Post-1997 Hong Kong: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eaning of‘High Degree of Autonomy’with a Specific Look at the Commonwealth of the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China Law Reporter,Vol.5,Issue 4,1989,p.168.按照这些学者的观点,香港的法律地位由《中英联合声明》所确立,它所拥有的自治权也来自于《中英联合声明》,照此推理,香港所拥有的对外事务权也应以《中英联合声明》作为法律依据。
第三种观点认为只有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才是香港特区对外事务权的法律依据。这种观点认为香港特区不是独立的国际法主体,不当然拥有国际法上的缔约权,其缔约权是中央政府通过基本法授予的。⑥参见吴慧:《香港的缔约权以及条约在香港的法律地位》,《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6期。“一个地方实体能否成为国际条约缔结主体,或者说有否对外缔约权,从根本上应该看国内法是否给予其必要的授权,因为条约的缔结适用国际法,但缔约机关的资格则决定于有关的国家的国内法”。⑦邓中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对外缔约权及有关问题》,《法学评论》1993年第2期。饶戈平教授认为,“宪法和基本法构成香港特区对外事务权的法律依据……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是中英之间谈判缔结的一项国际协定,在这里构成条约主体并承受国际法上权利义务的是中国和英国,而不是任何第三者。香港不具备该协定谈判和缔结的主体资格,不直接享有以联合声明为据主张自己权力的法律地位。换言之,联合声明不构成香港所获高度自治权力的法律根据和来源,香港在行使自己的对外事务权时,它所依据的法律只能是基本法而不是中英联合声明”。⑧饶戈平:《香港特区对外事务权的法律性质和地位》,饶戈平主编:《燕园论道看港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15页。
对比这三种观点,可以发现争议的焦点是《中英联合声明》可否作为香港对外事务权的法律依据。
首先,不妨从缔约权与缔约能力关系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顾名思义,缔约权是指缔结国际条约的权力。但这一定义并没有回答缔约权是产生于国际法还是产生于国内法这个问题。多数学者将缔约权(treaty-making power)与缔约能力(treaty-making capacity)混合使用。①参见袁古洁、丘志乔:《香港、澳门回归后的部分缔约权及条约适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王庆海、周振坤、孟宪铎:《从国际法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缔约权及条约适用权》,《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但仔细推敲会发现二者是有明显区别的。缔约能力被认为是国际人格最重要的表现,也是国家主权的一个属性,②李浩培:《条约法概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页。另可参见Anne Peters,“Treaty Making Power”,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https://opil.ouplaw.com/view/10.1093/law:epil/9780199231690/law-9780199231690-e1494?rskey=e4d2EH&result=1&prd=MPI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27日。直接源自于国家主权。③Olivier Corten,Pierre Klein,The Vienna Conventions on the Law of Treaties:A Commenta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07.而且一个国家的缔约能力,不以它已被其他国家承认为条件。④李浩培:《条约法概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页。虽然《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 条规定“每一个国家都有缔结条约的能力”,但国家的缔约能力并不产生于该条的规定,缔约能力是任何国际法主体固有的、内在的能力或权力,⑤Hersch Lauterpacht,“Report on the Law of Treatie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Vol.II,1953,p.100;Antonio Cassese,International Law,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38.《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 条只不过是对国家缔约能力的确认。缔约权是缔约能力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是国家内部某一机关所具有的对外缔结条约的权限。而这种国家内部缔约权限的分配由该国国内法进行安排。安妮·皮特斯(Anne Peters)虽然也将缔约权与缔约能力混合使用,但她认为缔约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国家的缔约权和国内某个单位或实体的缔约权,前者由国际法调整,后者由该国国内法调整。⑥Anne Peters,“Treaty Making Power”,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https://opil.ouplaw.com/view/10.1093/law:epil/9780199231690/law-9780199231690-e1494?rskey=e4d2EH&result=1&prd=MPI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27日。安妮·皮特斯所称国家的缔约权实际上等同于国家的缔约能力。概而言之,缔约能力与缔约权是有区别的:前者由国际法调整,是固有的、内在的能力或权力;后者由国内法调整,是一国内部不同机关的缔约权限。就我国而言,缔约能力(或者如安妮·皮特斯所称国家的缔约权)是我国国家主权的体现,是固有的、内在的能力或权力;同时根据《缔结条约程序法》等国内法律,具体的缔约权由不同机关行使。例如,根据《缔结条约程序法》第4—6 条的规定,国务院、外交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部门分别行使不同的缔约权限。因此,从缔约权与缔约能力的区别可以看出:一方面,香港特区不具有国际法上的缔约能力,它的缔约权不由国际法调整,也不由《中英联合声明》调整;另一方面,香港特区的缔约权来源于中央的授权,并非其固有的、内在的权力。具体而言,香港特区的这种缔约权由香港基本法规定和调整,是一种国内法上的权力。简言之,香港特区不具有国际法上的缔约能力,而只拥有国内法上的缔约权。
其次,从《中英联合声明》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看,声明不能成为香港对外事务权的法律依据。《中英联合声明》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国际法上的双边条约。在国际法上,只有条约的缔约主体(或称为当事方)才能享有条约下的权利,承担条约下的义务。《中英联合声明》的缔约主体是中国和英国,只有中国和英国才享有该声明所产生的权利,承担该声明所产生的义务。而香港不是缔约主体,因此不能直接承受《中英联合声明》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确切地说,香港是《中英联合声明》的客体或者对象。这一点也可以从《中英联合声明》的全称得到证实。《中英联合声明》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由此可知《中英联合声明》处理的是香港回归问题,即香港是《中英联合声明》的客体或者对象。作为客体或者对象,它不能承受《中英联合声明》下的权利和义务。《中英联合声明》第3 条及附件一规定香港可以拥有一定的对外事务权,但这不是直接赋予香港某项条约权利。《中英联合声明》第3 条及附件一是中国的单方面声明,是中国政府作出的承诺,也可以认为是中国政府承担的一项国际义务。概言之,香港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客体或者对象,不能直接享有声明下的权利。即使《中英联合声明》第3 条及附件一规定,香港可以拥有一定的对外事务权,它并不能因此就直接获得声明下的某些权利,而是需要在中国政府履行国际义务、在国内法上作出适当安排后,才能享有对外事务权。
再次,也可以从条约的国际效力和国内效力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条约的效力可以分为国际效力和国内效力。条约的国际效力是指条约对当事国的约束力,指一个国家参加条约后,要遵守条约的规定,履行条约的义务;条约的国内效力是指条约在当事国国内的效力,是指条约如何在当事国国内得到落实的问题,是当事国国内机关适用或实施条约的问题。①李鸣:《应从立法上考虑条约在我国的效力问题》,《中外法学》2006年第3期。换言之,对当事国产生法律效力并不等于在当事国国内获得了法律效力,不应认为条约一旦对一个国家开始生效它就在该国生效,它就成为该国国内法的一部分,②[英]安托尼·奥斯特:《现代条约法与实践》,江国青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6页。而是当事国必须按照其国内法规定的程序将条约规则转变为国内法规则,从而使条约在国内得到履行。而怎样给予条约以国内法上的效力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宪法。③[英]安托尼·奥斯特:《现代条约法与实践》,江国青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8页。
据此,对中国而言,《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效力是指中国要遵守声明的规定,履行声明的义务;《中英联合声明》的国内效力是指中国要按照国内法规定的程序将有关的条约规则转变为国内法规则,从而使条约规则在国内得到落实。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是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关于特别行政区的具体制度也由宪法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律予以规定。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根据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制定了香港基本法,基本法对香港特区的对外事务权作了具体规定。换言之,我国是以制定香港基本法的方式具体落实《中英联合声明》,将声明中有关香港对外事务权的承诺(国际义务)转化为国内法规则。对外而言,这是中国政府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履行了有关国际义务;对内而言,这是中国政府以国内法方式授权香港特区行使一定的对外事务权。
综上所述,从缔约权的内涵特别是与缔约能力的区别、《中英联合声明》的权利义务关系和条约的国际效力与国内效力等方面来看:香港特区不享有国际法上的缔约能力,只拥有国内法上的缔约权;香港不是《中英联合声明》的缔约主体,而是《中英联合声明》的客体或者对象,不能直接承受声明下的权利义务;香港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落实《中英联合声明》的国内法,声明中有关香港对外事务权的规定也是通过香港基本法落实。简言之,《中英联合声明》不是香港特区对外事务权的法律依据或权力来源,只有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才是香港特区对外事务权的法律依据或权力来源。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对外交往的主要成就
除香港基本法第13 条外,香港基本法第七章及第96、116、129、130、132、133、134、149 条等条款也授予香港特区广泛的对外交往权力,为维护、拓展香港的对外交流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回归以来,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特区对外交流合作取得巨大成就,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体现。
(一)对外缔结双边协定
香港特区的缔约权来源于中央政府的授权,不具有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缔约权限,只具有有限的、限于基本法规定范围的缔约权。①参见饶戈平:《香港特区对外事务权的法律性质和地位》,饶戈平主编:《燕园论道看港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页。香港基本法对香港特区缔约权的授权方式可以分为一次性授权、具体授权和另行授权三种类型。
首先,香港基本法第151 条一次性授权香港特区可以“中国香港”名义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签订有关协议。香港基本法第116 条关于香港可以“中国香港”名义“参加《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关于国际纺织品贸易安排等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贸易协定,包括优惠贸易安排”的规定也被认为属于一次性授权。②参见马新民:《香港特区适用、缔结和履行国际条约的法律和实践:延续、发展和创新》,饶戈平主编:《燕园论道看港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8页。同时,马新民参赞在该文指出,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51条,原则上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自行对外缔结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但2003年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外国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范本新增了资料交换条款,规定当事方“可在公开法庭程序或法庭判决中透露有关资料”,考虑到此项规定涉及司法协助事宜,属于基本法规定的须经中央政府具体授权的事项。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享有缔结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一次性授权的同时,对于上述税收资料交换条款,应获得中央政府的具体授权。在一次性授权领域,香港特区对外缔结协定时无须再获得中央政府的授权。
其次,在涉及国家主权的特定领域,香港基本法采取具体授权的方式允许香港特区对外缔结有关协议。在具体授权领域,中央政府主要采取事先逐案授权香港特区缔约的方式。香港基本法第96 条规定经中央政府协助或授权,香港特区可与外国就司法互助关系作出适当安排;第133条规定经中央政府具体授权,香港特区可与外国签订、续签或修改民航协议;第134 条规定经中央政府授权,香港特区可与外国签订执行第133 条所指民航协议的各项安排;第155 条规定中央政府协助或授权香港特区对外缔结互免签证协议。简言之,在司法互助、民航、互免签证等领域,香港基本法采取具体授权的方式,授权香港特区对外签订有关协议。
再次,对于香港基本法没有规定香港特区可以缔约的领域,中央政府可根据需要,依据香港基本法第20 条“另行授权”香港特区对外缔结有关协议。在另行授权领域,中央政府也是采取事先逐案授权的方式。
为保障香港顺利回归和繁荣稳定,中国政府同意英国政府授权香港与澳大利亚等国签订的46 项双边协定在回归后继续适用。这46 项双边协定包括16 项航空运输协定、3 项避免双重课税协定、6 项移交被判刑人协定、4 项移交逃犯协定、9 项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和8 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此外,香港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近百个互免签证协定。①参见饶戈平、李赞:《国际条约在香港的适用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 年,第87 页;王西安:《国际条约在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适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回归后,香港特区根据香港基本法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缔约权,签订了更多的双边协定。
首先,在一次性授权领域,香港特区与50 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其中仅与美国的协定签订于回归前,但美国于2020 年8 月单方面终止了该协定;②香港特区律政司:《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列表(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https://www.doj.gov.hk/tc/external/table6ti.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30日。与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智利及格鲁吉亚等6 个经济体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且全部在回归后签订;③香港特区律政司:《自由贸易协议(截至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一日)》,https://www.doj.gov.hk/tc/external/table11ti.html,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现有4 个成员国:冰岛、挪威、瑞士和列支敦士登,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30日。与新西兰签订了环保合作协定;④香港特区律政司:《环保合作协议(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三日)》,https://www.doj.gov.hk/tc/external/table9ti.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30日。与冰岛、挪威、瑞士等三国分别签订了农业协定;⑤香港特区律政司:《农业协定(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https://www.doj.gov.hk/tc/external/table13ti.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30日。与智利、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新西兰等签订了劳务合作协定;⑥香港特区律政司:《劳务合作安排(截至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日)》,https://www.doj.gov.hk/tc/external/table10ti.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30日。与欧洲共同体签订了海关合作及相互行政协助协定;⑦香港特区律政司:《中国香港和欧洲共同体关于海关合作及相互行政协助的协定》(1999年5月13日签订),https://www.doj.gov.hk/tc/external/pdf/HKC_EC_CCA_chi.pdf,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30日。与以色列签订了资讯科技及通讯合作事宜协定。⑧香港特区律政司:《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以色列国政府就资讯科技及通讯合作事宜签订的协议》(2000年3月7日签订),https://www.doj.gov.hk/tc/external/pdf/israel_agreement_Ch.pdf,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30日。
其次,在具体授权领域,香港特区与67 个国家签订了民用航空运输协定或民用航空运输过境协定,其中与47 个国家的前述协定是在回归以后签订的;⑨香港特区律政司:《民用航空运输协议及国际民航过境协议列表(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九日)》,https://www.doj.gov.hk/tc/external/table1ti.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16日。与31 个国家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全部在回归后签订,但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十国的协定已经被对方单方面中止;⑩香港特区律政司:《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列表(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https://www.doj.gov.hk/tc/external/table3ti.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16日。与19 个国家签订了移交逃犯协定,其中与17 国的协定签订于回归后,但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9 国的协定已经被对方单方面中止;①香港特区律政司:《移交逃犯的协定列表(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九日)》,https://www.doj.gov.hk/tc/external/table4ti.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16日。与15 个国家签订了移交被判刑人协定,全部在回归后签订,但美国在2020 年8 月单方面终止了该协定;②香港特区律政司:《移交被判刑人的协定列表(截至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一日)》,https://www.doj.gov.hk/tc/external/table5ti.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16日。与7 个国家或地区签订税务交换资料协定,全部在回归后签订;③香港特区律政司:《税务数据交换协定(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七日)》,https://www.doj.gov.hk/tc/external/table12ti.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16日。回归后新增互免签证协定10 项。④香港特区律政司:《其他协定》,https://www.doj.gov.hk/tc/external/international_agreement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16日。
最后,在另行授权领域,香港特区与东盟、英国、法国等签订了22 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其中15 项协定在回归后签订。⑤香港特区律政司:《促进和保护投资协议/投资协议列表(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六日)》,https://www.doj.gov.hk/tc/external/table2ti.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16日。
(二)参与国际多边活动
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是重要的多边国际舞台。香港基本法授权香港特区以适当身份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在中央支持下,香港在回归后广泛参与国际多边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果。
首先,参加国际组织。根据香港特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的数据,香港特区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或其他适当身份参与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共37 个,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等;⑥香港特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https://www.cmab.gov.hk/gb/issues/external1.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16日。香港特区以“中国香港”名义参加的不限主权国家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共60 个,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⑦香港特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组织》,https://www.cmab.gov.hk/gb/issues/external2.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16日。
其次,国际组织在港设立机构。经中央政府与有关国际组织达成协议,欧盟、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和常设仲裁法院等国际组织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⑧香港特区律政司:《国际机构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或运作的协定和安排(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https://www.doj.gov.hk/sc/external/table7ti.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16日。
最后,香港同胞到国际组织任职。在中央的支持和协助下,2006 年香港特区卫生署原署长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为首位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中担任最高职位的中国人,并于2012 年连任,在任长达十年。2019 年国家推送首批5 名香港青年人才赴联合国任职,⑨外交部驻香港特区特派员公署:《国家推送香港青年赴联合国任职实现零的突破》,http://hk.ocmfa.gov.cn/chn/zydt/201912/t20191223_6089236.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16日。2021 年再度推动5 名香港青年分赴不同国际组织任职。⑩外交部驻香港特区特派员公署:《外交部驻港公署举办“香港特区青年人才赴国际法律组织任职发布仪式”》,http://hk.ocmfa.gov.cn/chn/zydt/202109/t20210910_9522555.htm,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16日。
(三)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互设机构
香港基本法授权香港特区可以对外设立经济、贸易机构。根据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数据,香港特区在日内瓦、布鲁塞尔、伦敦、柏林、曼谷、迪拜、雅加达、新加坡、悉尼、东京、多伦多、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等世界主要城市设立了14 个经济贸易办事处。①香港特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经济贸易办事处》,https://www.cedb.gov.hk/sc/trade-and-investment/economic-andtrade-office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16日。
据香港特区礼宾处数据,经中央政府与有关国家达成协议,当前外国在香港设立的总领事馆达64 个、名誉领事馆56 个。②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礼宾处:《领馆及官方认许机构》,https://www.protocol.gov.hk/sc/posts_bodies.html#General_area,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19日。
(四)发放护照及出入境管理
香港基本法授权香港特区签发护照和旅行证件,并享有出入境管理权。经中央政府授权和协助,香港可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订互免签证协定。根据香港入境事务处的数据,当前已有168 个国家和地区给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持有人免签证或落地签证安排。③香港特区入境事务处:《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免签证或落地签证情况一览表》,https://www.immd.gov.hk/hks/service/travel_document/visa_free_acces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20日。
香港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在此居住和生活。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21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在香港的外国人约60 万,占香港总人口的8%。④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二零二一年人口普查简要结果》,https://www.censtatd.gov.hk/sc/press_release_detail.html?id=5156,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20日。
(五)对外经贸合作
回归后香港对外经济联系深入发展,国际经济地位显著提升。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1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香港在2020 年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约1192 亿美元,居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内地;截至2020 年底,香港吸收外来直接投资存量18849 亿美元,居全球第四位,仅次于美国、英国和中国内地。2021 年9 月,特区政府发布回归后的首份《香港营商环境报告》,该报告显示2020 年香港升至全球第六大货物贸易经济体,全年货物贸易总额约82000 亿港元。
据《香港营商环境报告》,2020 年香港境外母公司设立的驻港公司数目达9025 家,包括1504 家地区总部、2479 家地区办事处和5042 家当地办事处。其中内地1986 家、欧盟1560 家、日本1398 家、美国1283 家、英国665 家、新加坡453 家。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对外交往的意义与展望
国际化是香港的重要特征,也是香港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因素。香港回归后被授予广泛的对外事务权,对外交往成就显著,不仅有利于其保持繁荣稳定,而且对国家也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应坚持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继续支持香港巩固、拓展对外联系。
(一)香港特区对外交往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香港广泛的对外联系对实现国家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其一,香港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和节点。2015 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要发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2017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对“充分发挥香港的国际经贸、金融和专业优势,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作出了安排。2021 年商务部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关于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支持香港以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平台,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其二,香港广阔的国际经贸网络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依托港澳的海外商业网络和海外运营经验优势,推动大湾区企业联手走出去;要充分发挥港澳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支持香港、澳门依法以“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名义或者其他适当形式,对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参加有关国际组织,携手开拓国际市场;充分发挥港澳对外贸易联系广泛的作用,探索粤港澳共同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新模式,等等。
其次,香港广泛的对外联系是国家“外循环”的重要节点。从推动贸易往来,到引入外商投资、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再到深化金融市场双向联通,香港历来是内地与全球联系的重要窗口和桥梁。目前,三分之二进出内地的直接投资取道香港,而外资的内地股票和债券投资当中,有超过一半是通过香港进行的,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超过一半为内地企业,占香港股市总值约80%。①刘应彬:《从挑战中寻找机遇:香港金融业如何支持大湾区的发展》,香港金融管理局,https://www.hkma.gov.hk/gb_chi/news-and-media/speeches/2021/12/20211213-1/,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24日。香港是全球第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占全球人民币支付交易约75%,②鄂志寰:《融入双循环 打造香港新优势》,大公网,http://www.takungpao.com/finance/236134/2021/0824/623830.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 年3 月24 日。陈茂波:《香港目前处理全球约75%离岸人民币结算业务》,观点网,https://www.guandian.cn/article/20211212/278376.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24日。助推国家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香港还是内地对外贸易的重要转口港。2020 年内地约10.1%的出口货物(2632 亿美元)和14.3%的进口货物(2952 亿美元)通过香港转口。③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进出口贸易业概况》(2021 年8 月23 日),https://research.hktdc.com/sc/article/MzEzODkxODY0,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24日。
再次,香港与国际接轨的经贸规则是国家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典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国内规则体系是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规则制定权或者话语权的基础。香港法治健全,经贸规则接轨国际,营商环境世界一流。世界银行《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香港的营商环境在全球190 个经济体中排第三位。因此,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主动学习香港经贸规则,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既能促进内地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又有利于国家参与、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
最后,香港国际经济地位可以助力国家反制美国的对华全面竞争战略。特朗普时期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对华实施全面脱钩政策,拜登延续了脱钩政策,但将全面脱钩调整为精准脱钩。④张薇薇:《从“全面脱钩”到“精准脱钩”:拜登对华竞争策略转变》,国际网,http://comment.cfisnet.com/2021/0810/1323612.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30日。在金融领域,美国从特朗普到拜登都在推动对华资本切割。⑤孙立鹏:《美国加紧对华经贸“脱钩”》,《世界知识》2020年第12期。特朗普执政末期,美国于2020 年12 月正式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该法实质是为中国在美上市企业量身定做的新规,欲收紧乃至切断中国企业通过美国资本市场融资的渠道。拜登上台后,于2021 年6 月签署《应对为中国特定公司提供资金的证券投资所带来的威胁行政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21 年12 月正式发布《外国公司问责法》实施细则,进一步落实对华资本切割。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具有“反脱钩”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国对华资本切割政策的负面影响。香港金融法治和规则对内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可以协助内地金融领域改革开放,从而增强内地抵御美国对华资本切割的“内功”。
(二)高度重视香港特区拓展对外联系面临的挑战
香港对外交流合作的外部环境深受中美关系影响。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时期深陷困境,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不仅未走出困境,反而遭遇更多挑战。美国对港政策从属于对华政策,服务和服从于美国对华整体战略目标。中美关系的持续困境使香港对外交流合作的外部环境趋紧,香港成为美国重点制裁对象,如2020 年美国暂停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禁止向香港出口国防设备和敏感技术、对特区政府官员实施制裁、中止或终止与香港之间的三项协议等等。拜登上台后,美国继续沿用前述政策。除美国外,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也中止或终止了与香港之间的有关协议。因此,在中美关系未有根本性好转的情况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香港对外交流合作的外部环境仍将充满挑战。
此外,从香港对外交往的现状来看,香港更偏重与欧美的对外联系,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合作比较薄弱。例如,香港对外签订的贸易、投资等协议的对方当事国多为欧洲国家,司法合作方面的协议则全是欧美国家。这种对外交流合作的不平衡状态,可能令香港的对外联系受制于欧美,香港亟需拓展与欧美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交流合作。
(三)继续支持香港特区巩固、拓展对外联系
首先,加强国家外交权与香港特区对外事务权的协调。香港特区对外事务权源自中央政府的授权,必须服从于国家外交权,服从于国家整体的外交政策和对外立场,必须接受国家的监督。①参见周露露:《国家外交权与香港对外事务权关系浅析》,饶戈平主编:《燕园论道看港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页;饶戈平:《香港特区对外事务权的法律性质和地位》,饶戈平主编:《燕园论道看港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页。香港回归后,“刚果(金)案”“菲律宾人质事件”等曾引发关于国家外交权与特区对外事务权关系的争议与讨论。对此,国家应建立关于香港特区对外事务权的指导和监督机制;特区政府在处理具体的对外事务时,应主动征求外交部驻港公署的意见,外交部驻港公署也应加强对特区政府处理对外事务的指导。
在香港特区对外缔结协定方面,《缔结条约程序法》既没有专门对特别行政区的缔约权作出安排,②1990年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在向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根据中英和中葡联合声明,未来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经中央人民政府(即国务院)授权,可在一定领域内直接同外国缔结条约性文件,这一点已在香港基本法中作出了规定,在将要制定的澳门基本法中也将作出规定。这是根据‘一国两制’情况形成的特殊例外,《缔结条约程序法(草案)》未涉及。”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0年第6期。也不在特别行政区实施。在香港特区有权自行或单独缔约的领域,特区政府自行审批有关协定的缔结和生效,并自行对外办理相应程序,协定通常在签署后即按协定规定生效,不需要特区立法机关批准。①马新民:《香港特区适用、缔结和履行国际条约的法律和实践:延续、发展和创新》,饶戈平主编:《燕园论道看港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7页。由于香港特区采取不同于内地的缔约程序,为确保香港特区对外缔结的协定与国家外交政策和对外立场不相冲突,香港特区可就对外缔结协定进行本地立法,对谈判、签署、审批等事宜作出规定;国家在修改《缔结条约程序法》时,可增加香港特区(包括澳门)行使缔约权的具体规定。②参见黄德明、左文君:《国际法治视野下的缔约权——兼论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的修改》,《公民与法》2011年第1期;张磊:《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缔结国际条约的法律权力——以修订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为视角》,《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9期。
其次,巩固国际社会对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的承认。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受香港基本法保障,且以单独关税区身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因此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不取决于个别国家的承认。但在香港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贸关系中,其他国家或地区承认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是该国或该地区视香港为单个经济体并与之平等交往的重要前提。一旦该国或该地区不再承认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香港与该国或该地区的交流合作以及香港的国际地位将受到负面影响。目前仅美国公开宣布暂停承认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对香港与美国的经贸关系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鉴于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对香港对外经贸关系发展和繁荣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时应力促美国重新承认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和取消对港制裁措施,支持香港更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活动,支持香港与更多国家或地区签订经贸协定,等等。
再次,支持香港拓展对外交流合作关系。应坚定支持香港巩固提升三大国际中心地位,与更多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等在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建立联系或签订协定,支持更多香港专业人士担任国际组织高级职位和更多香港青年到国际组织实习或工作。香港在继续巩固与欧美国家交流合作的同时,应加强与东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支持香港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支持香港设立更多驻外经贸机构等。
最后,将国家层面签订的贸易、投资类协议适当扩大适用于香港。目前香港单独对外签订的贸易、投资类协定数量仍然有限,而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由香港较普遍地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谈判、签订协定可能也不现实。为解决这一问题,可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53 条的规定,经征询香港特区政府意见,并与对方当事国协商,将国家签订的贸易、投资类有关协定,扩大适用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