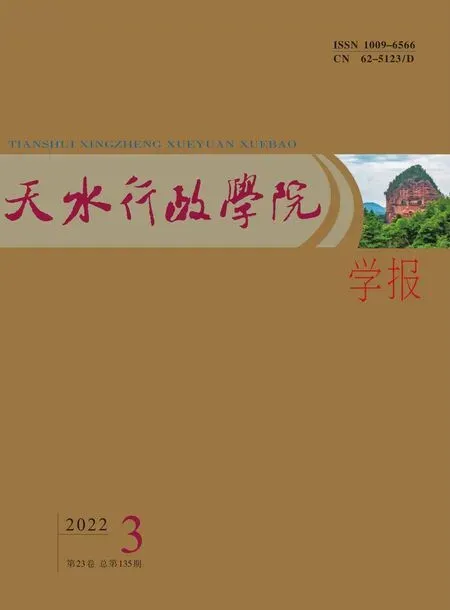朱熹对孔子圣人形象的维护
——“生知”与“学知”的矛盾及其解决
都兰雅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论语·季氏》载:“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提出了“生而知之”的说法。《论语·述而》 载:“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直言自己并非“生而知之”。《论语·为政》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这是暮年孔子对自己一生进境的回顾与总结,单纯从《论语》文本的字面意思来看,很自然会认为孔子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学而渐知。然而,朱熹解《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章,引尹氏之言称孔子“生知之圣”;朱熹解《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说“圣人生知,理固已明,亦必待十五而志于学”,认为孔子“圣人生知”。朱熹为了维护孔子的圣人形象,坚持孔子“生知”的说法。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以“生知”思想为论题的专题论文有十多篇。其中刘克兵、向春叶在其《朱熹“生知”的提出及其内涵》一文中,论述了朱熹在关于知识的来源上承认“生知”的观点[1];石磊在其《对“生知”思想的再解读》一文中,论述了生知思想与儒家的圣人信仰和天道信仰密不可分[2]。但关于朱熹是如何采取“生知”的观点来维护儒家的圣人信仰的这一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本文着眼于朱熹对《论语》的解读,试从孔子“生知”的说法出发,阐述朱熹用来维护孔子的圣人形象的诠释策略,以及反思朱熹这种诠释策略的局限,并尝试推测朱熹不得不采取孔子“生知”说法的理由。
一、朱熹对孔子“生知”的理解和诠释
“生知”的说法最早见于《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以及《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对于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又说“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从文义可以推断“生而知之”与“敏以求之”是不同的或者说是相反的。“生而知之”指生来就知,“敏以求之”则强调学的重要性。这章有两处难解:一是孔子是否是“生而知之者”?二是孔子为何要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对于孔子将人大约分为“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和“困而不学”者四等,从文义可以推断出从“生而知之”到“困而不学”是层次递降的关系,孔子表述了人可能出现的不同的认知类型。这章有三处难解:一是“生而知之者”对应什么人?二是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划分了人在认知上的差异,那么决定人在认知上的差异的根源是什么?三是“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中的“之”是指什么,也即“知”与“学”的对象是什么?”在研究朱熹对这两章的解读之前,有必要回顾朱熹以前学者对这两章的注解,为考察朱熹对孔子“生知”的理解和诠释提供历史背景。其中尤以邢昺《论语注疏》、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的解释最有代表性。
关于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又说“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北宋邢昺《论语注疏》引东汉郑玄注曰:“言此者,劝人学。”邢昺疏曰:“正义曰:‘此章劝人学也。恐人以已为生知而不可学,故告之曰:我非生而知之者,但爱好古道,敏疾求学而知之也。’”[3]可见,郑玄、邢昺没有明确表明孔子是否是“生而知之者”,并将此章所言之目的解读为“劝人学”。南北朝时期皇侃《论语集解义疏》 中疏曰:“孔子谦以同物。故曰我有所知非生而自然知之者也。玉藻云:此盖自同常教以身卒物者也。‘云好古敏而求之者也者’我既不生知而今有所知者。政由我所好古人之道疾速以求知之也。敏疾速也。”[4]可见,皇侃不同意孔子非“生而知之者”,而认为此章孔子所言乃是孔子的谦辞。
关于孔子将人大约分为“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和“困而不学”者四等,皇侃《论语集解义疏》释之曰:“此章劝学也,故先从圣人始也。若生而自有知识者,此明是上智圣人,故云上也。”[5]可见,皇侃认为“生而知之者”指圣人。邢昺《论语注疏》疏曰:“正义曰:‘此章劝人学也。生而知之者,上也者,谓圣人也。’”[6]可见,邢昺也认为“生而知之者”指圣人。对于决定人认知上的差异的根源,邢昺、皇侃未论及。
朱熹明确指出孔子是“生知之圣”。朱子《论语集注》解“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说:“生而知之者,气质清明,义理昭著,不待学而知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圣,每云好学者,非惟勉人也,盖生而可知者义理尔,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实也。’”[7]可见,朱熹引用尹焞之言称孔子为“生知之圣”。朱熹的解读认为孔子是“生而知之者”,实际上沿袭了皇侃对此章的观点,超出了经典文本的字面意思,不同于邢昺《论语注疏》对此章的解读,邢昺对此章的注疏并没有直接表明孔子是“生而知之者”,也没有明确质疑这是孔子对自己能力的描述。关于孔子为何要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朱熹沿袭了邢昺《论语注疏》“劝人学”的解读,同样解读为勉励人学。
朱熹肯定人禀受天之正理,圣人由于禀气清明而无人欲之杂,其本来禀受天之正理无所障蔽,这是圣人所固有的本性,自然符合天理,所以说“生而知之”;而不及圣人的人由于禀气驳杂而有人欲之累,故需要经过后天努力才能消除心中私意私欲对于天理的障蔽。他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8]心是人的主体精神,而性是天所赋予、人所禀受而存于人心中之天理,或者说天理落实于人心之呈现。朱熹对“生而知之”的主要含义作了明确解释:“生而知之者,气质清明,义理昭著,不待学而知也。”其中,“气质清明”从本体论基础的角度肯定了“生而知之”。朱子《论语集注》解孔子将人大约分为“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和“困而不学”者四等,说:“言人之气质不同,大约有此四等”,以“气质不同”说明了孔子所提出的“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的分类的本体论基础。朱熹认为孔子将人大约分为“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和“困而不学”者四等,产生这四类差别的原因,或者说划分这四等的依据,也即决定人认知上的差异的根源,是人的“气质”。朱熹在《论语或问》中复阐释道:“人之生也,气质之禀,清明纯粹,绝无渣滓,则于天地之性,无所间隔,而凡义理之当然,有不待学而了然于胸中者,所谓生而知之圣人也。其不及此者,则以昏明、清浊、正偏、纯驳之多少胜负为差。其或得于清明纯粹而不能无少渣滓者,则虽未免乎小有间隔,而其间易达,其碍易通,故于其所未通者,必知学以通之,而其学也,则亦无不达矣,所谓学而知之大贤也。或得于昏浊偏驳之多,而不能无少清明纯粹者,则必其窒塞不通然后知学,其学又未必无不通也,所谓困而学之众人也。至于昏浊偏驳又甚,而无复少有清明纯粹之气,则虽有不通,而懵然莫觉,以为当然,终不知学以求其通也,此则下民而已矣。”[9]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也有相关论述:“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然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浊之异。故上知生知之资,是气清明纯粹,而无一毫昏浊……。其次则亚于生知,必学而后知,必行而后至。又其次者,资禀既偏,又有所蔽。”[10]孔子分人为四类,从而有四等,朱熹以“气质”解释,因为人之“气质之禀”不同,具体言之,所禀之“气”“清明纯粹,绝无渣滓”,本来禀受天理无所障蔽,本性自然符合天理,则为“生而知之者”;所禀之“气”因“昏明、清浊、正偏、纯驳之多少胜负”之不同,心中私意私欲对于天理有所障蔽,则有“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困而不学”者之别。由此可知,朱熹不仅解释了“生知”的“圣人”是如何可能的,还讨论了次于圣人的人存在的原因,巩固了孔子所提出的“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的分类。故而朱熹强调“尊德性”的工夫,敦促人们通过存养心中所具之天理来极尽道德本体之全体大用,具体工夫包括消除心中私意私欲对于天理的障蔽,涵泳已经知道的与敦笃已经做到的。他说:“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11]
朱熹认为圣人“生知”无需“学”,由于圣人“生知”不需要学,因而不存在积累渐进的过程。他说:“生知之圣,不待学而自至。”[12]“愚谓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13]那么,是否意味着朱熹主张“生知”与后天的“学”是互斥的?首先,朱熹明确表达了“生知”不需要“学”,但是,“生知”并不会阻碍“学”。 《论语》 中孔子以“好学”自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朱熹注曰:“夫子生知而未尝不好学。”[14]根据朱熹释《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章曰:“生而知之者,气质清明,义理昭著,不待学而知也”,以及朱熹释《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章引述尹焞的话曰:“盖生而可知者义理尔,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实也”可知,朱熹认为“生知”与后天的“学”并不互斥,因为所谓“生而知之”并不等同于无所不知,朱熹将“生知”限制在“义理”层面上,孔子“生而知之”是指他“义理昭著”,即表现出对“义理”的全面理解,“不待学”就掌握的是“义理”,他仍然必须经过“学”才能获得有关礼仪、音乐、历史事件等方面的专门知识。
那么,在朱熹对“生知”的理解和诠释中,“生知”与后天的“学”之间的联系是必要的吗?也就是说,那些必须经过“学”才能获得的“礼乐名物,古今事变”等特定知识,对于孔子来说是必不可少吗?孔子是否有必要获得“义理”以外的知识?在《论语精义》中,朱熹引述了范祖禹的话来说明“学”对于“生知”的“圣人”的重要性:“范曰:……圣人虽有生知之性,欲致其道,未有不由学也。”[15]可见,范祖禹认为圣人虽生而知义理,如果想要实现“道”,也是需要“学”的。但是,朱熹也表明:“圣人紧要处,自生知了。其积学者,却只是零碎事。”[16]可见,朱熹认为“学”只是对圣人“生知”的“义理”的额外补充,朱熹预计由“学”产生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为了捍卫孔子的圣人形象,朱熹认为“生知”与后天的“学”之间的联系不是必要的。此外,朱熹强调的格物穷理致知的工夫所要得到的知识,其实也不在于具体事物的见闻之知,而在于义理之知、德性之知。朱熹说:“如今说格物,只晨起开目时,便有四件在这里,不用外寻,仁义礼智是也。如才方开门时,便有四人在门里。”[17]又说:“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镜子,本全体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使四边皆照见,其明无所不到。”[18]在朱熹看来,穷究物理可作为发明义理的手段,格物穷理致知的关键在于去除物欲对本心的障蔽以发明天赋仁义礼智之德性。
二、朱熹对“生知”的说法与指向“学知”的文本之间矛盾的疏解
朱熹认为孔子是“生知”的“圣人”,那么如何在“生知”的定位下理解孔子对自己一生进境的自述呢?《论语·为政》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的生命历程,体现了孔子的为学次第与进德阶序。根据朱熹的注解,“天命”是“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至所以当然当然之故也”[19],可见“天命”包含“义理”之意。由此可知,这段话表明,孔子并非天生就完全掌握“义理”,而是凭借强烈的智识渴求、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学而渐知”,最终达致了“从心所欲不踰矩”的自由之境,这与前面提到的朱熹认为孔子“生而知之”“义理昭著”不相契合。朱熹“生知”的说法如何涵容指向“学而渐知”的《论语》文本呢?“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一章有两处难解:一是这是孔子自述真实的人生经历吗?二是孔子此章所言之目的在于?在探究朱熹对此章的解读之前,有必要回顾朱熹之前此章的诠释史,为考察朱熹如何在“生知”的定位下诠释与涵容孔子指向“学而渐知”的进境自述提供历史背景。
王充提到“十有五而志于学”时,说:“所谓神者,不学而知。所谓圣者,须学以圣。以圣人学,知其非圣。”[20]可见,王充强调孔子所言“十有五而志于学”表明了“学”以成“圣”。韩愈《论语笔解》对于同章“五十而知天命”解为:“天命深微至赜,非原始要终一端而已。仲尼五十学《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曰知天命。”[21]可见韩愈也以“学而渐知”理解之。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引东晋时期李充对“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的解读:“圣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接世轨物者,曷尝不诱之以形器乎?黜独化之迹,同盈虚之质,勉夫童蒙而志乎学,学十五载,功可与立,自学迄于从心,善始令终,贵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约之以礼。为教之例,其在兹矣。”[22]在李充看来,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的本质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圣人为了“接世轨物”而设定的“为教之例”。这意味着,李充认为这段话是孔子的自述,但其所述并非圣人真实的经历过程,而是圣人用来教化常人的示范;孔子之所以要将其说成是自己的人生经验,目的是以其亲身经历来劝导常人,以其现身说法来“勉夫童蒙”。皇侃将李充之说概括为“隐圣同凡”:“此章明孔子隐圣同凡,学有时节,自少迄老,皆所以劝物也。”[23]北宋邢昺继承“隐圣同凡”之说,《论语疏证》云:“此章明夫子隐圣同凡,所以劝人也。”[24]对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程颐说:“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学而至,所以勉进后人也……”又说:“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者,圣人未必然,但为学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后进,成章而后达耳。”[25]可见,程颐认为此章既是“为学者立法”即勉进后人,便意味着孔子的生命体验“未必然”,实际上意味与孔子的真实生命与真切体验无关。
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的进境,朱熹对于这是否是孔子的真实经历的问题,持不可知的态度。朱熹说:“圣人此语,固是为学者立法。然当初必亦是有这般意思,圣人自觉见自有进处,故如此说。圣人自说心中事,而今也不可知,只做得不可知待之。”[26]又说:“愚谓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间,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学者以是为则而自勉,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讬也。”[27]据此可知,朱熹认为圣人对“进处”是“自觉”“独觉”的,从而“自名”“自说”,而不在圣人之位上的凡人对此无法揣度,“只做得不可知待之”才是尊重圣人、不加揣度的严谨态度。朱熹将程颐的解释思路称为“假设”:“伊川用作假设说”[28],“假”,即指程颐所说的“圣人未必然”,这与李充、邢昺所说的“隐圣同凡”的意涵相一致。“设”可以理解为程颐所说的“为学者立法”,这与李充、邢昺所说的“为教之例”“勉人志学”的意涵相一致。朱熹的解读避免了程颐“假设”中“假”的解释思路与李充、邢昺所说的“隐圣同凡”中“隐”的解释思路所存在的问题,即如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并非孔子的真切感受与如实描述,而不过是一种善意的虚构,那么“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起头的“吾”字就会虚化,并且与《论语·述而》“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的自陈相违背。朱熹的理解意味着,圣人对其“进处”的“自觉”“自名”并非学者应该着意的问题。朱熹又说:“圣人不到得十年方一进,亦不解悬空说这一段。大概圣人元是个圣人了,它自恁地实做将去。它底志学,异乎众人之志学;它底立,异乎众人底立;它底不惑,异乎众人之不惑。”[29]“圣人生知,理固已明,亦必待十五而志于学。但此处亦非全如是,亦非全无实,但须自觉有生熟之分。”[30]朱熹提出了圣人“异乎众人”的观念,这意味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首先是圣人切身的私密体验,其次才是面向凡人的说教;而且,虽然凡人与圣人的行为表现是类似的,但志学、立、不惑等行为背后的觉知程度有浅深之分,实现情态亦有生熟之别。
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的为学次第与进德阶序,指向孔子是“学而渐知”的。为了调和“生知”的说法与指向“学知”的自述之间的冲突,朱熹引入了“谦辞”的说法来解读此章。他说:“愚谓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命已成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间,必有独觉,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学者以是为则而自勉,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托也。后凡言谦辞之属,意皆放此。”[31]根据朱熹的解释,虽然孔子“生而知之”“义理昭著”,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阶段。这种避免自负的态度,显示了圣人谦虚的美德。由于孔子没有察觉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义理”,因此他努力为学与进德以逐步提高自己。这就解释了他对自己为学与进德之累积过程的描述。该累积过程是圣人“自觉”“独觉”的、是圣人切身感受到的进步之实现。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是孔子分享自己对进步之实现的觉察体验,这与孔子实际已经完全掌握了“义理”并无关涉,因此与孔子“生而知之”的说法并不矛盾。朱熹指出,孔子这种避免自负的态度根源于他诚实正直的觉察体验,而不是明知自己是“生知”的圣人而故意虚伪。
朱熹“谦辞”诠释策略的实质在于指出孔子实际拥有的能力与他以为自己拥有的能力之间的不一致。在“谦辞”的理解进路中,“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可以理解为孔子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生而知之”“义理昭著”的阶段,因此他努力为学以逐步提高自己。在朱熹“谦辞”的诠释策略下,指向“学而渐知”的《论语》文本与孔子“生知”的矛盾得到了调和,朱熹对于孔子“生知”的说法成为了《论语》原著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反映了朱熹为了维护孔子圣人形象所做的努力。
三、朱熹诠释策略的局限
朱熹认为孔子“生而知之”,并采用“谦辞”的诠释策略维护孔子的圣人形象。然而,朱熹的诠释策略中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朱熹“谦辞”的诠释策略是以对孔子的能力和主观感受的假设作为出发点,这种诠释策略存在问题,因为孔子的能力和主观感受总是很难被证实,因此面对同样的文本,基于对孔子的能力和主观感受的不同假设,解经的学者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朱熹“谦辞”的说法可能受到质疑。例如朱熹在解“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时说:“三者已非圣人之极至,而犹不敢当,则谦而又谦之辞也。”[32]朱熹认为孔子的能力已达到这三者,但孔子的主观感受是“不敢当”,所以这段也是孔子的“谦辞”。钱穆则认为“或以本章为谦辞,实非。”[33]钱穆认为这是对孔子自己弱点的自白,从而否定朱熹“谦辞”的说法。
其二,朱熹认为圣人之学、立、不惑的实现状态是圣人切身的私密体验,不在圣人之位上的凡人对此无法揣度,由此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圣人的为学次第与进德阶序对于众人来说可能成为空中楼阁,远离众人的经验,从而大大降低了孔子之言教的鼓舞价值。朱熹说:“大概圣人元是个圣人了,它自恁地实做将去。它底志学,异乎众人之志学;它底立,异乎众人底立;它底不惑,异乎众人之不惑。”朱熹提出圣人之学、立、不惑的实现状态“异乎众人”,将圣人之学、立、不惑的实现状态与众人区隔开来。与此相关,朱熹还论说道:“圣贤之学,非常情所能测,依约如此,须有与他人不同处耳。”[34]朱熹指出虽然凡人与圣人志学、立、不惑等行为表现是类似的,但背后的觉知程度有浅深之分,实现情态亦有生熟之别。可见,由于凡人对圣人之学、立、不惑的实现状态无法把握,那么以圣人之学、立、不惑的实现状态作为凡人的指引与提升就是悬空的。
四、朱熹不得不采取孔子“生知”说法的理由之推测
朱熹坚持孔子“生知”的说法,并采用“谦辞”的诠释策略使“生知”的说法涵容指向“学而渐知”的《论语》文本,朱熹有不得不采取孔子“生知”说法以维护孔子圣人形象的理由。
首先,“学而渐知”、通过“学”而成为“圣人”这一说法缺乏实例来证明“学”以成圣的可行性。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强调颜子为学的目标是“求圣人之道”,“学以至圣”是可以实现的。程颐说:“夫《诗》 《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35]另一方面,程颐也强调了颜子与圣人在境界上的差距:“然而所异于圣人者,盖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故曰:‘颜子之与圣人,相去一息。’……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盖伤其不得至于圣人也。”[36]可见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认为,如果颜回没有不幸短命死去,就能成为圣人,但这只是假设的说法。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肯定了尧舜汤武在成圣途径上有所区别,并肯定了汤、武是学而知之,尧、舜是生知,认为从结果上看四者皆为圣人。程颐说:“问:‘尧、舜、汤、武事迹虽不同,其心德有间否?’曰:‘无间。’曰:‘孟子言:‘尧、舜性之,汤、武身之。’汤、武岂不性之耶?曰:‘尧、舜生知,汤、武学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37]但在儒家的传统认识中,尧舜和汤武的确不可混为一谈。大致说来,前者是圣人的代表,而后者则更多地被视作贤人。按照《中庸》的理解,圣人的特点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贤者则是“择善而固执之者也”[38],这说明两者区别在于圣人先天与“道”为一,圣人固有的本性自然符合天道,不依赖后天追求学问的过程,因而是“生而知之”;而贤者则不能直契道体,故而需要后天具体的为学过程和择善工夫,即“学而知之”。从这个意义上讲,“为学”所能实现的只是贤人境界,与圣人仍有距离。
其次,孔子与“圣人之道”的同一性关系,构成朱熹解经时的主要心态。如果不采用孔子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之说,朱熹的解经行动就失去了支援,从而失去了上契圣人之道的可能性。具体来说,解经儒者大抵认为解经行动是在探问文字间讯息,以解明经典文字背后的“圣人之道”内涵,达到揭露神圣性真理的目标。如何达到此种经典理解与诠释?孔子实为儒者解经时的重要支撑点,以孔子为圣人,并成为经典发言人。儒者相信经典意义的确解需以符合孔子的意思为准。那么,如果认为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说法意味着孔子是“学”以成“圣”的,那孔子是什么时候成为“圣人”的呢?如果认为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时成为圣人,根据朱熹《论语序说》,只有《论语》宪问篇第十四“莫我知也夫”章和同篇“陈成子弑简公”章是在哀公十四年、孔子七十一岁时所说的,也就是说《论语》中只有这两章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一章能确定是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后所记载的孔子言行,其他的或是孔子“七十”以前的、或是无从考证时期的。显然,不能根据这种理解只选取《论语》的一部分作为圣人的言行,舍弃其他。由此可知,朱熹之所以辩称孔子“生而知之”,恐怕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论语》中孔子的言行几乎就不可能或很难解释为圣人的言行,从而难以上契圣人之道。此时的问题,不再是孔子客观真实情况的确定,而是贴在孔子身上的神圣性内涵的问题。
综上所述,朱熹强调孔子“生知”,并说明了“生知”与“学”并不互斥,又以“谦辞”的诠释策略说明了孔子自述其为学与进德的过程与孔子本来“生而知之”并不矛盾,从而孔子“生知”的说法能够涵容指向学而渐知的《论语》文本,维护了孔子的圣人形象。朱熹的诠释将程颐、邢昺、皇侃等的解读推进了一步。同时朱熹的诠释也反映了与前代儒者所共同的解经心态,即以孔子为圣人,将经典意义的归趋指向孔子,从而解明经典文字背后的“圣人之道”内涵。这体现了解经儒者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这些讨论有助于读者理解朱熹对《论语》的诠释,补充现时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