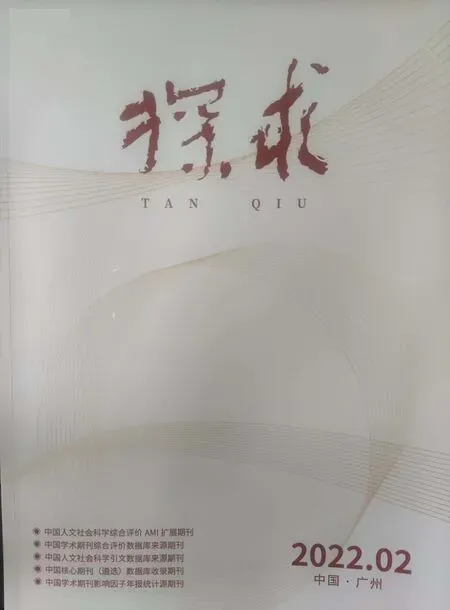“内部事务原则”演变下国际证券市场管辖权的划分
□贾海龙 汤圣琳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证券市场也日趋国际化。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金融市场不断繁荣发展,跨境证券监管合作日趋频繁,但与此相伴的管辖权问题也对我国的证券监管体系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挑战。2021年12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制度型开放”[1],而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无疑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组成部分,且证券市场的良好运行需要高水平的制度保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无疑对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国际化指明了政策方向。不过,我国要实现证券市场高水平的国际化还需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其中首要问题之一即是如何界定我国证券市场国际监管范围。
一国公司进行海外证券融资,证券市场地无疑对该公司及其活动享有立法管辖权以及随之而来的行政监管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同时市场地监管规则、司法程序和裁决需要境外(往往是公司设立/注册地)的承认、配合和执行。而公司设立/注册地无疑也对公司拥有一般的管辖权,在实体法上也很可能制定了与市场地不同的规范,这就在国际法上造成了多重管辖权问题、域外执行问题以及规范冲突。针对上述法律冲突问题,域外发达证券市场地的法律制度曾围绕“内部事务原则”的演进进行构建和实施,同时配合以国际合作的技术性规范,本文将对其进行批判性考察,进而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建议。
一、证券市场国际监管范围界定的传统路径
为了避免冲突,合理划分市场地与设立地的管辖权或规范事项范围非常必要。市场地的外国公司管辖权的事项范围最初由一般国际法来确定,具体到证券法中便形成了公司的“内部事务原则”。该原则认为,凡是属于公司成立、存在和组织的内容皆属于公司“内部事务”,由公司设立地法管辖;公司在海外证券市场地的证券活动则属于市场地领土范围内的行为,由市场地法来进行管辖。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内部事务原则”是一种法律选择的规则,它选择了设立地的法律来管理公司内部事务的纠纷。
(一)“内部事务原则”的确立
作为划分证券市场国际监管范围的传统方法,“内部事务原则”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美国解决州际法律冲突的产物,并通过判例形成而不断发展而来[2]。早在十九世纪初期,美国各州普遍认为公司是各州的附属物,公司内部事务的管辖权专属于其成立地州。这种地方主权的思想与内部事务原则所体现的对公司成立地州的尊重相契合,使得该原则之后在各州达成共识。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各州商业公司在地域上的流动性越来越强,州立法机构虽然被迫放宽对公司法的某些限制,但仍然要求公司应与其设立地州保持实质联系,这使得公司不能够自由的“选购”公司法,自然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3]。在这种限制性的条件下,各州又希望能够吸引外来资本,这种矛盾的情况导致了所谓的“弱化形式”的公司设立竞争[4]。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十九世纪末期,新泽西州率先打破了属地公司法的传统,通过修改本州的公司法以增加其自由化程度,从而吸引州外公司来本州注册成立,这种公司自由设立制度造成了之后各州“强化形式”的公司设立竞争。1968年,在“保罗诉弗吉尼亚州”一案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暗示各州无法排斥从事州际贸易的州外公司,这使得“从事州际贸易的公司可以去寻找最有利的州注册”[5]成为了可能。应该认为,“内部事务原则”在促进这种竞争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该原则更倾向于站在公司的角度,尊重设立地州法律就是尊重公司对公司法的选择[6]。在之后的公司大兼并运动中,“内部事务原则”虽然与属地公司法时代截然不同,但仍然在各州逐渐达成了共识。随着跨国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的日渐频繁,各国监管机构为维护证券市场的正常运作而开始对跨国证券活动进行监管,“内部事务原则”也因此成为各国证券监管遵循的基本原则并沿用至今。
(二)“内部事务原则”的理论基础
“内部事务原则”的理论优势及其实用性帮助各国证券监管机构在证券市场兴起之初划定了市场地和设立地的管辖权范围,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两地之间的管辖权冲突,使得市场地和设立地都能够更好地对国内的公司进行监管。多年以来,各国学者和法院对“内部事务原则”出现和存在的正当性一直有所探讨,因此,可以得知对其理论基础的剖析是理解该原则的关键所在。
传统的理论解释认为“内部事务原则”的存在具有三大正当性。第一,从合同的角度来看,该理论被认为是构建公司合同的补充条款;第二,该理论适应实际情况,即公司设立地所在国比营业地所在国更加具有管理公司内部事务的利益驱动力;第三,“内部事务原则”的正当性还被认为是宪法所赋予的。美国最高法院在CTS Cor p V.Dynamics Cor p of Amer ica和Edgar v.MITE Cor p案中认定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反并购法案违反了宪法中的休眠贸易条款,似乎暗示了休眠贸易条款是“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虽然这些解释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不合理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些解释证明了“内部事务原则”的重要价值以及它的实用性,即“内部事务原则”不但尊重私人意思自治,还明确了法律规则的适用,其高效性和可预测性都为其延续奠定了基础。
(三)运用“内部事务原则”存在的问题
“内部事务原则”虽然得到了广泛的适用和认可,但是不管是从该原则适用之初所发生的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互相攻击”,还是到现在证券市场兴起而引发的监管模糊地带出现,都可以看出“内部事务原则”的运用并非一帆风顺。随着国际市场的发展和各国对证券监管事项的主张,该原则也逐渐暴露出其无法满足现实的监管需求这一问题并且其在实践中经常被背离。
“内部事务原则”赋予了公司自由选择公司设立地的权利,跨国企业利用这一点开始通过选择法律规制较弱的国家作为设立地而其主要经营活动却在另一个辖域内的方式来逃避监管,这种公司进行“流浪”的行为随着国际交通和通讯成本持续的降低而在国际层面蔓延。市场地指望公司设立地提供基本水平的公司内部事务法律规范的侥幸被击碎,像开曼群岛这样的辖域根本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规范公司的内部事务。而一旦公司内部事务缺乏根本规范,则市场地证券法规范往往也就没有了任何实质意义。在这一情况下,市场地开始通过行为地法、发行地法、交易所在地法和其他一些相关的法律[7]来对“流浪”公司进行监管,以保护本地的公司及投资者。在这一情况下,“内部事务原则”的扩张发展,导致市场地和公司设立地的管辖权界限变得逐渐模糊,一国公司可能就其内部事务要接受市场地和公司设立地的多重管辖,这种情况对公司的存在及其活动都会产生影响。基于此,划分“内部事务原则”的具体规范范围,成为各国证券市场监管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证券市场国际监管范围的演进
一般而言,证券市场监管者不可能任由公司内部事务造成公司市值的下跌进而损害投资者,无视传统公司内部事务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掩耳盗铃,各国证券法无法严格适用“内部事务原则”。“内部事务原则”松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公司事务与证券事务进行区分十分困难,也即公司事务大多与证券事务混合在一起,证券监管如果不涉及公司“内部事务”将无法实现其目标;二是市场地总是重视本地投资者保护,具有充分的动力来突破对公司事务和证券事务人为的区分。
(一)“内部事务原则”的补充
“内部事务原则”的不足在越来越多的公司在爱尔兰、百慕大、开曼群岛这样的管制严重不足的地方注册这一背景下愈发严重。特别是对于面积狭小的公司上市地,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在境外设立,本地的公司法一般都不适用于上市公司,在上市公司注册地管制不足的情况下,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就处于一个非常自由的管辖真空。而对于上市地而言,不利于保护本地的中小投资者,不利于本地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对于不愿意突破“内部事务原则”的上市地而言,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取对“内部事务原则”进行补充的途径。香港就是一个采取补充途径的典型。香港交易所的上市规则规定,其一,外地公司在香港上市前,必须向交易所证明其设立地或注册地的法律提供的股东保护水平至少相当于香港法律提供的保护水平;其二,如果设立地或注册地的法律存在明显的漏洞,特别是对于股东的权利保护不足,则上市公司必须在公司章程中纳入保护股东的条款,补足设立地或注册地法律的不足,以达到香港法对股东的保护水平。
可以看出,香港的做法主要是通过公司章程来补足公司设立地或注册地对于公司内部事务管制的不足。该途径保留了上市地根据“内部事务原则”不管辖外国公司内部事务的传统,但是为了保护上市地的投资者,通过对公司章程进行要求来对“内部事务原则”进行补充。然而,该途径事实上难以真正解决“内部事务原则”带来的监管不足问题。其一,公司注册地可以制定非常详细而严格的公司法,提供与上市地法律水平相当的股东保护水平。虽然这样做在刚开始会吓跑一部分“流浪”公司,但像百慕大这样的地方根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很好的执行自己的公司法,股东也很难跑到这些地方去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其公司法中对股东权利的保护条款仅是纸面上的权利。其二,如果公司注册地的法律保障不堪大用,规定在章程中的股东保护条款确实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是与正式和完善的法律相比,其作用有限。
(二)“内部事务原则”的例外
基于保护投资者的压力,“内部事务原则”逐渐在实践中被背离。根据以色列赫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的利赫特教授(Licht)对英美两国相关案例的考察,证券法领域主要通过发展出“影响原则”、“长臂原则”和外国公司的“归化标准”,扩大了市场地管辖权的事项范围,创立了“内部事务原则”的例外[8]。不过,目前而言,“内部事务原则”在国际证券法中依然属于一般法律原则,没有遭到直接的否定,对其背离依然是以表面上对其发展的方式进行的。
影响原则主要指的是外国公司的行为影响到本国的利益,特别是影响到本国投资人的利益,则本国会因此获得对外国公司的管辖权,并将本国法律规则适用于外国公司之上。该原则也是美国在证券领域树立“长臂原则”的一个基础。以美国为例,第一,美国法下的反欺诈条款适用于任何对于美国国民的证券欺诈行为,无论该行为由谁实施或在何处发生;第二,反欺诈条款适用于由向海外居住的美国国民出售证券所招致的损失,但重要的是在美国发生的行为对损失有重要关系;第三,《商品交易法》适用于在美国境外为在芝加哥交易所内执行订立期货合同的人。
崔(Choi)教授和古斯曼(Guzman)教授重申了“内部事务原则”难以正面突破的间接理由:国际礼让原则的必要和普通法国家遵循先例原则对该原则生命进行了延续。然而,“内部事务原则”的扩张发展模糊了市场地与公司设立地管辖权的界限[9],因而孔(Kung)等学者指出如果一国公司就其公司事务接受多重管辖的话,多法域不同的法律规范会造成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会影响到公司的活动,还会影响到公司的存在和组织等更为根本的问题。这种一般规则“名存实亡”的情况事实上造成了判断市场地事项管辖权的不确定性,也给市场地与公司成立地的管辖权冲突增加了变数。
(三)公司法对外国公司的适用
某些法域逐渐不再满足于对“内部事务原则”的修修补补或者例外突破,开始全面背离该原则。美国重要州的公司法已经明确规定适用于外国公司的“内部事务”,如果这些公司符合某些标准。当然这是最为激进的做法,也是证券法学者主张和设计的方案,但易引起法律冲突。与之相对,在实践中通过法院进行个案判断,确定本国公司法规范在一定范围内适用于外国公司,这是一条保守路径。无论是公司法全面适用于外国公司,还是有选择的适用于外国公司,“内部事务”的划分已经不再是对外国公司进行法律适用的标准。
将公司法适用于外国公司,美国有着典型的法律实践。美国的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对外地公司规范采取了非常清晰的原则,即专门在公司法中为外地公司规定了特殊适用规范,即外地公司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适用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公司法的规定。如《加利福尼亚公司法典》第21章专门为外地公司而设,列出外地公司受到本地公司法管辖的外地公司的标准,凡是符合标准的外地公司则一律适用本地公司法的规定。因此,加利福尼亚州并不管制所有外地公司,其公司法第21章要求管制那些与该州有重要联系的公司。该章特别规定,“如果外地公司因其上一年度的资产因素、工资因素以及销售因素的一半位于本州,或者有超过一半有表决权的证券由本州人持有,则外地公司受本法的管制。”外地注册成立的公司每年必须递交报告表明是否达到上述标准,加州公司法在外地公司报告显示符合上述标准30天后开始适用,直到新的年度报告显示不符合标准的年度结束。
三、证券市场国际监管合作实践
无论是对“内部事务原则”进行补充,或者是创造例外,抑或是摈弃该原则,市场地与注册地在监管技术层面的合作是必须的。特别是注册地对于市场地在监管技术层面的配合,对于市场地的有效监管至关重要。
(一)证券市场国际监管的双边合作
1.谅解备忘录
谅解备忘录(Memor andum of Under st anding)是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证券监管机构就证券监管合作事项所签订的一种陈述或者声明,以实现双边监管信息共享为主要目的。该文件不具有国际法上的强制约束力,但是相较于传统的签订条约的方式,其自身的保密性和易于修订性使其成为各国监管机构在跨国证券监管合作中更加青睐的方式[10]。谅解备忘录在保障签订双方监管权的基础上使得各监管机构能够就约定的监管事项开展合作,这些监管事项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逐渐丰富,各国证券监管机构以此为基础进行了信息共享、协助调查和联合视察等证券监管合作。美国和欧盟国家在实践中经常使用谅解备忘录来处理跨国证券事务,目前美国证监会(t he U.S.Secur it 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以下简称SEC)已经与多个国家的证券监管机构签订了谅解备忘录,这些框架协议加强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促进了信息分享、对其他法域证券监管体系的了解以及监管机构之间的信任[11]。我国也充分利用谅解备忘录来进行证券执法合作,截止到2020年12月,我国证监会与境外证券监管机构签署了66份证券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对于证券期货的合作事项、方式以及监管权力的划分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2.司法互助协议
司法互助协议(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reaties)是指缔约双方在互相认可和配合的基础上签订的涉及国际证券监管的双边条约。根据条约的规定,除特殊情形外,缔约的一方法院有义务在约定的刑事、民事等法律层面对提出申请的另一方提供充分的司法协助。相较于前文所述的谅解备忘录,司法互助协议需要缔约双方经过正式的程序进行签订,对于缔约双方具有法律拘束力,其灵活性和及时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12]。在证券领域签署司法互助协议,使得双方证券监管机构能够通过获取证据协助、法律文书送达等方式来进行跨境执法,有利于对跨境证券犯罪与过度投机行为进行打击,同时,通过这一方式进行证券监管合作,有效地避免了各国因国内证券法产生的监管权而引起的冲突,从而保证了各国证券法的有效实施[13]。
(二)证券市场国家监管的多边合作
1.国际证监会组织
国际证监会组织(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以下简称IOSCO)是一个以各国证券监管机构为主要成员的国际性组织,其目标是建立全球统一的信息披露准则和会计准则,加强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的对话和相互理解并促进全球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在这一目标下,国际证监会组织在证券市场国际监管的多边合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便于跨境证券监管,IOSCO认为在跨国证券公开发行与首次上市方面应通过提高披露信息的可比性来促进跨境证券发行和上市,同时又要确保对投资者的高水平保护。因此,IOSCO于1998年9月发布了《外国发行人跨国证券发行与首次上市国际披露准则》(International Disclosures Standards for Cross-Border Offerings and Initial Listings by Foreign Issurers,以下简称《初次披露准则》),就外国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或将其股票在外汇交易所上市时应提供的披露信息达成了国际共识。在IOSCO的鼓励下,世界各国开始接受《初次披露准则》中的规定并加以实施,例如SEC就在1999年9月通过对表格20-F的修订来吸纳该准则。随着跨境证券活动的不断增加,IOSCO于2002年5月制定了《关于咨询、合作与信息交换的多边备忘录》(Multilateral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并在此基础上于2017年发布了《关于磋商、合作与信息交换加强版多边谅解备忘录》(Enhanced Multilateral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为各成员国提供了丰富的监管机制和监管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各国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14]。IOSCO一系列的举措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统一的监管标准,为推进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5]。
2.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会计准则作为编制跨国发行与上市信息披露文件的前提和基础,为发行人信息披露提供了框架。因此,促进跨境证券发行和上市的国际监管还必须在跨国发行与上市的会计标准方面达成国际共识。基于此,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以下简称IASB)与IOSCO于2000年合作开发了国际会计准则(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以下简称IAS),以此来解决国家或地区层面未解决的实质性证券监管问题。与此同时,IASB还积极与诸如财物会计准则委员会(the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这类的国家标准制定者合作建立高质量的国际会计准则,并且在SEC的鼓励下试图解决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和IAS之间的重大差异。欧盟也要求欧盟范围内的上市公司不得晚于2005年使用IAS。通过高标准的IASB使得发行人不需要在多个监管区域内准备多套财务报表,大大提高了各辖域的监管效率。
3.美国公众会计监督委员会
证券监管合作必须建立在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标准和会计准则上,但是没有共同的审计和执行,该信息披露标准和会计准则毫无用处[16],因此,跨境审计监管也是证券监管国际合作中需要重视的一部分。自从2005年以来,美国公众会计监督委员会(the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以下简称PACOB)与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的审计师在信息交换、调查和审查方面建立了合作审计协议。根据审计协议进行的合作包括PCAOB定期与母国监管机构联合审查并进行信息共享。就美国上市公司而言,PCAOB要求对这些公司进行审计的非美国审计师必须根据PCAOB的规则进行注册。此外,未在美国注册的公共会计师事务所也要接受PCAOB与在美国注册的公共会计师事务所相当的审查和调查。PCAOB与其他监管机构进行合作,有效地减轻了审计师因法律摩擦引起的法律责任,并完善了跨境审计的问责机制。
四、界定我国证券市场国际监管范围的建议
“内部事务原则”早在我国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就有所体现,但2010年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4条中对该原则作出了新的规定,形成了以“内部事务原则”和“真实本座主义”相结合的外国公司法律适用原则,避免了对“流浪”公司的监管漏洞。而具体到我国证券法领域中,则以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2条第4款这一规定来确定我国证券市场国际监管的域外管辖权。从这一规定来看,我国似乎采取了与美国重要州相似的方法,明确规定当外国公司符合某些标准时,我国法律对此具有管辖权,但这种背离“内部事务原则”的方式是否适用于我国还值得商榷。与此同时,不管“内部事务原则”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命运,发达市场地如美国和欧洲已经在监管的双边和多边层面发展出来了比较成熟的技术性制度,而我国由于实践的匮乏,在这一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因此,我国不论是在证券跨境监管原则方面还是监管合作的技术层面,都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一)明确证券跨境监管原则及适用标准
《证券法》第2条第4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扰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市场秩序,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处理并追究法律责任。”这一条款突破了绝对属地管辖原则的限制,正式确立了我国证券法的域外管辖权制度。从这一规定中不难看出,我国对于域外证券监管的范围主要以“扰乱境内市场秩序”和“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这两项效果来作为界定标准[17],这种以效果原则作为域外证券监管核心原则的方式是对“内部事务原则”本身的一种发展,为其创设了例外。这种并未直接否定“内部事务原则”的做法值得肯定,也符合我国一直以来在有关法律中以“内部事务原则”作为监管核心原则的理念。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一做法在实践中如果操作不当很有可能产生法律冲突。因此,我国目前应当在坚持以“内部事务原则”为主,例外规定为辅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对该原则的适用标准作出更加明确规定。首先,应结合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和经济政策,对《证券法》第2条第4款所规定的境外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进行具体界定,在此基础上明确扰乱境内市场秩序等不同行为的概念和类型,将证券跨境监管的边界确定下来。其次,可以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有关的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等方式来逐步完善跨境监管的操作规则,强化证券市场国际监管的可操作性及规则适用的法律效力。
(二)健全证券市场国际监管的合作机制
随着世界资本全球化的不断加快,我国证券市场的发行和交易活动也日趋国际化,在这一背景下,证券市场国际监管的合作与交流显得十分必要。近年来,我国积极探索与其他国家的跨国监管合作,签署了多项双边合作谅解备忘录和司法互助协定,并在《证券法》第177条中确立了证券跨境监管的合作机制。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现有的监管合作技术并不成熟,缺乏明确具体的操作规则且执法力度不强。基于此,一方面,我国应该积极推动双边、多边跨境监管合作,以IOSCO作为桥梁和纽带,加强与成员国的合作与交流,加大制定国际标准的话语权,并进一步制定更具体的操作性的规则,在未涉及的重点执法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扩大我国在国际证券监管方面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我国应当适度放宽证监会跨境监管方面的权限,赋予其一定的立法、司法和执法权力,对于重大、特殊的证券违法行为证监会应具备强制传唤、强制执行等权力[18],对于在监管过程中推诿扯皮的监管主体,证监会应具备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力。与此同时,我国应该形成以证监会为主,其他监管机构为辅的监管体系,明确各个监管主体的分工和责任[19],加强各监管机构的配合与协调,适当参考国外监管机构的实践情况,落实同境外监管机构合作时境内各主体的具体安排。
(三)进一步推动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作为推动我国制度规则与国际最佳实践进行深层次对接的具体举措,一直以来都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点制度安排,也是促使我国证券市场国际监管合作的有力推手[20]。为了加快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2022年2月11日,我国证监会发布了《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监管规定》,进一步拓宽了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的适用范围,也为我国与境外证券监管机构共同建立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合作机制提供了可能。目前看来,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我国证券市场进行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仍然是大势所趋。在国内层面,我国需要抓住注册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明确内部事务原则在我国证券监管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学习国际先进制度来继续完善域外管辖权的有关立法,强化现有制度规则的透明性和有效性,协调各项监管规则的适用情况,实现国内监管制度的有效衔接。同时,在国际层面,我国应当加强与境外监管主体的合作,扩大在管辖权事项方面的相互认可度,形成区域性制度互认,并在监管技术等方面达成共识。与此同时,也需要总结现有经验,发挥自身特有优势,引领跨境监管主体在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影响力进而形成国际制度,构建起符合我国自身利益的国际证券监管制度体系[21],为我国证券市场的长久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