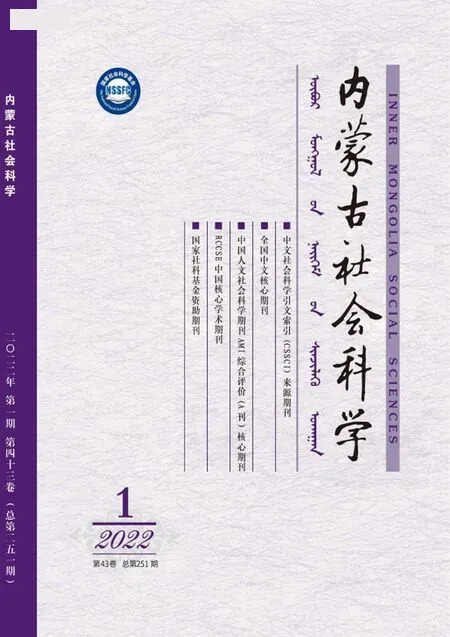论长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促进与影响
王绍东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长城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它修筑的时间之长、经过的地区之广、发挥的作用之全面、体现的精神内涵之丰富,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独树一帜、举世无双的。长城作为代表性符号,积淀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延绵厚重、灿烂辉煌的精神内涵。千百年来,长城守护着中华民族的文明血脉,凝聚着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2019 年 8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嘉峪关长城考察时强调:“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1)参见《习近平在甘肃考察时强调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团结一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http://china.cnr.cn/news/20190823/t20190823_524743923.shtml,2019年8月23日,2021年5月15日。历代中原王朝修筑长城,主观上是想将游牧民族阻隔在北方草原,以减少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战争与冲突,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南北地区不同民族、不同人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自古以来,长城地带就是环境过渡带、农牧交错带、民族交融带,为各个民族提供了交流往来、学习互鉴的舞台。历史上,长城地带蕴含了多种文化因素,但最终都融入到了中华文明之中,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典型表现地区。
一、铁器牛耕、马上骑射与长城的修筑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长城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随着铁器逐步取代木器和骨器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生产力有了革命性提高。在以木器和骨器为主要生产工具的耒耜农业时代,土地开发的能力有限,“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1](卷9P.146)。到了战国时期,铁犁和牛耕普遍使用,土地开垦能力增强十倍,“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2](卷24上P.1125)。土地的大量开发,使粮食产量得到了稳定增长。《孟子·万章下》记载:“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3](卷10上P.272)也就是说,在战国时期,一个男性成年劳动者精耕细作生产的粮食除了可以满足家庭的口粮供应外,还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成为积累的财富。
农业生产的稳定和高效使一部分人可以摆脱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手工业、文化的创造及社会管理工作。农业促进了社会分工,分工加速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土地的大量开发与粮食产量的提高,导致农耕地区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的快速增长,又进一步促进了土地的开垦。在这样的循环过程中,农耕生产区不断开拓扩张,土地的价值不断提升,各诸侯对土地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春秋时期的“五霸”、战国时期的“七雄”,都是在土地争夺过程中消灭了诸多小的诸侯国,不断扩张自己的控制范围后发展壮大的。最初的长城,如楚长城、齐长城等,是楚国、齐国这些诸侯国在吞并其他诸侯国或夺取了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空地后,修筑的对新获取的土地加以保护的军事设施。后来,各诸侯国之间在中原地区进行竞争,一些竞争不占优势的诸侯国为了防止自己的土地被敌国夺走,也修筑长城加以护卫,如赵国、燕国的南线长城,秦在魏、秦之间修筑的长城等。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属于农耕经济区,农耕经济区的周边是“夷狄”所在的混合经济区。战国秦汉时期,随着农耕经济的强劲扩张,混合经济区的部落要么完全转为农耕经济,要么继续向不适宜农业的北方地区迁徙,转向专业化的游牧生产方式。
游牧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当发生雪灾旱灾等重大灾害时,牧草被覆盖或者枯死,草原的生存环境骤然恶化,出现连锁反应。《太平广记》记载:“唐调露之后,有鸟大如鸠,色如鸟雀,飞若风声,千万为队。时人谓之鵽雀,亦名突厥雀。若来,突厥必至,后则无差。”[4](卷139P.1005)《旧唐书·五行志》对此事亦有记载:“调露元年,温傅等未叛时,有鸣鵽群飞入塞,相继蔽野,边人相警曰:‘突厥雀南飞,突厥入塞之兆也。’”[5](卷37P.1368)当牧草被破坏后,野生动物难以获得食物,只能离开受灾地南下,牲畜也因缺乏营养而大量死亡。在面临生存困境时,游牧民族常常南下农耕地区进行掠夺。他们马上骑射,生产条件与战斗条件高度统一,“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6](卷110P.2879)。他们依靠骑兵的快速机动性南下,向农耕民族发起进攻和掠夺,对农耕文明造成很大冲击和破坏。
农耕民族在生产过程中依赖其积累的粮食和财富对抗自然灾害,为了保持生产的持续进行,特别需要社会的稳定。历史上,农耕民族主要靠车兵、步兵作战,行军缓慢、机动性差。游牧骑兵移动速度快、机动性强,来如飙风、去如闪电,迂回包抄、分合自如。他们一旦进入农耕地区,便抢劫粮食,掠夺人口,甚至烧毁房屋,将农民的多年积蓄劫掠一空。如中原王朝以大军出击,游牧骑兵则快速撤离。而由于北部边境地域辽阔,战线极长,后勤供应困难,战争消耗高,民众负担重,大军深入难以持久。汉代的晁错曾经分析说:“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2](卷49P.2285)
但骑兵作战长于机动,短于攻坚。针对这种情况,中原王朝便在农牧交错地带修筑长城,将骑兵阻挡于长城之下。然后利用其预警体系、调兵体系、后勤保障体系等,变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掌握对游牧骑兵作战的主动权。北魏的高闾曾经分析修筑长城的必要性:“北狄悍愚,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业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赍资粮而饮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扰而已。历代为边患者,良以倏忽无常故也。”[7](卷54P.1201)他建议北魏政权应该学习秦皇、汉武的做法,在北方地区修筑长城以对付柔然。在他看来修筑长城有多种好处:“计筑长城,其利有五:罢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其利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其利五也。”[7](卷54P.1202)可见,自战国时期开始,中原政权不约而同地在北方地区修筑长城,就是为了对付游牧民族的骑兵南下,将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长城以北,更好地保护农耕文明。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8](P.1800)
当前,学界在研究长城时出现了一种倾向,就是把长城的修筑历史越推越早,甚至把石器时代的环壕、早期文明的石城等都当作长城看待。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墙都是长城,环壕、石城、城墙与长城之间有着根本区别。前者主要是为了保护人和财富,后者主要是为了保护土地;前者规模小,一般呈环状,后者规模大,一般呈带状。若依这样的标准来看,长城应该出现在铁器和牛耕使用并广泛普及、土地价值上升、对土地争夺日趋激烈的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铁犁与耕牛在为长城奠基。
二、长城地带的民族互动与交融共生
战国秦汉时期,中原统治者纷纷在北方地区修筑长城,既是为了巩固向北方地区开拓的土地,也是为了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加以隔离,减少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战争,更好地守护农业文明。正所谓“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9](卷90P.2992)。在长城南北,不仅生产方式不同,自然环境、文化风俗也有着很大差异。“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10](卷32P.373)
农耕生产方式与游牧生产之间有着强烈的互补性,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无法用人为手段加以隔绝的。游牧民族需要得到农耕民族的粮食、手工业品等资源补充,农耕民族也渴望获取游牧民族的大牲畜及畜产品,这既有助于边疆地区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增强中原王朝的经济军事实力。除了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外,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文化上也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因此,相互联系、彼此交流、互通有无是双方的共同愿望,并不会因为长城的修筑而彼此隔绝。“中原历代王朝修筑长城,其主观目的是为了阻隔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联系,但由于两种文化之间具有强烈的互补性,长城又建立在农耕区与游牧区的过渡地带上,客观上,两者之间的联系不仅没能阻断,而且在长城地带相互冲突、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相互吸收,因此,长城在客观上发挥了融通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功能。”[11]长城的修筑使北方地区广大的农牧交错带变为了农业耕作区,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前所未有地接近。以战国时期为例,“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而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郡。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6](卷110PP.2885~2886)靠近北方的秦国、赵国、燕国,都采取了击胡的策略,向北方地区扩张领土,然后设置郡县,迁徙移民,发展农业生产。为了对付游牧骑兵的侵扰,三国不约而同地修筑长城,以保护农耕居民。
秦始皇北击匈奴,将长城继续向北方推进,并将秦、赵、燕长城连接起来,修成了东起辽东、西到嘉峪关的万里长城。汉武帝时期,将匈奴赶到了大漠以北,同时也将长城推进到阴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区。长城的修筑使农业生产区极大地向北方推进,农耕居民从黄河流域向长城以南的农牧交错地区大量迁徙。汉代的晁错就曾建议,将长城修筑与移民实边结合起来,国家给予物资援助,帮助他们在边疆地区安居乐业。“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戎)[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2](卷49P.2286)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分居长城南北,彼此间距离更近,交往更密切。
长城不是一条单纯的墙体,而是由一系列设施组成的防御工事。战国秦汉时期,与长城配套的设施包括边城、障城、烽燧、邮亭等,构成了烽燧、屯田、仓廪、邮驿交通和野战驻军五大体系。其功能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阻遏游牧民族的南下,将农耕生产方式向北方推进并加以保护;二是通过烽燧预警、信息传递、道路连接,强化了长城的一体化建设。明长城在注重防御的同时,则突出了关城、马市的建设,在长城沿线设立九边重镇的同时,在长城南北交通要道上建设了一批著名的马市和关城,如杀虎口、张家口等。关城既强调其守边的功能,也注重其通关功能。通关的目的就是打开关口与游牧民族进行互市贸易,并对这种贸易进行规范和管理。贸易通道的打开,可以实现双方经济之间的互补,满足彼此的物资需求,达到双方互利、减少战争的目的。
农耕民族对于游牧民族的畜产品特别是大牲畜的需求十分迫切。皮毛、肉食、奶制品的输入,可以增强北方居民的御寒能力,增加蛋白质摄入,提高其生活水平。牛、马等大牲畜的输入,不仅能够改良中原地区牲畜的品种与质量,而且牛、马用于耕田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马用于战争可以提高国家的军事实力。自战国秦汉时期,长城沿线就有马市存在。汉初实施和亲政策,“明和亲之约,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6](卷110P.2904)。隋唐时期,与突厥、回纥“缘边置市”[12](卷84P.1871),“以金帛市马”[13](卷50P.1338);宋朝与辽之间“置互市以通有无”[14](卷186P.4563)。长城边关马市贸易的长期存在,说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有着天然的、不可割裂的联系。
明代隆庆和议后,马市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除了政府组织的大型马市外,一些交通便利的边关墩堡也逐渐发展成农耕、游牧民族贸易往来的聚散地。“边外复开小市,听虏以牛羊皮张马尾易我杂粮布帛,关吏得税其物以充抚赏。”[15](卷8P.98)通过贸易,汉民得到了大牲畜和畜产品,蒙古人得到了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国家获得了稳定、增加了税收,是一种三赢的结果,“俺答纳款,马市互易,边疆无警,畿辅晏然,汉唐以来所未有”[16](P.12)。长城沿线马市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兴盛,到了明朝末年,“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中原”[17](卷2)。这种情况延续到清代,“边市贸易继续进行,加上政府采取鼓励、保护和减轻关税等政策,长城地带的互市市场又有新的发展,日益开放的民间民族贸易市场大多成了繁华的商业城市”[18]。明后期边将方逢时作诗云:“雁门东来接居庸,羊肠鸟道连崇墉。关头日出光瞳昽,于今喜见车书同。”[19](P.412)内地与北疆差异的缩小、“车书同”局面的形成,为清代将中国北部完全纳入大一统政权奠定了基础。
长城地处农耕与游牧的边缘交错地带,长城以南温暖的气候和农耕民族积累的财富,如同磁石一样吸引着游牧民族千方百计地进入这里。在长城地带,既有游牧民族学习农耕民族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提高生产力水平,以致进入长城以南,与农耕民族更密切地交融,乃至逐步融入华夏民族行列的历史事实;也有中原农耕民族需要学习游牧民族的畜牧、军事技术,改良畜牧品种,进行“胡服骑射”,实现富国强兵的生动事例。在这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频繁交往,使双方的经济交流、民族交融、文化融合得以逐步实现。罗哲文先生指出:“长城,这一两千多年一直起着安定、和平、保障作用的防御工程,除了它发挥其主要的防御功能之外,它还起着南北文化交叉对话与交流的纽带的作用。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各种现象的反映,但它同时又反过来促进政治、经济的发展。通过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和政治和解,长城这一南北交叉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0](P.204)
三、长城促进了中国历史上的局部及整体统一
农耕民族在发展历程中面临着两个强大挑战:一是自然灾害的挑战,特别是水旱灾害的挑战;二是游牧民族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农耕民族必须团结起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式。
为了更好地抵御游牧民族的冲击,中原农耕民族需要加强整体力量,建立大一统的王朝。秦能够统一中国,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受游牧民族的影响,具有重功利、轻伦理的民族性格有关。秦朝统一后,派蒙恬北击匈奴,将匈奴赶出了“河南地”,连接了原有的战国时期秦、赵、燕修筑的北方长城,并将长城向北方地区拓展。在修筑北方长城的同时,则极力拆毁原有的各诸侯国内部的长城。秦始皇三十二年在碣石门刻辞曰:“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太平。堕怀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平。黎庶无繇,天下咸抚。”[6](卷6P.252)与此同时,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统一的措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6](卷6P.239)。秦始皇意在借此把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各种障碍统统铲除。统一文字、度量衡显然有利于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凝聚力的加强;拆除诸侯国原有的内部长城等防御设施,既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统一,也可以防止各诸侯国贵族借此展开分裂活动。
与在北方地区修筑长城相伴的,则是长城的道路交通网建设。长城能够发挥军事防御作用,道路交通是必不可少的。与长城沟通的道路有多种形式,包括平行道、丁字道、十字道等。修筑与长城平行道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递烽火信息,调动长城沿线的军队相互支援,集中优势兵力针对来犯之敌。丁字道是从内地连接长城的道路。北方地区路途遥远、资源匮乏,无论是行军打仗、修筑长城,还是屯田驻守、皇帝巡视,都需要得到内地的人力、物力援助,修筑从内地到北方长城的道路,成为巩固北部边防的重要措施。秦朝北击匈奴,筑长城,“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6](卷6P.256)。这条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军事高速公路的秦直道,长期发挥着联通内地与长城地带的作用。十字道则穿越长城南北,保障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往交流。西汉时期,随着汉朝不断向西北地区推进,大漠南北的道路愈加畅通。“在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后,北方道路网络基本形成,东自辽东郡,西至张掖居延地区为一线的右北平郡、代郡、定襄郡、云中郡、五原郡、朔方郡及居延地区为十字路口,往来漠南、漠北及中原地区的道路都能畅通。”[21](P.25)
与长城相关道路的建设,首先加强了中原各个地区的联系与往来,将中原地区更加紧密地连接为一个整体。其次,也加强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联系、交流与往来,这种作用在历史上一直得到了发挥。李逸友先生在研究战国秦汉长城时,对此有着切实的感受:“长城墙体和烽燧址在草原上很明显,而且有些段落就利用长城为道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无法打听道路,只要紧跟着长城走就不会迷失方向。”[22]祝勇在《长城记》中对长城与道路的关系有一段精彩的论述:“道路是作为长城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长城意味着拒绝,它回避着冲突,而道路则意味着联系。”[23](PP.55)长城的修筑,促进了长城南北的道路交通网建设;道路交通网的建设,则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与贸易往来;经济的交流与贸易的往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文化的交融,强化了“长城内外是一家”的民族认同。
长城的修筑在促进中原地区的团结与统一的同时,也促进了长城以北地区游牧民族的交融与统一。长期以来,北方地区存在着众多的混合经济部落,这些部落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6](卷110P.2883)随着农耕民族不断向北方拓展,众多的戎狄部落或者被中原农耕民族所吞并,或者北上加入到游牧民族的行列。游牧生产方式需要大规模蓄养牲畜,“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6](卷110P.2879)。为了防止对草场的争夺造成部落间的战争,需要建立统一的政权来划分草场资源和确定不同部落的迁徙转移路线。
同时,长城的修筑阻隔了游牧民族南下的通道,游牧民族为了突破长城的防线,也需要凝聚成集体的力量,匈奴政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秦汉之际,趁着中原王朝改朝换代之际,匈奴冒顿杀父立国,打败东方的东胡和西方的月氏,并将众多草原部落凝聚到自己麾下,统一了蒙古高原。“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6](卷110P.2890)匈奴政权的建立,使游牧民族能够对中原王朝形成强大的压力。白登之围后,汉朝被迫与匈奴签订和亲之约,匈奴以军事压迫的方式突破了汉朝的长城封锁。以后,突厥、柔然、鲜卑、契丹、女真等继承了这一传统,实现了对北方地区的统一。局部统一的实现,为全国范围的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全国范围的统一,则巩固了“华夷一统”、天下归一的意识和成果。“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的两个统一——农业区的统一和游牧区的统一,终将形成混同南北的一个大一统,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24](P.262)
游牧民族常常将“饮马长江”作为目标,而农耕民族则通过修筑长城等方式“不教胡马度阴山”。农耕生产方式与游牧生产方式的互补性及相互间不可隔断的联系,使长城阻隔胡人南下的主观目的难以完全达到。游牧政权与中原王朝之间必然存在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交往和互动。“由于经济上互补关系的存在,中国历史上农业区、游牧区和高寒草原,以及南方山岳地带的经济文化交流是长期大量存在的,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经济基础。”[25]
四、长城南北的文化认同
在农业文明发展的初期,农耕民族占据了最适宜农业开发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商周时期,农耕民族便有了“中国”“华夏”与“夷狄”的概念。“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与南夷北狄相对应的‘中国’概念。在古代中国的想象中,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荒芜,住在那里的民族也就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越低。”[26](P.44)对于具有地理位置优势、气候优势、自然资源优势、生产方式优势、文明发展程度优势的“中国”与“华夏”来说,他们更加充满自信,更加自觉地团结凝聚。所谓“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27](卷18P.400),将“华夏”与“夷狄”进行区分。这种区分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28](卷56 P.1587)。在文化优越感产生的同时,华夏民族亦产生了道德责任感。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夷狄”进行影响教化,“以夏变夷”。“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9](P.3)华夏对“夷狄”并不完全是排斥,也包含了吸纳、包容与改造。“夷狄”只要接受了华夏文化的熏陶,也可以进入华夏行列。华夷之间的交融,对中原政权也多有益处。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魏绛就曾提出“和戎五利”的理论,即“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28](卷29P.840)。对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中原政权向来采取军事征服与德化柔服相结合的策略。
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之所以千方百计地进入长城以南,虽然主要是由经济与环境因素导致的,但也有其对华夏文化钦慕的原因。就整个中国的地理条件来看,北边是草原与大漠,西边与西南面是高山,东边与南边是大海,中部地区有黄河、长城、珠江等三大水系,不仅土地平坦肥沃,而且气候适宜,是周边地区向往和羡慕的地区。这样的地理环境致使周边民族愿意向中原地区聚拢、靠近,形成了内聚性的特点。第一个建立强大游牧政权的匈奴,与中原王朝之间就经历了对抗、和亲、内附、融合于华夏民族的过程。历史上,很多长城以北的民族和政权,都“思汉威德,咸乐内属”[2](卷96下P.3930)。《后汉书》记载白狼王慕化归汉作歌三首,其中《远夷乐德歌诗》曰:“大汉是治,与天合意。吏译平端,不从我来。闻风向化,所见奇异。多赐(赠)[缯]布,甘美酒食。昌乐肉飞,屈申悉备。蛮夷贫薄,无所报嗣。愿主长寿,子孙昌炽。”[9](卷86P.2856)诗歌反映了游牧民族民众向往中原大一统政权的心声。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气候干冷化变化和中原政权分裂衰落等因素影响,游牧民族纷纷跨越长城进入黄河流域建立政权。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政权不约而同地选择以中原地区曾有的国号为自己的国号。如匈奴建立的“汉”“赵”“大夏”政权,羯族建立的“后赵”政权,鲜卑建立的“前燕、后燕、南燕、北燕”政权,氐族建立的“前秦”政权等。拓跋鲜卑建立“北魏”政权,他们从森林走向草原,再从草原走向中原,自觉学习汉族的文化,“渐变胡风,遵循华俗”[30](卷23P.279),最后融合于华夏民族的行列之中。吐谷浑的第二代首领吐延曾对部下表达心声:“大丈夫生不在中国,当高、光之世,与韩、彭、吴、邓并驱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浅窜穷山,隔在殊俗,不闻礼教于上京,不得策名于天府,生与麋鹿同群,死作毡裘之鬼,虽偷观日月,独不愧于心乎!”[31](卷97P.2538)他了解中原历史,渴望成为西汉的韩信、彭越,东汉的吴汉、邓禹那样的开国英雄,建功立业,流芳百世。仰慕华夏文化,主动学习华夏文化,成为这一时期游牧民族的共同追求。
这一时期,游牧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后,不约而同地学习中原文化,将儒家文化视为正统。《魏书·序纪》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7](卷1P.1)不仅如此,按照历史记载,包括匈奴在内的游牧民族大多与华夏一些古老的部落有着血缘的联系。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索隐》引乐产《括地谱》加以说明:“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6](卷110PP.2879~2880)南北朝之后,黄帝几乎被塑造成了各族的共同祖先。对于这种现象,顾颉刚先生认为,各个民族通过祖先认同,意在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强化彼此间的认同。“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分散得远了,所以情谊疏了,风俗也不同了。如今又合为一国,咱们应当化除畛域的成见!’这是谎话,却很可以匡济时艰,使各民族间发生了同气连枝的信仰。”[32](卷1PP.110~11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融为隋唐时期更加深度的大一统创造了条件。隋唐的帝王都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脉,他们的民族观念更加开放,也更加具有平等性。唐朝采用以攻为守的策略,不修长城以自我局限,通过军事进攻化塞外为辖地,达到统辖农牧社会的目的。相对于以往的君主,唐太宗更加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他曾对臣下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33](卷198P.6247)贞观四年,唐朝征服东突厥后,“时诸藩君长皆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可汗”[34](卷200P.5494)。中原民族的最高君主“皇帝”和游牧民族的最高统治者“天可汗”的称号集中在唐太宗身上,表明长城南北的农耕和游牧两大地区的民众前所未有地汇聚在了一个皇朝政权之下。
清朝的建立将中国的统一推进到新高度。清朝历代皇帝就强调长城南北是一家,康熙指出,在他统治时期,“满洲、蒙古、汉军、汉人毫无异视,一以公正处之”[35](卷251P.489)。他认为应该废止长城的修筑,民众一心与民族和睦是更坚固的长城。“帝王治天下,自由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故,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35](卷151PP.677~678)康熙皇帝不再修物质的长城,而重视精神长城的铸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进一步化解了“中国”与“外夷”的隔阂,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文化上的认同。
近代以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中国遭受了帝国主义的入侵,逐渐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侮、掠夺和歧视,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事实上,共同的痛苦比共同的欢乐更有凝聚力。就民族记忆而言,悲伤比胜利更具有价值,因为他们强调责任感,要求成员共同的努力。”(2)参见Ernest Renan,What Is a Nation?Homi K. Bhabha ed.,Nation and Narration,转引自石硕《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启示》,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面对列强的蚕食鲸吞,中国人民意识到只有团结一心、患难与共,才能赶走侵略者,获得民族的解放和复兴。翁独健先生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也使我国各族人民深深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命运,从而加强了团结,加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和民族意识。”[36](绪论P.16)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长城作为两千年来防御外敌、守护文明的军事工程,就转化为一种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坚贞不屈的精神力量。
1933年,日军从东三省向热河、察哈尔进攻,中国军队的抗战在长城沿线展开。面对日军的飞机、大炮、机枪等现代化武器的攻击,中国军队利用长城等掩体,以大刀、长矛等较为落后的武器与日军展开近距离肉搏战,表现出了血战到底、不屈不挠的精神气概。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把长城作为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精神特质揉入其中。“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歌声激励着中华儿女团结一心、浴血奋战,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使中华民族再次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国歌后,长城蕴含的伟大精神进一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同、继承和发扬光大。
长城地带作为农牧交错地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仅有刀光剑影、战争冲突,更多的是你来我往、交汇激荡、文明互鉴。长城地带不同族群、不同生产方式、不同制度与文化间碰撞交融、频繁互动,由冲突渐趋融合,由多元走向一体。各民族在这一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既体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更蕴含着解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密码”[37]。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38]历史上,长城地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发展、成长壮大,正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