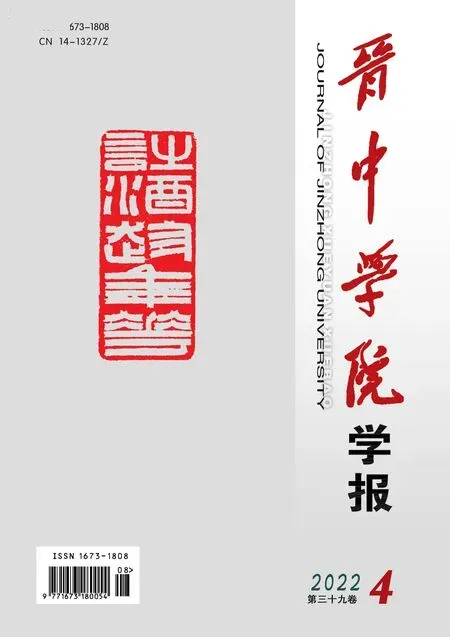异质文化间的语言差异与意象解码
韩 芳
(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Clare Kramsch 在“Language and Culture”一书中,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有这样的一种阐释:“Language expresses cultural reality,...embodies cultural reality,...symbolizes cultural reality. (语言表达了文化现实,......体现了文化现实,......也象征着文化现实。)”[1]他认为语言与文化是共存的,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体现并固化了一种具体的特定的文化现象,反映了不同文化的特定语言之间必然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以体现在语音、声调或句子结构等很多方面。不同国家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生存环境及文化环境,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象,体现在文学与艺术作品中,即为文化意象。特定的语言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具有该文化所独有而异族文化所缺少的文化情结和文化意象。
翻译作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桥梁,不仅承担着两种语言之间的互涉与转换工作,更是将一种语码承载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种语码解构、生成和表达的跨文化的对话活动。换句话说,翻译既不是单纯的语言对等和语言转换,也不是纯粹的文化侵入,而是在社会、文化和思维等众多层面展开的一项具有互文性质的语言转换活动。文化的异质性、流变性、多样性,以及语言各自所固有的文化积淀和体现使原文本和译入文本彼此之间的对话变得异常复杂。从语言的取向到目的,从语言的结构安排到语言的使用方法和技巧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深受其意义和价值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文化语境的制约和导引,“更受交际双方在理解话语时拥有的社会文化知识、认知能力等情景语境的制约和影响”[2]。此外,译入语意义的生成、原语与译入语中意象与联想的横向超越、意义的赋予与意象的解码既是对语言的转换、偏离与变异,更是对原语文化的认知、解码与阐释。
一、异质文化间的语言差异——形合、意合的动态阐释和意义外延
众所周知,英汉两种语言无论其形态变化,还是组合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异。“汉语由于重意合,没有严格的句子结构”,[3]“汉语的一句话是一个主题连锁,它所形成的一个言谈单位不一定是单独的句子,而可以是在同一主题下互相联系的若干句子。汉语的一句话是视点上流动、形态上松散、内容上完整的一句话;而英语的一句话就是一个言谈单位,是视点上固定、形态上自足、关系上完整的一句话”[4]。英语主谓分明,形态严谨,注重以形显意,有明显的形合倾向;而汉语则是通过内在的意义联系进行语义结构的对接,句法限制不严,方式灵活多变,更多强调的是意合效果。比如,英语语言中常常出现复杂的从句,以体现文体的优雅和思维的缜密,而汉语语言多用成语或排比,力求言简意赅,以表现文章的节奏韵律和语言的生动活泼。英汉句法结构的本质区别和差异,英汉语言各自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使我们认识到在从原语到译入语的转换过程中,语言层面的差异贯穿于始终。
现以高健(1)的译作《英国乡景》(2)为例,分析译者在理解文本的过程中,如何通过语言层面的选择与吸收、转换与变异寻找和创造异质文化文本之间的关联与链接,再现原文的风格和内涵。
The residence of people of fortune and refinement in the country has diffused a degree of taste and elegance in rural economy that descends to the lowest class.(English Rural ScenesWashington Irving)
富人雅士的精筑别墅之美又浸假而传至下层社会,因而在整个乡间蔚成风气。(《英国乡景》)
这段原文可理解为“富人们的居室弥漫并传播着一种情趣和雅兴,这种情趣和雅兴也传到了下层人中”。这样的翻译虽然保留了原文的形式对等和语言表层结构意义的对应,但却显得刻板呆滞、缺乏变化,“质实而不空灵,则神味索然”[5]。然而,译者并未因循守旧,受原文语法规则的束缚,他大胆地打破了英文中主谓结构的严格排序,把原文中作为宾语的taste and elegance 提升到句子的主语地位,把diffused 和descends 两个动词糅合在一起,通过语言表层结构的重新整合,构建了新的句式结构,增加了原语和译入语之间深层结构的关联性,寻找到了语用意义的平衡,把这段译成了:“富人雅士的精筑别墅之美又浸假而传至下层社会,因而在整个乡间蔚成风气”。在这段翻译中,译者对原语语言结构的微观调整改变了话语的表面语言特征,打破了原文中的显性链接,依靠意义关系构成了语句,从而再现了原文的风格特征,并实现了原语的认知效果。
再看另一段译文:“Nothing can be more imposing than the magnificence of English park scenery.Vast lawns that extend like sheets of vivid green,with here and there clumps of gigantic trees heaping up rich piles of foliage.”(English Rural ScenesWashington Irving)
英国园林景致的妍丽确实天下无双。那里真的是处处芳草连天,翠茵匝地,其间巨树蓊郁,浓荫翳日。《英国乡景》高健译)
这段英语的视点分别是“magnificence of English park scenery”和“vast lawns”。其中第一句采用了带有“nothing...more ...than”比较级的从句,从形式上来突出园林景致的妍丽无比。第二句中that 插入lawns 和extend 中间,从形式上看是一个定语从句。当它的意思没有表现完整时,又用with 短语加以补充说明。两个句子均是结构分明、关系完整的形合布局。此处译者超越了英汉句法结构差异的限制,在两种语际的转换中,解构了原语中“nothing...more...than”的句式,用“天下无双”这一成语巧妙地实现了原语意义的价值联结。随后又对that 定语从句进行适当偏离,接连使用了四个带有偏正结构的成语:芳草连天、翠茵匝地、巨树蓊郁、浓荫翳日。汉语译文这种流水式的连动句的使用,以动促景,以意显形,组成了连续有机的画面,从语义上弥补了形合的空缺,从韵律上表现了形合效果,从内容上体现了园林景致的妍丽。译文中形式、结构、语义等语言微观的改变,动态地、形象地展现了原文最大的语境,激活了读者的认同感,实现了原文与译文的最大关联,体现了原作的神韵,产生了诗学效果,最终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和语言交流。
由此可见,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语际之间动态的阐释性活动。翻译中形合与意合、表层的衔接与深层的认知,都体现在语言语境中的意义偏离与转换以及非语言语境中意义的解构与具象中。
二、异质文化间的意象解码——语言结构的重新整合与价值转换
在不同文化中,语言不仅具有指称意义,还具有语用意义。指称意义涉及语言语境中语言的微观结构,即语音、语法、词汇所表现的意义[6]23-25以及语言的前后搭配、上下文语言连贯等内在的联系;而语用意义则涉及非语言语境中语言的宏观结构,即社会、文化、情感使用域等方面的意义以及交际双方生成和理解话语时拥有的社会文化知识、认知能力等情景语境对语义理解的制约和影响。[6]由于特定的感知方式和社会文化知识的不同构建,具有语义或意义对应体的形象或意象,在被语言进行描述和言说时,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根据以上译文我们可以看到,汉语在意象组合关系的建立上比较自由,主观化程度高,而英语更注重概念间的逻辑联系在形式上的体现,不拘泥于意象的组合顺序。[7]英语和汉语语义结构上的这种异质性或差异性,使得一个个词语对事物情景的具体描述和组合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意象编码,使一种文化中具有的比喻意象很难在另一种文化中找到对应的匹配,因此无法进行形式对等和意义对等的转换,难以实现等价意义或等价概念的意义表达。然而,语言的深层次与基本意义之间通常存在着折射性的转向或隐喻过程,语言与语言、文化与文化互涉互融的过程中隐含着各种各样的关联与暗合。译者可以利用语际间存在的基本和广泛意义的转换条件,超越文本的表层结构,突破约定性的文化规范,把原语的结构意义和隐含意义投射到目的语的表达中。再看高健的另一段译文:
The cherishing and training of some trees;the cautious pruning of others;the nice distribution of flowers and plants of tender and graceful foliage;the introduction of a green slope of velvet turf;the partial opening to a peep of blue distance or silver gleam of water.(English Rural ScenesWashington Irving)
某些树木的当植当培,当剪当伐;某些花卉的当疏当密,杂错间置,以成清荫敷秀、花影参差之趣;何处须巧借地形,顺势筑坡,以收芳草连绵,茵茵席地之效;何处又宜少见轩敞,别有洞天,使人行经其间得以远眺天青,俯瞰波碧。(《英国乡景》高健译)
对于英文中层层递进、曲折迤逦的排列组合和形象描述,译者应用汉语修辞的排比和对称、押韵和叠韵,在目的语中进行了形合与意合的转换和重构,使译文看上去跌宕多姿,读起来酣畅淋漓,与原文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有异域风格之情,达到了神、形、义完美的统一,实现了异质文化意象在译入语文本中新的表现形式。
意象的解码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转喻或形象描述,是一种文化再现于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表现,“是把原话语在原文言内语境、情景语境及社会文化语境中承载的意义和信息改由译入语码来承载”的文化对话活动。[8]这种语言交际和文化对话活动中,信息的传递更多地需要依赖语言使用的客观环境——语境来实现。语境是认知主体——译者对语义理解的认知前提,也对其语义理解形成了制约和影响。语言交际中,译者不但要借助语境理解原作者的话语、原文语码所传递的信息,而且要通过语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感受。当语义与语境发生冲突时,当原作的形象信息不符合译入语境下的社会、文化规约和语言习惯,无法使读者产生等同的联想和情感时,译者需要借助词汇、结构、逻辑整合的差异性、灵活性,选择不同的视角、构建不同的意象去理解和把握某个感知到的事物和情景,以不同的语言风格传达、呈现新的意义,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实现一种文化赋予某意象的意义在另一种文化中的重构。这其间译者的认知语境必须与语言的表现联系起来,把整个语言材料同其交际背景和语体特征联系起来,同其使用的语境结合起来,调动生成话语和理解话语时拥有的社会文化知识和认知能力,充分利用一切可以被利用的知识潜能,并且协调大批信息,构建各种语义成分,运用各种关联、暗合等翻译技巧,使客观世界的描述更加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规范,使语言更具穿透力、表现力和解释力,更能展现原文的内涵和神韵。在高健的另一段译文中,这一点体现得更加至善至美。
...the pot of flowers in the window,the holly providently planted about the house to cheat winter of its dreariness,and to throw in a semblance of green summer to cheer the fireside.(English Rural ScenesWashington Irving)
在这一段语言转换过程中,如果按照等效、等值的理论,无论是指称意义还是语用意义,都很难在译入语中找到完全的对等来实现意义的生成,更无法体现原文的意境。而当译者根据文本的上下文语言所使用的主客观环境,对语言词汇、语法的微观结构进行适度的偏离和变异后,意象的描述空间立即变得广阔、自由和灵活:
......窗台上盆花簇簇,五色绚烂,环室则广植一些不太费钱的冬青,置身其间,恍然有冬去春回之感,而进入室内,熊熊壁炉之侧却又清荫片片,满眼凉绿,与炉火相映成趣。(《英国乡景》高健译)
此处作者脱离了常规意象与对应感知事物之间等价等值的联系,选择了意象的不同激活点,将静态的意象对象“盆花”“冬青”变成了动态的意象描述;将providently 巧妙地进行了词义和词性的变异,扩大了原文情景表现的空间;根据原语语境的隐含意义对“holly”这一原语文化信息进行了价值转换,扩大了这个西方人用在冬季圣诞节的文化饰物的语义联想,赋予了该词春的概念,使读者产生了“冬去春回、清荫片片、满眼凉绿”的新的意象感受。此外,在对“to cheat winter of its dreariness”和“to throw in a semblance of green summer to cheer the fireside”这两句抽象的意象联想进行语言编码和组合时,译者根据文化视角赋予语言意义的不同含义,通过对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意义创造性的映射、转换以及阐释,做出了超常规的、具象的意义编码与整合,实施了非等价等值的意象重构。译者这种文化认知和语言结构的重新整合与价值转换,产生了出其不意的修辞效果。“......熊熊壁炉之侧却又清荫片片,满眼凉绿,与炉火相映成趣。”译文这种新颖的、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深入浅出的语言描绘,把原文中造成读者阅读时难以定义的抽象概念和形象信息巧妙地予以了贴切自然的具象阐释和表达,形象地再现了原语中负载的隐含意义和信息,增强了译文的愉悦性、怡情性、可读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而英汉两种语言在语言形态及组合方式上均具有显著差异,这就要求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将其信息用符合译入语习惯的方式传达出来。而另一层面的文化意象的翻译就不仅是语言层面的符号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在对原语文化意象解码的过程中,译者不应对其简单复制,在使原语文本跨越译入语文本思想、文体、语言、语义之间、视阈之间的障碍时,译者应多维地、创造性地拓展其语言发挥作用的空间,积极地、主动地对译文进行全面、深入、直观的艺术处理和变异阐释,[9]拆解异域文化语境中不同的意象编码和思维定势,彰显异质文化中的情韵义理、色泽音响和形神风貌。
注释
(1)高健:山西大学教师、著名翻译家,出版过译作十余种,代表作为《英美散文六十家》,发表论文或其他文章数十篇,曾获译协“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2)English Rural ScenesWashington Irving(《英国乡景》华盛顿·欧文)——高健译注,选自《英美散文名作一百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239-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