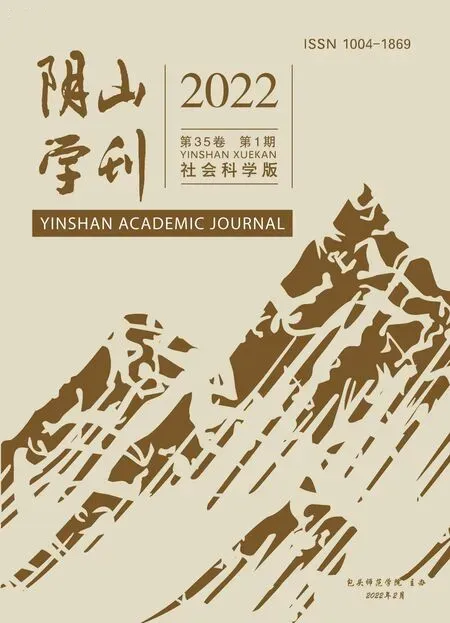王家卫《花样年华》的旗袍叙事和男性凝视 *
杨 光 祖,谢 蕊 冰
(西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电影《花样年华》是王家卫执导,于2000年上映的文艺爱情片,改编自刘以鬯的小说作品《对倒》。影片讲述了发生在1960年代一个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一个有夫之妇苏丽珍与一个有妇之夫周慕云,作为租居的两人因发现伴侣互相厮混出轨,失意、痛苦下,通过武侠小说的写作,及在复盘伴侣出轨的过程中渐渐相爱。但是,两人顾及周围邻里流言,对道德的恪守,尤其苏丽珍对丈夫的依恋,最终分手,周慕云远去新加坡。
男女主角由梁朝伟、张曼玉扮演,他们过人的演技和绝佳的外貌、神情,是该片成功的关键。而导演王家卫也是一代宗师,他对镜头语言的把控炉火纯青。整部影片情感压抑、环境朦胧,通过幽深的巷道、层层回廊、斑驳的墙面和暧昧的镜子,还有不断飘动的红色布幔,呈现了一个非常动人,但又极端克制的爱情故事。电影中对周太太和陈先生这一对发生婚外情的人物,也就是故事的引发者,没有给正面镜头,只是给了几个有限的背影。而把几乎全部的镜头都聚焦在周慕云、苏丽珍身上。而片名和片中的歌曲,是周璇在1940年代演唱的《花样的年华》,使得电影更加具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
“电影的全部就是关于如何在空间放置人物的身躯。银幕上的身躯和形象的力量驱动着叙事、表述系统、话语、需求、欲望、影片的情感和观众。”[1]本文着重讨论电影《花样年华》中的女性身体,因此,以影片主人公苏丽珍的身体作为主要对象。身体不仅是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还是推进剧情发展的媒介,具有很复杂和深刻的意义。尼采说:“将身体作为审美的主体,首先需要将人作为身体,所谓的哲学-美学都必须以身体为主体。这是美学的第一原理。”[2]因此,通过身体理论去阐释《花样年华》无疑是一种崭新的解读。梅洛-庞蒂说:“让身体成为世界的工具,让身体世界化,让世界经由身体的世界化而获得自身的表达。”[3]64
一、旗袍叙事与女性心理
黑格尔说:“如果在现代要替一个当代人物造像,就有必要根据这个人物的现实生活来确定他的服装和外在环境,因为他既然以一个现实的人的身份来提供艺术作品的题材,他的外表方面,其中主要包括服装,就绝对必要按照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样子去塑造。”[4]电影《花样年华》对空间的选择处理很有特色,狭窄的走廊,昏暗的街道,变幻的楼梯、墙面,帘幔的摇晃等,施加旗袍更多的束缚,导致旗袍的活力和情欲无法自由绽放。除去角色本身的压抑,观众一方面能感受到汹涌的情欲,另一方面也能感受到当时社会道德对女性的禁锢和主人公的极力克制。本来,身穿旗袍,肢体的活动就受到服装本身的限制,就像苏丽珍压抑在心底却无法见光的情感。身着的各色旗袍就像黑暗的牢笼,将苏丽珍困在其中,没有丝毫的宽松,不容许些许的放纵与出轨。那高耸的衣领,像城墙般坚固地抵挡着情欲外泄;复杂的盘扣像盾牌般守护着领口,阻挡着对胸口的窥探,那被遮挡的部分却又让人浮想联翩。可以说,《花样年华》是一部关于旗袍叙事的电影。它对旗袍的再现和表现,可以说短期内无人能够超越。
影片中苏丽珍共换了26件旗袍,变换的旗袍表现着主人公复杂迷乱的心理。身着颜色艳丽的旗袍,则是为了更好地掩饰苏丽珍内心的无奈迷惘,通过夸张的色彩,遮挡那无法表达的内心情感。当苏丽珍和周慕云一起讨论他们的太太和先生怎么勾搭到一起,开始了把他们蒙蔽在外的婚外情时,苏丽珍一再说,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周慕云也总是说,又不是真的,你难过什么?但最后发现,他们俩,和他们的太太、先生一样,也忽然互相爱上了。这就是:对倒。在这里,王家卫没有责怪谁,也没有用道德去谴责谁,他只是呈现而已。但正是这种非常克制的呈现,让电影具有了极其强大的张力和艺术魅力。
电影《花样年华》的服装设计师张叔平说:“以前的上海人爱面子,不管家境多不好,出去见人总要打扮得风风光光。苏丽珍应该是这样子,化好妆,梳好头,穿好衣,完全是一个打扮俗艳的女人。此外,考虑过电影的意念,人物的外表夸张虚饰,心里实有许多的weaknesses(弱点)和conflicts(冲突),这些旗袍更加要做得花哩花碌。每一场戏都准备多件旗袍,一试走位,我便决定哪一件感觉恰当。总括而言,我要的是一种俗气难耐的不漂亮,结果却人人说漂亮。”[5]看来,张曼玉就是有气质、有气场,硬是靠她的26件华丽的旗袍,把一个美丽多情而又富有道德感的女子呈现出来了。有人责怪这个电影故事性不强,肤浅苍白,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有了张曼玉和她的不断变换的旗袍,这个电影就是一部载入史册的电影杰作了。
旗袍在整部电影中作为女性身体的象征,链接了苏丽珍克制的道德感和人性最深处的情欲。苏丽珍在复盘周慕云的妻子勾引自己丈夫时妩媚的神情,与身着的旗袍交相呼应。影片中情绪的转换和男女主角内心情感的变化,通过不同色彩的旗袍与场景展示出来。苏丽珍所穿的旗袍都是高领、圆襟、十字袖、过膝的样式,衣领高耸强调着她脆弱的美丽和复杂的心理。整体气质和谐,恰到好处的衣领,端庄却不失亲和。设计师把1940年代的旗袍和1960年代的旗袍风格结合起来,让这26件旗袍更加富有特色,更具生命力。可以说,这26件旗袍也是《花样年华》的精魂,赋予了电影独特的格调。
影片中,张曼玉扮演的苏丽珍穿着绮丽的旗袍,涂着橘色的口红,妆容精致,打扮得体。这样明亮的色彩和昏暗的环境形成反差,苏丽珍的打扮与周遭的对比,更衬出自己的落寞。冷热两色,明暗对比,刻画出苏丽珍迷茫的形象,同时昏暗的场景既表达了家庭婚姻带给她的落寞失意,也隐喻出与周慕云在这段不能见光的感情中的苦闷。
影片前半部分,苏丽珍的旗袍颜色以素雅的淡色为主,这显示出她性格里温柔低调的一面,每每与人对话时低头浅笑,优雅从容。后半部分,旗袍的花纹开始复杂、深色,暗示出她内心的孤寂和情欲的萌动。在看孙太太打麻将时,一件白底红黄交织的旗袍,与她之前穿的素色旗袍形成反差。脱下原来的衣服换上另一风格的衣服,便意味着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男女主在宾馆约会的场景,苏丽珍身着红色蕾丝旗袍,与以往端庄成熟的形象产生对比。蕾丝本是情欲的表达,在这里凸显着两人情愫的萌动。在楼下来回徘徊,又在旗袍外加了外套。其实苏丽珍是非常传统的,也可说是1960年代女性情感和社会情况的写照。在幽暗的环境下不断变换的旗袍,红色、碧绿、花色、枝叶,仿佛具有了生命,在充分刺激眼球的同时也彰显着女性对爱情的向往。深蓝色的旗袍投射出内心的忧郁,土色的旗袍折射出内心的空虚。
“如果我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1)见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1时16分。当苏丽珍终下定决心和周慕云一起走时,他的房间已经空荡无人,一面镜子将苏丽珍内心的波动展现无遗。现实中的苏丽珍像被镜中的苏丽珍凝视着,苏丽珍眼眶中的泪水,又像是诉说着内心的挣扎矛盾。镜子是最真实的表达,将苏丽珍内心所隐藏的不愿见人的东西呈现出来。苏丽珍与周慕云两人就像镜像般存在,同样的情感遭遇,同样陷入新的感情,两人相互拉扯又相互包容。镜头侧面拍摄苏的上半身,胳膊搭在妆台上像是在寻找支点,泪水涌出,身形落寞。此时的她身着绿色格纹旗袍,与房间窗帘荡漾的红色格格不入。绿色本是象征希望的颜色。这一室的红,与身着绿色旗袍的苏丽珍相互映衬,变成了生机不再的褐。当苏丽珍再次来到周慕云的住处,蓝色的旗袍衬托她的忧郁悲伤。嗅着他的气息,点燃一根烟,拨通电话两相无言,最终带走了她的绣花拖鞋,似乎来过,又未曾来过。
作为同样以旗袍出彩的影片,电影《色戒》对王佳芝女性身体的处理与苏丽珍不同,她的身体是一种革命叙事,当然在情色的镜头里,也是一种类虐恋叙事。在那种变态的扭结中,是情与欲、革命和情感的较量。电影《色戒》的故事是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上海发生的一段故事,汤唯扮演的女大学生王佳芝色诱梁朝伟扮演的易先生。为了符合人物角色,她的旗袍颜色多以黑色、藏蓝等暗色为主,剪裁极为修身,配合精致的盘发及妆容,刻画出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小资女性形象。王佳芝的服装从最初的学生装转换成性感的旗袍,也是一种故事的推进,某种意义上,旗袍在这里也是一种叙事。与苏丽珍不同的是,王佳芝最终选择了爱情,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影片开始时身着白色棉布旗袍,塑造出一个青春的女学生形象;王佳芝为了色诱易先生,身着的旗袍腰身明显,两边的开衩高到大腿根,从开衩中看到修长的双腿,女性身体诱惑的曲线尽显。《色戒》中的旗袍与《花样年华》的作用类似,都是通过色彩、样式来表达女主心理的变化。
二、女性身体呈现的道德与情欲
人类一直在遗忘或鄙视身体,从古希腊柏拉图、《圣经》到笛卡尔,中国从先秦到近代,身体总是在灵魂之下。文学艺术更多的是歌颂灵魂,身体要么不提,要么就是被批判的对象。一直到尼采,才开始重新认识身体。社会学家吉登斯说:“社会生活与我们的身体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深刻的、本质性的关系。”[6]王家卫长期生活在香港,深受欧美现代思想的浸染,她能通过女主角的旗袍和女性的身体来推进故事,表达自己的电影主题,可谓得风气之先。而张曼玉确实也是天赋过人,她能通过旗袍和自己的身体语言,把那种复杂、暧昧,痛苦的感情呈现得如此之好,也让人不得不钦服。
《花样年华》里,苏丽珍本真的形象内敛清雅,因探明丈夫出轨而扮演另一身体,这具身体是别人的,是放荡诱惑的。本真的身体愤怒失落,扮演的身体诱惑风流。苏丽珍通过不同的身体身份来展示本真身体和欲望身体的共享及对抗。《花样年华》不以情节故事见长,它的叙事是意识流的,镜头是恍惚迷离的,叙述上以第三者客观视角表达。苏丽珍和周慕云在未发现丈夫(妻子)出轨前都只是邻居而已。影片开头讲述苏丽珍和周慕云在同天同栋楼里租到房子,后又在同一天搬家。工人屡次搬错的家具,狭窄的楼道,都预示着两家复杂的“缘分”。苏丽珍的丈夫和周慕云的妻子双向出轨,两人出轨的身体成为后续剧情发展的载体。当出轨的两人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伴侣时,苏丽珍的身体被压抑从而产生不满;当她与周慕云复盘丈夫(妻子)出轨的过程中,苏丽珍的身体是带着目的性且充满诱惑的,但同时也可看出这具“诱惑”的身体上的重重束缚。
影片开场,特写镜头拍摄苏丽珍的脸部,她从容地和房东相谈租房事宜,表情温婉,苏丽珍的身体被框在门框中间,镜头的左右摇晃、门的不停开合预示着苏丽珍未来摇摆不定。狭窄的楼道,昏暗的灯光,隐喻出她人生的灰暗。苏丽珍此时呈现出的状态是娴静典雅,精致的盘发、得体的妆容、修身的旗袍,配合狭窄的场景,可以感觉出苏丽珍与周遭环境之间的紧张感。影片04分37秒时,大家在房东陈太太家里打麻将,周慕云的妻子身姿性感地坐在苏丽珍的丈夫身旁,可以从周太的身体形象预感到后续故事。苏丽珍的形象是端庄,周太太的形象是性感,这样相反的身体形象可以反映出苏的丈夫对不同女性身体的欲望。
影片20分58秒,苏丽珍借口去周慕云家,周慕云的太太开门,可以从身后的镜子看见她的背影,与苏丽珍说话时镜头拍摄苏丽珍的正脸,大片留白显示了她内心的孤寂空虚。苏丽珍虽然试探着敲开周慕云的家门,她的身体却倚靠在门框并未进入家中;对谈中她的表情不再平静,带着一丝慌乱。影片中出现大量的房间镜头,将其设定为背景也是有一定寓意的。苏丽珍租住的是房间,也是家,那么家作为极具隐私性的场所空间,却因第三者的闯入,形成了对苏丽珍身体压抑的隐形者。女性的身体是男性欲望的产化物。我试图将影片中周太太性感的身体姿态,定义为苏丽珍丈夫欲望的萌芽。尼采曾说:“肉体是一个大的理性,是具有一个意义的多元,一个战争和一个和平,一群家畜和一个牧人。”[7]从影片可看出,苏丽珍和周太太在身体形象上的差异,一个端庄大方,一个性感妩媚。苏丽珍和周慕云在复盘出轨的过程中,镜头多次拍摄由苏丽珍扮演的这具“身体”的特写,诱惑的眼神,挑逗的手指,迷离的神情。但这与苏丽珍本真的身体形成反差。周慕云两次在出租车上握苏丽珍的手,以及苏丽珍说的“我今天晚上不想回家”(2)见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1时13分26秒。,表达了这具所扮演身体内在的欲望萌芽。与其说是渴望,不如说是本真身体对不幸婚姻的无声反抗。苏丽珍的身体被夹在欲望和道德现实间,苏丽珍的欲望是探明丈夫出轨的真相,这是一个身体对另一个身体的被占有的表现。
两人总说“我们不会像他们一样的”(3)见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55分31秒。,但苏丽珍的身体同时也代表着道德、欲望,这与她欲望的身体相悖。周慕云在宾馆租房写小说,苏丽珍去看他,匆匆走上宾馆的楼梯,又匆匆走下楼梯,又在楼梯扶手上低头沉思。这时镜头的拍摄为:苏丽珍走向周慕云租住的房子,镜头先拍摄她快速行走的双脚,表达这段走廊的长度;从侧面拍摄苏丽珍上下楼梯及低头沉思,来表达苏丽珍内心的挣扎不定;苏丽珍从周慕云的房间离开后,镜头拍摄苏丽珍离开时脚步的特写。短暂片段的出现,表达了苏丽珍对周慕云情愫的涌动,却又被社会道德、邻里流言束缚的心理,这是两种欲望的斗争。复盘,意为探明出轨,也是对丈夫出轨行为的隐形反抗。于苏丽珍而言,欲望促使身体出走,道德促使身体回归。亨利·列斐伏尔指出,身体也是一种空间,“每个身体都是空间,也都有自己的空间:它在空间中塑造自身,同时也产生这一空间。”[3]89我们通过电影中苏丽珍的身体姿势、踪迹,就可以发现她的身体空间是狭小的,是自我压抑的。在办公室,她仅仅是一名老板的秘书,帮助老板处理一些事情,她无法自我做主。在家里,我们能感觉到丈夫的强势和能干,她是附属性的和被支配的。搬家,是她在指挥着搬,丈夫根本就没有出现。而且丈夫经常出国,尤其经常去日本,带过来一个高档煮饭煲,她就很有成就地让大家体验,并让丈夫帮大家从日本买。影片1时13分58秒,在日本公干的丈夫为苏丽珍点了一首歌曲,苏丽珍坐在矮小的板凳上,面色愁苦;周慕云与苏丽珍一墙之隔,手里抱着煮饭煲低头沉思,镜头的左右移动营造了不安紧张的情绪,隐喻着在道德流言束缚下两人情愫涌动的心。如若将两人此时的状态拼接,多像一面完整的拼贴画。这里,就可以看出,她的身体空间,就是以丈夫的空间为自己的空间。她走不出丈夫的空间,总是以丈夫为中心。这就是她在发现丈夫已经出轨,并和周慕云的妻子在日本旅游,她和周慕云在复盘伴侣出轨的过程中,也相爱了。但她还是走不出她被丈夫规定的身体空间。她总是说,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其实,是她无法掌控自己,她是被掌控的。
身体的一切特性诸如欲望、感官、变幻和生成,都是与生命共享的。苏丽珍有家庭,但丈夫出轨,在这个现实状态下,在模拟复盘的过程中通过“欲望身体”理解身体,这种身体通过周慕云的“假象身份”来建构自我的慰藉。最后两人分别,苏的痛哭是以周慕云为中心的两种身体的不舍,在这里苏丽珍欲望和道德身体相融合,或许在此时的环境下,苏丽珍的确是将周慕云模拟的对象看作真实伴侣。影片最后,两人最后一次模拟分别的场景,苏丽珍拒绝了周慕云的心意,两人被一面栅栏隔开。长镜头先拍摄苏丽珍的肢体,可以看见她的手臂颤抖,紧接着用手紧掐自己的手臂,手背青筋暴出,随着镜头的转换,她的脸上泪水涌出,眼神空洞,随后在周慕云的肩头痛哭,悲寂的感觉油然而生,长镜头的拍摄方法将那份无法直言的感情完美表达。
苏丽珍的身体姿态是非常不舍的,她感受到自己在丈夫那里缺失的情感,身体的隐喻在苏丽珍扶手哭泣中被放大。最后一次模拟的结束,苏丽珍这具欲望的身体不再,这具身体存在的使命在哭泣中结束。这具欲望的身体对道德的身体来说始终是束缚,苏丽珍在反抗丈夫出轨的同时,揭示出了身体背后所隐藏的道德意识。福柯认为:“一切道德活动确实是与身处其中的现实有关,与它依据的规范有关。但是,它还包含一种与自我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对自我的意识’,而是把自我塑造成‘道德主体’。其中,个体限定了自身作为这一道德实践的对象的范围,明确了自己对所遵循的戒律的态度,以及把自我的道德实现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8]在《花样年华》中,苏丽珍对这种规训精神领会深刻,她在“成为”丈夫与周太太同类人的边缘游走后,选择成为道德主体。
影片最后,苏丽珍站在门口催促孩子庸生,影片最后也没有交代这孩子的父亲是谁,只留给观众遐想。镜头聚焦在苏丽珍与儿子身上,模糊了周边。此时周慕云站在门口,房门将两人分割成两个空间,没有敲门打扰,两人最终还是在自己的空间下前行。但值得思考的是,从苏丽珍与儿子的站位中看出,有一块地方是明显空缺的,不知是不是导演给孩子父亲留下的站位?
整部影片中,苏丽珍都没有处理好自我与外界的关系,她和周慕云在复盘的过程中的情感错位,让苏丽珍无法适从。这段情感横在两人之间的隔膜是道德,持续的纠结贯穿全场。直至影片结束,她依然沉浮在这种纠结里。“康德在‘论崇高’后得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命题,美包含了道德。正如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儒家美学也包含伦理道德,强调审美和道德不能分开。”[9]苏丽珍在丈夫出轨的痛苦中,和周慕云越走越近。但这份感情包含着“羞耻感”,在潜意识中他们都不想做伴侣的翻版。为避免邻里的闲话,尤其因为自己潜意识里的道德约束,她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同坐出租车,为了避免邻里的怀疑,不能一起在楼门口下车。在苏丽珍的心里,她不可能和丈夫一样出轨,但同时也控制不住对周慕云的关心。周慕云生病,朋友随口提起想喝芝麻糊,苏丽珍煮了一大锅芝麻糊请邻居喝,实则为了周慕云,避免邻里的闲话邀请大家共食,她掩饰得很小心;两人写武侠小说,忽然房屋主人回来,害怕被猜疑,只好待天亮才回到自己房间;出租车上,苏丽珍躲避了周慕云的手;下雨不能撑着周慕云的伞回家,原因是邻居认得他的伞等等。这些都可看出社会道德和邻里的巨大力量,使苏丽珍的情感受到压制。
《花样年华》以隐喻的身体方式展现了苏丽珍在情感中痛苦的经历,她的灵魂和身体在痛苦的驯服中挣扎。苏丽珍的喜怒哀乐都随着两个男人对她的态度变化着。苏丽珍和周慕云的感情是互相救赎,她把对自己丈夫的“情”转移到周慕云的身上,来平复自己情感上的创伤,但最后她还是退缩回去了。电影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发现,苏丽珍还是深爱着周慕云,但她错过了那个机缘,结果永远没有了。
三、男性凝视下的女性身体
王家卫说:“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不是四个人的故事,是两个人的故事。”[10]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看电影,就能看出这一点。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两个人,都没有出现正面影像,只是出现了几个残缺的背影和不多的对话而已。苏丽珍丈夫常年在外公干,在陪伴、精神、忠诚上都是失职的,丈夫的缺席意味着丈夫本职的丧失,也是为后续的出轨做了铺垫。《花样年华》虽说是一部以情感为主的电影,但也隐形地看到了男性话语的存在。苏丽珍作为家庭主妇,丈夫是她情感、金钱等的依赖;在对周慕云产生情感后,因道德等因素这段感情最终以分离收场。苏丽珍作为一个走不出丈夫“范围”的女性,她与周慕云的爱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变味的出逃,在这段关系中,苏丽珍是“凝视”的对象,周慕云是“凝视”的主体。“‘凝视’(gaze)——携带权力运作或者欲望纠结的观看方法。它通常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产物,观者被权力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位置,被观看者沦为‘看’的对象同时,体会到观者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11]
苏丽珍和周慕云都扮演了对方生活中缺失的角色,苏丽珍将自己隐藏在所扮演身体的阴影下,可能是她本真的身体的欲望需要这种角色呈现,这场名为探究的游戏,亦是补偿,是虚构的假象对现实的补偿。苏丽珍在这场游戏间再次陷入周慕云的情感中,苏丽珍的角色定位——依靠丈夫的女性/与周慕云产生纠葛的已婚女性,她的两个角色都躲不开男性,像是男性下的阴影;她或许找到了真相,但她也付出了代价,女性的悲哀得以尽现。
这场爱情在社会道德的棒打下分道扬镳,这种道德又名:从一而终。苏丽珍暗淡的人生与这两个男性的所为息息相关,或是说以婚姻为枷锁的前提将苏丽珍禁锢,为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弱势地位敲下审判锤。波伏娃《第二性》认为“女性之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作为男性中心文化的‘他者’而被建构的。”[12]9苏丽珍的丈夫作为婚姻承诺者的形象坍塌,而苏丽珍被规定不能有除婚姻伴侣之外的情感。“婚姻是传统社会赋予女性的命运。”[12]199以苏丽珍为代表的女性像是带上了镣铐,只能作为男性的影子或附属品。她们不能追求自己的爱情,追求自己的自由。她们是属于丈夫的。但苏丽珍的情感归属在丈夫身上得不到回应,她将自己放在男性附属品的层面,她失去了自己作为女性主体的立场。整部电影苏丽珍对人介绍自己都是我丈夫姓陈,苏丽珍只是一个有着夫姓的女人。她的遭遇体现着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困境,种种细节揭示着男性话语的地位。“王家卫电影是一种混杂着女性目光的男性视角的电影。”[13]
此外,抛开道德因素从人的需求本性考虑,周慕云的妻子出轨满足了女性自身对情感需求的追逐。道德本就是社会意识的基本形态,饮食男女,食色,性也,是否可以认为在满足自身情感方面,周慕云的妻子为苏丽珍做了“表率”?正如彭富春所言:“人是身体。……身体就是人的生死爱欲。这要求不要把人理解为没有肉身的漂浮的灵魂和语言的符号,不要追求死亡之后的永垂不朽或者死而复生,而是回到身体所处的现实世界。……它既不是动物性的,遭到嘲笑和唾弃,也不是神圣性的,受到推崇和膜拜,而是人性的,是合乎人的本性和生活的,因此也是值得理解和尊重的。”[14]
苏丽珍无法放下自己是“陈太太”这一身份,无法从自己给自己做的栅栏中走出。朱迪斯·巴特勒说:“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是不同的,而社会性别是生理性别的文化建构。”[3]83前文提到过,苏丽珍的两种身份都是通过丈夫及周慕云所构建的,妻子的身份是在丈夫婚姻前提下所真实存在的,扮演的身份无法通过社会伦理以及苏丽珍自身所强加的潜意识。周慕云在远走前像苏丽珍求爱,希望一起远走高飞,但苏丽珍无法从自己原有的家庭身份中出走。是苏丽珍不想走吗?不是的,她想走,但是她没有找到可以从这些枷锁中脱离的方法,所以这段感情画上了并不完美的句号。她保全了她的婚姻,以陈太太的身份继续活着。或许苏丽珍想过改变这种性别身份下暗含的男性权利,与周慕云复盘也好,动了情也好,这都是对男权绝对话语的一次冲击,虽然以失败告终;她回到了原本的生活,接受了这种无力的命运。作为观众而言,只有唏嘘感慨。“身体是来源的处所,历史事件纷纷展示在身体上,它们的冲突和对抗都铭写在身体上,可以在身体上面发现过去事件的烙印。”[15]
王家卫作为男性叙述者对苏丽珍的整体塑造,是站在男性审视的角度。王家卫以男性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感受的空间,苏丽珍作为女性丧失了主体性,在导演王家卫及周慕云的眼中成为“被看”的“他者”存在。苏丽珍的“身体”是整部电影进程的主线,自我身体和欲望身体二者交缠,自我打败了欲望,意味着她的身体不是她自己的,她没有能力支配自己的身体。波伏娃认为:女性的身体是由社会规定出来的,是社会文化强加和扭曲的结果。张金凤在《身体》一书中认为:“按照波伏娃的看法,在主体与身体的关系之中,两性之间是有差异的。在父权制社会里,妇女被贬抑为等同于身体,她就是她的身体,她的身体就是她;与此相反,男人却并不被限制在身体之中,男人的价值不与身体密切相关,他的意义超越了身体。”[3]81所以,在电影里,作为男人的周慕云,可以从妻子的背叛里走出来,爱上苏丽珍,并向她求爱。苏丽珍虽然也爱上了周慕云,但她的身体告诉她,她不能如此做。她还是退回到自己的那个属于丈夫的身体之内,为那个已经不爱她的丈夫守节。可以说,就苏丽珍来说,那个几乎没有出场,也没有正面影像的丈夫,才是主体,才是她自己。波伏娃说:“女人是由男人决定的……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16]那么,这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一部分女性的选择,但也是导演王家卫男性的凝视,是他的一种选择。不管周慕云,还是苏丽珍的丈夫陈先生,作为男性,都是自立的、独立的,但作为女性的苏丽珍却不是,她在电影中的弱势地位极其强烈,在两个男人之间,她都没有自己。她一直是恐慌的、担心的、哭泣的、柔弱的,甚至在最后一刻,她也是摇摆的,无法决定自己的未来。电影里,苏丽珍的那个老板何先生自己有外遇,让苏丽珍为他在妻子和情人之间周旋,但当他接到了周慕云找苏丽珍的电话,感觉到她也有了外遇,却有一种高傲的鄙视。这也是男权的凝视,也可以说是导演王家卫的凝视。
当然,王家卫也是尽量真实地书写这两对男女的情感,并没有做道德意义上的评价。即便那私通的两位不在场的男女,电影也没有谴责他们,只是呈现而已。但作为电影主角的周慕云、苏丽珍,我们可以感觉到周慕云的独立、自主和苏丽珍的退缩、挣扎。电影最后,周慕云把他对苏丽珍的爱情这个秘密埋藏在柬埔寨吴哥窟的那个墙洞里,标志着这一段情感的结束。但等周慕云离开后,镜头显示那个墙洞里,却生长着青青的绿草。这又暗示着什么呢?电影快结束时,出现了下面一句话:“那个时代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4)见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1时28分50秒。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暗示着像苏丽珍这样的女性也已经“都不存在了”?一批展示身体消费的新女性要上场了?或者,就连这种纯洁的爱情,也“都不存在了”?这部电影只是对历史的一种怀旧而已?怀念这个世界还曾有这样的一种爱情,这样的一对男女?或者,甚至这部电影也是对香港的一种隐喻?王家卫对苏丽珍的塑造,肯定有自己的男权眼光和凝视,这毫无问题。但他的这种怀旧和凝视里,也有着他的无奈和苍凉。毕竟一个时代过去了,另一个汹涌澎湃的消费时代来临了。身体,尤其女性身体,也成了一种畅销的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