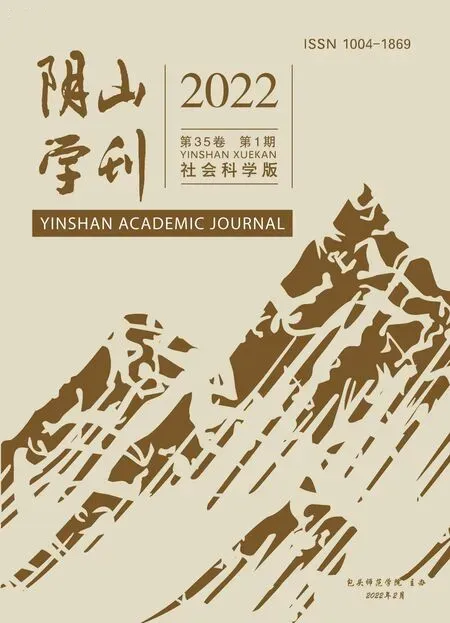古代丝绸之路谣谚述论 *
傅 绍 磊,郑 兴 华
(宁波财经学院 象山影视学院、人文学院,浙江 宁波 315175)
古代丝绸之路谣谚是在特定历史空间下产生的文化传播现象,能够普遍反映社会各个阶层、方面的心声、问题,是揭示古代丝绸之路社会文化面貌及其历史变迁的重要研究角度。本文就结合谣谚文本,通过研究古人对“丝绸之路”的认知模式揭示历史上“丝绸之路”的文化认同,为“一带一路”合作向纵深化、长远化方向发展提供历史文化的经验参考。
一、古代丝绸之路与谣谚的生成环境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以中国西北边陲为起点,贯通中亚内陆腹地,一直延伸到西亚、欧洲等地;海上则以东南沿海为起点,北上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南下东南亚、印度,甚至远至非洲沿岸,形成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在唐宋鼎盛,延续明清,有着幅员广阔、复杂多元的地理环境和长期动态的持续过程。而且,中国与沿线国家频繁互动,形成极为复杂、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代丝绸之路的形成意味着从地理空间的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平台的构建,从而为谣谚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生成环境。
(一)地理环境
汉武帝将西域纳入中国版图,推动西域及其周边地区进入当时人们的认知领域,带来最直接的审美冲击就是广袤,《汉书·西域传》:“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1]3871西域三十六国在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尚未延伸到中亚内陆,但是,已经与传统的中原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衬托个人的渺小,影响谣谚形成苍凉的气息。西汉公主刘惜君和亲西域乌孙,思念故国,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云云;乌孙国,在西域西北部,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所以,刘惜君感觉与汉朝天各一方,因为广袤的地理空间而加剧了对故国的思念[1]3903。西域在匈奴西南面,界线模糊,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也并不严格区分。李陵在匈奴境内与苏武诀别,歌以咏志,“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云云,不自觉地以“万里”“沙幕”形容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广大地区[1]2466。海上丝绸之路在谣谚语境中的形象则经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反映的是人们对海洋认识的变化。中国是内陆国家,文化中心远离沿海地区,而且,受到航海技术的限制,长期以来海外交往极为有限,对海洋的认识也就颇为贫乏,主要局限于东南沿海的近海,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最主要范围。近海海洋环境颇为单一,唐宋以来,虽然商贸、外交等逐渐频繁起来,但是,航道范围并没有突破近海,“潮水来,岩头没。潮水去,矢口出。”[2]福建港口众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从而形成独特的海洋文化,通过谣谚表达海洋形象。歌谣中的海洋属于沿海,环境颇为规律,潮起潮落,是当地人们对海洋的基本认知。宋元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兴盛,航程延伸,渡海远洋,面对更加广阔的海洋,从而突破原来的认识,推动海洋形象在谣谚中复杂起来,“日本好货,五岛难过。”中国与日本的交流历史悠久,明清时期,形成从明州、泉州经长崎到日本的固定航线,是中国古代海外交往的重要航线。所谓的“五岛”就是长崎的五岛列岛,以航行环境恶劣而闻名,在古代的航海技术条件下,对于从海路东渡日本造成严重威胁,于是,在歌谣的语境中就是危机四伏的场所,代表的是当时人们对于海洋的全新认识,与早期海上丝绸之路时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3]456。
(二)政治环境
古代丝绸之路受到中原王朝政局动荡的深刻影响,影响谣谚充满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西北边陲,特别是凉州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要塞,早在两汉时期就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互动的前沿,魏晋南北朝,孤悬塞外,还是难以避免地受到政治动荡的波及,至是,谣言验矣。”[4]2229当时凉州政权多有更迭,也激发谣谚的活跃,《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传》:“凉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学,清辩有志节。初适扶风马元正,元正卒,为玄盛继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抚前妻子逾于己生。玄盛之创业也,谟谋经略多所毗赞,故西州谚曰:‘李、尹王敦煌。’”[4]2526尹氏毗赞李玄盛创业凉州在当地传为美谈,谣谚相传。海上丝绸之路远离中原王朝统治中心,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主要由当地官员维系。当地人们多通过谣谚褒贬官员治理水平,表达对于中原王朝的认同程度,《后汉书·贾琮传》:“旧交阯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特敕三府精选能吏,有司举琮为交阯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5]交址郡于元鼎六年设立,东邻北部湾,物产丰富,自西汉以来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逐渐成为商贸繁荣地区,因为“京师遥远,告冤无所”,官民关系也就更加微妙。中平元年,正值中原黄巾起义,交址郡动荡。贾琮治理有方,获得当地人们高度认同,终于反映到谣谚之中。所以,交址郡虽然偏居一隅,但是,还是受到中原王朝政局影响,影响所及,也传递到当地谣谚。
(三)商业环境
古代丝绸之路商贾云集,推动众多城市的商业发达,为人津津乐道,通过谣谚广为传播,反映沿线城市繁荣,形成文化影响,形成商业与文化相得益彰的局面,《容斋随笔》卷九:“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6]唐朝对外来民族、文化极为包容,从而推动丝绸之路的兴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作为陆、海丝绸之路向中国内陆延伸的重要城市,唐代扬州、益州聚集大量西域胡商,经营致富,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数一数二的都市,所谓“扬一益二”是也。谚语因为民间的广泛传播而更加深入人心,久而久之就进入诗歌等文学之中,徐凝《忆扬州》:萧娘脸薄难胜泪,桃叶眉尖易觉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诗歌显然受到“扬一益二”谚语的影响,而徐凝是中唐诗人。由此可知,扬州等商业城市的繁荣在盛唐之后一直持续。
(四)文化环境
宗教等外来文化也随着外来民族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汉唐时期,逐渐达到极盛,魏晋南北朝乱世,逐渐与民族、地方政权相结合[7]1531。而在隋唐时期,随着政局逐渐趋向稳定,宗教文化的传播也转向制造谣谶,通过影响政局而逐渐进入主流文化语境,《大唐创业起居注》:“开皇初,太原童谣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东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拟于东海。”(1)《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传》:“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840页。唐长孺以为“金山白衣天子”与“白旗天子出东海”等都与弥勒信仰有关,由此可知,外来宗教文化影响下的谶语延续时间之长,远不止唐代。《白衣天子试释》,《山居存稿三编》,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20页。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当时社会对于外来宗教文化的接受程度颇为可观,所以,所谓的“白旗天子”“白衣天子”等谣谶也就能够形成足够强大的影响力,连隋炀帝都深信不疑。总体而言,随着丝绸之路而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必须经过广泛传播,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才能够获得认同;谣谚因为能够和社会各个阶层接触而成为颇为理想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外来文化刺激谣谚的产生,随着谣谚的传播而获得认同,是传播现象,也是文化现象。
二、古代丝绸之路谣谚的传播主体
古代丝绸之路不断突破地理的界限而集合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终于形成多元化的中外交流平台。独特的传播主体推动丝绸之路悄然进入人们日常生活,也成为丝绸之路文化难以分割的部分。
(一)胡商
外来音乐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原王朝[8]。胡商起到重要的纽带作用,《旧唐书·音乐志》:“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和之。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胡儿令羯人白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9]1069胡商人数众多,流动频繁,遍布各地,基于娱乐等需要,逐渐将外来音乐及其歌谣带到民间社会,往往在胡商聚集的酒店,由胡姬表演,很受欢迎,李白《少年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士人的参与则推动外来音乐及其歌谣的中国化,以通俗的方式传播更加广泛,《一切经音义·苏莫遮冒》:“亦同‘苏莫遮’,西域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或以泥水沾洒行人;或持罗缩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冒就是后来的词牌名“苏幕遮”的原型,当时却是娱乐色彩浓厚的外来歌舞形式。
(二)士兵
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冲突频繁,士兵长期驻扎。战争的压力和苦寒的地理环境激发士兵产生复杂的情绪,歌以咏志,形成后来的鼓吹曲辞、横吹曲辞,而且,在音乐、歌词等方面都胡汉杂糅,《乐府诗集·横吹曲辞》:“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已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10]309横吹曲从北狄来到南越七郡,也能够被接受,足以说明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情绪的强烈共鸣能够超越不同的地理环境,激发共同的情绪体验,所以,胡汉士兵歌谣往往互相影响,普遍传唱。但是,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等军中之乐代表的毕竟只是特定的主题,所以,在经过士人的加工之前传播的范围还是有限,只是限于边境和宫廷仪式。
(三)宗教人士
外来宗教进入中原王朝之后,因为文化差异,传播面临严峻的本土化挑战,必须以通俗易懂的形式面对最广泛的受众,《高僧传》卷一三:“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11]所谓的“傍引譬喻”,实际上就是通过引用谚语、俗语等,从而更加方便受众接受宗教教义。唱导经过不断完善,发展成俗讲、变文,在唐朝颇受欢迎,《乐府杂录·文叙子》:“长庆中,俗讲僧文叙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12]文叙号为“俗讲僧”,说明俗讲、变文等说唱形式对于宗教而言,已经出现专业化趋势。从唱导到俗讲、变文,谣谚也就通过宗教人士深入浅出的宗教教义宣传而广为传播。
(四)士人
古代丝绸之路谣谚源于民间,多为口头产生,易于变异、散佚,只有经过士人转化为书面形式,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流传后世。作为古代文化程度最高的阶层,士人毫无争议地在中外交流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认知、了解、认同异域文明,推动中外交流向着更加广泛、深入的方向发展。所以,士人记录、改编,甚至发明谣谚往往有着相对明确的目的,终于让谣谚出现在史书、文学、金石等文献之中,帮助后人回顾历史真相。
三、古代丝绸之路谣谚的传播内容
谣谚作为特殊的记录方式,以更加直接原始的形式反映古代丝绸之路动态嬗变过程和社会各个侧面,通过谣谚内容,能够以独特的角度认识古代丝绸之路。
(一)自然名物
古代丝绸之路是当时人们认识中原王朝以外世界的窗口,最直接的风景就是新奇别样的异域名物。《史记·大宛列传》:“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13]3170汉武帝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获得西域各地马匹,因为不同于中原所有,所以,引起激赏,以为歌谣,《史记·乐书》:“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13]1178《汉书·礼乐志》:“天马来,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来,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来,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来,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来,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来,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1]1060、1061天马歌谣属于官方,不但记录西域马匹,而且表达汉朝威服四夷的强烈自豪感,代表的是当时官方对丝绸之路的态度。民间谣谚在记录自然名物的基础上主要是表达当时人们独特的审美体验,而极少意识形态色彩,庾信《燕歌行》:蒲桃一杯千日醉,无事九转学神仙。蒲桃即葡萄,也代指葡萄酒,从大宛进入汉朝,越来越受到欢迎,到了南北朝后期,已经极为风靡。事实上,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国力强盛,就能够最大限度地接纳通过丝绸之路输入的物资,远不止马匹,从而成为谣谚的重要内容[13]3173、3174。
(二)社会民生
古代丝绸之路大大提升了边境地区对于中原王朝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东南沿海,长期以来因为偏居一隅而以蛮荒形象出现在当时人们的语境中;成为丝绸之路前沿之后,越来越获得重视,风土人情也就逐渐成为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高怿《群居解颐》:“岭南地暖,其俗入冬好食馄饨,往往稍暄,食须用扇,至十月旦,率以扇一柄相遗,书中以吃馄饨为题,故俗云:踏梯摘茄子,把扇吃馄饨。”[3]786、787岭南因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地处偏远却逐渐发展,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人文荟萃,引人关注,《明诗综》记录大量岭南谣谚,从中可以发现当地独特的社会民生,是后人认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社会风土人情的宝贵史料。
(三)政治趋势
古代丝绸之路对于中原王朝、周边民族政局嬗变极为敏感,加上人口流动频繁,信息密集,往往形成谣谚反映政治趋势。魏晋南北朝,凉州政权频繁更迭,成为凉州谣谚中的重要内容。永嘉年间,凉州刺史张轨遣北宫纯、张纂、马鲂、阴浚等率州军击破王弥于洛阳,又败刘聪于河东,京师歌之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凉州鸱苕,寇贼消;鸱苕翩翩,怖杀人。”永嘉年间,长安谣曰“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建兴年间,焦崧、陈安寇陇石,东与刘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太熙年间,谣曰“蛇利炮,蛇利炮,公头坠地而不觉。”不久,张寔被杀;永元年间,谣曰“手莫头,图凉州。”张茂以为信,诱杀贾摹,于是豪右屏迹,威行凉域;太元年间,张骏之立也,姑臧谣曰“鸿从南来雀不惊,谁谓孤雏尾翅生,高举六翮凤皇鸣。”后张骏复收河南之地[4]2223、2229、2232、2234[7]2194。凉州地处丝绸之路要塞,属于高度开放性社会,与中原王朝、周边民族关系密切,互动频繁。所以,政局嬗变波及的范围更大,而不仅限于张轨等高层政治集团,每当重要政治事件前后,谣谚不但反映而且参与其中,与政治趋势之间形成紧密联系。
(四)战争冲突
古代丝绸之路战争频繁,强烈冲击地方社会秩序、价值观念。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讨匈奴,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夏,又攻祁连山,捕首虏甚多。汉朝对匈奴、西域诸国态度颇为强硬,主要以军事力量经营对外关系。歌谣说明的是匈奴等周边民族对于汉朝武功的敬畏。唐朝民族态度更加开放、宽容,在军事的基础上,更加注意政治安抚,文化感召,从而获得周边民族的认同,以谣谚表达心声。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征讨高昌,先是,其国童谣云:“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9]5296高昌是汉朝西域都护府旧地,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避难场所,聚集大量汉族人口,对中原王朝颇为认同,只是迫于突厥压力而摇摆不定,当充分意识到唐朝经营西域的决心和力量之后,终于有所归属。所以,童谣不但是在陈述唐朝高昌军事力量对比的事实,更是在表达归附唐朝的意愿。事实上,丝绸之路上的战争冲突在中原王朝的歌谣中更加频繁地出现,一方面,因为不断的军事胜利,歌颂将士英武风采,抒发四夷来朝的豪情壮志,《上之回》: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10]227。另一方面,则因为长期的兵役而宣泄强烈的反战情绪,《陇头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10]371。
四、古代丝绸之路谣谚的记录
谣谚搜集,古已有之。周朝就已经有专门的采诗官等机构,通过搜集谣谚了解民间基层,从而为社会治理提供依据,形成《诗经》等传世文献,《汉书·艺文志》:“《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1]1708周朝采诗传统因为儒家的推崇而在历史上一直保持,通过乐府等音乐管理机构运作,影响谣谚从口头传播进入书面记载,以文献的形式保存,流传后世。
古代丝绸之路谣谚最初主要来自边境地区,作为当地社会民情的反映;后来逐渐随着外来音乐大量进入中原王朝,以周边民族歌谣的形式进一步书面化;因为古代没有特定的“丝绸之路”概念,所以,也就不可能集中归类,而是分散保存在不同的文献中:
正史: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坚持“礼失而求诸野”,强调在民间寻找礼乐制度的依据,从而影响后世史家对于非官方非书面化史料的重视,推动谣谚等流行于民间基层的口头史料进入官方主流语境。所以,历朝正史修撰都大量采用谣谚,特别是在外来民族传记、地理志、礼乐志、会要政书等正史中,就有为数众多的谣谚,反映中外交流多元化的历史真相。《史记》《汉书》等则为后世正史采用外来民族谣谚提供了可以参照的体例,引起强烈反响。
笔记史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形成士人私家著述传统,比官方正史记录谣谚的范围更大,能够对正史进行合理补充。汉唐时期,士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中外交流的时代潮流之中,而且,诉诸文字,以唐朝杜环为例,天宝十载随安西唐军西征中亚,作为战俘被送往阿拉伯,获得优待,游历西亚北非,又从海路经过东南亚辗转回到唐朝,几乎是全程往返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著有《经行记》记录沿途见闻。事实上,当时行走在丝绸之路上,或者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的士人远不止杜环一人,笔记史料更是卷帙浩繁,从而能够更加系统地记录丝绸之路谣谚。
诗歌总集:谣谚在古代长期被纳入诗歌的范畴,从而能够进入历史上各种类型的诗歌总集。《诗经》、汉乐府等歌谣因为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和高度的艺术性而获得儒家的激赏,成为士人学习的典范,后世出现大量衍生作品。汉唐士风刚健外向,士人崇尚游历,特别以从军边塞为荣,从而激发汉边塞题材等谣谚不断焕发新的审美生命力,《出塞》《从军行》《塞下曲》等纷纷成为士人创作的常见主题,每个时代都赋予独特的意义,终于形成唐代边塞诗歌的繁荣局面。
谣谚总集:宋元以来,谣谚逐渐与诗歌拉开距离,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意味着谣谚现实意义的回归,推动谣谚总集的出现。宋朝周守忠的《古今谚》采摘古今俗语又得近时常语,虽鄙俚之词,亦有激谕之理;漫录成集,名《古今谚》,古谚多本史传,今谚则鄙俚者多矣;明朝杨慎《古今谚》《古今风谣》采录古今谣谚各为一编,都是古代颇为重要的谣谚总集。但是,周守忠年代过早,而杨慎则记录粗疏,所以,不甚完备,体例芜杂;古代谣谚总集堪称集大成者当属清朝杜文澜《古谣谚》,在前人基础上引书八百六十种,辑得谣谚三千三百余条,而且引述本事,注明出处,有疑难则详加考辨,极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