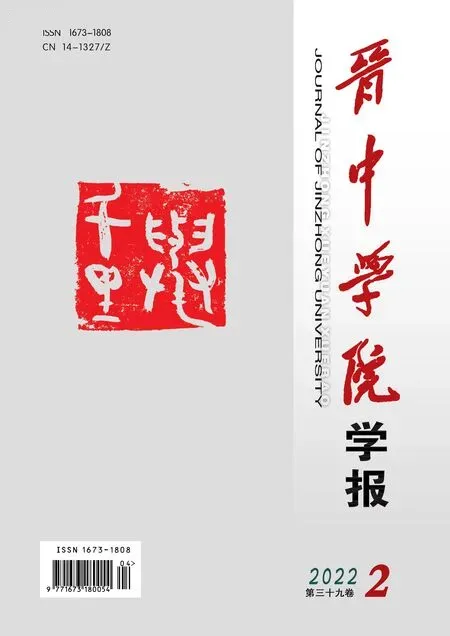清代五台山境域的寺院修缮与地方资助
王惠君,王 涛
(1.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山西 忻州 034000;2.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天津 300382)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菩萨又名曼殊室利,曼殊与满洲发音相近,乾隆帝所谓“曼殊师利寿无量,宝号贞符我国家”[1]185,意在明示满洲政权与文殊菩萨某种意义上的关联,五台山佛教成为清政府抚绥蒙藏、加强统一的重要工具。清代是五台山佛教的繁盛时期,尤其在康熙至嘉庆年间清帝十余次登上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意在构建满汉蒙藏多元一体的国家形态。[2]本文主要结合馆藏清代档案、石刻碑文和地方志书等文献资料,对清代五台山境内寺院的修缮与地方社会的资助作扼要考察和梳理。
一、清代五台山寺院概述
五台山由五座台顶组成。台顶内的区域称为“台内”或者“台怀”,外部地区则为“台外”,台内与台外共同构成五台山脉所覆盖的广大区域。由此推之,寺院大致分为台内寺院与台外寺院两大类。[3]60
台内寺院主要指以台怀镇为中心形成的五台山核心寺院群,包括显通寺、塔院寺与菩萨顶等闻名中外的寺院。五台山地处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的接壤位置,因此呈现出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特点,台内寺院分为汉传佛教寺院和藏传佛教寺院两大系统,即青庙与黄庙体系。在清代,显通寺为青庙首寺,寺内设有专门的青庙管理机构——僧纲司(亦称都纲司)。菩萨顶为黄庙首寺,札萨克喇嘛统领全山大多数黄庙僧众,章嘉呼图克图则管辖镇海寺等6座黄庙。[4]150,158
台外寺院广泛分布于五台、繁峙、崞县和代州等州县区域,由当地设立的僧正司或者僧会司管辖,和台内寺院分属不同的僧官系统,但是又常常与台内寺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成为后者的下院。比较知名的台外寺院中,佛光寺和南禅寺至今保存着唐代的木质结构,台麓寺则是清帝朝山时的主要行宫。[5]106,118,126
明清两代,五台山作为距离京师最近的佛教名山,深受皇室的支持和推崇。显通寺、塔院寺和菩萨顶等各大寺院都不同程度得到行政系统的资助,并展开了一系列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修缮活动。其中,显通寺分别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四十六年(1707)和乾隆二十八年(1763)得到皇室敕赐帑金进行重修。菩萨顶作为清代的皇家道场,在阿王老藏、老藏丹贝和老藏丹巴师徒的主持下也进行了多次修缮,并与清廷保持着良好的政教互动关系。[6]43总体来看,大型寺院在皇室和官府支持下的修缮活动,亦是皇权在五台山内的形象展现,充分表明世俗权力积极介入五台山寺院事务的倾向。
对于为数众多的中小寺院而言,经年的风吹日晒,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地维护和修整。这些寺院缺乏行政系统的加持和赞助,主要依靠地方民众的资助和捐施。历史上重修是中小寺院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由于受技术和财力的限制,通常需要各个方面的协调配合才能完成。
二、寺院修缮资金的筹集
五台山内诸座寺院常年善男信女络绎不绝、香火不断。除了普通信众捐施资助外,地方官府和基层民众也积极支持和资助五台山寺院的修缮活动。概括起来,资金筹集大致有以下几个渠道:
一是地方存公耗羡。耗羡通常指正额钱粮之外的一种附加税,在雍正年间被正式纳入地方财政收入之中。最早动用存公耗羡修缮寺院的记录,见于乾隆十年(1745)四月时任山西巡抚阿里衮的一份奏折。阿里衮奏报,五台山五座台顶,除中台尚属整齐无须修补外,其余多已朽烂欹斜,康熙帝驻跸的行宫亦须修整。阿里衮委派内务府员外郎卓尔代查勘后,预估4所行宫和4座台顶的修缮总共耗银12 635.9两,乾隆帝朱批:“正项不可,可于火耗存公内筹之”,工程自五月十五日动工,至九月初七日完工,耗时近4个月,“修理东台、西台、南台、北台四处台顶以及清凉寺、台麓寺、罗喉寺、白云寺内行宫四所俱已修理完整”,共计耗费11 475.9两白银,剩余部分银两,阿里衮令人添置所需帐幔、毡帘以及佛前供器等。[7]乾隆十五年(1750),阿里衮奏报,修缮菩萨顶用银5 909两,殊像寺用银1 983两,粘补余处用银309两,所有支出均从乾隆十二年(1747)耗羡银内拨付。[8]乾隆十八年(1753),署理山西巡抚胡宝瑔上奏,修缮五台山沿路桥梁、道路和营尖等项共开支1.3万余两白银,除去乾隆帝特别敕赐的1万两白银支用外,其余3千余两开销则于“乾隆六年存贮耗羡项下支销”。[9]
二为官员养廉银。雍正十一年(1733),时任山西巡抚石麟扣发晋省官员养廉银9千两,“以补民之欠项”。乾隆十年(1745),阿里衮奏称,由于通往五台山的山路狭窄,需要将其间顽石凿平并拓宽至六尺余方,估计工程耗银3 750余两,继而申请拨发养廉银以维修道路,乾隆帝同意此项请求。[10]嘉庆六年(1801),五台山暴发山洪。洪灾过后,山西巡抚伯麟委派平定州知州朱宏前往勘估损坏情形。次年四月,伯麟核实上奏,五台山内台怀、台麓和白云寺3座行宫,加上宽滩子、金刚库、涌泉寺三处尖营,共需修理费9万两。伯麟与藩司张师诚、臬司米绍曾商议后,“将此项工费银九万两零,由巡抚两司四道及经管税务之太原府、潞安府并平阳府养廉内分年摊捐。”[11]
三是五台山生息银。乾隆二十一年(1756),山西巡抚明德动议将司库所存闲置白银共计1.4万余两交予商户运营,每年大致获取利息1 700余两。[12]至此,山西地方实质上设置了五台山寺院修缮的专项基金,用来支付每年的各项基本开销。嘉庆二年(1797),山西巡抚蒋兆奎奏报,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之后,五台山内遭受雨水天气,山水涨发,十余处庙宇多有损坏。经雁平道张师诚复勘,藩司司马亲往确估无浮,最终核实需要维修银1.7万余两。当时生息银经过40余年的稳定运营,抛除日常支出外,已经积累到6万余两,因此,蒋兆奎建议“应请即于此项内如数动支,毋庸另筹帑项”[13]。嘉庆七年(1802)四月,山西巡抚伯麟奏称,普乐院、菩萨顶和显通寺等17处寺院,殿宇房间坍塌,地基下陷,墙垣岸坝多被冲坏,均急需修理,合计共需3.2万余两白银,实为不小的数目。当年生息银仍有4.7万余两的结余,在此情况下,伯麟亦建议“请即于此项内如数动支,毋庸另筹帑项”,嘉庆帝随即“依议妥办”。[14]嘉庆九年(1804)三月,山西巡抚伯麟为迎接来年嘉庆帝的巡山活动,与张师诚亲赴五台山,查勘山内各行宫、尖营以及寺院的损毁情况,其中白云寺行宫损毁严重,寝宫后层及内侍膳房、东配殿、东朝房、牌楼、照壁均已全部坍塌。涌泉寺尖营与金刚库尖营的塌陷亦十分严重。[15]同年九月,伯麟离职,张师诚护理山西巡抚,派遣雁平道赵文楷核实勘察五台山工程,共需1.6万余两白银,张奏报将此项开支从生息银中支付,嘉庆帝同样“依议速办”。[16]经过此次修缮后,生息银所剩无几。
四为商人的捐输。清代山西商人中最具经济实力的当属河东盐商。乾隆年间,由河东盐商运销的河东盐引达60万道之多,合1.4亿多斤,销往晋、陕、豫三省近120个州县。[17]乾隆二十五年(1760),山西巡抚鄂弼奏称,负责管理河东盐务的萨哈岱禀报“河东新旧商人刘公朴、范天锡等恭闻明春皇上恭奉皇太后銮舆临幸五台山,商众欣逢盛典,感激殊恩,敬输银三万两,以充经费”[18]。乾隆帝批示量力建造,剩余银两仍然归还商人。工程完结后,合计修缮30余处庙宇,共耗费白银近2.6万两,剩余4千余两。
五是信徒捐施。除了上述资金来源外,大多数寺院的日常修缮更多依赖信徒的捐施,这是寺院更稳定和大宗的收入来源。古计沟村重修碧霞寺,住持广益“敦请约中绅庶,商议重修庙宇之事,约中人无不乐从。遂夅纠首某某,与住持仝心募化,化得布施若干。鸠工庀材,自夏徂秋,功方告竣”。[19]700乾隆三十三年(1768),佛光寺重修东殿,“五台县正堂加三级王家正捐银五十两,北楼路窦村镇营城守厅加一级董锦捐银二十两”[20]736。嘉庆十四年(1809),石咀乡古计沟观音庙重修,得到各商号的赞助,其中,“增泰号助钱三百文,怀远号助钱三百文,五成当助钱三百文,东盛号助钱三百文”[21]698。实际上,信众群体包含广泛,有行政官员,有商贾巨富,也有乡间望族,更有人数众多的地方平民。
三、寺院修缮与资金使用
皇室的资助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其使用亦比较灵活。通常情况下,清帝更愿意根据自身喜好将资金赐给相关寺院和僧人。清代菩萨顶成为皇家道场,每次清帝巡游五台山,菩萨顶为拈香朝拜的必经之处,其显赫地位可见一斑,因此,清帝每次对菩萨顶僧众的敕赐也最为丰厚。康熙帝第一次朝台射杀一虎,射虎之地被命名为射虎川,康熙回京后立即拨发3 000两帑金,在当地新建了台麓寺,其中寓意不言自明。乾隆帝则对殊像寺情有独钟,早在乾隆十一年(1746)就敕赐1 000两赏金修缮,还特地下令仿照殊像寺的建筑风格和内部格局,在承德避暑山庄新建另一座“殊像寺”,成为承德外八庙之一。三世章嘉活佛自幼与乾隆朝夕相处,深受乾隆帝信任,因而得到大量敕赐赏金,在山内买地置产,扩充寺院规模。总之,皇室资助具有强烈的帝王个人色彩,仅能惠及少数寺院,由于敕赐赏金的周期并不固定,亦未被纳入财政资金的使用范畴,因此缺乏官方必要的监督,亦缺乏连续和稳定性。
雍正朝耗羡归公改革使得五台山寺院修缮得到了财政系统的正规支持。明清两朝,耗羡事实上包括了本色粮米征收中的雀耗、鼠耗以及折色银两中的火耗。由于清代主要征收折色银,所以耗羡收入中火耗占据大头。[22]到康熙末年,耗羡已经成为地方官员搜刮民脂民膏的主要收入来源。为杜绝官员私征滥收,整顿财政秩序,雍正帝展开耗羡归公的改革,将耗羡纳入正规财政收入当中。乾隆十年(1745)五顶寺院与行宫的修缮活动中,阿里衮得到乾隆帝同意后,随即从山西藩库领取火耗银两,并派遣员外郎卓尔代、雁平道黄文晖、归绥道通安布等赴五台山亲自监督办理。由于资金有限,五台山其他寺院并不在阿里衮的修理范围之内,“以至糜费帑金,应听各寺僧人自行粘补”[23]。修缮资金由道台级别的官员来进行监管使用,实际上赋予了后者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是山西地方首次动用存公耗羡来进行寺院的修缮活动。由此反映出耗羡归公后,地方财力进一步增强的趋势。此后存公耗羡被多次支用,以支持五台山庙宇的修整和建设。
官员养廉银则在一段时期内扮演着临时救火队员的角色。养廉银伴随着耗羡归公而生,目的是为了弥补官员微薄的薪俸,尽可能地杜绝官场腐败。实则官员养廉银在雍正、乾隆和嘉庆三朝都存在被克扣和挪用的情况,用于弥补资金短缺。养廉银挪作他用,一方面容易引起官员的反感,另一方面使用缺乏透明度,乾隆帝似乎意识到了上述问题。乾隆二十六年(1761),山西巡抚鄂弼的一份奏折,反映出当时朝廷拨发足够的帑金,用于修缮五台山寺院,不再强令官员公捐养廉银弥补资金缺口。[24]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地方财政一旦吃紧,上级经常要求官员摊捐养廉银弥补资金短缺。有学者认为,到乾隆朝中后期捐廉的名目及事项则越来越多,伴随人口激增、物价上涨,河工、赈济以及战事迭起,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在不断增大,地方倡捐养廉银以补财政缺口逐渐成为常态。[25]因此到嘉庆七年(1802),养廉银被再次挪用修缮五台山寺院。时任山西巡抚伯麟建议,扣发官员5年的养廉银来筹募资金,实质上是寅吃卯粮式透支未来的做法。
无论是皇室的资助,抑或是存公耗羡和官员养廉银,在五台山寺院修缮时都因时因事因人而异,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属于迎接皇帝朝山时的应急开支。在此情况下,山西官方亟须一笔稳定的收入来应对五台山寺院的常规性修缮工作。乾隆二十一年(1756),山西巡抚明德动议设置生息银的初衷,主要用于皇帝朝山活动前的寺院修整活动,实际上一直延续至晚清,成为一项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生息银设立后三年,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五台山首寺显通寺发生火灾,烧毁房屋70余间,僧众损失惨重,灾后的重建工作仅靠僧人财力难以为继。因此,时任山西巡抚塔永宁建议:“应请俟寺工兴举后,察看僧力果不能继,随时酌量动拨前款银两,以助工程之用。”[26]由此看出,生息银除了用于日常的修缮外,还被用于处理突发事件中所造成的相关损失。除此之外,山西官方亦注意扩充生息银的规模,乾隆二十五年(1760),鄂弼声称:“据禀上年各商捐输经费三万两,系通纲商人踊跃公捐,今余剩银两无从分给,请仍留司库公用。”[27]本应归还商人剩余银两,最终被留公使用,归入早前设立的生息银项目中,“一并交商营行运,以一分交息,每年所有息银同前案生息,均为台山岁修工程及省会公用之需”[27]。
由于生息银交予行商经营,因此本金和利息一直在稳定增长,成为五台山修缮资金最可靠的来源。嘉庆二年(1797),山西巡抚蒋兆奎奏报,“查有台山营运生息一款,前经奏明留为修理该山庙宇之用,节年积存息银六万五百二十一两零。”[12]由此可见,自乾隆二十一年(1756)设置以来,生息银除了支付五台山修缮工程花费,短短40余年,积累高达6万余两白银。工程兴修实为肥差,因此朝廷一直三令五申,要求山西巡抚和道台严格监管,“总期工坚料实,帑不虚糜,毋使胥吏工匠人等侵冒浮销,转不必欲速致有偷减草率诸弊方为妥善”[13]。嘉庆年间,工程逐步由山西巡抚分配给各个知县负责,其中贪腐现象时有发生。嘉庆十四年(1809),署理山西巡抚初彭龄奏报,太谷县知县苏佐清曾负责山内寺院修缮,领取过6千两工程银,苏后被革职,但是工程银未全数交还,剩余部分被个人私吞。[28]自道光即位直至清朝覆灭,清帝再未上山,官方设立的生息银还在缓慢积累。鸦片战争爆发后,战火由广州延烧至东南沿海一带,战争耗费巨大,清廷财政日渐支绌,只好从各地藩库抽调资金。道光二十二年(1842),山西巡抚乔用迁奏报,在晋省库贮捐监正项内动银1万两,又在五台山公用项内动银1.6万两。[29]五台山生息银被调拨充作军费使用,日常的寺院修缮活动无疑受到很大的影响。
相较而言,地方民众举力支持下的寺院修缮活动,资金使用情况更为透明。以地处繁峙县岩头乡安头村的圭峰寺为例,寺院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行了一次重修,由纠首侯光宗负责牵头,在本村及周边元山村、南磨村和官地村募化,对寺院进行了一番修葺。按照惯例,全部捐施人姓名和金钱数额都被刻石记载,另外还有香火田的位置和亩数,经理此次修缮活动者为热衷于村中事务的耆宿村民,这是乡村民众共同修缮村庙最典型的做法。[30]232道光六年(1826),地处繁峙城关镇笔峰村的永清寺重修,除了捐施人姓名和捐施数额外,工程花费明细亦开列于后,比如“石匠工钱十五千二百二十五文。木匠工钱六千七百六十文,泥匠工钱二十三千三百零五文,画匠工钱十六千五百文”等,记载十分详细。
四、结语
康熙、乾隆和嘉庆三朝是地方官府参与五台山寺院修缮的高峰时期,官方通过存公耗羡、养廉银、商人捐输和生息银等多种方式资助五台山寺院的日常维护和重修活动。另一方面,广泛外出募化和接受信众捐施依然是大多数寺院获得修缮资金最常见的方式,几乎贯穿王朝始终。概而言之,五台山寺院修缮资金的来源和使用,反映出清代五台山佛教受到中央和地方的支持和资助,亦体现出皇室、官府和地方之间的互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