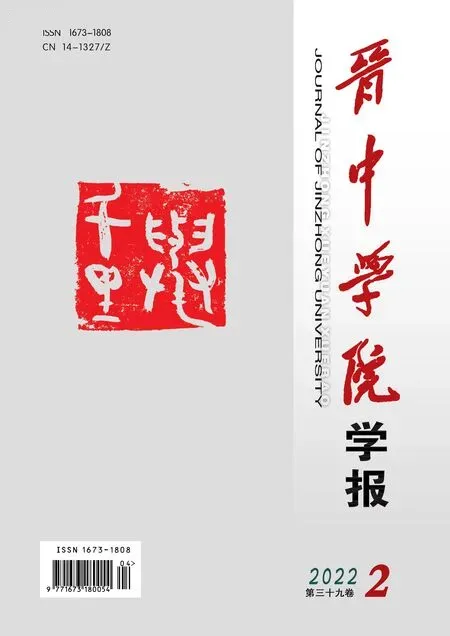论礼法融合的内在逻辑演化
周 斌,乔雅楠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从严密性的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法律缺乏西方思想文化中逻辑性极强的义理推演,或者说其逻辑性并不十分彰显。但如果从传统伦理学角度去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层本质,把逻辑推理视为一种可能性的研究方式,也可以发现蕴藏于其中的建构模式具有一定的逻辑特色。“仁”的本质在于由“仁者,人也”发微而形成的“爱人”之意,藉此便从人伦关系层面衍及至法律的亲伦精神,依此可诠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仁、礼、法”三者承转接续的逻辑进程。这一逻辑进程与中国古代社会“己、家、国”的伦理实体序列是并行不悖的,它们均以“仁”的诠释为论证基础,以“仁”的内外意蕴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法理本质的逻辑基点,两者错落有致而又相互交织,彼此融合而演绎出中国传统法律内在逻辑的伦理建构态势。
一、仁者爱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逻辑起点
“仁”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为仁由己”层面上强调人应以修身为本,二是在“仁者爱人”的层面上协调“己”与他人的相互关系。如果说《中庸》中以“人”来界定“仁”之“仁者,人也”的论断是中国传统法律中“仁——人”关系的逻辑支点,那么《论语》中以“爱人”作为“仁”的本质规定,则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内在的“仁、礼、法”这一内在逻辑起点。从实质上讲,“仁者,人也”与“仁者爱人”是融合的,“爱人”正是从“仁”与“人”的相互规定中推衍而来的,这是儒家仁学内在的逻辑使然。
在先秦史籍中,以“爱”释“仁”者多有论及。如《国语·晋语一》云:“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吕氏春秋·爱类》云:“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这些解释都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仁”的敬爱、关爱之意。如果在更为直接、更为明白晓畅的层面上表达这层涵义,必首推孔子在《论语·颜渊》中对“仁”的明确定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孔子关于“仁”的“爱人”之意,《大戴礼记·主言》中亦有引述:“仁者,莫大于爱人。”孟子对孔子的这一思想进一步明确为“仁者爱人。”(《孟子》)《淮南子·泰族训》也说:“所谓仁者,爱人也。”在儒家看来,“仁者爱人”的用意非常深刻,是协调人我关系的根本性道德要求。朱熹从仁与爱的相互规定性上对此作出深刻诠释,“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朱子语类》)孔子的仁爱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也影响深远,费尔巴哈把“仁爱”视为“健全的、纯朴的、正直的、诚实的道德,是渗透到血和肉中的人的道德,而不是幻想的、伪善的、道貌岸然的道德”[1]577-578。
不过,儒家虽然不遗余力地强调“仁者爱人”,但“爱人”的程度或者说力度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因人而异,有着极其鲜明的等差性,即所谓“爱有差等”。“爱有差等”是由中国古代宗法血缘的社会结构决定的,最切近的“爱”的对象当然是与“己”血缘关系最为亲密的人(如父母、兄弟等),之后以“能近取譬”的“为仁之方”,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依此类推。这种依据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而体现的“仁爱”精神,反映于中国传统法律中,就是司法原则上的荫亲制、缘坐制和亲属相容隐,这些制度体现了儒家伦理与中国传统法律的密切结合。
荫亲是指官员的亲属承受官职及犯罪减免等特权制度,受荫的亲属犯十恶以下之罪的享有减轻刑罚、赎刑或免刑之特权。例如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八议”制度。其中,“议亲”是最主要的官荫之律,谓皇帝袒免以上亲(1)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2]17此外,如《唐律疏议》第9条《请章》关于“皇后荫小功以上亲入议,皇太子妃荫大功以上亲……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第10条《减章》中关于“诸七品以上之官及官爵得请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已下,各从减一等之例”等内容都属于官荫之律。依此可见,中国传统法律按照等级制度与五服制下的亲疏远近,细致地规定了不同亲属的庇荫情形。这种因亲疏远近而形成的特权观念,其实质就是“爱有差等”原则的法律体现。
体现中国传统法律这一原则的还有缘坐制度。缘坐制是指中国古代因与犯罪者有血缘亲属关系而受株连坐罪的刑罚制度,凡犯谋反等重罪,亲属一般都问斩,或没官为奴、判处流刑,且要没收家产。如中国传统法律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2]321依据这一条款,对于“谋反及谋大逆者”的惩罚将牵连其诸多亲属,这种惩罚方式虽然使无罪之人难以幸免,但是对于每一个体来说,如果你对亲属怀有仁爱之心,那么你就不应犯上作乱。亲属关系的远近亲疏使相应的法律惩罚力度不一,从而彰显了儒家伦理“爱有差等”的精神。
此外,与缘坐制度相关联的还有亲属相容隐制度,也极为典型地反映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从法条来看,容隐制与缘坐制无疑是难以相容的,因为容隐允许亲属间相互隐瞒犯罪行为(2),而缘坐是因一人有罪而株连亲属。由于中国传统法律有“首告免缘坐”[2]432的规定,所以被株连者可以通过揭发犯罪之亲属而免于惩罚,可以说这是对容隐的限制。不过,从儒家伦理的角度来分析容隐制度,显然与缘坐制有着相同的意蕴,即亲属之间的关爱之情。在《论语·子路》篇,我们可以从孔子与叶公的对话中发现这一点。“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可见,“父子相隐”所体现的正是他们相互间的“仁爱”,这种“仁爱”是一种基于宗法血缘基础上的天然情感。朱熹对此解释说:“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论语集注》)亲情问题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是极其复杂和深刻的,从法律上看似乎有徇情枉法之嫌,并涉及伦理秩序与伦理正义的问题,从伦理上看与儒家历来提倡的先义后利原则有所相悖,如果将其置于现代西方伦理学的语境中则彰显了“善”与“正当”何者优先性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亲亲相隐”的激烈论证,更加表明这是一个聚讼不已的焦点问题。
总之,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儒家依据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而体现的“仁爱”精神可谓至深至切。荫亲制、缘坐制和容隐制所揭示的,正是中国传统法律在家族伦理形态中彰显的“人道亲亲”原则。
二、由仁及礼: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在逻辑演进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在逻辑演进中,“仁”体现的“爱有差等”是以礼的形式外化的,仁与礼的连接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在逻辑演进的基本径路。
“礼”本身有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是在中国历史文化中自然生成的,由于儒家关心社会秩序的构建,故最注重“礼”。同时,“礼”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基本概念,其涉及面之广、包容性之强,成为历代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在逻辑建构中,关于“礼”的理解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最基本的涵义应当包括与宗法等级制度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和道德规范。典章或礼节主要是从制度层面而言的,例如《周礼》中关于祭祀、朝觐、丧葬等国家大典以及用鼎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等具体规制等等。道德规范主要是就礼的伦理价值而言,指以“仁”为基本内涵的人伦道德体系。从历史渊源来看,礼起源于祭祀中的仪式和程序。礼即“禮”。《说文解字》:“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豐,行礼之器也。”《礼记·礼运》中也有一段描述礼的起源的话,“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大意是说,礼最初是从饮食开始的,古时候人们把黍米和掰开的肉放在石头上烧熟来吃,在地上挖坑蓄水用手捧着喝,抟土做鼓椎而用土做鼓来敲,仍然可以向鬼神表达敬意。[3]269这就表明,礼是远古社会中敬畏天地鬼神的产物,并由此形成极为繁冗复杂的礼仪制度。同时,这些礼仪制度在周公时期就与“以德配天”的理念相结合而被植入道德内蕴。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4]可以说,周公之礼是因道德而设,已经具有一定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不过,制度性的礼在伦理价值规定上呈现出道德规范的特质,则是源于孔子因“礼崩乐坏”而萌生的“以仁释礼”之故。
“以仁释礼”就是以“仁”的观念摄入礼制之中,使礼制蕴含“仁”的精神实质。“仁者爱人”的理念植根于远古社会的宗法血缘亲情,而“礼”以祭祖敬先的形式所反映的思想是“慎终追远”,因而包含着与“仁”观念相等同的伦理亲情。故《礼记·丧服四制》中说:“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丧有四制,变而从宜,取之四时也。有恩,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知,人道具矣。”(《礼记》)这段话以丧服四制为例,对礼本于人情而凸显的伦理道德做了形象的描述。不过,《礼记》最初为西汉的戴圣所纂辑,如果要追溯“以仁释礼”的发端还需回到《论语》的文本之中。
孔子以其深邃悠远的思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礼乐崩坏”的形势下从“仁”的观念入手,对“礼”做出本源性、本质性的诠释。在孔子看来,礼之本在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这就标示了仁之于礼的根本性。仁和礼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仁是本质,礼是现象;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以仁为体,以礼为用。《论语》中常以“孝”为例对“仁本礼用”进行说明:“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孝”是礼的基本要求,但是仅“有养”还不符合孔子之意,只有以“敬”或辅之以愉悦之色才能体现孝子的真情,这种真情的根基就是“仁”。孔子对宰我的“不仁”之论,也是对仁本礼用的鲜明诠释。三年之丧是仁之于礼的规定,《礼记》云:“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故曰‘无易之道’也。”(《礼记》)这就表明,服丧三年是适应人情而制定的,藉此来表明亲属与外人、亲近与疏远、尊贵与低贱的界限,不可以增减,因此是不可改变的制度。在孔子心目中,宰我之所以认为“三年之丧,期已久矣”(《论语》),在于他缺乏遵循丧礼所必须的内在依据——“仁”。“仁”在此处是内蕴于心的伦理亲情,所谓“其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斩衰三年,以恩制者也”(《礼记》)正是此意。为父服斩衰三年之丧,就是根据亲情原则制定的“无易之道”。随着汉唐时期礼法融合的演进,“仁本礼用”思想深植于中国传统法律的义理之中。中国传统法律对违反丧服制度的犯罪予以惩罚,就体现出对亲情伦理的维护。“诸闻父母若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自作、遣人等,徒三年;杂戏,徒一年;即遇乐而听及参预吉席者,各杖一百。父母之恩,昊天莫报,荼毒之极,岂若闻丧。”[2]204“父母之恩,昊天莫报”,父母之恩大于天而无以为报,所以人生之最大灾难莫过于闻其丧亡。如果丧制未终(3),就脱去丧服穿吉庆之服,或者忘却哀痛欣赏音乐、玩各种游戏,或者是遇到别人奏乐就去听奏的、遇到庆礼酒宴参与其中,这些不孝行为显然都严重违背了礼的要求,而其深层原因即是对父母丧失了仁爱之心。总之,在儒家伦理体系中,仁礼之间存在着表里、体用的关系,不仁必不能守礼,只有立足于仁,礼才具有本质性的规定,才得以彰显雄厚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另一方面,礼作为形式、现象这一外部性规定,成为“仁”之内容、本质等内在性规定的外化形态,也就是说,“仁”只有在礼的表象中才能将隐性意蕴呈现出来。孔子所谓“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就是这层意思。
事实上,仁与礼之间的相互规定性,无论仁作为礼之本源,还是礼作为仁之表征,两者都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之中。孔子“以仁释礼”,使作为协调宗法等级关系的礼具有了更深刻的意蕴。一方面,“仁”所彰显的“爱有差等”的制度性依据就是“礼”,从礼的历史沿革来看,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论语》)就是针对以等级制著称的周礼而言的。另一方面,礼的等级制以“仁”为精神内核,虽然礼仪制度的等级性并非全然由仁来规定,但仁之“爱有差等”的特质使礼内在的等级理念更加庄重、浓厚。因此,孔子“克己复礼”之诉求是由道德意义而外化为制度意义的礼,是在“等差之爱”的道德原则基础上确立的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制度。这也表明,所谓“孔子之礼仅是道德之礼”“孔孟忽视礼的制度属性”等认识无疑是偏颇的,孔子一生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以修身为本的“为己”之学,更是学以致用的治国安民之道。正是孔子以“仁”来规定“礼”,使“等差之爱”融入等级制度中,与孔子一脉相承的孟子才有“仁政”之论,荀子之礼才能实现与法的历史连接,并成为汉唐时期礼法融合的理论渊源。从政治伦理的层面来看,这一历史性过程的理论逻辑发微于孔子的“正名”之说。
孔子“正名”的目的不是探求认识论与逻辑学上的“名”与“实”的关系问题,而是通过辩正名份来维护“礼”的秩序。春秋时代的“礼崩”是孔子正名说的社会历史背景,具体表现为“八佾舞于庭”(《论语》)的僭越行为,孔子为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因而试图以“正名”来扭转这一危局。《论语》有两处记载孔子的“正名”思想。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
这一段径直指出“正名”的必要性,另有一处虽未直言,但显然规定了“正名”的具体内容。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
为了避免陷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失序状态,孔子认为君臣父子要在品行、责任、地位等方面符合各自的名份,唯有如此才能构建阶级统治所必需的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和宗族亲亲关系。(4)如果说“仁”是孔子之礼的内在依据,那么“正名”则是依于“仁”而实现礼的必然路径。因此,“礼”之所以必须“履”,是因为它符合“仁”,“名”之所以必须“正”,是因为这样才能达到“仁”。[5]176-186
孔子关于仁与礼的关系构建,只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在逻辑演进的拓展阶段,然而这一阶段是必不可少的,缺乏仁与礼的相互规定性,就无法从基础性层面上展示与中国传统法律密切结合的儒家伦理正义思想,也无从建构中国传统法律庞大而细密的伦理秩序。同时,孔子关于礼的论述,虽然在深层意义上也涉及法的理念,诸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等都表明孔子之礼包含了法的内蕴,但是在礼与法的链接上,孔子之礼与中国传统法律的贯通显然还缺乏明显的历史传承,这一任务只能靠儒学后人来完成。至战国中后期,孔子所创的儒家学派不断分化,史称“儒分为八”(《韩非子》)。其中思孟学派成为孔学正宗,而荀子则独辟蹊径,沿着儒法兼容的路径建构出以“隆礼重法”(《荀子》)为旨归的学说,从而导引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义理模式。
三、礼法合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在逻辑整合
礼与法的结合,在思想渊源上与“仁”存在着理论逻辑的继承性,这是因为道德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本土资源,是礼治功能得以发挥的潜在因素,并以礼的形式加以实现。“仁、礼、法”的衔接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法律的内在逻辑形态,即在于“仁者爱人”所彰显的亲疏远近与礼所设定的等级序列相媾和,并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和保障,深层本质在于:理顺亲伦之序,方能循礼行事,行事必依于礼,而礼所不容必为法之所禁。从中国古代制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分析,礼法结合的可能性不仅在于治国功能上的宏观契合,也需要在理论微观层面上通过荀子之“分”这一概念所具有的礼法关联性加以引证。
关于礼与法在治国功能上的相似性,学界的探究极为繁密并已呈推陈出新之势,如从中国古代制度层面所阐发的礼与宪法的关系模式,从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中所得出的礼与自然法之间的密切关联等等。尽管这些探讨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甚至还存在着激烈的论争,但表明礼法关系研究已进入纵深阶段。不过,要从根本上追溯礼法契合汇融的精神,并依此体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在逻辑本源,必须将研究视角首先定位于先秦的历史坐标之中。
礼作为治国的基本纲领,或者说礼被赋予法的浓郁色彩,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十分鲜明的特征。对此,历代史籍记载颇详。《左传》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又说:“礼,王之大经也”,《国语》中说:“礼,国之纪也”。诸如此论,都意在表明礼在治国理政中的根本作用,并在本质上强调了礼在维护社会秩序时可与法的功能相提并论。法家学派的管子将“礼”作为国家“四维”之首,他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由此可见,礼作为治国纲领的极端重要性。依照传统观点,礼所体现的治国之道即是“礼治”,从操作层面来看应属于德治范畴。不过,将礼归于德治体系并不意味着礼单纯性地强调主观自律性,由于礼所显现的制度性形态,势必使其具有某种外在的法治意蕴。实际上,孔子损益周公之礼并力求“克己复礼”的意图就十分明确地显示了礼的两重性涵义。孔子主张“齐之以礼”“为国以礼”(《论语》),就是把礼视为伦理政治的基本手段。在他看来,人们的一切言行举止都应符合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而且孔子直言不讳地指出礼的治国要义在于治民。他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又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礼所以能起治民之效,是因为礼是判断人们言行是否合理、妥善的基本标准,所谓“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礼记》)司马迁以类比的方式进一步强调礼的规范作用,“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圆之至也”,并将“礼”视为“人道之极”(《史记》)。
显而易见,礼之于治国治民的规范效应与法的专有功能是亦步亦趋的,两者基于共同价值目标而呈现出义理层面的相容性特征。不过,礼与法的关系探究如果仅仅止于这一宏观性的分析,还无法深入说明礼与法相容的原初性因素。那么,这种原初性因素是什么呢?一个基本的论证途径就是从礼之于治国治民的规范效应的作用机制入手,使礼与法的价值归依的同向性得以展示。实际上,所谓原初性因素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血缘特征,继而孔子通过以“仁”释“礼”,从而使人伦等差之爱繁衍为具有制度性特色的“正名”之说,其实质即是以礼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作用机制。孟子也肯定礼的宗法等级性,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这就将礼所确立的尊卑上下原则与其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衔接起来。不过,无论是孔子的“正名”之说,还是孟子对礼的进一步诠释,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彰显了礼的制度性特征,但孔孟所处历史时代条件的局限性,使其无法构建礼与法之间实质性的理论链接。如果要在由仁及礼的逻辑演进基础上,依据礼的宗法等级特征这一原初性因素与法形成内在关联,继续回旋于孔孟的理论思维中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建构“仁、礼、法”的中国传统法律的内在逻辑进程,必须着眼于当时的社会历史变迁,对孔孟之礼加以改造,赋予“法”的特色。这一任务是由荀子来完成的。
荀子生活的年代,是战国纷争行将结束、封建大一统的局面即将形成的交替之际。这一社会历史变迁决定了孔孟之礼的价值滞后性,同时也为荀子礼学的形成创设了时代条件。与孔孟之礼的根本区别在于,荀子之礼的本质是政治制度,礼的政治功用极为显著,而其道德意蕴呈现式微倾向,这是荀子关于礼法关系建构的可能性前提。如果从理论论证的深层链接来分析,荀子则是以“分”这一概念作为礼与法的契合点来寻求礼法之间的属性关联,这一点首先表现在荀子对礼的起源的说明。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
按照荀子的推理,礼因人的欲望纷争而设,而礼的具体运作是规定每个人的名分,使其“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淮南子》)。此处,“故制礼义以分之”是这段话的核心,荀子通过引入“分”这一概念来揭示礼的重要性质和功能。所谓“分”,即名分,是中国古代社会用以维持等级制度的方法和观念,具体是指各种和人或物的名称所相应的职分、地位、等级、权利、身份、亲疏关系、所属关系等等。在《非相》篇中,荀子将“分”的观念与礼的功用进一步强化,指出“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将礼之于名分的规定性推向了极致。不过,“分”或“名分”的概念并非荀子所创,与“礼”——“分”关系相观照的是法家理论中的“法”——“分”关系。先于荀子数百年之久的管子就曾指出“律者,定分止争也。”(《管子》)
法家另一代表人物商鞅则以鲜明的寓意诠释了法所具有的“定分止争”的作用。“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名分定,则大轴贞信,民皆愿悫,而各自治也。”(《商君书》)这就表明,治世之道的根本在于名分是否划定,确定了每个人的名分等级,就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商君书》)如果说荀子之礼是规定名分的工具,那么荀子之前的法家早已赋予法之于名分的规定性了。故可说,荀子“以礼定分”是基于儒法双向源流,一是荀子之礼渊源于孔孟之礼,沿袭了孔子的“正名”理论,对儒家的礼治思想做了系统的发挥,荀子之“分”的基本要义仍是通过对尊卑贵贱的界定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二是依据法家关于“法”——“分”之规定,自创了“礼”——“分”的关系定式。这是荀子基于儒学根本大义的同时,吸纳了前期法家的精神实质,从而因循儒法两条理路并加以糅合,通过“分”这一中枢性的概念使礼与法之间形成属性融合。这一属性融合的内在进路,是对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的历史归综。(5)同时,以“分”作为礼与法相链接的中枢概念,也体现了礼之于法的先在性和统驭性的特征。荀子对此作了重要的说明。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所谓“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即是将道德视为礼的终极旨归,而“《礼》者,法之大分”表明了礼本法末的关系特质,礼是法的根本,是法的灵魂,法律规范源于礼义道德观念,因而非礼则无法。显然,荀子“为法以礼”“隆礼重法”的语意与孔子的“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的逻辑进路是一脉相承的,都体现了礼之于法的先在性和统驭性。如此之法即体现了“伦理法”的特征,荀子之所以在《修身》篇中直言“礼法”,其用意也正在于此。“礼法”概念的设定体现了荀子对国家法律制度的重新确立,是对法家“壹法”“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等纯粹法观念的修正,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宗法伦常这一原初性因素的必然逻辑指向。
于此,荀子以“分”这一中枢概念将礼与法的本质相贯通,以儒法结合的政治文化模式为后世封建正统学术的发展设计了基本的蓝图,清代谭嗣同所言“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6]337,可谓是对荀子思想的历史价值的准确定位。荀子将礼视为“法之大分”,成为后世立法的理论先导。后世历代诸子关于礼法的言论,皆是对荀子思想的诠释与疏解。叔孙通关于礼仪和礼器制度的立法形式、陆贾“中和”之治、贾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言,以及董仲舒之“春秋决狱”等等,都是在荀子礼法关系论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这些观念融于制律进程中,依次表现为《魏律》首次引入“八议”制度,《晋律》开创“准五服以制罪”先河,《北魏律》创“存留养亲”之法,《北齐律》制定“重罪十条”,直至“一准乎礼”的《唐律疏议》,皆是荀子礼法思想的影响所致。之后宋元明清的法律制度,虽因时而有变,但在总体上还是“一准于唐”。
中国传统法律作为礼法融合的完善形态,从表层来看是律文与礼的密切结合,但从其内在的逻辑演进来看,其文化确证性在于荀子礼法思想的建构,此前的仁礼关系说是这一建构的中间环节,而孔子关于“仁”与“爱人”的语义衔接则为仁礼关系说预设了理论逻辑基点。“仁”与“礼”作为儒家伦理规范的基本要素,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在逻辑演进中显示了法的伦理精神。正如明代学者方孝孺所言,“古之人既行仁义之政矣,以为未足以天下之变,于是推仁义而寓之于法,使吾之法行而仁义亦阴行其中。”[7]“推仁义而寓之于法”,即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内在逻辑的理路定式。反之,儒家伦理化的法典势必对社会道德形成极大的效力,从而使“法行而仁义亦阴行其中”。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在逻辑演进中,礼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将仁的精神移入法中,而荀子则以“分”这一中枢概念确立了礼与法之间的属性相容。
注释
(1)袒免者,据礼有五:高祖兄弟、曾祖从父兄弟、祖再从兄弟、父三从兄弟、身之四从兄弟。
(2)亦有学者认为,“隐”字在此的意思是沉默,即亲属作证的沉默权利。参见林桂榛,《关于“亲亲相隐”问题的若干辨正》,《哲学动态》2008年第4期。
(3)关于服父母斩衰丧的时间,《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其时间之阶段进程说:“王公以下三月而葬,葬而虞,三虞而卒哭。十三月小详,二十五月大详,二十七月禫祭。”禫:除服之祭名。《释名》:“禫,孝子之意澹然,哀思益衰也。”故禫制定二十七月。
(4)“正名”是孔子的政治学说,也是他的伦理思想,后世的封建道德又称为“名教”,其源盖于此。
(5)荀子所讲的“法”,不同于法家之“法”,而是包括礼法、规范制度和刑律在内的总称。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认为法就是以刑为主的律令,如《韩非子·定法》:“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而荀子之法与此不同,他认为法是以礼为本源的,礼的精神是法的运行依据,因而荀子往往使用“礼法”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