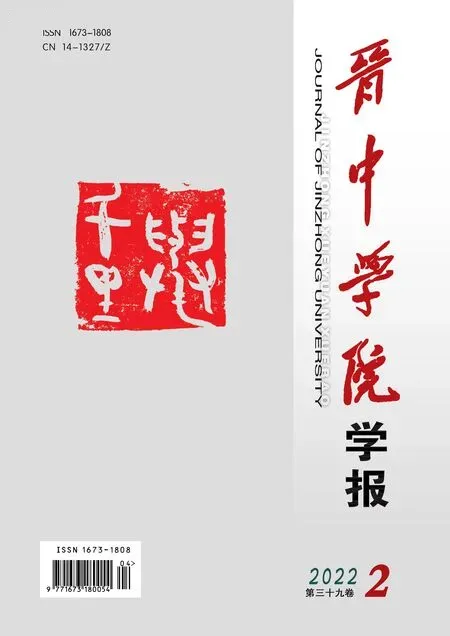为什么小明不能当村长?
——赵树理《李有才板话》细读
管冠生
(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截至2022年1月,知网“篇名”检索“李有才板话”,可得研究文献38篇,但无一提出“为什么小明不能当村长”这个问题,当然也就不能对此进行思考,因此本文略去文献综述的工作而直接进入自己的论述,并在此过程中与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对话交流。
一、如何看待阎恒元们的“坏”?
有论者把阎恒元视为“敌对势力”[1],这是不对的。《李有才板话》于1943年10月完成,时值抗战,只要阎恒元不站到日伪一方面去,他的存在就是合法的,焉能看作“敌对势力”?就小说描写来看,“一只虎”阎喜富的所作所为似乎比阎恒元更恶劣——阎恒元的劣迹包括押地、不实行减租、捆人、打人、罚钱、吃烙饼等[2]51-52,而阎喜富抗战前“当过兵,卖过土/又偷牲口又放赌,/当牙行,卖寡妇……/什么事情都敢做”,抗战后当了村长“说捆就捆,说打就打,说教谁倾家败产就没法治”[2]22-23——但“县政府特别宽大”[2]29,只要阎喜富赔偿大众损失便罢,对阎恒元更无彻底铲除的意思,只叫他“退租退款又退地”[2]55,随之罢免了他的委员职务。
《李有才板话》没有把阎恒元写成敌对势力,只是说他“坏”,而“坏”的人物并不止他一个。《李有才板话》为阎恒元、阎家祥、张得贵、阎喜富、刘广聚、陈小元等六人编了快板,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坏”,例如陈小元的歌上来就是“陈小元,坏得快”[2]37。不过,这六人当中,阎恒元堪称总“坏”或者说是“坏”的源点,其他五人是分“坏”或者说是从源点扯出去的五条线:阎家祥是阎恒元的儿子自不必说,张得贵“跟着恒元舌头转”[2]21,阎喜富“有恒元那老不死的给他撑腰”[2]22-23,刘广聚“拜认恒元干老头”[2]23,陈小元“穿衣吃饭跟人家恒元们学样”[2]53。简言之,被阎恒元“团弄”住了就得“坏”。
“陈小元,坏得快,/当了主任耍气派,/改了穿,换了戴,……锄个地,也派差,/逼着邻居当奴才”,陈小元的“坏”表现在有了权之后只为自己考虑,别人成了他使唤的工具,原先平等、互助的朋友关系变成了支配/被支配的主奴关系。本来,陈小元“因祸得福”成了武委会主任大出阎恒元意料,弄得阎恒元很后悔,要把他“团弄”住,刘广聚说:“那家伙有那么一股拗劲,恐怕团弄不住吧!”阎恒元说:“咱们都捧他的场,叫他多占些小便宜,‘习惯成自然’,不上几个月工夫,老槐树底的日子他就过不惯了。”[2]36果然,“广聚有制服,家祥有制服,住在一个庙里觉着有点比配不上”(广聚用公款为他做了新制服),“广聚有水笔,家祥有水笔,小元没有,觉着小口袋上空空的”(阎家祥送他一支),“广聚不割柴,家祥不割柴,小元穿着制服来割了一回柴,觉着不好意思”[2]36,扛着锄头往地里走,被家祥一问,“脸红了,觉着不像个主任身份”[2]37。由此观之,陈小元之所以“坏”了起来,固然是上了阎恒元的套,但其自身本就有“坏”的基因与“学样”的心理,随着掌权与身份的变化,把高高在上、贪图享受、好逸恶劳视为了正常现象。
陈小元变“坏”证明阎恒元那一套真管用。遇到事情,阎恒元总有法子,并且法子总是有用。仔细看看,他的法子其实是一个套路。
丈地时,阎家祥认为村干部里“只有马凤鸣不好对付,他最精明,又是个外来户,跟咱都不一心,遇事又敢说话”。阎恒元却说:“马凤鸣好对付:他们做过生意的人最爱占便宜,叫他占上些便宜他就不说什么了。”[2]30在阎恒元看来,“最难对付的是每二十户选的那一个代表”,然而也有招来对付与瓦解:“用点小艺道买一买小户,小户也就不说话了——比方你看他一块有三亩,你就说:‘小户人家,用不着细盘量了,算成二亩吧!’这样一来,他有点小虚数,也怕多量出来,因此也就不想再去量别人的!”[2]30-31事实表明,马凤鸣果然被“团弄”住了,连老秦都说:“我看人家丈得也公道,要宽都宽,像我那地明明是三亩,只算了二亩!”[2]34阎恒元的套路或自己说的“艺道”就是用小惠小利喂,这一招可谓无往而不胜(除了老杨没中招之外)。要破这一招实在困难,因为占便宜、自私自利本是“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阎恒元最终未被完全铲除是有象征意味的。亦因此,与其认为陈小元被腐化“说明封建思想对新兴农民依然具有不可小看的诱惑性和腐蚀性”[3]56,倒不如说它表明了人性的复杂与幽暗。
二、村长人选看什么?
阎恒元的法子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抓住了人性自私自利、贪图享受的一面。这一面是如此根深蒂固,连被派去锄地的小顺都说:“成天盼望主任给咱们抵些事,谁知道主任一上了台,就跟人家混得很热,除了多派咱几回差,一点什么好处都没有!”[2]37话中流露着对陈小元的不满,但“抵些事”是什么意思呢?他想得到什么“好处”呢?这“好处”恐怕不是对公的,而是对己的。换言之,只要有机会,老槐树底不止陈小元,包括小顺都可能、都可以被阎恒元“团弄”住,被“坏”抓住。
或曰,“坏”抓不住李有才。李有才似乎是个完全进步的人物形象,有论者认为,他以集中了民间智慧与艺术才能的板话作为武器,“既深刻地教育了群众,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与影响甚至超过了老杨:“阎家山的贫苦农民在老杨到来之前已经在民间的人伦情感和集体意识主导下凝聚在一起,不待阶级话语和阶级斗争渗入之时便尝试着以群体之力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社会秩序和等级差别。因此,一开始农民对李有才的信任是超过了农救会主席老杨的,只有在斗争取得胜利之后农民才真正从心底里接纳了老杨”[4]。姑且不谈贫苦农民在老杨到来之前是否真正“凝聚”在了一起,这种看法忽略了更多细微而有趣的内容。
“打虎”选村长时,老槐树底可以推出小保、小明、陈小元三个人。按老陈的意见,叫小明参选,得票会更多,因为“小明见邻居们有点事,最能热心帮助”[2]35,或者说“小明叔交人很宽”(1)。当陈小元以武委会主任的身份得意归来,“小顺道:‘试试!看他老恒元还能独霸乾坤不能?’小明道:‘你的苗也给你锄出来了。老人家也没有饿了肚,这家送个干粮,那家送碗汤,就够她老人家吃了’”[2]36。比较来看,小顺有争夺权力的意思,而小明才真正是个不忘本、可以依赖的好人。但类似军师角色的李有才说:“我说个公道话吧:要是选小明老弟,保管票数最多,可是他老弟恐怕不能办:他这人太好,太直,跟人家阎恒元那伙人斗个什么事恐怕没有人家的心眼多。”[2]24
小元推举小保。但李有才说,小保也不宜当村长:“小保领过几年羊,在外边走的地方也不少,又能写能算,办倒没有什么办不了,只是他一家五六口子全靠他一个人吃饭,真也有点顾不上”[2]24。小明推举小元,理由是“在大场面上说个话还是小元有两下子”[2]24,这得到了李有才的认可(“依我说,小元可以办”)。
由此来看,老槐树底人考量村长人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能“在大场面上说个话”,这个素质和能力很重要,既可视为“心眼多”的表征,又可作为“能人”的标志——老杨说:“你不要说没有人,我看这老槐树底的能人也不少,只要大家抬举,到个大场面上,也能说他几句!”[2]47说话就是斗争,或者说,说话是“斗个什么事”的常见形式与重要方式;有话不敢说、不会说、说不到点子上,都会使公私利益受损。二是家里负担少或没负担(例如,“小元家里只有一个老娘”[2]34,比小保负担轻)。一比二更被看重。
让我们理一下:“为人很痛快”[2]35的老陈推举小明,小明推举小元,小元推举小保。小保是三个人中最能在大场面说话的人(“小保领过几年羊,在外边走的地方也不少”意思就是小保见过世面,能在大场面上说话),但因为家里负担重,退而求其次,小元作了村长候选人。掌握了权力的小元很快变“坏”了。斗倒阎恒元后,村长终于选了小保。问题便是:谁能保证小保不蹈小元的覆辙呢?毕竟,他比小元能说,且家里的困难比小元多。当然,最能说会道的是李有才,李有才能不能被“坏”抓住,难下定论。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当官首先看的不应该是心眼多不多,而是心眼正不正;不是人能不能,而是好不好。换言之,当官的根本素质不是“心眼”而是“心正”,根本要求不是“能人”而是“好人”(2)。所以,老陈骂小元“出来进去架两条胳膊”,“像个什么东西!”[2]51-37不像个东西、不是个东西的人不能推举他当官。——像小明那样“太好,太直”的人不能被推出竞选村长、当村长,这才是《李有才板话》与李有才本人留下的最值得思索的问题。
三、章工作员的问题出在哪里?
当然,不同的解释者会从文本中发现不同的问题。有论者认为,“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在农村地区有效开展党的工作。而当他把这一政治性的思考转化为文学形式时,选择了以两种语言的差异性来表征章工作员和老杨同志的不同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的书面语无疑代表了脱离地方实际、好高骛远的工作态度;而口语则代表了值得赞赏的实事求是的精神”[5]。通过细读,我们发现小说所写并不能如此简单概括。
“打虎”选举时,李有才先去送牛,再来开会,因为在其印象中,不论什么会,章工作员“开头总要讲几句‘重要性’啦,‘什么的意义及其价值’啦,光他讲讲这些我就回来了!”[2]25“重要性”“意义及其价值”就是“代表了脱离地方实际、好高骛远的工作态度”的书面语,但这次章工作员“跟从前说话不同了,也没有讲什么‘意义’与‘重要性’”,而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事办事,让大家对阎喜富提意见。章工作员革新了选举办法,“按正规的选法,应该先选村代表,然后由代表会里产生村长”,但这次事情紧急,便用三个碗代表三个候选人,“每人发一颗豆,愿意选谁,就把豆放到谁的碗里去”[2]27。结果小元只比刘广聚少两票,叫阎恒元“心里着实有点不安”[2]27。此外,章工作员并非偷懒耍滑之人,丈地要每二十户选一个代表,阎家祥不想选(觉得代表难对付),但阎恒元说“不妥!章工作员那小子腿勤,到丈地时候他要来了怎么办?”[2]30丈地时章工作员果然到了现场。
由此来看,若笼统说章工作员“脱离地方实际、好高骛远”,有些冤枉,也有些片面。那么,为什么阎家山在他手里由一个“问题村”变成了“模范村”呢?斗争胜利后,“因为村里这么大问题章工作员一点也不知道,还常说老恒元是开明士绅,大家批评了他一次。老杨同志指出他不会接近群众,一来了就跟恒元们打热闹,群众有了问题自然不敢说。其余的同志,也有说是‘思想意识’问题或‘思想方法’问题的,叫章同志作一番比较长期的反省”[2]52。章工作员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这应该从老杨那里对比发现。
老杨来组织农救会时,先把《会员手册》“大概讲了一些”——讲还是要讲的,但老杨是“大概讲”,不是像章工作员那样一讲一大晌——接着转入实际的组织工作,小保便说:“明天你就叫村公所召开个大会,你把道理先给大家宣传宣传,就叫大家报名参加,咱们就快快组织起来干!”[2]48这是从前章工作员的做法。老杨不同意这样做,因为“一来在那种大会上讲话,只能笼统讲,不能讲得很透彻;二来既然叫大家来报名,像与恒元有关系那些人想报上名给恒元打听消息,可该收呀不收?”他的办法是叫李有才编歌,把“入了农救会能怎样怎样”编个歌传出去,“凡是真正受压迫的人听了,一定有许多人愿意入会”[2]48。小说开始时说过,李有才的歌的传布范围只是老槐树底,所以听到歌的人就是那里的贫苦群众,“然后咱们出去几个人跟他们每个人背地谈谈”[2]48。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阎恒元那一派的人排斥出去:“介绍会员不叫他们知道,是怕那些坏家伙混进来。”[2]50
为什么开会讲道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只要阎恒元能参加,那么事情就很容易被阎恒元操控。为什么李有才的歌会发生作用?因为阎恒元听不到,也无从干预。等阎恒元知道农救会成立了,也派人找农救会个别会员背地谈谈,说阎恒元永远不离阎家山,等工作人员走了,“你还出得了老村长的手心吗?”[2]51有人就要退会。李有才又编了歌,这次不是用口传出去,而是贴满了全村,“连老恒元门上也贴了几张”[2]51,击退了谣言。阎恒元门上被贴上了李有才的歌,这是阎恒元在阎家山彻底失势的表征。
本文认为,章工作员的问题是满足于执行上级的文件或命令,对现实斗争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既无心认识又认识不足。开会做宣传没有错,也不能说无效,但更重要的是对阎家山的村政局面要有清醒而深刻的认知,而这是章工作员不愿下功夫做的工作。“打虎”选村长时,他让大家提意见,一时见无人开口,“在台上等急了,便催道:‘有没有?再限一分钟!’”[2]26一个等不及的干部怎么能做扎实、细致、深入的工作呢?丈地时,刘广聚和阎家祥大谈“飞归得亩”之类的数学问题,大家“都听不起劲来,只是觉得丈量得太慢”,章工作员却觉得“办法很细致”,说是“丈地的模范”,就往另一个村去了[2]31。大家觉得“太慢”误工而章工作员觉得“细致”模范,感受如此不同,表明章工作员不是“大家”中的一员——丈地人员除了以刘广聚为首的村干部,还有他指派的十几个“最穷、最爱打小算盘”、“像老槐树底老秦那些人”[2]30的所谓代表们,故此处的“大家”指的不是刘广聚等操控局面的既得利益者,而是老秦等穷户——忘记了或根本就没认识到斗争要依靠贫苦群众,真相的发现也必须依靠贫苦群众。老杨对章工作员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四、老杨是怎么炼成的?
县农会主席老杨来检查督促秋收工作,“叫区农会给他介绍一个比较进步的村”[2]39,为什么不选一个比较落后的村呢?落后村的问题摆在明处,老杨在实践工作中应该早就认识到了所谓“进步”“模范”等名号之下往往隐藏或掩盖了诸多问题。此一选择便显示了老杨之与众不同。
他的装扮——“头上箍着块白手巾,白小布衫深蓝裤,脚上穿着半旧的硬鞋至少也有二斤半重”[2]39——叫刘广聚以为是某个村的送信员。这可以与下面的事情相联系:“八一”检阅民兵,小说写道“阎家山的民兵服装最整齐,又是模范,主任又得了奖”[2]39。据此,阎家山再次成为“模范”、变“坏”的小元得了奖只是因为“服装最整齐”,而“服装最整齐”背后阎恒元鼓捣的不法事情无人清楚,也无人有心想弄清楚;正如章工作员只因“飞归得亩”而判定阎家山是“丈地的模范”,而区公所和县里亦不调查就采信了他的看法。可见,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相当的范围内较普遍地存在着(3),表面文章、字面工夫是多么容易地迷惑人!
看过介绍信,刘广聚才知道眼前站着的是县农会主席,便请老杨到自己家里吃饭,被拒绝了,“还要讲俗套,老杨同志道:‘这是制度,不能随便破坏!’”[2]40毫不讲情面。阎恒元不以为意,又使出老法子:“他要那么执拗,就把他派到个最穷的家——像老槐树底老秦家,两顿糠吃过来,你怕他不再找你想办法啦?”[2]40
老秦“以为衙门来的人一定得吃好的”[2]40,特意做了两三碗汤面条,毕恭毕敬双手捧给老杨。“他越客气,老杨同志越觉着不舒服,一边接一边道:‘我自己舀!唉,老人家!咱们吃一锅饭就对了,为什么还要另做饭?’”[2]41吃了第一碗,就自己走到大锅边,舀山药蛋南瓜。不但吃穿和老百姓一样,到场子里打谷子,“拿起什么家什来都会用”,博得大家赞誉“真是一张好木锨”[2]42,和陈小元锄地“觉着不像个主任身份”截然不同。阎恒元的“坏”在老杨身上彻底失效了;只有“老杨同志”才是阎恒元的真正克星。
那么,这样一个老杨是怎么炼成的呢?“广聚见他土眉土眼,说话却又那么不随和。”[2]40“土眉土眼”说明老杨原本就是农民出身,“随和”意味着“讲俗套”[2]40,会说客气话、人情话、场面话,“不随和”换一种表达就是“太直”。但老杨对村长刘广聚不随和,对老秦等穷户却“随和”:“不要这样称呼吧!哪里是什么‘先生’?我姓杨!是农救会的!你们叫我个‘杨同志’或者‘老杨’都好!”[2]41称呼很有讲究:张得贵叫阎恒元一口一个“老村长”,叫老杨“你老人家”,明显是讨好奉承;老槐树底人(包括叙事者)叫章工作员从来都是“章工作员”,纯粹把他当作一个浮在上面的官来对待;称呼老杨,要么直接称“你”(小顺道:“你就没有听见‘干梆戏’?……”[2]53),要么称“杨同志”(李有才对刘广聚说:“县农会杨同志找我回来谈话,叫你去开门啦!”[2]45),彼此平等而带着朋友般的感情(4)。老杨是个官,骨子里却自认是个农民,这是他跟其他官员根本不同的地方。他指出章工作员“不会接近群众”,那是因为后者已不认自己是群众。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老杨和小明是《李有才板话》中两个同样“太好,太直”的人。只是一个未被推出竞选村长、当村长,另一个则一步一步成为县农会主席。虽然对老杨的成长及从政经历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愿意相信,只有当“老杨同志”有制度化的保障且常态化地出现时,中国民众的人性心理以及政治文明才可能获得质的转变与提升。
注释
(1)这话出处是:组织农救会时,老杨说:“得找几个人去跟愿意入会的人谈话,然后介绍他们入会。”小福就推荐小明:“小明叔交人很宽,只要出去一转还不是一大群?”老杨便说:“我说老槐树底有能人你们看有没有?”[2]48显然,“交人很宽”交的是老槐树底的人,不是阎家山的任何人;另外,此处小明能成为“能人”是因为他是个“最能热心帮助”人的“好人”。
(2)“好人”出自小说第十回:老陈骂小元,老杨说:“这老人家也不要那样生气!一个人做了错,只要能真正改过,以后仍然是好人,我们仍然以好同志看他!”“好人”也有不同类型,像小明和老杨应该是天生的好人。
(3)小说第九回,老杨到区上把阎家山的问题一说,“区救联会、武委会主任、区长,大家都莫名其妙,章工作员三番五次说不是事实。最后还是区长说:‘咱们不敢主观主义,不要以为咱们没有发现问题就算没有问题……要真有那么大问题,就是在事实上整了我们一次风’”[2]51。
(4)年轻的、斗争的中坚力量如此。而老秦自始至终把老杨视为“先生”。斗倒阎恒元后,他甚至跪在地上给老杨和区干部们磕头,并说“你们老先生们真是救命恩人呀!”[2]54有学者认为,“老秦这个人物在整部作品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前进一步就是李有才,后退一步就是陈小元,或者张得贵……‘唯上’的奴性,‘唯利’的价值观、等级意识和报恩思想,就是老秦文化心态的全部构成。身为被压迫者,却甘心受虐,连一点反抗的欲望都不存在——这就是农民令人震惊的文化性格”(席扬《农民文化的时代选择——赵树理创作价值新论》)。如此批判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和根本问题:老秦文化心态如何,取决于“先生们”怎么做。如果“先生们”都像老杨那样,老秦肯定会改变;如果老杨只是偶然地、随机地出现,那就不可能指望老秦的文化心态破旧立新。
——小明篇——请假
——上课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