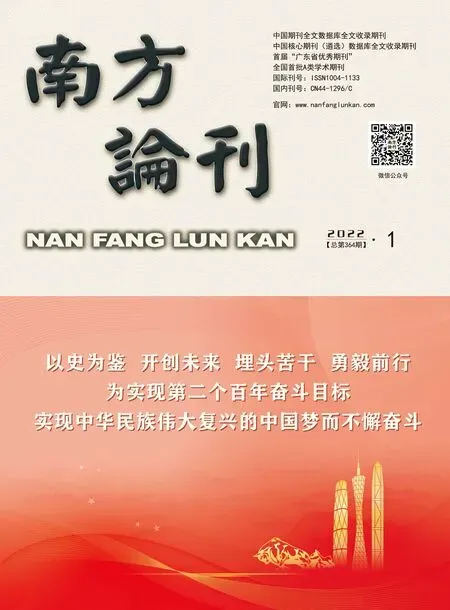“新文明观”视域中的“生态人”界定:场域、人格与观念
侯巍巍 马波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广东茂名 525000)
引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中国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推动了物质、政治、精神、社会以及生态“五位一体”文明的协调发展。他强调:“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依法治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显然,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全新的论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文明观”。笔者认为,这种“新文明观”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之中也都得到了充分体现,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基于学术研究的旨趣,论文拟从“生态人”模式内涵界定的视角诠释这种“新文明观”。模式研究或类型化研究是学术研究之中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表明了人们对社会生活进行逻辑抽象概括的学术需要,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种解释普遍本质的途径与框架,因而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法律人”模式亦为模式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生态人”模式是与“经济人”模式、“社会人”模式等人性假设相映衬的一种人之模式,在兼顾人的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加强调人的生态利益与生态理性诉求,亦彰显了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生态人”模式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既是抽象的也是具象的,它是一种“理想类型”,但又有着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关于“生态人”的内涵界定,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下关注的重点不同,内涵也不尽相同。如果说伦理学背景下的“生态人”强调的是“具有保护生态环境意识的生态人”,经济学背景下的“生态人”强调的是“具有利益属性的理性生态人”,社会学背景下的“生态人”强调的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生态人”。那么,法学视域下的“生态人”则更多强调的是“呈现在环境法之上,具有法律人格和具备环境法治观念的理性生态人”。
一、场域新形态:“生态人”呈现在环境法之上
所谓“呈现在环境法之上”,指的是“生态人”存在于环境法场域之中。“场域”原本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后经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出了所谓的“场域论”。布迪厄认为,场域属于关系性的范畴。“一个场域(field)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的场域概念,不能理解为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也不等同于一般的领域,而是在其中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1]有学者总结提出,“场域”具有相对独立性、不确定性以及多维空间性三个重要特征。“第一,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不同场域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会相互作用和影响;第二,场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立体空间,具有不确定性;第三,场域是一个关系网络的多维空间。”[2]事实上,社会空间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场域,如法律场域、政治场域、教育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等。笔者认为,如果将法律体系整体视为一个场域,那么在法律场域内部,还可以按照部门法的标准再分为民商法场域、经济法场域、刑法场域、行政法场域、社会保障法场域、环境法场域等不同的领域空间,且这些场域之间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如果说民商法、经济法场域下的人之形象是“经济人”、行政法场域下的人之形象是“政治人”、社会法场域下的人之形象是“社会人”,那么环境法场域下的人之形象则是“生态人”。郑少华教授提出,生态法是环境法的新法域,可以作为私法、公法、社会法之外的第四法域来映衬“生态人”。“如果我们主张人作为生态中一份子,人与自然是平等的,那么自然的意志如何表达?其权利如何配置?如是,为解决上述难题,环境法必须寻找新的法域归属,那就是生态法作为第四法域。由此形成私法—公法—社会法—生态法,对应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团体社会—生态社会,对应人的四层身份:市民—公民—团体人—生态人。”[3]笔者认为,尽管场域与法域内涵不同,场域应用于整个社会科学范畴,法域则主要应用于法学理论范畴,但它们的共同性在于“确定一定的独立空间”。场域重在描述社会领域的关系空间,而法域则重在描述法律适用的地域空间。笔者认为,“生态人”是存在于环境法场域之中的一种重要人之形象,而“生态法”则是环境法的新法域,是介于法体系与法部门之间的中位法概念。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提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方案》中将“生态环境”连在一起予以表述。严格意义上讲,生态与环境概念是有语义差别的。“环境着眼于人类外在的部分,而生态则将人与环境统一起来思考,两者保护的着眼点和整体观明显不一样,表明了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深化和递进,反映了不同时期和不同科学理论对法学研究的影响。”[4]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组建“生态环境部”,不再保留“环境保护部”,并提出“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此处,也是将“生态环境”连在一起予以表述。可见,“生态保护”与“环境保护”是同等重要的,那么作为生态保护依据的生态法与作为环境保护的环境法又是何种关系呢?事实上,关于环境法与生态法的概念界定,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习惯。例如,俄罗斯就称之为生态法。部分国内环境法学者也都提出过“生态法”的概念。严格来说,两者的内涵与外延都是不同的。环境的概念外延强调“以人类为中心”,而生态概念则强调“以生态系统为中心”。因此,笔者认为“环境法”主要针对的是满足现实需要的部门法,“生态法”指的则是一种未来可期的理想法,或者说生态法是环境法未来更高层次的发展形态,两者之间是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汪劲教授认为,环境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具有自身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调整对象是人类的环境利用关系,调整方法则体现出综合性的特征。“环境法是指以保护和改善环境、预防和治理人为环境损害为目的、调整人类环境利用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除了具有法的本质特征(如规范性、强制性等)外,还具有与其他部门法所不同的固有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法律规范构成的科技性、法律方法运用的综合性以及保护法益确立的共同性。”[5]陈志荣博士则认为,生态法包含了环境法暂时无法纳入其中的诸如生态价值理念、生态整体利益、生态法律行为和生态法律关系等为归依的生态法域特征。“生态法是一个以生态整体主义为价值理念追求、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分析起点、以生态法律行为为核心范畴、以生态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部门法。这些特征凸显了环境法独有的特征,明显区别与传统法律部门,在此意义上生态法就是狭义的环境法。”[6]陈志荣博士认为,生态法就是狭义的环境法,也是一个部门法。笔者认为,如果采用法域划分的分析框架,可以将生态法作为私法、公法、社会法之外的第四法域;如果采用场域划分的分析框架,环境法则可以界定为法律体系场域之下的部门法领域空间。两者之间是“当下”与“未来”,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一来,环境法以现实的环境利用关系为调整对象,具有与其他部门法调整对象所不同的重要“环境要素”特征,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已经得到了法学界与实务界的普遍认可。二来,生态法具有诸如生态价值理念、生态整体利益、生态法律行为和生态法律关系等为核心的生态法域特征,作为未来可期的理想法又预留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可以渐次成长为环境法发展的高级形态。因此,本文对于“环境法”与“生态法”不再做语义区分而混合使用。
二、人格新样态:“生态人”具有法律人格
所谓“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指的是“生态人”具有法律人格,或者说“生态人”可以成为法律上的主体,有资格成为法律世界游走的人。“人格”一词来源于古罗马的“persona”,在罗马法本来的语义上,“persona”原本只是用来指称法律主体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的不同身份。“人格,作为法律上的拟制,在法律的逻辑结构中,具有其一定的意义。人格是法律世界的最基础概念,没有人格概念的存在,法律世界的一切制度构建都无从谈起。法律上的人格,即法律人格。”[7]人格的内涵经罗马法的“主体资格”创造,《法国民法典》的“权利主体”改造以及《德国民法典》的“权利能力”塑造而形成了今天多元语义的“法律人格”概念。有学者认为人格内涵丰富、形象多变,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一是指具有法律地位的权利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二是指作为权利主体法律资格必备条件的民事权利能力;三是指一种受保护的利益,即人格利益。也即是说,人格一词同时在‘法律主体’、‘权利能力’与‘人格利益’的语义上使用。”[8]对于“生态人”是否具有法律人格这个问题,鉴于“人格”一词可以同时在法律主体、人格利益与权利能力的语义上使用。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分别从“‘生态人’是否可以成为法律主体”“‘生态人’是否享有人格利益”“‘生态人’是否具备权利能力”三个维度上予以“间接反证”。
对于“生态人”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笔者认为,可以从“生态人”是法律的创造物、拥有规范的人格化、生态人具有自为性以及“生态人”可以成为联结法律和现实的桥梁四个维度进行论证;对于“生态人”具备权利能力,可以强调“生态人”享有生态(环境)权利和承担生态(环境)义务的资格视角进行论证;而“生态人”享有人格利益,则可以从抽象维度的“生态人”与具象维度的“生态人”两个视角进行阐释。抽象维度的“生态人”对应的人格是“抽象人格”,所保护的法益是“生态利益”,而不是具体的肖像、姓名、名誉、隐私等法益。具象维度的“生态人”对应的人格是“具体人格”,自然人所拥有的生命、健康等人格权所保护的法益与环境权密切相关。笔者认为,“生态人”具有法律人格,或者说“生态人”可以成为法律上的主体。需要注意的是,“生态人”的法律人格与传统民法意义上的“人格”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生态人”法律人格表征的是生态时代的诉求,而传统民法意义上的“人格”则主要关注的是“人在民法中的存在方式”。“法律上的变革并不是孤立进行的,法律上生态人模式的转型伴随着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学科一系列的发展以谋求顺应这个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生态危机并不意味着一个问题,而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是更深邃地思考我们自身,思考人类如何存在,而选择生态人,践行生态人的行为模式便是我们求生于生态危机这个时代的唯一方法。”[9]说到底,人格构造变迁是生态时代的产物,“生态人”法律人格的塑造因应了生态环境保护对于“人之形象”的期待。法律发展与进化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法律上的人的形象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可以说,法律形象变化的动因既是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发展,也是源于既有法律框架无法满足生态时代法律生态化的内在诉求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传统人格立法将生命的保全和促进置于关注的焦点,实质上是具体时代背景下的历史性产物。因此,如果这种制度赖以存在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则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亦应及时调整,以体现变化了的时代背景与生活在新时代背景下之主体的权利要求。也就是说,分析现代社会中个体因为自身的完满实现而应当享有之人格权利的内容,应当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10]“生态人”的人格与传统的法律人格存在的不同,可以归结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特别关注和试图将环境权纳入生态人的人身权之中。蔡守秋教授认为,“生态人”模式的确立可以得出“法律既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结论,而公民环境权则可以视为生态人的人格权利。“环境权是生态人所固有的,为维护主体调整人格所必备的权利。在生态人看来,对人格利益进行现代扩展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关于生态人具有法律人格这个问题的更多探讨,考虑到涉及的其他问题较多,笔者拟另行撰文阐释,在此不再赘述。
三、法治新价值:“生态人”具备环境法治观念
所谓“具备环境法治观念”,指的是“生态人”具备主客观认知能力,对法治有独立的理性判断,并形成内化的法治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人的观念是对客观现实的能动反映,是客观存在在人的头脑中的主观印象。显然,人的认识不是来自天赋的观念,不是来自头脑本身,而是后天形成的,它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提出要推动全社会增强法治观念,“要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增强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使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原则”。
显然,法治观念来源于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强调人们对于法治的理性认知与法律至上信仰。“人们通过对法律的性质、地位、作用以及法治的理念、原则和运行机制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对法治在内心中所形成的理性之认知、产生的敬畏之感情、树立的坚定之信念。由此可见,法治观念的实质是法律至上、以法治国。”[12]环境法治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环境法治实质上包括两种状态:静态的环境法律制度与动态的环境法律运行。“环境法治既包括一国静态的环境法律制度,也包括环境法律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态运行和实现状态。”[13]笔者认为,环境法治在理念层面、运行层面以及制度层面都有不同语义理解。“在理念层面上,环境法治是指一种体现生态正义、生态安全等核心价值理念的思想;在运行层面上,是指一种环境法律实现的过程与状态;在制度层面上,是指在环境法律基础上建立或形成的以可持续发展原则为指导的制度、程序和规范体系。”[14]
“理性”一词源于在西方,“从古希腊时代起,理性一直是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并最终建立起这样一种理性主义文化信念:世界是合乎理性的存在结构,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可以通过理性把握世界的结构,从而控制和操纵自然”。[15]对理性的探究与追问,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一部人类的进步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人类理性的发展史。苏格拉底提出,“德性就是理性”。在康德看来,理性是全部高级的认识能力,康德将理性分为纯粹的理性和实践的理性。“康德指出,理论理性(纯粹理性)涉及理性的理论运用或思辨运用,实践理性则关乎理性的实践运用;实践理性主要不涉及人的认识技能,而是与‘欲求的机能’关系紧密。理论理性首先以说明世界为目标,与之相关的活动主要表现为认知,具有描述性的特点;实践理性则以改变世界为指向,与之相关的活动更多地展开为评价,具有规范性的特点。”[16]德国社会学巨擘马克思·韦伯则把理性划分为两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韦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演进的分析,看到了科学技术对推进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及资本主义对财富的追逐和对效率的推崇,因此他把理性划分为两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17]笔者认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描述的侧重点不同。工具理性重在描述“手段与行动”,价值理性重在阐释“价值与追求”;工具理性重在“脚踏实地”,而价值理性则强调“仰望星空”。“马克思·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一书,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展开了经典诠释。他认为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周围环境和他人客观行为的期待所决定的行动,这种期待被当作达到行动者本人所追求的和经过理性计算的目的的条件或手段。价值理性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坚信某些特定行为的——伦理的、审美的、宗教的或其他形式的——自身价值,无关于能否成功,纯由其信仰所决定的行动。换句话说,工具理性强调手段——目的的合理性;而价值理性注重信仰和理念,要求所追求的目标必须符合某种伦理道德或者人类内心深处的某些信念。”[18]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将理性划分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主观理性本质上关心的是合于目的的手段,客观理性则指向的是事物存在的意义,关心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19]哈贝马斯认为韦伯过于强调工具理性而忽略了价值理性,使社会成员面临着丧失自由和意义的危机,为此,他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交往理性强调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话语共识,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达到法理的合理性。”[20]
什么又是“理性生态人”呢?吕忠梅教授曾提出“生态理性经济人”的概念,也就是将“生态理性”纳入“经济人”的理性之中,这样既可以保持“经济人”在一般经济性活动中的正常利益,同时又增加生态性的考虑,保证“经济人”的活动不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的后果。“生态理性经济人”的侧重点还是“经济人”,只是嵌入了“生态性”的考量,“就是将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与自然价值统一协调的新型人性标注”。尽管“理性生态人”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但显然“理性生态人”侧重点必然是强调人的“生态性”,而不是“经济性”。恐怕,这就是“理性生态人”与“生态理性经济人”最大的不同。蔡守秋教授、吴贤静博士等都撰文专题讨论过“生态理性人”问题,蔡守秋教授所阐释的“理性生态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理性生态人是指具有环境意识和环境法治观念,会计算环境利益,寻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佳化、最大化的人。”[21]是的,“理性生态人”对于“生态人”的要求不仅仅是具备“生态文明意识”这么简单,还要具备“理性”。当然,笔者所强调的“理性”,更多的是价值理性、实践理性与交往理性,强调“生态人”应当具备沟通回应与反思能力,即“生态实践理性”。“除了强调反应、体现和尊重生态科学理性所揭示的自然生态规律外,还特别关注通过民主化、法治化的社会参与、对话、沟通、商谈和合作,达成环境与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社会公共事务的共识,进而推动环境与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社会公共目标的实现。”[22]
四、余论
需要说明的是,“生态人”模式的建构并不能通过简单的否定“经济人”模式与“社会人”模式来证成,而必须“兼容并蓄”,有保留、有批判,有整合。经济学之中的“溢出效应”理论告诉我们,外部性包括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而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发挥正外部性效应。“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和非排他性,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活动因其外溢性可为其他地区带来生态环境效益。”[23]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顽强奋斗的伟大创造,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术语革命”与理论创新。笔者认为,“生态人”模式与其说是对“经济人”模式与“社会人”模式的一种批判,毋宁说它是一种更加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诉求与生态安全价值理念的全新人之形象。它矫正了以往过于功利性的“经济人”与“社会人”等人之模式的内在缺陷,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时代精神,回应了“环境法革命”这个时代主题,是一种更加契合生态文明新时代诉求的人性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