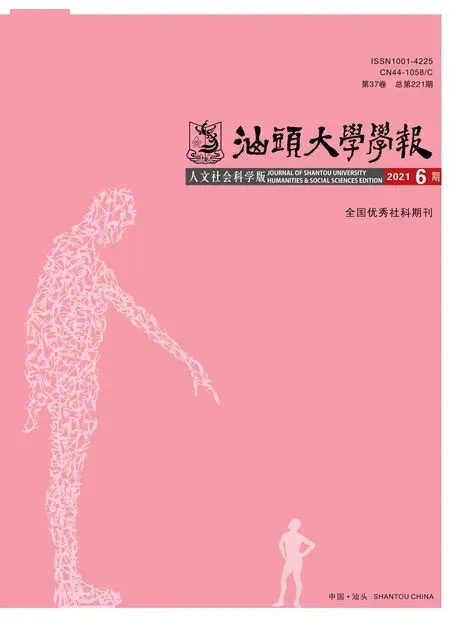再探《乐府诗集》中“晋乐所奏”与“本辞”之关系
徐韫琪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一、“晋乐所奏”辞与“本辞”的界定
(一)界定角度:入乐情况与文献来源
关于“晋乐所奏”辞的概念,学界普遍认为指由荀勖“撰旧词施用”[1]608的乐奏时代为晋的乐奏辞,而关于“本辞”的概念,学界至今仍存在分歧。《四库提要》对《乐府诗集》作题解云:“每题以古词居前,拟作居后,使同一曲调,而诸格毕备,不相沿袭,可以药剽窃形似之失。其古词多前列本词,后列入乐所改,得以考知孰为例,孰为趋,孰为艳,孰为增字、减字”[2]1696。《四库提要》虽指出了《乐府诗集》的编纂体例和优点,却未具体阐释“本辞”的含义。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中提及郭集《塘上行》本辞结尾的套语为入乐痕迹,认为郭集中的“本辞”及“晋乐所奏”辞“皆增加之本,而本词则久佚矣。后人不得其本词,因此本增减略少,遂以当之。而未察后六句之不相属。”[3]22可见纪氏认定本辞应文意连贯,不应有入乐及增删痕迹,而郭氏之举殊为未察。
20 世纪初以来,研究者进一步注意到“本辞”的定义及其与乐奏辞的区别与联系,其界定方式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从乐奏、演唱的角度界定,二是根据其文献来源界定。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从“入乐与否”的角度区分本辞与乐奏辞:“用于音乐的一篇,分做数解,以便演奏。其中字句为‘不整齐体’和‘重复体’,全篇结构比本辞长。本辞一篇,大半无解。因为不施之于音乐,所以无分解的必要。其中字句为‘整齐体’,很少重复。”[4]30朱自清的《中国歌谣》在“诗的歌谣化”一节中分析了郭集中的《西门行》,提出“本辞就是徒歌”,并将其与《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对照,认为“本辞是从古诗化出来的,而那首晋乐所奏是参照古诗与本辞而定的。”[5]52刘永济则认为“本辞”不入乐,“郭集每以协律之辞与本辞并载,其本辞皆五言古诗也”[6]128,并认为“协律之辞”对古诗进行了“增损字句”的加工。相比之下,陆侃如、冯阮君的判断则更加谨慎:“所谓‘本辞’大约是未经晋乐工修改者”[7]118,并未断言其是否进入官方乐奏序列或入徒歌。值得一提的是,20 世纪80 年代初萧涤非、王季思两位学者针对《东门行》校勘问题的论辩促使郭集“本辞”与《宋志》“古词”的概念进一步明晰,即《宋志》“古词”概念涵盖了汉代无名氏乐歌和晋乐所奏的汉民歌,而郭集中的“本辞”指“未经晋乐府加工过的汉代本来的歌词”[8]18。近年来相关讨论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如崔炼农指出“本辞”相较于乐奏辞是最初(前次)入乐之辞[9]。张建华认为“本辞是所在曲题最初、最原始的歌诗”,尚未进入宫廷音乐体系,是“同一曲题乐府诗创作的本源参照,它是汉乐府处于民歌或俚歌阶段的状态。”[10]但张建华在讨论郭茂倩“本辞”概念时纳入了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中的“本词”概念,忽视了二者的差异,吴兢使用的“本词”概念指两汉无名氏作品(强调非魏晋拟作),不能将其视作《乐府诗集》中“本辞”概念的源头。
除了从乐奏、演唱的角度进行界定,以逯钦立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试图通过“本辞”与“晋乐所奏”辞的文献来源或沿革关系以进行区分。如逯钦立在《〈古诗纪〉补正叙例》中指出“凡郭氏作晋乐所奏者,据《宋书·乐志》也,作本辞者,则本之《文选》及《玉台》等集也。”[11]151王淑梅认为郭集中的“本辞”即乐奏之本,是荀勖“撰旧辞”时用作底本的旧歌诗。[12]与此相反,法国汉学家桀溺(J-P.Dieny)从修辞和逻辑的精致程度出发,否认“本辞”是“晋乐所奏”辞的原始文本,认为“郭茂倩把‘乐所奏’的歌辞和‘本辞’这两种文本之间的关系弄颠倒了”[13]178。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晋乐所奏”一节中表示完全赞同桀溺的看法,并从文献来源稳定性的角度提出来源于史书《宋志》的乐奏辞更接近原始文本,而来源于文学选集的“本辞”经过了文人的大幅加工:“所谓‘本辞’其实代表了对《宋书·乐志》中乐府歌辞进行规范、修整并且赋予连贯性的努力。”[14]373
综上可知,目前学界关于“本辞”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中前三种观点均认为“本辞”在先,乐奏辞在后:
①本辞为不入乐的徒诗;
②本辞为尚未入乐演奏的民歌歌词;
③本辞为初次(晋之前)入乐的歌词;
④本辞为“晋乐所奏”辞的修改版本。
(二)“本辞”内部的差异性
目前学界关于“本辞”尚未形成一个共识性定义,仍有继续探讨的价值和空间。笔者认为,十篇本辞内部存在较大差异,从作者归属的角度看,《西门行》《东门行》《满歌行》《白头吟》属汉代无名氏作品,与有主名的三曹乐府诗不可一概而论。这四篇汉代无名氏乐府的“本辞”虽未入晋乐,但亦有可能入前代乐府。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在《皑如山上雪》(即《白头吟》)下指出“竹竿何嫋嫋”后四句已是“先时入乐所加,其文迥不相属”[3]5。对此纪氏给出的解释是:“历代之乐,音节遞殊,故其增减入乐之词,亦辗转更改不止一本。”另《西门行》本辞中“逮为乐,逮为乐,当及时”具有鼓点般的紧凑节奏感,颇似叠唱痕迹。而《东门行》《满歌行》本辞虽无分解、叠唱、套语等明显入乐痕迹,依然不排除入乐的可能。
三曹“本辞”既可能是最初不入乐的案头创作,也可能入魏乐。三曹作品在当时能否进入宫廷演奏序列成为官方乐章,与其身份和权力密切相关[15]170。曹植《怨诗行》“明月照高楼”一篇在经荀勖整理之前应未入乐。《宋志》收录乐府诗一般先取诗开头两字,再标注所属曲调,然后标作者和分解情况,如:
周西 短歌行 武帝词 六解
秋风 燕歌行 文帝词 七解
但《宋志》在收录“明月照高楼”一篇时,却未标所属曲调,只标了“明月 东阿王词 七解”,意味该诗此前应未曾入乐[16]。曹植未必像其父那样有“躬著雅颂,被之瑟琴”[17]1155的权力,他本人也说所作“不敢充之黄门”[17]1143,故《怨诗行》《野田黄雀行》应未入魏乐。另《怨诗行》在《文选》中标为《七哀诗》,在《玉台》中标为《杂诗》,皆徒诗题目,益可证其最初为不入乐的徒诗写作。但不能据此推断三曹本辞皆不入乐。前文已述,纪容舒指出《塘上行》本辞“出亦复苦愁”至结尾为入乐痕迹,且武帝本人“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18]46,乐辞在创作完成后即可配乐演奏,操、丕父子又具有至高的政治权威,那么二祖名下的“本辞”有极大可能已入魏乐。如魏文帝《铜雀园诗》最初为书面创作,后入瑟调《善哉行》、瑟调《东门行》[19]242。另曹丕《短歌行》“仰瞻”在《乐府诗集》中标为“魏乐所奏”,引《古今乐录》:“王僧虔《技录》云‘魏氏遗令,使节朔奏乐,魏文帝制此辞,自抚筝和歌。’”[20]447此篇虽不在十篇“本辞”中,亦可作为曹丕之作入魏乐之旁证。
因此,以“是否入乐”区分本辞与晋乐所奏辞是不全面的,徐嘉瑞、刘永济等前代学者关于“本辞不入乐”的判断值得商榷,崔炼农关于“本辞是前次入乐之辞”的判断亦未尽然,两方皆忽略了十篇“本辞”内部的差异性。由此可推,郭茂倩设定“本辞”的标准未必在于其是否入乐,纪容舒在《玉台新咏考异》中对郭茂倩的批评或许出于误解。但“本辞”与“晋乐所奏”辞相对而设的文献价值无可怀疑,这一概念的提出必然存在某种划分依据。笔者认为,郭茂倩搜集乐府诗的过程中,除了参阅乐书等音乐类文献,也势必会排查其他各类别集、总集,其中郭茂倩发现一些别集、总集中收录的乐府诗与《宋书·乐志》等乐类文献中面貌不同,因此做了本辞与乐奏辞的区分。二者之间不仅存在文献来源层面的区别,亦隐含先后关系的判断,即郭茂倩推断“本辞”面貌早于“晋乐所奏”辞,故以“本辞”冠名。对此以桀溺、宇文所安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后文将予以回应。笔者从文献来源的角度提出关于“本辞”的界定思路,为进一步印证所持观点,下面将对“本辞”与“晋乐所奏”辞的文献来源加以考辨。
二、“晋乐所奏”辞与“本辞”的文献来源
(一)“晋乐所奏”辞的文献来源
前文已述,逯钦立认为《乐府诗集》中分解的“晋乐所奏”辞来自《宋书·乐志》,但并未详加证明。青子文则在《汉魏俗乐歌辞及其在晋宋的流变》一文中全面考察了《乐府诗集》所载乐奏辞的文献来源,提出见于《宋志》中的51 篇乐奏辞文本以《宋志》为据,进一步印证了逯氏的说法[21]75。本文所讨论的十篇《乐府诗集》“晋乐所奏”辞(《乐府诗集》国图藏宋刻本)属51 篇见于《宋志》(中华书局1974 年本)的乐奏辞,仅以下几处字词差异,无调换、增减章句的现象,应为传抄讹误:
《苦寒行》“北上”,《宋志》作“暝无所宿棲”,《乐府诗集》作“瞑无所宿棲”。《宋志》作“中道正裴回”,《乐府诗集》作“中道正徘徊”。
《塘上行》,《宋志》作“傍能行仪仪”,《乐府诗集》作“傍能行人仪”。《宋志》作“使君生别离”,《乐府诗集》作“使君生离别”。《宋志》作“倍恩者苦栝”,《乐府诗集》作“倍恩者苦枯”。
《东门行》,《宋志》作“它家但愿富贵”,《乐府诗集》作“他家但愿富贵”。
《怨诗行》,《宋志》署《东阿王词》,作“流光正裴回”,《乐府诗集》作“流光正徘徊”。
《白头吟》,《宋志》作“蹀唼”,《乐府诗集》作“蹀躞”。《宋志》作“晴如山上云”,《乐府诗集》作“皑如山上雪”。
《满歌行》,《宋志》作“伶仃荼毒”,《乐府诗集》作“零丁荼毒”。《宋志》作“莫秋冽风起”,《乐府诗集》作“暮秋烈风起”。《宋志》作“去去自无它”,《乐府诗集》作“去去自无他”。《宋志》作“此一何愚”,《乐府诗集》作“此何一愚”。
此外,“晋乐所奏”辞的分解亦同于《宋志》中著录。故《乐府诗集》中“晋乐所奏”辞的文献来源可基本定为《宋书·乐志三》。
(二)“本辞”的文献来源
逯钦立提出《乐府诗集》中“本辞”来自于《文选》《玉台》等文集,但未进一步加以证明。笔者对郭集中“本辞”与收录于文集中的文本加以比勘,发现《乐府诗集》十篇本辞中有七篇可从《文选》(李善注胡刻本、六臣注四部丛刊景宋本)和《玉台新咏》(寒山赵氏覆陈玉父本)中找到完整线索,具体如下:
《短歌行》“对酒”见《文选》卷二七。《文选》作“何时可掇”,本辞作“何时可辍”。本辞无“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八字。
《燕歌行》“别日”见《玉台新咏》卷九。本辞同《玉台》。
《苦寒行》“北上”见《文选》卷二七。《文选》作“悠悠使我哀”,本辞作“悠悠令我哀”。
《塘上行》见《玉台新咏》卷二(署甄皇后)。《玉台》作“从军致独乐”,本辞作“从君致独乐”。
《野田黄雀行》,《文选》作《箜篌引》见卷二七。《文选》作“亲友从我游”,本辞作“亲交从我游”;《文选》作“生在华屋处”,本辞作“生存华屋处”。
《怨诗行》,见《玉台新咏》卷二署《杂诗》《文选》卷二三署《七哀诗》。本辞同《玉台》。《文选》作“君怀良不开”,本辞作“君怀时不开”;《文选》作“贱妾当何依”,本辞作“妾心当何依”。
《白头吟》见《玉台新咏》卷一,署《皑如山上雪》。《玉台》作“鱼尾何蓰蓰”,本辞作“鱼尾何簁簁”。
经比勘可知《乐府诗集》中“本辞”与《文选》《玉台》中所录文本相似度极高,异文多为个别字词差异。仅《短歌行》一处本辞无“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八字,应为脱漏。对于未被《文选》《玉台》收录的《东门行》《西门行》《满歌行》本辞,逯氏认为“尚不知根据何书”[11]151,但仍推测其来自于与《文选》《玉台》性质相似的文集。对此崔炼农提出不同观点,认为本辞应来自于某种综合性乐书而非诸家文集,核心理由之一即十首“本辞”中,字句与今本《文选》《玉台新咏》所录大同者仅七曲,尚有三曲未见被文学总集或别集收入的线索,占总数近三分之一[9]。他所说的“尚有三曲”即《东门行》《西门行》《满歌行》,而事实上,三曲亦有被其他文集收录的依据。尽管《东门行》《西门行》《满歌行》在现存文献中只能追溯到《宋志》,但《要解》中的题解为我们呈现了《宋志》之外、来自“诸家文集”的另一重文献面貌。笔者试从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入手,梳理《乐府诗集》“本辞”辑自诸家文集的线索。
唐人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以下简称《要解》)屡被《乐府诗集》征引,吴兢在序中介绍著述目的是批评历代文士“不睹于本章,便断题取义”的风气,力求还原乐府题的本事与本章。而关于书中所引文献的来源,作者明确说明“余顷因涉阅传记,用诸家文集”[22],可知《要解》的文献来源为传记和诸家文集。需注意的是,吴兢撰《解题》所涉猎的“传记”并非人物传记,而是泛指史书中的记载。青子文从类序、所收乐府题、乐奏时代等方面考辨出《要解》中“乐府相和歌”类所引乐府辞以《宋志》为主要依据[21]60,即吴兢所言“传记”实为《宋志》。《宋志》并非《要解》所引乐府辞的唯一资料依据。《要解》论及古辞《步出夏门行》“天上何所有”、曹魏乐府《善哉行》“有美一人”此二篇时,题下注“此篇出诸集,不入乐志”,今本《宋志》确未收录。而《玉台》恰收有“天上何所有”一篇,《魏文帝集》收“有美一人”篇,正印“篇出诸集”之说。此外,除明确标注“篇出诸集,不入乐志”外,吴兢在收录非《宋志》著录的古辞时也有未标出处的情况,如《要解》所引《长歌行》古辞未见于《宋志》,而是来自《文选》,对此吴兢并未注出,这提示我们详细考察吴兢所引古辞的具体来源。
《要解》用“右古词云××”的形式对一篇作品的介绍包括概述古辞原意与直接引用两种,介绍中常既有与《乐府诗集》所录本辞相洽的部分,又有与晋乐所奏辞契合的部分,呈现了参考文献来源的双重性。《东门行》解题介绍古词有“妻子牵衣留之”的表述,属于概述古词原意(不需要与古词逐字对应)。《乐府诗集》本辞中为“舍中儿母牵衣啼”,晋乐所奏辞为“儿女牵衣啼”。本辞中“牵衣啼”的主体为“儿母”,晋乐所奏辞主体为“儿女”,显然本辞中“儿母”的表述与《要解》中“妻子”(妻与子)更符合。而《要解》中“且曰今时清,不可为非也”的表述又与晋乐所奏辞结尾“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的说教相契。《西门行》解题有“昼短苦夜长”,本辞中为“昼短苦夜长”,晋乐所奏辞为“昼短而夜长”,可见本辞与《要解》中所引古词相合。《要解》中“无贪财惜费,为后世所嗤”的表述又与晋乐所奏辞结尾“贪财爱惜费,但为后世嗤”相符。《满歌行》解题引古词“为乐未几时,遭时崄巇”,本辞为“遭时崄巇”,晋乐所奏辞为“遭世险巇”,所引古词同于本辞。而《要解》“终言命如凿石见火”又与晋乐所奏辞“命如凿石见火”相符。可见吴兢著录同一篇乐府题的古词时,参考了不止一种文献。
既然《要解》的文献来源是《宋志》及诸家文集,则吴兢著录《西门行》《东门行》《满歌行》时参考的异于《宋志》的文献应本自诸集。进一步说,吴兢撰《要解》所采文献与《乐府诗集》“本辞”所据文献具有同源关系,吴兢参阅的诸家文集中,应存在与《乐府诗集》中《西门行》《东门行》《满歌行》本辞面貌一致的文本,只是后来失传了。除《要解》外,《文选》李善注中也留下了蛛丝马迹。《文选》左思《咏史诗》“外顾无斗储”句注:“古《出东门行》曰:‘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乐府诗集》中《东门行》本辞为“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而晋乐所奏辞为“盎中无斗储,还视桁上无悬衣”。李善所注引文同于本辞,不同于晋乐所奏辞,可见李善见到并引用了与本辞面貌一致的文本,并极有可能来自诸集。至此,十篇本辞在《乐府诗集》以前的诸家文集中皆有著录线索,郭茂倩应有条件从中辑录本辞,则本辞之文献来源应为区别于乐书的集部文献。
三、“晋乐所奏”辞与“本辞”的先后关系
(一)判定思路的差异
关于“本辞”与“晋乐所奏”辞的沿革关系,学界普遍观点是“晋乐所奏”辞是在“本辞”基础上的加工。如萧涤非认为“晋人每增加本词,写令极畅,或汉晋乐律不同,故不能不有所增改。”[23]79曹道衡根据“西”“依”在汉魏西晋所属不同韵部考辨出《怨诗行》“晋乐所奏”辞为东晋后南方人所改,且推测“晋乐所奏改本辞‘西南’为‘东北’,大约因为曹植封地均在都城洛阳之东,故据东阿地址而改。”[24]184类似观点不一一列举。与主流观点不同,崔炼农《〈乐府诗集〉“本辞”考》分析《塘上行》发现“本辞”有“主文而整理”痕迹,推测其“当在乐奏辞基础上改造而成,是经过转录整理的歌辞文本。”[9]但这一观点又与其最终得出的结论(本辞为最初或前次入乐之辞)相悖,逻辑未能自洽。针对这一问题,以桀溺、宇文所安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提供了颇为新颖的思路,即认为“本辞”是对“晋乐所奏”辞的加工,并给出了颇具新意的论证。
桀溺的《驳郭茂倩——论若干汉诗和魏诗的两种文本》运用文本细读法将十首本辞与乐奏辞一一比照,根据修辞精致程度和文本逻辑脉络,推断出“本辞”当为乐奏辞的改写本,试图“对千余年来被奉为圭臬的郭茂倩理论提出质疑,并证明它是错误的,借此引起中国文学史专家们的注意。”[13]179如他根据《怨诗行》“本辞”中“清路尘—浊水泥”的对比乐奏辞中“高山柏—浊水泥”更巧妙,认为改编者不可能把“如此难得的佳句轻易放弃”[13]133,更可能是“本辞”对乐奏辞匠心独运的改造。桀溺分析《白头吟》乐奏辞时认为其结构松散且用字不得体,故将“本辞”看成“在《宋书》那个拙劣的文本基础上,经多次修改而成的。”[13]139宇文所安继承了桀溺的基本观点,他从写抄本生成的角度进一步探索材料的来源及性质,并对来源于《宋书》与《文选》《玉台》等文集的文本性质及稳定程度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分判:
诗集是为了阅读的愉悦而编选的,而音乐传统中的歌诗集似乎旨在校正和保存宫廷音乐传统本身……当被收入文学总集中,音乐传统中的歌诗都按照当时的文学趣味进行过加工整理。[14]34
《宋书·乐志》体现出数代学者在歌诗文本保存方面的细心……在《玉台新咏》中以及在其他地方将《宋书》中的材料按照6 世纪早期对诗歌的认识转换为“诗”的现象,至少会促使我们思考那些现已亡佚的资料的文本状况。它同时也提醒我们,6 世纪的编者往往按照自己的观念,对文本进行随意的改变。[14]29基于上述基本观点,宇文所安将来自于《宋志》的“晋乐所奏”辞视为更早的、更可靠的文本,补充和加强了桀溺的论证,提出“所谓的‘本辞’其实代表了对《宋书·乐志》中的乐府歌辞进行规范、修整并且赋予连贯性的努力”[14]373。宇文所安以《满歌行》为例详细分析了乐奏辞被更改的痕迹,这一点延续了桀溺的逻辑,即文意更连贯、形式和韵律更讲求的文本是被修改的结果,最终指出本辞是对晋乐所奏的一次不成功的改造。
(二)“本辞”非“晋乐所奏”辞的加工
宇文所安从文献来源、编纂目的等角度对乐志与文集的性质分析无疑可贵,但“本辞”是否真的如他所说、是乐奏辞的改写本?辨析这一问题,不妨继续从乐书与文集的收录角度加以思考。
首先,宇文所安多次强调《宋书·乐志》作为官方文献的严肃性,然而他忽略了音乐类文献尽管忠实记录了某一时代的演奏情况,与前一时代相比,其所收录的文献仍可能是“变动不居”的。囿于现存文献,我们无法找到十篇乐奏辞在《宋志》以前乐书中的记录,但不妨以保存在《史记·乐书》中的两篇《天马歌》[25]1178与《汉书·礼乐志》中的两篇《天马歌》[26]1061作以参照:

不难看出,《汉书·礼乐志》中的《天马歌》删去了《史记·乐书》中的“兮”字,将汉武帝的七字楚声短歌变成三字一句的形式,且明显扩充了篇幅,增添了登天升仙的内容。正史中的乐类文献固然会被史官审慎地著录,但其施用属性也决定了它会受到场合和配乐的深刻影响,王淑梅即指出《天马歌》在汉成帝时期被作为祭祀歌诗并加以修改,“反映了郊祀歌乐由初创时期的自由奔放日趋威严整肃的过程,也反映了日渐神圣的庙堂祭祀的需要”[27]。由此可见,《汉书·礼乐志》中的文本其实是后世根据实际需要而不断修改、润饰的结果,相较于前代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变动,那么沈约编《宋志》时,所收乐府辞亦可能经过增删加工。另外,尽管从成书时间来看,《宋志》的定稿稍早于《文选》和《玉台新咏》,但晚出版本中的文字反而较早期传本保留原初特征的情况在版本学史上也屡见不鲜[28]91,故不能仅据成书时间断定《宋志》所收较《文选》《玉台》更近原貌。
其次,如确如宇文所安所说,《文选》《玉台》在收录时将《宋书》中的材料按照6 世纪早期人们对诗歌的认识将其转换为“诗”,那么从编集逻辑来看,编纂者几乎没有这种必要。不妨以曹植作品为例,关于曹植文集的编纂时间有确切记载,最晚亦在景初中曹叡下诏“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馀篇,副藏内外”之时。[18]527且《陈思王曹植集》在《隋书·经籍志》中亦有著录[29]1059,可见萧统和徐陵编集时依然能够阅读并作为参考。那么萧统和徐陵在收录曹植作品时,几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忽视既有的别集,反而根据《宋志》所载的入乐分解且加入表演套语的“东阿王词”,重新改写出一首《七哀诗》。退一步说,即使文集编纂者这样做了,为何只选取个别篇目进行改写?如文帝《燕歌行》在《宋志》中录有两篇,《玉台》编者为何只改“别日”一篇而不改“秋风”一篇?对此作者尚未给出相应的解释。由此可见,“本辞”不应为“晋乐所奏”辞的加工整理本。桀溺基于修辞精致程度的分析不足以颠覆本辞与乐奏辞的先后关系,宇文所安提出《文选》《玉台》的编者“按照自己的观念,对文本进行随意的改变”,并未给出切实可靠的文献依据,亦不符合文集编纂的逻辑。
综上所述,《乐府诗集》中“本辞”的概念是与乐奏辞相对的“原本”之辞,其内部有较大的差异性(有无署名、作者身份),不应从入乐与否的角度一概而论。郭茂倩将“本辞”与“晋乐所奏”辞分类著录的出发点在于区分其文献来源,即他在编纂乐府诗时通过爬梳集部文献,摘寻出与乐书类文献面貌不同的一批文本,将其命名为“本辞”,并隐含着“本辞”在先、乐奏辞在后的关系判断。本辞的来源为诸家文集,只是后来亡佚了。《乐府诗集》中“晋乐所奏”辞采自《宋书·乐志》,是晋代乐工根据施用场合及入乐要求对“本辞”进行增损的产物,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乐府诗表演形态。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乐奏辞文本的稳定性不若文集可靠,正史中保存的歌辞亦不能代表乐府诗的原始状貌。《文选》《玉台新咏》等集部文献对乐府诗的著录原则为实录,其价值应得到进一步重视。
四、反思与总结
本文通过梳理“本辞”与“晋乐所奏”辞的概念、文献来源及沿革关系,试图补充并修正前辈学者的观点,并以此为契机探讨运用“手抄本文化”相关思路研究古代文学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囿于现存文献的限制,研究者较难厘清文集编纂者对文本进行“加工整理”的具体程度,即编者是否会按照个人或时代的审美标准,对文本内容进行改动、进行多大程度的改动,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充实的文献支撑。近年来“写钞本的生产与流动”这一思路在学界颇为流行,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新角度,使得学者能够突破辨伪学的立场,充分关注到文本的流动性及“钞者”的创造性,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但该方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于乐府学相关研究,仍有待检验。西方《圣经》校勘学常将修辞等级较低的文本视作更原始的文本,或许这也是宇文所安等学者将“晋乐所奏”辞视作更早文本的原因之一。然而乐府这一体系亦有其特殊性,为了配合表演,入乐后文本修辞等级和审美价值降低的现象并不鲜见。若秉承“粗糙文本早于精致文本”的先验式判断,将“本辞”视作对“晋乐所奏”辞的加工,恐缺乏切实的文献依据作为支撑。这也提示古代文学研究者在运用新方法时,必须充分考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立足文献,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