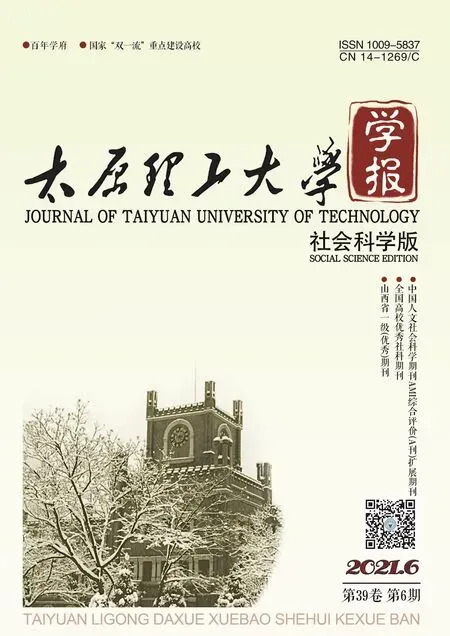西游宝卷的刊刻与传播
车 瑞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旅游与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西游故事的生成与发展贯穿于从寺院俗讲到民间大众及文人墨客的过程,使用了口头传播与文字传播双重媒介。宝卷是古典小说、戏曲杂剧、传说故事在民间传播的主要方式。明清到民国时期,宝卷以手抄、官刻、坊刻等不同方式同时存在,它们是宝卷传播史的重要环节。西游宝卷在《西游记》小说刊行前后均有存在的依据,它不仅拓展了《西游记》的传播领域,见证了中国出版技术从木刻到石印再到铅印的过程,更是西游出版史乃至中国出版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抄本与刻本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宝卷的传播是以抄书和刻书(手抄本和印刷本)两种方式同时进行的。“从形式上看,明清时期的戏曲文本往往是抄本与刊本并行的。在印刷技术广泛应用于文学书籍传播之前,大多数的文本是依靠抄写的方式完成的。明清时期虽然印刷技术已有长足的发展,但对于戏曲而言,其手抄本的传播一直都存在。”[1]不仅是戏曲,包括小说、宝卷在内的其他形式的文本也多以手抄形式流传于世。“演唱宝卷的特点是照卷本宣扬,因此,六七百年留下了大量的卷本,其版本有手抄本、印刷本(包括木刻、石印、铅字排印本),而尤以手抄本为多。”[2]从明清直到民国后期,无论木刻、石印还是铅字印刷都无法替代大量手抄本宝卷的存在。即使活字印刷出现后,用手抄仍然是宝卷传播的主要形式,甚至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北方农村依然有抄写宝卷的行为。正因为“明代抄书成风,抄本广泛流行,才为书坊主购买并刊刻抄本提供了可能”[3]。手抄宝卷的存在为后来刊刻宝卷提供了素材和物质基础。
西游宝卷最重要的接受群体是“抄录者”,他们既是宝卷的接受者又是如今可见最为庞大的宝卷传播者,传抄者有奉佛弟子、宣卷艺人和普通民众。现存最早以“宝卷”命名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金碧抄本是由蒙古人脱脱氏于元代(公元1372年)抄录,原为郑振铎收藏,现藏北京图书馆。佛教徒以抄写经卷为功德,题识“弟子脱脱氏施舍”,意即本卷是作“功德”施舍的。脱脱氏算是最早抄录宝卷的人。
最初宝卷抄写者不署姓名、籍贯、年代,因此信息很难确定。到了清代及近现代,民间宝卷抄录者才有了个别信息。江浙民间宣卷艺人使用的宝卷,绝大多数为师徒传抄,也有个别奉佛弟子编写、抄录或供个人阅读,或送宣卷人去“宣扬”。
清代因《西游记》小说问世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遂出现许多有关西游故事的手抄宝卷。手抄本又分新中国成立前繁体字手抄本和当代简体字手抄本,其中繁体字抄本较多。这些抄本有的只有姓名,如《西游记宝卷》士洪抄本、《唐僧宝卷》屈文斌抄本二种、《陈光蕊宝卷》吴介人抄本、《江流宝卷》秦敬昌抄本、《丝绦宝卷》周焕文抄本、《新编说唱沉香太子全传》许如来抄本、《天仙宝卷》周俊德抄本和许锦斋抄本、《家堂宝卷》金仰贤抄本、《赴任受灾》顾仁美抄本、《西藏宝卷》丁财宝抄本、《唐王游地狱》王玉兴抄本、《翠莲宝卷》陆根汝抄本。有的抄本则包括抄录者姓名、字号、书斋、书坊名或地名,如《佛说八牛宝赞》大同县工石金村赵德雷记、《真经宝卷》尼禅悦尚古堂抄经弟子江润兴抄录、《江流宝卷》辛酉香溪山人抄本和吴邑居士殷鹤泉抄录、《佛说江流和尚生天宝卷》五福堂记抄本、《增补双熊梦十五贯宝卷》积善堂抄本、《刘全进瓜宝卷》甘肃山丹抄本、《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甘肃山丹抄本、《唐王游地狱宝卷》甘肃张掖新抄本、《陈子春恩怨宝卷》南丰永联村陆文淦己卯年抄本等。
苏州戏曲博物馆所藏《江流宝卷》,又名《唐僧宝卷》《江流子宝卷》《谋官夺印》《唐僧出世》, 有十四个手抄版本[4],包括殷鹤泉抄本、翁汉庭抄本、戴云祥抄本、顾峻山抄本、金芝田抄本、李超然抄本、吴家琛抄本、徐敬记抄本、周梓祥抄本、沈少梅抄本等。手抄本的存在为西游宝卷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是西游接受史中民间参与度极高的传播方式。
据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统计,目前海内外公私藏元末明初以来的宝卷约一千五百多种,版本约五千余种。除了手抄本,其他多为木刻本、石刻本或铅印本。按照版本可以将宝卷分为刊本、重刊本、刻本、手抄本等,其中刊本、重刊本以官府刻印机构为主,而刻本则以私人印书房为主。最初宝卷刊刻以内经厂木刻本为主,也就是官刻本。
从明中叶罗清创立“五部经”到清康熙年间,民间秘密宗教发扬壮大,以罗清“五部经”为例,“自明正德四年首次刊刻以后,直至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共刊印了十八次,再加上尚无法确认具体年代的翻刻本,共有二十余种之多”[5]。民间秘密宗教的兴盛最初与皇权支持密不可分,正德皇帝即明武宗朱厚照笃信佛教,自称“大庆法王西觉道圆明自在大定丰盛佛”,嘉靖皇帝朱厚熜更是迷信方士、尊崇道教,这就使教派宝卷的大行其道得到了最高政权的庇护。宝卷刊刻繁盛一时,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印制精美,装帧考究,与佛教典籍不相上下。明朝内经厂造版印制的教派宝卷刊刻精良,印制精美,装帧华丽,与佛经相似多为经折装,一般人难以辨别真伪。
许多后起的教门组织如西大乘教、黄天教、弘阳教、圆顿教、还源教等,也竞相攀附上层社会,因而得到朝中权贵、太监、公主的资助,拥有丰厚的资金得以在内经厂刊印宝卷。“明朝万历年间,是中国民间宗教史上颇引人注目的时期,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诸种民间教派蜂起,印经造卷也最为活跃。”[6]有的教门领袖本身因传教敛财致富,也常常出资刊印宝卷。从无为教“五部六册”到弘阳教“五部经”,再到还源教“六部六册”,无论是真官刻,还是伪官版,都极大地拓展了民间秘密宗教的传播范围与密度,民间宗教在借助庙堂之力宣扬圣威的同时也传播了自己的教义,达到了颂圣与宣教的双重目的。
除了手抄本和官刻本,宝卷还存在大量坊刻本。“坊刻就是由各种非政府的专门刻书机构,如刻经铺等来完成刻印的一种形式。”[7]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指出,“在政府刻书、私人刻书和书坊刻书三大系统中,坊刻不仅兴起最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而且影响最大。官刻和私刻就是在坊刻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8]。据缪永禾统计明代坊刻共有400余家[9],这些坊刻机构大多集中在北京、南京、苏州、杭州、上海等地。
明清时期宝卷的刻印除了内经厂即官刻以外,主要是坊刻和私刻,包括善书铺(善房)、经坊(房)、书坊、书店等,它们有的有教团背景以期兴教纳众,有的是商人身份追求经济利益,有的只是私人刻印渴望祈福禳灾,但都对宝卷的刊刻做出了贡献。为了适应民间秘密宗教的发展,很多善书铺、经坊、书坊都专门刊印和出售过宝卷。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统计清代有刻书记录的书坊三十一家[10],张祎琛《清代善书的刊刻与传播》统计有刻书记录的书坊至少还有三十余家[11],而这些书坊中一半以上都刻印善书。而同治至民国期间,仅长沙、湘潭、常德等地就有三十多家善堂刻善书,其中不乏宝卷刊刻[12]。可见善书与宝卷刊刻、传播已成为明清至民国时期重要的宗教信仰活动。
二、装帧与版画
装帧与版画是宝卷的重要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早期教派宝卷装帧与佛经极为相似,封皮继承佛经梵夹装的形式,封面与封底由硬纸板制成,表面蒙以染色布料或绫罗绸缎,封皮以泥金字签写书名,正文皆由整张长幅的纸张折叠而成,形制庄重。如《混元弘阳临凡飘高经》明万历刻本,白棉纸印本,封面用上等花纹织锦装饰,书签为泥金印于瓷青纸之上,开本宏阔,字体镌刻工致,点划斩方,笔划舒展,每册经卷皆有大量整版版画,版画镌刻极为精整,题材各异。明初到嘉靖隆庆书籍的装订一直流行包背装,至万历始广泛使用线装形式。线装书工艺简易,节约纸张,降低成本。
纵观前期教派宝卷版画,主要包括宗教图像、护道龙牌、情节插图、杂宝纹饰及人物绣像等。前期宝卷扉画以宗教人物图像、龙牌为主,后期民间宝卷则以人物绣像为主。
明清教派宝卷扉画多为宗教图像,内容以佛教、道教人物为主,卷首有群佛朝拜版画,并有三面护道龙牌,有的卷末有无字书牌或莲花牌记,以示庄严。宝卷中版画以情节插图为主。配图形式包括上图下文、下图上文、单叶全图,也包括右上图文并茂、右下图文并茂、左上图文并茂、左下图文并茂等。
《混元弘阳临凡飘高经》明万历刻本,卷下“取旃檀临凡送经取经遇弘阳法普度众生作证品第二十四”出现了一幅有关《西游记》的版画(图1)。其中猪八戒、圣者、白马栩栩如生,另外三位僧人,穿袈裟者应为旃檀老祖,老祖三次临凡,右下角应为第一次转化的荷担僧,牵马者应为第二次转化的唐僧。与小说内容有所不同。

图1 《混元弘阳临凡飘高经》明万历刻本
除了情节插图,早期教派宝卷留白处还有很多杂宝纹饰,杂宝纹又称多宝纹,《中国美术大辞典》将杂宝纹定义为:“瓷器的传统装饰纹样之一……所取宝物形象较多,元代有双角、银锭、犀角、火珠、火焰、火轮、法螺、珊瑚、双钱等,明代又新增祥云、灵芝、方胜、艾叶、卷书、笔、磬、鼎、葫芦等。”[13]“吉祥纹在元代已经出现,流行于明代。题材主要有多宝、送子图等寓意吉祥的图案。其中以多宝纹最常见,它由双角、方胜、宝珠、银锭、书卷、宝钱等组成。”[14]前期教派宝卷中多宝纹最为常见,虽与内容关联不大,但种类繁多,触目即是,造型独特,意蕴深远,增加了宝卷的神秘性和仪式感,详见表1。

表1 明清教派宝卷杂宝纹饰
宝卷是三教合一的产物,既有佛教教理又有道教思想和儒家精义,因此宝卷纹饰既有佛教吉祥法器,如法轮、法螺、宝瓶、如意、珊瑚、金鱼等,又杂糅了道教太极图、葫芦、拂尘、拍板、莲花,还有儒家推崇的书籍、画卷、艾叶等清雅之物。这些图案寓意深刻,“莲花”寓“出于浊世而无所染”;“宝瓶”即插花净瓶,有“圆满无漏”之义;“金鱼”有“活泼解脱”之义;“海螺”也称“法螺”,佛教法器,据说能吹出“妙音吉祥”;“蝙蝠”寓意“遍福”。最为典型的是火焰珠纹,图像变化丰富,出现频率极高,“火焰龙珠纹已不是某种单一文化的象征,而是兼具了已经深植于中华文明中的儒、佛、道三教思想,成为能够为社会广大阶层均能接受的一种文化符号……最终作为佛修心、道养身、儒治世三教合一思想的体现”[15]。火焰珠纹不仅在瓷器、壁画、金属器物、石刻、服饰上大量存在,也是教派宝卷经常使用的宗教符号。此外还有组合形,如金铤、方胜、钱币、艾叶、荷花等各类杂宝系以绶带。这些杂宝纹饰有的出现在曲调名或佛偈下,有的则随意散置,貌似没有实际意义,但它们却以世俗吉祥物的方式传达出民间宗教的庄重性和神秘感。
人物绣像有单独绣像,如《梁皇宝卷》,也有群像,如《绘图唐僧宝卷》(图2)。这些人物配图均为宝卷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次要人物无有涉及。

图2 《绘图唐僧宝卷》民国,惜阴书局石印本
三、募捐与销售
宝卷刊刻是一个复杂艰辛的过程,从募捐集资到开板印刷,再到销售分发,不仅要说服受众集资捐款,又要布施分发教化民众,既要印制精良吸引读者,还要占领市场防止盗版。
早期教派宝卷获得王公贵族的倾囊相助,但随着政府的镇压和受众的下延,中下层民众成为宝卷最大的接受者和刊版宝卷的集资者,他们是佛道弟子和宣卷人募捐的主要对象,因此说服受众捐资刻印就成为宝卷传播的重要举措和手段。宝卷募捐对象不受限制,善男信女均可捐款,数额无论多寡,尽力而行。《三祖行脚因由宝卷》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刻本,由信士周丙、朱和敬募重刊。资助银钱有十八元、三元、二元、一元、五百文不等。每字刻工一文六毫,共付刻工钱四十八千文,余钱五千一百文,印送二十五部,计钱六千文,无名氏敬印十部。实在无钱,也可以听受、诵读、抄写的方式代替,都被视为积聚功德的行为。
针对不同的对象,募捐的方式又有所不同,具体包括:现世果报型、开门见山型、典型案例型、循循善诱型。
(1)现世果报型。这是宝卷募捐最常见的办法。宝卷产生伊始,宗教人士与信众一般认为宣卷是积累功德的一种方式,以成书年代较早的《护国佑民伏魔宝卷》为例:“满宅内,毫光现,普降吉祥。有病人,宣宝卷,灾除病退。无子人,宣宝卷,定得儿郎,买卖人,宣宝卷,无阻无碍。万事通,都称意,本利还乡。伏魔卷,功德大,无边利益。又增福,又增寿,又灭灾殃。宅内供,伏魔卷,邪魔不入。”
《消灾延寿阎王卷》:“捐资重刊广传者,上奏准世世荣显报;遇灾难印传者,逢凶化吉;病者印传,愈疴疾而得长生;夫妇至戚不相和睦,子孙不肖,肯印传者,均能亲受改过。”
《因果宝卷》:“尔大众将此诸说刊布刻传,务使人人晓悟。若有能以善书传一人者,当十善;传十人者,当百善;传大富贵大豪杰者,当千善;捐貲重刻,广布无穷者,万万善。世人果能文相劝勉,吾必将众等公德保奏天庭,则生生世世,永获福禄无涯矣。”
这些带有募捐、集资、祈福性质的募捐方式能够满足人们的世俗要求和实用心理,具有强烈的劝善积德观念和现世报应思想。捐款布施形式不拘、数额不限,有捐钱有捐物,有的几文钱,有的数百两,但均能趋福避祸,无一不规劝身处现世的民众以募捐、刊印、抄写、传播宝卷,以及信佛、行善来获取福报。
(2)开门见山型。这种方式利用民众的鬼神信仰,以替神代言的方式直接向民众募捐,宣扬为来世修行,获取彼岸世界的功德。
《二郎宝卷》:“因为老爷经一部,留下恐怕功不成。钱粮浩大难刻板,普化十方众善人。有法无财难成事,同共发心助一功。舍财如意修来世,老爷保佑不亏人。多增福来多增寿,保佑子子与孙孙。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刻下经板,流传在北京。妙道一部经,刻板少金银。单等源来客,宝卷才完成。”
《护国佑民伏魔宝卷》:“诸大众,为伏魔,有缘有分。众打夥,舍资财,结果完成。休说道,舍资财,妄求福利。开下板,造下经,留在北京。普天下,人请经,家中宣看。”
这类宝卷以神佛的名义,向民众直言舍资或布施,开门见山,目的明确。
(3)典型案例型。这种方式以受众身边的具体施财者为案例,增强说服效果,扩大营销范围。
《泰山真经》:“你看施财老长者,独自刊板在北京。不用他人钱一文,自己要把功果成。……长者发心如意舍财,多亏女裙钗,二人共同。同把板开,同受福禄,同坐莲台,同生净土。同伴佛如来。夫妇共一心,施财留经文。娘娘来加护,准定得子孙。”这种方式以董家三口人舍资助刊终得福报为例,有强烈的说服力,获得受众认同心理,达到募化的效果。
(4)循循善诱型。有些宝卷或以出版商的身份,或以宣卷人的口吻对该卷进行简单介绍,劝人请经刻印施送。
如《三茅真君宣化度世宝卷》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苏州元妙观得见斋重刻本,牌记左边题:“此卷字字朴实,苦心点化,乃有益世道之书,凡烧香信士,务要多请几本回去,传送四方亲友,时时宣诵,则烧香功德,格外加倍”。右边题字:“请此卷者必须十分敬重,将新布包好,清香供奉,可以驱邪、镇宅、发福、消灾。”以驱邪、镇宅、发福、消灾等福报作为劝导善信广印广施的诱因。
募捐与集资是宝卷刻印的重要方式,带有鲜明的民间自发性与自为性,不仅见证了古代印刷行业的进步,也推动了古代慈善事业的发展。
宝卷既有商品价值又有宗教价值,宝卷的流通形式有盈利与非盈利之别。非盈利的宝卷印行多采用集资助刊、免费发放或布施的流通方式,这种流通方式有着明确的规定,有“宝卷流通八法”与“宝卷流通十三则”。宝卷刊印开始是以宗教性质的祈福积德为号召,但随着近代石印技术的发达,印制宝卷逐渐成为商人逐利趋新的工具,宗教化走向商品化,非盈利性与盈利性共生。民国期间出版商大量印制强调劝善惩恶的宝卷,使宝卷流通增添了商业色彩。为了促进销售,宝卷刻印时会使用序跋、凡例、广告、药方等方式,或增加作品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或引起受众的重视和兴趣,或具有实际的急救功效。
序跋。宝卷刊印时,编著者会延请他人作序或跋,以此增加作品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这些序跋的作者,或文化素养较高,或社会地位颇尊,或亲历宝卷功效。他们对于宝卷的评价会引起受众的重视和兴趣,从而影响其阅读和购买行为。所以序跋的写作在宝卷传播过程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凡例。《普静如来钥匙佛宝卷》凡例中有这样的规定:“凡普济教徒有请钥匙宝卷者须布施洋二元,有请皇极卷者须布施洋一元。凡普济教徒每人有代请钥匙宝卷五百部者赐一三代宗亲排位一座,代请皇极卷一千部者赐一三代宗亲排位一座,如有发愿布施大洋五百元者亦赐一三代宗亲排位一座。”
广告。民国期间宝卷刊印数量巨大,刻印机构层出不穷,为了充分占领市场,各书局、书店纷纷登载广告扩大销量。如上海惜阴书局《金凤宝卷》卷末附书局广告:“惜阴书局经售各种戏剧图考、唱戏指南、南腔北调、谜语集成。各种袖珍足本武侠小说、连环图画、苏杭宝卷、淮扬唱本、笑话大王,各数十种至三百种,名目繁多,不克备载。备有目录,函索即寄。出版部地址:闸北顺徵路天保里西便是。”
药方。为了提高宝卷的实用性,有时也会在宝卷末尾附加药方,以应百姓不时之需。《清源宝卷》旧刻本,对自缢、溺水、中毒、中暑、难产、咳嗽、痢疾、胃病等急难杂症均有详细的对症药方和禁忌。在封建社会医疗水平不够发达的农村,这无疑是最为便捷又行之有效的促销手段。
序跋、凡例、广告、药方的使用丰富了宝卷的刊刻形式,更扩大了宝卷的传播范围,增加了宝卷的消费群体,为近代印刷史做出贡献。
宝卷是中国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游记》则是民间宝卷最大的语料库。从西北到华北,从河西走廊到江浙一带都有许多与西游故事相关的民间宝卷。而西游故事与说唱文学原本就是相互存在的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文化资源,明清民国时期西游宝卷的刊刻与传播表现出抄本与刻本平分秋色的态势。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宝卷从最初的木刻经折装到木刻线装再到石印平装,装订方式的变迁不仅大大降低了宝卷刻印的成本,也扩大了受众持有率,曾经宝相庄严、刻印精美的经折装被线装本、石印本替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娱乐性代替了宗教性,世俗化取代了神圣化。手抄本从明清到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持续存在,多以繁体楷书存世,数量繁多,版本各异。由于宝卷特殊的宗教性、娱乐性、商业性,使宝卷在传播与流通过程中盈利与非盈利同时存在。一方面通过寺庙、善书局、乡会广为捐赠布施,另一方面书坊、书局、书店又将其作为盈利工具大行刊印,但都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促进了宝卷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