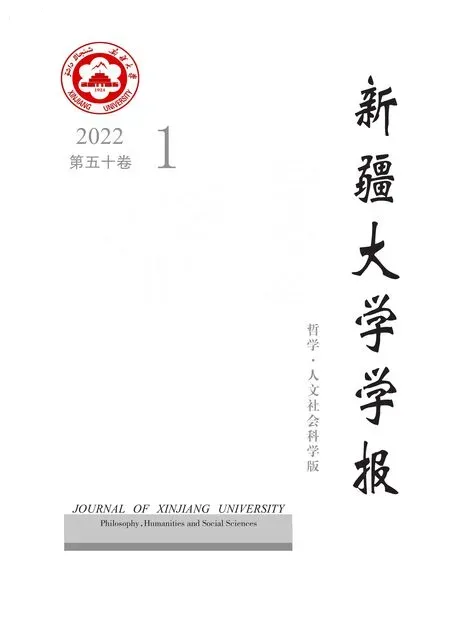巴阿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区为何冲突频发?*
张 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问题的提出
“部落”与英文“Tribe”对应,指依赖血缘和亲缘关系而组织集体生产和生活的团体。在南亚国家,具有部落组织形态的地区的安全形势往往存在着不稳定性。那么,部落地区为何冲突频发?
冲突指发生在同一空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之间相互竞争、争斗、对抗的过程。按照拉尔夫·达伦多夫的“烈度”和“强度”指标,本文所指冲突是带有暴力行动特征的烈度最高的对抗形态,在强度上呈现不同维度。国外学术界对于部落社会生态以何种因果路径促发地区冲突一直缺乏系统解释框架。欧美学术界常将部落地区看作是失序的非文明体系和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带有明显价值观偏向。国内学术界关于南亚部落问题研究着墨不多。
本文将以分析内生性成因为重点,试探讨整体性解释部落地区为何冲突频发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选取巴阿边境地区作为案例,“杜兰线”两侧生活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部落群体——普什图人。19世纪以来,普什图部落地区接连发生或被卷入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继承人战争(集中于1773—1842年)、三次阿富汗反英战争(1839—1842年、1878—1881年、1919—1921年)、英印边境部落地区反英斗争(1849—1900年)、暴力普什图尼斯坦运动(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1979—1989年)、阿富汗内战(1992—2001年)、阿富汗反恐战争期间的巴阿边境动乱(2001—2021年)等事件。①普什图尼斯坦运动有两个支流,一是阿卜杜·加法尔·汗及其后人领导的温和主义政党运动,二是地方毛拉伊皮法齐尔发动的普什图部落区的暴力斗争。参照冲突的定义,这里特指普什图部落区暴力斗争。普什图人在其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当前中巴经济走廊正拓展为中巴阿三方合作,对巴阿边境部落地区安全进行评估,对于防范海外投资风险有现实意义。
判别内生性成因的关键指标是指该因素应是独立导致暴力冲突发生的充分条件。本文将推动主体行为发生的内生性成因界定为“重要的需要”,借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重要的需要”分解为权力、认同、安全、财富四项。②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行为动机分解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参见〔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30页。同时,当研究权力、认同、安全、财富四项内生性成因与部落地区冲突之间的联系性时,需要界定因果关系在何种群体层面上进行讨论。因此,有必要首先对部落研究话题所涉及的族类群体概念进行界定。
二、“部落”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部落”及其相关概念的辨析,需要从“民族”概念的界定出发。“民族”的汉语意义一度兼具“Ethnic Group”与“Nation”之义,对“部落”概念造成了影响。随着当代欧美政治实践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英文中“Ethnic Group”与“Nation”有了明确区分。“Nation”指代主权性群体,“Ethnic Group”指不具备政治属性的族类社会群体。国内学术界采用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提出的“国族”一词,专门与英文“Nation”对照,恢复了“民族”与“Ethnic Group”的对应。目前学术界公认“部落”已经具备“民族”(Ethnic Group)的基本特征,并逐步放弃使用“部族”进行部落相关话题的研究,统一使用“部落”。氏族(Clan)则是部落的基本构成单位。
嵌套(Nesting)是部落群体的基本组织形态,即多个家庭形成氏族,氏族(或包含胞族层级)构成部落,多个部落组成的部落群被外界识别为某个民族(或其中一部分)。①这里指核心家庭,即只包括父母和未成年子女的小家庭,并非扩展家庭的概念,下同。如果该民族具备建立政治实体的条件,可被称为国族。本文强调“部落群”(Tribes)概念。“部落群”是对多个亲缘性或地缘性较强的部落构成的大群体统称,可能是部落间的松散组织或带有军事联合性质的联盟(Tribal Confederacy)。
按照上述概念对普什图人进行描述,应称其为普什图部落群。巴阿边境的普什图部落群分为四个部分:一是阿布达里(Abadli)/杜兰尼(Durrani)部落群,包括波帕尔扎(Popalzai)、巴拉克扎(Barakzai)、阿里克扎(Alikozai)、阿查克扎(Achekzai)等部落;二是吉尔扎(Ghilzai)/加尔吉(Ghalji)部落群,包括霍塔基(Hotaki)、卡洛蒂(Kharoti)、纳西尔里(Nasiri)、苏莱曼(Sulaiman)等部落;三是以白沙瓦谷地为中心的部落群,指巴基斯坦境内的优素福扎(Yusufzai)部落;四是山地普什图部落群,如阿弗里迪(Afridi)、瓦济尔(Wazir)、马苏德(Masud)、谢兰尼(Sherani)、莫赫曼德(Mohmand)等部落。普什图人与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其他民族组成国家,曾建立阿富汗杜兰尼王朝。②菲利克斯·格罗斯将国家分为两种类型——公民国家和部落国家(译著译为部族国家),后者保留了传统部落集合体的遗留。阿富汗杜兰尼王朝即是部落国家的典型代表。这是本文要将阿富汗王朝继承人战争和阿富汗作为国家行为体的三次反英斗争纳入部落地区冲突的原因,其可被看作普什图部落群的内部冲突,以及普什图部落群与英国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参见〔美〕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王建娥、魏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三、中心假设与论证
(一)关于社群结构视角的假定
部落相关群体的组织具有嵌套特征,权力、认同、安全、财富四项内生性成因在决定主体暴力行为时,会以群体层次结构的约束性为前提。部落相关群体的结构指的是群体的层次性、构成每一层级系统的单元的排列定位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因为树敌是冲突关系成立的前提,构成社群中每一层级系统的单元定位和单元间的相互关系不同,敌手认定的情形就会不同。
我们通过普什图人的组织结构来探讨,并将其与俾路支人对比。普什图人群体结构具有多重层级,群体规模按从小至大进行排列依次为家庭、氏族、部落、部落群(部落群形成民族)。
在家庭层级,普什图人是父权制家庭形式,内部关系呈现等级制特征,家庭系统稳定性较强。俾路支人也如此。在氏族层级,普什图人遵循父系血缘关系,在氏族领袖的选择方式上遵循完全的自由竞争制。俾路支人也以父系血缘确定氏族网络,但以长子继承制为基础选择氏族领袖。因此在普什图人氏族内部,家庭之间(即有资格的成年男子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俾路支人氏族内部关系稳定。在部落层级,普什图人的自由竞争原则仍然适用于部落领导人的选择,同时领袖的地位除了来自他自己的宗谱关系和实力外,还须说服本氏族成员和其他氏族服从。俾路支部落领袖在实力最强的核心氏族中选择,遵从父系权威基础上的大致顺序继承,且部落成员的集体服从意识强。因此,普什图部落是自下而上的结构,俾路支部落是自上而下的结构。在部落群层级,普什图各部落内部奉行平等原则,部落首领的选择需要经历自由竞争与民主选举的过程,各部落首领对其部落难以保持长久领导,也就更别提进行有效的部落间合作了。俾路支部落首领对所在部落有严格控制,各自独立,不接受超越其权威之上的领导,无法形成超部落组织。普什图与俾路支部落群内部都呈现派系主义(Factionalism)特征,部落之间的关系不稳定。①See Henry Rosenfeld.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Military in the Process of State Formation in the Arabian Desert,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65,Vol.95,Iss.2,p.174.
综上,普什图人在家庭层级呈现等级制,在氏族、部落、部落群三个层级呈现平等主义特征;俾路支人在家庭、氏族、部落三个层级呈现等级制特征,在部落群层级呈现派系主义特征(图1)。俾路支人容易出现以部落为中心的集团化的对立对抗模式,表现为部落与他者之间的冲突,部落内部相对稳固。普什图人呈现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体化对立对抗模式,表现为家庭中的成年男子(或其松散联合)与他者(成年男子、氏族、部落、其他民族、非本国族)之间的冲突。

图1 普什图部落社群结构(上)与俾路支部落社群结构(下)比较
普什图人的这种个体化对立对抗模式导致普什图部落地区所发生的典型冲突有其发生规律,可归结为三种类别:一是同一民族内部(如氏族内部、氏族之间、部落之间)的冲突,包括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的王位竞夺导致的波帕尔扎部落萨多扎氏族内部矛盾、巴拉克扎部落穆罕默德扎氏族内部矛盾、波帕尔扎部落与巴拉克扎部落之间的矛盾,以及阿布达里/杜兰尼部落群与其他普什图部落之间的冲突;抗英、抗苏战争时期普什图部落群的内部矛盾。二是部落群构成的民族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之内的其他民族,或者与带有其他民族背景的中央执政者之间的冲突。例如,边境普什图人与巴联邦政府之间的矛盾;普什图部落群对抗塔吉克和乌兹别克军阀。三是部落群构成的民族与同一政治共同体外的其他群体(非本国族)之间的冲突。例如,普什图部落群的抗英、抗苏和反美运动。这里的集团对抗可看作是普什图人松散的联合体与他者之间的对抗,他们在其集团内保持自主性。我们将阐述部落地区冲突的内生性成因来对社群结构视角做进一步说明。
(二)巴阿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区冲突的内生性成因探讨
1.权力逻辑
权力指精英人物(部落相关群体中的领袖、潜在的领袖竞争者、宗教权威)改变其他行为体的行为或控制事物发展的结果而施加的影响或施加影响的能力。一般有两种情形:
一是来自抱负和野心的驱动,即精英人物主动地争夺权力或试图对权力分配实施影响。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继承人战争、第一次阿富汗战争和第二次阿富汗战争中惨烈的王权争夺是典型例证。阿赫迈德·沙去世后,王朝陷入激烈的继承人战争。波帕尔扎部落萨多扎氏族出现内讧,争权主要在阿赫迈德·沙的两个儿子之间,以及四个孙子之间展开。由于王权部落与其他部落有广泛政治联姻,权力争夺过程伴随阿布达里/杜兰尼部落群与其他普什图部落之间的斗争。舒贾复辟后,遭到以巴拉克扎部落为代表的阿布达里/杜兰尼部落群以及其他普什图部落群的反对。多斯特·穆罕默德重新登上王位后,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孙辈陷入王位争夺战。这些竞争主要表现为普什图民族内部(如氏族内部、氏族之间、部落之间)的冲突。
二是来自对自身地位的关切,即遭到外部威胁或侵夺时,精英人物为预防和阻止权力的受损或丧失而实施防御性或报复性活动。此种情形突出地表现为民族群体对民族外的他者的抵抗。普什图各部落、氏族首领(包括阿富汗王权代表人物)、宗教权威与外国政府之间曾发生数次激烈冲突,因为这些外部入侵行动对当地精英人物的原有权力形成挑战,并且殖民主义侵略、强权政治统治、新社会治理模式引入将引发部落权力结构的裂隙或解体。例如,阿克巴·汗领导阿富汗民众起义赶走了英印军队,助其父亲重新上位;第二次阿富汗战争中,希尔·阿里及其两个儿子领导巴拉克扎部落与英国殖民主义者抗争;阿曼努拉·汗发起第三次阿富汗战争,保护巴拉克扎部落王权。在阿富汗抗苏、反美运动中,普什图各部落、氏族首领以及当地毛拉为维护传统部落秩序抗击外来侵略者。
社群内部的精英可能是阵营化的,在存在高度竞争关系的群体内,获得成员个体的支持对增进精英人物的权力至关重要。因此发起抗争行为是加强在社群内部资源累积和权力集中的手段。这在“民主化”特征突出的普什图部落内部表现明显。在部落内部,部落首领的权威来源于氏族成员的支持,被称作“势”,展示和增进“势”的方法之一是发起冲突,如原部落首领向其他部落宣战以加强对本部落的统治、部落首领的潜在竞争者(氏族首领)发动本氏族力量对抗其他氏族以显示自己的声望和能力。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普什图氏族内部,如在杜兰尼王朝王位争夺战中,波帕尔扎部落萨多扎氏族内部、巴拉克扎部落穆罕默德扎氏族内部的亲兄弟、堂兄弟之间的冲突。
2.认同逻辑
认同对冲突行为发生与发展的影响机理是:第一,认同使得个体成员相对于周遭社会关系的同一性保持着稳定。当同一性遭破坏时,个体会实施应激性行为(包括暴力)。第二,认同的塑造是社会比较过程,个体在对比中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群体,导致内群偏私行为。第三,群体认同可能引发情境性从众行为。
普什图人的认同基于个体,以成年男子投诚的某个上级权威为中心形成从属性(即组成小团体“Qawm”),①“Qawm”是研究普什图社会的重要概念。它的本义是“稳固团体”,指具有共同基础的统一行动单位,可以指代任何一种普什图群体的组织性团结。它的核心关系是从属与庇护,即一位团体领袖保护其成员不受团体外的他者侵犯,成员民主地推举这位领袖并服从他的指挥,类似于中文“圈子”。See Afghanistan Research Reachback Center.My Cousin's Enemy is My Friend:A Study of Pashtun“Tribes”in Afghanistan,Fort Leaven Worth:KS,2009,p.8.但仍然保持相当程度的个人独立,这体现在投诚对象的可更换性上。他们围绕着认同中心,与其他内群成员一起参与集体行动,包括暴力行为。普什图人对超部落组织缺乏认同感,阿赫马德·沙凭借强人政治促进超部落组织的构建,但他去世后乱局不断,波帕尔扎部落与巴拉克扎部落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普什图人部落联盟认同感的缺失。
普什图部落之间会借助共同文化原则作为暂时的认同纽带,包括民族独立统一思想和伊斯兰教。在阿富汗的三次抗英战争中,保持普什图人的独立、免遭外族蹂躏,是各部落共同参与抵抗运动的目标之一。普什图尼斯坦运动中山地普什图各部落民众在宗教权威伊皮法齐尔的鼓动下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暴力袭击巴基斯坦驻军。普什图各部落的抗苏战争、在阿富汗内战中与塔吉克人等的较量,以及反恐战争期间的抗美运动,也是团结在维护普什图人的主导地位和圣战的旗帜下。然而,与其说是对民族统一的忠诚和对宗教的虔诚带动了部落联合,不如说是普什图人在个体化的社群结构中、基于对个人独立的重视所导致的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感和对外来干预的反感,促使他们接受了号召。部落联盟认同的虚弱性依然暴露,比如第一次阿富汗战争中波帕尔扎部落与巴拉克扎部落之间的冲突;1897年部落区反英斗争中山地和白沙瓦谷地普什图部落群的内部关系、国王阿布杜·拉赫曼·汗为代表的阿布达里/杜兰尼部落群与他们的矛盾;抗苏战争中阿布达里/杜兰尼部落群与吉尔扎/加尔吉部落群之间的矛盾。
3.安全逻辑
安全,指狭义人身安全概念,即免于暴力造成的肉体伤害。将安全拆分为四个方面,即主体、客体、不安全的来源、维护安全的方法,那么可表述为主体使用某些方法保护客体不受不安全来源的影响。②See Yejun Wu,Fansong Meng.Categorizing Security for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2018,Vol.11,Iss.4,p.77.普什图人为什么常常采取暴力手段(消极安全方法)实现人身保障?
第一,部落相关群体是未过渡至现代国家或完全融入现代国家体系的人的集合体,没有将保护生命的事务交给专职他者。部落群体的生存环境易受外来致命性打击,在部落各自为政、结盟不易的普什图社会,单个部落对实现其首要功能即保障成员人身安全更加重视。当外部挑战出现时,部落成员的安全敏感度更为显著。
第二,普什图人的部落结构特征让其对安全有特殊理解。普什图人部落、氏族内部派系特征突出,依靠分裂敌对(Segmentary Opposition)原则维持部落、氏族内的关系平衡。例如,氏族内近亲间形成两大对抗集团“杜拉”(Dulla),成员可根据情势变化随时改变站队,通过集团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实现集团和氏族整体的安全。但是,这容易诱发部落、氏族内部的冲突。
第三,血缘是维持部落社会存在的纽带。大量至亲死亡意味着族亲网络消失,部落社会也失去了发展基础。血缘的纽带关系让亲属之间不愿意看到彼此受外来他者伤害,将个体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视为集体事务,常常以集体行动解决纠纷。普什图人的群聚结构是按照父系血缘构成地理分布,对集体安全的高度依赖性和广泛参与性提高了其被卷入暴力冲突的机率和冲突强度。危急时,即使是崇尚内部竞争和个人主义的普什图人也会牺牲个体安全来保全集体延续性。普什图人只有在战争时才会和平,①See Charles Lindholm.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a Tribal Society:Swat District,NWFP,Pakistan,Asian Survey,1979,Vol.19,Iss.5,p.485.说的并非普什图人实现了和平,而是出于集体需要将暴力冲突焦点转移至外部。这反映在他们的抗英、抗苏、抗美斗争中。
4.财富逻辑
导致冲突的财富动机有:维持生存必需实施捕食行为、因经济掠夺或剥削引发反抗。普什图人基于财富动因发生的暴力冲突表现为成年男子个人(或其松散联合)与他者之间的经济纠纷。
劫掠是山地普什图人地区出现暴力冲突的一大诱因。在瓦济里斯坦,马苏德男子有打劫商旅和城镇居民的传统,而以经商为生的瓦济尔男子是受害者。当英印政府拓展疆土至此时,马苏德男子将英国商人和士兵纳为劫掠对象,他们还认为获得英方丰厚津贴的捷径是要展示他们的讨厌,②See Milan Hauner.One Man against the Empire:The Faqir of Ipi and the British in Central Asia on the Eve of and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981,Vol.16,p.187.引发了与英国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吉尔扎/加尔吉部落群的成年男子也有克扣买路钱的习惯。当过境抵达喀布尔的英国人改变主意削减这笔原本支出时,吉尔扎/加尔吉人在英军撤离喀布尔途中杀戮了大量士兵及其家眷。
在部落地区,部落、氏族首领和核心血缘氏族的成年男性占据大量土地,土地所有权属及其赋税收入是男子的经济权益。英国入侵阿富汗期间,大批土地所有者因拒绝向英印政府缴纳重税而失去土地。优素福扎部落的氏族首领纳比·阿米努拉·汗·洛伽尔参加了第一次阿富汗战争,成为抵抗运动的重要领袖。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执政期间对农村的土地改革引发了普什图人的激烈反抗,成为他们参加抗苏战争的强大驱动力。普什图人社群结构的自由竞争性也在土地权益争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父亲的土地继承权进行分配时,他的儿子X和Y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依次类推X的儿子a和b之间、Y的儿子c和d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a和c、b和d可能分别结盟形成杜拉以争取优势,土地权益分配让近亲出现集团对抗,使a和d、b和c之间产生“塔伯(Tarbur)之争”。③See Joshua Foust,Nathan Hamm.Afghan Tribal Structure Versus Iraqi Tribal Structure,Cultural Knowledge Report by Human Terrain System-Research Reachback Center,2008,September 26,p.222,网址:https://info.publicintelligence.net/USArmy-AfghanTribalStructure.pdf,访问日期2021年6月1日。
四、巴阿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区冲突的新样态
社群结构不是孤立的、封闭的体系,社群结构之外的异质力量会试图冲击和进入体系,对原结构产生影响:一是同化,即将结构内的系统或单元发展为同其一样的异质力量。如果异质力量带有暴力特征,这种特性会被复制至被异化的系统或单元身上;二是强化,即深化原结构的层级系统内的单元间互动关系。如果原结构中层级系统内的单元互动关系不稳定,这种矛盾会加剧;三是扭曲,即改变原结构的层级系统关系或系统内的单元间的联系性,但是原结构有其生长周期和发展规律,会抵制异质力量从而形成冲突。
战乱可能造成社群结构出现裂痕、缺损,体系的虚弱正好给异质力量可乘之机。这正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巴阿边境部落地区发生的情景。伊斯兰激进主义力量利用普什图人的宗教信仰(普什图人以正统穆斯林自居),进入在战争中受创的普什图部落体系,使部落地区冲突出现了新样态。
20世纪40年代以来阿富汗伊斯兰宗教政党崛起,政治伊斯兰主义者在人民民主党当权后来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形成以七派联盟为代表的伊斯兰党派组织。巴基斯坦国内的宗教运动团体在伊斯兰化政策刺激下迅速发展。苏联入侵阿富汗成为两国宗教团体相互结合的机会。普什图部落地区民众开展反苏战争后,政治伊斯兰主义者与阿富汗境内的部落社会形成联系,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渗透至部落抗争运动中。美国、沙特、巴基斯坦合作培植穆贾西丁投入抗苏战争,巴国内的宗教政党和学校担负后勤保障责任。从此,伊斯兰激进主义力量开始在巴阿边境部落地区孕育,并逐步进入普什图社群结构,其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同化部落成员,让其思想更加保守、行为更加激进。受部落生存环境、自身功能和内部结构的影响,普什图人常常采取消极安全的方法实现人身保障。虽然方式激烈,但目的是为了保证个体的人身安全和集体血缘的存续。其中,宗教没有终止普什图人的内部或对外冲突,而是让社群结构保持着“冲突的动态均衡”,如通过调节社群内部的集团平衡以防止过度内耗、通过号召一致抵御外部威胁。伊斯兰激进主义力量则将“圣战”概念与普什图瓦里(Pushtunwali)中的激进要素揉搓,怂恿部落群体或个人参与暴力冲突,让其充当满足其特定诉求的工具。
二是强化了普什图社会中以成年男子为中心的个体化冲突模式。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以普什图人所遵循的庇护与从属关系形成新的圈子“Qawm”,利用旧的规则玩新的政治游戏。①See Olivier Roy.Afghanistan:Back to Tribalism or on to Lebanon?,Third World Quarterly,1989,Vol.11,Iss.4,p.74.在抗苏战争时期,伊斯兰党派组织将武器和经费分发作为施展影响力的渠道,与部落民众和地方毛拉建立联系;阿富汗塔利班通过资源分享、群体保护招募部落成员,构建在群体中的“势”。不过小团体建立的新式庇护与从属关系仍然具有易变性。抗苏战争时期阿富汗境内的地方抵抗运动基于利益选择归属于某个伊斯兰党派,有的为了获得更多资源而不断更换门庭;②参见〔哈萨克斯坦〕苏·马·阿基姆别科夫《阿富汗症结与中亚安全问题》,汪金国、杨恕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8页。当前活跃于边境地区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的成员也相互倒戈反叛。因为杜拉策略教导普什图人可根据利益和情势变化随时改变立场。
三是介入部落体系的权力竞夺。早期阿富汗政治伊斯兰主义者与穆萨希班一系国家当权者间的矛盾已经显露出这些竞争者对于传统部落精英把持权力的觊觎。当人民民主党夺权后,这些落败的城市宗教精英迅速填补了阿富汗农村地区部落、氏族首领去世或逃亡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战乱促使大批逃离家园的普什图部落青少年在受到瓦哈比主义和迪欧班迪思想影响的宗教学校和难民营中长大。他们缺乏部落规则的教化,组建阿富汗塔利班取代政治伊斯兰主义者成为新的权力竞争者后,同样不会受制于部落、氏族权威。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极端组织在巴阿边境地区滋生后,伊斯兰激进主义力量与部落首领、长老和宗教人士的矛盾最终公开化。一些极端派伪装成普通毛拉怂恿部落民众参与暴力,不惜杀害部落、氏族首领以逼迫他者就范。穆沙拉夫与普什图部落首领达成和解协议后,极端派借机处置了一批部落首领和长老。③参见〔巴基斯坦〕里亚兹·穆罕默德·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冲突·极端主义·抵制现代性》,曾祥裕、赵超兰、孟雪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第222页。
导致部落地区冲突发生的内生性成因是权力、认同、安全、财富,其因果逻辑是争夺权力、群际认可、人身防御、竞争或保护财富。伊斯兰激进主义力量在促发部落地区冲突上遵循认同逻辑和权力逻辑,在进行群际排异和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伴随人身防御和财富追逐。他们的活动对普什图部落社群结构造成了新影响。以宗教排异为核心特征的暴力活动,以及与部落、氏族领袖进行的权力竞争,使得当前普什图部落地区的冲突已经逐步偏离传统意义上的部落动乱范畴(以单纯的部落、氏族对外或内部冲突为表现形式)。部落、氏族之间的冲突,或者是部落、氏族内部领导人争夺权威的斗争存在,但已不是地区主要矛盾。部落、氏族的传统对外抗争活动,部分与排异活动合流,部分转化为传统领袖反抗激进主义组织夺权。④合流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对区域外的外部政治力量(非本国族)的反抗,如普什图部落群与阿富汗政治伊斯兰主义者共同抗苏;普什图部落群参加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保卫先知教法运动等组织的反美运动;二是反对区域内的其他民族或带有其他民族背景的世俗政权,如普什图部落群加入阿富汗塔利班对抗反塔联盟,普什图部落群加入阿富汗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巴基斯坦塔利班与巴联邦政府的对抗。两者的合作因“共同的敌人”在部落主义、民族解放、宗教排异之间找到了结合点。以上情况使得巴阿边境部落地区冲突复杂化。
五、结论
文章通过对巴阿边境普什图部落社会进行考察,建立了探讨部落地区冲突频发的内生性成因的理论框架。以上结论修正了西方学术界关于部落问题的偏见,即将部落社会看作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伊斯兰激进主义是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热潮和长期大规模战乱背景下蔓延至部落社会而非由部落社会自主产生的,部落地区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保守的社会氛围只是给异质力量的扎根创造了条件。当前巴阿边境的宗教激进主义力量只是组成了网络,但未形成完全取代部落社群结构的社会系统。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与部落社会还处于博弈中,巴阿边境部落地区的安全走向将取决于两者的关系。
2021年8月阿富汗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阿富汗塔利班取代阿富汗政府执掌政权。结合前述巴阿边境部落地区冲突发生内生性成因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做出预估:一是普什图部落群参与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的反美运动是当前巴阿边境地区冲突的突出表现,美国撤军意味着引起这一冲突形态的外部根源得到消解;二是美国撤军和阿富汗塔利班取得暂时政权主导权不能解决阿富汗国内民族矛盾,阿富汗内战随时有复发风险,将延及巴阿边境地区。如果某些外国势力又再次插手,那么事态将更加复杂;三是阿富汗塔利班是巴阿两国政治伊斯兰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其能否为铲平伊斯兰保守主义思想生长的土壤而积极努力需要观察。虽然美军这一异端暂时消除,但是以疯狂排异为目标的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将会塑造更多靶子,加上普什图社会中以成年男子为中心的个体化冲突模式,将会对该地区的暴力活动走向产生影响。例如“伊斯兰国”组织已将在他们看来当权“变质”的阿富汗塔利班立为攻击目标;四是阿富汗政局变化不代表巴阿边境地区多种部落矛盾关系的结束。阿富汗塔利班不能代表全体普什图人,它寻求结束战乱的和平态度不能等同于普什图部落群对待其他群体也持有相同看法。普什图部落群与伊斯兰激进主义者之间也存在对立关系。以上这些情况都给巴阿边境部落地区安全带来了变数。
本研究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启示。当前有许多学者已意识到考察倡议沿线区域部落生态的重要性。对各国部落相关群体进行历史文化知识点梳理是必要的,但探讨还应致力于部落概念和部落社会系统的深层次研究。在这方面,欧美学术界走在了我们前列。在理论建构上,其19世纪中期以来进行的部落社会变迁研究和部落功能结构分析产生了大量文献。在政策评估上,美国研究机构注意到阿富汗部落与伊拉克部落结构的不同,告诫军人不能将伊拉克方式运用于阿富汗战场。①See Joshua Foust,Nathan Hamm.Afghan Tribal Structure Versus Iraqi Tribal Structure,Cultural Knowledge Report by Human Terrain System-Research Reachback Center,2008,September 26,pp.217-224,网址:https://info.publicintelligence.net/USArmy-AfghanTribalStructure.pdf,访问日期2021年6月1日。这些思路值得借鉴。部落群体的细节有差异,但其结构系统具有稳定性,掌握其中的变与不变将是部落社会生态研究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