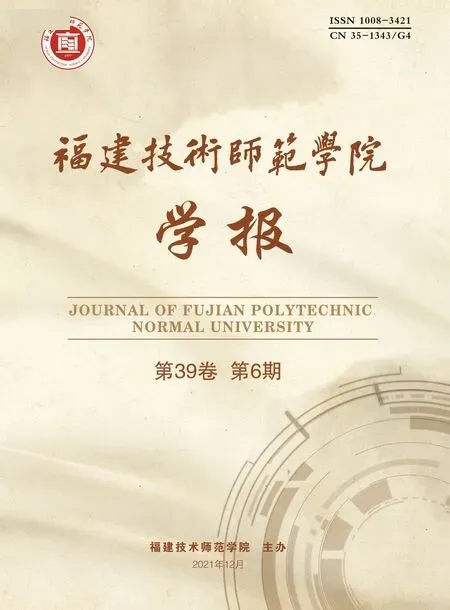论《权力与荣耀》的空间叙事
黄海燕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文化传媒与法律学院,福建福清 350300)
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是当代最伟大的英国小说家之一,马尔克斯曾说如果他没读过格林的书,他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威廉·福克纳、V.S.奈保尔、J.M.库切、威廉·戈尔丁等把格林视为精神导师。《权力与荣耀》是格林的代表作,曾获得英国霍桑登文学奖。
小说取材于格林1937年至1938年冬天的墨西哥之行,但小说以墨西哥历史上的“基督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追捕与逃亡的故事。在20世纪20年代的墨西哥,塔瓦斯科州是反教权思想最严重的地方,小说中的塔巴斯克是作者化用塔瓦斯科的名字得来的,政府宣布天主教非法,所有的神职人员只有2种选择:要么抛弃信仰被迫结婚,要么被执行枪决。小说中的主人公没有名字,他的称呼只有“神父”或“威士忌神父”,因为他是嗜酒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威士忌神父为了逃避政府的迫害,已经东躲西藏8年了。小说从他逃亡的最后几天开始写,他本来可以翻过塔巴斯克省北部群山,再往北,或者走水路,坐小火轮到拉斯卡萨斯,这样就安全了。但他始终没有离开,总觉得有种使命未完成,负责追捕神父的中尉与神父两次偶遇,神父都侥幸逃脱,最后在混血儿的诱骗下,神父被中尉抓捕并被执行枪决。
现代作家力图改变传统线性叙事模式,通过空间并置、频繁穿插、印象主义、重复叠加等手法,打破事件发展的时间序列,表现出一种追求空间化的效果趋势。空间叙事理论肇始于约瑟夫·弗兰克的论文《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等论著推动了空间叙事理论的发展。加布里尔·佐伦的《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一文对叙事文本中的空间结构的分析可能是目前最完整的。本文主要采用加布里尔·佐伦和列斐伏尔的空间叙事理论,从文本空间、社会空间剖析《权力与荣耀》空间叙事艺术。
一、文本空间:精妙地编织故事
加布里尔·佐伦的《走向叙事空间理论》把文本空间结构划分为3个层次:地志学层次、时空体层次和文本层次。其中的文本层次的空间即文本所表现的空间,它受到3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语言的含糊、不具体,叙述的详略等影响空间效果;二是文本的线性时序影响空间运动与变化的方向和轨迹;三是文本的视点影响叙事空间的重构[1]141-142。在《权力与荣耀》中,格林主要通过打断文本的线性时序达到空间叙事的效果,他把主线故事与副线故事并置,采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两类人物不同的象征意义。
《权力与荣耀》中,有主副两条叙事线索:主线讲述中尉追捕威士忌神父的经过,副线讲述白人群体(白人医生坦奇、费娄斯上尉一家为代表)在墨西哥的生活。主线故事发展的线性时间经常被副线故事打断,威士忌神父在逃亡的过程中与白人医生坦奇、费娄斯上尉一家有过短暂的交集(见图1)。约瑟夫·弗兰克在《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中把这种讲述故事的方法界定为:“并置”。所谓“并置”是指在文本中并列地置放那些游离于叙述过程之外的各种意象和暗示、象征和联系,使它们在文本中取得连续的参照与前后参照,从而结成一个整体[2]Ⅳ。大卫·米克尔森在《叙事中的空间结构类型》一文中也认为“缓慢的速率,事件结局的欠缺,甚至是重复——都是空间形式的正当印记”[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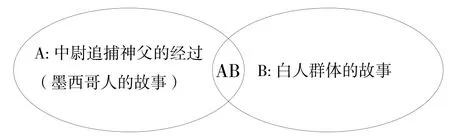
图1 主副线故事并置
为了更好理解小说的情节设置,我们借助字母和数字来梳理小说的如下结构。
《权力与荣耀》中有两个系列:自我觉醒的墨西哥人的故事系列(A)与走下坡路的白人的故事系列(B)。其中属于A系列的故事有(数字按照小说中叙事的时间先后排列),A1:逃亡中获得精神自救的神父的故事;A2:推崇强权厌恶宗教的中尉的故事。属于B类故事的系列有,B1:英国牙医坦奇的故事;B2:种植园主费娄斯上尉的故事;B3:抢劫银行的杀人犯美国人杰姆斯·卡威尔的逃亡故事(见表1)。

表1 小说结构梳理
我们按照小说叙述的顺序梳理情节:第一章,英国牙医坦奇的苦恼(B1)。逃亡中的神父在海港小镇偶遇英国牙医坦奇,坦奇邀请他到自己的小屋躲避烈日炙烤(B1A1)。因为要为一个男孩的母亲作临终忏悔,神父错过海港小火轮,只好继续逃亡(A1)。第二章,中尉的职责与宗教观念(A2)。第三章,费娄斯上尉一家的生活(B2)。神父逃到费娄斯家里,费娄斯的女儿珊瑚收留并帮助他躲过中尉的追捕(B2A1A2)。第四章,坦奇的往事与懊恼(B1)。费娄斯家的故事(B2)、中尉的感动(A2)。第五章,中尉准备枪杀人质,抓捕神父(A2)(见表2)。

表2 主副线故事交叉叙事
我们发现,小说情节采用的是主线与副线故事穿插叙述的方式,故事章节交替。主线讲述的是中尉与神父之间的追捕与逃亡的故事,副线反映的则是众多白人在墨西哥这个异域他乡的生活现状。小说分章介绍与神父逃亡有交集的白人的故事,第一章交代白人坦奇的故事,第二章讲述费娄斯一家的故事,主副线故事围绕着一个中心事件展开,即神父的逃亡与反省自悟。这种叙事策略使故事产生“陌生化”的效果,章节交替式叙述使读者的注意力在一章到另一章前后交替,阻碍了小说向前叙述的历时发展,小说具有了“空间形式”特点。
埃里克·S·雷比肯指出,空间叙事的作者往往“用修辞的方式把一个价值系统塞给了我们,其中每个部分都有一个系统;此外,各部分之中的并列结构把体现这个整体的一个价值系统也塞给了我们”[3]135。帕藤(Patten) 认为《权力与荣耀》中“有两个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结构:一个是时间结构,它按照时间顺序和因果逻辑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即展示追捕神父的过程;一个是空间结构(spatial,radial),它揭示神父所具有的静态形式上的象征意蕴”[4]27。
《权力与荣耀》中穿插的每个西方白人故事都围绕墨西哥的威士忌神父的逃亡与觉醒展开,墨西哥人为主角,西方白人为配角。有些白人,比如费娄斯上尉、德国人一家都曾对神父施以援手,但并未能让神父最终逃脱,他们的帮助是无效的。因为神父的逃亡就是他的天路历程,他逃亡的意义不是地理层面上的,而是心理层面上的。他不断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领悟到信仰的真谛,最终选择不逃,坦然殉道,成为圣教徒。就像耶稣为了替犯罪的人类赎罪走上十字架,威士忌神父身上散发出圣洁的光芒。世俗强权与精神信仰,谁该拥有荣耀之环?答案不言自明。中尉虽然是迫害神父的刽子手,但他并非毫无人性,只是执著自己的信念,认为只有消灭宗教,才能使人们摆脱贫穷,但最终他感到胜利的空虚,他的信念开始动摇。神父作为格林的代言人,向中尉说出了格林的观念:只有政治没有精神信仰是很危险的。小说中的白人无一例外都与威士忌神父打过交道,而且都被神父某种程度上感化。某种意义上说,神父化身成了他们的“精神之父”。
大卫·米克尔森在《叙事中的空间结构类型》中指出,除了并置的情节线索,还有反复出现的意象都是取得叙事结构空间性的手段[5]31。《权力与荣耀》的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墨西哥塔巴斯克省,整个地区都是这种地貌:河流、沼泽和森林。小说通过讲述神父逃亡的过程,全面勾勒了小镇的地形地貌以及自然气候:湿热的海边城镇、落后的村落、肮脏的沼泽地、幽暗的红木树林。落后、肮脏、湿热、泥泞、灰尘……所有这些意象的描写,构成了如地狱般的小镇地理空间。伊芙林(Evelyn Waugh)认为格林的天赋突出表现在他对那些场景的描绘上:大汗淋漓和感染,美丽的日落时分,人人平等的妓院,秃鹫……可以规避的法律,间谍,贿赂,暴力和背叛。他采用照相机式的写法描写重要的细节……这是现代的讲故事的方式。这些照相机拍摄式的场景描写形成一个个可供读者想象的画面,它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空间上的,而不是时间上的,场景本身就构成了小说叙事结构的一部分。
二、社会空间:异域与“家宅”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他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6]48。空间不是空洞无物的,而是社会力量建构而成的,这些力量隐身在空间的实体形态中。河流、沼泽、森林、住宅、广场等是《权力与荣耀》中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小说人物的活动场所,也是不同群体或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价值观念交流碰撞的社会空间。我们从社会空间的角度,从《权力与荣耀》中抽象出两类空间:异域与“家宅”。
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说到“家宅”负载的人生的重要意义,“家宅是我们在世界中的一角。我们常说,它是我们最初的宇宙。它确实是个宇宙。它包含了宇宙这个词的全部意义”[7]2。人物能从空间中获取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哪怕身处其间危险重重,仍然能从中寻找到福祉,那么空间是家宅;人物与空间相对陌生,不可调和,甚至惶惶不可终日,空间变成了异域。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是墨西哥塔巴斯克省的某个小镇,这是一个贫穷落后、肮脏湿热的地方,但对于威士忌神父而言,这是生于兹长于兹的家乡,他最初想逃离的是一个信仰被禁锢的小镇,而不是逃离家乡。真正的地狱在心中,威士忌神父最终意识到,正是家乡的落后,哪怕如同地狱,他才更应该留在这里,这是殉教者的义务。村落乡亲用性命保护神父,不惧中尉威胁,死也不说出神父的下落;监狱中虔诚信仰的牢犯,即使身陷牢笼,仍然不改变自己的信仰;小男孩深夜请神父为母亲做临终忏悔……威士忌神父在逃亡过程中找到了“家宅”的意义,也领悟了生命的价值。
相比之下,对于那些离开家乡,身居异国的西方人,墨西哥的这个小镇是陌生的、隔阂的、不安定的异域空间。人物与空间尖锐冲突,这种冲突“潜藏着价值的冲突、制度的冲突、甚至文化的冲突”[8]28。小说开端,作者给读者画了一幅海港小镇的素描,画面上的典型意象有:毫无怜悯之情的烈日、悬挂在空中冷漠地观察人类的兀鹰、腐尸、湿气、石头般坚硬的路面、随时会下沉的破烂小火轮、阳光炙烤的小广场。英国来的牙医坦奇是一个误入异乡、身心俱毁的白人。他听从岳母的安排,到小镇开设牙科诊所准备捞金返乡,但事与愿违,墨西哥战事不断,比索不断贬值,他已经15年没有与妻子联系。他幻想像在殖民地时期一样大把捞钱,衣锦还乡,但现在美梦破灭了,就像小说中女孩唱的歌,一朵染上真正爱情鲜血的玫瑰花。这块土地本应是黄金地,现在则成了困住他的牢狱。异域他乡的一切让他反胃。“房间”是“家宅”意象的一个基本的空间元素,因为人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房间的四壁之间度过。坦奇极力想把自己房子布置得如同家宅一样,小说写到他房间的布置,“餐厅里有两把摇椅摆在一张没有铺桌布的餐桌两旁,另外还有一盏油灯、几份美国出版的旧报纸和一个橱窗……这位牙医的手术室窗外是个小院,几只火鸡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摇晃着它们并不怎么华丽的羽翼……窗户上安着一块带图案的彩色玻璃:圣母从纱窗后面看着院子里的火鸡……坦奇先生说这块玻璃是我在他们打劫教堂财物的时候弄来的。牙科诊所要是不安上一块花玻璃似乎不怎么对劲,不够文明。在我的家乡——我说的是英国——他们总是挂着‘笑面骑士’”[9]11。火鸡、笑面骑士、圣母、小花园、威士忌以及孩子在后花园玩喷壶等,这些家乡的意象使坦奇先生越发增生思乡之情。但外在的摆设不能填补内心的失落,“家宅”是能安放生命价值的地方,这个小镇对于坦奇先生而言只是陌生的异域。“家?我的家就在这儿。……家这个词只是用来指西面有墙环绕着的一个人可以在里面睡觉的地方。坦奇先生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家……家像是一张风景明信片,同另外一些明信片撂在一起”[9]7-9。生活的不易化作愤怒的抱怨:没有人与他讲英语,没有先进的设备发挥它的医术,没有酒可以解愁,他的发财梦破灭了,所以在他眼中,这个地方如同地狱,他对这种寂寞的空虚已经习惯了,就好像习惯于看到镜中自己的面孔一样。他早已沉沦下去。
费娄斯上尉是一个善良的、无用的种植园主,他经营一家香蕉公司,尽量摆出一副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的困境、孤独的境遇,但无法适应墨西哥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因为在他们眼中,墨西哥人都是一些野蛮人。费娄斯太太犯头痛病,整天躺在吊床上,从未走出房间,她感觉身处的小镇是巨大的“坟墓”,她无时无刻不在与恐惧斗争,以致身心交瘁。“在这个奇怪的地方,死亡一年一年地向她走近了。所有的人都打点好行装离开这里,而她却仍然必须留在这个无人来访的墓地里,留在地面上的一个巨大的坟墓里”[9]36。他们的女儿珊瑚死后,他们搬离小镇,但家里的人似乎不大欢迎他们回家。“这对夫妻像两个在陌生城市走迷了路的孩子,失去大人照管,叫人看着非常古怪……两个人都被抛弃了,他们必须互相扶持”[9]260-262。
对于坦奇先生、费娄斯夫妇来说,房间本应是躲避异域环境的“家宅”,但他们的房间仅仅只有四壁,不是福祉,而是枷锁。他们觉得“都是这个鬼地方害的”[9]9。按照巴什拉的说法,这是离开“家宅”之后的原初性失落后的不适应感,“陋室的原初性属于每个人,无论富有或贫穷,只要他愿意梦想。所有的庇护所,所有的藏身处,所有的卧室,都有共同的梦境价值。当新的家宅中重新出现过去的家宅的回忆时,我们来到了永远不变的童年国度,永远不变就好像无法忆起。我们体验着安定感,幸福的安定感”[7]4。但他们并没有在新宅找到原初性,异域空间带给他们的是不适应感。
三、空间叙事与人性内蕴
何其莘在《权力与荣耀》中译本的“代译序”中写到:“在格林的作品中,读者看到的并不是艾略特(T.S.Eliot)诗作中那种一片干旱的荒原,而是一个被评论家称作‘格林之原’(Greeneland)的世界,一个由多种信仰、多种性格、多种经历的人组成的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精神世界。正是由于格林在他的作品中创造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但更接近现实的世界,才使他成为20世纪最受读者欢迎,同时在评论界又颇有争议的英国作家之一。”[9]11“格林之原”一词由评论家马歇尔(A.C.Marshall)在1940年5月出版的《视野》杂志中首次提出。后来的《牛津英语词典第一辑补录》(A Supplement to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I)中将之定义为“一个用来描述格雷厄姆·格林小说背景的术语,破旧不堪、沉闷压抑是这一背景的典型特色”[10]42。格林的文学世界是复杂的,具有深刻人性内蕴的,他选择异域题材,并非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表达彷徨动乱的世界中人性与道德的矛盾冲突。《权力与荣耀》的空间化叙事正好能彰显格林这种复杂多变、游移不定的态度。
根据谢利给格林写的传记《格林的一生》(The Life Of Graham Greene),格林1938年刚刚离开墨西哥时,对这个国家和人没有好感,但回到伦敦之后,当他拿起笔创作《权力与荣耀》时,他的态度有所转变,他把英国和墨西哥的宗教仪式进行了对比,“‘切尔西的弥撒似乎形同虚设;没有人用双臂抱成十字架的姿态跪下来,没有一个女人跪在过道上’它像痛苦本身一样让人震惊。我们不自责。也许我们需要一场暴力。伦敦对他来说是一个文化冲击”[11]23。当时的英国伦敦正处于二战即将爆发的恐怖氛围中,与墨西哥的混乱并无二致。1518年,天主教传入墨西哥。1821年墨西哥独立,天主教被新国家的掌权者所接受,成为了墨西哥的国教。1857年,墨西哥民族英雄胡亚雷斯担任墨西哥临时总统,宣布实行政教分离,从此墨西哥进入几十年的反教权运动时期。教会势力逐步被削弱,特别是墨西哥政府颁布的1917年宪法,规定教会不能拥有地产,教堂归政府所有,神职人员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谈论国家政治,公共学校不能讲授宗教科,教会不能随便传教等。教士纷纷外逃。1926年的“卡列斯法”导致墨西哥政教关系破裂,引发持续3年的基督战争。政教关系不断恶化。直到1936年,卡德纳斯政府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领域,宣布不打算发动反对宗教的运动,立法层面放宽对教会的限制,关闭的教堂才重新打开大门,被迫流亡海外的牧师逐渐回到了家乡。
《权力与荣耀》以政教斗争最为激烈的20世纪20年代的墨西哥作为故事背景,格林无意表达对墨西哥的反教权运动的政见,而是把墨西哥作为20世纪初期混乱世界的缩影,通过墨西哥人与白人两个群体的不同表现揭示动乱世界中人性与道德的矛盾冲突。
小说采用主副线故事交替并置的手法,主线故事塑造的是堕落但具备反省能力的墨西哥人形象,副线塑造的是“走下坡路”的白人群像,两个形象系列相互对照。小说中的墨西哥人形象大致分为3类:一是制造恐怖环境的人,包括警察、侦探等政府执法人员,他们手执武器,面无表情,到处追捕叛国者,以中尉为代表,他们认为信仰不能解决人们的现实问题,只有发展经济,增长物质财富才能使人们的生活好起来。二是被环境毁掉的人,包括生活在暴力恐怖环境中的孩子们、唯利是图的混血儿。他们没有信仰,贫困饥饿,为了生存,甚至会变得无比邪恶。三是对抗环境、超越环境的人,包括乡村百姓和威士忌神父,他们渴望心灵的纯洁与精神的救赎,认为信仰比物质财富更加重要。虽然政府悬赏重金缉拿威士忌神父,但他们无一人愿意为了赏金出卖神父。小说通过这类人形象的塑造说明即使在高压贫穷的环境中,信仰仍能使人们团结起来,让生活充满希望。
以威士忌神父为代表,劣迹斑斑的神父最终获得灵魂救赎,也成为感化他人的圣徒。生前与他打过交道的人不同程度被他感化。坦奇邂逅神父时就把他当做知己,向他倾诉自己的家事,最后坦奇看到神父被押往刑场,“他好像正在看着一位邻居在挨枪子”[9]265。 当神父被枪决后,他感到一阵恶心,闭上了眼睛,“这次他一定要离开了,一去就不复返了。……坦奇感到一阵可怕的孤独,因为胃痛而弯着腰。那个身材矮小的人会讲英语,听他讲过他几个孩子的事。他觉得自己被人抛弃了”[9]266。贫困村落的村民虽然物质贫乏,但依然怀着极强的信仰,一个个轮流在神父面前告解,哪怕神父困得都睡着了。面对中尉的质问与威胁,没有一个人出卖神父。虽然他们不敢公开反抗中尉,但他们以实际行动无声地支持神父。美国人杰姆斯·卡威尔是政府悬赏缉拿的抢劫银行的杀人犯,杀人越货,罪行累累,生前毫无信仰,他对神父说“你不用为我操心了。我这个人已经完了”[9]228。但他先暗示神父拿走他的手枪,接着又暗示他把刀拿走自卫,他在几个小时前还想着悔罪。
威士忌神父在小说中虽有罪恶,但最终以身殉道,成了具自我牺牲精神的父亲(father)的形象。“父亲”在格林小说中有3层寓意:一是血亲关系上的父亲;二是象征意义上(mataphorical)的父亲,即神父;三是上帝,天堂中的父亲。精神之父(spiritual)比血清之父(physical)更加重要,在宗教信仰已然丧失的20世纪,格林置换了传统的天父与圣子原型意义,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儿子由父亲代替,他小说中的主角履行作为父亲的职责而殉身[4]2。根据谢利的《格林的一生》记载,威士忌神父的原型来自格林在回国途中遇到的一个德国人,他称他是罕见的“令人愉快的德国人”,德国人曾经被关进墨西哥的监狱,牢房里挤满了小偷和杀人犯,地板上爬满了蠕虫,八天没有食物和水。让格林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温柔,对生活充满感恩和非凡的善良”[11]23。小说中的威士忌神父的善良来自这位德国人,同时,格林给予他特殊的身份——犯忌的神父,他身体羸弱,因为嗜酒而被称为“威士忌神父”,而且有一个私生女,对于一位神父而言,他无疑罪孽深重,但他在逃亡的过程中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同时给民众精神上的希望。
从威士忌神父形象的设定上,我们看到格林小说不断再现的主题:从有罪的精神生活中体验信仰的力量,格林小说中的主角厌倦一成不变的家庭婚姻生活,他们沉溺于罪恶之中,虽然他们也为罪恶所累,但罪恶又是其成长为精神之父的必需……《问题的核心》中男主人公斯考比为了隐藏自己的通奸行为以及他与叙利亚商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断撒谎。最后,他因无法面对谎言而选择自杀。格林认为斯考比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自认其罪并勇敢背负起这一重担,而那些自甘堕落的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有罪。《斯坦布尔列车》中奥佩牧师面对津纳医生的疑惑,他认为忏悔如同精神医生的心理治疗,最后的结果都是让人重新获得做人的意愿和力量,甚至精神分析家比教士更灵验。从中我们看到格林对待宗教的犹疑态度。
小说根据格林的1937年至1938年冬天的墨西哥之行的经历写成,但“任何作家对异域文明的见解,都可以看做是自身欲望的展示和变形……寻找作为他者的异域文明,也许正是另一种方式的寻找自我,是另一种变形的自我欲望。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在是我们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12]13-14。格林拥有其他作家难以匹敌的异域情怀,他着重把墨西哥塑造成一个拥有精神信仰的地方,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乌托邦世界。但墨西哥对于格林来说是个陌生的世界,自然环境、政治环境以及人文环境都与西方迥异,物质的落后与观念的封闭使得格林笔下的墨西哥世界成了一个恐怖的异域空间。这种感受通过异域空间与“家宅”空间场景描写出来。墨西哥这块神奇的土地如同试验场,他笔下的西方人在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自然、文化环境中的生存状态,水土不服、孤独寂寞、沉沦无助,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中的西方人形象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堕落的人类的象征。
正是通过主副线故事情节并置、异域与家宅两类社会空间的对比,格林一方面通过坦奇、费娄斯上尉审视墨西哥人,一方面,又通过神父、中尉审视西方人。这种双向审视下的墨西哥形象与西方形象都带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墨西哥物质上落后,但追求精神信仰,西方白人精神空虚,但某种程度上源自环境的局限。
这种对人性的复杂性的审视与格林的个人经历以及敏感的性格有关。格林的父亲是英国公立学校校长,但他在父亲的学校学习很不愉快,他悲观厌世,几次自杀,他频繁地逃学,父母甚至送他去做心理治疗。“对于格林来说,学校生活使他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人世间的罪恶——特别是背叛——野蛮国家,以及生活在边界上所感受到的那种刺激和恐惧。”[9]2(代译序)在格林的自传《生活曾经这样》(A Sort of Life)中,他写到地狱般的学校生活,“一个人因为相信地狱所以才会开始相信天堂。但相当长时期,他能相当熟悉地描述地狱……终日嘈杂没有安宁的集体宿舍,没有锁的抽水马桶,……郊外马路上马车走过的声音,这些都是痛苦经历的一部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片刻安宁”[13]6。格林于1926年在诺丁汉皈依天主教,为的是娶天主教徒薇薇安,后来两人分居,但遵循天主教教义,两人并没有离婚。他被称为天主教作家,但格林对天主教的态度是犹疑的。格林的小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很突出地表达了这种态度。男主人公奎里是伦敦的高级建筑工程师,他感觉长期自私的生活已经吞噬了他所有的情感,如同麻风病患一样。他远离喧嚣的伦敦,前往非洲寻求精神疗救,他的非洲之旅是人性意义上的自救,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皈依,他的精神救赎乃是寻回失落的善良。
格林作品的基调是邪恶力量过于强大,以至于在人间恶性畅通无阻,善行寸步难行。格林的一生都在寻求冒险,他总是试图逃离无聊单调的生活。约瑟夫·康拉德对格林创作影响巨大,康拉德的殖民叙事建构了“黑暗的中心”——非洲刚果,《权力与荣耀》建构了叙事空间——墨西哥。格林比康拉德小47岁,他生活在英国殖民帝国的辉煌时期,比康拉德有优势,康拉德只是停留在港头船上远望那些东方国家,而格林则是背起行装,深入内陆,和当地人一起生活,他的异域题材小说都是建立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他深入拉美、非洲,在亲身经历过的事实面前,他更多的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探索人性的复杂,而较少的进行浪漫幻想,他的小说带有精神性,在精妙的故事情节表层下的人性的探索,这也是格林的异域小说的独特性。
四、结语
《权力与荣耀》的叙事手法使我们更倾向于从空间的角度看待这部小说,首先在故事的讲述上,采用主副线故事并置的方法,使得墨西哥人形象与白人形象形成对比,突出墨西哥作为人文主义的乌托邦色彩;在场景描写上,采用照相机似的呈现方法,详细描绘,着重写出人物精神感知上的空间意象。再者,小说塑造异域和家宅两类相互冲突的社会空间,墨西哥人能在家乡寻求到精神的寄托,而西方白人因为只是把墨西哥当做发横财的殖民地,当黄金梦破灭后,他们无法找到身处其间的价值,异域成了牢狱。格林有时通过中尉、神父眼光看西方人,有时通过坦奇、费娄斯夫妇看墨西哥人,保持相对清醒的双向审视的文化意识,这使得小说的叙述带有相对真实客观的色彩,某种程度上消解帝国主义话语,他的小说体现出政治、文化、人性、宗教等多个层面的交互性,《权力与荣耀》更多地凸显普遍人性的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