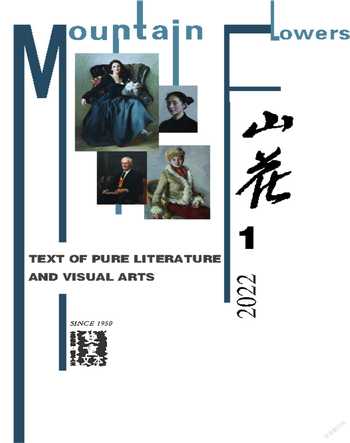“你如何能不知疲倦地写下去?”
顾奕俊
张玲玲新的小说《W与M》,涉及到就她们这一代作家群体而言所形成的具有交汇意味的文学“起点”的描述:“我和M认识是在入校后的第二年。当时我们都在一所三流学校读书,都参加过新概念作文大赛,不同的是,他比我大两届,共参加过两次,第一次未曾获奖,第二次获二等奖;我参加了一次,并未获奖。”[1]当我们重新观照1999年由《萌芽》杂志社发起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并试图将之看作是由“纸媒诞生”与“网络重塑”合力形成[2]的年轻写作者的文学“起点”时,我们更需要注意的也许并非是那些成名于新概念作文大赛、现已成为“流量担当”的名姓,而是通过一届又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举办所积累、并对应当下特定年龄群体写作者构成“传统”“脉络”的风格特征、审美趣味,包括相应的转向及动因。事实上,以新概念作文大赛作为自我文学创作“起点”的写作者,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起码分野出了两条可供辨认的路径:其一,坐享借由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然构建起来的规范法则与数量依旧可观的阅读受众群体;其二,则是毅然决然地“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不过如果以此作为分类依据的话,参照张玲玲近期的小说创作,她似乎并不能完全被归入这两类写作者对象范畴内——尽管张玲玲和众多同辈的写作者一样,都面临着肇始于个体经验的最为直接的书写困境。
本文标题所引用的“你如何能不知疲倦地写下去?”一句,来自于《W与M》当中“我”对于青年作家M的诘问。M无疑是照单全收“新概念遗产”的那类作家,且在不断自我重复的校园青春里获得了难以轻易摆脱的“安全感”。正是由于这种“安全感”,令“我”忍不住发问:“你如何能不知疲倦地写下去?毕竟我们正急切地步入下一个阶段不是么?毕竟我们的青春期早就结束了不是吗?”但联系到张玲玲本人的创作变化,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又或许能够将热衷于校园文学题材书写的作家M与“我”皆理解为是张玲玲在相应时期的“截面”(或许也可以说是“化身”)——“我”关于“下一个阶段”的诘问与M“但总有人会十七岁”的回答其实都可能是来自于张玲玲本人的“声音”。很显然,其有趣之处恰恰在于“声音”与“声音”的悖反。
《W与M》裹挟着青年作家转型期必然要遭遇的问题,即如何应对写作过程中将会出现的自身经验的匮乏性。当“我”不断强调“我们正急切地步入下一个阶段”,实则暗含着令很多写作者停滞不前的障碍物:作者如何获取到能够匹配笔下那个虚拟世界的“新”的“经验”?这从侧面也触及到另一个话题:因为所谓“下一个阶段”也指涉“另一群”迥异于校园文学受众群体的阅读对象,所谓“新”的“经验”,在此背景下也应指认为是呼应“下一个阶段”阅读对象的路径视野、审美趣味、叙事风格、书写立场。然而M所言“但总有人会十七岁”却又表明,沉溺于“新概念遗产”的写作者对于过往青春片段与校园文学主题的重复使用,对于“永远都将到来”的青年阅读群体所具有的“持久”的经验有效性。至少对于作家M来讲,支撑他“不知疲倦地寫下去”的主要因由就在于这种明显已显现出“穷途末路”迹象的经验写作总能在某一特定阅读群体对象当中形成意料之中的迎合与共鸣。由此,我以为,张玲玲写作《W与M》的驱动力之一并非是基于某种肯定性的姿态,而是基于无法自我消解的困惑——因为两种看似“合理”的“声音”,最终传递的却是创作观念层面难以调和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是《W与M》内嵌的“声音”与“声音”的冲突,但结合《W与M》里的W与M,《嫉妒》里的许静仪与谷雪,张玲玲近些年发表的一系列小说里,主要叙述人物之间的显性关联却往往细若游丝(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任何交集)。这是应着重思考的地方,也由此或许能形成某种具有延伸性的分析。张玲玲晚近以来的小说往往有意识地标示出相关情节线索的具体年份,但标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引出个体、群体与时代之间貌似显而易见的关联。我在阅读《嫉妒》之后曾作过这样的笔记:“如果说‘1997年’是聚焦《嫉妒》的一个‘绳结’,‘绳结’的突出意义并不是要让这些大多出生于1985年以后的年轻人与九十年代的宏大话语形成结构并置,如同她们的父辈那样旋即被编织为历史表情的某帧画面,而是自‘绳结’始,少女们需要独自去守护不容外人窥探的秘密。”小说叙写谷雪、许静仪如何掩饰自身特殊经历与隐秘念头的过程,同时也是在向读者呈现出一类青年群体逸出文学史规训的个人成长史。当然,如果读者无法察觉到这一“底面”,那么张玲玲小说中所标示的时间刻度反而会成为读者阅读时的障碍。
而相较于《嫉妒》中人物与人物的“双线并行”,《W与M》中以第一人称视角出发的小说叙述者“我”则借由他人的过往经历继而产生的特定经验与情感结构的挪移与转化展开叙述,这构成了张玲玲现今小说创作中人物之间微妙的串联点。我们先回到张玲玲2019年出版的小说集《嫉妒》。该小说集中如《嫉妒》《岛屿的另一侧》《去加利利海》《新年问候》等作品中,张玲玲会有意识地设置出或姐妹、或同学、或师徒的角色对称结构。角色对称结构的设置一方面试图“引出”相关小说人物之间的“殊途”,但与此同时,张玲玲又通过带有对位法性质的“殊途”映照出人与人的不乏吊诡意味的“同归”。《岛屿的另一侧》的叶晨和表姐叶怡似乎接受了某种历史偶然性的召唤,但小说结尾处叶晨的内心独白则表明看似截然相反的个体在情感生活、精神状况等方面却有着耐人寻味的叠合(或者说,叶晨“接续”了叶怡已被命运之神终止的日常生活):“说来讽刺,原本她曾寄望跟表姐走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却殊途同归。走到叶怡去世的年纪,也站在了叶怡以前的处境:喜欢一个不属于她的人,再被这个人逐步放弃。”[3]故而,我们在考察张玲玲这一时期小说的人物及人物关系时,就不应仅仅以简单的“比较”方式去进行言说,因为她们或许南辕北辙的生存处境与未来走向(即某种受到时间诡计所操纵的“现实的歧路”),实质上可能只是另一类视角观照下的“反复”或是“延续”。但如果依此而论,“你如何能不知疲倦地写下去?”这一命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反复”“延续”都已然设定了相应的,能够预测的尽头。不过颇具意味的是,以张玲玲最近发表的《W与M》《夜樱》《移民》诸篇为例,我们能注意到人物之间或“反复”或“延续”的命运轨迹却逐渐深刻地反作用于文本之外的写作者张玲玲,以及她将要选择的写作走向。在上述所举例的三篇小说里,张玲玲都更为明显,也更为坦率地展露出“我”的视角、“我”的生活、“我”的情感。这里所指的“我”,不仅涉及的是直观的叙述视角,也包含着某种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来回穿行、不断形成情感振荡与积蓄的主体结构。《W与M》中,“我”是一个对于同辈人写作方式深感困惑迷茫、同时又在私人生活推衍出的迷宫里打转的新闻记者;《移民》中的“我”依旧是名记者,这次所要探寻的是一位海外侨商扑朔迷离的“前半生”;《夜樱》中的“你”是变形的“我”,是为了生计而要忍受与年幼女儿分离的母亲。梳理这三篇小说也会让人觉察到,张玲玲正在为进入“下一个阶段”而作着各种准备。也正因为要形成阶段与阶段的跨越,张玲玲必须重新审视“自我”与“文本”的距离。
毋庸置疑,小说集《嫉妒》已然提供了足够令张玲玲在文学界形成一定辨识度的“标签”。但关于“现实的歧路”“人生的殊途同归”这些命题,《嫉妒》阶段的张玲玲似乎更愿意成为抽身而出的旁观者与复述者,而进入“下一个阶段”则要求张玲玲考虑何谓“个人经验”、何谓“写作经验”,考虑从何处汲取与转换能够有效内置于小说文本当中的情感经验。有意思的是,读到《W与M》的结尾,我总认为,这是张玲玲在回答写作小说集《嫉妒》时期的那个自己。她在陈述他人面对外部强力时的脆弱,却又因他人脆弱表象背后的执著而为自己似乎感到厌倦的写作确立了新的立足点:“她一直以为是台风阻断了去岛屿的道路,后来发现不是。如果人真的想去一个地方,什么都无法阻挡,雨会停,道路会变干,群山会被移除,海水和云柱可以分开,只要等得够久,足够虔诚,总会到达。只是你不一定要去那里。你常常困于中途,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去哪个方向。”《W与M》并不是一个“准备好了”的小说,我的意思是,“准备好了”也可能意味着某种饱满而缺乏提升空间的呈现样式,因为作者对于一切都显得太过于成竹在胸。
而张玲玲似乎因这篇小说不断出现、随之消失的“身影”而意外获得了关乎自我生活与写作、跨越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启示录”。
同样在不久前亮相的小说《移民》,发表于《花城》2021年第1期“花城关注”栏目。该期同时还刊登了张玲玲、谢青皮、王苏辛、卢德坤等人的讨论文章。张玲玲在论述王苏辛的小说《冰河》时,指出了她所认为的小说写作的“难点”所在:“小说写作中,最困难的仍然是故事的展开而非世界观的设定,是人物关系的搭建而非人物历史的堆积,是行动的往前而非凝滞不动。”[4]而在《中华文学选刊》编辑部2019年第1期面向青年作家所作的问卷调查活动中,被问到“是否认同历史感、现实感的匮乏与经验的同质化是当代青年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时,张玲玲的回答是这样的:“不太认同,读过同代人中一些历史感不错、现实感强烈、有异质感的小说。加上目前都在倡议,所以当代写作者或多或少都能够意识到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所以有选择地去拉长小说的叙事时间、写父辈、写时代等等,将小说加入各种现实元素、现实空间的书写。是不是真有必要,也不一定,小说完全可以不写历史、不写现实。比起这些宏大的观念,青年写作者真正需要解决的可能反而是更微小、更细节的问题。”[5]这两段论述中有几处应被提取出来的关键点:“故事的展开”“人物关系的搭建”“行动的往前”“更微小”“更细节”。《W与M》《夜樱》《移民》三篇小说中,“我”(包括《夜樱》中作为“我”的变形的“你”)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叙述视角,同时也是小说作者张玲玲的特殊的介入形式,由此在文本中推动“人物关系的搭建”,成为“故事的展开”的至关重要的条件项。但“故事的展开”与“人物关系的搭建”并非張玲玲写作的最终目标,因为当张玲玲未曾过多掩饰地就将现实语境的“自我”纳入到虚拟世界时,她显然更希望由此能催生出“行动的往前”的驱动力。驱动力所指涉的对象即是小说世界的芸芸众生,也是陷于经验困境与情感泥淖的现世中人,这是张玲玲现阶段小说创作的更深层次的用意。所有种种又是借助“更微小”“更细节”的部分去引导、去彰显。
而谈到“历史”“现实”,《W与M》《夜樱》《移民》的“现实”与“历史”则是建立在相互交织却又彼此怀疑的基础上,逾出了很多同辈写作者因经验层面的“非此即彼”而趋于简单粗暴的观念局限。《移民》提及了张玲玲这一代写作者在某个时间节点非常流行的“写法”:“我还记得最开始的那几年,很多人会主动过来,跟你讲故事,想分析个人的‘历史究竟如何沿着看似合理的路径走进了错误的房间’,又或者,他们是如何沿着看似任性的路径去到了正确的房间,时不时的,会说出一些深具诗意和哲理的句子,却很少意识到,诗意和哲理照在他们的经历当中。”[6]不可否认的是,张玲玲在最初进行写作的时候也必然会在“房间”与“路径”之间、因需要作出“正确/错误”的单项判断而犹豫不决。但张玲玲显然又很快意识到这种犹豫不决将会造成的“经验的幻象”,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何谓“正确或合理”,何谓“错误或任性”。《M与W》的“W”部分假如依照“曾经的张玲玲”的“写法”,经历了丈夫离世、家庭破产的W更多可能是如同张玲玲在《嫉妒》中所述的“在这条漆黑的甬道走着,无法找到出口”[7],或者说,W正在走向“错误的房间”。但就是这样一个“至暗时刻”,“我”作为聆听者、旁观者主动进入到文本的叙述当中,袒露那些自己曾经以为进入“错误的房间”的记忆画面。那些记忆画面是属于个人的“伤痕史”,但从“现实”重返“伤痕史”,“我”却不再仅仅以正确与否进行判断,因为回忆(包括通过回忆召唤出的那些过去式的印象痕迹)也会让一个自以为的失败者意识到被“伤痕史”所遮蔽的否定、错乱、焦虑、失望、孤独等词汇的反面。而从他人经历中获得的种种并不只是为了拓展自己固有的认知边界,而是试图重新调整一度被某种极端而激烈的情感所支配的观念态度与经验结构。小说《移民》尽管以多重视角去讲述“潘”的“前半生”,但其意义并不是讨论其身份底细(相反,这篇小说以“许多谜题待解”告终)。事实上,正是因为听到了多个有关“潘”的“人生版本”,以及借由其多种“人生版本”折射出“自我”的经验镜像,并在其间辨认出一种区别于纯粹怀旧行为的异质,这使得“我”(包括与“我”相关联的写作者)得以远离某条可能将会遁入黑暗与恐惧的深巷,如同某一个瞬间的“潘”,“在叙述这个时刻的时候,他的语气充满笃定和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讲,当《W与M》中“我”向W抛出“你如何能不知疲倦地写下去?”之问时,W以他的立场、方式进行了回应,而正在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写作者张玲玲则通过《W与M》《夜樱》《移民》等作品作出了另一种回应,并在此走向了一条和众多曾经从同一“起点”出发的同辈所不同的道路。我们对于张玲玲的期待也正在于此。
注释:
[1]张玲玲:《W与M》,《山花》2022年第1期。
[2]吴俊:《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的流变与转型——以〈萌芽〉“新概念”作文、新媒体文学为中心》,《小说评论》2019年第1期。
[3]张玲玲:《岛屿的另一侧》,《嫉妒》,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71页。
[4]《对谈》:极少数获益者的文学幻觉最终是要破灭的》,《花城》2021年第1期。
[5]《新青年,新文学: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上)》,《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5期。
[6]张玲玲:《移民》,《花城》2021年第1期。
[7]张玲玲:《嫉妒》,《嫉妒》,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