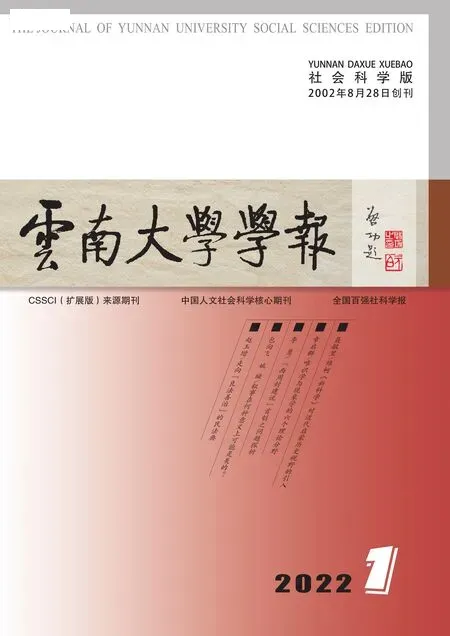唯识学与现象学的六个理论分野
章启群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唯识学含藏佛教哲学中最精致的认识论思想,胡塞尔现象学作为20世纪影响力最广泛的欧洲大陆哲学流派,其认识论开拓了当代最新锐的哲学认识论视野。近几十年来国际国内学界展开了关于唯识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不仅拓展和深化了佛教哲学尤其是唯识学哲学研究,也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哲学现象学的研究。由于很多缘故,本文不想具体评述学界对于唯识学和现象学比较研究的成败得失,只是从六个核心问题上论证唯识学与现象学理论上的似是而非,即根本的理论差异,以期推进学术的发展,并期待缁素两界硕学大德赐教。
一、“识”与“意识”
“识”是唯识学的核心概念。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是意识。“识”是否完全等同于“意识”一词,是唯识学与现象学之间关系最基本也是最重大的问题。

梵文与“意”对译的是manas。manas原意“思量”,即思维、筹划、计量之意,与现代汉语“意识”和英文consciousness词义近。由此可见,唯识学中将“识”与“心”“意”概念互用,并非这几个词之间意义全等,也只是在这几个词意指认识能力(intellect)这个特定含义的交叉之处。
此外,唯识宗还将“心”用来专指阿赖耶识。例如《唯识二十颂释》云:“安立大乘三界唯识。以契经说三界唯心。”(7)黄宝生:《梵汉对勘唯识论三种》,第210页。此处“心”即指阿赖耶识。窥基《成唯识论述记》曰:“集起义是心义,以能集生多种子故,或能熏种于此识中,既积集已,后起诸法,故说此识名为心义,‘心意识’中‘心’之心也。”(8)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第211页。《成唯识论》对此也专有说明:“谓薄伽梵处处经中说,心、意、识三种别义。集起名心,思量名意,了别名识,是三别义。如是三义虽通八识,而随胜显,第八名心,集诸法种起诸法故。第七名意,缘藏识等恒审思量为我等故。余六名识,于六别境粗动间断了别转故。如《入楞伽》伽他中说:‘藏识说名心,思量性名意,能了诸境相,是说名为识。’”(9)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317-318页。早先中国学者很多将“识”解释为“心”,将阿赖耶识与心等同,历史上也有很多说法。《成唯识论》大体上把这三个概念对应不同的识,即阿赖耶识对应“心”,末那识对应“意”,其余六识对应“了别”。
此处涉及唯识学的主要是前三条。就是说,即使是在唯识学中,“识”在不同情况下至少有以上三种意义。但是,不仅一般读者对于“唯识”之“识”这些多种具体含义不甚了解,常常望文生义,简单地将“识”解读为现代汉语中的“意识”一词,甚至英文世界包括权威的梵英词典,通常也将而vijāna翻译为conciousness,即基本对应于现代汉语的“意识”一词。(12)词典原文:vijāna. (P.viā T. rnam par shes pa; C. shi; J, shiki; K. sik 識). In Sanskrit, “consciousness”; a term that technically refers to the six types of sensory consciousness (VIJāNA): eye, or visual, consciousness tongue, or gustatory, consciousness (JIHVāVIJNA); body, or tactile, consciousness (KāYAVIJNA); and mental consciousness (MANOVIJNA). These are the six major sources of awareness of the phenomena (DHARMA) of our observable universe. Each of these forms of consciousness is produced in dependence upon three conditions (PRATYAYA):the “objective-support condition” (āLAMBANAPRATYAYA), the “predominant condition” (ADHIPATIPRATYAYA), and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condition” (SAMANANTARAPRATYAYA). When us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six forms of consciousness, the term vijāna refers only to CITTA, or general mentality, and not to the mental concomitants (CAITTA) that accompany mentality. It is also in this sense that vijāna constitutes the fifth of the five SKANDHAs, while the mental concomitants are instead placed in the fourth aggregate of conditioning factors The six forms of consciousness figure in two important lists in Buddhist epistemology, the twelve sense fields (YATANA) and the eighteen elements (DHTU). With the exception of some strands of the YOGCRA school, six and only six forms of vijāna are accepted. The Yogācāra school of posits instead eight forms of vijāna, adding to the six sensory consciousnesses a seventh afflicted mentality which creates the mistaken conception of a self, and an eighth foundational or storehouse consciousness (LAYAVIJNA).见Robert E.Buswell Jr. and Donald S.Lopez Jr.: The Princeton Dictionary of Buddhism.Princerton University Press.2014.这个词条对于唯识学的误解很大也很多,可以写专文论证。这里只能暂略。由此可见这样的误读流传之广。这种对于“识”的普遍误读,自然割裂和损伤了唯识学的极为重要的思想,对于唯识学的理解产生了巨大的片面性。
世亲所作《唯识三十颂》主要内容为说明唯识之识的相、性、位。“相”即识之相状,“性”即识之自性,亦即本质,“位”指转识成智获得解脱的不同阶段。《唯识三十颂》第一颂和第二颂上半部云:
由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识所变。此能变唯三:谓异熟、思量,及了别境识。(13)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1页。
关于这一个半颂,《成唯识论》用了近一卷半的文字进行解释。以下只节选相关论述:
世间、圣教说有我、法,但由假立,非实有性。……彼相皆依识所转变而假施设。“识”谓了别,此中识言亦摄心所,定相应故。“变”谓识体,转似二分,相、见具依自证起故,依斯二分施设我、法,彼二离此无所依故。(14)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2页。这里只是安慧关于“变”的观点。
大致内容是,世俗和佛教中一些教义所指说的“我”和外界事物,都是假设的说法。“我”和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假象,并非实有。“转相”意即“我”和万物暂时呈现的假象和名目,实质上它们都是“识”所转变而来的。“我”和万物只是心识所变的相貌,假为施设。唯识学的目的,就是破除众生把一切法视为实有的观念。一切所变识相都表现为能变的见分和相分,即万物都能够展示自身而被人们感知,然而皆为识所变。而“识”意指“了别”。同时此识亦含摄心与心所的相应功能,即意识与意识对象的相应功能。各种识的生成转变,看似我和万事万物在显现,被佛教某些教义说成为见分、相分,其实都是假象。见分指由识生起的对外界事物看法,相分指外界事物为识呈现出来的形相,见分、相分必须由内识自证,此即自证分。(15)本文所有关于《成唯识论》引文解释,均参见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和慈航:《成唯识论讲话》。关于见分、相分、自证分、证自证分含义及相关思想在下文专论。因此,离开识不能有二分。只有识是我和万事万物生成的根本原因。
颂言“此能变唯三”,意指识能转变有三种:即异熟识、思量识和了别境识,称“三能变”。《成唯识论》进一步解释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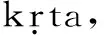
大意是,识相有能变和所变两种。识所变的相即万事万物为无量数种,然而能变的识(vijāna)只有三类。第一类是第八识异熟识(vipāka- vijāna),也叫阿赖耶识(ālaya- vijāna),是初能变;第二类是第七识思量识(mcetanā-vijāna或 cint-vijāna),亦名末那识(manas- vijāna)识,为二能变;第三类是了别境识(vijāpti- vijāna),为三能变,包括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前六识。这其中阿赖耶识是本识,即根本,其余七识皆由第八识转而生成,故称转识。关于八识转变各种行相的具体原因和根据,即“因能变”和“果能变”,以及习气、熏染、有记、无记、有漏等术语概念,此处暂略不论。这里只是说明“有八识生现种种相”,即由八识生成万事万物,包括“我”。而且,“八识体相差别而生”,是说明八识所指摄是各不相同的。此说重点在于,一切我相和法相都离不开三能变识相,一切所变识相都表现为能变的见分和相分,而不是另外实体,意即一切诸法都是头脑所思和所得而成。
综上所述,根据唯识学思想大致概括一下“识”的义域,至少有以下几点不同:
(2)识所转变的“了别境识”之“前五识”,意指眼、耳、鼻、舌、身感官知觉认识,可相当于英文sensation 或sense词义。
(3)识所转变的“了别境识”之第六识是意识(mano- vijāna),意指就是现代汉语意识一词,与英文consciouseness重合度极高。但第六识意识亦有想象、推理、判断的认识功能。(20)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第1089页。
(4)识所转变的第七识“思量识”亦称“末那识”(manas- vijāna),意指自我意识,也是“我”的本体,可与英文ego对应。
(5)第八识“异熟识”亦即阿赖耶识,则比较接近中国哲学“道”“无”这类概念,或可用西文logos一词来对应。当然,阿赖耶识与道、无、logos之间亦有本质的巨大差异。因为,阿赖耶识不仅具体转为前六识和第七识,可以转为遍计可执性、依他起性等缘起法,可以进入转世、轮回,最终还可以化为圆成实性,进入寂灭,断灭轮回,成为菩萨、佛。这些功能则是道、无、logos等概念所不具备的。(21)黄宝生认为:“隋达摩笈多译《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唐玄奘译《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和唐义净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中都将这个vijāna(‘识’)译为‘神识’。这里可以顺便提及,在昙无谶译《佛所行赞》中,也将婆罗门教确认的轮回转生主体ātman(‘自我’)一词译为‘神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两者之间暗含的相通之处。”(黄宝生:《梵汉对勘唯识论三种》,第3页注②)
由此可以大致概括唯识之“识”的诸多意指:第一,具有智力功能,即具有判断、明辨的思维认识功能;第二,具有构造功能,即可以转成“八识”,前五识是感觉功能,第六识是意识,第七识末那识是自我意识,即“我”的本体,而第八识阿赖耶识则是宇宙万有的总摄,并且具有永恒性;因此第三,唯识之“识”即阿赖耶识具有形上性。阿赖耶识的这种形而上性质,近似于西方哲学的logos和中国哲学的“道”、“无”。就“识”此义而言,任何其他文字是无法翻译的。
从这些分别看出,唯识学中的八个识意涵差异极大。从构词法来说,虽然“阿赖耶识”、“末那识”、“了别境识”等作为偏正结构词组的主词都是“识”,而仅仅拘泥於汉字“识”具有的判断、分别的含义来理解vijāna,很容易陷入误读。尤其是作为与道、无、logos相近的含义的阿赖耶识,如果将其中的vijāna理解为“识”,不仅在语境体系中极为不准确,而且涉及对于佛教唯识学的根本误解。而将全部八识中的vijāna尤其是阿赖耶识之“识”翻译成英文consciousness,则更是一个可怕的错误。(22)周叔迦:“这唯识宗的名词,简略地可以使我们了解他对于宇宙同人生的解释。‘唯’是单独的意思,‘识’是分别的意思。这个名词的解释就是说:宇宙同人生,全是分别的现相。他说宇宙之间,空无所有,只是有一种能力存在。由这种能力运动的结果,便幻生出无尽的时分、方分,种种宇宙人生来了。这种能力便叫作‘识’。”(《唯识研究》第1页)
最后,除了八识之外,还有一个作为八识之源的“识”本身。八识皆由这个“识本身”转变而成。然而,在转变成八识之后,所有万事万物的根源,聚焦到由它转变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也上升成为“本识”,这个最本源的“识”却自然隐身消失。唯识学的这个理论表述令人感觉,这个作为八识之源的“识”,只是一个逻辑前置,近似于“无”。当然,“无”的字面意思是“空白”,而“识”却有了别、分别等明确的字面意思。但“识”本身这些字义对于作为逻辑前设的“识”本身,似乎没有任何意义。(23)这种思维方式反而颇类似中国哲学家王弼对于“大衍之数”的解释。《易·大传》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大衍之数何以有一不用?王弼认为:“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见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47-548页)王弼把“一”解释为太极。它是存在于万物之中,而非独立于万物之外的宇宙之源。它的本质特性是“不用之用,非数而数”。除了太极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具备这一特性。其实这个“一”也是“无”,是宇宙之最高本体。“太极无体”,意即这个最高的本体,乃“非于万物之后之外而别有实体”,而是即体即用之“无”。唯识学变现为八识的最终的“识”,就是这个“一”和“无”。可参阅章启群:《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3页。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就存而不论了。
胡塞尔在1901年出版的《逻辑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第二卷中开始使用“现象学”这个词,以后便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现象学”,意即关于“现象”的哲学。早年胡塞尔在布伦塔诺(F.C.Brentano)的影响下,先是以描述心理学为起点,走上了与弗雷格(G.Frege)和罗素(B.Russell)不同方向的数学基础研究之路。自从英国经验论以来,在哲学基础上出现的又与哲学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心理学,被称为内省派的心理学。它与19世纪形成的科学主义实验心理学不同。实验心理学注重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的心理的行为表现,而内省心理学则重研究人的内在意识经验,强调知识、情感和意志等内在经验之间的关联和统一性。从洛克(J.Locke)到穆勒(J.S.Mill),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始终是内省派心理研究和逻辑心理主义的大本营,心理学被他们认为是比逻辑学更基本的研究。这种观念自康德开始也对德国产生影响。胡塞尔的老师布伦塔诺就是当时著名的内省心理学派的哲学家,他认为应该在心理学之中来寻找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因为科学公理和人的内在知觉判断的普遍正确的基础,就是人的内在经验的自明性。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胡塞尔意识到这种描述心理学的方法不能真正解决数学和逻辑的思想基础问题。1900年胡塞尔发表《逻辑研究》第一卷,对心理主义展开了深刻、系统的批判。胡塞尔认为,经验心理学试图通过观察、实验和归纳,把心理活动当成时空中的生物现象,因而不能区分作为自然的心理过程的经验与真正的心理经验。经验心理学的对象是个别的与偶然的事实,所以这类经验性陈述不可能导出精确的科学法则。相反,真正的逻辑性陈述不包括具体事件,因此,其真值是必然的。这标志着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超越,走上了现象学的本质探索之路。当然,这里胡塞尔批判的只是经验心理学的原则,并未反对理论心理学。胡塞尔正是通过描述和分析内在心理状态及其结合以及其活动方式,展开了在意识与确定性之间的艰苦探索,创立了他的现象学。
在胡塞尔看来,所谓“现象”,就是作为认识对象的事物在意识中的“显现”。因此,现象就是意识,胡塞尔现象学就是关于意识的哲学。在认识过程中,意识与意识对象的关系、意义的发生及其构成,是胡塞尔关注的焦点。实质上这也是哲学上的一个老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是,胡塞尔现象学所聚焦的意识,首先便排斥了心理学的内容。
此外,作为一种意识的哲学研究,胡塞尔现象学试图对人类意识提供描述的特殊形式,极力探求一种人类的纯粹意识状况。这种纯粹意识除了排斥上述的心理学内容,还要悬置日常生活经验,甚至知识和概念(这些问题本文在以下小节逐一展开)。可见,胡塞尔研究的意识(consciousness),与唯识学之“识”(vijāna)之间,具有多么巨大的差异!如果对于唯识学的“识”与现象学对象“意识”缺乏清晰的辨析和认知,表明对唯识学和现象学的核心概念出现误读,这就不可避免造成现象学与唯识学比较研究基础的坍塌,因而建筑于其上的任何讨论皆无意义。
二、 “二空”与“悬置”
唯识学主张“万法唯识”,即所有事物包括我都是空无,即“我、法二空”,只有识存在。可见“二空”说是一种形上学。现象学在讨论对象事物意义是如何呈现的问题时,首先要求意识处于纯粹意识的状态,因此要把意识中的经验内容以及知识和观念暂时排除出去。现象学采取的这个方法叫作“悬置”。可见现象学的“悬置”是方法论的,即对一切事物持怀疑论态度,假设万物皆“空”。很显然,“悬置”和“二空”之间只有表面的相似,而具有方法论与形上学的本质不同。
关于“二空,《成唯识论》开篇即由此展开:
今造此论,为于二空有迷谬者生正解故,生解为断二重障故。由我、法执,二障俱生,若证二空,彼障遂断。断障为得二胜果故:由断续生烦恼障,故证真解脱;由断碍解所知障,故得大菩提。又为开示谬执我法迷唯识者,令达二空,于唯识理如实知故。复有迷谬唯识理者,或执外境如识非无,或执内识如境非有,或执诸识用别体同,或执离心无别心所。(24)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1页。
所谓“二空”即是法空、我空,也就是外在世界和“我”皆为空无。玄奘译注编撰《成唯识论》的目的,首要就是破拆人们对于“二空”的迷惑和误解。(25)玄奘此说糅合了安慧等人的观点。参见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3页注[四]。这些迷谬就是“我执”和“法执”。“我执”就是主张起主宰作用的灵魂即“我”存在。“法执”即主张客观物质事物是实体性存在。人们由于这些迷谬,因此出现“二重障”,即烦恼障碍和所知障碍。如果证悟法空、我空,这些障碍就会破除消失,人生就会获得胜果或大菩提,得大自在。引文中列举了几种与识相关的谬误。第一是小乘一切有部的观点,认为“外境如识非无”,意思是外在世界实有,即我无但法有。第二是大乘空宗的“内识如境非有”,意思是识和外在世界皆无,否认了识的实体性存在。第三是《楞伽经》“执诸识用别体同”的观点,意思是八识用途不同,本体是一,把本识阿赖耶识与其他七转识混为一体。第四是小乘经量部的看法,即“执离心无别心所”,意思是除心之外没有心所法,即强调心是实在而否认识的实在。可以看出,《成唯识论》在这里既批评一切“有”的理论,也批评一切“无”的理论;既批评体用之识有别的观点,也批评离开心就没有心所法的看法。
与以上所有观点根本不同的是,在唯识宗看来,诸法和我皆空,但识是“有”不是“空”,即“二空识有”,唯有识为真实命根和根本实在。一切事物,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识变现的假设幻境。因此,《唯识三十颂》曰:
是诸识转变,分别、所分别。由此彼皆无,故一切唯识。(26)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488页。杨维中先生说:这一颂是“此论颂最核心的一颂,一般科判为‘正辨唯识’。”(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518页)
《成唯识论》解释云:
是诸识者,谓前所说三能变识及彼心所,皆能变似见、相二分,立转变名。所变见分说名分别,能取相故。所变相分名所分别,见所取故。由此正理,彼实我、法,离识所变皆定非有。离能、所取无别物故,非有实物离二相故。是故一切有为、无为,若实若假,皆不离识。“唯”言为遮离识实物,非不离识心所法等。……唯既不遮不离识法,故真空等亦是有性。由斯远离增、减二边,唯识义成,契会中道。(27)这是护法的观点,难陀等人观点从略。中道:梵文Madhyamāpratipad,意谓脱离极端,不偏不倚,是最高真理。(见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488-489页)
大意为,诸识转变是指识的三能变及其心法、心所法所转变的见分、相分,故有“转变”之名。所转变的见分就是分别,因为它能够吸取相分。做转变的相分叫所分别,因为是见分所取的。可见外界事物和我,离开识都是非实体的存在。因为离开能取见分和所取相分以外,没有别的事物。所以一切有为法(识所变)、无为法(识之体),不管是常住实法,亦不管是不相应假法,都离不开识。“唯”字是为了否定离识之外的真实事物,并不否定不离识的心所法、见分、相分、真如等。所以远离增、减二边见,无心外法,除增益边,这就是成立唯识,契合中道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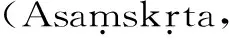
为此,《成唯识论》对于“法空识有”进行细致解说:
我法非有,空识非无,离有离无,故契中道。……谓依识变妄执实法,理不可得,说为法空。非无离言正智所证唯识性故,说为法空。此识若无便无俗谛,俗谛无故真谛亦无,真、俗相依而建立故。拨无二谛是恶取空,诸佛说为不可治者。应知诸法有空、不空,……故现量境是自相分识所变,故亦说为有。意识所执外实色等妄计有故,说彼为无。又色等境非色似色、非外似外,如梦所缘,不可执为是实、外色。若觉时色皆如梦境不离识者,如从梦境觉知彼唯心,何故觉时于自色境不知唯识?如梦未觉不能自知,要至觉时方能追觉,觉时境色应知亦尔,未真觉位不能自知,至真觉时亦能追觉。未得真觉恒处梦中,故佛说为生死长夜,由斯未了色境唯识。(31)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492-494页。
大意为,俗众所谓的我是无,只有真如和识是有。按此来说离有离无,就能契合中道。一方面,依照识变的见分和相分,来妄执万法为实有,当然不能成立,因此说万法为空;另一方面,虽然说法有(非无),而在离开妄执之后,证得正智和唯识性,也会认为万法为空。然而,如果认为识为无,那就没有俗谛了,俗谛没有也就无真谛。真谛和俗谛相互依存,否认真俗二谛就是恶趣空。诸佛都说恶趣空为不可救药。由此可知,一切法都有空和不空两种。在现量境(当下),万事万物是识变现为自己的相分,因此可以说为有。而相反的是,意识执着外界自然事物以为真实,这是虚妄计度产生的,故说为无。很显然,其他虚妄计度所执外法,看外在事物,其实犹如梦中之物,似是而非,都不是实在之物。等到觉醒之时人们方才觉悟。而众生在没有觉悟的时候,正如长夜之梦,不知万法唯识的道理。
概而言之,我、法之种种相状自性为空,皆为识之变现。大千世界,皆为假立虚幻之外境,而唯有识为实有。从《成唯识论》这个辨析中就可看出,“空”的义域被拓展到更深的本体论层面。
胡塞尔现象学要把所讨论的对象的一切,必须以直接展示和直接指示的方式加以描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现象学必须寻求它的起点。胡塞尔认为,现象学必须严格地清除一切对实存的设定。他把一种内在的(immanent)客观性,看作必须是,而且只能是观念的。在他看来,笛卡儿的怀疑性考察“我思故我在”,虽然提供了一个思维的绝对内在的明证性,但他又用“我思”来证明“我在”,企图由思维的明证性来确定经验自我的明证性,则不能成立,因而是无效的。“思维存在的明证性”与“我的思维是存在的”、“我思维地存在着”的明证性是有区别的。前者是绝对被给予性的,后者是自然科学和心理学中的客体。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客体当然不是绝对被给予性的。
薪酬立法和执法的公平是公务员薪酬市场化改革的保证,由于薪酬制度的弹性及标准的模糊导致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不公平。
胡塞尔认为,由于思维是一种绝对的被给予性,所以思维的直观认识(不是经验认识)是内在的。内在的,就是明证的。这个内在的之所以是确定无疑的,是“因为它没有表述其他什么,没有‘超越自身去意指什么’,因为这里所意指的是完全相应的自身被给予的东西”。(32)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0页。因此,思维的直观,可以获得认识的明晰性。这种明晰性是任何科学和经验的认识所无法达到的。比如,“一个想看见东西的盲人不会通过科学论证来使自己看到什么;物理学和生理学的颜色理论不会产生像一个明眼人所具有的那种对颜色意义的直观明晰性”,因此,“直观是无法论证的”。(33)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10页。与科学相比,所有科学知识对于这种直观来说仅仅是科学现象,因此,这些科学的成果和知识相对于这种直观来说都是不可靠的。
相对而言,胡塞尔把日常经验的思维看作为“超越的”。“超越的”意即指向思维之外的事物。认识要说明超出思维内在的外界事物,就必须要说明思维与外界事物的统一性,即要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因此必然会陷入认识如何可能的困境中。思维的内在直观认识则不具有这个问题,它意指的就是本身被给予的东西。要达到认识的明晰性,必须从科学的认识返回到思维的直观认识,从超越的认识返回到内在的认识,这就是胡塞尔所要求的“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现象学还原又称“先验还原”(transcendental reduction),目的是把认识活动中的主体还原到纯粹的思维内在性上去。胡塞尔说:
现象学的还原就是说:所有超越之物(没有内在地给予我的东西)都必须给以无效的标志,即: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有效性不能作为存在和有效性本身,至多只能作为有效性现象。(34)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11页。
后来胡塞尔用了一个希腊文词“ξποχη”(中译“悬置”)来表示这种超越之物的无效性,意即把所有超越之物“悬置”起来。“悬置”并非是清除,而是存而不论,即将那些超越之物用括弧括起来,就像数学里括弧中的东西一样,也像一种被切断电路的电线一样存在在那里。胡塞尔这种“悬置”的含义,第一是把我们从日常生活、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接受的理论或意见都放到括弧里,置于一边存而不论;第二是把一切存在,甚至是具有绝对自明性的存在(譬如我自己的存在)也要放到括弧里,置于一边。在我们的知识、经验、信仰、趣味甚至我们自身存在都被“悬置”以后,在先验还原的终端就出现了意识的“现象学剩余”(residue),即一个绝对的、必然的、纯粹的自我意识的区域。
实际上,胡塞尔这里“悬置”的不是物,“而是对物的一切荒谬解释”。于是,“一个当下可见的事实是,这里排除的是包括我们的意识在内的全部实在,而那种剩余物被称为‘纯粹的’或‘先验的意识’。”(35)泰奥多·德布尔:《胡塞尔思想的发展》,李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325、317、326页。这个纯粹意识为了自己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的东西。这是一个绝对的存在域,一个绝对的或超出经验的主观性的领域。意识的绝对被给予性保证着它的绝对存在。正因为如此,胡塞尔说:
现象学的还原这个概念便获得了更切近、更深入的规定和更明白的意义:不是排除实在的超越之物,而是排除作为一种仅仅是附加存在的超越之物,即:所有那些不是在真正意义上的明证被给予性,不是纯粹直观的绝对被给予性的东西。(36)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14页。
从上述比较可知,唯识学“我、法二空”理论,将主体和客体的先在性消解了,这与现象学的“悬置”思想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相近。但是,“二空”之余剩下的是“识”。“识”又分三阶段变现为八识,第一变为阿赖耶识,类似道或logos,第二变为“我”,第三变为“六识”。而现象学的“悬置”之后,剩余只是纯粹意识。因此,在具体认知过程中,唯识学“二空”思想的认知主体,是个“实有的”普通肉身,“我”及其我所具备全部经验、知识、信仰等是先在的,包括一切先在的观念、思想,并且自然发挥作用,认知主体的纯粹意识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现象学经过先验还原即“悬置”后的认知主体,实现了肉体、心理、知识和经验意义上的“空”,只存留纯粹意识。
另一方面,唯识学认为,作为认识对象的“现象”,是识变现的结果。而现象学认为,作为认知对象的“现象”,其来源和实在性则存而不论。当然,现象学不否定感觉的真实性,更不推论事物本身存在的虚无性,只是“悬置”对象事物。这是唯识学与现象学的又一个本体论之别。
可见,混淆了唯识学的“二空”说与现象学“悬置”说,也是对于唯识学与现象学在认识世界上根本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严重误读。
三、 “二分”与“显现”
在唯识学看来,无论是外在世界万事万物,还是作为主体的“我”,都是“识”“变”或者“转变”而来的。这个“转变”呈现出来就是“见分”和“相分”。见分指由识生起的对对象事物的看法,相分指识为对象事物呈现出来的形相,或者是由内识转变出的客观境相。现象学认为,现象就是作为认识对象的事物在意识中的“显现”。唯识学的“二分”说与现象学的“显现”说,可见二者表面有相似之处。但是,实质上具有根本的不同。
关于“二分”,《成唯识论》有充分和明确的表述:
彼相皆依识所转变而假施设。“识”谓了别,此中识言亦摄心所,定相应故。“变”谓识体,转似二分,相、见具依自证起故,依斯二分施设我、法,彼二离此无所依故。或复内识转似外境,我、法分别熏习力故,诸识生时变似我、法。此我、法相虽在内识,而由分别似外境现。诸有情类无始时来,缘此执为实我实法,如患、梦者,患、梦力故,心似种种外境相现,缘此执为实有外境。愚夫所计实我实法都无所有,但虽妄情而施设,故说之为假,内识所变似我似法,虽有而非实我、法性,然似彼现,故说为假。外境随情而施设,故非有如识,内识必依因缘生故,非无如境,由此便遮增、减二执。境依内识而假立,故唯世俗有,识是假境所依事故,亦胜义有。(37)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2页。
大意是,万事万物都是“识”的转变。“识”本义了别,这里包括心法及其相应俱起的心所法。“变”就是每个识从它自体转变生起,有二分境界呈现。因为所有万事万物都是“幻有”,故《成唯识论》在“二分”前用了“似”作界定。
此段文字中,关于“识变”有三种观点。第一是安慧,认为识体生时,转似相分、见分,因为相、见二分都依据自证分。依据相、见二分假说有我(见分)、法(相分)。但这种我、法离开相、见二分都不能存在。
第二是难陀等,认为由于内识转变出似外而实内的客观境相,由于似我似法的熏习,各种内识生起的时候,就变现为似我、似法来。这些我、法之相都是识变现的,但由于内识的虚妄分别作用,它们被看作好像是外在的东西。普通大众妄执外在世界之物为实有,就像色盲或梦游者一样,把假象和梦境当作真实。
第三是护法等,认为愚蠢的人认为实有的我和法,其实都是不存在的。但随顺虚妄心情而虚假施设,所以说为假有。把内识变现好像是有我有物,其实是假有,只是似我、似法在显现。外境是假有,而识不同于外境,是实有。内识必须依仗内因和外缘才能生起,所以不像外境那样是无。由此排除了增、减二种错误主张。从俗谛来看,外境是有;从真谛来看,识是实有。
简言之,在唯识学看来,无论是外在世界万事万物,还是作为主体的“我”,都是“识”“变”或者“转变”而来的。这个“转变”呈现出来就是“见分”和“相分”。见分指由识生起的对对象事物看法,是主体对于对象事物的认知和把握。相分指对象事物为识呈现在感官面前的相状,或者是由内识转变出的客观境相、影像。当然,这些境相似外而实内。周叔迦先生说:“宇宙既是这阿赖耶识的相分,所以换一句话说,便是宇宙充满在这阿赖耶识之中,不过宇宙在这阿赖耶识中,并不是如同我们人所见的形况。”(38)周叔迦:《唯识研究》,第25页。用唯识学语言说,相分是识所缘的对象,见分则为识之能缘。(39)《成唯识论》云:“似所缘相说名相分,似能缘相说名见分。”(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134页)
周贵华教授进一步解释说:“相分是见分之所缘内境,亦是见分生起之所依,所以称为见分生起之缘,即作为所缘(ālambana)之缘(pratyaya)。所谓所缘缘(ālambana-pratyaya)。但对见分而言,其所缘之相分不仅有自识所转变而成者,还有余识所转变而成者。这样,作为见分所缘缘的相分,可分为两种:一者为见分之直接所缘缘,称亲所缘缘,即为自识所变之相分;二者为见分之间接所缘缘,称疏所缘缘,即为余识所变之相分。”(40)周贵华:《唯识通论——瑜伽行学义诠》(下),第421页。他还认为:“识之亲所缘缘有二:一者为自识转变而成之影像相分,此是有分别之识与智所缘;二者为圆成实性真如,为无分别根本智所缘。”“影像相分者,谓当识生起时,由识转变而成之外境显现者,与见分相待俱时而起,从逻辑上看,是由作为识体之见分带现而起,故是见分之直接所缘境。此中,‘带’谓见分为识体领而俱起,‘现’谓在见分前现起为影像境。但同时,见分又要以相分为所缘缘才能生起。如《成唯识论》卷一:‘自识所变似色等相为所缘缘,见托彼生,带彼相故。’”“圆成实性真如是识之离言实性,当识生起时,与识不一不异而俱,方便说为为识所挟带而有,且由于其无相,不能变相而缘,只能无分别地亲证,即冥契,故亦是直接所缘境。”(同前,第421-422页)所谓亲所缘缘,就是每个人亲证(用六识亲自验证)的事物,而疏所缘缘,则是每个个体间接验证的事物。(41)周贵华说:“识之疏所缘缘,亦是见分所缘之境,但非是见分相待而起之自影像相分,而是余识转变而成者。”“疏所缘缘之例,如:众生自八识聚中余识所转变而成之相分;他众生之识所转变而成之相分。”(周贵华:《唯识通论——瑜伽行学义诠》(下),第422、423页)
从哲学思维的角度说,广延性物体呈现的具体表象,最终来源于概念思维。就具体的认知过程来说,相分作为识之所缘对象,可以认为是客观的。见分作为知之能缘,可以认为是主观的。从这里看出,所谓相分,具有某种“呈现”或“显现”的意思。做出这样的判断还基于对唯识学“识变”概念的考辨。
唯识学使用“变”(包括“转变”)一词,在《唯识三十颂》中共出现五次,即第一颂“彼依识所变,此能变唯三”,第八颂“次第三能变”,第十七颂“彼诸识转变”,以及第十八颂“如是如是变”五处,这五处“变”的梵文都是Priāma。而其中用“转”的梵文则为pravartate。关于“变”或“转变”的问题,众多的唯识专家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周贵华教授认为,“由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识所变,此能变唯三”,“此中之‘转’,勘梵文为pravartate,即生起、现起之义;‘变’、‘能变’,勘梵文为Priāma,即转变之义。三种能变指三类识,即阿赖耶识(‘异熟’)、末那识(‘思量’)即眼等六识(‘了别境识’)。以能变名八识,意味此八识皆有转变之功能作用。”就此可见,“转”和“变”之间还是具有不同含义。在他看来,“转,即现起/生起,梵文为pravartate,藏文译为’byung ba,汉译译为生、起、转等。在识之转变与显现中,‘转’用于指相分,以及见分之现起/生起。……‘转’与‘变’之义差别是明显的。‘转’是从果上而言的,指相分以及见分之生起/现起;‘变’则是从因上而言的,指识由转变而成相分以及见分。”“变成与变生(摄变现)含义差别明显。变生(摄变现)指识转变而从其自体生起相分,或者见、相分,识自体仍存,与所变生之相分,或者见、相分,同为依他起性之体性。但变成意味,在识转变后,唯有见、相分,二者皆为依他起性之体性。”他还说:“相分依于识之转变而在见分前现起(章案:即表象客观呈现未进入意识之前),故称识转变而现起相分,所谓变现。但依于转变而生起之见分在见相的能所形式的关系中是不现前的(章案:此处意谓表象与意识是分开的),因此不能说识转变而现起见分,而应说识转变而生起见分,即应称变生。在此意义上,见分与相分皆是识变生的,而唯有相分是识变现的。”(42)周贵华:《唯识通论——瑜伽行学义诠》(下),第404、410、412、411页。意思是,见分是识变的潜在状态,相分是识变的现实状态。相分的这种现实呈现状态与“显现”一词的含义非常接近。
而且,玄奘还着意“转变”中的“显现”之意。周贵华教授认为,在世亲唯识学中,“影像/相分虽然是幻有性,但为有体法,即依他起性,完全不同于遍计所执性质的外境、二取这样的无体法。换言之,相分虽是依于识现起而不离于识,但与识一样是依他起性,二者在存在性上平等。因此,世亲用‘转变’(玄奘多译为‘变’)来替代‘显现’,而主张相分是识转变而成的。”“转变/变这一术语,虽然很好地说明了相分以及见分与识之因果关系,但没有直接强调出相分作为影像而现起/现在前之义。因此,在玄奘所译的唯识学典籍中,就出现了‘变现’一语。‘变现’义为,识生起时,转变而现起相分。如《成唯识论》云:‘有漏识上所变现者,同能变识皆是有漏,纯从有漏因缘所生,是苦集摄,非灭道故。……然相分等依识变现,非如识性,依他中实。’(《成唯识论》卷十……)意为,识生起时,即变现或说转变而现起相分,而此相分虽与见分有能所性质之别(‘非如识性’),但同见分皆是因缘而生,为依他起性。”(43)周贵华:《唯识通论——瑜伽行学义诠》(下),第409、410页。意思是相分具有对象一定的客观性。
而日本学者上田义文则明确认为:“《成唯识论》中所展开的唯识学体系以相分见分起于识这一转变思想为根本。……那么,世亲唯识学的建构以什么概念为基础的呢?答案就是Pratibhāsa这一概念。”“Pratibhāsa的汉译有显现、显现似、现似、似、变似等多种方式。其含义有二:一、为‘所得知(所见、所闻、所觉、所知)’,‘显现’正含此意。二、所得知者虽然被得知,但是却非实际存在,故被喻为幻、梦。”但是,“在《成唯识论》中,Pratibhāsa与Priāma被完全混淆。”例如,“在《三十颂》第十七颂Priāma的解释中,就把‘转变’变成了‘变似’。识体转变相分见分,这既是‘转变’,同时也是‘显现’。‘转变’(Priāma)与显现、似(Pritibhāsa)被认为同义。”(44)上田义文:《唯识思想入门》,第11、12-13、85、86页。
上田义文的这一观点,与周贵华居士基本相同,周贵华居士还作了进一步的分别说明:“显现,梵文为ābhāsa,pratibhāsa,prabhāsa,avabhāsa等,藏文一般译为snang ba,在唯识学中之基本用法是虚妄显现,即无似有显现,或者无显现为有。……此意义上之显现可分为两类:一者总略性质的显现(ābhāsa等),如无外境但似外境显现,或者无外境显现为外境;二者各别性质的显现(pratibhāsa 等),如《辩中边论》云:‘识生变似义,有情、我、及了。’此中,‘变似’勘梵文为显现(pratibhāsa)。引文意为,识生而各别显现为义、有情、我与了别,但此所各别显现之‘义’等,非有。”(45)周贵华:《唯识通论——瑜伽行学义诠》(下),第409页
以上引文中的论证证明,《成唯识论》所用的“转变”(Priāma)一词自然含有“显现”(Pritibhāsa)之意。可见,唯识学所谓识变为见分、相分之意,确定含有现象“显现”、“呈现”之思想。而且,这种“显现”也展示了事物的本质。《成唯识论》曰:“虽诸有情所变各别,而相相似,处所无异。如众灯明,各遍似一。”(46)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140页。尽管在唯识学看来,法、我皆空,一切事物为幻有,但这个“幻有”也具有暂时可感知的实有性质。
胡塞尔现象学始终关注的就是“现象”。现象,希腊文 φαιν′ομενον,胡塞尔认为该词具有两个涵义:
(1)一方面是指客观性在现象中显现出来,(2)另一方面是指客观性,这个客观性仅仅是在现象中显现出来的,并且是‘先验地’在排除了一切经验前提的情况下显现出来的客观性。(47)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4页。
胡塞尔还认为,在认识现象学中,现象首先被用来表示显现本身:“根据显现和显现物之间本质的相互关系,现象一词有双重意义。φαιν′ομενον(现象)实际上叫作显现物,但首先被用来表示显现本身,表示主观现象。”(48)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18页。显现,从另一角度说,也是对象事物在意识中的呈现,是一种主观现象。因此,确切地说,在显现中的那些事物不是对象本身。就是说,对象事物呈现为某种“现象”,实质上也是一种意义的构造。这个“被给予的”意义并非完全属于对象事物本身的。胡塞尔说:“如果在这里为了使被称为‘被给予性’的东西得以出现而需要这种形成和构造的现象,那么这些现象就在其变化的和非常奇特的结构中,在某种意义上为自我创造对象。”(49)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60页。尽管在现象学还原之后,对象也是只有在认识中才是被给予的。因为,人的认识活动或能力不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到处都同样适应的空洞的形式,像一个空口袋,在里面可以随意装进东西。内在的被给予性并不像它最初所显示的那样简单地在意识之中,就像在一个盒子中一样。相反,内在的被给予性开始只在“现象”中显示自己。
对象只有在认识中才是被给予的,表明对象在意识中自我构造的性质。思维对象这种自我构造的性质,正揭示了思维的对象性质。胡塞尔说:
任何思维现象都有其对象性关系,并且任何思维现象都具有其作为诸因素的总和的实在内容,这些因素在实在的意义上构成这思维现象;另一方面,它具有其意向对象,这对象根据其本质形成的不同被意指为是这样或那样被构造的对象。(50)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13页。
对象是在思维意向的意义上构造自身,显示出被给予性。因此,认识过程中,思维必定具有意向。“认识体验具有一种意向,这属于认识体验的本质,它们意指某物,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对象有关”。(51)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12页。当然,胡塞尔认为这种思维的意向并非直接指向外在实体,而仅仅是思维对象自身构造的一种活动特征,即一种指向意义的意向。认识与对象在本质上的这种相互联系,显示出目的论的相互依存性。“而只有在这种联系中,客观科学的对象,首先是实体的时空现实的对象才构造自身”,成为思维把握的对象。(52)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64页。因此,对象只是一种意向的东西,它在认识中构造着自身,同时也就构造着认识。
思维的这种意向性,不仅是认识思维的本质,也是认识活动的本质。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上任何被给予我们意识中的事物不仅是只以一种方式显示出来,而是不断以新的方面或新的外观来显示给我们。同一种颜色在绵延的时间中表现为浓淡不断更新的色彩,同一个形态也表现为不断变化的外观。一个物体在每个人所看到的印象中并不必然是绝对相同的。某人看到某物体,只是意味着他自己当下的意识内容被有规则地置入。他之所以能以这样的方式看到“这一物”,是与他的意识活动的意向性密切相关的。(53)就像朱光潜先生说的,一个画家、一个植物学家与一个商人看到同一棵古松的形象是不同的。见《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8页。“一般对象本身只存在于它与可能认识的相互关系中”。(54)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64页。因此,胡塞尔说,解决了这一问题,实质上就是“阐明认识的本质和认识与认识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意义的大问题”。(55)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64页。
可见,胡塞尔现象学关注的“现象”就是“显现”,也就是意识。这里的“显现”与唯识学的“二分”含义十分接近。但是,“二分”与现象学的“显现”理论之间仍存在重大或本质的不同。
还是回到《成唯识论》对于《唯识三十颂》第十七颂曰“是诸识转变,分别、所分别。由此彼皆无,故一切唯识”的解释:
是诸识者,谓前所说三能变识及彼心所,皆能变似见、相二分,立转变名。所变见分说名分别,能取相故。所变相分名所分别,见所取故。由此正理,彼实我、法,离识所变皆定非有。离能、所取无别物故,非有实物离二相故。是故一切有为、无为,若实若假,皆不离识。“唯”言为遮离识实物,非不离识心所法等。或转变者,谓诸内识,转似我、法外境相现。此能转变即名分别,虚妄分别为自性故,谓即三界心及心所。(56)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488-489页。
虽然前文已有解释,这里还是重复一下。按照护法等的解释,颂文“是诸识”是前文所说三能变的“八识”及其心所法,都能变现为相似性的见分、相分,故有“转变”之说。所变中以所变见分叫做分别,因为见分能取于所变的相分,生起种种分别,因此叫分别。识所变相分叫所分别,因为它是见分所取之相。根据这种正确理论,人们所主张的一切实我、实法,离开识的所变,都是肯定不存在的,因为离开能取见分和所取相分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事物。没有真实事物能够离开能取、所取二相。所以一切有为法(识所变)、无为法(识之体),不管是常住心色实法,亦不管是不相应行假法,都离不开识。唯识的“唯”字是为了否定离识之外的真实事物,并不否定不离识的心所法、见分、相分、真如等。而难陀等认为,“转变”就是说的我们内心,转变出来了相似的(依他)我相和法相,以为是外面境界相状显现。所以这个能转变的识就叫分别,虚妄分别是它的自体,这三界众生的心和心所就是能分别。可见,转为见分、相分的有八个识,还包括三界众生心、心所法之物,包括一切有为法、无为法,意识对象只占其中极小成分。
按照以上所引《成唯识论》文字所述,宇宙万物都是由八个识转变出能分别的见分,和所分别的相分。首先,关于第八识阿赖耶识的见分和相分,《成唯识论》在解释《唯识三十颂》第一颂“不可知执受、处、了”时说:
此中了者,谓异熟识于自所缘有了别用,此了别用见分所摄。然有漏识自体生时,皆似所缘、能缘相见,彼相应法应知亦尔,似所缘相说名相分,似能缘相说名见分。若心、心所无所缘相,应不能缘自所缘境。……若心、心所无能缘相,应不能缘,如虚空等,或虚空等亦是能缘。故心、心所必有二相。(57)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序言》,第134页。
大意是,这里所说的“了”,意指异熟识在自己的所缘事物上有明了分别的作用,这种明了分别的作用由见分所摄。(58)分别:梵文vibhājya,思量识别各种事物之理,是心法和心所法的异名。参见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461页注[二〇]。有漏心即分别,是五法中的分别。阿赖耶识无漏位的性状,这里就不讨论了。然而当有漏识自体就是凡夫具有的阿赖耶识生起的时候,都好像有所缘的相和能缘的见这两种相状显现出来。那么,第八识的心、心所亦是这样。好像有所缘的相状称为相分,好像有能缘的相状称为见分。“故识行相即是了别,了别即是识之见分。”(59)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135页。如果心法、心所法没有所缘之相状,就那见分就不能缘自己的境界。如果心法和心所法没有能缘之相,应当是不起能缘作用,如虚空等一样,或者说虚空等也是能缘。所以心法、心所法必有能缘、所缘二相。也就是说,异熟识或阿赖耶识(也就是每个现实生存的普通个体)对于所有所缘事物的明了分别,都与心、心所相关。可见这里的见分、相分之“境”,绝不仅仅是意识对象。
按照唯识学理论,在一个普通有情众生的八识之中,阿赖耶识为根本,余七识依存于阿赖耶识。周贵华居士认为:“诸转识或诸法之显现本于阿赖耶识,在每一刹那形成一幅图景,且随着阿赖耶识相似相续地流变,而有幅幅相似之图景相续地展现。简言之,宇宙的形形色色的现象,皆可归为八识,最终根于阿赖耶识,而联系为一体。”在认识活动中也是这样。“不仅八识之聚呈现一图景,而且每一识皆是图景识……而且此八小图景识各各之显现独特,不可取代,互相补充,聚为一大图景识。此中,各小图景识是相应于各自所缘境而成立的。八识聚之图景识为诸识和合而成,故可称和合图景识。……八识之小图景识和合为和合图景识。起关键作用者为意识与阿赖耶识。”(60)周贵华:《唯识通论——瑜伽行学义诠》下,第425-426页。
此外,唯识学把外境作为识的相分,依他起性所摄。但唯识不是一个识聚。因此,所有见分、相分或者说呈现在普通个体之前的显现对象,都与八个识及其心、心所相关,而且每一普通众生皆有自境界中之三界图景呈现。因而“二分”绝不是纯粹的意识活动。《成唯识论》有很多相关表述。例如:
“识”言总显一切有情各有八识,六位心所,所变相、见,分位差别,及彼空理所显真如,识自相故,识相应故,二所变故,三分位故,四实性故,如是诸法皆不离识,总立识名。(61)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493页。
“识”从总的方面说明一切众生各有八识,各有遍行、别境、善、烦恼、不定六位心所法,各各自体分及此所变相、见二分,及色、心分位与二十四不相应等,以及二无我空道理所显现的真如。因为心法是识的自相,心所法是识的相应法,色法是心、心所二种所变的相分,二十四种不相应行法是心法、心所法和色法的分位,无为法是识的实性,即心法、心所法、色法、不相应行法的实性。这些“色法”之“色”有变坏、质碍、示现等义。有质碍就是说事物由基本粒子构成,因而有广延。如是这样的五法都不能离开识。而所有外界事物名称亦为假立。
具体的认知活动也是这样:
极成眼等识五随一故,如余,不亲缘离自色等。余识识故,如眼识等,亦不亲缘离自诸法。此亲所缘定非离此,二随一故,如彼能缘。所缘法故,如相应法,决定不离心及心所。(62)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492页。
大小乘都共同承认的识称“极成”的识。眼等五识极成识,以及五识中任何一种,和其余四识一样,不能直接缘取离开眼识之外的色等。因为其余的识也是识,和眼识一样,亦不能直接缘取离开自识的各种事物。这种直接所缘(相分)肯定离不开识。因此,相分、见分只随一摄取,不能分别摄取,如同能缘见分离不开识体一样。因为是所缘法,就如心、心所相等法一样,肯定离不开心法和心所法。不离开心法、心所法的意思,就是经验所感知的不是纯粹的,与心理、精神活动一体同时进行。例如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也是一种观感,但是有强烈的心理内容,不是纯粹的知觉活动。
大略来说,见分、相分是识内在结构,摄为一识(摄心所)。而八识的相分各不相同,前五识的相分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感觉对象,包括色、声、香、味、触五尘。第六识意识的相分是六尘,除前五尘之外再加法尘(色、声、香、味、触、法)。第七识末那识的相分是阿赖耶识的见分。阿赖耶识的相分是根身、器界、种子,实际上是宇宙万有。每人有八识,摄为一识聚。或者说每人有识聚,含摄八识。对八识而言,其自所缘境各不相同,意识除外,意识不仅缘自所缘境,亦可缘其余诸识之所缘境,乃至一切法。前五识之境皆为有漏法。
由此可见,首先,“二分”同时具有本体论、存在论和认识论的意义。从本体论角度说,整个现象世界是六识的相分,就是说现象世界的本质是前六识。所变识相,就是一切我相和法相都离不开三能变识相,证明一切所变识相都表现为能变的见分和相分,一切诸法都是头脑所思和所得而成,体现了万法唯识是哲学上的观念论(idealism,或称唯心论)。因此,二分说首先是本体论,是全部外在世界构成原理。
从存在论的角度说,第七识末那识取第八识之见分为内自我,是阿赖耶识的相分。这是末那识的特点,即无间断“恒审思量”,妄执自我。“我”,或者说当下的具体生存个体(相当于海德格尔的“此在”),是末那识的幻相。这是末那识的相分,也是阿赖耶识的见分。
从认识论角度说,前六识是末那识的相分,而感知的现象世界是六识的相分。现象或表象的构成,则属于认识论,与具体的个别的当下的认识活动相关。可见只有在具体的认知过程中,二分法才属于认识论。前六识见分与相分又属于一体,表明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其实合二为一。这种情况在几乎所有西方哲学家理论中都存在。例如黑格尔的理念论是本体论,具体的认知则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个体与认知对象发生的相互作用。当然,理念也在根本上支配认识,认识也是对于理念的把握。
此外,就认识论而言,“二分”不仅仅关涉感知的意识活动,也与心理活动相关。因此,“见分”也不能等同于意识意向性,其中有心理、情绪、观念等内容,当然也有心理甚或意识的意向性。
太虚大师认为:“今以法相唯识连称,则示一切法(五法三相等)皆唯识所现,唯,不离义。识,即百法中之八识及五十一心所。其余四十一法亦皆不能离识而存在,以一切法多分受识之影响而变化故。现有二义:一、变现义,如色法等。二、显现义,如真如等。法相示唯识之所现,而唯识所现即一切法相,唯识立法相之所宗,故法相必宗唯识。”(63)太虚:《法相唯识学》,第29-30页。而涉及“真如”的问题,本文在第六节详述。
胡塞尔现象学的“显现”说,意在描述对象事物在意识中的呈现过程中,具有意义意向性特点,而唯识学“二分”说,则是万事万物在个体面前的展示,不仅仅是一种意识活动,还包括情感、心理等等因素,因此也不仅仅是认识意义上的,还有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的。由此可以看出,唯识学的“二分”,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显现”之说,具有多么遥远的距离!
四、“自证分”与“意向性结构”
见分、相分、自证分、证自证分,是唯识学“识变”即识之转变各种事物过程中的重要概念。见分、相分是识内在结构,摄为一识(摄心所)。相分和见分所依的自体是自证分。自证分是二分认识的明证。意向性结构是胡塞尔现象学所论证的意识的内在结构,是对象事物“意义”呈现的根据,对于认识活动具有根本的意义。自证分与意向性结构这两个概念之间也具有似是而非的特点。
唯识学关于四分理论,应该首见于难陀提出见、相二分学说。后来陈那认为,除见分、相分,还有自证分。自证是证明自体的作用。当见分发生作用时,自证分便给以证明。安慧继承了难陀和陈那的思想,虽然也承认三分说,但认为识法分别只是“虚妄分别”,在此分别上的见、相二分即“二取”(见分属于能取,相分属于所取)是遍计所执性,都是不实在的。只有自证是实在的,属于依他起性。因此,从心分来说,见分、相分、自证分三分实际就是一分,即自证分。后来护法又提出四分说,即见分,相分,自证分,证自证分。(64)参见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183-188页;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136页注[三]。《成唯识论》主要体现了护法的思想。因此,我们由《成唯识论》入手。
关于见分、相分、自证分以及证自证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成唯识论》有集中论述,为了完整理解唯识学自证分的思想,故全文录引这段较长的文字:
达无离识所缘境者,则说相分是所缘,见分名行相,相、见所依自体名事,即自证分。此若无者,应不自忆心、心所法,如不曾更境,必不能忆故。心与心所同所依根,所缘相似,行相各别,了别、领纳等作用各异故。事虽数等,而相各异,识、受等体有差别故。然心、心所意义生时,以理推徵各有三分,所量、能量、量果别故,相、见必有所依体故。如《集量论》伽他中说:“似境相所量,能取相自证,即能量及果,此三体无别。”又心、心所若细分别应有四分,三分如前,复有第四证自证分。此若无者,谁证第三?心分既同,应皆证故。又自证分应无有果,诸能量者必有果故。不应见分是第三果,见分或时非量摄故,由此见分不证第三,证自体者必现量故。此四分中前二是外,后二是内。初唯所缘,后三通二,谓第二分但缘第一,或量非量,或现或比,第三能缘第二第四,证自证分唯缘第三,非第二者,以无用故,第三第四皆现量摄。故心、心所四分合成,具所、能缘无无穷过,非即非离唯识理成。是故契经伽他中说:“众生心二性,内、外一切分,所取、能取缠,见种种差别。”此颂意说众生心性二分合成,若内若外,皆有所取、能取缠缚,见有种种,或量非量,或现或比,多分差别,此中见者是见分故。如是四分或摄为三,第四摄入自证分故。或摄为二,后三俱是能缘性故,皆见分摄,此言见者是能缘义。或摄为一,体无别故。如《入楞伽》伽他中说:“由自心执著,心似外境转,彼所见非有,是故说唯心。”(65)此前文字为“执有离识所缘境者,彼说外境是所缘,相分名行相,见分名事,是心、心所自体相故。心与心所同所依缘,行相相似,事虽数等,而相各异,识、受、想等相各别故”。说小乘(除正量部外)主张离识之外,有一种实在的所缘境界。他们认为,外境是所缘的对象,相分是行相,而见分叫做“事”,因为见分是心法、心所法的自体之相,相分是心、心所的行相。心法和心所法都同所依一根,同所缘一根,俱缘一境,因此它们的行相相似。“事”虽然是多种,其行相各不相同,因为识的行相是了别,受的行相是领纳,想的行相是计度名言,行的行相是行为造作,所以心、心所的行相各有区别。(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135页)
全文大意为:达到领悟离识之外就没有客观外境的人们,则说相分是所缘的境界,见分属于行相。而相分和见分所依止的自体则称为“事”(梵文artha,为因缘和合产生的有为法。),这个“事”即自证分。如果没有自证分这个自体,心法和心所法就不能回忆从前所作之事,就像未曾发生的事情一样必然不能回忆。虽然心法、心所法所依之根相同,所缘之相相似,但行相各有不同。因为识的行相是了别,“受”的行相是领纳,“想”的行相是计度名言,“行”的行相是行为造作,所以心、心所的行相各有区别各不相同。“事”虽然是多种,其相各不相同,因为识、受、想、行等的自体有差别。然而每一个心法、心所法产生的时候,在道理上推论,则每个都有三分的区别:第一是能量,第二是所量,第三是量果。所量是相分,能量是见分,相分和见分一定要有所依的本体,那就是自证分。如《集量论》说:“外在的似境之相分是所量,能取相的见分是能量,自证分就是量果。能量、所量、量果的本体是一,故三种本体没有区别。”如果对心法、心所法再仔细分别,应当有四分,即前三分加证自证分。没有证自证分就不能证明自证分的存在。既然自证分与证自证分都是一种内心之分,应当是都能证知。假设自证分缘见分时,见分是所量,自证分是能量,如果没有证自证分,自证分就没有量果了。因为,凡有能量就必有果量。不应把见分称之为自证分的量果,因为见分通三量,有时候是非量,是错量,是不可靠的。因此,见分不能证知自证分,证知自体一定要依靠现量。每个心、心所都有四分,四分之中,相分、见分属于外在之缘,自证分和证自证分属于内缘内。另外,相分只属于所缘之境,而见分、自证分和证自证分不仅通所缘,还通能缘。就是说,见分只能缘相分,有时候是正量,有时候是错量,而现量和比量都有。自证分不但能缘见分,而且能缘证自证分。而证自证分只能缘自证分,不能缘见分。因为见分缘自证分,没有缘证自证分之用。自证分和证自证分都属于现量,所以可以互量,又可以互证。由于这些道理,无论心法、心所法,都由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合成,具有所缘和能缘。既然自证分可以反证证自证分,就不用四分之后第五、第六……证明,故没有无穷演绎的过错。四分不是一个,也不可以分离,非相即亦非相离,唯识道理由此成立。《厚严经》说:“众生之心有二性,内里二分为一性,外面二分为一性;所取是相分,能取是见分,被此二分所缠绕,所以见到种种差别和不同。”意思是众生之心由内、外二性合成,都有所取、能取的缠缚,见分有种种差别,或者是非量,或者是现量,或者是比量。颂中“见”指见分。上面这种四分,也可以合为三分,就是将第四分证自证分合入自证分。或者将四分合为二种,一分为相分是所缘,后三分见分、自证分和证自证分都是能缘,属于见分所摄。此处所说之“见”,不单指第二分,凡有能缘的功用,都属于见分。或者四分合为一种,因为它们本体无区别。如《入楞伽经》说:“由于自己内心的执着作用,虽然有心转变的境界,也认为有实在外境的产生。其实人们所见的客观外境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唯心。”
此段文字虽然烦琐,但有几个要点:
第一,自证分是相分和见分依止的本体,也称作“事”。
第二,如果没有自证分,心法和心所法自身就不能有忆念功能,就像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不会回忆一样。
第三,外境之相分是所量,内识见分是能量,自证分是量果。能量、所量、量果的本体是一,故三种本体没有区别。(量:人的认识,如同以尺子量布,故喻之为量。)
第四,如果对心法、心所法再仔细分别,应当有四分,前三分加证自证分。没有证自证分就不能证明自证分的存在。既然同是心的分有,那就应当是都能被证知。没有证自证分,自证分就没有量果。不应当把见分称之为自证分的量果,因为见分通达三量,有时候为错量有时为正量。因此,见分不能证知自证分,证知自体一定要依靠现量。
第五,四分之中,相分、见分是外缘外,自证分和证自证分是内缘内。自证分能缘见分和证自证分,证自证分只能缘自证分,不能缘分见分。
第六,心法、心所法由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合成,没有无穷演绎的过错之过,具有所缘和能缘,非相即亦非相离,唯识道理由此成立。
深入理解关于自证分的这六个要点,必须要了解唯识学四分和自证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具体内涵。按照吕澂先生说法,四分思想源于小乘经量部。经部对于大乘的影响,第一是心法缘境的“带相”说。经部认为心之缘境不是直接的,心缘之境非境本身,而是以境为依据,由心变现出来的形象(变相)。换言之,心法缘境都是间接以影像为凭的,心所知的是心自身的变相。这一观点与因果异时论有关,因为第一刹那是根境,第二刹那识生时已经没有实物了。后来陈那将 这个思想引导入瑜伽学说之内。第二就是“自证”理论。自证有两种意思:一是心自己了解自变之相。但经部原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第二种意思,即心在了解对象时,同时还对本身有反省作用。譬如灯既照亮了物,也照明了自身。就像眼见青草之时,同时也了解自己“见”了,后来的回忆也知道“见”了青草,这就是证明。(66)参见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143页。由此可见“自证”和“回忆”之说基本含义。
首创二分说的难陀,主要是立足于世亲在《摄大乘论》中提出唯识成立的三点理由:第一是唯识无义。“义”即境。意思是心法中只有识而无境;第二是有见、相二。意思是虽无实境,但幻境亦有来源,来源就是识。心与境是以“见”“相”关系统一在识中;第三,种种相生起。意思是六识生起的种种相,仍在识的范围内。由此三点推论而成立唯识。此外,难陀同时又与种子说相联系而创种子新熏说。“在他看来,见相分之转变、显现,是由于种子的功能,种子则由熏习而起。”这里也可以看出,见、相二分永远不能离开识。后来陈那认为,相分引起见分,见分所得与相分一模一样。因此,相分(所缘)也就是内境。这样,第一,相分是有实体的,实在的。第二,见分也有其行相。这被称为“有相唯识学”。在此基础上,陈那提出自证分概念。他认为,“见相交涉的结果,就是见了解相,这种了解,是亲切的自知,所以叫它‘自证’(证指触证,如手亲自摸到而无间隔)。自证是用来作为心的自体的,同时用来证明自体的作用。换句话说,当见分发生作用时,自证分便给以证知。”(67)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183、186、185页由此可知,自证分含有亲历、亲证的意思。
很多大德和专家对于自证分的解释,基本上大同小异。太虚大师说:“识有三分:一自体分,二见分,三相分。见分为能知,相分为所知,识即知识,显得知识即是能知。……浑然不觉的觉心为自体分,自体分分能所知则有见相二分,见分为识体一种觉知之用。相分为见分所知之相。体,见,相,合称三分也。八识各有各之相分见分自体分,其各心所亦然也。复次,唯二分能知为心,三分皆所知为境,自体分为浑然不分之心觉,亦可成所知境。能缘即能知,所缘即所知,能知二分,指自体及见分而言。浑然不分之自体分,略同罗素非心非物之中立一元,然一分别则成见分相分,见分即能了知相分,而见相分皆依浑然一体之自体分,此自体分一名自证分,以有同时又了知于了知之见分故。换言之,不惟了知知识何种,并了知何种知识,皆自证分之义也,自体分见分相分皆所知境称所缘三分。自体分见分为能知心称能缘二分。”(68)太虚:《法相唯识学》,第52页。
杨维中教授认为:“唯识宗又把心的能缘、所缘作用分作能量、所量、量果三量。‘量’意为量度,心识能量度境相的作用叫作能量,被心识所量度的境相叫作所量,而果量是量度已成后的效果。唯识宗以三量配合‘四分’以说明认识的过程:第一,见分缘取相分。唯识宗认为,人们的认识直接所面对的并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识体上变现出来的相、见二分。认识过程进行之时,以相分为所量,见分为能量,自证分为量果。而除五识所缘的‘相分’之外,其余诸识之相分均不排除主体的执持变现作用。第二,自证分缘取见分。这是认识主体对认识能力及其所为做的第一层次的反思审定。当其进行时,以见分为所量,自证分为能量,证自证分为量果。第三,证自证分缘取自证分。这是认识主体自身的自我反省,当其进行时,以自证分为所量,证自证分为能量,复以所量自证分为量果。第四,自证分缘取证自证分。这是认识主体反过来对主体的反思系统进行的反省审定,当其进行时,以证自证分为所量,自证分为能量,复以所量证自证分为量果。将此四个阶段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唯识宗不将其关注重点放在认识主体如何形成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上,而是深入细致地探究认识主体的心理过程。”(69)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下),第700页。
可见,所谓自证分,就是相分和见分所依赖的自体。自证分的大致特点,第一是识体本身的功能;第二是有亲证性,例如通过回忆来证明发生的亲历亲为事件;第三具有自明的性质,像光照一样自明自证。但是,自证分概念不具有现代内省心理理学的含义,完全停留在日常经验范围之内的描述性上,当然也不是自我与世界表象存在的证明。
之后护法虽然提出四分说,理由是“‘见’‘相’二分是一重关系,对于心的全体来说,这是比较外围的一部分。到了‘自证’,就属于核心部分,属于内缘,而内缘复有能所。能,就是‘证自证’,所,就是‘自证’。这又是一重关系。由这两重关系就构成了四分说。”(70)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188页。但是,证明存在自证分的是证自证分,证自证分是否需要被证明?周贵华居士说:“在自证分被证自证分认知之后,证自证分亦必须有能认知者。那是否还需要再区分出一个证证自证分?由此乃至有无穷个证证……证自证分?这样的无穷后退没有终结,但事实上认知过程是有个终结的,因此,护法认为,证知证自证分者必须落实在已有的相分、见分与自证分中。相分、见分不能是认知内在认知元素者,此在前已述。但自证分作为内在认知元素,完全可以承担认知内在认知元素之任,因此,认知证自证分者,即是自证分。这样,自证分与证自证分二者间构成一个认证之循环,从而终结了识之整个认知过程。换言之,证自证分认证自证分,自证分认证证自证分,二者互证构成循环,避免了认证之无穷后退,将识之整个认知过程予以终结。”(71)周贵华:《唯识通论——瑜伽行学义诠》(下),第415页可见,所谓证自证分的设立,其实是四分说一种逻辑意义上完整的需要。
对于证自证分以及四分的关系,周叔迦先生比喻说:“这自证分譬镜子,这见分便是镜子的光明,这相分便是镜子里的影像,这证自证分便是镜子的他,有了他,然后这镜子才能东西南北随意所照。证自证分的作用是对自证分的,自证分的作用是对见分的,见分的作用是对相分的”。(72)周叔迦:《唯识研究》,第19页。韩廷杰先生也比喻:“相分如镜中像,见分如镜子的明净,自证分如镜体,证自证分如旋转镜体的把。”(73)玄奘译,韩延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序言》,第19页。
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一词来自拉丁文“intendere”,这个概念出自中世纪哲学。胡塞尔从布伦塔诺那里接受了这一概念,并由此建构了他学说的核心理论。有人说:“胡塞尔是一个有体系的思想家,他把认识论、本体论、逻辑和现象学联系起来,并作为一种方法论,发展了这些学说。几乎所有这些工作的基础,是他的意向性理论。”(74)David Woodruff Smith and Ronald Mc Intyre: Husserl and Intentionality,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2,p.14。胡塞尔自己也说:现象学,不论作为意识的哲学理论,还是作为对人类意识提供描述的特殊形式,简单说就是意向性的理论。意向性“表现了意识的基本性质,全部现象学的问题……是分别地来源于此”。(75)胡塞尔:《观念1》ξ146,F.Kersten 英译本,第349页。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emenological philosophy,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2.参见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50页。
胡塞尔首先采用了布伦塔诺关于所有意识都指向对象或是意向的见解,但胡塞尔不是根据意识所指向的(direct toward)真实对象,或是伴随意识指向动作的实际精神观念来说明意识的意向性,而是根据意识所指经的(direct through)抽象的内涵结构(语言意义的模拟)来说明意识的意向性。如果说,布伦塔诺的意向性是一种心理的意向性,那么,胡塞尔的意向性则是一种意义的意向性。从本质上说,胡塞尔使用的“意向”一词,与通常含义“意图”无关。胡塞尔意向性学说的目的是描绘意识的性质,在日常语言表达方式中挖掘底层的意义或观念性结构,从意识的先验结构中寻找逻辑的基础。由此亦可见,胡塞尔现象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不是心理而是意识。意向性,在这里涉及一个根本性的认识论问题。
胡塞尔认为,日常的意识活动的对象不是一种精神的或“内在的”(immanent)实体,而是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实体,或者说是一个物理对象。某人看到一棵树,他的知觉对象不是一个意义资料(sense-datum),或其他什么意向的对象,而就是自然界中的物理的个别体一棵树。只有内省的意识活动是指向主体的状态或是主体自己的意识流中的过程。正是由于存在这两种不同的意识活动,所以,在认识活动中,指向对象的意识活动或经验,与意识活动意指(intend)的对象是有区别的。例如在观察一棵树或一朵花时的意识活动,与我们的意识在活动时所指向的某一对象不是一回事。而胡塞尔不关注意向经验的对象(object),因为对象是独立存在的,它不能造成这个意识活动的意向性,“意向关系”明显地独立存在于它们的对象之外。能够造成意识活动的意向性的是意识活动的“内容”(content)。意识活动的内容和对象不同,内容是关于意识活动所指向对象的东西。胡塞尔说:“我们从不说一个意向的内容意味着一个意向的对象。”(76)胡塞尔:《逻辑研究》V,ξ17, J.N.Findlay 英译本。Logical Investigation, Humanities Press, New York, 1970.正是在关于意识内容的探究中,胡塞尔提出了他的意向性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noesis”和“noema”。(77)这两个词都是希腊文。noesis的原义是“智慧”“理解”;noema的原义是“认知”“思”。学界一般认为﹕胡塞尔的noesis 是意向行为或作用,noema是意向对象或客体。但这种解释不太精确。
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把意识活动区分为性质(quality)和材料(matter)两个部分,把意识的内容分为“实在的”(real)和“意向的”(intentional)或“观念的”(ideal)两种。意识活动的性质是区分一个意识活动是判断、愿望、希望、爱、恨等不同种类意识活动的东西。比如,某人A看到桌上的猫,某人B看到白金汉宫里的英国首相,他们尽管看到的对象不同,但在意识活动上有同样性质。而某人C判断民主党的候选人将被选为总统,某人D希望民主党的侯选人将被选为总统,尽管他们指向的对象相同,但在意识活动内容上具有不同性质。任何意识活动的内容必须包括某种性质。但是,相同性质的意识活动也许会有根本不同的意向所指。不同性质的意识活动在意向性上也有相似之处。意识活动内容的成分就是“材料”。在一个意识活动中,意指与对象所达成的关系,并非它意指哪个对象,而是这对象怎样被意识活动知觉。因此,尽管意识活动具有同样的主体和同样的对象,如果人们在意指共同对象时的“方法”(ways)不同,他们的意向性也不同。譬如说,想到毛泽东夫人江青的意识活动,和想到“四人帮”之一江青的意识活动,尽管所指是同一个对象,但材料不同,内容也不同。
在胡塞尔看来,意识活动的“实在的”内容,不是在时空的意义上适合于物理的对象,而是某些“真实的”实体在当下意义上适合于意识构成的东西。它是一种抽象的具体,类似于书本上描写的事物。譬如鲁迅《阿Q正传》对于阿Q的描写是非常具体生动的,但是《阿Q正传》中的阿Q只是通过文字让我们联想出来的一个人物,毕竟不是我们肉眼所见的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人,没有血肉之躯,不具有时空中的物理的性质。阿Q这样一种人物形象,就是胡塞尔说的意识的“实在的”内容中的东西。
与“实在的”内容相对照,意识活动的“意向的”内容是一个“理念的”或抽象的实体,是“理念的经验种类”(ideal species of experiencing),它是意识活动的“意向的本质”(intentional essence)。这种本质或种类,类似于在广泛的柏拉图主义意义上的可分有的“理念”,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永恒的普遍性或“型式”(types)。这种“理念的经验种类”能够具体化在特殊的、短暂的或时空意义上的个别事物之中。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为某种类似于形式的东西,或者一个概念的实体。例如,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可以成为对于阿Q的一种本质概括。这种“精神胜利法”的理念即类似于胡塞尔所说的意识活动中的“意向的”内容。当然,胡塞尔描述的是一种意识活动,鲁迅写作《阿Q正传》是一种把思想外化的艺术创作活动,两者迥异。
胡塞尔认为,一个意识活动的“实在的”内容,在每一个意识活动的境况中把一个“理念的”或抽象的东西具体化。因此,一个意识活动的“实在的”内容是这个意识活动字面上体现的部分,是一个具体的实例。就像鲁迅通过阿Q这样一个人物,来体现某种“精神胜利法”的理念一样。而一个意识活动的“理念的”内容,是一个概念的实体,一个我们理解语言时所掌握的同样种类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认作一个意识活动的“意向的”内容为意识活动的“含义” (meaning)或“意义”(sense)。通过它的效能,意识活动指向它的对象,并作为一个表达的意义,关联到它的所指。意识活动中的“意向的”内容不是直接地在意识活动中。作为一个理念的实体,它的存在独立于这个意识活动之外,不是这个意识活动的“实在的”(real)成分,但它具体化于意识活动的“实在的”内容中。(78)弗雷格在《论意义和所指》(On Sense and Reference)一书中,从“描述”(presentation)中区分了“意义”(sense)。在弗雷格看来,一个描述或观念,是主观的,局限于某人的意识。但一个意义是对象的存在,它包括“描述的范式”(the mode of presentation)。胡塞尔区分实在的和意向的内容非常近似于弗雷格区分描述和意义。
后来在《观念》中,胡塞尔改变了他把“意向的”内容和“实在的”内容与意向的关系作为实体范畴的作法。他不再把“意向的”内容作为本质或型式,而是作为一个理念实体的特殊的范畴,它与“实在的”内容的相互关系存在于适当的不同的方式中。在《观念1》第三章中,胡塞尔正式提出了后期意向性理论中的核心概念:noesis和noema。这两个概念与胡塞尔关于意识的内容和对象的理论密切相关。noesis是关于一个意识活动的“实在的”内容的成熟概念。noema是关于一个意识活动的“意向的”或“理念的”内容的成熟概念。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作为意识的实在的和意向的内容,它们都不是在意识活动中被意指的外在实体,即不是客观外在的物理世界的事实。noesis与以前的“实在的”内容相比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在《逻辑研究》中,“实在的”内容被允许是从经验的、自然科学的观点来作纯粹描述分析。在《观念》中的noesis,仅仅是在“纯粹现象学的”或“先验的”状态中被研究的,它被置于把意识看作产生于自然世界的经验的心理的观点之外;第二,在《逻辑研究》中,“实在的”内容是一个意识活动的意向本质的简单具体化。但noesis不是简单地具象“意向的”内容,而是扮着复杂的任务的角色,即通过它在一个意识活动中的出现,作为对一个经验的“意义的给予”(giving of sense),提供这个意识活动的意向。这个“意义的给予”是这个意识活动的“意向的”内容的主要构成。
noema是除了在一种特殊反思活动中外我们不能意识到的实体。一个意识活动的对象是当我们“perform”(经历)或“live through”(体验)那个意识活动自身时呈现出来的东西。在那个过程中,我们经历(undergo)指向那个对象的经验。但一个意识活动的noema不是我们经历或体验那个意识活动时我们所能意识到的东西。我们不能在一个先验的noema背后发现某个最终实在对象的心理学的意义,它就是存在自身。只有采取“现象学的态度”,反省我们正式体验的经验,才能使noema苏醒。只有在现象学的还原中,才能过滤出noesis和noema。
由此可见,胡塞尔现象学中noesis的基本成分,是经验的“意义给予”部分。这个被给予的“意义”是noema的基础成分。通过noesis在一个意识活动的出现,提供这个意识活动的意向,作为对一个思维活动的“意义的给予”。这个“意义的给予”是这个意识活动的意向内容的主要构成,它使noema中的“意义”出现。实质上,在意识活动中的noema中的“意义”(Sinn),是主体的对在意识活动中关注对象的“意思”(sense)或“感知”,是主体对意识活动本身的一种意识。意义出现,表明对象的意思算是(as)被意识活动的主体所接受(conceived)。这样,作为一个主体的对象的“意思”,“意义”按照意识活动中所意指的描述了这个对象,并把主体的这些特质或“判断”(determination)归因于这个对象。胡塞尔描述的这个在意识活动中很迅疾亦很复杂的整个行为,就是一个完整的意识活动过程。(79)以上所述请参阅David Woodruff Smith and Ronald Mc Intyre: Husserl and Intentionality,pp.110-130.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在一个意识活动中,这些意义给予和表达的活动的基本结构,就是意向性。也就是说,一个意义的表达不仅仅是表达了一个意义,而且总是指向一个对象。因而意义本身也总是指向某一个对象。因此,意义也是对象的现实的表现方式。意义决定特殊的意向关系,它是意向性理论的关于内容的关键概念。意义虽然在字面上不是意识活动的一部分,但它是这个意识活动的理念结构。可是,意义作为理念的内容,它本身在含义上必须是内在的。从noesis和noema的全部内涵可以看出,胡塞尔在他的理论中竭力排斥意向性的对象接近(object-approach)。尽管现象是意向性的,任何现象的意义都是由其所处的意向性结构来决定的,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一个意义对于对象关系的意向,那么,意向性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语义的”关系。很明显,即使对象不具有物理性的存在,意义还是存在的。
所以,在胡塞尔看来,毋宁说意义是具体化于意识中,而不是说在对象中。胡塞尔说:
作为自然中的物,树本身与如是被知觉的树是不同的。后者是知觉的意义,不可分割地从属于知觉。树本身可以燃烧,可以被分解为化学成份等等,但意义——这一知觉的意义,它是某种必然属于其本质的东西——不能燃烧,它不具有化学成份,没有力,没有实在的属性。(80)转引自泰奥多德布尔:《胡塞尔思想的发展》,第423页。
我们在这里的关注点,必须从自然经验的对象转移到传达这些经验的意义上来。因此,当胡塞尔谈到意义时,总是指的对象性(即对象的表现方式)和符号所意指的事件。当他具体地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去接近事物本身时,指的是直接去接近那事物本身的现实给定性,即能为人们直觉的意义形式,以及构造它的意识行为,即赋予符号以意义的那种意识行为。胡塞尔在这里提出的对象构造的思想,是先验现象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无论从理论还是从逻辑上来说,意向性学说是牵动胡塞尔全部现象学的核心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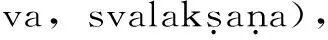
五、“现量”与“本质直观”

唯识学的现量思想主要源于陈那。他的《集量论》首先将量的种类分为六种,即现量、比量、声量、喻量、义准量、随生量。现量是当场感性所知。比量是推理所得。声量是语言的量,指各派的圣教教义,例如有“圣教量”“圣言量”等。喻量就是类推。义准量为举例一个便准知另一个。随生量是指一个事实跟随一个事实的推断,如进房无人便知主人不在家。后三个都是属于直接推理的。因此,陈那认为,六类中只有现量、比量才具有独立的意义。其次,陈那认为,离开概念为现量,运用概念为比量。但是,“概念都不是从正面表示意义,而是通过否定一方承认另一方的方法,所谓‘遮诠’构成的。例如,青色的‘青’这一概念是怎样构成的呢?就是表示‘青’为‘非青’。由否定一方(遮)来表示另一方(诠)。这种遮诠说,也是陈那量论的一个特点。”(83)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191页。周贵华居士认为:“诸识见分(摄自证分、证自证分)取境,按妄实、正误分,有三差别,即现量、比量、非量。现量是直接、亲切之认知;比量是由推理比知者;而非量则是非现非比之虚妄错误之认知。若能量所量二俱现前,而能量于所量亲去无谬,是为现量。若所缘境不现前,或现前而不明了,由能缘心,借助余缘,以推度比知余理余事,是为比量。若由能缘心于所缘境,不能现前证知,妄生执见,或比度差谬,是为非量。”(周贵华:《唯识通论——瑜伽行学义诠》(下),第418页)可见,唯识学所谓的现量,基本意思与佛教传统说法无异,大意为亲历现场、在场、当下认知的意思。
《成唯识论》提到现量有几处,很多是与四分说在一起:
此四分中前二是外,后二是内。初唯所缘,后三通二,谓第二分但缘第一,或量非量,或现或比,第三能缘第二第四,证自证分唯缘第三,非第二者,以无用故,第三第四皆现量摄。故心、心所四分合成,具所、能缘无无穷过,非即非离唯识理成。(135页)
此段文字上节曾引用过。大意是,四分之中,相分、见分属于外在之缘,自证分和证自证分属于内缘内。另外,相分只属于所缘之境,而见分、自证分和证自证分不仅通所缘,还通能缘。就是说,见分只能缘相分,有时候是正量,有时候是错量,而现量和比量都有。自证分不但能缘见分,而且能缘证自证分。而证自证分只能缘自证分,不能缘见分。因为见分缘自证分,没有缘证自证分之用。自证分和证自证分都属于现量,所以可以互量,又可以互证。由于这些道理,无论心法、心所法,都由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合成,具有所缘和能缘。既然自证分可以反证证自证分,就不用四分之后第五、第六……证明,故没有无穷演绎的过错。四分不是一个,也不可以分离,非相即亦非相离,唯识道理由此成立。
这里的意思是,众生之心由内、外二性合成,都有所取、能取的缠缚。见分有种种差别,或者是正量即正确的认识,或者是非量即错误的认识。见分是现量和比量都有,自证分、证自证分都是现量。从认识主体来说,唯识学认为前六识核心是“心”。但是,唯识学的认知活动其实就是万事万物的生成活动,即识变现为万事万物的活动,不是纯粹的意识和感性知性与认知对象的活动。因此,认知即是生成。诸识种子生成之相,也就是所认知之果。而重点在于,这个过程与心法、心所法不能分离。在论述心法、心所法所依存的原理中,《成唯识论》提出三种所依:
诸心、心所皆有所依,然彼所依总有三种:一、因缘依。谓自种子,诸有为法皆託此依,离自因缘必不生故。二、增上缘依。谓内六处,诸心、心所皆託此依,离俱有根必不转故。三、等无间缘依。谓前灭意,诸心、心所皆託此依,离开导根必不起故。(84)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259页。
所依,即事物生起所依靠的条件。这里指出因缘依、增上缘依、等无间缘依三种,即是事物生成的三种条件。因缘依即种子依。“诸有为法皆託此依,离自因缘必不生故”,意即没有自己的因缘,事物本身肯定不能发生,表明种子自身即含因缘,一切生成事物必须以此为依赖。增上缘依,即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各种心法、心所法都依靠此依,因为没有六根,心法、心所法无从生起。等无间缘依,指前面的意念灭除,后面的心理和认识活动才能产生。因为没有引导的意念,一切不会发生。(85)除此三缘外还有“所缘缘”,共四缘。关于四缘,周叔迦先生曾通俗易懂进行描述:“这因缘是说‘两法相生成缘’。如由种子生成树,这树又生种子”;“这等无间缘是‘两法相让成缘’。如两人相随行走,必定要前人向前走一步,那后边才能向前补上他的位置”;“这所缘缘是‘两法相待成缘’。譬如人有夫的名称,是因为他有妻”;“这增上缘便是‘两法相助成缘’。譬如由种生芽是因缘,但是单独的种子不能生芽,必须埋在土里,用水灌溉”。他认为,“一切色法的生起只须两缘,便是因缘和增上缘。因为色法的生起是杂乱的,所以不须等无间缘和所缘缘。”而“一切心法的生起是要具足四缘,便是前眼识灭,后眼识才能生,前眼识是后眼识的等无间缘……这眼识了别色,耳识了别声,都是所缘缘。因为识有四分,却是因为先有相分,才有见分,但是相分又是因为先有色法。所以就见分说:相分是见分的亲所缘缘,色法是见分的疏所缘缘。就自证分说:见分是自证分的亲所缘缘,相分是自证分的疏所缘缘。就证自证分说:自证分是证自证分的亲所缘缘,见分是证自证分的疏所缘缘。”(周叔迦:《唯识研究》第31-33页。)周贵华居士把唯识学的缘起论概括为七个特点:第一,缘起与空之相应性;第二,缘起之有为性与显现性;第三,缘起之因果平等性;第四,缘起之唯心性;第五,缘起之心因性(心种子性);第六,缘起之俱时性;第七,缘起之整体性。(见周贵华:《唯识通论——瑜伽行学义诠》第三编第四章第二节)但是,增上缘依仍然局限在六根即认知感官范围内。等无间缘依是意识活动的一种惯性,而且由于前面的意念对于后面意念的引导作用,等无间缘依与意识意向性有点相关。就认知活动的范围而言,种子缘依仍然是最广泛的。关于种子依的具体解释,《成唯识论》说:
……种自类因果不俱,种、现相生决定俱有,故《瑜伽》说无常法与他性为因,亦与后念自性为因,是因缘义。自性言显种子自类前为后因,他性言显种与现行互为因义。《摄大乘论》亦作是说,藏识染法互为因缘,犹如束芦俱时而有,又说种子与果必俱,故种子依定非前后。(86)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260页。《摄大乘论》说:“阿赖耶识与杂染法互为因缘,如柱与焰,展转生烧。”(成唯识论,第116页)
种子自类相续,前念种灭后念种生,像这样的因果关系不能同时俱有,但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肯定同时俱有。所以《瑜伽师地论》说非永恒的事情以他性为因,亦以后起的念的自性为因,这就是因缘。自性是说种子本身前后为因,即种子生种子。“他性”是说种子与现行互相为因。《摄大乘论》说,阿赖耶识与污染事物互为因缘,正如捆在一起的芦苇相互支撑不倒一样。就像烟火和蜡烛不可分离相互为因一样,种子与结果同时具有。因此,种子依一定是不分前后。可见,所有的感知活动,作为万事万物之因的种子,与现行之果同时发生,互为因缘,这样的感知内容和认知空间是难以计量的。
很显然,种子与心、心所法都有关联。在心、心所法生起的时候,相关的“识”是八个,不仅仅是前五识和第六识意识,还有末那识和阿赖耶识,而阿赖耶识则是本体。关于八识之间及所缘关系,《成唯识论》曰:
本识中种容作三缘,生现分别,除等无间,谓各亲种是彼因缘,为所缘缘于能缘者,若种于彼,有能助力或不障碍,是增上缘。生净现行应知亦尔。现起分别展转相望容作三缘,无因缘故。谓有情类自他展转容作二缘,除等无间。自八识聚展转相望,定有增上缘,必无等无间,所缘缘义或无或有,八于七有,七于八无,余七非八所仗质故,第七于六五无一有,余六于彼一切皆无,第六于五无,余五于彼有,五识唯託第八相故。自类前后第六容三,余除所缘,取现境故,许五后见缘前相者,五七前后亦有三缘,前七于八所缘容有,能熏成彼相、见种故。同聚异体展转相望,唯有增上。诸相应法所仗质同,不相缘故。或依见分说不相缘,依相分说有相缘义。谓诸相分互为质起,如识中种为触等相质。不尔,无色彼应无境故,设许变色亦定缘种,勿见分境不同质故。同体相分为见二缘,见分于彼但有增上,见与自证相望亦尔。余二展转俱作二缘,此中不依种相分说,但说现起互为缘故。净八识聚自他展转皆有所缘,能遍缘故。唯除见分非相所缘,相分理无能缘用故。既现分别缘种现生,种亦理应缘现种起,现种于种能作几缘?种必不由中二缘起,待心、心所立彼二故。现于亲种具作二缘,与非亲种但为增上,种望亲种亦具二缘,于非亲种亦但增上。依斯内识互为缘起,分别因果理教皆成。(87)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535页。
大意为,阿赖耶识种子可作因缘、所缘缘、增上缘三缘,而变生现行为分别的各种事物形式。这里所说的分别,指心、心所法而言。因缘就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和条件,所缘缘就是相互关系和条件,增上缘是相互有利和帮助的条件和关系,等无间缘是补位递进的条件和关系。种子唯独不能作等无间缘,因为是等无间缘就心、心所法而说,有间隙,因此种子不能有等无间缘。具体说,种子三缘,其因缘就是八识各有亲生种子,这就是八识的因缘。如善恶种生善恶的现行;所缘缘就是能缘心法和心所法的种子;增上缘就是,如果有的种子对于现行法的生起能够给予助力,或不起障碍作用,此即增上缘。杂染和清净种子生现行都是如此。现起的分别,或自他,或自类,八识前后各种现行分别展转关联关注(相望),容许有所缘缘、增上缘、等无间缘,但没有因缘,因为不是亲历的缘故。有其他三缘,例如现起的眼识,关注、联想耳、鼻等现起识,就是增上缘。如果第六识意识能缘前五识等,或第七识末那识能缘阿赖耶识,这些就是所缘缘。对于一个有情众生来说,来自自己或他人分别,展转关联关注,就有所缘缘、增上缘,没有等无间缘和因缘,等无间缘唯有自识有。
假如一人自己八识聚合现起,辗转关联关注,那就一定有增上缘,因为此缘通于一切。一定没有等无间缘。关联后八识的现起,各自对于它的自类识具有开导力,就是等无间缘。因为不是自识前后关联关注。所缘缘或有或无。无是因为阿赖耶识对于其余七识有所缘缘的意思,即阿赖耶识相分为前五识作所缘缘。阿赖耶识四分为第六识意识作所缘缘。阿赖耶识见分为末那识作所缘缘。总而言之,阿赖耶识的四分本质,即为前七识的见分变为相分缘,所以阿赖耶识对于末那识有所缘缘之义。然而,前七识关联关注于阿赖耶识没有所缘缘的意思,因为阿赖耶识不缘前七识,不依前七识而生,只缘自己的三境。
末那识望于第六识意识和前五识,没有所缘缘的意思。由于第六识意识通于一切法,前五识望于第六识意识有所缘缘的意思。其余六识望于末那识,一切都没有末那识所缘缘之义,因为,末那识只缘阿赖耶识见分,不缘于前六识。第六识意识关联关注于前五识,没有这种所缘缘之义。因为前五识只托阿赖耶识所变现为境相,不待第六识意识所变色等为自境的缘故。然而,前五识关联关注于第六识意识,则有此所缘缘之义,因为第六识意识能缘前五识。
相关于自类前后展转为缘的问题,自身八识,一一自类前后相关联关注,第六识意识可以有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三缘,其余七识只有二缘,即等无间缘、和增上缘,因为它们只缘现境。陈那《观所缘缘论》中,说允许五识后念见分缘前念相分,末那识亦如此,因而前五识和末那识,前与后自类相关联关注亦有三缘,即因缘、等无间缘、增上缘。若以自身八识相关联关注而言,前七识关联关注于阿赖耶识,可以有所缘缘,因为前七识都能熏成阿赖耶识的相分、见分种子。
相关于同聚异体问题,同聚,指约心与心所和合似一;异体,指约心心所法相用各别。同聚异体之识,如诸识俱时心、心所各自分别相关联关注,虽是同聚,而是别体。对此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只有增上缘,没有因缘、等无间缘和所缘缘。另一种认为,或依见分同聚,心、心所说不相缘,因为没有能缘俱时见分的。若依相分来说,有相缘之义,因为一切相分都是互为本质而得生起,故同聚心所的相分必然依仗心的相分为本质而起,就像如本识中诸法种子同时为触等五种遍行心所法的相分本质。若非如此,无色界中既然无色,那么五种心所应没有它们的所缘之境。假设允许无色界第八识也能变现下界的色等,然而触等五种心所法如本识一样,仍是决定缘种,不能说第八识心所六个见分的境不同于一个本质。从诸相分容许互为本质来说,所以有相缘之义。
相关于同体相分问题,同体是说诸心心所,虽各有四分,但都是一识所变,故名为同体。于四分中相分关联关注于见分,能为其所缘、增上缘二缘。可是见分关联关注于相分,就没有所缘缘,只有增上缘。因为相分在道理上是没有能缘用的。见分与自证分展转相关联关注,如见分关联关注于相分,亦是这样。唯有增上缘,而没有所缘缘。因为见分通非量,不能内缘,所以没有所缘。其余的自证分与证自证分辗转相关联关注,俱作为所缘缘和增上缘。因为彼此互相为缘,假定以此内向的二分相望于外向的见分和相分,就唯有增上缘而没有所缘缘之义了。然而,我们还要知道,此中如前所说的相分与见分为二缘,不是依于种子为相分的说法,而是但就现行互相为缘之说。
净八识聚自他展转相望,都有所缘,因为一一都能遍缘一切法,不过在同体的四分中,一定要除去见分望于相分的非所缘缘,因为一切相分从道理上说,肯定没有能缘的作用。既然现起分别缘其种子和现行而生,则其种子从道理上来讲应当亦应当缘其现行和种子而生起,现行和种子对于种子来说能作几种呢?种子肯定不能由中间二缘(等无间缘、所缘缘)生起,因为这二缘待心法、心所法为果才能成立。今依因位现行望自亲所熏种能为二缘:因缘、增上缘,与非亲种不辨体故,除自种外只有增上缘。于一切位,种子望自亲种亦具二缘:因缘、增上缘,于异性非亲种亦只有增上缘。依这内识若种若现互为缘起,一切分别若因若果,能生所生,从理从教皆能成立。
以上极为繁琐的叙述,实际上展示了一个数学上的组合问题:四缘与八识各有两种可能,八识之间各有两种可能,再加上每个识有四分,又与前面四缘构成组合关系,合起来约有数百种组合。从上述细碎的阐述中可知,唯识学的八识在具体的认知过程中,不仅彼此相互关联关注缠绕,还与认知对象即外境的各种条件互为关联关注缠绕,因而绝不是单纯的意识和感性、知性的知觉活动。唯识学曾用“百法”概括宇宙万物,包括精神、物质一切现象。周叔迦先生说:“这百法是包罗万象的总纲,八识又是百法的主脑。”(88)周叔迦:《唯识研究》,第14页。百法:心法八种、心所法五十一种、色法十一种、心不相应行法二十四种、无为法六种。可见仅仅在具体的认知过程中,对于八识运动的描述也是难以尽言的。(89)周贵华教授比较简略地概括了八识在认知过程中的功能、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他认为:“八识皆以了别(vijapti)为通相。”详见周贵华:《唯识通论——瑜伽行学义诠》(上),第205-208页)周叔迦先生说:“仔细的研究,凡是看见一种颜色或听见一种音声,要经过五种意识同前五识相互作用,方能完全了别的,这五种作用叫做‘五心’。一、率尔心:这是前五识在刹那间忽然的了别。二、寻求心:这是意识因前五识生起而起寻求。三、决定心:这是意识因寻求而决定了别。四、染净心:这是意识由了别后生起好恶贪嗔的念。五、等流心:这是因意识的好恶而前五识与意识于相当时间中同等的流转,成就善或不善。”(周叔迦:《唯识研究》第11页)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八识见分都有现量,尤其是前五识。可见现量中,各种识、心、心所及其所缘的可能性是个巨大的量。甚至在禅修灭尽定过程中,六转识与心法、心所法仍然不离身。(90)《成唯识论》曰:“契经说,意法为缘生于意识,三和合触,与触俱起有受、想、思。若此定中有意识者,三和合必应有触,触既定与受、想、思俱,如何有识而无心所?若谓余时三和有力成触生触,能起受等。……无心所心亦应无。如是推徵,眼等转识于灭定位非不离身。”(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245-246页)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即唯识学认为,现量境不能证明对象实有:
色等外境分明现证,现量所得宁拨为无?现量证时不执为外,后意分别妄生外想。故现量境是自相分识所变,故亦说为有。意识所执外实色等妄计有故,说彼为无。又色等境非色似色、非外似外,如梦所缘,不可执为是实、外色。若觉时色皆如梦境不离识者,如从梦觉知彼唯心……(91)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492页。
问:色、声、香、味、触五种外境,分明由五识现证,是现量所得,怎么说为无?答曰:现量证时不能认为是外法,当以后第六识进行虚妄分别的时候,才能称为外法。所以现量境是识变现为自己的相分,因此可以说为有。而相反的是,意识执着外界色法以为真实,这是虚妄计度产生的,故说为无。很显然,其他虚妄计度所执外法,看外在事物,其实犹如梦中之物,似是而非,都不是实在之物。这种梦中之物等到觉醒之时方才觉悟。
由此可以看出,唯识学一方面以真觉作为推论证据,实际上是消解了认知是否正确的问题;另一方面,唯识学认为,如果认识不到法空、我空和万法唯识的原理,即使我们所见事物历历在目,亦皆为虚妄认知,即错误认知。就是说,现量的意思,一是所见认知正确与否;二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所有正确认识都是非量。


胡塞尔现象学认为,仅仅依赖于先验还原,现象学还不能达到它的目的。因为先验还原只能还原到纯粹内在的意识上去,只能把超越的东西悬置起来。现象学倘若止步于此,终止与个别的被给予性,它就不能解决认识论中的根本问题,即不能实现对于思维内在与外在事物之间关系本质的揭示,不能解决任何关于人类认识的问题。所以,现象学必须由对于思维内在领域的描述,到达外在的超越之物。而对内在与超越之物的根本区分,则是通过“本质直观”(intuition of essence)来实现的。
“本质直观”就是“本质还原”(eidetic reduction)。胡塞尔通过先验还原发现了纯粹思维的明证性,但这种思维只是个别的被给予性。这里的问题还是在于,这种思维内在的、个别的东西,与外在世界的、一般的事物之间是否具有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关系?在对思维的考察中,胡塞尔发现,事物的一般性也并不缺少这种绝对的被给予性。例如,对桌上一张吸墨纸的红进行直观,就会由纸上的红而发现一种红的颜色,即红的一般之物。这时候,吸墨纸不再是我们的注意中心,这种红已经不再依附于吸墨纸而伸展为一种普遍的颜色。在这种情况下,“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被意指的不再是这个红或那个红,而是一般的红”。(94)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50页。胡塞尔把这种直观叫作“本质直观”,亦就是“本质还原”。
在本质直观中,一般性即一种普遍的本质,也是绝对被给予的。本质还原后留存下来的就是本质或本质一般性。在本质直观中,必须不去触及那些作为出发点的个体对象的具体存在,而仅仅朝向一般本质的存在。因此,本质直观对对象本身的存在不感兴趣,而只对把握到的对象的本质的存在感兴趣。比如说,在本质直观中,我们对那张吸墨纸本身不感兴趣,而只是对那张吸墨纸的红颜色感兴趣。这也是对个体对象存在设定的扬弃。但是,胡塞尔仍然认为,本质直观获得的一般性,在实在的意义上仍然是超越的。就是说,这种一般性仍然不能达到思维内在的绝对的明证性。
胡塞尔认为,认识论上的一般错误是对内在的超越。就是说,一般的认识论超越了思维的内在绝对的明证性,而企图去说明外在事物的本质。因为,思维在这里与外在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不具有思维内在认识的绝对明证性。本质直观中的一般也是对内在的超越。为了避免陷入这种认识上常见的陷阱,胡塞尔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内在。第一种是实在的(reell,与intentional相对)内在,即意识的实在内容,指个别的意识活动和感觉材料。在这个内在的意义上,一般是一种超越;第二种内在是指绝对的、明晰的被给予性,也是绝对意义上的自身被给予性。它不仅包括第一种内在,而且还包括实在的超越之物,即一般内在。这种一般内在是指被意指对象本身的一种绝对直接的直观和把握,它构成明证性的确切概念,即被理解为直接的明证性。本质直观所达到的就是这种明证性。就是说,本质直观所达到的明证性虽然不是属于思维实在的内在,但是,这种明证性却达到了一般内在。胡塞尔说:
如果直观、对自身被给予之物的把握是在最严格意义上的真实的直观和真实的自身被给予性,而不是另一种实际上是指一个非给予之物的被给予性,那么直观和自身被给予之物的把握就是最后的根据,这是绝对的自明性。(95)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45页。
这样,本质直观就使现象学的领域突破了实在内在的樊篱,扩展到绝对被给予性的领域,即从思维的个别的内在活动,达到思维与存在的广阔的认识活动领域,现象学因此而实现了它的真正目标。可见,本质直观作为一种手段,是现象学必不可少的方法。它不仅解救了现象学方法的困境,而且把现象学的研究领域从思维内在伸展到外在事物,从个别扩展到一般。
本质直观就是直观事物。在本质直观中,事物简单地存在于此,并且存在于意识的真正明证的直观中。胡塞尔认为,在本质直观中,纯粹意识中给定的现象就是对象的本质,现象的本质或本相就是呈现于纯粹意识中的东西:
如果我们在完全的明晰性、成为完全的被给予性中直观到“颜色”是什么,那么被给予之物便是一个“本质”,并且,如果我们在对一个一个的感知进行观察时,在被给予性中纯粹地直观到“感知”自身是什么,那么我们也就直观地把握住了感知的本质。(96)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第79页。
通过本质直观,我们可以实现由事物的外在存在到本质的精神上的转变。比如,由一个个别的红纸、红布,转变到红这种本质,由此时此地的个别事物转变到一种本质。在本质直观中达到对个体对象存在的扬弃,即本质还原。而且,胡塞尔还认为:自身被给予性“伸展得有多远,我们现象学的领域,即绝对明晰性的领域,真正意义上的内在领域也就‘伸展’得有多远”。(97)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第14页。在本质还原中,对象在意识中的位置被忽略,而对象不变的、普遍的特点则被揭示出来。
如果说,在先验还原中,朴素意识中被给予的东西变成了纯粹意识中的先验现象,它把握的是对象;那么,在本质还原中,现象变成了纯粹意识中的本质,它把握的是对象的本质。本质还原的依据是直观的明证性。明证性也就是明晰、无疑的直观本身。胡塞尔说过:“如果认识批判从一开始就不能接受任何知识,那么它开始时可以给自己以认识,并且自然,它不论证和逻辑推导这些认识……相反,它直接指出这些认识”。(98)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11页。直接指出认识就是纯粹直观。“这种明证的直观本身就是最确切意义上的认识”。(99)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63页。在胡塞尔看来,明证性之所以能成为依据,就是因为它是不需要论证和推理。如果用已有的知识作为前提来推论和论证,得出结论的东西必然不是最根本的知识。最根本的东西是无法论证和演绎的。因此,现象学的本质直观“证明了一个基本的命题:认识论从来不能并且永远不能建立在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基础上”。(100)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35页。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这种直观的明证性并不是感觉上的清楚明白。胡塞尔认为,感觉论的明证性是心理主义的范畴,与他的现象学的明证性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胡塞尔现象学极力避免思维和意识的自然化,即思维的日常化。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是纯粹意识中显现的本质,这种明证性是绝对的被给予性。而感觉论的明证性则不具备这些内涵。同时,感觉论的明证性注重的是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外在印象,而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却忽略事物本身的具体存在,仅仅直观一种普遍的本质。
在本质还原中,作为一种纯粹的直观和把握的对象,事物的本质是绝对的被给予性的。这样,本质还原不仅使现象学的本质研究成为可能,而且把意识对象引进了现象学的研究领域。本质直观中的这个被给予性,胡塞尔认为,也是对象构造着自身的存在方式。因此,被给予性问题,“就是在认识中任何一种对象的构造问题”。(101)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8页。胡塞尔说,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这种被给予性,就会发现“在对一种声音的体验中,即使在现象学还原之后,显现和显现物竟是如此地相互对置着”。(102)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15页。用这样的观点来看,我们就会有“两个绝对的被给予性:显现的被给予性和对象的被给予性”。(103)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15页。实际上,这种认识现象和认识客体之间奇特的相互关系,可以说到处都能表现出来。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很显然,唯识学的“现量”概念,是指认知活动中认知主体亲身在场、当下感知。而且,作为认识主体的“心”,基本上与六识、三性、百法交接,绝不是纯粹意识。而从佛教的角度说,现量在所得智下所观照的,也不是物理现实的对象世界。即使就世俗的意思来说,所谓四分也不仅仅是意识的活动,还有心理的活动。第六识意识的活动中,与心理活动交错进行,也绝不是纯粹意识。在“现量”这个亲力亲为的感知过程中,不仅认知主体所有的认知功能(感性、知性、理性、直觉、想像等)被刺激活跃起来,而且所有的心理(欲望、禁忌、偏爱等)和精神(悲观、乐观、怀疑主义等)功能也被刺激起来,并同时与认知活动混合一体,获得主体当下的认知结果。这个认知结果对于那个具体的认知主体来说,可能是最真实的感知。但是,这个认知基本上是个性化的、独特的认知结果,不具有普遍性。现象学“本质直观”概念,是指认知主体经过“悬置”之后的纯粹意识,对于对象事物所进行的观照活动。在这个观照过程中,一定要排除对象的物理性存在,只关注事物普遍性的“本质”。因此,“本质直观”的结果被认为一定是具有普遍性的,而绝非个性化的、独特的认知结果。由此也可见,在唯识学的“现量”概念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概念之间,几乎很难找到相同之点。
六、“真如”与“事物本身”
唯识学作为佛教一个宗派的教义,其指向无疑是宗教的目的,认识的最高目标是证得真如,方法是修行。胡塞尔现象学的根本目标是解决认识中“意义”的确定性问题,回到“事物本身”,基本是哲学认识论。二者的分野一目了然。
唯识学也有普遍真理的追求。但是从根本上说,佛教的认识主体没有实在性(无我)。佛教最初提出的“四圣谛”(意即四种真理),又把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被归纳为十二缘起和刹那灭,其根本思想是“空”,并试图通过涅槃解决烦恼问题。大乘佛学否认任何世俗的永恒原理,与哲学相关的认识论只限于经验,所追求的是获得根本智,认识佛家真理。所谓般若根本智就是照事物原样去认识事物,事物原来无知无相,所以也应以无知无相来观察它。后来的佛教学者,将般若自照的性质说成“无分别”,但又不同于木石之无知和执心之无记等等。对般若(智慧)还区分“根本智”和“后得智”,前者观察事物之“共相”,后者照事物之“自相”。“共相”是空性,“自相”则以空性为基础。最后还在“根本”“后得”之中分了若干层次。到了获得般若的成熟阶段,不用着意可以任运自在。这个阶段相当于十地修习中的第八地,小乘佛教修道达到的阿罗汉果位。而唯识学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有清净心、如来藏、圆成实性等。
佛家认为,获得真理的主要障碍是人生之惑,总共包括十二有支(因缘),即从无明乃至老死。(104)十二支:又称十二缘起。缘起,梵文pratityasamutpāda,意谓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待条件(缘)而起。这些惑的断除也是通过见道和修道。见道有两种,一是真见道,即证得我、法二空所显真理,断除烦恼、所知二障的分别随眠。二是相见道,也分两种,即观非安立谛和缘安立谛。由此进入真如法界如来住地。
瑜伽行派在修道实践上不同于其他宗派所常讲的解脱、涅槃,而是讲“转依”。“依”即依赖、依仗之意。“所知依”指有情众生根据一般知识作为人生行为的依仗和依赖,是染,是迷,“转依”就是要“转识成智”,转变为对于佛教真谛的认知领悟,是净,是悟。(105)周贵华:“‘瑜伽’/‘相应’在瑜伽行学中更多是在胜义层面上界定的,而用于称谓对真理的亲证。亲证是对真理的直接把握,是与真理的冥契。具体而言,首先是在修行过程中的加行道终端跨入见道的刹那,真实智慧生起而证入真如,即此方可称为相应。在因位的圣者难以一直或者虽然能够一直但不能圆满地处于相应状态,只有在果位之佛才能一直且圆满地处于相应状态。这是‘相应’在瑜伽学中的最根本意义……”“前文对瑜伽行之名进行了一番辨析,目的在于强调瑜伽行学之根本核心是修相应,以生起并圆满实证真理之智慧。”(周贵华:《唯识通论——瑜伽行学义诠》,第2、3页)唯识学因此提出“转识成智”,由三性达到三无性,成佛解脱。《唯识三十颂》第二十五颂云:“此诸法胜义,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识实性。”这里所说的“诸法”指“三无性”,由此进入真如。三无性也是智。唯识宗将修道途径落实到圆成实性的修炼。步入唯识修炼的阶段和方法是“五位”,即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修习位、究竟位。前四位是过程,第五位为结果。
《成唯识论》对于各位的修行状况和果位进行描述。关于资粮位,《唯识三十颂》第二十六颂曰:“乃至未起识,求住唯识性。于二取随眠,犹未能伏灭。”意即资粮位是通过福德二业和智慧所达到修行的阶段。各位菩萨对于识的外相和体性,在资粮位能够深刻信仰和理解。但在资粮位不能认识能取、所取二空,是有漏位,处于有所知障、烦恼障阶段。
关于加行位,《唯识三十颂》第二十七颂曰:“现前立少物,谓是唯识性。以有所得故,非实住唯识。”在此位要通过四加行,即暖、顶(意思是极顶,顶位所修的寻思叫“上寻思”)、忍、世第一,修“四寻思”,获得四种如实智,达到二无我认识,获得无漏智。“四寻思”第一为名寻思观。即一般人认为事物的名称表示与此物相应的实物,因此而有喜怒哀乐之情。唯识学认为这都是假名,是信识上的假立;第二为事寻思观。即万事万物都是识的相分,虚幻不实;第三为自性寻思观。唯识学认为事物自性皆非实有,是识的变现;第四为差别寻思观。唯识学认为事物的大小、长短等差别之相都是假有,离识不可得。认识到人们观察寻思事物的名、义、自性、差别都是假有,由此为因,有相应“四如实智”。(106)参见周叔迦:《唯识研究》,第55页。在加行位能够渐次制服铲除所取和能取,引生对最高实在的认识。
关于通达位,《唯识三十颂》第二十八颂曰:“若时于所缘,智都无所得。尔时住唯识,离二取相故。”(107)《成唯识论》说:“若时菩萨于所缘境无分别智都无所得,不取种种戏论相故。尔时乃名实住唯识真胜义性,即证真如,智与真如平等平等俱离能取、所取相故,能、所取相俱是分别,有所得心戏论现故。……故应许此有见无相。加行无间此智生时体会真如,名通达位。”(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623-624页)在通达位,以无漏现行二智(根本智、后得智)证悟实相,通过八识成就“四智”:1.大圆镜智相应心品,像大圆镜那样显现诸处、境、识影像。2.平等性智相应心品,平等观察一切事物和自我。3.妙观察智相应心品,观察各种事物的自相和共相,断除一切疑惑。4.成所作智相应心品,在身口意三业实现自己的誓愿,成就一切应当做的事情。四智心品永离恼害,故名安乐。清净识是无分别的,或者与根本无分别智相应,或者与后得无分别智相应。前者是对空性真如之证知,后者是对一切相之如实显现。而佛位圆满清净识,即无垢识,完全无分别任运显现,与四智相应。此中四智,谓阿赖耶识所转之大圆镜智,末那识所转平等性智,意识所转之妙观察智,前五识所转之成所作智。四智相应即是无上正等正觉。简言之,通达位可以见道,体会真如,认到真理,把握到瑜伽行的中观思想。(108)参见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708页。
再进步到修习位,《唯识三十颂》第二十九颂曰:“无得不思议,是出世间智。舍二粗重故,便证得转依。”在修习位,按照所认识的道理,反复修行,伏除烦恼,断除余智障。(109)《成唯识论》云:“……由数修习无分别智断本识中二障粗重,故能转灭依如生死及能转证依如涅槃,此即真如离杂染性。如虽性净而相杂染,故离染时假说新净,即此新净说为转依,修习位中断障证得。虽于此位亦得菩提,而非此中颂意所显,颂意但显转唯识性,二乘满位名解脱身,在大牟尼名法身故。”(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635-636页)牟尼:梵文Muni,意思是寂、寂寞、寂静,静止身、口、意三业之学道者的尊号,又译为仙人、贤人或佛。再进一步修根本智,便可达究竟位。
至究竟位,《唯识三十颂》最后一颂曰:“此即无漏界,不思议、善、常。安乐、解脱身,大牟尼名法。”全出二障,功德智慧无不周备,不同小圣,所以称为圆。能至无尽未来,教化有情众生,使他们也悟入唯识的相和性。究竟位获得无上果位。
一个人如果这样认识唯识问题,就不会颠倒错误,善备福、智二资粮,这样就能很快进入法空,证得无上觉,从生死轮回中拯救拔除出来。违背教理恶趣空者不能成就这样福、智,肯定应当相信一切唯识之理,获得十波罗蜜,证得十真如:
十真如者:一、遍行真如,谓此真如二空所显,无有一法而不在故。二、最胜真如,谓此真如具无边德,于一切法最为胜故。三、胜流真如,谓此真如所流教法于余教法极为胜故。四、无摄受真如,谓此真如无所系属,非我执等所依取故。五、类无别真如,谓此真如类无差别,非如眼等类有异故。六、无染净真如,谓此真如本性无染,亦不可说后方净故。七、法无别真如,谓此真如虽多教法,种种安立而无异故。八、不增减真如,谓此真如离增减执,不随净染有增减故,即此亦名相土自在所依真如,谓若证得此真如,已现相现上俱自在故。九、智自在所依真如,谓若证得此真如已,于无碍解得自在故。十、业自在等所依真如,谓若证得此真如已,普于一切神通、作业、总持、定门皆自在故。虽真如性实无差别,而随胜德假立十种。(110)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678-679页。杨维中说:“就起体性而言,‘涅槃’与‘真如’并无分别,都是诸法的真实体相。二者的不同方面则主要有二:其一,从言教的角度,真如是诸法的真实本性,而涅槃则是诸佛自内(心体)转依所悟得的心理境界;其二,转依后诸佛总揽的一切法唯是无漏功德,唯是菩提大用,因而诸佛依此所得‘四智’住于生死救度众生,这也就是唯识宗‘四种涅槃’义中之最高者——‘无住处涅槃’。”《中国唯识宗通史》(下),第737页。
但真如也是“识之实性”。“或相分等皆识为性,由熏习力似多分生,真如亦是识之实性,故除识性无别有法。此中识言亦说心所,心与心所定相应故。”(111)玄奘译,韩廷杰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714页。因此,总而言之,统而言之:
谓诸菩萨于识相性资粮位中能深信解,在加行位能渐伏除所取、能取引发真见,在通达位如实通达,休习位中如所见理数数修习伏断除障,至究竟位出障圆明,能尽未来化有情类复令悟入唯识性相。

这是唯识学所有论证的最后指向。(113)杨维中先生说:“‘瑜伽’的基本字义是‘连结’,可引申为‘将心连结于一境’的修行。这本来是共通于印度宗教界的修行方法之一,然弥勒、无著等论师赋予其独特含义,因而成为佛教的修行方法。关于‘瑜伽’的具体内容,最胜子所造《瑜伽师地论释》有文字说:‘一切乘境、行、果等所有诸法,皆名瑜伽,一切并有方便善巧相应义故。’此中的‘相应’即指‘法随法行’……菩萨‘法随法行’是‘止观’之行,也就是‘瑜伽行’。”(《中国唯识宗通史》(下),第488-489页)“总之,唯识相、性,依他圆成,无非是说明依他如幻,使修唯识行者,断妄染执障,证到圆成真理,而成三身万德的佛果。然佛果功德,殊妙无边,非少修行可能证圆,必须经历‘资粮’、‘加行’、‘通达’、‘修习’、‘究竟’五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妙觉四十一阶,历经三大阿僧祇劫,方能至三身万德之佛地。”(同前,第520页)
胡塞尔现象学主要任务是认识本身的批判,即解决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实质上这也是哲学上的一个老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胡塞尔看来,“生活和科学中自然的思维对认识可能性的问题是漠不关心的”。(114)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7页。后期胡塞尔还认为,科学不仅不是唯一的真理,而且还把我们的实际的世界变成一种单一的理念的世界:“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正是这件理念的衣服使得我们把只是一种方法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存有。”(见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58、62页)在日常的自然生活中,人们显然不会去思考“我们的认识是否可靠”这样一类问题,而自然科学也只能告诉我们某物“如何”,而不能告诉我们某物“是什么”。科学关注的是认识的结果,从未关注认识本身。正因为如此,尽管人类的科学和技术正在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成果灿烂辉煌,但是,这些都不能回答“认识是否可能”这样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知识还不能等同于真理,科学自身还没有获得这种明晰的最终真理性的证明。因此,就哲学而言,人们还是处于这样的困境中,即我们如何能够确信我们的认识是与自在的事物一致的?我们的认识如何能够“切中”这些事物?自在事物同我们的思维活动以及那些给它们以规则的逻辑规律是一种什么关系?同时,科学本身是精神的一种产物,因而我们还不能用以自然为对象的那种科学来考察科学本身。这些问题未解决,科学在实际上就不能得到可靠性的明证。而现象学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科学才能成为知识。因此,现象学的目标也可以说是为一切科学寻求一个确定的基础。由于这个目标,现象学号称自己的方法就是“回到事物本身”这一原则。
就现象而言,布伦塔诺认为,全部世界现象分为两大类: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物理事物是有颜色、有声音、有广延性的,等等。然而,各种观察和感觉,特别是物理学理论向我们表明,外界对象并没有这些性质,代替它们的是另外一些性质,例如光波和空气的振动等。但是,这类性质也不存在于心理的主体之中。在这里只存在着有关的活动,或更确切地说,存在着的是这种活动的承担者。因此,严格说来,没有什么颜色和声音,而只有看颜色者和听声音者。只有心理现象是内知觉的现象,也是自明性知觉的现象。因此,只有心理现象才有真正的存在。从逻辑上说,物理世界不能有“真的”或“非真的”这类谓词,例如石头或树林,不可能是真的或假的,只能是实在的或非实在的。因此,真理既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也不存在于先验的主观世界,而是存在于心理现象中,即具有明证性的直接经验中。普遍正确性乃是内经验界自明性的自然结果。因此,在布伦塔诺看来,哲学研究因此必然归属为心理研究。
心理现象的总特征就是“意向性”(Intentionalitat),即意向对某物的关系。我们看到,人们不会说“我感觉” “我想象” “我判断” “我高兴”等,总是说“我感觉到某物” “我想象某物” “我对某物下判断” “我对某物高兴”等,这表明,每一种意识实质上都是关于对象的意识。胡塞尔在布伦塔诺心理主义基础上,进行了现象学的艰难探索。胡塞尔现象学理论的根本意图,不是把对象当作哲学思维的对象,不是把具有意义的语言符号当成研究对象,也不是孤立地把意义本身当成研究对象,而是把对象的表现方式归结为意义,将意识的给定方式,即赋予符号以意义之活动本身当作研究对象。胡塞尔的这种意义意向性学说,从根本上打破了根据外在因果律来说明事物的观念。它把人们的认知活动重心,从外在存在的物理世界的物的结构,转移到主体的意识的结构中。人们不再只是从外在的客观世界中去寻找认识事物的最终根据,而是从意识活动本身来寻求认识活动中意义的构成。
胡塞尔是把意向性的构成物或构成中的被给予物,当成是最终的存在。认识现象学因此也成为关于现象、显示、意识行为的认识科学。让现象作为显现者,以自己显现的方式被人们意识,这就是“朝向事情本身”的原则和意指。胡塞尔现象学这个认识论的转换,不仅揭示了一直被哲学和科学遮蔽的人们认识活动过程中的一些本质现象,而且也暴露了我们知识构成的一种本质结构,从而开启了20世纪哲学发展的一个崭新起点。我们传统观念所认定的知识的确定性也因此动摇。因为,与我们意识相关的某物的意义,无论如何不是某物全部的、最终的意义。 很显然,这里“事物本身”的指向就是意义的确定性。
可见“真如”与“事物本身”的区别不仅是认识论的,还是宗教与哲学的。
七、小 结
兴盛于5世纪的佛教唯识学,和成书于7世纪的《成唯识论》,与诞生于20世纪初的胡塞尔现象学之间,相差一千三百余年。这个巨大的历史长度基本上可以展示这两种哲学思想存在深深的鸿沟。
唯识学描述的“现象”,即大千世界,都是识的“转变”。万事万物都是由识生成、构造出来的,此即“万法唯识”意指。胡塞尔现象学认为,“现象”就是显现,也就是意识中呈现的对象事物。因此,在本质上说,现象也是意识。可见,唯识学的“识变”说与胡塞尔的“显现”说有类似的地方,即都把现象看作是主观的外化。其次,唯识学宣称“法、我二空”,除了外在世界在本质上是空,“我”在本质上也是空,是“无我论”。胡塞尔现象学在论证“意义”确定性的时候,首先也是“悬置”一切事物,包括“我”。在这一点上,唯识学与现象学也有类似。但是,在“现象”构造和呈现的具体描述中,以及关于对象世界的认知过程中,唯识学与现象学存在巨大差异,具有根本不同质的意指。
首先,就哲学而言,唯识学“万法唯识”思想中包含形上学的命题,因为唯识学否认任何物理性事物的实在性,包括“我”的实在性。而现象学主要讨论哲学认识论问题,只是“悬置”万事万物,对外在世界存而不论,没有否认物理性世界的实在性,不具有形上学含义。
其次,唯识学论证的逻辑是“法、我二空”,即外在世界和“我”都是虚幻存在,由此证明“唯识实有”。而现象学的指向是论证对象世界呈现出来的确定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与“识”完全不同。因为,唯识学之“识”可转变为八识,每个识都有其种子,因此,“识”也包罗万象。而现象学只是讨论意识,不关注心理现象和精神活动,也不关注世界的物理构成。
再其次,就时代性来说,唯识学的知识背景是公元七世纪人们的生活经验常识,而现象学的知识背景则是以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因此,唯识学从纯粹感觉出发把握对象,以经验和体验为依据,很少展现概念构造和抽象逻辑演绎的力量。而现象学则是属于20世纪的学术体系,具有严密的概念系统和逻辑力量。这是唯识学与现象学在理论品质上的根本分歧。
最后一点,唯识学归根结底是宗教理论,指向宗教,引导信众由三性到三无性,成佛涅槃。而现象学作为哲学,由解决认识中意义的确定性问题,进而解决科学合法性问题。因此唯识学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对象世界也具有不同的逻辑时空:唯识学构造的时空是三界,包含过去、现在、未来,具有立体圆形时空性质。虽然这其中的论证有认识论成分,但是在很多问题上已经超出哲学的领域。而现象学的时空仅仅是现实世界,展示了平面线性时间,宗旨是人类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
初稿草成于京西魏公村退园,岁次2020年12月31日中午,寒气凛冽而阳光明媚。定稿于2021年2月2日傍晚,甲子最后的冬日。
-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维柯《新科学》对近代启蒙历史视野的引入
- 从疑难出发:《形而上学》B卷的辩证法阐明
- 《墨子·经上》原经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