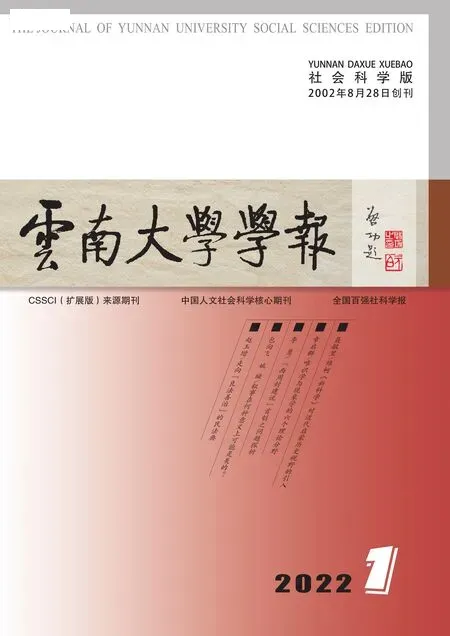维柯《新科学》对近代启蒙历史视野的引入
聂敏里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一
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种历史批判的意识便已经开始发育,并且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不仅广泛体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们所进行的大量有关城市史、市民社会史、艺术史的撰著工作中,而且更为深刻地体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对古代文献的卷帙浩繁的校勘工作中。因为,正是在这个工作中,一种按照古代著作家的实际历史状况来理解他们的思想、订正他们的著作的历史批判的意识,已经成为校勘者们的普遍的科学共识。对此,加林曾经这样评论道:“正是在对待过去的文化,对待历史的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明确地确定了人文主义的本质。这种态度的特征并不在于对古代文化的特殊赞赏或喜爱,也不在于更多地了解古代文化,而是在于具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历史观。……发现古代世界就是衡量自己同古代世界之间的距离。他们首先应同古代世界脱离开来,然后再确定同它的关系。”(1)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15页。相关的讨论也可参考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40-145页。这样,正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学者的历史书写和文本校勘工作中,一种历史意识已经开始发育。
但是,实践是一回事,对这种实践形成明确的理论自觉则又是另一回事。当我们观察早期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文献时,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尽管这些启蒙思想家,例如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卢梭等,在确立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人的主体权利等方面,确实将自身与整个古代思想传统拉开了距离,并且在此意义上是启蒙的,但是,就他们仍然诉诸一种先验理性和一种普遍社会模式而言,他们恰恰在历史思维方面是需要启蒙的。历史对于这些早期启蒙思想家来说只存在两个阶段或者两种状态,这就是史前阶段和文明阶段,或者启蒙前的状态和启蒙后的状态。启蒙前的状态究竟是怎样的,他们有着种种不同的见解和想象,但是,启蒙后的状态是怎样的,他们的观点却几乎一致,这就是,这是一个自然理性之光普照的世界,是一个自然法被普遍遵循的国度,在这里,历史不是刚刚开始,而是已经结束。但是,由于在前启蒙时期历史尚未开始,而从启蒙前的状态向启蒙后的状态的过渡又仅仅是通过一种逻辑转换的方式“突然”完成的,因此,实际上,在早期启蒙思想家那里就从来没有历史,历史意识在他们那里诚然是匮乏的。(2)相关论述参见彼得·蒙兹的“‘新科学’的理念”(Peter Munz, “The Idea of ‘New Science’”, in Vico and Marx, affinities and contrasts, Giorgio Tagliacozzo, ed., Humanities Press, 1983):“启蒙不能历史地说明它自己的存在。人们可以把这种无能看作是一个内在的弱点。而这并非由于启蒙者对过去不感兴趣,而是由于恰恰是启蒙的观念使得对过去的一种历史的理解成为不可能,并因此证明它是一个领域而且仅仅是一个领域中的巨大障碍。启蒙始终不能说明它是如何产生的。……所需要的是一种可以把过去作为一系列导致启蒙的事件链索来研究的新科学,好让启蒙可以被给出一个起源,使其看上去远非一种奇迹。奇迹已经从所有其他思想中被排除出去了,不能容许它对我们的历史知识保有控制权。……这样留给扬巴蒂斯塔·维柯去做的就是,提出启蒙所需要的这种新科学,把我们的历史知识加到我们所有的那些启蒙在其中已经取得胜利的领域的知识之上。”(pp.2-5)
显然,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维柯的思想史意义被凸现出来了。因为,在他的《新科学》中,人类社会第一次通过一个清晰的历史过程被予以构造,人类社会不再属于自然,而是属于历史,他的《新科学》在自然世界之外为人类构造了一个历史世界,并且宣布只有这个世界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是人类自己的创造物。这相较于早期启蒙思想家的那种缺乏历史意识的先验理性,当然是又一次思想启蒙。因为,现在,理性有了自身的限度,这就是历史限度。理性意识到自身是有局限的,它不是无时间的普遍性,相反,它自身就在时间之中,它在本质上只能是历史理性。就此而言,维柯对历史意识和历史科学的引入,无疑是对启蒙观念的极其重要的补充。因为,没有历史意识的启蒙观念是不完整的,并且自身仍然是有待启蒙的。只是由于历史感或者说历史的限度意识成为理论的自觉,并且形成了一门“新科学”,从文艺复兴以来经过“人的发现”、“主体性的确立”的近代启蒙思想才得到了重要的推进。(3)相似的观点可以参见古斯塔沃·科斯塔在《维柯著作选》的《中译本序》中的论述,在那里,他明确地把维柯的《新科学》看成“意大利对启蒙运动哲学的最重要贡献”,并指出维柯著作的杰出编辑者尼古拉·阿巴尼亚诺的研究纲领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引出一种足以容纳像维柯这样一位思想家的新的拓宽的启蒙运动概念……让他进入英法启蒙运动的hortus conclusus[殿堂]”(利昂·庞帕编译:《维柯著作选》,陆晓禾译,周昌忠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页),同时,他还勾勒了由彼得罗·皮奥瓦尼领导的那不勒斯维柯研究中心、克罗齐、加林等为代表的意大利维柯研究对维柯思想与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内在紧密关系的论证,从而破除了维柯思想置身于18世纪启蒙运动之外的神话。
二
但是,由此一来,针对维柯的《新科学》,我们要首先予以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新科学》何以是“新”科学?“新科学”究竟“新”在何处?(4)维柯《新科学》的英译者之一费希(Max Harold Fisch)在《新科学》英译本的“导论”中曾经对“新科学”的“新”做过简要说明。参见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xxxiii-xxxiv.
在已有的研究中,尽管人们早已承认了维柯的“新科学”作为历史科学的开创意义,但是,从保守主义的立场和反现代、反启蒙的立场出发,一些研究者仍然愿意忽视这一点,而更多地强调维柯的“新科学”作为一门哲学人类学、政治神学、神话学、诗学、甚或反科学的意义。(5)马克·里拉的《维柯——反现代的创生》是这一倾向的典型代表。参见马克·里拉:《维柯——反现代的创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以下。从而,面对这个问题,阐明维柯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将他的这门科学称作一门“新”科学,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此而言,研究者们普遍地将维柯的“新科学”同他首创的所谓“真理—创造物”(verum-factum)原理联系在一起来解释。但是,一些研究者似乎仅仅注意到这个原理表面的那种反对或者说贬抑自然科学(这在维柯那里就是指以笛卡尔主义为代表的近代物理学)的特征,因此将它简单地同整个近代科学对立起来,并更进一步地通过一种简单化的处理将它同整个近代启蒙运动对立起来,却没有更为深刻地认识到这个原理内在的、只能属于现代思想的维度和一门历史科学的内涵。(6)参见马克·里拉:《维柯——反现代的创生》,第149-153页。相反的观点参见Jeffrey Barnouw, “Vico and the Continuity of Science: The Relation of His Epistemology to Bacon and Hobbes”, Isis, Vol. 71, No. 4 (Dec., 1980), pp.609-620.因此,对这个原理的这些理论内涵首先予以阐明,就是我们的任务。
“真理—创造物”原理是维柯在他的《论从拉丁语词源发掘的意大利人的古代智慧》(7)De Antiquissima Sapientia Italorum ex Linguae Latinae Originibus Eruenda,本书中译名采用了陆晓禾的译法,见利昂·庞帕编译《维柯著作选》第79-120页。张小勇对该书的译名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一著作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在《新科学》中他又对其做了重要的扩展和发挥。
在《论从拉丁语词源发掘的意大利人的古代智慧》中,维柯首先是从词源学的角度提出这一原理的。他考察了拉丁语的“真理”和“创造物”两词,指出“真理”(verum)就词源学的意义来说是可以和“创造物”(factum)一词互换的,从而就确立了“真理就是创造物”的原理。他这样说:“在拉丁语中,verum[真理]和factum[创造物]是可互换的,或者用经院哲学家的话说,它们是可转换的术语……这样,人们可以推论,古代意大利哲学家持有下述关于真理的信念:真理就是创造物。”(8)维柯:《论从拉丁语词源发掘的意大利人的古代智慧》,见利昂·庞帕编译:《维柯著作选》,陆晓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3页。
人们或许会认为维柯提出这一原理的方法过于简单,但实际上,它是建立在更为深刻的观察与思考的基础上的。维柯告诉我们,人类的理解和认识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创造活动,我们只是由于通过在思想中组织认识的材料,才达到了思想上的认识和理解。他这样说:
像阅读是人集合形成语词的文字要素的行为一样,理解也是集合一个事物的所有要素,借助这些要素能够表达最完全的观念。(9)维柯:《论从拉丁语词源发掘的意大利人的古代智慧》,第83页。
正如神的真理是上帝按他所知加以安排的产物,人的真理也是人按他所知安排事物的产物。知识就是对借以按照心灵对模式的认识来创造事物的属或模式的认知,因为心灵安排要素,创造事物。(10)维柯:《论从拉丁语词源发掘的意大利人的古代智慧》,第84页。
真理等同于对一切要素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建构了这个事物世界,并且如果它愿意的话,它还能够建立无数个世界。(11)维柯:《论从拉丁语词源发掘的意大利人的古代智慧》,第84页。
因此,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和理解,是因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的对象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我们创造了什么,我们也就能够认识和理解什么。而凡不是我们所创造的,我们也就不能达成对它的认识和理解。在此基础上,维柯便区分了神的真理和人的真理。神的真理是神的创造物,只有神才能理解和认识,而人只能认识和理解由他自己所安排和创造的事物,这构成了人的真理。
尽管维柯承认神的真理的完满性,认为人的真理相对于神的真理是片面而破碎的,例如,他这样说,“神的真理是事物的立体表示,如同一座塑像;人的真理是一张素描即平面表示,犹如一幅绘画。……神的真理是立体,因为上帝把握万物;人的真理是平面的,因为人仅仅把握事物的外表,”(12)维柯:《论从拉丁语词源发掘的意大利人的古代智慧》,第84页。“我们所讨论的事物——存在、统一、形状、运动、肉体、理智和意志——在上帝那里是一个整体,而在人那里,它们则是分割开的。在上帝那里,它们是活的,在人那里则是死的”(13)维柯:《论从拉丁语词源发掘的意大利人的古代智慧》,第86页。,但是,这并非构成维柯因此否定人的真理乃至人的认识能力的基础,相反,却构成了维柯由以确立人类知识的有效性的根据。(14)相关论述可以参考[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英]R.G.柯林伍德译:《维柯的哲学》,陶秀璈、王立志译,郑州:大象出版社,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第2-8页,第15-16页。他这样说:
因此,当着人着手研究事物的本性时,他最终意识到,不可能达到他的目标,因为他在自身中并不包含构成物赖以存在的要素;他还意识到,这是他自己心灵的局限性造成的,因为一切事物存在于他自身之外。人把他的心灵的这个缺陷转到有用的目的上,他从而借助人们所称的抽象为自己发明了两个东西;可以画出来的点和可以倍增的一。……这样,他为自己制作了一个形状和数字的世界,他能够将它整个包含在自身之中,通过延长、缩短和联结线,通过加、减和计算数字,他得出了无限多成果,因为他在自身中所察知的真理是无限的。(15)维柯:《论从拉丁语词源发掘的意大利人的古代智慧》,第87-88页。
这就是说,自然界作为神的创造物,其在本性上属于神的真理的认识范围,由于人类不能创造它,从而,它在本质上是人所不能获知的。但是,这并不因此就消除了人的知识的可能性,或者说将人的认识导入不可知论,相反,却使得人的真理、人的知识成为可能,因为,就像神能够认识的是他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一样,人也能够认识他自己所创造的东西。这样,对于维柯来说,数学知识和几何学知识由于完全出自于人类心灵的构造,就是人类可以完全获知的,构成了确定的人类知识。他这样说:“人的好奇心在探索其本性不允许他探求的真理时,却产生了两门对人类社会极有用的科学,即算术和几何学,由此产生了力学,后者是人类所必需的一切工艺之父。”(16)维柯:《论从拉丁语词源发掘的意大利人的古代智慧》,第88-89页。而物理学,当它严格地将其自己的研究范围限制在人的实验活动的范围内,而不是企图去认识神的创造物——自然时,它同样也能够达至确定的人类知识。他这样说:“在物理学中,我们能够造成与某些物理学理论相似的结果来证明那些理论,而当为了证实自然事物的观念,我们能够作一些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创造某种与自然相似的东西,这些观念就被认为是最清晰的,并得到最广泛的承认。”(17)维柯:《论从拉丁语词源发掘的意大利人的古代智慧》,第89页。
因此,在这里,假如有人试图说明维柯是反科学的,那么,他的理解当然就是片面的。(18)伯林是这种意见的主要制造者,参看他的《维柯的知识观》(见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33-143页)维柯所反对的是企图达成像神一样全知全能、对人的认识能力未加限制的(自然)科学知识,但却根本不反对人能获得在人类自己创造活动范围内的事物的科学知识。事实上,通过这一区分,他便将科学知识奠立在了人的创造活动的基础上,使得科学知识的人类性质得以阐明。(19)参见Jeffrey Barnouw, “Vico and the Continuity of Science: The Relation of His Epistemology to Bacon and Hobbes”, Isis, Vol. 71, No. 4 (Dec., 1980), pp.609-620.显然,就维柯区分神的知识和人的知识,将人类认识的范围限定在人能够把握的知识范围内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启蒙”的了。(20)参见古斯塔沃·科斯塔在《维柯著作选》的《中译本序》中的论述:“照阿巴尼亚诺的看法,维柯应被看作‘una manifestazione integrante dell’ illuminismo settecentesco’ [‘18世纪启蒙运动不可或缺的表现’],因为他同洛克和牛顿一样,也试图界定人的能力。维柯同英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相似关系清楚地表明,他同笛卡尔的对立必须按照他自己时代的文化来解释。”(利昂·庞帕编译:《维柯著作选》,第2-3页)他的“真理—创造物”原理所阐明的不过是科学知识的主体性内涵或者说人类学内涵,它表明科学知识与其说是“非人的”,不如说是“属人的”,它与其说是人的异己之物,不如说是人的属己之物,它是人的主体心灵的创造,它在根本上是人的主体知识。就此而言,维柯的知识观没有一点是与现代知识观相反对的,他的“新科学”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是对现代科学的反对,相反,它是对近代启蒙主义科学知识观的深化。
三
但是,这还不是维柯的《新科学》之所以是“新”科学的关键所在。对于维柯来说,他的“新”科学的“新”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对人类社会生活世界的引入和对这个世界的历史性质的阐明。他的“新科学”的全新的价值就在于,他在启蒙理性的内部引入了历史理性,他用历史理性替换了从古典传统继承而来的、因而桎梏着启蒙理性的发育和发展的自然理性。(21)对启蒙理性和自然理性的区分,参见聂敏里:《启蒙的前提》,《人文杂志》2018年第8期。而维柯完成这一思想转化的关键就在于他在《新科学》中对“确实的东西”(the certain)这个概念的阐明。
正如克罗齐所正确指出的,这虽然属于维柯知识论的第二个阶段,但同他的知识论的第一个阶段却是紧密相连的,尤其是与“真理—创造物”这个原理。(22)参见[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英]R.G.柯林伍德译:《维柯的哲学》,陶秀璈、王立志译,第15页。
在《新科学》第一卷第二部分“要素”第137条中,维柯这样说:
不知道什么是事物的真实(true)的人们就费心地去抓住那是确实(certain)的东西,以便如果他们不能够凭借知识(scienza)来满足他们的理智,至少他们的意志还可以安置于意识(coscienza)之上。(23)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62-63. 维柯《新科学》的中译本是由朱光潜先生于1986年翻译出版的,最早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目前唯一可用的一个汉译本。但是,由于朱光潜先生翻译这本书时年事已高,有些重要术语的翻译或未经过仔细地推敲、琢磨,因而同历史学、政治学、哲学和诗学方面已经积累起来的比较成熟的汉译概念体系多少有些乖舛,给研究和引用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本文的写作尽管抱有对朱光潜先生筚路蓝缕工作的极大敬意,具体的引文仍然直接从菲什、伯金的英译本译出。下同。
在这里,维柯的一个关键性的做法就是把“真实”和“确实”对立了起来,而这一对立立刻就能使我们想起在《论从拉丁语词源发掘的意大利人的古代智慧》中神的真理和人的真理的对立。事物的真实,由于人不是事物的创造者,因此也就是人所不能够真正认识的,只有神才能够对此有全面、完整的把握。而人只能够去认识人作为其创造者的东西,在这方面获得专属于人的知识。它们虽然不如神的知识那样在事物方面是“真实”的,但是,它们却具有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性,这就是,它们对于人而言是“确实”的,它们是人所能够把握的“真实”。如我们所知,在《论从拉丁语词源发掘的意大利人的古代智慧》中,属于人的认识能力范围之内的知识只有两门,这就是数学和几何学,它们由于是人类理智的创造物,从而是人完全可以把握的。但是,在这里,当维柯用“确实的东西”来规定人的知识的对象,以便将它与神的知识的对象即事物的“真实”区分开来时,我们注意到,他所做出的一个重要的扩展就是,他在人的理智之外引入了人的意志,从而实际上就将人的知识从理智静观的范围扩展到了意志选择的范围,使它不再仅仅局限于数学和几何学,而是还可以包括别的知识内容,亦即人类意志活动是其创造者的事物。但这样一来,问题就是,这是一些怎样的知识呢?它们的对象如何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些“确实的东西”呢?
在紧接着的第138条中,维柯对此做出了初步的说明。他这样说:
哲学沉思理由,由此产生对真实的东西(the true)的知识;语文学观察人类选择是其创作者的东西,由此产生对于确实的东西(the certain)的意识。(24)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64.
在这里,“哲学沉思理由,由此产生对真实的东西(the true)的知识”无疑是就自然科学知识而言的。由于事物的终极原因是在上帝那里,因此,对于这部分东西,我们的知识只能是表面的、外在的和不完整的。但是,在这一条的后半句话中被提出来与“哲学”相对的“语文学”却显然具有另外的特征。因为,语文学所关注的恰恰不是自然,而是历史,是人类的历史生活世界及其语言、文字的遗存。维柯用“人类选择是其创作者”来对语文学所关注的对象加以限制,恰恰表明在这里所涉及的正是人的意志活动及其产物。克罗齐阐明了这一点,他说,“后者处理人类意志的决断,即人类自由选择的意见,追随权威,由此产生关于确实的东西的知识”。(25)[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英]R.G.柯林伍德译:《维柯的哲学》,第20页。引文根据英译文有所修改,见Benedetto Croce, The Philosophy of Giambattista Vico, The Macmilian Company, 1913, p.31.“维柯的所谓语文学不仅研究词和词的历史而且研究事物的历史,因为词与事物的观念紧密相连。这样一来,语文学家应该处理战争、和平、联盟、旅游、商业、习俗、法律、币制、地理学、编年学以及其他一切与地球上的人类生活相关的学科。一言以蔽之,在维柯的判断中,当然也是正确的判断,语文学不仅包括文学或语言的历史而且涉及事件、哲学和政治的历史。”(26)[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英]R.G.柯林伍德译:《维柯的哲学》,第20-21页。这就表明,对于维柯而言,语文学所关注的对象正是他所谓的“确实的东西”,它们同自然事物本身的真实当然是有区别的,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对于人类而言却是“确实的”,因为它们是发生在人类生活范围内的“真实”而“确实”的东西,换句话说,它们是显现在人类生活范围内的事物的“真实”,是人类能够“确实”把握的东西。
《新科学》接下来的第139条是对此的证实和澄清。维柯这样说:
这条公理凭它的后半部分把所有的语法学家、历史学家、批评家们都包括在语文学家之中,他们都致力于对人类语言和行动的研究:既有内务的,例如在他们的习俗和法律之中的,也有外事的,例如战争、和平、联盟、旅行和贸易。(27)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3.
这样,随着“语文学”的知识内涵被澄清,“确实的东西”(the certain)这个概念就同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事物关联在一起。它和“真实的东西”这个概念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指向事物的真实、实在的方面,是属于事物的在其自身的存在,但因此就不是人类知识的对象;而人类知识所能够确实把握的却恰恰是他的意志的活动及其产物,而这不是别的,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世界。正是在这个世界中的一切,由于是我们自己的意志的对象,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活动亲手创造出来的,其中凝聚了我们的情感和欲望、热情和冲动,我们经历了其中的全部细节点滴,所以,我们对它们显然拥有完整、全面的知识。(28)参见[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英]R.G.柯林伍德译:《维柯的哲学》,第15-16页、第19页;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5页,第137页。我们虽然不能说我们由此能够获知就事物本身而言的真实的知识,但是,我们却的的确确可以说获得了对于我们而言的确实的知识,它的确实性是对于我们的行动、我们亲身经历的生活而言的确实性。事物方面的真实的知识是属于神的,我们对于它们显然只能拥有完全外在的知识,但是,关于那些属于我们的确实的东西,我们的知识却显然是内在的,是生动而具体的。这是属于人的社会生活的确实性,它当然和事物的自然存在完全不同,如果事物的自然存在指的是事物就其自身而言的存在的话。
既然有关事物的真实方面的知识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维柯就完全有理由要求将认识的目标由对事物本身的关注转到对那些对于人类来说确实的东西的关注上来,而这当然也就是要求建立一门关注人类社会生活事物的新科学。他在接下来的第140条提出了这一任务:
这同一条公理表明,哲学家们不通过诉诸语文学家们的权威而赋予他们的推理以确实性,他们曾经如何半途而废了,而且同样表明,后者不费心通过诉诸哲学家们的推理来赋予他们的权威以真理的核准,他们也曾经如何半途而废了。如果他们早就这样做了,他们就会更有益于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且他们在构思这门科学上就会对我们有所预示。(29)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3.
在这里,通过要求哲学家诉诸语文学家的权威以赋予他们的研究以“确实性”,维柯就等于是将哲学限制在了人类知识的范围内,要求哲学不再去关注那些有关事物本身的、形而上学的真理,而是去关注人类社会生活的领域,在这里获得确实的知识。但这也就意味着将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引入到语文学的领域,就语文学所涉及的是人文学科而言,也就是要求赋予人文学科以哲学思维的科学性,使得它们经得起严格推理的检验。显然,如此一来,所造就的就是一门全新的科学,这也就是关于人的社会生活领域的科学。
这样,通过对“确实的东西”这个概念的阐明,并且把它所指涉的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确立为人类知识真正的对象,维柯实际上也就等于是更新了传统的知识观。因为,在自然理性的支配下,整个古典哲学的知识观说到底就是认识事物本身的真理。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一卷第1章中所刻画的认识的途径,“从对于自然不太清楚但对于我们较为清楚的东西引导至对于自然较为清楚、较为可知的东西”(184a19-20),就是对这种知识观的经典表达。巴门尼德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是其所是”、甚至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说到底都是事物之自身或者说事物作为其自身的存在。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所沉思的三类实体也不外乎就是这样的存在,尽管在他那里他诉诸的是观念的清晰明白,亦即诉诸的是主体理性,而不是单纯的自然理性。显然,当我们勾勒出这样一条思想线索,维柯思想的革命性就显现出来了。因为,通过将人类的知识限定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他实际上也就赋予了真理以主体内涵和历史内涵,将真理从古典真理观所规定的那种独立、自在的位置上拿了下来,而把它与出自人类意志的实践活动关联在了一起。这当然是在真理观上的一个重大的发展,是一个完全现代的真理观。这一点,我们只要想一想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和他的那个同样具有高度主体性内涵的命题——“人为自然立法”,就可以充分明白了。
而一旦将人类知识限制在人的社会生活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的知识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性质也就是不言而喻的,维柯在“原则”部分中的第331条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他这样说:
民政社会的世界无疑是由人所创造的,它的原则因此应当在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的各种变状中被找到。任何人反思这一点,就不能不惊奇,哲学家们竟然会倾全力于对自然世界的研究,后者既然上帝创造了它,就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竟然会忽视对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后者既然人创造了它,人就能够逐渐认识它。(30)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96.
在这里,维柯所使用的“民政社会”(civil society)和“民族世界”(the world of nations)这两个概念,如费希在“导论”中所指出的,“是一个由异教各民族放到一起而构成的世界,甚至在他们尚未完全彼此分离时;不是一个直到这些民族进入商业的、外交的、结盟的、联邦的和彼此之间的战争与和平条约的关系之中时才被首先创造出来的世界,而是一个被认识到早就存在着的世界,尽管在这些关系中并且通过这些关系经历着进一步的发展”。(31)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xxii.这样,它就是一个处于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的世界,但是,却由于其中“民族”的由其拉丁语词源natio而来的“生殖或产生”“创始或诞生”的含义,(32)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xxi.具有了历史的内涵,也就是说,这个人类社会生活的世界同时是一个历史演化的世界,它经历了并且正在经历着各种社会关系的演变。维柯按照“真理—创造物”的原理,将这个世界与属于神的认识范围的自然世界对立起来,并把它看成是哲学家们更应当着力去加以研究的对象,显然就暗示了他的“新科学”的历史科学的性质。
而如果说这一点在第331条中还仅仅是一种暗示,那么,“方法”部分中的第349条便可以说是维柯对此的最明确的宣示。他这样说:
因此,我们的科学凭借每一个民族在其兴起、发展、成熟、衰落和消亡中的历史转而与此同时去描述一个在时间中经历的理想的永恒的历史。确实,我们大胆断言,谁沉思这门科学,谁就在向自己叙述这一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就他通过“它过去不得不是、现在不得不是和将来不得不是”的证据给他自己创造了这一历史而言。因为,上面设定的头一条不可置疑的原理就是,这个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创造的,它的面貌因此必然在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的各种变状中被找到。而且历史不可能比这更确实的了,如果谁创造事物谁也就叙述事物的话。现在,正像几何学,当它从它的元素中构造量的世界或者沉思那一世界时,它在为它自己创造它,我们的科学也是如此[它为自己创造民族世界],却具有一种更大的实在性,因为必须处理人类事务的各种制度比起点、线、面和形体来更为实在。而且,读者啊,正是这个事实是一个论证,表明这些证据是神圣的,应当赠予你们以神圣的快乐,因为,在上帝那里,知识和创造是同一回事。(33)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04-105.
这段话的经典意义在于,在这里,维柯将他的“真理—创造物”原理与他在《新科学》中所阐发的“确实的东西”的概念熔为一炉,从而为揭示他的“新科学”的历史科学性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表明,几何学诚然是人的心灵的创造,但是,同样属于人类心灵创造的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相比于几何学所研究的点、线、面来却要具有“更大的实在性”。这样,科学研究的目标就由单纯的自然科学领域转向了人文科学的领域,它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世界,而这就是一个民族的世界。但是,不仅这个民族的世界是由人创造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它是人自己的创造物,从而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个兴起、发展、成熟、衰落和消亡的历史,并且在这里体现出一个“过去不得不是、现在不得不是和将来不得不是”的历史规律,而这也就是所谓的“理想的永恒的历史”。这样,对人类社会生活世界关注并研究的这门科学在本质上就是一门历史科学,它不是以简单地叙述发生在其中的各种“确实的”事件为满足,而是也要探求其内在的原因,并追寻普遍的规律。这是它的科学性的体现,但是,毫无疑问,由于研究的对象由单纯的自然存在转向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存在,它也就是一门“新”科学。
维柯当然充分意识到了他的这门科学的全新性质,在《新科学》第五卷的最后,亦即第1096条中,他这样自豪地宣称:
因此,我们不禁要给予这部著作以“新科学”这一惹人忌妒的头衔,因为,就其论证像关于各民族共性的论证那样普遍,就属于每一门科学的那一特性在其理念上是完美的而言,这远不是要不公正地为它骗取它本应有的正当权利,而且对于这一特性塞涅卡已经为我们用他的恢宏的言辞提了出来:“这个世界是一个渺小之物,除非它为对整个世界的研究提供材料”。(34)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415.
这就是说,它虽然是一门历史科学,它虽然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生活领域中的事物及其发生、发育、发展的模式,但是,它却同样具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理论的普遍性和严谨性。它实际地实践了维柯所提出来的哲学与语文学的结合,既赋予了人文学科以哲学思维的科学性质,又赋予了哲学思维以人文学科所特有的社会历史内涵。这二者的结合就是一门“新科学”。
四
在阐明了这一点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看看维柯是怎样在《新科学》中系统地把历史的视野、历史的原则、历史的方法引入进来的。
《新科学》是以一个非常独特的“序论”开始的,这就是按照一种古代传统做法,以图形象征的方式来涵括全书思想的核心要旨,然后以文字的方式对它进行扼要、细致地解说。这样,“置在卷首的图形的说明,作为本书的序论”就构成了《新科学》一书的导论部分,而正是在这个导论中,维柯逐步地引入了他的“新科学”亦即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视野。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维柯对所谓的民政世界(the civil world)或者民族世界(world of nations)格外重视,远胜于通常形而上学所关注的自然世界(natural world)或者物理世界(physical world)。而所谓“民政世界”或者“民族世界”,如前所说,所指的就是人类的社会历史生活领域。而维柯鲜明地意识到,对于人来说,他首先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他与其说是一个自然的存在,毋宁说是一个社会的存在,他拥有和他的自然存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存在方式,这也就是他的社会生活。从而,和早期启蒙主义思想家更多地关注自然、关注人的自然本性亦即人的永恒不变的自然存在不同,维柯在《新科学》中却集中关注人的社会存在。我们看到,在“序论”中,针对他所给出的那幅图形,维柯这样描画说:
地球,或者物理的、自然的世界,是由祭坛仅仅以一部分支撑的,因为,直到现在,哲学家们仅仅通过自然秩序沉思神圣的天意(divine providence),因而只表明了它的一部分。……但是哲学家们还没有就它的最适合于人类的那部分来沉思上帝的旨意,因为人类本性具有这一主要特性:即是社会的。(35)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
在这段话中,通过与物理世界或者自然世界的对比,人的社会存在或者说人的社会属性就被维柯提出来,当成哲学家应当着力加以沉思的内容。这当然构成了他的“新科学”的全新的内容之所在。换句话说,“科学”在他那里现在不再单纯地意味着“自然科学”,而是也意味着“社会科学”,人类社会现在成了科学所应当着力研究的对象,而社会存在也成了更适合于人的存在方式。

“序论”接下来的一段话已经向我们暗示了这一点:
在提供这一特性中,上帝这样规定和安排了人类的各种制度,从而,既然人已经由于原罪而从完满的正义堕落,而且与此同时几乎总是想要去做十分不同的、完全相反的事情——以致为了私人的利益他们像野兽一样孤独生活,他们便被这同样的利益所引导,而且沿着前述的不同的和相反的道路像人一样生活在正义中,并且将他们自己保持在社会中,而且由此观察到他们的社会本性。(37)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pp.3-4.
这段话当然是对上引文中的那个“神圣的天意”的解释,但是却已经将人类社会存在的历史性隐含在其中。因为,在这里,人的社会存在没有被设想为是人的一种自然的存在方式——古代自然法传统对人的社会存在的理解就是这样的,而是按照基督教的原罪理论和末世理论,被看成需要通过某种特殊的历史过程才能够达到的。(38)维柯同基督教的关系,可以参看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第六卷《革命与新科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8-100页。起点是人从完满正义的堕落,因而野兽一样的生活,但是,由于私人利益的驱使,人却走向了社会的联合,生活在社会之中,并且建立起各种社会的制度。因此,如果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城邦的动物”时,他是就人的自然本性而言的,那么,当维柯在这里指出人的社会属性时,他却是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的产物来理解的。对于维柯来说,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社会性的,而是逐渐获得社会性的,人像人一样生活,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
要对这一点有更清楚地把握,我们就还必须对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天意”这个概念进行考察,因为上述的历史内涵正是通过这个概念被表达出来的。但对此的最清楚地阐明并不在“序论”当中,而是在“原则”第341条中:
但是人,由于他们的腐化的本性,处于自爱(self-love)的暴政之下,它迫使他们将私人利益作为他们的主要的引导。由于追求每一样对他们自己有用的事情,而不追求任何对他们的同伴有用的事情,他们就不能控制他们的情感将它们引向正义。我们因此确立如下事实:人在野兽状态中仅仅欲求他自己的福利;娶了妻子有了孩子后,他就欲求他自己的福利连同他的家庭的福利;进入了民政生活后,他就欲求他自己的福利连同他的城市的福利;当那个城市的统治扩展到了若干个族群,他就欲求他自己的福利连同民族的福利;当各民族通过战争、和约、联盟和通商而联合,他就欲求他自己的福利连同全人类的福利。在所有这些境遇中,人都主要欲求他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是凭着神圣的天意,他才能被保持在这些制度之内,作为家庭社会、城市社会、最后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来实践正义。如果不能达到他所欲求的一切利益,他就被这些制度所限制,去追求他分内的那些利益;而这就被叫作正义的。所以,调节一切人类正义的就是神圣的正义,它被神圣的天意所掌管以保存人类社会。(39)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01-102.
在这里,维柯就向我们勾勒了一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图景,这就是从人的野兽状态出发,到他的家庭生活、城市生活、民族生活,直至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员。它们不是同时存在的,而是处于一个历史演化的进程之中,而在这里起推动作用的并不是什么超出于人的东西,却恰恰是人的自爱的本性,他的私人利益。私人利益使人和人敌对并分离,但是,私人利益也迫使人和人联合起来,并且由于这种联合所带来的私人利益的增进而使得这种联合也不断发展。维柯所提到的家庭社会、城市社会、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种演进的阶段,它和像霍布斯、洛克所勾勒的由人类的前政治、前社会状态到政治、社会状态的过渡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维柯思想中的自然法传统因素。但是,如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在霍布斯、洛克那里不存在历史,人类的政治、社会状态是一次性完成的;而在维柯这里,它却被置于了一个连续的、合理的历史的过程之中,具有了历史性质。因此,在这里凸显出来的就不单单是人的社会存在,而且是人的历史存在。维柯“天意”概念的根本内涵正体现在这里。换言之,与其说维柯通过他的“天意”概念想要表达一种目的论式的世界观,不如说他用这个概念想要表达一种历史主义的世界观。他的“天意”连同这里所提到的“神圣的正义”不过是历史规律的代名词。他用它们来表明,人类社会处于一个具有必然性的历史演进的过程之中,我们因此需要“历史地”去寻求属于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类正义”。显然,由此一来,除了那个作为历史规律的“神圣正义”之外,没有任何超出历史之外的正义,就自然法传统所寻求的社会正义来说,它现在被明确地赋予了历史的限制。
这样,很清楚,尽管人的社会性是维柯特别予以重视和强调的,他在“序论”中所提出并加以讨论的三种制度,即宗教、婚姻和埋葬制度,就是对人的社会性存在的揭示,但是,他并没有将人的社会性按照自然法传统的方式来处理,即把它予以永恒化,而是独特地对它做了历史化地处理,也就是说将它的存在及其实现建立在了一个历史的过程之中。这样,历史性构成了社会性的本质,人的社会存在不仅是在历史中逐渐获得的,而且是在历史中逐渐发展的。维柯因此就赋予了启蒙主义的自然观、政治观以一个历史的视野,而他所说的“这门科学在这方面便成为神圣天意的一门理性的民政的神学”,(40)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4.其所内涵的也正是他的“新科学”作为历史科学的性质。
只是在这一历史视野的基础上,维柯才引入了一个“新批判法”的概念。在“序论”第7条中他这样说:
此外,这里还可以指出,在本书里,以一种迄今为止一直缺乏的新批判法(new critical art),通过进入到对有关这些同样的[异教]各民族的创始人的真相的探索中(在这些民族中要经过千年以上才产生出迄今为止批判所关注的那些作家),哲学从事于检查语文学(亦即,所有取决于人类选择的制度的学说;例如语言、习俗和各民族在战争与和平中的事迹的所有历史),对此,由于原因的极度的晦暗不明以及结果的几乎无限的繁杂,哲学一直惮于处理;而且要通过在其中发现在时间中由各民族的历史所经历的一个理想的永恒的历史的设计,将它归结到一门科学的形式上去。(41)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
在这里,所谓“新批判法”不是别的,就是一种历史批判法或者说历史分析法,即对各种思想材料、观念材料采取一种历史批判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和认识,从而赋予它们一种历史的秩序(所谓的“一个理想的永恒的历史的设计”)。而在这种方法被运用之前,显然,这些观念材料都是非历史地呈列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并不能够“历史地”来看待它们,把它们看成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的特定社会生活方式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要么看成一堆杂乱的习俗堆积,要么看成反映了一种永恒的人类生活的图景。这样,在引入历史视野的同时,维柯也达到了历史方法的自觉,对于他来说,历史意识已经上升到了完全清晰的理论意识的水平。
五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维柯在《新科学》中所确立的历史原则和历史方法做进一步讨论,而这不是别的,也就是对人类事物、人类社会生活做历史观察的原则和方法。
在《新科学》第一卷第二部分“要素”中,针对第一部分通过对“时历表”的注释和资料顺序排列而赋予曾经存在过或发生过的各种人类活动、人类观念、人类制度、人类事务一种历史的叙述顺序,维柯指出,正是从这种基本的历史叙述中可以概括出一些基本的原则,它们构成了他在进行这种历史叙述、历史观察时所依据的基本的原则方法。
维柯所给出的他的这门新科学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历史批判的原则。他首先指出,人类的心灵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爱把自己当作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第二,爱根据自己熟悉的东西来推论自己不熟悉的东西,从而,这就造成了人们在处理有关人性起源的题材上的一切错误的根源,这就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启蒙了的、开化了的、宏伟的时代,他们判断人性的起源,而这个起源由于事物的本性,必定本来是微小的、粗陋的而且十分晦暗的”。(42)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1.由此,维柯就概括了在此基础上容易产生的两种人们心灵上的认识假象,也就是所谓的“偏见”(conceit):一种是民族的偏见,一种是学者的偏见。而这两种偏见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爱把自己所知道的、所熟悉的、所具有的看成是最真实、最自然、最恒常、最古老的。例如,对于前一种偏见,维柯这样说:“每一个民族,无论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都一直有同样的偏见,即,它在所有其他民族之前就发明了给人类生活带来舒适安逸的事物,它的可记忆的历史一直回溯到世界的开端。”(43)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1.而对于后一种偏见,亦即学者们的偏见,维柯又这样说:“他们认为他们所知道的和世界一样古老。”(44)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1.这样,维柯就等于是否定了人们在观察人类历史时那样一种非历史的、无批判的思想方式,而要求针对人们心灵所爱犯的这两种错误建立起历史批判的原则和立场来。
因此,在“要素”I中,针对“由于人类心灵的不定本性,凡是它失落在无知的地方,人就把他自己当作一切事物的尺度”(45)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0.,维柯这样说:
121 这条公理说明了人类的两个共同特点,一方面,谣传在其过程中逐渐生长,另一方面,谣传在事情本身面前被戳穿。在谣传从世界开端处起流行的漫长过程中,它一直是一切夸大的意见的持久的根源,这些意见一直以来都是针对那些我们所无知的远古文物,依据于塔西佗在《阿格里柯拉传》中所提到的人类心灵的那一特点,在那里他说,未知之物总是被夸大。(46)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0.
而在“要素”IV中,针对学者们的偏见,维柯这样说:
128 这条公理也消除了学者们关于古人有无比智慧的一切意见。它判定这些东西犯了欺骗罪,即,迦勒底人琐罗亚斯德和西徐亚人阿那哈尔西斯的神谕,它们从未流传给我们,以及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的《波伊曼德》,《俄耳甫斯教》(或者俄耳甫斯的诗歌),以及毕达戈拉斯的《金句》,就像所有较富有洞察力的批判家们所同意的那样。它还谴责埃及象形文字被学者们所赋予的所有神秘的意义以及他们读入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那些哲学寓言都是粗暴的。(47)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1.
这些段落都清楚地反映了维柯历史意识的自觉和一种历史批判理性的立场。它表明我们不应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切古人的说法都予以轻信,而是应当对它们采取批判地分析和鉴别的态度,从而发现“历史的”事实和真相。而这种历史批判理性的立场无疑是对启蒙理性的补充,它表明正是在学者所自诩的清明的理性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历史的限度,这是我们认识上种种混乱的根源之一,而发现这种限度,对它们执行历史的批判,无疑会有助于我们认识的澄清。
而正是在这一历史意识的基础上,维柯才在第二部分“要素”的第147和148条中讲出了如下两段堪称是石破天惊的话。他说;
147 各种制度的本性不过是它们的在一定时期、以一定方式的生成。只要时期和方式是如此这般,生成的制度也就是这样,而不是别样。(48)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4.
148 各种制度的不可分割的特性必定是由于它们由以产生的变状或方式。根据这些特性,我们因此就可以证实本性或生成情况是这样而不是别样。(49)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4.
这两段文字的价值和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说第一次以明确的语言宣示了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考察总要基于它由以产生的一定的历史条件,没有在历史之外的事物,任何事物都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并且因此受到它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制约。如果说“历史主义”是一个“家族相似”概念,亦即,不是只有一种历史主义,而是有多种历史主义,那么,能够给予不同的历史主义以“家族相似”的共同特征的,恐怕正是这条基本原则。而就在此之前没有一个哲学家清楚地表达过这个原则而言,同时,就早期启蒙主义思想家甚至连历史意识都是缺乏的,支配他们的更多的是自然理性而言,维柯这里的这两段表述当然就使自文艺复兴以来处于觉醒之中的历史意识上升到了历史理性的层面,意味着一种理论的自觉,即能够自觉地以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和审视事物。因此,相对于自然法传统对永恒的人类制度的期许,维柯在这里的观点就是将人类制度放到了它们由以产生的各种历史条件下,使其受到各自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规定。显然,这样一来,永恒的人类制度就不存在了,存在的总是某种特定的历史制度,它因为是历史的,才是真实的,我们才能够对其特性获得确实的认识。
上述原则实际地构成了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中从事具体的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例如,在第二卷《诗性的智慧》的第十部分,亦即“诗性时历”的部分,维柯正是从历史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时序倒错”的概念,对人们在历史研究中所犯的这一类型的错误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他说:
735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四种时序倒错,位于将时间放得过早或过晚这一熟悉的、总的标题下。第一种是把本来必定充满着事实的时代弄成事实空虚的时代。这样,我们在其中发现了人类民政制度的几乎所有起源的诸神时代,却被博学的瓦罗作为黑暗时代而予以忽视。第二种是本来事实空虚的时代却变成了充满事实的时代。这样,根据下述错误的信念,即神话传说都是由英雄时代的诗人们、特别是由荷马创造的,仅有二百年之久的英雄时代就被塞满了属于诸神时代的所有事实,而这些事实应当被放回到它们所属的时代中。第三种是把本应划分开的时代合在一起,以免例如希腊在俄耳甫斯一生的跨度内应当似乎就由一种野兽的状态过渡到了特洛伊战争的辉煌(这就是时历上的怪论,我们在我们对时历表的注释〔79〕中已经要求注意)。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就是把应当合在一起的时代划分开来。由于这种时序倒错,在英雄们漫游之后三百多年,希腊殖民者才被带入西西里和意大利,相反他们是在这同一批英雄漫游的过程中以及作为其结果被带到那里的。(50)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81.
这样,以历史批判的态度,将所处理的材料不仅首先看成是“历史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批判地分析它们所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来正确地赋予它们以其历史存在的合理性,这就是维柯的历史科学的核心内涵。它向我们深刻地表明,历史化不是简单的情境化,历史事件不仅仅是一些具有特定情境的具体事件,呈现一个历史情境只足以表现历史事件的个性,却并不足以呈现历史事件作为历史存在所特有的历史性。只是在对历史事件自身受其规定和限制的历史条件的深入分析和揭示的基础上,历史事件作为历史存在所特有的历史性才被呈现出来了。这也就是“历史科学”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传记”、更不是“历史小说”的原因所在。历史科学是原因和条件分析性质的,而不是单纯事件描述性质的。只有对事件采取这样的一种观察方式,才是真正“历史的”观察方式,并且也才可能谈及一门严谨的历史科学。
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看到,在后面的“方法”部分,维柯就明确地指出了如何来运用这种历史批判的原则和方法。他这样说:
338 为完成为本科学所采取的那些原则的奠定工作,在第一卷中剩下的就是讨论它所应当遵循的方法。它必须从它的题材开始处开始,就像我们在公理〔314〕条中说过的那样。因此,我们必须和语文学家们一道返回,从丢卡利翁和皮娜的石头,安菲翁的岩石,自卡德摩斯的犁沟中涌现出的人,或者维吉尔的硬橡木,来达至这门科学。我们还必须和哲学家们一道来达至这门科学,从伊壁鸠鲁的蛙,霍布士的蝉,格劳修斯的傻子们;从没有天神的看顾或协助而被投入这一世界的那些人那里,……这也就是说,要从荷马的独眼巨人那里,在他们之中柏拉图认识到了家族状态中的最初的家长们〔296〕。(这就是语文学家们和哲学家们已经提供给我们的关于人类原则的那门科学!)我们对它的研究必须以这些生物开始以人的方式思想的时候为开端。在他们的骇人听闻的野蛮和不受约束的野兽般的自由中,没有任何办法来驯化前者或约束后者,除了对某种神性的畏惧的思想,对它的畏惧是将一种趋于疯狂的自由归于职责的唯一的强有力的办法〔177〕。为了发现这最初的人类思维在异教世界兴起的方式,我们碰到了令人绝望的困难,已经花费了我们足足二十年的研究。我们曾不得不从我们的这些人类的、精致的本性下降到那些十分疯狂而野蛮的本性,这些本性我们根本不能想象,只有以巨大的努力才能理解。(51)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00.
显然,在这整段话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一句:“它必须从它的题材开始处开始”,这句话道出了维柯的新科学的历史科学之本质。它表明,在对题材的处理中,首要的是呈现题材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只是在将它们放到了它们适合的历史条件下,按照给定的历史条件来理解,研究的对象才呈现出了它们真实的面目。同时,也只是将不同的题材放到它们各自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中,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才体现出来了,这就是它们自身所具有的历史的差异,而这也构成了它们自身作为历史存在的本质。因此,和通常人们关于理解所以为的相反,正确的理解不是通过取消理解对象的历史性或历史差别而获得的,而恰恰是通过建立起理解对象的历史性或历史差别而获得的,只是通过历史地分析和批判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本质上是历史性的理解,我们才达到了对理解对象的正确和真实的理解,相反,那种取消了这种历史分析和批判的维度的所谓诉诸原义的理解,却恰恰会由于犯了非历史的错误,而误将某些当代的观念、意识、共识、文化塞入所理解的古代材料中,而造成对材料的无法理解和错误理解。而这种历史性的理解之所以可能,其原因仅仅在于,我们恰恰就是历史性的存在。
实际上,在“要素”部分,维柯已经将这一点概括成了一个基本的原理,他说:
314 诸学说必须从它们所处理的题材开始处开始。(52)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92.
然后解释说,“这条公理被普遍地运用于这里所讨论的一切题材中”。(53)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92.这就表明,这种历史的方法是应当得到普遍运用的方法,而正是通过对它的运用,我们才达成了对我们所研究的材料的正确的理解。据此,维柯便对格劳秀斯、塞尔敦和普芬道夫三个人的法律体系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批评:
部落自然法学说的三大领袖〔格劳秀斯、塞尔敦和普芬道夫〕对上述六个命题都毫无所知,这一事实导致他们三人在建立他们的体系之中都一致犯了错误。因为他们相信完满形式的自然公正已被诸异教民族在他们的开端处就已经理解;他们不曾反思,在任何一个民族中还要经过两千年左右哲学家们才出现;……(329)(54)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 of the New Science”,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pp.94-95.
这样,人的社会性以及由这一社会性所应当建立起来的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便应当看成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从而,自然法现在不再可能是自然的,而是历史的了。这就是维柯“新科学”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在将近代自然法的研究置于一个历史视野内,维柯以历史理性取代了自然理性,赋予了启蒙以历史的维面,而这当然是启蒙思想的深化与发展。
-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从疑难出发:《形而上学》B卷的辩证法阐明
- 唯识学与现象学的六个理论分野
- 《墨子·经上》原经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