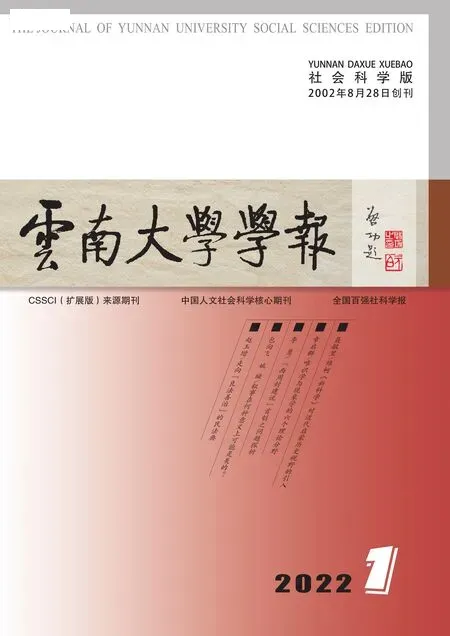从疑难出发:《形而上学》B卷的辩证法阐明
吴亚女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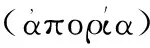
本文不赞同将疑难法和辩证法在根本上区分开的做法,这不仅与亚里士多德的文本相悖,而且会导致更大的解释困难,即考察疑难如何能够带来疑难的解决。在本文看来,传统解释的问题不在于将疑难法和辩证法关联起来,而在于未经仔细审查就匆忙地从B卷转移到《论题篇》,并且基于一种错误的辩证法概念来解释B卷,质疑传统解释的研究者与其说是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不如说是揭露了我们在B卷的疑难法和《论题篇》的辩证法关系问题上的理解欠缺。
在本文看来,疑难法和辩证法的关联远比之前观点所认为的要紧密得多。本文将从以下方面澄清B卷方法论的辩证法内涵:首先,疑难是辩证法所运用于之上的问题的定义核心,从疑难出发的做法所要求的正是辩证法的运用。其次,亚里士多德在B卷对疑难的提出、展开和解决给出了准规则说明,它们与辩证法的运用规则一致。由此,我们将阐明《形而上学》B卷的方法论所具有的辩证法特征,从而为确定两者之间的同一性提供有利的依据与论证。
一、什么是疑难
在B1开头,亚里士多德用了较长的篇幅讨论疑难的来源以及必要性,然而并没有对疑难的含义做出任何说明。被明确提及的对于“疑难”的定义出现在《论题篇》145b3位置,疑难是“相反推理的相等”。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个定义是错误的,准确来说:
相反推理之间的相等似乎是产生疑难的东西,因为当我们思考问题的两个方面时,似乎就每一个人来说全部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自然会困惑于采用两个中的哪一个。(Top.145b18-20)
在这段关于疑难与相等的相反推理关系的描述中,疑难的基本含义是心理学层面的,具体来讲是由于存在两个相反的推理,其中每一个的说服力相当,从而使得心灵由于无法抉择产生困惑,思想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亚里士多德反对的是在疑难的定义上发生的因果倒置,他并不否定在次要意义上,“相反推理的相等”也可以被叫作疑难(Top.104b12-14),这一意义指向的是疑难的逻辑—方法论含义。当疑难在这一层面被使用时,意味着存在一些对立的观点、论证、论题等,我们要阐明疑难所包含的特定逻辑结构。(3)Rossi,G.Going through Aporiai:The Critical Use of Aristotle’s Dialectic, 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52), 2017.p.235; Rapp C.Aporia and dialectical method in Aristotle[C]//. The Aporetic Tradition in Ancient Philosoph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p.120-121.疑难还有第三种含义,即能够使人感到困惑的事物的状态,事物本身或者事物中的某些东西是疑难性的,这导致思想陷入进退两难状态。(4)Owens, J.The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Aristotelian Metaphysics: A Study in the Greek Background of Mediaeval Thought. Toronto: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1978. pp.214-217.
疑难存在着三个含义,基本含义是理智的不能行进状态,另外两个含义是导致困惑的特定逻辑结构以及能够导致思想不能前进的事物的状态。亚里士多德在B卷使用了疑难的这三种含义,马迪根统计了疑难在该卷出现的次数,并对它们在不同地方的用法进行了判定。根据他的分析,疑难一共出现了15次,其中三分之一的是使用了原初含义,其他地方则是分别使用或者混杂使用了后两种派生意义。(5)Aristotle Metaphysics Book B and Book K1-2, translated with a commentary by Arthur Madig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See:Introduction,p.xx.
人们自然会提问,这三个含义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显然,疑难的三个含义可以呈现为“疑难性的事物——疑难的逻辑结构——心灵的困惑”三层结构,不过只有某一类特殊的疑难才可能具有这样的结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疑难有不同的类型,经验科学中出现的多数疑难不涉及逻辑—方法论的内涵,哲学或逻辑的疑难的产生则与普遍信念相关,这些疑难能够展开相应的逻辑结构。(6)Owen,G.E.L.Tithenai ta phainomena[C]//. Aristotl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68.p.170-171.针对后一类疑难,我们也可以区分出表面的疑难和真正的疑难,前一种疑难源于理性的犯错,后一种疑难产生的原因在事物自身。亚里士多德在B卷处理的问题正是这一类,智慧以首要的本原和原因为研究对象,他这样描述智慧(者)的一个标准:
智慧者能够理解困难事物,甚至那些对人类而言并不容易理解的东西(因为感知觉,对所有人而言是共同的,因而是容易的,也不是智慧);……这些东西,比如最普遍者,或许对人来说最难理解,因为它们距离感觉最远。(Metaph.982a10; 982a24-26)
智慧的特殊性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首要的本原和原因,即永恒的不运动的分离的不可感的实体——不动的动者,它们距离感觉最远,但我们只能首先从感觉出发来认识首要的本原和原因,这样一来必然会受制于现象的多,即感知经验和共同信念的杂多,围绕着它们产生各种对立的意见以及论证,导致思想陷入无法前进的境地。对此,我们能采取的方法便是亚里士多德在很多地方提到的,从对我们可知的东西到对自然可知的东西的方法,这一方法有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呼——辩证法。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主张认识要从“对我们较为清楚的东西”,行进到“对自然较为可知的东西”(Phy.186a16-20),这个过程是逐渐远离感觉的过程,并且涉及了两种认识状态的转变,就我们而言的认识状态是感觉经验,就自然而言的认识状态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我们单单分析疑难的内涵和结构,就得到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即,B卷主张的疑难法与辩证法就基本特征来看极其相似。
二、疑难作为辩证问题的定义核心
在那些将B卷方法与辩证法严格区分开的学者中间,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辩证法是一种从普遍信念出发的论证方法,而B卷主张的是一种从疑难出发的方法。然而并非所有对立的普遍信念都能够导致疑难,而且即使其中一些导致了疑难,这些疑难也不能够被还原为普遍信念,因此基于疑难的方法和基于有声望的意见的方法是两种不同的方法。(7)珀利提认为,B卷大部分的疑难与之前思想家提出的观点所造成的困境相关,但是如果认为这些疑难出自于前人相互对立的意见,从而考察疑难的方法就是辩证法的变形,将面临两个问题:首先,B卷文本强调的是考察疑难能够使我们达至形而上学,而没有提及普遍意见。其次,如果要支持传统观点,那将面临一个文本上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明确表示有一些疑难的材料并不来自任何前人,它们被偶然地忽视了,而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发现它们的人,这表明其中有一些疑难具有非意见性的一面,cf.Politis,Aristotle and the Metaphysics,pp.75-77; Halper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参见Halper, One and Many in Aristotle’s Metaphysics:Books Alpha-Delta.,p.282.
针对这种观点,我们只需引用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对辩证法的界定就可以了,他是这样说的:
辩证法作为辩证论证的方法,来源于问答双方在会话沟通中的相互对抗。亚里士多德的界定包括:第一,从被接受的前提出发构建推论;第二,避免接受相反的推论。前一点是提问者的活动,目的是将被回答者接受的议题作为命题进行推理,得出一个从前提得来的或是荒谬或是矛盾的结论,并让回答者承认该结论。而后一点是回答者的活动,要避免接受提问者的论证以及与自己一开始所说的不一致的结论。由此可见,辩证法包含了两个部分,一部分针对提问者,是一种能让其拥有者从可利用的材料中为一个给定的结论构建出最有效的可能的论证的系统性技艺,另一部分针对回答者,通过指明错误的原因来揭露提问者的不正确的论证。
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更多的篇幅用于讨论就提问者层面而言的辩证的方法,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回答者在揭露提问者的错误论证之前,同样需要知道提问者是如何进行推理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所有从普遍信念出发的论证都属于辩证法的范围,或者是辩证法与疑难并无关联。相反地,提问者力图让回答者承认与自己所接受前提相悖的论证及结论,这就自然地使得回答者陷入疑难的境地,而解开疑难的方式是阐明提问者论证的错误之处,维护原有的主张。
这样,我们就明确了究竟什么是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尽管从普遍信念开始是一般起点,但可争论性才是辩证法的核心,这尤其体现在提问者和回答者双方的争论上,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意见和论证,这显然就是我们在上一部分谈到的疑难的逻辑—方法论含义。辩证法并不处理全部的或是那些并不构成疑难的普遍信念,而是处理那些足以构成辩证的问题的普遍信念。这些问题必须都满足一个限定条件:它们伴随着疑难。(8)Rapp C. Aporia and dialectical method in Aristotle.The Aporetic Tradition in Ancient Philosoph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35-136.
那么首先,应该规定什么是辩证的命题和什么是辩证的问题。因为不是所有命题或所有问题都被算作辩证的:因为没有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会将无人主张的东西作为命题,或者是把对每一个人或所有人都明白的东西作为问题。因为后者不包含疑难,而前者无人主张。(Top.104a2-8)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是在普遍信念的区分下对辩证的命题和辩证的问题进行说明。辩证的命题必须是某种普遍信念,而辩证的问题则要求包含疑难。如果亚里士多德对命题和问题不加区分的话,那么判定辩证的问题是否成立的标准同样应该是它们要作为普遍信念为某一群体所接受,然而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强调的是“疑难”。史密斯指出,辩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围绕着议题产生了争论,论辩双方的对抗导致了疑难的产生,从而也就确定了双方讨论的是辩证的问题。相比之下,辩证的命题并没有承担这样的功能,它只在确定另一方所接受的意见时才会作为问题出现。(9)Aristotle,Topics Books I and VIII: With Excerpts From Related Texts, translated with a commentary by Robin Smith,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p.92-93.可见,疑难界定了什么是辩证的问题,并将它与辩证的命题以及一般的问题区分开。
既然疑难构成了辩证的问题的核心,考虑到疑难存在多种含义,那么亚里士多德是在什么意义上认为疑难成为辩证的问题的内在要素呢?我们要预先指出,亚里士多德对于不同的辩证的问题的论述都包含了疑难的心理学含义,即心灵的困惑或思想上的不前进。但是,他对相互冲突的普遍信念以及相反推理的讨论指向了疑难的逻辑含义。关于辩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说的:
(辩证的问题)关于它们或者是人们对之没有意见,或者是多数人与贤哲的意见相反,或者是贤哲的意见与多数人相反,或者是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有相反的意见。(Top.104b3-5)
我们暂且将“人们对之没有意见的问题”搁置起来,仅仅依据后面三种情况就可以得出,如果关于某一问题存在着为不同的群体所接受的普遍信念的话,那么它就能成为辩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列举了三种可能的情况,但无论哪一种情况,其核心都是对立的普遍信念,也是论辩双方或多方的对抗。
亚里士多德对辩证的问题的界定让我们联想到了B1的表述。在那里,亚里士多德说要考察的疑难“包括某些人对此有不同认识的问题,以及除此之外碰巧被忽略的问题”(Metaph.995a26-27)。前一类问题显然是那些由于不同群体所接受的普遍信念之相互对抗而造成的疑难,而后一类“碰巧被忽略的问题”,如果有另一种表述的话,就是对于这些问题人们并不持有什么意见,这正是上文定义里提到的第一种情况。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意见的缺失,而不是由于它们不会被任何一个群体所接受,不存在相互的对立,从而也就不足以构成辩证的问题。一些学者强调,由于亚里士多德明确表示有一些疑难的材料不来自任何前人,它们偶然地被忽视了,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发现它们的人,可见疑难具有非意见性的一面,从而就与辩证法区分开了。然而,这些偶然被忽略了的问题是指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并不持有任何观点,而不是说如果有人提出意见,它们不会被任何一个群体接受,不存在相互的冲突,从而就不足以构成辩证的问题。辩证法家和哲学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不同,辩证法家的操练必须面对着回答者进行,两个人可以更好地展现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哲学家熟练地掌握这项技艺,不需要搭档就可以独自完成这项工作,即,亚里士多德在那些被忽略的问题上,可以同时提出两个甚至多个能够被接受的冲突的论题及论证,在思想中造成疑难。因此,珀利提等人通过强调那些被忽略的疑难的非意见性,从而主张疑难法与辩证法并不相同的做法显然不能成立。
三、解惑的一般规则说明
既然疑难构成了辩证的问题的定义核心,那么当亚里士多德主张要从疑难开始探究时,他面临的对象同时也是辩证法所要处理的问题,从疑难出发的方法可能就是辩证法。但仅仅阐明它们处理同一类对象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说明这两种方法就规则来讲也是一致的。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相关联的倾向:一种是认为B1只是一种概念分析,顶多就是对考察疑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说明,不能算作是规则;另一种是认为,即使B卷的疑难以某种标准形式呈现出来,但这与疑难的解决并无关联,并不构成某种解惑的一般方法。(10)Crubellier, M.&Laks,A., Aristotle:Metaphysics Beta——Symposium Aristotelicum,pp.11-13,pp.45-46.
针对第一种研究倾向,我们要指出,亚里士多德给出了准规则说明,他在B1用了3个比喻来为疑难辩护,这些辩护共同地表达了一个观点:疑难可以走向其对立面——前进。其中,第一个辩护是这么说的,
疑难所包含的否定表明了一种无法行进的困难状况,而前进则指向某种良好的状况,这两个对立的概念通过解惑而连接起来,从而疑难能够从自身中发展出摧毁自身的因素,前进不仅是某种良好状况,而且伴随着疑难的解决。前进和疑难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它们的实现正是通过解惑来实现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般性规则就是:从疑难经由解惑到前进的线性推进。
人们可能会觉得这条规则过于简单明白,但我们要看到,由于解惑是连接疑难的提出和解开两个环节的一系列过程,居间的位置决定了它既可能接近疑难,也可能接近前进,或者是处于较为中间的位置,因此它至少具有三种含义:1.接近于疑难的含义,包括一般性地提出疑难,以及给出疑难的逻辑构成;2.居间的含义,表示基于被提出的疑难以及逻辑构成,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讨论、分析和审查,其目的在于疑难的解决的整个过程;3.接近于前进的含义,表示疑难即将被解开。我们主要关注前两种含义,一旦我们弄清楚了疑难如何被提出以及如何得到考察,那么它的解决也就是自然的了。
对第二类研究者来说,亚里士多德用以处理诸疑难的标准程序可以分为三步:首先是呈现出一个确定的难题,这个难题由两个互相排斥的论题构成;其次,展开围绕着论题进行的两个或两组彼此冲突的论证;最后,避免对两个论题表示出支持或反对的立场,这时候心灵就处于困惑的状态。(11)Crubellier, M.&Laks A.,Aristotle:Metaphysics Beta——Symposium Aristotelicum,p.8.显然,尽管他们赞同B卷试图提出一种关于解惑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基本规则是提出疑难,尤其是将疑难的逻辑构成展示出来,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解惑1。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单纯地将疑难展现出来而不进行任何判断如何就能够导致疑难的解开?他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又必须承认疑难是能够被解开的,结果只能诉诸概念上的说明或者是哲学史背景了,或者是说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存在一个统一的规则说明。

罗西主张《论题篇》中辩证法训练包含两部分,其一是论证相反的论题,其二是对论证进行批判性分析。在她看来,仅仅是将导致疑难的相互冲突的论题及其论证呈现出来(即解惑1),并不足以带来疑难的解决,还需要对相反的论题的论证进行考察分析,以确定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甚至是确定每一个当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是解惑2可能承担的功能。不过,并不是全部第二类研究者都可能同意,在修正传统的对辩证法的解释基础上进一步研究B卷方法论和辩证法的关联。克吕贝里耶和拉克斯倾向于将B卷的方法和辩证法区分开,他们的核心依据是《论题篇》中辩证法所处理的问题由相反的论题构成,而B卷的疑难则表现为矛盾的论题,而这两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被区分开了的,并且他们还将处理这两种疑难的角色区分为调停者和审判员。(13)Crubellier&Laks,Aristotle:Metaphysics Beta——Symposium Aristotelicum,pp.9-12.基于这样的考虑,第二类研究者认为B卷的解惑与《论题篇》的解惑并不相同。
我们认为克吕贝里耶等人的区分并不成立。B卷的疑难只有部分疑难是以矛盾的形式呈现的(虽然占多数),而且这些疑难也不都是严格矛盾的,它们只有被限定在某一特定前提情况下才构成了矛盾的论题,还有一些疑难以相反的论题的形式表现。亚里士多德在其他文本中区分了相反和矛盾,但这一区分在B卷和《论题篇》并不是那么重要,毕竟亚里士多德如果在严格意义上使用疑难,即疑难由完全矛盾的论题构成,而双方都具有同样的理性说服力,那么疑难是不可能被解开的。更可能的情况是,亚里士多德使用某种矛盾的形式来表现疑难,但这只是为了强调疑难对思想造成的阻碍,而在具体的解惑过程中,亚里士多德需要分别考察问题的两方面以进行判定。
所以,解惑一般规则要求的是:当人们面对疑难时,他首先要做的是正确地将疑难提出来,然后对它们进行考察,一旦完成了这两项工作,那么使思想陷入绑缚的疑难将被解开。解惑1的主要功能是对疑难形成正确的理解,只有将构成疑难的诸论证清楚明白地展现出来,我们才能够知道思想所困惑的问题是什么。直接与疑难的解决相关的是解惑2,人们将按照一定的规则对提出的疑难进行讨论、分析和审查,使得思想摆脱疑难的束缚。关于解惑2,罗西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主张。她认为,在辩证法的哲学运用中,解惑的规则是对问题的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也就是对构成疑难的每个论证都进行研究以发现其中的正确和错误,而不是通过反驳一方以证明另一方的正确。(14)Rossi,Going through Aporiai: The Critical Use of Aristotle’s Dialectic,p.211.在我看来,这一规则也是B卷的解惑所要求的,从而可以不仅仅根据B卷的疑难形式,而且可以根据亚里士多德在其他文本当中的论述以说明解惑的具体规则是怎样的。
四、解惑的具体规则与辩证法的运用
严格意义上的疑难是没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解惑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由于亚里士多德所使用的疑难并不是缺乏行进的道路,而是所有的行进道路看起来都是可行的,从而要选择哪一个反而成了问题,或者是所有的道路实际上都不能够通往目标。当我们审视B卷的诸疑难时,我们会发现它们都对应着多个回答,这些回答之间对立,各自都作为一条道路,从而造成了疑难。(15)Aubenque P. Aristotle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Philosophy Today,6(2),1962,p.77.既然这些回答是相反而非矛盾的,那么就不能够在发现其中一些不可行之后,转而宣称其他的回答是正确的,而是应该对他们每一个都进行审查分析,判断每一个的正确和错误。
所以,解惑的另一条具体规则是:在疑难的逻辑结构展开前提下,在构成它们的诸多论题和论证之间往返穿梭,即,对各方进行分析、考察和评价。“法庭比喻”很好地表达了这一规则的内涵,“他必定处于更好的位置作判定,当他听了所有针锋相对的论证,就像法庭上的争辩双方一样”。(Metaph.995b1-3)亚里士多德将解惑的过程比作法庭审判,原告和被告分别进行陈词辩护,之后审判员各自依据对双方的辩护进行判断,遵从法律的规定公正地加以处理和裁决,这一过程与解惑的前两个含义相对应,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审判员所承担的职责,他必须对双方提出的证据和相应的辩护进行分析、考察和评价,以确定其中的正确和错误。
在B1中,亚里士多德更多地讨论到了解惑的一般规则,尤其侧重于强调其中将疑难的逻辑结构展开的内涵,这是因为“关于全部这些问题,不仅凭借真理而前进是困难的,就是很好地以言语来考察疑难也是不容易的”。(Metaph.996a16-18)鉴于此,本文同意许多学者强调的B卷在《形而上学》起到的是预备性的作用。但亚里士多德也提到了上述的具体规则,除了法庭审判的辩护表明了解惑2之外,他在第一个辩护中讨论解惑的必要性时,强调解惑能够带来思想的前进,而前进往往伴随着之前疑难的解决,他用“绑缚—解开”的意向来描述这一过程。根据我们对解惑结构的分析,他在这里不止是在讨论如何正确地提出疑难,更是强调了对疑难进行分析考察,后者的主要目的是疑难的解决。

辩证论证所包含的两种能力与解惑的两种能力是对应的,当运用辩证法对哲学问题进行解惑时,既要求将围绕着同一问题的对立的论题各自的论证展现出来,而每一个论证都是提问者所造成的反驳;也要求对对立的每一个论证的分析、考察和判断,如果回答者能够阐明提问者论证错误的根据,那么就不用被迫接受与自己主张矛盾的结论,当然也可能发现自己主张的论题存在的真与假。后一种能力更为关键,因为它直接指向疑难的消除,与之相应的回答者的地位就得到了提升,解决也作为一种要求更高的能力在辩证论证中得到训练。在这种训练当中,回答者不再是柏拉图对话中总是被揭露其无知的角色,而是与回答者处在势均力敌的状态,而且也不再起着消极性的对抗作用,要求拒斥提问者的论证和结论,相反地,提问者在进行批判性考察前需要接受提问者的论证,由于他的这种合作性倾向,对立的论题和论证才真正地在他心中造成了疑难,从而提问者和回答者的辩证论证活动就成为了联合探究,疑难的解开也就可能伴随着对问题的全新解释。
解惑1,即反驳的能力是预备性的、基础性的,这不意味着它是不重要的或可以忽略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
因此应当预先研究全部的困难。这不但是为了这些(原因),而且是因为不首先考察疑难而探究的人就像是不知道他们将往何处去的人一样,除此之外,因为他仍然不知道是否找到所探寻的东西;目的对他来说是不清楚的,而对于感到困惑的人来说是清楚的。(Metaph.995a34-b1)
只有将构成疑难的诸论证清楚明白地展现出来,我们才能够知道思想所困惑的问题是什么。因此,整个B卷的主体便是由15个相互关联的疑难构成,亚里士多德在B1概述了这些疑难,然后在2至6章中进一步地将每一个疑难的逻辑结构充分地展开,而B卷之后的其他卷在主题上与B卷有大量的重合,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大体上是对这些疑难的深入研究,这也就是解惑2,即解开能力的运用。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疑难2至4这三个问题在Γ卷1至3章得到了明确的回答,对公理的研究和对本原的研究属于同一门科学,存在一门研究全部实体的科学,这门科学与其他研究实体的部分的科学不同,并且这门科学除了研究实体,也研究实体的本质属性,亚里士多德如何得出这三个结论实际上是解惑2的具体操作的呈现。
综上,B卷的疑难法与《论题篇》的辩证法之间的关联远比现有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要密切得多。尽管B卷所表现出来的解惑的规则要求与传统的对辩证法的解释并不相同,但是我们并不能同意珀利提等人的观点,主张疑难法和辩证法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旦我们要重新确立这两种方法的关联,我们可以首先确定B卷核心概念“疑难”的多重含义,在此基础上确立这两种方法的对象的关联,疑难构成了辩证的问题的定义核心,并且阐明B卷所主张的解惑的两个规则与辩证法的两种角色和能力之间的一致性。但无论如何,重新将B卷的疑难式方法纳入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范围内,都有赖于对B卷文本的审查以及对《论题篇》的辩证法的双重角色和程序的澄清。本文认为,珀利提等研究者将同意这一结论,因为他同样意识到了B卷方法与传统的对辩证法的理解存在差异,B卷的解惑要求一种合作性的探究,接纳对方的论题和论证,并尝试从疑难当中获得生产性的结果;而辩证法更接近于争论性的论证,参与对话的双方是对抗性的非合作关系,只不过他的处理是将两者区分开,而我们则通过对它们进行了一次解惑而产生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主张。
-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维柯《新科学》对近代启蒙历史视野的引入
- 唯识学与现象学的六个理论分野
- 《墨子·经上》原经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