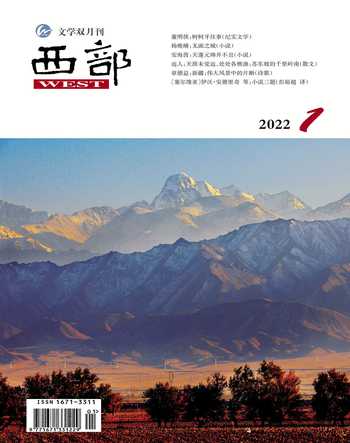双脑筑城记
杨枫
在那场实验开始前,老徐只是一名废柴俱乐部的普通新会员。
众所周知,任何优等大学都有所谓的“主旋律”:大一刷分,大二打比赛,大三混实验室,大四实习……整条道路犹如走钢丝,稍有不慎,便将坠入万丈深渊,浑浑噩噩度过残存的数年岁月,泯然众人矣。废柴俱乐部正是为此而生,以收容各路落难同胞,互帮互助为己任。
俱乐部的新人通常会再挣扎一阵子,但是人生啊,一旦跌倒,再爬起来可没那么容易。大多数人最后都还是选择与自己和解,躺平一阵,再去找别的出路。因此,当老徐在迎新会上大喊“我和你们这帮人不一样”时,我们只当他是开玩笑,大家该吃吃,该玩玩,甚至还要他来试试《幻世-3》T大特供DLC,接进副脑,在虚拟世界当几天学神,快乐快乐,气得他跑到洗手间哭天抹泪,又引来一阵哄笑。
可是后来,老徐的成绩竟然真的涨了。
这要多亏他在网络中心工作的朋友老李。
彼时,拜新问世的副脑所赐,校园网的网速一直很烂。
副脑是装在颅内的流体计算机,与大脑双向连通,构成完备的脑机系统。用通俗但不准确的话讲,就是我们可以用操作旧式电脑的方式来对大脑动手动脚了。
副脑上装载了不少炫酷功能,从猝死预测机到数字货币投资专家,应有尽有。在大学里,使用频率最高的当然是学习机制:想学什么,只要从云端下载资料到副脑,让信息处理单元反复刺激大脑的记忆区,形成长期记忆即可。水平高的学生还会把经验和灵感记录成文档,再次输入副脑,从而形成更有效的自反馈回路。
大学生活因此天翻地覆。渴求知识的莘莘学子开始向数据中心发动一轮又一轮的DDoS攻击,引得网管们叫苦不迭。老李那会儿刚刚加入网络中心,急需做出业绩,压力自然更大。而在西西弗斯之路上一去不返的老徐也刚刚绝望地发现:他已经穷尽了所有手段,却仍然无力回天。
一天,在夜宵食堂,二人历史性地会面了。老李端着餐盘,一屁股坐到老徐面前。二人先照例就日常生活大吐苦水。等到氛围恰到好处,老徐的怨念即将飞跃巅峰,老李便顺势问他,要不要来参加一个试验。
“我打算搭一个小型分布式网络。”他兴冲冲地说,“我写了一个模块,能让副脑开启无线热点。参加实验的人互开WIFI,组成P2P网络,把资料切块,随机存储到彼此的副脑里。这样一来,数据就分散到每个人身上了,读写都不用走主干网和数据中心,节省下来的带宽就可以分配给其他服务,提升校园生活质量。”
老徐听得一头雾水,却不愿在友人面前露怯。
“听着不错,可这跟我有啥关系?”他转而抛出最关键的问题。
“嘘——后面这事你可別外传。我给你写了个后门,能读取加密数据块,自动往记忆区写。也就是说,不管你醒着睡着,只要有数据过你这儿,你都会一直在学习。这可能会让你觉得累,但我保证,绝对不伤身体,而且大概率能迅速提升成绩。”
听到这里,老徐立刻精神了。走投无路的他几乎立刻便接受了友人的邀请。后来的你问我答不过是走走形式。
“为什么找我?”
“随机抽样。”
“不可能,肯定有什么原因吧。”
“其实还有一个隐含的实验,是我的私人课题。”
“什么实验?”
“说细节你也不懂。我就是想看看在这样的超载学习环境里,你这类学生能提升到什么境界。也不用你额外做什么,让我观察记录你的成绩和学习过程就好。”
“哼,瞧不起我是吧?等着瞧。”
“行,那你提交组网申请,回头我给你单独装环境。”
事情就这样成了。首批受试者来自各个学院,平均成绩为中等偏上,凑齐了所有学科,但是后门程序唯老徐独占。受试者组成的副脑集群采用RAID-486策略存储数据切片,会保证所有的文件块每周在老徐这里轮换一轮。
实验启动后,信息洪流日夜冲洗着老徐的大脑,把数倍于常态的资料注入海马体。每天醒来,老徐都会去做老李准备的调查问卷。问卷上的问题五花八门,严重超纲,涵盖从室女座星云到夸克世界的方方面面。可他却渐渐喜欢起这些题目,因为每次做题,他都会发现自己学会了更多的东西,诸如一套数学理论,一组外科手术总结,或是一种新提出的计算机算法……穿插其间的优等生私藏札记则如同钢筋梁架间的熔焊,融合知识和知识,构造出五花八门的精巧建筑。
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老徐的秘密。当他在俱乐部的派对上表演手工求解高维旅行商问题,使出五花八门的奇技淫巧时,我们只是觉得不可思议。这家伙大概只是一时水土不服,才会沦落到此处,真正属于他的,应该是特等奖学金联盟吧。
不出所料,期末考试,老徐拿了大满贯,顺理成章地拿到了特学联的入场券。接受校报采访时,他再次引述了那句关于成功、天赋和汗水的破烂名言。他的黑眼圈则成了名言的确凿证据,一层一层挂在眼袋周边。
他感谢他的朋友老李(但巧妙回避了真相),表达了对尖子生的崇拜,却唯独没有提到俱乐部。尽管当他家中遭遇飞来横祸,经济包袱死死咬住他时,是我们拿倒卖VR游戏外挂的钱帮他摆脱了困境。
那是他入学以来最大的危机:他家单亲,农村户口,入学第一年,母亲出了车祸。拿到我们的援助款时,他没有感谢我们,只是吞咽着眼泪,不停地说自己是个废物。我们倒也没什么怨言,反而特理解他。他讨厌自己,迫切想要翻身。多积极啊。为了家人而力争上游,俱乐部的成员们又何尝不想如此呢?如果有可能,谁又会真的接受混吃等死的状态呢?
大三开学,分布式网络实验宣告成功。系统正式上线,老李当选模范员工。摆脱了重压的数据中心也终于能让人舒心选课了。
选课结束后,老徐来办退会。我们发现他的黑眼圈更重了,让他注意身体。
“没事,习惯了。”他摆摆手,办好手续,摇摇晃晃地走了。
那时我们仍然对他的颅腔一无所知,遑论他所承担的重负。在漫天飞舞的八卦中,我们只知道他要去综合科学研究院的王牌教授手下实习。选实验室那阵子,邀请雪片般飞进他的邮箱。而按照社员的说法……妈的,他挑选offer的样子,活像翻阅情书的校花校草。
他如愿以偿地进了最好的实验室,开始做课题。
接着,他又挨骂了。
更好的环境自然要求更高。后门程序只给了他敲门砖,而且出于安全考虑,大幅限制了读写模组的吞吐量,还过滤掉了很多冗杂数据,从而限制了他的飞升高度。
他去找老李解除限制。老李打量着他的倦容,摇了摇头,没有同意,送了他两张温泉酒店的券,要他去放松放松,还跟他说,他已经今非昔比,不需要后门也能应付得来。实验还是要慢慢来,急不得,急不得。
面对友人的关怀,老徐无言以对,但教授几近人格否定的责备却同样刻骨铭心。于是,利用过去攒下的学识,他完成了以往做不到的事:他从机器码层面破解了后门程序,重写了一版,放开了诸多限制,还新增了完善的交互界面,以便微调。
深夜,他启动新版后门,先沿用旧配置,然后慢慢提升强度。过了一会,后脑疼了起来,像是在被针扎。他这才缓慢降低洗脑规模,待刺痛钝化,才去休息。他自知背叛了友人,但第二天,当他完美地回答了教授的问题,还抛出了全新的扎实假设,令教授刮目相看时,愧疚感便随之烟消云散了。
他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Cell》,第二篇,NIPS,接着是《Science》《柳叶刀》。有社论宣称百科全书学派即将迎来文艺复兴,附录是他和各界名流的合影、合作者的称赞和报菜名般的学术成果,却无一字提到他是如何忍耐头痛,不断接受日益升级的折磨的。
他们也没提到当老李猜到了原委,去找他对峙时的场面。
“停手吧。不然我只能公开这一切了。”
“公开吧,但是要记住,是你把我卷进来的。而且不要忘了后来那些我帮你做,挂你的名,帮你刷奖学金的项目。”
“我是在关心你!”
“我知道。所以,就当无事发生,好吗?”
老李张嘴,闭嘴,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出局了。老徐接手了他拖拖拉拉的实验,继续挑战自我,直到程序的资源消耗抵达硬件极限。
从此,二人的友谊便只剩下室友关系了。
有老徐这种超人在,校园学术圈的氛围势必会发生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视他为领路人,嗷嗷待哺,静候他输出新的灵感,供他们延拓细枝末节,赚取履历上的点数。
半年后,就连我也绕不开这座大山了。我那时正在带领俱乐部给海洋塑料清污项目设计微机器人集群,其中,预测洋流运动的模型用到了老徐设计的算子。算子很难懂,我写邮件问他,他没回,我又换了几种渠道,去信也都石沉大海。
后来有一天,凌晨两点,我去社团活动室通宵,发现他独自一人蜷在沙发上。我没撤銷他的门禁,所以他能进来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会来。我装作若无其事,坐到他对面,却发现他双目无神,正在哭泣。
“怎么了?”
“没事。”
“你看着可不像没事。”
我盯着他,递过纸巾。他避过我的目光,两眼血丝密布。
片刻寂静,然后他问我怎么看现在的学术环境。
“为什么问这个?”
他伸出两根手指,在看不见的系统设置面板上开启了应用共享。一瞬间,璀璨的星群点燃了整个房间。他坐在星河中央,告诉我,每一颗星星代表一封求助邮件。
群星间还交织着猩红色的河流,它们是向他的大脑发起的攻击记录。
“成天到晚应付这些东西,我快不行了。”
“不回不就好了?大不了弄几个小号,或者写一套代理人系统帮你处理呗。”
他摇摇头,抽出吸管,搅动着手边的星星,说这些就是经纪人系统的分析结果。它们虽然保护他,却也剥夺了他的生活,甚至像家长一样指挥着他的一举一动。
“所以,现在你出名了,但你还是不开心。”
他没说话。他沉默了很久。
“我觉得我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过了一会,他又说。
“一开始家里穷,我以为是要回报父母,可是财富自由了,反倒没感觉了。”
“你的量化投资模型赚了?”
“赚翻了,下个月要跟塞拉证券谈收购合同。”他点点头,“说回来,当初我还觉得追求的是成绩、排名、点数,但这些……感觉就像毒品,越升越没成就感,就要去挑战更大的问题。”
“那就继续做更大的问题,继续深挖。做学术本来就要掀开世界的面纱,探索本质……”说到这,我反倒觉得我像个班门弄斧的小丑。我甚至意识到,在特学联的迎新面试上,我也跟他说过类似的话。
“探索本质……也对吧,我也是这么想的。”
接着,他跟我说,他正在尝试解决千禧年难题。
“那你之前的研究呢?”我提起要问他的算子。来之前我已经大致弄懂了,还找到了改进的空间。“我隐约觉得它能解决材料力学领域的几个关键问题,还能开辟几个新的研究方向。”
“送你了。”
我愣住了,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
“哦,所以你并不在乎探索与发现,你只是把科研当成打怪升级。”
“可能吧。”他垂下头,避让开我的叱问。
“我知道这可能是死胡同,也试过去改变生活,去旅行,去运动,去种些花花草草,摆弄些瓶瓶罐罐,认识一些人,出去喝酒唱歌看电影逛街,或者上云端干同样的事情,甚至还申请过私人云空间,在里面创造世界。但你能想象那种沉闷吗?太简单了,做什么都太简单了。人们也都头脑简单,说出来的话全是错误和偏见,烦。”
“所以,最后我发现,还是得回到这里。”他指了指半空中浮动的问题描述。
“那你哭什么?”
“因为我解了好久也解不出来,正好你来了,就跟你发发牢骚。”
“……祝你好运。”我想走了。简直是自取其辱。我不知道老徐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此时,有关水论文之风的批判尚未成为主潮,我依旧无从知晓它对老徐的智慧造成的巨大打击,无从知晓他之所以难以破关,正是因为作为他灵感源泉的T大科研社群正在成群结队地收受他的施舍,沦为他的附庸,而非他的助力。
也许他想坦白一切,却举棋不定?又或者他在转弯抹角中完成了自我说服?无论如何,这些后知后觉的反省都已经于事无补。那时,我只是熄了火,疲惫地站起身,打消了通宵达旦的念头。而他也只是抿着嘴唇,低下头,展开一张张虚拟草纸,继续他的闯关大业。
我走出俱乐部,群星谦逊地为我让开道路。星光在虚构的气流下翻滚,飞腾,绕着老徐旋转,犹如笼罩周身的圣光。
可我只觉得他可悲。和那些黯然退场的俱乐部会员相比,他只不过走得更远些罢了。
老徐的真正对手出现在2036年的首届双星交叉科学技术大会上。
收到邀请函时,他刚刚通关了PhD,正要从地火行星际飞船发动机的设计工作中脱身,留下海量的重要成果。同期,他还遗弃了很多项目,看得出来,他累了。
新生的盛会邀请他去当特邀嘉宾。这与其说是他的荣誉,倒不如说是组委会的。唯一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开幕式上,还将有另一人与他一道登场。
一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新手,有趣。
他漫不经心地翻阅会议议程,从开幕式往后顺着看,第一眼就看到了新手的论文题目。
《黎曼猜想的两种证明方法》
朴实无华,但掷地有声。他头皮发麻,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这不是他正在攻略的题目么?
身份反转,新手骤变强敌。论文题目的后面跟着“已经同行评议确认”的粗体注记,次序紧跟在开幕式之后,显然意在为大会造势。他唤醒信息流模组。果然,关于此事的话题热度正在飙升。而更令他感到眩晕的,是他的对手虽然执意要在开幕前保守秘密,却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一件事:他的研究受到了老徐的启发,他为此感谢他。
收到致谢,老徐只感到头皮发麻。有人在他撑起的科学天空上戳了个洞,飞出去了。为什么自己没有想到解法呢?是什么启发了面前这位比他还要年轻的新手?他一遍又一遍地扫描着自己的心智仓库,变换着检索算法,一直到视野中弹出颅温警告,依然一无所获。
他写邮件给那位年轻学者,言辞尽可能礼貌。对方回复得很快,提到了一个简单的定理,出自一篇早被他抛到脑后的论文的中间步骤。他得到了终点和一个起点,中间的路径却依然云雾缭绕。含糊其词的回应令他勃然大怒,他开始盘算自己的未来,想要从计划中挤压出足以与对方抗衡的新发现、新创造。
他不断逼问自己,逼问后门程序。空闲资源很快就不够了。于是,他开始手动干预资源分配。
脑壳之下的数字生态系统中,供他娱乐的程序率先死去,接着是侍奉他日常起居的辅助组件,最后是用于人格修补(用来弥补洗脑造成的损害)的那些。他小心翼翼地拆解自己,将其献祭给大脑深处的学术熔炉,炼不出宝藏,也要硬炼。带宽不够用了,就切断所有无关链路,中断与外界的联系;存储不够用了,就删除应用、音视频和日常照片……可他仍然一无所获——或者说,面对一道千禧年难题的解法,那些收获全都一文不值。
大会正在按部就班向他走来。他先是诅咒自己,接着诅咒T大的无能,诅咒全校师生的笨拙和懒惰,最后诅咒后门程序,气急败坏地做了一个假设:在来自数据中心的知识之外,数十万T大人一定在各自的私人空间中存放了更多的智慧,而这些要么是被他们偷偷藏起来了,要么就是被过滤器滤掉了。
对此,他做了两手准备。他先带头发起了一场跨校运动,鼓励大家共享知识片段,在开源协议的约束下互帮互助,以改良学术氛围。可是这一活动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收获什么启示,反而让他又倒贴了不少思想结晶。到了这时,时间也不够了。于是,他采取了最后的手段:取消一切过滤条件,让副脑彻底暴露在数據流中,全盘通吃。
限制解除的瞬间,他晕了过去。
数据块在看不见的空间里飞来飞去,他将一切尽收脑中。这之中不仅包括他梦寐以求的知识大厦,还包括办公材料和社会新闻,包括虚拟树洞里写给老师的问候,情人间的分手信和海誓山盟,甚至包括废柴俱乐部采购游戏的账单和收藏小电影的番号……
山呼海啸的信息垃圾汹涌而来。他的大脑超载了,但程序却没有终止,仍在持续不断地灌注资料。
琐碎的信息构成了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进而参与人格的塑造。在固化了太多碎片以后,老徐的大脑逐渐变成了人格的游乐场,你的人格,我的人格,他的人格,她的人格……T大全体师生的隐私数据汇成了人格的海洋,造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精神分裂。老徐的意识被困在汹涌的波涛中,在外人看不见的汪洋里,发出A的声音,挥舞着B的双手,踢蹬着C的腿脚,水中倒映出D的脸庞,而这张脸,也是由成千上万的大头照拼成的。
一切都结束了。等到老李回寝室,发现老徐时,他正躺在地上抽搐,口吐白沫,说着十余种语言串联而成的胡话。
老李慌忙给医院打电话,接着眨眨眼睛,关闭了给自己用的后门程序副本。结束进程,打开控制面板,卸载程序,一气呵成,毫不犹豫。
卸载完程序,他又去卸老徐的。可老徐却渐渐安静了下来,胡言乱语也慢慢变成了低沉的嘟囔。
老李凑近去听,发现老徐说中文了。话语中,八卦似乎越来越少,科学规律则越来越多。
接着,老徐睁开眼睛,环顾四周,伸手擦净嘴角的白沫,然后坐起身。
“副脑的容量不够开新程序了,共享你的白板过来。”
老李照做了。二人的视野中随之浮现出一张悬空画布。
老徐的眼睛转了转,在虚拟画布上写下一个希腊字母。他开始移动头部,一边转头,眼珠一边滚来滚去,写下更多的公式,更多的证明。
“老徐,你没事吧?”
“老徐,谁是老徐?”
他面无表情,继续摇头晃脑。画布的左上角有一行小字:“关于P≠NP的证明”。
相关调查启动后,俱乐部来了一位意料之外的客人,带了一份意料之外的礼物。
“这个给你们。”活动室里,老李把一张存储卡放在茶几上,放在棋牌和骰子中间。我们递给他一听冰镇可乐,他扯下拉环,喝了一口,看着易拉罐里的泡沫,若有所思。
他又猛灌了几口,才开始讲述真相,揭露老徐头颅中的秘密。我们看完了老徐被送医前提交的数学证明,又回顾了近日的报道。最后,老李告诉我们:老徐忘记了关于自己的一切。他的脑内似乎形成了一种自卫机制,清除了所有的冗余信息,只保留对他最重要的部分,让他能够继续活着,继续钻研知识。
昔日的老徐,如今成了T大的化身。他得到了最好的磁盘清理程序。只不过,他自己的人格,也被划进了垃圾堆里。
“人脑是最高明的骗子,你永远想不到为了自保,它会做出什么事。”
最后,老李擦擦额头上的汗,感慨道。
“说真的,虽然我知道他渴求知识,但一直理解不了为什么他要那么偏执。上大学之前他就这样,最爱给人讲题,给全班所有人讲,还开直播。有人会了他不会的,他就气得不行……可能是家教如此吧,独生子,从小到大都被期待,就容易这样。”说到这里,他叹了口气,“没他,我上不了T大。找他测试,也是看他那样,想反过来做点好事。没想到弄成这样。”
我们依然什么都没说。
靠着后台日志,老李得到了老徐的完整学习路径,还过滤了其中的污染。把路径图谱导入副脑,按图索骥,将知识输入大脑,就可以迅速领悟人类知识的全景,而不必遭受信息过载之苦。
“这个应该对你们有用。”老李拾起芯片,示意我们谁试一试。
有些人看看我,我依然没有表示,于是也没人应他。他自己也觉得讨了个没趣,又闲聊了几句,便告辞了。
事后,在法庭上,他想借芯片来争取宽大处理,失败了。芯片确实帮助到了一些会员,甚至还帮我重新规划了俱乐部的培训计划。但一码事归一码事。
老徐则全程沉默,直到法官宣读审判结果。法警带他离庭时,面对山呼海啸的闪光灯和质问,他说:“歌德-巴赫猜想解决了。”
窃听校园网的计划解体了,吸食副脑集群的老大哥也消失了。
二人都离开了学校。老李坐了牢,老徐进了精神病院。没过多久,一家赫赫有名的科研机构保释、聘用了他们,在机构内组建起强化版的脑联网,把后门程序写进了所有科研人员的脑袋里。机构的学术影响力从此扶摇直上九万里,四百余名研究员,个个堪比门萨俱乐部的秘密大师。
或許,对他们来说,只要能攀登科学高峰,其他怎么样都无所谓吧。
老徐自己自然是无所谓的。只要应激性过滤机制不被打破,他便能一直钻研学术,代价不过是人格缺失。这是他的追求,他成功了。
很难说他留下的足迹就是最好的——他后来独立解出了那位新晋天才挑战的问题,但手法笨拙乏味。而我也从图谱中找到了很多迂回、冗余和重复。
但他至少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老李离开之后,我拿起卡片。
“主席?”
“你们谁想试试,就拿去吧。”我说,“东西挺贵重的。记得备份,别弄丢、弄坏了。”
“主席呢?”
我摇摇头。当社长要保证成绩在年级前10%,我也很享受亲自探索未知的乐趣。像这样坐享其成,我不甘心。
但我知道不该歧视知识。我知道有人需要它,还有很多人和老徐一样。
而我不想他们变得和老徐一样。
于是我拿起卡片,和几位干事一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各自存了档,最后交给刚刚问我主意的社员。
“拿去用吧。”
他点点头,我也点点头。
俱乐部又热闹起来。我继续埋头备课,同时盘算着论文怎么写,晚饭吃什么,该把女朋友的名字赐给哪颗星星,作为她的生日礼物。房间里,全人类的智慧沉睡在十五克的芯片里,从一个人手中传递到另一个人手中,沾了些微汗水,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