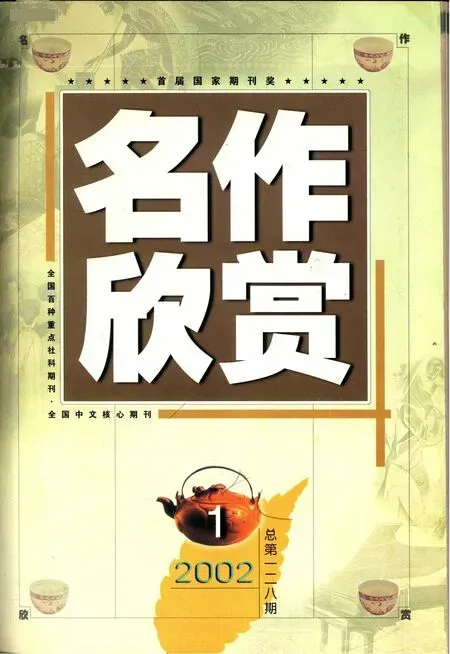深入人心的歪理邪说
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十三首,是我国古代组诗中的名作。明人黄文焕说:“陶诗凡数首相连者,章法必深于布置。”(《陶诗析义》卷三)或许出于同样的感悟,对于这首诗的内在思想脉络,景蜀慧在《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政治主题疏释》一文中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文章认为,这组诗的思想主题与魏晋易代的历史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其对第十一首“巨猾肆威暴”的论析最令人信服。但通常的古典诗歌选本以及文学史的相关论述,大都漠视组诗中各诗之间的思想关联,而主要关注第一首“孟夏草木长”和第十首“精卫衔微木”,事实上,这两首诗也确系陶渊明笔下的名篇。对第一首诗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而对第十首诗则不然。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卷四载此诗: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夭无千岁,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一作何复)悔。徒设(一作役,又作使)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所谓宋刻递修本,实际是北宋僧人释思悦的汇校本,对于“化去”“徒设”二句的异文,思悦根据其所见陶集各本已经做了标注。思悦是宋代苏州虎丘寺的一位僧人,曾经在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大力校勘陶集。也就是说,在思悦之时,这首诗的文本只有以上三个异文。诗中“形夭无千岁”一句,现存宋元陶集各本也完全相同,如宋绍熙三年(1192)曾集刻本《陶渊明诗》(诗一卷杂文一卷)、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补注一卷)、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甚至包括宋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卷二)和所谓苏体大字本陶集,这句诗都没有异文。
南宋诗人曾纮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曾纮字伯容,号临汉居士,南丰(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人。父曾阜,子曾思。曾纮属于江西诗派的后学,博学善属文,有《临汉居士集》七卷、《江西续宗派诗集》二卷(见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五、二百四十九《经籍考》,元脱脱《宋史》卷二百九《艺文志》以及明李贤《明一统志》卷六十)。明廖道南《楚纪》卷四十七《阐幽外纪》前篇载:
曾纮,字伯容,其先南丰人。父阜,字子山,徙家襄阳。纮负高才,善吟咏。……子思字显道,亦有诗名。(明嘉靖二十五年何城李桂刻本)
但曾纮的诗名,在后世已经不显,真正给他带来一点声誉的是其对陶渊明《读〈山海经〉》其十“形夭无千岁”一句的解说,这就是所谓“曾纮说”:
余尝评陶公诗:语造平淡,而寓意深远,外若枯槁,中实敷腴,真诗人之冠冕也。平生酷爱此作,每以世无善本为恨。顷因阅读《山海经诗》,其间一篇云:“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且疑上下文义不甚相贯,遂取《山海经》参校,经中有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下句“猛志固常在”意旨相应。五字皆讹,盖字画相近,无足怪者。间以语友人岑穰彦休、晁咏之之道,二公抚掌惊叹,亟取所藏本是正之。因思宋宣献言“校书如拂几上尘,旋拂旋生”,岂欺我哉!亲友范元熙寄示义阳太守公所开陶集,想见好古博雅之意,辄书以遗之。宣和六年七月中元临汉曾纮书(刊)。
末句“书刊”二字,令人费解,而曾集刻本此句无“刊”字,当系明人为了伪装成北宋本陶集随意添补的,其墨色模糊,笔画生硬,亦足以证明此点。此文作于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比思悦校勘陶集的时间晚了半个世纪。此文今见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之附录(《宋本陶渊明集二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第236—237页)。古代刊刻的十卷本《陶渊明集》都有这篇“曾纮说”,有的作为附录见于陶集之末,如影宋抄本《陶渊明集》十卷、明嘉靖剑泉山人刊本《陶渊明文集》十卷,有的见于《读〈山海经〉》其十三的诗后,如曾集刻本《陶渊明诗》,有的见于《读〈山海经〉》其十的诗后,如元刊本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参见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六十七集部,清光绪万卷楼藏本)。
尽管“曾纮说”从古到今都存在很多争议,但现在已经被多数读者接受,“刑天舞干戚”几乎已经成家喻户晓的陶诗名句。如景蜀慧指出:
至于刑天之神话,见于《海外西经》:“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据袁珂考证,刑天为炎帝之臣,其神话乃皇帝与炎帝斗争神话的一部分。渊明诗中用此典,映射现实之处自是不言而喻。就当日史实而言,有一事似可注意:刘裕亲征司马休之前,曾遣使送密信招降征西府录事参军韩延之,信中称其西征止罪及司马父子,余者一无所问,并有“吾虚怀期物,自有由来,今在近路,是诸贤济身之日,若大军相临,交锋接刃,兰艾杂揉,或恐不分”等语,是威胁亦是诱劝其悔之及早。而延之覆信慨然称:“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耳。”其言正是“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之意。信中所称臧洪,是汉末著名节烈之士,因为府主张超复仇而被袁绍所执,面对袁绍之逼诱,义不肯降,指斥袁氏“四世五公,可谓受恩,今王室衰弱,无辅翼之意,欲因际会,多杀忠良以立奸威,惜洪力弱,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何为服乎”。因而被杀,其所言所行,亦正是“形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也。从这些情况看,渊明在此诗中用作为炎帝之臣的刑天虽断手犹不隳其猛志的故事,亦极可能与韩延之诸人忠于司马,不臣刘氏之事迹有关。
其对这首诗的阐释就是建立在“曾纮說”的基础上的,类似的情况在学术界非常普遍,所以现当代的古典诗歌选本和文学史也大都遵从这一陶诗文本。
实际上,这种情况可能与朱熹等名人对此说的肯定有密切关系。《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
或问:“形夭无千岁”,改作“形天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经》分明如此说,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芗林家藏邵康节亲写陶诗一册,乃作“形夭无千岁”,周丞相遂跋尾,以康节手书为据,以
为后人妄改也。向家子弟携来求跋,某细看,亦不是康节亲笔,疑熙丰以后人写,盖赝本也。盖康节之死在熙宁二、三年间,而诗中避畜讳,则当是熙宁以后书,然笔画嫩弱,非老人笔也。又不欲破其前说,遂还之。
周丞相是指宋丞相、益国公周必大,宋朝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邵雍(1011—1077),字尧夫,谥号康节,宋朝著名的隐士和诗人。朱熹通过对邵雍手书陶渊明《读山海经》诗笔迹的鉴定,肯定了“曾纮说”。而这恰好是周必大否定“曾纮说”的一個重要旁证。按周氏《文忠集》卷十八《跋向氏邵康节手写陶靖节诗》云:
康节先生蕴先天经世之学,顾独手抄靖节诗集,是岂专取词章哉!盖慕其知道也。宣和末,临汉曾纮谓旧本《读山海经》诗“刑夭无千岁”,当作“刑夭舞干戚”,某初喜其援证甚明,已而再味前篇专咏夸父事,则次篇亦当专咏精卫,不应旁及他兽。今观康节只从旧本,则纮言似未可凭矣。(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周紫芝《竹坡诗话》曰:
有作陶渊明诗跋尾者,言渊明《读山海经》诗有“形夭无千岁,猛志固有在”之句,竟莫晓其意。后读《山海经》云:“刑天,兽名也,好衔干戚而舞。”乃知五字皆错。“形夭”,乃是“刑天”,“无千岁”乃是“舞干戚”耳。如此乃与下句相协。传书误缪如此,不可不察也。
此外,宋洪迈《容斋随笔》卷第二“抄传文书之误”条、元吴师道《礼部集》卷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及清杭世骏《订讹类编》卷三“陶诗刑天舞干戚”条(民国嘉业堂丛书本),均肯定了“曾纮说”。可见肯定派的阵容是比较强大的。
但是,“曾纮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不仅是一种荒谬的学术判断,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歪理邪说。
首先,“余尝评陶公诗”云云表达的观点,并非曾氏之首创,苏东坡曾说:
吾于诗人无所好,独好渊明诗。渊明作诗不多,然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沈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东坡题跋·评韩柳诗》)
显而易见,曾纮的对陶渊明的评论是对苏东坡观点的剽窃,由此可见其为人之无耻。至于“平生酷爱此作”的“此作”,也指代不清,令人疑惑,但与剽窃东坡相比,这已经不算什么大毛病了。
此外,曾氏引《山海经》赘述其大意说“刑天,兽名也”,清张定鋆《三余杂志》卷八“刑天”条:
今《山海经》原文:刑夭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原注云:“是为无首之氏。”据此则人类非兽类矣。曾以为兽名,不知何所据也。(清道光刻本)
换言之,曾氏毫无根据地把人说成了兽,其学识之低下可见一斑。曾氏又说“口中好衔干戚而舞”,《山海经》原文是“操干戚以舞”,为了配合其““刑天兽名”说,他随意把“操”字改成了“衔”字,又在前边添加了一个“好”字。《山海经》第七《海外西经》:
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野兽如何能够与天帝争神?清沈涛《交翠轩笔记》卷三:
《山海经》“刑天”,本当作“形夭”,天训为残,即《淮南·坠形》所谓“形残之尸”,古“刑”“形”二字,率相通假,见于汉碑者不一而足。“天”与“夭”乃字形相近而误。《诗》“天夭是㭬”,《后汉书·蔡邕传》作“夭夭是加”可证。细绎诗义,谓形已残而犹舞干戚,故曰猛志固常在也。(清道光刻本)
“夭夭是加”,见蔡邕《释诲》;“天夭是㭬”,见《诗经·正月》。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四十二:
右《等慈寺碑》,今在汜水县,太宗破窦建德之所。其文有云:“愍疏属之罪。方滞迷涂;念刑夭之魂,久沦长夜。”……今碑文作“夭”字,疑唐以前《山经》本作“刑夭”,后人转写讹为“天”耳。“形”与“刑”,古人亦通用,然则渊明“形夭”二字非误矣。(清嘉庆十年刻同治钱宝传等补修本)
清钱大昕云:
今碑文却作“夭”字,疑唐以前《山经》本作“刑夭”,后人转写讹为“天”耳。“形”与“刑”古人亦通用。然则渊明“形夭”二字非误矣。其云“恒沙”,即“亹亹”之异文。
清董诰辑《全唐文》卷一百四十八《等慈寺碑》“刑天”即讹作“形夭”。《山海经》第三《北山经》: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这里说“常衔西山之木石”是精卫的行动,但“衔”的动作居然被曾氏移给了“刑天”。可见曾氏不仅擅改陶诗,甚至连上古典籍《山海经》也不放过,足见其信口雌黄之恶劣学风。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对“形夭无千岁”一句“五字皆讹”的解说,尤属荒唐可笑。在古籍传写或刊刻中,因形似致讹确实是常见的现象,但一句五言诗的连续五个字全部因形似而致讹,求之千年古籍,也没有一例可为旁证。曾氏怀疑“形夭”“猛志”“上下文义,不甚相贯”,倘若果然如此,还用怀疑吗?宋周必大(1126—1204)《二老堂诗话》“陶渊明山海经诗”条:
江州《陶靖节集》末载宣和六年临溪曾纮谓:靖节《读山海经诗》其一篇云:“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不贯,遂按《山海经》,有云:“刑天,兽名,口衔干戚而舞。”以此句为“刑天舞干戚”,因笔画相近,五字皆讹。岑穰、晁咏之抚掌称善。余谓纮说固善,然靖节此题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如前篇终始记夸父,则此篇恐专说精卫,衔木填海,无千岁之寿,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并指刑天,似不相续,又况未句云“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何预干戚之猛耶?后见周紫芝《竹坡诗话》第一卷,复袭纮意,以为己说,皆误矣。(明津逮秘书本)
可见宋人已经开始质疑“曾纮说”,但周氏所言缺乏力度。元方回《桐江续集》卷十二“辨渊明诗”条:
渊明《读山海经》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无千岁,猛志故常在”,此四句皆以指精卫也,谓此禽之寿,焉有千年,而报寃之意未尝泯耳;若所谓“形天,兽名,口中好衔干戚而舞”者,《山海经》信有之。曾纮偶见此,即改“形天无千岁”为“刑天舞干戚”,然辞意不相谐合,盖近世读书校雠者好奇之过也。予谓“形天无千岁”为是,不当轻改。(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针对曾氏擅改陶诗一事,方回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微禽移木石,欲以塞东洋。赋寿何能远,衔寃未始忘。起脾讹越婢,澎浪转彭郎。轻改刑天字,于文恐未详。
“于文恐未详”一句深刻揭示了这种行为的弊端,那就是把自己一时的想法强加给古人,破坏古人作品的原貌。清陶澍曰:
“刑天舞干戚”,正误始于曾端伯。洪容斋、朱子、王伯厚皆从其说,独周益公以为不然。近世犹有伸周绌曾者,如何义门、汪洪度皆是。微论原作“形夭”,字义难通,即依康节书作“刑夭”,既云夭矣,何又云无千岁?夭与千岁相去何啻彭殇,恐古人无此属文法也。若谓每篇止咏一事,则钦䲹、窫窳,固亦对举。若谓刑天争神,不得与精卫通论。未知断章取义,第怜其猛志常在耳。以此说诗,岂非固哉高叟乎?”
陶澍所言是非常深刻的。丁福保指出:
陶注非是。《酉阳杂俎》卷十四:“形夭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为目,脐为口,操干戚而舞焉。”则“形夭”之夭,不作夭折解。据《酉阳杂俎》及陶诗,知陶公当时所读之《山海经》,皆作“形夭”,且“形夭无千岁”,与上下句文义亦相贯。宜仍从宋刻江州《陶靖节集》,作“形夭无千岁”为是,不可妄改。
在此基础上,王叔岷进一步指出:
《海外西经》之“形夭”,曾氏引作“刑天”,形、刑古通。毕沅《山海经新校正》称唐《等慈寺碑》作“形夭”,郭璞《图赞》亦作“形夭”,并与《酉阳杂俎》合。则此诗“形夭”二字,本于《山海经》不误。“无千岁”三字,亦当从丁说,无烦改字。“形夭无千岁”,谓形夭为帝所斩也。“猛志固常在”,谓其仍能操干戚而舞也。陶公杂诗之五:“猛志逸四海。”張溥《陶彭泽集》本“固”作“故”,丁氏笺注本同,古字通用。这些意见都是非常中肯的。
然而,时至今日,“曾纮说”在被人们遗忘的同时,其擅改“形夭无千岁”为“刑天舞干戚”的恶果,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遵从。这种情况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学术在逻辑思维方面的欠缺,即不善于辨名析理,而偏重于具象的感悟,现代学者亦常食古不化,缺少现代的理性和质疑的精神。
作者:范子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悠然望南山——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中古文学的文化阐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