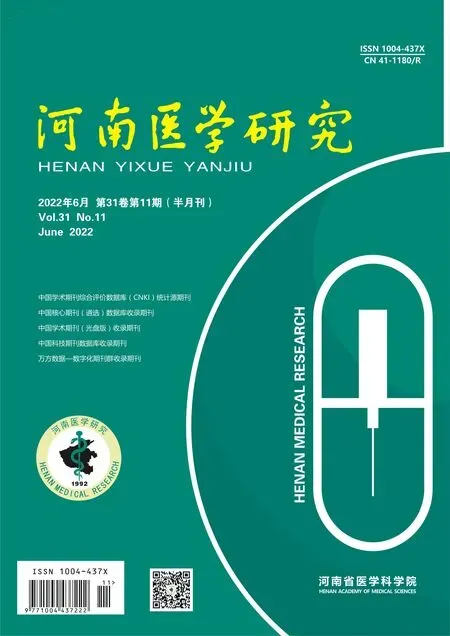运动性高血压的研究进展
房慧雯,侯婷,赵红梅,黄胜楠,肖暖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全科医学科,河北 保定 071000)
心脑血管疾病拥有庞大的患病人数和极高的再住院率和病死率,是我国医疗卫生系统沉重的负担。既往全国性抽样调查显示,高血压作为心脑血管病重要的危险因素,其发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到2015年我国成人居民高血压发病率为27.9%,现患病人数约为2.45亿[1-2]。目前临床上常用的高血压的诊断方法为静息状态下非同日测量3次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140 mmHg(1 mmHg=0.133 kPa)和(或)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90 mmHg,但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在确诊为高血压之前已经发生与高血压相关的器官损伤[3]。因此,探寻敏感性、特异性强的检测方法/指标对识别具有高血压或高血压伴器官损害发病风险的患者具有重大意义。研究表明,标准运动测试中的过高的血压反应(hypertensive response to exercise,HRE)可能是敏感的预测指标之一[4],运动血压过高是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又一危险因素。本综述旨在总结有关目前运动性高血压的最新进展,探讨其潜在临床意义,并对治疗方案进行进一步探究。
1 HRE的定义和流行病学
HRE是指在心肺运动测试(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ing,CPET)过程中或刚结束时血压值超过正常反应性增高生理范围的现象,也称运动性高血压。与明确的静息血压分级标准[5]形成对比的是,由于运动中的血压反应与运动方式(功率自行车、台阶、跑台等)、运动负荷、研究人群、年龄、性别、体能、测试时间等许多因素有关,运动有关的血压升高反应的分级并不十分明确。关于HRE的定义目前国内外尚未得到一致的意见。一般认为次极量运动负荷下(心率达最大心率的85% ~90%)男性收缩压峰值≥210 mmHg,女性收缩压峰值≥190 mmHg即为HRE[6];然而美国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脏协会对运动测试的指南更新中提出,收缩压峰值>214 mmHg被定义为CPET中的HRE[7];也有研究将HRE定义为在第2级(3~6 min)运动时或运动后恢复期3 min时,收缩压和舒张压≥研究人群中同性别年龄的第95百分位的收缩压和舒张压数值[8]。因此,目前仍没有关于HRE阈值的明确结论。
由于HRE的阈值定义缺乏统一,各研究中人群、种族、检测方法的不一,导致发病率的统计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既往研究发现,在静息血压正常的年轻人群中HRE的发病率为18%,在健康的中年男性群体中发病率为40%,而在心血管疾病风险较高的人群中HRE的发病率较高,如2型糖尿病患者的HRE发病率甚至达50%,隐匿性高血压中达40%[9-10],在未治疗的一级高血压男性患者中约为40.4%[11],表明HRE可以作为潜在的风险标志。此外,HRE与心血管疾病的传统危险因素如年龄、吸烟、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静息血压和总胆固醇与高密度胆固醇之比有关,也与肥胖、健康状况、腰围有关[12]。
2 运动性高血压的临床意义
2.1 运动性高血压与高血压的关系
2.1.1 HRE是未来新发高血压病的强预测指标 在静息血压正常(办公室血压<140/90 mmHg)的人群中,运动血压升高意味着未来患高血压的风险增加,并且运动峰值血压越高,未来高血压发病风险越大。Jae等[13]发现,在静息状态下血压正常的健康男性人群中,运动收缩压峰值为181 mmHg是平均5 a随访期间发生高血压的独立预测因素。Berger等[14]将受试者的平均运动SBP和DBP反应分为4个级别(SBP≤158 mmHg,158 mmHg<SBP≤170 mmHg,170 mmHg<SBP<183 mmHg,SBP≥183 mmHg;DBP≤73 mmHg,73 mmHg<DBP≤77 mmHg,77 mmHg<DBP<82 mmHg,DBP≥82 mmHg),通过随访发现运动血压级别越高的受试者未来新发高血压的累积概率显著增加,并且运动SBP或DBP每增加5 mmHg,高血压发病风险分别增加11%和30%。HRE预测高血压独立于临床静息血压和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并不受运动测试方式、强度、数据分析方法等差异的影响,且在次极量强度下发现了最强的关联[15]。由于次极量运动反映了与日常生活活动相称的心血管负荷,因此与诊室血压相比,次极量运动时血压升高幅度可能是评估慢性血压负荷的更好指标。
2.1.2 HRE与隐蔽性高血压的关系 临床上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高血压(masked hypertension,MHT)是心血管和全因死亡率以及偶发高血压的风险增加相关因素,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有密切联系。最近研究发现在次极量运动中,过高的运动血压与MHT的高发病率有关,HRE患者的MHT发病率达58%[16],运动血压是否可以作为临床上发现MHT的辅助方法,降低MHT的漏诊率,仍需进一步探索。
2.1.3 HRE与高血压前期的关系 高血压前期和HRE也可能存在潜在的相关性。Miyai等[17]通过长期随访发现HRE是高血压前期患者的独立危险因素。在静息血压正常的人群中,运动血压过高者比运动血压正常者的平均静息血压略高[18]。这表明HRE可能是原发性高血压早期发展的标志,并暗示高血压前期、HRE、隐蔽性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状态可能存在潜在交叉。Fazio等[19]在20例高血压前期患者中发现48%的患者患有HRE,并且与无HRE的高血压前期患者相比,患有HRE的高血压前期患者每个运动阶段的收缩压、相对室壁厚度、等容舒张时间、全身血管阻力及总动脉僵化程度均较高。高血压前期患者中HRE的高发率与心血管重塑的关系表明在日常反复出现的物理压力下,病理生理学上的收缩压升高可能在高血压心血管损害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收缩压对运动测试(任何强度)的反应可能比诊室血压更好地预测未来的静止收缩压[7],但目前临床上仍多以诊室血压测量来确定血压状况。在无诊室外血压评估的情况下,真正的血压控制可能由于白大衣高血压的存在而被高估,或由于单一静息血压读数可能不足以反映24 h的总血压负荷而被低估。因此,运动血压作为独立预后指标的真正效果最好通过动态监测整体血压情况来评估。目前仍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来充分阐明运动血压在揭示诊室测量所遗漏的潜在高血压方面的能力。
2.2 HRE与心脏结构的关系HRE与心脏结构异常密切相关。HRE患者的左心室肥厚风险是无HRE患者的2倍以上,并且有更高的平均左心室质量、左心室质量指数和左心室相对壁厚[20]。而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增加了致命性心律失常发生的风险,孟昊等[21]发现老年高血压合并左室肥厚(lef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LVH)患者心律失常的发生率较不合并LVH患者明显增高。虽然HRE与心脏结构异常以及心律失常相关,但现有研究尚不能确定HRE与心律失常是否有关系。
2.3 HRE与心血管事件HRE是除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外,未来心血管病的发生及死亡风险增高的相关因素,Lee等[22]发现次极量运动收缩压与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呈正相关,提示运动高血压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然而对冠状动脉疾病及扩张型心肌病患者的前瞻性研究表明,HRE与病死率的增加并无关联,运动血压过高可能是对不良后果的保护,可能是因为这种反应反映了心肌较高的储备功能。Kallistratos等[23]对160例左室射血分数为(33.00±8.00)%的收缩期心力衰竭患者进行随访后发现运动高峰时SBP≥160 mmHg和脉压≥75 mmHg的患者预后最为良好,而运动峰值时SBP<160 mmHg及脉压<75 mmHg的患者的心脏死亡风险各增加了4倍和3倍,提示临床医生在用运动血压评估患者心血管病风险时应结合患者的基本情况和基础疾病,不能认为运动血压过高一定是危险信号。
2.4 HRE与脑血管事件近年有研究提示HRE是脑血管损害的体现[24],但此类研究较少,脑血管损害机制可能与心血管损害机制一样,与交感神经系统亢奋、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过度激活、血管内皮功能受损、遗传因素等有关。Giang等[24]通过长期随访发现,运动高峰时SBP≥210 mmHg的男性卒中风险最高,且风险与吸烟、血糖、胆固醇和BMI无关,而运动高峰时SBP每增加24.6 mmHg,卒中的风险增加34%。Mariampillai等[25]也发现最大运动负荷时的SBP与卒中风险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同时(运动峰值SBP-静止SBP)>99 mmHg的卒中风险比73~85 mmHg的人群增加了2.6倍。目前静止时SBP与卒中风险之间的关系已被证实,对于脑卒中,最大运动量时的SBP是独立于休息时血压的最强预测因素之一。
2.5 HRE与心血管疾病其他靶器官损害对心血管疾病靶器官损害的研究发现,HRE与肾脏疾病关系密切,2型糖尿病患者运动中过度血压反应的受试者运动后30 min白蛋白-肌酐比值明显高于正常血压反应组[26]。但HRE是通过何种机制对肾脏产生影响,对肾脏病的预后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尚不明确。目前仍缺乏与其他靶器官如眼部、微血管的研究。
3 HRE的治疗方案
3.1 生活方式的干预虽然HRE对于心脑血管疾病预后的重要性国内外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运动性高血压是否需要治疗、如何治疗尚无定论。目前尚无关于运动性高血压的防治指南,其治疗多以生活方式的改善为主。研究发现,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改善运动中过高的血压反应,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增加氮氧化物的生物利用率和改善动脉硬化等实现的。(1)合理的有氧运动:目前已有明确证据表明有氧运动能降低高血压患者的静息血压,而HRE发现于动态运动中,并且高强度的运动可能会增加氧化应激从而导致运动血压的升高,每周4次的综合运动(5 min拉伸热身运动,20 min抗阻运动,30 min有氧运动)是有效的改善HRE的运动方式[27]。(2)合理饮食:增加膳食纤维及植物来源蛋白质的摄入,减少脂肪摄入,戒烟戒酒,特别注意要限制盐摄入,限盐(每日10 mmol)可以在不影响中枢和外周血流动力学的前提下降低高血压患者运动时的血压[28]。(3)心理因素:不良情绪会导致交感神经系统过度活化,而心理状态越好、更乐观的人运动前后的心率及血压变化越小[29],因此在生活中应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3.2 药物干预目前关于HRE的药物治疗研究多为小样本、单中心的随机对照试验,临床上尚未推广对HRE患者进行药物治疗。用于高血压治疗的药物能降低运动血压,其机制可能是由于抑制交感神经系统和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活性。既往研究表明,基于β受体阻滞剂的单一或联合治疗,与高血压患者较低的运动血压相关[30]。同时,运动前进行鞘内芬太尼注射可能通过减弱骨骼肌的神经信号使高血压患者在运动中异常升高的血压下降[31],虽然鞘内芬太尼注射降低运动血压的持续时间尚不明确,且临床应用存在一定困难,但此方法无疑为HRE的治疗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4 讨论及展望
HRE对于高血压的预防具有重要作用,既往研究表明HRE与高血压、心脑血管事件、心脏结构具有潜在的相关性,并能预测患者的预后,因此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但目前运动血压尚未像其他心血管高危因素如高脂血症等引起广泛的重视,并且在临床工作中运动血压的测量需要多科室的协助,这使得运动血压在临床工作中的应用并不普及。临床工作中应增加对运动血压的重视,对静息血压正常的HRE患者积极随访,作为危险人群尽早启动心脑血管病的一、二级预防,争取做到心脑血管病的早发现,早治疗。评估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病情时应将诊室血压与运动血压相结合,尽早发现HRE,综合评估血压和靶器官损害的情况,指导降压治疗方案。
同时,目前临床运动试验实施过程中HRE的诊断阈值尚未确定,目前对于HRE的研究多以外国人群为基础,且多是小规模的非对照试验,因此,尽快明确适合我国人群的运动血压具体阈值对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目前HRE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了,根据国内外既往研究,考虑其与交感神经系统亢奋、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过度激活、血管内皮功能受损、遗传因素等有关。但目前对HRE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长期随访发现其对心脑血管病的预测作用,对于发病机制的研究尚不多,HRE究竟是因为运动时心输出量的增加超过了自身调节的范围、血管的收缩或舒张功能异常而导致的,还是只是超前提示心脑血管损害的一种表现,仍无定论。日后关于运动性高血压的研究可通过长期追踪随访,探讨经治疗后的HRE患者与未经治疗的HRE患者的预后情况,以此为HRE是否有治疗的必要增加依据。目前需要临床医生提高对HRE的重视,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测量阈值及诊断标准,进一步探索发病机制和临床意义,寻找合适的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