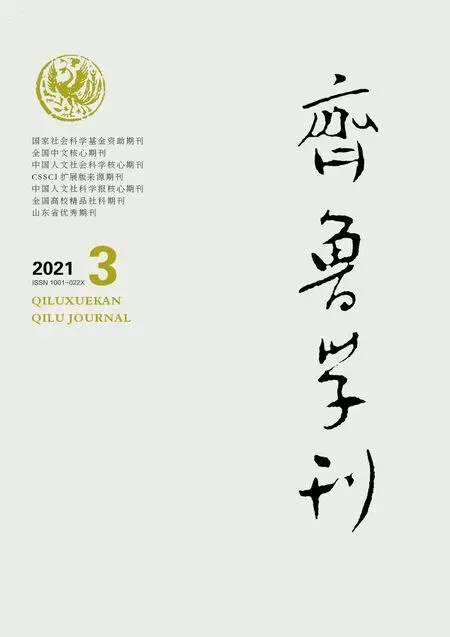《论语》编纂中的“取”与“舍”
——以上博简与《论语》的对比为视角
王红霞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273165)
《论语》的成书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1](P1717)也就是说,《论语》是集结孔门弟子的“课堂笔记”和所见所闻编纂而成的,其内容当然不是所有弟子的原始记录,而是经过编者筛选和编辑而成。究竟是如何编纂的一直是学界未解之谜。
汉代流传三种不同的《论语》版本,鲁《论》、齐《论》和古《论》,然而,三种版本在主体规模和内容上并无太大差异。今本《论语》为西汉张禹以鲁《论》为主,兼采其他,整理而成的“张侯论”。因此,今本《论语》虽不是《论语》的原貌,然以今本《论语》为底本,考察《论语》编纂时的思想倾向,当大致不谬。
在今本《论语》与上博简及其他典籍对读时,不仅要看《论语》编纂中“选取”了哪些材料,还要看“舍弃”或者“简略”了哪些材料,由此得以管窥《论语》编纂的取舍标准,为研究《论语》成书提供新的思考。笔者不揣浅陋,拟从入仕观、鬼神观、刑政观三个方面加以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一、 入仕观
今本《论语·子路》有这样一段话: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2](P133)
这段内容又见于上博楚简《仲弓》,其内容较《论语》中记载要丰富得多:
季桓子使仲弓为宰,仲弓以告孔子,曰:“季氏……使雍也从于宰夫之后,雍也憧愚,恐贻吾子羞,愿因吾子而辞。”孔子曰:“雍,汝毋自惰也。昔三代之明王,有四海之内,犹来……与闻之,夫季氏,河东之盛家也,亦[可]以行矣。为之,余诲汝。”[3](P196-197)
上博简《仲弓》中,季桓子邀请仲弓为邑宰,但仲弓希望借助孔子辞去季桓子的聘任。孔子认为这是仲弓不勇于任事的“自惰”行为。他提出三代明王皆是招揽贤才辅助治国。季氏家族为河东显赫之家,也需要贤才辅佐。具有“南面”之才的仲弓可以借助季氏施展才华,所以应该入仕。孔子还说,做了宰邑后有不明白的问题,孔子可以教他,以解除其后顾之忧。总之,孔子从多个方面劝告仲弓,认为他应该接受季桓子的邀请。从《论语》中,只能看到仲弓向老师请教如何为官的内容,而上博简《仲弓》则把季桓子的邀请、仲弓的犹豫、孔子的鼓励和支持、仲弓向老师请教为政之道的这个过程都详细记录。对比可知,《论语》编纂者在选取材料时更着重孔子为政理念的部分,而舍弃了孔子支持弟子从政的内容。
当然,《论语》中也有孔子支持弟子从政的内容,比如《论语·公冶长》:“子使漆雕开仕。”[2](P43)孔子曾劝漆雕开从仕为官,然而,漆雕开并没有像仲弓那样,听从老师的建议去做官,而是回答说:“吾斯之未能信。”漆雕开认为自己在诚信方面修养还不够,不具备做官的能力。孔子听到这个回答后很高兴,“子悦”。这段话的重点不是孔子劝解漆雕开从仕,而是“子悦”。孔子这里的“悦”,不是悦其不仕,而是对其能自我检视的态度表示满意。以此来看,《论语》此处意在说明,孔子认为个人的德行修为要比从政为官更为重要。《孔子家语》也有这段记载,内容略有不同:
(漆雕开)习《尚书》,不乐仕。孔子曰:“子之齿可以仕矣,时将过。”子若报其书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悦焉。[4](P441)
不同于《论语》中只说“子使漆雕开仕”,《孔子家语》具体说明漆雕开本身就不喜欢从政为官,而专注于研习《尚书》。以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他当然了解漆雕开的个性。然而,即使这样,孔子依然劝说漆雕开从仕,他说:“你这个年龄也应该从政了,否则将错过时机。”孔子从年龄的角度鼓励漆雕开从仕,有时不我待之意。对此,《论语》并未提及。
对于弟子主动提出仕禄之事,《论语》是怎么记载的?“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P19)仅从文义来看,孔子虽然没有否定子张求仕,但是告诉子张谨言慎行,多闻博学,言语中透漏出不愿弟子急于谋求禄仕之意。子路为官后,提携同门,让子羔为费宰。孔子听说后,非常不高兴,说:“贼夫人之子。”[2](P118)“贼”是戕害意,显然,孔子认为子羔学未成熟,让他从政是害了他。子路随口辩解,孔子说“是故恶夫佞者”,表示讨厌狡辩之人,连子路也一并否定了。这段对话的着重点是要学有所成之后才能为官,不能汲汲于求位。《论语·里仁》还载有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2](P38)这句表明孔子虽不避位,更注重的是从政所具备的才德。
《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积极入仕的心态,也记载了他支持弟子做官。但是,细绎《论语》可以发现,《论语》中对孔子支持弟子在什么年龄、什么条件下弟子从政并未有具体说明,对支持弟子入仕的语言比较简略,而对于讨论弟子不适合入仕的内容,则详细记载。今本《论语》让我们看到的是孔子更注重弟子的德行,一定要在德行足堪为政之时方可。如果弟子能够反躬自省,不急于早日为官,孔子还非常欣慰。如果德性不足而急于入仕,孔子则非常反感。由此可以推断,《论语》的记载中,相对于事功,孔子更注重个人德行。钱穆根据《论语》得出:“孔子之教,在使学者由明道而行道,不在使学者求仕而得仕。若学者由此得仕,亦将藉仕以行道,非为谋个人生活之安富尊荣而求仕。故来学于孔子之门者,孔子必先教其志于道,即是以道存心。”[5](P92)
《论语》中的孔子不愿弟子热衷于利禄,这与简帛中呈现的积极支持弟子为官有所不同,这或许恰是孔子弟子在编纂《论语》时取舍的一个标准。罗新慧也注意到了今本《论语》的从政思想与简帛《仲弓》篇有所不同,并分析说:
编定《论语》一书的孔门弟子,属于“后进”。以曾子、子夏为代表的这些孔门弟子努力的目标是为“帝王师”、传播孔学,而不是直接入仕从政。孔子劝说仲弓从政的思想与他们所想有一定距离,所以在编定《论语》时将这部分材料加以删削,亦是儒家“后进”弟子思想发展的必然。[6]
诚然,《论语》编定者的目标虽未必是“帝王师”,然其并不热衷于入仕从政则是肯定的。钱穆就说过:“孔子门下,冉有、子路的军事、财政;宰我、子贡的言语、外交;子游、子夏的文学著作,都在外面有表现,但孔门弟子中更高的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称为‘德行’,列孔门四科之首,而实际却反像无表现。”[7](P160)颜渊、闵子骞、冉伯牛都没有做过官,仲弓曾做过季氏的邑宰。“无表现”,是指少有或者根本没有政治建树。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特点,那就是为人敦厚、朴实、谦恭、孝悌。这正是《论语》重德行、轻事功的体现。
二、 鬼神观
《论语》中孔子极少谈论鬼神,子路与孔子的一段对话颇可玩味: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2](P113)
对于子路问怎样侍奉鬼神及人死后情形的发问,孔子没有正面回答,而要子路先把生的道理搞明白,把活着的人服侍好。面对樊迟的提问,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2](P61)。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敬”,但“远之”,专心致力于引导人们走向义。《论语》还记有“子不语怪,力,乱,神”[2](P72)的话。从《论语》来看,孔子尽量避免主动谈论鬼神,对于别人提出的鬼神问题,他要么避而不答,要么引导至道德,进而更关注人本身的价值。
上博简《鲁邦大旱》一文让我们看到孔子对鬼神的另一种态度。文中记载鲁哀公时鲁国发生大旱,哀公向孔子咨询解决之道。孔子提出弭灾之法,让鲁哀公不要爱惜圭璧币帛等宝物,用来祭祀山川。弟子子贡表示质疑:
夫山,石以为肤,木以为民,如天不雨,石将焦,木将死,其欲雨或甚于我,或必待吾名乎?夫川,水以为肤,鱼以为民,如天不雨,水将涸,鱼将死,其欲雨或甚于我,或必待吾名乎?(1)释文参见裘锡圭:《〈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鲁邦大旱〉释文注释》,《裘锡圭学术文集·简牍帛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85页。
子贡认为如果山川有神灵的话,天不下雨则树木枯萎,河水干涸,鱼虾死亡,山神、水神应该更着急,不需要祭祀也应该及时下雨,何必依靠祭祀攘除旱灾。子贡的提问不无道理。可惜,简五是残简,只有“孔子曰:於乎……”几个字,我们无法得知孔子如何回答这个刁钻的问题。然而,从上下文意可以判断,孔子之意并非鬼神本身,而是为了百姓福祉。近来发现的大量《日书》,反映了当时百姓崇信鬼神相当普遍。可见,祭祀山川是孔子基于百姓的认知而提出的解决办法。《易传》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鲁邦大旱》恰恰体现了孔子神道设教的理念。廖名春认为孔子不废鬼神祭祀是“君子以为文”[8],有“神道设教”的用心。这种看法并非个例。孔德立提出:“《鲁邦大旱》简文可知,当时的民众普遍信仰求雨的‘说’祭,国君带领民众举行祭祀活动,取悦于神灵,实际上是消除百姓恐慌、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模式,也是建立政府公信力的有效方式。《鲁邦大旱》所载,孔子建议国君顺应民意、祷祝山川,以取悦神灵的方式禳灾,这种行为在性质上无疑属于‘神道设教’的范畴。”[9]上博简《三德》也有“鬼神禋祀,上帝乃怡”[10](P293),“民之所欲,(鬼)神是有(祐)”[10](P302)的话,这里谈到百姓所想所欲,鬼神会庇佑,与《鲁邦大旱》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他典籍中也有不少孔子论鬼神的内容。
《礼记·中庸》记孔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11](P780)鬼神虽然看不见,听不到,但是在我们周围,其功德体现在万事万物上。世人当整齐礼服,庄重祭祀。在这里,孔子肯定了鬼神的存在,只是我们通过肉眼无法感知而已。“(孔子)对鬼神之事采取融通的态度,并不否定鬼神的存在”[12]。鬼神还具有教化功能,《礼记·祭义》记曰:“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11](P688)而《孔子家语·哀公问》中谓“明命鬼神,以为民之则”[4](P216),鬼神不但使百姓敬畏、服从,还成为百姓遵从的法则。总之,鬼神使百姓有敬惧之心,“斋戒以事鬼神,择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11](P803)。
然而,孔子虽然肯定鬼神的存在,也认可神道设教,但对于鬼神的细致探讨,他则拒绝回答,防止人们沉溺其中。《说苑·辨物》记载子贡与孔子人死后有无知觉的对话。孔子说,如果我说有,那么孝子贤孙将不忍心下葬,妨碍了正常的丧葬和生活;如果我说没有,则不肖子孙会弃而不葬。“在孔子那里,鬼神根本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价值判断,因而为了民生,孔子不否定鬼神,也极少谈论鬼神,而是要人们把精力集中于人事上”[13]。
回看《论语》,无论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还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都从未否定过鬼神,而是对鬼神抱有虔敬之心。颜世安提出:“《论语·述而》记‘子不语,怪、力、乱、神’,当非一般意义的不言神,而是不言地方神怪。这不只是孔子个人态度,是鲁国贵族的一种传统。”[14]子不语的“神”并非泛指一切神灵,而是特指地方神怪。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地方鬼怪,其他鬼神孔子是认可和谈论的。但是,由于《论语》中关于鬼神的记载仅寥寥数语,再加上语气处处体现的是远离鬼神,注重现世的人,从而让人产生误解。结合简帛和其他典籍,我们发现,孔子并非无神论者,而是在人神关系中以人为本。孔子希望人们对鬼神有敬畏之心,又不沉迷于鬼神之事,而是专注于人,“一方面,鬼神关系到祖先和神明,有助于维持教化、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所以要尊敬。但是另一方面,鬼神之事又难知,如果太依赖了,太当真了,就容易诬誷。在若即若离之间,显示了孔子的智慧”[15](P43)。《论语》慎言鬼神,避谈神道设教,这或许也是孔子弟子在编纂《论语》时的一个取舍标准。
三、 刑政观
《论语·为政》篇记孔子之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P12)这段话在《礼记·缁衣》、郭店简《缁衣》以及上博简《缁衣》中都有出现,只是文字略有不同。分列如下:
《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礼记·缁衣》:“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11](P824)
郭店简《缁衣》:“长民者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劝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免心。”[16](P62)
上博简《缁衣》:“长民者,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免心。”[3](P78)
这四处在文意上没什么差别,均是孔子更注重德和礼之意,因为“齐之以刑”的结果是百姓表面上遵守刑法,内心却无羞耻之心。但是,仔细分析却有多处细微差别。
其一,在文字顺序上不同,《礼记·缁衣》、郭店简《缁衣》以及上博简《缁衣》三篇,都是先谈“德”“礼”,后谈“政”“刑”,唯有《论语·为政》是先谈“政”“刑”,后谈“德”“礼”。显然,较之其他三篇,《论语》语句更加简练明了,文字的语气中明显更强调后面一句,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重要意义。
其二,《礼记·缁衣》、郭店简《缁衣》和上博简《缁衣》皆说明教以政令和刑罚,将“民有免心”“民有遁心”,百姓会想方设法逃避刑令的惩戒。而教之以道德和礼仪是“民有格心”“民有劝心”,百姓有向善之心。只有《论语》加上了“耻”的概念。若民无所羞愧,那么,虽不敢为恶,仍有为恶之心。若民耻于不善,则无为恶之心,且日臻向善。对比之下,《论语》的语气更为凝重,二者差异更为强烈。
其三,《礼记·缁衣》、郭店简《缁衣》和上博简《缁衣》,用的是“教之……齐之……”,唯有《论语》用的是“道之……齐之……”,“教”是教育,而“道”是引导,两字意思相近,故在现代汉语中“教导”常连用。“道”还有一层含义,“谓先之也”[17](P54),以某某为先之意,《论语》此处除了表达德礼之治与刑政之治的优劣,还说明了两种治理方式顺序的先后问题。朱熹说:“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17](P54)尽管朱熹认为德礼为治国之本,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刑者是辅治之法,不可偏废。但如果仅读《论语》这句话,这层意思是读不出来的。朱熹此处的这种解释,当是结合其他文献得出的结论,而非仅凭孔子的这一句话。
《论语·子路》篇中仲弓向孔子问政,上博简《仲弓》也有这段文字。学者普遍认为,上博简《仲弓》与《论语·子路》源出一处,内容更加丰富。其中,《论语》中的“赦小过”,在《仲弓》中是“宥过举罪”(2)原整理者释为“赦过举罪”,陈剑、杨怀源、侯乃峰释为“宥过举罪”,参见侯乃峰:《上博楚简儒学文献校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88页。。但是,“宥过举罪”毕竟与“赦小过”还有文意的差别。《周易》曰:“君子以赦过宥罪。”[18](P362)《孔丛子·刑论》曰:“故宥过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19](P60)“宥过举罪”“宥过赦小罪”“赦过宥罪”表达略有不同,意思无甚差别。孔颖达疏:“赦谓赦免,过谓误失,宥谓宽宥,罪谓故犯。过轻则赦,罪重则宥,皆解缓之义也。”[20](P52)无心为过,有心为罪。据此,“宥过举罪”是指宽宥无心的过错,而举发有心之罪。《论语》只谈到“赦小过”,没有涉及“罪”的问题。从语气上看,其重点并非谈论“罪”或者“过”的问题,而是要求执政者有宽宥之心。对于何谓“宥过举罪”,上博简《仲弓》记孔子之言:“山有崩,川有竭,日月星辰犹差,民无不有过……刑政不缓,德教不倦。”由于竹简残坏,我们无法知悉全文,然而,“民无不有过”似乎是对“赦小过”的解释,“刑政不缓,德教不倦”则表明孔子认为刑罚和德政两方面均是治国之要,不可偏废。从上博《仲弓》篇可知,孔子认可刑政的价值,但这样的思想在《论语》孔子与仲弓的对话中没有体现,只保留了“赦小过”的内容。
《孔丛子·刑论》也有仲弓向孔子请教刑教之事:
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为教,古有礼然后有刑,是以刑省。今无礼以教而齐之以刑,刑是以繁……夫无礼则民无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19](P51)
孔子认为古今皆有刑罚,只是古时刑少,当今刑繁,究其原因是古代人有礼,而今人无礼。在无礼的情况下,百姓不知羞愧,就须正定刑律,这样,百姓为了免受惩罚而不去犯罪。礼教和刑教都是政教的一部分,只是刑教层次略低一筹,刑教是礼教缺失下的补充。在这里,孔子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刑教的必要性。上博简《鲁邦大旱》中孔子说旱灾的发生是“失诸刑与德”,孔子把“刑”与“德”并列,且“刑”置于“德”之前,由此可见孔子重视刑罚的作用。
《孔子家语·刑政》记载了孔子“刑政相参”的理念:
孔子曰:“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颛五刑必即天伦。行刑罚则轻无赦。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尽心焉。”[4](P355)
孔子明确说明圣人治理国家并非只是用教化,对那些教化之后仍不知改变,损害道义,败坏风俗之人,要使用刑罚。而且,施行刑罚时,即使犯罪很轻也不能随意赦免,因为“刑”就是“成型”之意。由此体现刑罚的威严。《左传·昭公二十年》记孔子赞赏子产治国,评论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21](P1421)孔子主张治国“宽猛相济”,与“刑政相参”相一致。《孔丛子》中,孔子所说的“五刑所以佐教也”[19](P18),也与“刑政相参”的意义相当。
倘若仁政无效,需要辅之以刑。在具体量刑方面,孔子也有说明。上博简《季庚子问于孔子》中,孔子提出根据犯罪程度的轻重,给予不同的惩罚方式:“大罪杀之,臧罪刑之,小罪罚之。”[3](P244)大的罪行当然要处于死刑,中等大小的罪要处于肉刑,而小罪罚钱自赎。在赦罪方面,也是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宽刑,不能盲目免除,“大罪则赦之以刑,臧罪则赦之以罚,小则訿之”[3](P244)。
回看《论语》,涉及到刑罚处寥寥可数,仅凭《论语》文字,会有孔子重德轻刑之感。结合新出简帛和其他文献可知,孔子的治国理念是德主刑辅,强调以德为主、为先。但是,孔子认定刑罚也必不可少,认可刑罚的价值,并不轻视刑罚。“《论语》中的孔子只讲德而不谈刑,这是编者为了塑造至仁至德的孔子形象而善意地舍弃了孔子的刑罚语录。其实,完整的孔子政治思想应该包括德、刑两个方面,即以仁政德治礼乐教化为主,辅之以必要的刑罚”[22]。孔子官至大司寇,主管鲁国的刑狱诉讼,自然对刑罚的利弊了然于胸。他当然明白,治国仅靠德礼教化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德礼未达之处,必须有刑政辅佐。《论语》强调德,而罕言刑,其目的虽然未必是“为了塑造至仁至德的孔子形象”,然而编纂者有意删削刑政内容,突出德礼,当为事实。
四、《论语》与上博简的关系
从《论语》与新出简帛、传统典籍的对比来看,《论语》与简帛等文献在思想上稍有差别。在入仕方面,《论语》凸显孔子希望弟子不汲汲于禄位,而是能够淡泊名利,专心修身,不重事功,而简帛中则能看出孔子支持弟子积极入仕。在鬼神方面,《论语》强调孔子慎谈鬼神,而新出简帛和其他典籍表明孔子也不否认鬼神,甚至支持神道设教。《论语》中的孔子在治理国家方面更注重德和礼,对刑政的价值则谈论较少,而简帛中的孔子认为治国当德主刑辅,同时也注重刑政的价值。
《论语》与上博简均为七十子及后学所记,二者写定时间大体都在战国中前期。那么,具体孰先孰后呢?如果《论语》在先,那么上博简反映的是孔门后学借孔子之名“增加”了新的思想内容。如果是上博简在先,那么,《论语》则是在编纂过程中有意“删削”部分内容,意在突出孔子注重德礼的思想。这是儒家思想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关涉到孔子思想的原貌及早期儒家思想的发展流变。
由于文献缺乏,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未充分讨论,但已有学者对此进行初步探讨。比如晁福林教授将上博简《仲弓》与《论语·子路》篇相关内容对读,认为上博简《仲弓》当是《论语》编纂时的材料来源,《论语·子路》是在上博简《仲弓》的基础上加以删定而成的:
今得《仲弓》篇可以推测,它很可能就是当时“数十百篇”之一。孔门弟子记载孔子言行甚伙,后来选编《论语》一书时加以删削,上博简《仲弓》很可能就是删削而不存之篇,但其重要内容则保存于《论语·子路》篇中为一章。[23]
显然,晁福林教授认为上博简《仲弓》在前,《论语》编定在后。而郭齐勇教授则恰恰相反,他对读《论语·颜渊》第17至19章与上博简《季康子问于孔子》,认为《季康子问于孔子》“使我们对晚年孔子在衰落的鲁哀之世的政治主张的了解变得丰满起来”,并将其定为《论语》的“传文”,进而推测“或者这正是七十子后学面对现实问题而发展孔子、假托孔子的表现”[24]。笔者拟从逻辑推理的角度略作分析。
其一,《论语》文字更为简洁、凝练。
上博楚简《从政》中也有与《论语》相近的文字:
毋暴,毋虐,毋贼,毋贪。不修不戒,谓之必成,则暴;不教而杀,则虐;命无时,事必有期,则贼;为利枉事,则贪。[3](P162)
《论语·尧曰》记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楚简《从政》与《论语》此句意义相近,而《论语》的语句更为工整,如“不教而杀,则虐”在《论语》中是“不教而杀谓之虐”;“命无时,事必有期,则贼”,在《论语》中是“慢令致期谓之贼”;“不修不戒,谓之必成,则暴”在《论语》中是“不戒视成谓之暴”。显然,《论语》的编纂者在孔子原话的基础上,又重新调整语言的前后顺序,用词更凝练,且加以排比,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上博楚简《君子为礼》中:
颜渊侍于夫子。夫子曰:“回,君子为礼,以依于仁。”颜渊作而答曰:“回不敏,弗能少居也。”夫子曰:“坐,吾语女。言之而不义,口勿言也;视之而不义,目勿视也;听之而不义,耳勿听也;动之而不义,身勿动焉。”颜渊退,数日不出。[门人问]之曰:“吾子何其瘠也?”曰:“然,吾亲闻言于夫子,欲行之不能,欲去之而不可。吾是以瘠也。”[3](P253)
《君子为礼》简文与《论语·颜渊》“颜渊问仁”章相近: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2](P123)
上博简的“口勿言也,视之而不义,目勿视也,听之而不义,耳勿听也,动而不义,身勿动”,在《论语》中成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张光裕认为“简文所言与《论语》大意相若,两者所强调者虽有‘不义’与‘非礼’之异,然实有同工之妙”(3)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君子为礼》“说明”部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53页。。之所以变成这种高度凝练整齐的排比句,“是《论语》编纂者艺术加工的产物。我们看到,加工前后的孔子语录,艺术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君子为礼》中这几句话很普通,不会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而到了《论语》,编纂者将其提炼成四个‘非礼勿……’的整齐句式,而且有意识地将‘言’‘视’二句互换位置,使第二句句末的‘听’与第四句句末的‘动’押韵,经过这种点石成金的艺术处理,思想内涵没有任何变化,但孔子这四句话却一下子就成为千古名句了”[25]。仔细分析可知,“《论语》所记当是经过润色、加工的结果,而本篇所记较之《论语》为原始”[26]。
《论语·颜渊》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上博简《仲弓》曰:
[附简]:孔子曰:“雍?政者,正也。夫子虽有举,汝独正之,岂不有匡也?”仲[弓]……[3](P198)
由于附简残损严重,无法确知更多内容。然而,《论语》中的“政者,正也”确实比楚简《仲弓》“唯正者,正也”要简洁。
上博简的文字相对粗疏、繁复,而《论语》文字更为简洁、凝练,句子排比工整,节奏明快,语义更为突出。按照“后出转精”的逻辑,《论语》当为时稍晚。倘若是孔门后学借孔子之名表达个人见解,应在内容上加以改变,而不是使文字变得潦草、粗糙,这不利于思想的传播,也有悖常理。
其二,《论语》部分内容言犹未尽。
前文已谈到,上博简《仲弓》与《论语·子路》源出一处,仔细对读,可发现二者在行文中的差别。《论语·子路》的原文是:
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2](P133)
《论语》中,当仲弓向孔子问政时,孔子回答的是“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三个方面,而只具体回答了“举贤才”的内容,对于如何“先有司”,如何“赦小过”都没有涉及。而上博简《仲弓》中,对于仲弓问政,孔子回答的是:“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宥过举罪。”“老老慈幼”在《论语》中没有记载,上博简则记仲弓说“若夫老老慈幼,既闻命矣。夫先有司为之如何”,说明仲弓对“老老慈幼”已了然于胸,而接着问何谓“先有司”,孔子回答说:“夫民安旧而重迁……是故有司不可不先也。”对于“举贤才”的内容,《论语》与上博简《仲弓》内容几乎完全一致。《论语》对“赦小过”也没有具体说明,上博简《仲弓》则对“宥过举罪”进行了解释。
按照一般逻辑推理,既然孔子提到了“老老慈幼”“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四个方面,就会具体解释这四个方面。“老老慈幼”没有什么新意,《论语》中则仅保留了“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三个内容。上博简《仲弓》完整保留了孔子与仲弓的对话,在具体解释这三方面意思时,《论语》只有“举贤才”的内容,显然没有把话说完,言犹未尽。“《论语》绝大多数内容为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内容普遍比较简洁,但事实上,孔子与弟子的谈话不可能如此简单。因此,可说《仲弓》篇是孔子与仲弓之间比较完整的对话记录,而《论语》所记则经过剪裁。换言之,《论语》与楚简《仲弓》之不同,从形式上看,首先表现为《论语》所记只重提示而不重铺陈,《仲弓》则记前因后果;其次,《仲弓》详记夫子之言,《论语》则只取夫子言之精粹者。在这个意义上,可说《论语》是精华篇”[6]。反之,如果说孔子所论本来就如《论语》所记,只具体地谈到了“举贤才”的问题,而对“先有司”和“赦小过”并没有加以解释,那么,上博简《仲弓》中对此的说明是孔门后学假托孔子之言,则明显过于牵强,不合逻辑。
综上所述,《论语》不是孔门弟子的原始记录,而是经过编者筛选、编辑而成。上博简《仲弓》《从政》《君子为礼》等资料或为《论语》的材料来源。《论语》的编纂者除了对这些材料在语言上加以凝练,句式上排比整齐,偏重记言外,更重要的是对诸多材料的裁剪,取舍之间体现了编纂者的思想,显示了《论语》特定的选材标准。所以,上博简不同于《论语》的思想,或许不是孔子弟子加入了新的思想,而是恰恰相反,是孔子本有的思想。
五、 《论语》编纂取舍蠡测
无论是《论语》,还是上博简,大体不离孔子思想,然在倚重倚轻之间略有出入,原因为何?
其一,《论语》作为“语”类文献的特点决定的。《国语·楚语上》有云:“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27](P485)这类称之为“语”的文献,其特征是“明德”,“只要是围绕这种体用特征编选的,不论其篇幅长短,也不论是重在记言,还是重在叙事,都可称之为‘语’”[28]。钱穆在《论语新解》中就说《论语》《国语》《新语》《家语》等书都属于语类,“语,谈说义,如《国语》《家语》《新语》之类”(4)参见钱穆:《论语新解》,上下编中间说明部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这种语“大义”的明德书籍,其著述性质决定了《论语》凸显孔子专心修身、注重人事、强调德行和礼义方面的内容。
其二,《论语》编纂者将自己的思想投射到《论语》中。即使在主观上,编纂者力求真实呈现孔子的语言、行为和思想,尽可能保存孔子思想本真,但是在编纂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个人的好恶代入其中。这是任何书籍编纂中都会或多或少出现的问题,完全的客观极难做到。倘若编纂者主观上确实为了凸显孔子的德行,或者在领悟孔子思想时便是如《论语》这般解读,更会在材料的选择及语言的排比上下功夫,仔细斟酌。诚如杨宽所言:“古代传经与诸子书的编辑,往往以一个学派的内容为主,既有大师讲授的记述,或有师徒问答的记录,更有弟子发挥师说的述论。”[29](P502)由此推想,常为后世学者诟病的“非儒”思想可能并非向壁虚构,或许在编纂中不能尽赅其余,也或许是孔子的本来思想被有意无意地隐去。
其三,对外应对社会巨变,特别是墨家的挑战。战国之初,严刑峻法产生,兵戈征伐增多,礼崩乐坏更为严重,社会陷入混乱。社会形势的变化使社会思想也经历了一次深刻变革,儒学也正面对极大的挑战。
春秋时期,入仕多是由老师或者同门好友向卿大夫举荐,或者因才学出众,声名远播而引起执政者的注意,进而招揽入仕。在求仕之路上,个人恭己以待,虔敬恭肃地修养自己,等待机会,一般不能主动出击。战国初期则出现主动求仕现象,特别是墨家主动游说王公大臣。公孟子(5)惠栋、孙诒让认为公孟子是孔子弟子,宋翔凤认为公孟子是曾子弟子。孙诒让《墨子闲诂》:“惠栋云:公孟子即公明子,孔子之徒。宋翔凤云:《孟子》公明仪、公明高,曾子弟子。公孟子与墨子问难,皆儒家之言……此公孟子疑即子高,盖七十子之弟子也。”参见《墨子闲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491页。认为这是“行而自炫”[30](P566),是一种自我标榜的行为。另一方面,各级部门在选任官员时急功近利,强调事功,而忽略德行。因而,《论语》在编纂时着重凸显德行是从仕的根基,倘若德行学问的培植不够,急于求政,无异于舍本逐末。
战国初期,战乱频仍,朝不保夕,身若浮萍,个人的力量犹显微薄,崇信鬼神之风更甚。墨家更是提出“明鬼”思想,不但力证鬼神存在,提出“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有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鬼神何谓无乎”[30](P268),还认为鬼神可主持正义,明察善恶,“奖贤而罚暴”,提出“故鬼神之明,不可为幽间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30](P284)。在鬼神的威慑之下,人们不敢胡作非为,天下才可大治。“(三代圣王)率天下之万民以尚尊天、事鬼、爱利万民,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至今不已”[30](P69)。因此,《论语》编纂时罕言鬼神,未言神道设教,目的是不让人们将儒墨混为一谈,同时让人们摆脱鬼神观念的支配,将精力放在现实的人生中,靠人为努力推进社会进步。
由于社会动荡不安,违背礼法者增多,严刑峻法遂产生,“周衰刑重,战国异制”。墨家将法令的合理性归于上天,认为鬼神保障了刑罚的执行力。为了让大家都能“兼相爱”“交相利”,墨子提出要“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30](P153)。墨家学派内部纪律严格,墨家成员还必须完全听命于集团首领“巨子”的命令,巨子对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权力,即使做官,也必须严守墨家纪律,并向团体交纳一定的俸禄。这与儒家学派宽松的风气截然相反。儒家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P11),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当政者要修养德行,率先垂范,百姓心悦诚服地效仿。而墨家虽然也认可德行,但是更注重外在的威逼利诱,特别是刑罚的威吓。这与儒家思想大相径庭,故而《论语》中慎谈刑政。
简言之,为了凸显儒家思想的特点,廓清儒墨之别,《论语》编纂时对两派“似同而实异”的内容加以删减,使得两派思想判若云泥,不至于混淆。
其四,对内增强孔门凝聚力。颜回是孔门众望所归的衣钵传承人,可惜早亡。孔子去世后,为了维系孔门,有若曾被推举为儒家的带头人,不久即因不能服众而被赶下台,孔门后学遂分崩离析。“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6)对于韩非子“儒分为八”的问题,学界有不同看法,吴龙辉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八派不是同时并存的,而是“孔子死后在孔门后学争正统的斗争中先后涌现的以孔子真传自居的八大强家”。参看吴龙辉:《原始儒家考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08页。。孔门后学相继离鲁,儒家衰落,“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31](P1159)为了传承师说,凝聚孔门,阐明儒家大义,部分弟子合力编纂《论语》。
总而言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动,儒墨两家学派关系紧张,儒家思想在孔门后学的重构下,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画卷。然而,孔子至孟子之间的史料多未传世,不能详知。幸运的是,上博简使我们得以管窥画卷一角。《论语》的成书极其复杂,今本《论语》除了七十子的编纂外,还有汉儒的删订,几经辗转,历时几百年,具体难以详知,更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早期儒学的传承丰富而复杂,《论语》编纂者是孔门后学的部分弟子,代表着早期儒学思想重构中的一个面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论语》不能涵括孔子的所有思想。如果这一推测无误,可以推进我们对早期儒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