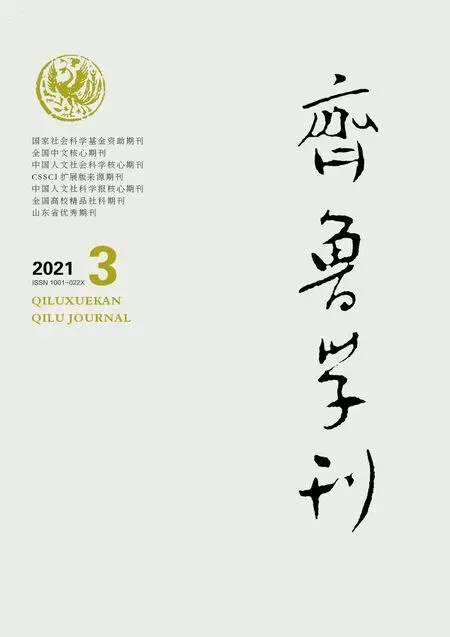《红楼梦》中的馈赠与回报
陈庆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日常生活中的馈赠,既涉及馈赠一方,也涉及接受馈赠的一方,而不同的馈赠者和不同的受馈赠者,引发了馈赠和回报的多样性。《红楼梦》在深入把握不同馈赠者和受馈赠者微妙差异的基础上,写出了人格类型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展现了社会场景的重新组合和社会生活的微妙变动,精彩纷呈,大有深意。
一、主动馈赠关联的两种人格类型
《红楼梦》中的馈赠行为,从馈赠一方来说,可大体分为两种:主动馈赠和应人之求而馈赠。在主动馈赠者中,最为抢眼的是薛蟠、宝钗兄妹。薛蟠是出了名的“呆霸王”“滥情人”,宝钗则是出了名的涵养好、会做人,这样天差地别的一对兄妹,却又同样热心于向他人赠送钱物;虽然同是主动馈赠,其馈赠动机和馈赠方式却又迥然相异。
先说作为主动馈赠者的宝钗。宝钗不止一次馈赠他人钱物,而对湘云的馈赠留给读者的印象尤深。在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大观园中开始有了诗社。兴高采烈的湘云提出“先邀一社”,做个东道,众人都兴奋地答应了。大大咧咧的湘云似乎没有意识到,做东是要花钱的,倒是细心的宝钗替她有些担心:“既开社,就要作东。虽然是个玩意儿,也要瞻前顾后,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后方大家有趣。你家里你又做不得主,一个月统共那几吊钱,你还不够使;这会子又干这没要紧的事,你婶娘听见了越发抱怨你了。况且你就都拿出来,做这个东也不够。难道为这个家去要不成?还是和这里要呢?”一席话提醒了湘云,让湘云不免踌蹰起来。这时候,宝钗适时地提出了自己的馈赠方案:“这个我已经有个主意了。我们当铺里有个伙计,他家地里出的好螃蟹,前儿送了几个来;现在这里的人,从老太太起,连上屋里的人,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前日姨娘还说:‘要请老太太在园里赏桂花吃螃蟹。’因为有事,还没有请。你如今且把诗社别提起,只普同一请,等他们散了,咱们有多少诗做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说,要他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再往铺子里取上几坛好酒来,再备四五桌果碟子,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呢?”湘云听了,心中自是感服[1](P456)。这一次馈赠,据刘老老粗略计算,至少花了二十多两银子[1](P474-475)。
一般说来,主动馈赠他人钱物,虽是热心快肠的好事,却也不能贸然行事。理由很简单:那个需要馈赠的人,可能是一个自尊心容易受到伤害的人。所以,馈赠方在表达其馈赠意愿时,如果不充分顾及对方的自尊心,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方式,而是率意而行,极易给人以食嗟来之食的感觉。人是这样一种生命存在:他不仅有物质的需求,也有心理的需求。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为了满足物质的需求,可以置自尊心于不顾;但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为了保持尊严,不仅可以放弃物质利益,甚至可以放弃身家性命。在需要馈赠的人中,当然既有前者,也有后者。《孟子》中那个断然拒绝食嗟来之食的人,就是后一类人的范本。
“世事洞明皆学问”,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足够的人生经验,能否以恰当的方式馈赠他人就是尺度之一。比如《红楼梦》第一回,写甄士隐让贾雨村体面地接受馈赠,就展现了一个好的馈赠方应有的风度。甄士隐赏识贾雨村抱负不凡,也早知贾雨村境况潦倒,需要馈赠,却迟迟没有说出馈赠意愿。不是不愿馈赠,而是怕伤了贾雨村的脸面。所以,一直要等到两人开怀畅饮,“雨村饮干,忽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挂名,只是目今行李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能到得——’”,士隐不等雨村说完,当即表示愿“代为处置”[1](P9)。甄士隐之所以选在开怀畅饮的场合,且要等贾雨村开口才说出馈赠意愿,就是怕唐突了贾雨村,有小看人之嫌;之所以“不待说完”,立即接上话头,就因为这才足以显示他“久有此意”,他是看重贾雨村才慷慨提供馈赠的。馈赠人让受馈赠方有被看得起的感觉,这是一种处事的境界。
甄士隐是个中年人,他在馈赠贾雨村时所显示的练达与通透,虽令读者心仪,却不会感到惊讶。与甄士隐相比,宝钗的那种处事技巧,不仅令读者心仪,而且有些惊讶,因为宝钗还那么年轻。宝钗确实年轻,也就是十四五岁而已。比起同龄人来,宝钗的成熟常常超出读者的预期。这一方面是由于她的经历,父亲的早逝和哥哥的糊涂使她过早地在家里扮演了顶梁柱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她的自律,她好像总在提醒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大家都赞许的好人。好人通常都是好相处的,但如果还想“扬名立万,那就一定要靠更为重要的美德或长处”[2](P65)。说话说到别人心里去,做事做到让别人打心眼里高兴,都是必要的前提。宝钗善于观察生活,对各色人等都有深切的了解,她的“会做人”的处事技巧就是在努力做好人的过程中养成的。
馈赠湘云是宝钗处事技巧的一次精彩演示。在馈赠湘云之前,她和湘云已是无话不说的朋友,第三十二回湘云曾私下里对袭人说:“我天天在家里想着,这些姐姐们,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是没妨碍的!”[1](P385)正因为宝钗已是湘云最信任的“姐姐”,她才会主动提出馈赠湘云,否则她是不会这样做的。尽管如此,宝钗也没有忘记补上一句:“我是一片真心为你的话。你可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们两个就白好了。你要不多心,我就好叫他们办去。”湘云忙笑道:“好姐姐!你这么说,倒不是真心待我了。我凭怎么糊涂,连个好歹也不知,还是个人吗!我要不把姐姐当作亲姐姐待,上回那些家常烦难事,我也不肯尽情告诉你了。”[1](P456)这里,宝钗对湘云的体贴、湘云对宝钗的信任以及两人之间的亲密,都写出来了。宝钗比湘云大不了多少,可湘云对她的依恋是真的像妹妹依恋姐姐一样,其原因在于,宝钗真有做姐姐的范儿。
宝钗的这种范儿不仅表现在馈赠湘云一事上,也表现在她对宝玉、黛玉等人的体贴和关心上。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之后,宝钗来探望,特意带来了一丸散瘀血热毒的药,又叮嘱袭人:宝玉“要想什么吃的玩的,悄悄的往我那里只管取去,不必惊动老太太、太太、众人,倘或吹到老爷耳朵里,虽然彼时不怎么样,将来对景,终是要吃亏的”[1](P406)。何以要袭人悄悄往宝钗那里去取“吃的玩的”,贾府里又不缺这些东西?盖宝玉挨打,就因为在贾政看来,这个儿子不求上进,而“流荡优伶”“荒疏学业”[1](P399),倘挨打之后还讲究“吃的玩的”,一旦让贾政知道了,是不会有宝玉的好果子吃的。宝钗既体贴宝玉,又留意到不让贾政知悉,她的思虑之周全,是别的女孩子比不上的。
第四十五回还写到了宝钗对黛玉的呵护。宝钗和黛玉曾经相互疑忌,第三十回之前,宝玉和黛玉的好几次吵嘴,都是因为黛玉放不下宝钗那个可以和宝玉的玉相配的金锁;而第三十回宝钗对于宝玉的冷嘲,即“宝钗借扇机带双敲”,其实也是在敲打黛玉。一段时间里,钗、黛两人仿佛成了不能共处的情敌,但这种紧张关系不久就结束了。第三十二回,当黛玉确切知道,宝玉仅仅认她一个人为知己后,黛玉不再跟宝玉争吵,不再计较宝玉跟宝钗的交往。在黛玉看来,宝玉虽依然与宝钗亲密,但那不是知己之情,因而也不必在意。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一向被视为钗、黛关系的分界线。在这一回之后,两个年龄相仿的女孩,成了极其要好的闺蜜,即《红楼梦》第四十五回所说的“金兰契”。宝钗对黛玉的馈赠就是在两人已极其要好的背景下发生的。
黛玉犯了旧疾,宝钗提醒她需要吃燕窝粥加以调补。当黛玉感叹:“虽然燕窝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了,每年犯这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那些底下老婆子丫头们,未免嫌我太多事了。”[1](P559-560)宝钗并没有接着黛玉的话头,立刻就说愿意送燕窝粥给她,而是先把“同病相怜”的姐妹之情说足了,才仿佛不经意地提到了这个意思:“我明日家去,和妈妈说了,只怕燕窝我们家里还有,与你送几两。每日叫丫头们就熬了,又便宜,又不惊师动众的。”[1](P560)宝钗之所以没有单刀直入,而是绕了一个大弯,意在给黛玉一种感觉:这不是劳力费心的施舍,而是姐妹之间的举手之劳。盖黛玉曾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而她的母亲贾敏,据王夫人说,那种大家闺秀的范儿,王夫人自觉远为逊色,由此可以想见,当年黛玉的境遇是何等优越。这样一个女孩,一旦由掌上明珠沦为寄人篱下,自尊心尤易受到伤害。如果宝钗在成为黛玉的知交之前提出馈赠黛玉,很可能被视为优越感的显示。宝钗以“同病相怜”“举手之劳”作为馈赠理由,才是黛玉愿意接受的。黛玉后来总是把宝钗当作姐姐,如同湘云把宝钗当作姐姐一样,这是一个契机。
从宝钗对湘云、黛玉的馈赠可以看出,在同龄人中,宝钗的姐姐范儿确实有一种魅力,即使是像黛玉这样一个心思细腻的女孩,也心悦诚服,乐意接受这位姐姐给予的体贴和照料。与“会做人”的宝钗相比,同样是主动馈赠他人,“呆霸王”薛蟠却是另一种做派。
薛蟠和宝钗是一对兄妹,处世风格却迥然相异。宝钗馈赠的都是和她关系亲密的人,其馈赠常与友情相伴;薛蟠馈赠的人,却很少是有深交的,几乎每一次馈赠都有利诱的嫌疑。宝钗馈赠朋友的结果,是友情更加深厚;薛蟠利诱他人的结果,往往像完成了一桩荒唐的交易。薛蟠以为,只要他舍得花钱,没有人不愿跟他成交。他的混账逻辑和莽撞性格,常常令读者忍俊不禁。
薛蟠曾给了金荣不少馈赠。第十回,金荣的母亲胡氏训斥金荣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不在那里念书,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了?那薛大爷一年也帮了咱们有七八十两银子。”[1](P118)这每年七八十两银子,《红楼梦》里没有明说是薛蟠主动给的,还是金荣伸手要的,但从相关情节来看,应是薛蟠的主动馈赠。第九回有这样两段叙述:“原来薛蟠自来王夫人处住后,便知有一家学,学中广有青年子弟,偶动了‘龙阳’之兴,因此也假来上学读书,不过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白送些束脩礼物与贾代儒,却不曾有一点儿进益,只图结交些契弟。谁想这学内的小学生,图了薛蟠的银钱穿吃,被他哄上手了,也不消多记。”[1](P110)“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爱东,明日爱西,近来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丢开一边;——就连金荣也是当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见弃了金荣;近日连香玉亦已见弃。”[1](P111-112)所谓“被他哄上手了”,所谓“见弃”于薛蟠,正见得薛蟠是主动的一方,被哄上手的当然是被动的一方。他今日喜欢这个,明日喜欢那个,那些贪图物质利益而不顾惜体面的人,一再让薛蟠得逞,他也因此而对生活有了他那套混账看法。
薛蟠没有想到,世上的人并不都是金荣一类。有贪图物质利益而不顾惜体面的人,也有为了尊严而唾弃物质利益的人,甚至有因为尊严受到亵渎而大打出手的人。人与人的巨大差别,构成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薛蟠习惯了与金荣等人打交道的那种方式,他也用这种方式去和柳湘莲打交道,当然免不了碰壁。柳湘莲何许人也?那是连贾宝玉也肯结为知交的人。柳湘莲的社会地位自不能与宝玉相提并论,但其人品之不俗,却足与宝玉比肩而立。这样一个人,岂容薛蟠亵渎和玩弄?薛蟠之所以惹恼了柳湘莲,就是因为他故伎重演,用了玩弄金荣的手段来跟柳湘莲打交道。第四十七回“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写的就是这事。薛蟠开口就拿“做官发财”来引诱柳湘莲,柳湘莲当然“恼恨”;而柳湘莲对薛蟠的痛打,也从反面说明了馈赠方尊重受馈赠方的重要性。或者说,一个甘于在人格上自轻自贱的人,是不配接受馈赠的;一个仅仅馈赠那些自轻自贱者的人,其实也小看了自己。
二、应人之求而馈赠:荣国府三代主妇的慈善之举
寻求馈赠的人,有的是熟人,有的不是熟人。有趣的是,在《红楼梦》中,这两种不同的情形,都跟刘老老有关。
《红楼梦》第六回“刘老老一进荣国府”,写的是一个贸然寻求馈赠的刘老老。她的女婿王成,其祖上曾和王熙凤的祖父连过宗。后来,他家从城里搬到了乡下,把刘老老接来过活。这年秋末冬初,狗儿因家贫而气恼,刘老老情急之下,遂舍着老脸去贾府求告。一家人在商量求助于贾府一事时,刘老老道:“只是许多时不走动,知道他如今是怎样?这也说不得了!你又是个男人,这么个嘴脸,自然去不得。我们姑娘年轻的媳妇儿,也难卖头卖脚的,倒还是舍着我这副老脸去碰碰。果然有好处,大家也有益。”[1](P70)刘老老的口气,明摆着是去撞大运。一家人处于急需援手的状态,病笃乱投医,与贾府并没有足够的信任关系,怎么能做太大的指望呢?
刘老老带着外孙来到贾府,见到的唯一主子是当家少奶奶凤姐。能不能得到馈赠,就看凤姐的意思了。此前凤姐从来没有见过刘老老,也不知道刘老老究竟能跟自己扯上什么关系。她让周瑞家的去问王夫人,王夫人说:“原不是一家子;当年他们的祖和太老爷在一处作官,因连了宗的。这几年来不大走动。当时他们来了,却也从没空过的;如今来瞧我们,也是他的好意,别简慢了他。要有什么话,叫二奶奶裁夺着就是了。”凤姐这才明白王成祖上与其祖父的瓜葛,不禁说了一句:“怪道既是一家子,我怎么连影儿也不知道!”[1](P78)看得出来,凤姐与刘老老之间,其实挺疏远的。
尽管关系疏远,在明白了刘老老的求助意愿后,凤姐还是送了刘老老二十两银子。对于贾府来说,二十两银子是一个不大的数目,但对于刘老老而言,那可是一笔不菲的资产,所以刘老老“喜的眉开眼笑”。临走时,凤姐还嘱咐了一句:“改日没事,只管来逛逛,才是亲戚们的意思。天也晚了,不虚留你们了。到家里该问好的都问个好儿罢。”[1](P79)这里,凤姐说的倒不是纯属敷衍的客套话。
《红楼梦》第三十九回,刘老老二进荣国府,因为已是熟人,可以坦然地以亲戚身份见面了。她带来了许多新鲜瓜果蔬菜,一见平儿的面,就说:“家里都问好。早要来请姑奶奶的安、看姑娘来的,因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石粮食,瓜果菜蔬也丰盛,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并没敢卖呢,留的尖儿,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腻了,吃个野菜儿,也算我们的穷心。”[1](P474)刘老老的这几句话,可别小看,它表明,现在的刘老老,已经不是一个贸然来贾府求助的人,而是来看亲戚的,虽然一个是乡下的穷亲戚,一个是城里的富亲戚,但确乎有了亲戚的情分。所以,贾母在和刘老老聊天的时候,一口一个亲戚不断:“你们这些老亲戚,我都不记得了。亲戚们来了,我怕人笑话,我都不会。”“今日既认着了亲,别空空的就去。不嫌我这里,就住一两天再去。我们也有个园子,园子里头也有果子,你明日也尝尝,带些家去,也算是看亲戚一趟。”[1](P476-477)贾母还给了刘老老一个极亲热的称呼:“老亲家。”
刘老老这次来,并没有明确说出寻求馈赠的意思。不过,既然是亲戚,又是乡下来的,贾府自有其“惜老怜贫”的一贯做派。所以,这一次,刘老老的收获真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一是成了贾母的座上宾,参与了大观园中的饮宴游艺活动,世上那些没见过、没吃过的东西,这次都见到了、吃到了;一是得到了来自贾府不同人等的馈赠,除了王熙凤的外,还有贾母、王夫人的,连宝玉也送了一份礼物,平儿、鸳鸯等也各有表示。王夫人的礼物比较简明,且为刘老老一家做了长远规划:两包银子,每包五十两,共是一百两,“或者做个小本买卖,或者置几亩地,以后再别求亲靠友的”[1](P515)。有了这笔资产,就算得乡下的一等人家了。王熙凤的礼物则以品种多样见长,平儿一一拿给刘老老瞧,说道:“这是昨日你要的青纱一匹,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实地月白纱作里子。这是两个茧绸,作袄儿裙子都好。这包袱里是两匹绸子,年下做件衣裳穿。这是一盒子各样内造小饽饽儿,也有你吃过的,也有你没吃过的,拿去摆碟子请人,比买的强些。这两条口袋是你昨日装果子的,如今这一个里头装了两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难得的;这一条里头是园子里的果子和各样干果子。这一包是八两银子。——这都是我们奶奶的……”[1](P515)这一节既写出了凤姐馈赠之丰厚,更写出了她对刘老老的那种亲戚情分。当刘老老不好意思带那么多礼物走时,凤姐又笑道:“也没有什么,不过随常的东西。好也罢,歹也罢,带了去,你们街坊邻舍看着也热闹些,也是上城一趟。”[1](P514-515)言谈之间,已没有了富贵贫贱的隔阂。
贾母的礼物,是由鸳鸯转告刘老老的:“这是老太太的几件衣服,都是往年间生日节下众人孝敬的。老太太从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没穿过的,昨日叫我拿出两套来送你带了去,或送人,或自己家里穿罢。这盒子里头是你要的面果子。这包儿里头是你前儿说的药,梅花点舌丹也有,紫金锭也有,活络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样是一张方子包着,总包在里头了。这是两个荷包,带着玩罢。”[1](P517-518)同样是送礼物,与王熙凤相比,贾母显示的是另一种身份。那各色名贵的保健药品,不光王熙凤不大可能有,连王夫人也未必那么齐全。
难得的是宝玉也送了刘老老一份礼物:成窑钟子[1](P518)。其实,这个成窑钟子并不是宝玉的,而是妙玉的。因为刘老老用过这个茶杯,妙玉嫌脏,不要了。宝玉征得妙玉的同意后,以自己的名义送给了刘老老。读者印象中的宝玉,似乎只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连他的奶妈李嬷嬷也不受他的待见。其实,宝玉不喜欢那些婆子,是因为婆子们的做派令他讨厌。他对刘老老确有几分喜欢,大概因为刘老老竟有本事信口开河讲一些宝玉喜欢的话,待人接物也机智有趣。
贾母、王夫人和凤姐,这是贾府的三代主妇。三个人的个性和经历大为不同,但在馈赠刘老老这件事上,却显示出了一以贯之的厚道。其中,凤姐的所言所行让人看到了她的可爱之处,而王夫人也展现了她性格中让人敬重的一面。
王熙凤是《红楼梦》中典型的强势人物。她的心机和毒辣,她的冷酷和贪婪,她的逢场作戏和霸道,在“协理宁国府”“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变生不测凤姐泼醋”“逼死尤二姐”等情节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她“嘴甜心苦”,“明里一盆火,暗里一把刀”[1](P853),其狠毒心肠和狡诈手段常令读者感到恐惧和厌恶,以致许多人都没有留意到,凤姐也有她的人情味。
与对刘老老的热心馈赠形成呼应,王熙凤对邢岫烟的体贴也不失为佳话。第四十九回曾这样描写凤姐与岫烟的关系:“邢夫人便将岫烟交与凤姐儿……凤姐儿亦照迎春分例,送一分与岫烟。凤姐儿冷眼敁敠岫烟心性行为,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样,却是个极温厚可疼的人。因此凤姐儿反怜他家贫命苦,比别的姊妹多疼他些。”[1](P607)第五十一回,平儿未跟凤姐商量,就拿了凤姐一件“半旧大红羽纱的”衣裳送给邢岫烟,是因为凤姐怜贫惜弱、看重岫烟的一面早已为平儿所了解。较之邢夫人的一味啬刻,凤姐无疑要高出几个档次。
王夫人给读者的印象有其恶劣的一面,尤其是金钏儿和晴雯两个女孩的早逝,她都是“罪魁祸首”。但王夫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坏人”,毋宁说,王夫人确有许多长处,从不吝啬就是其长处之一。金钏儿死后,她给了金钏儿父母一大笔抚恤金,又把金钏儿的月例一并给了金钏儿的妹妹玉钏儿。这样一些举动,与邢夫人、赵姨娘等人相比,真可算是天壤之别。这次给刘老老的馈赠,白花花的一百两银子,出手是挺大方的。
作为大观园的保护人,贾母让许多读者打心眼里喜欢。她看出晴雯的聪明能干,把她放在宝玉身边,正好对了宝玉的心思。“勇晴雯病补孔雀裘”一节,如果当成宝玉的回忆文字来看,更有一种深情和悲怆的意味,也是对贾母眼力的认可或表彰。在贾府被抄之后,“散余资贾母明大义”,足以见出她的深谋远虑,也表明了一个事实:平日那个热衷于享乐、总是带着孙儿孙女们吃酒行令的老太太,其实成竹在胸,对人生和家族自有其擘画。她溺爱宝玉,当然是其短处,但宝玉的行事可爱,乃是其溺爱的前提,要是宝玉和贾环一个德性,贾母无疑会持另一种态度。贾母的为人处世,有她一以贯之的分寸。她送给刘老老的那些名贵保健药品,真能体现“老寿星”的气度。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馈赠刘老老一事上,贾府三代主妇,尽管其性格和人格差异巨大,其和善厚道却大体一致。“慷慨或慈善,驱使我们做的那些普受赞许的好事,和感激所推荐的责任相比,更是自由随意,也更无法强求。”[2](P95)正因为慈善是无法强求的,所以贾府三代主妇对于刘老老的馈赠更显得难能可贵。
贾府的这种家风,即所谓的贵族范儿,构成了贾宝玉不可或缺的生活环境。
三、受馈赠方的回报与社会生活的变迁
在馈赠方与受馈赠方的互动关系中,受馈赠方也是不容忽略的。
从馈赠方的馈赠意愿来看,受馈赠方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馈赠方眼中卓荦不凡的人,馈赠方之所以提供馈赠,是因为看重这个人;一种是馈赠方眼中身处困境的人,馈赠方之所以提供馈赠,是因为同情这个人。一般说来,前一类受馈赠方,往往更受人们瞩目。
东晋郭澄之的《郭子》一书,记载了刘道真的一件轶事。安北将军刘道真年轻的时候,困顿沦落,捕鱼为生。他擅长唱歌和吹口哨,听的人常常流连忘返。有个年老的妇女,看出他是个有本事的人,加上喜欢他的歌声和啸声,于是炖了猪肘给他吃。道真一口气吃完,却并不道谢。老妇人见他还未吃饱,又炖了一只猪肘给他,道真吃了一半,另一半还给了老妇人。后来,道真担任了吏部郎,负责官员的遴选,老妇人的儿子正做小令史,道真便越级提拔了他[3](P184)。与老妇人的两只猪肘相比,道真的报答,真的可以用“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来形容。刘道真的做法表明,那些才具不凡而受恩不谢的人,他们的酬报是不能用世俗的尺度来衡量的。
在《红楼梦》中,与刘道真相仿的是贾雨村。他一出场就给人抱负不凡之感。那年中秋佳节,对月有怀,想到平生抱负,未能施展,有“玉在匵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之吟;酒添豪兴,又口占一绝:“时逢三五便团圞,满把晴光护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1](P8-9)甄士隐以“飞腾之兆”许之,他本人也同样以此自期。所以,当甄士隐以“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1](P9)助其行色时,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这一细节,显示了贾雨村以豪杰自负的心态。
只是,贾雨村对甄士隐的回报却令人大跌眼镜。靠了甄士隐的馈赠,贾雨村上京赶考,中了进士,后来补了金陵应天府知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一边是抢女杀人的薛蟠,一边是无辜被殴致死的小乡绅之子冯渊,而所抢之女即甄士隐之女英莲。这件案子并不复杂,难的是如果他秉公办事,触犯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虽然报答了恩人甄士隐,却可能会葬送前程。于是他听从了门子的建议,胡乱判了此案,“便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之言寄去”[1](P47)。他之所以“疾忙修书”,无非是赶紧向薛蟠的舅父王子腾邀功。这里,支配贾雨村的是关于个人得失的盘算,而不是知恩图报的心理。
贾雨村对贾府的回报尤其令人悚然。《红楼梦》第三回,贾雨村因给黛玉做过家庭教师,黛玉的父亲林如海把他推荐给自己在朝廷做官的二舅子贾政:“这贾政最喜的是读书人,礼贤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风,——况又系妹丈致意,因此优待雨村,更又不同:便极力帮助,题奏之日,谋了一个复职,不上两月,便选了金陵应天府,辞了贾政,择日到任去了。”[1](P26)贾政是个君子,他对贾雨村的帮助,确乎是尽其所能,贾雨村则是擅长“机变”的角色。贾府得势时,贾雨村也曾如蝇逐膻,只要有机会就造访贾政,且总要请宝玉叙谈一番,意在与荣国府的这位继承人保持亲密关系。而一旦贾府失势,他就不惜落井下石,以图自保。贾府被抄之前,先是被御史参奏,“主子还叫府尹(贾雨村)查明实迹再办。你说他怎么样?他本沾过(宁荣)两府的好处,怕人说他回护一家儿,他倒狠狠的踢了一脚,所以两府里才到底抄了。你说如今的世情还了得吗”[1](P1381)。这里,贾雨村昧着“良心”行事,支配他的仍是关于个人得失的盘算,而不是知恩图报的心理。
说到对贾府的回报,与贾雨村适成对照的是刘老老。
一进贾府的刘老老是个有几分胆怯的乡下老妇人。她的胆怯是有缘由的:与贾府主子的地位悬殊太大,又是贸然求助,心里不免有几分忐忑不安。给读者的感觉,也是怜悯与轻视参半。
二进贾府的刘老老扮演了一个“女清客”的角色,让人联想到《金瓶梅》里的“篾片”应伯爵。西门庆之所以跟应伯爵亲近,就因为所有陪他玩的人中,谁也不如应伯爵有趣。应伯爵的人生信念是:“如今时年尚个奉承”[4](P1037),“你若撑硬船儿,谁理你?”[4](P1038)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拿自己混迹江湖的本事陪西门庆寻欢作乐,效果自然非同一般。据玳安说,不管西门庆有什么烦恼事儿,“只他到,略说两句话儿,爹就眉花眼笑的”[4](P860)。他是《金瓶梅》中数一数二的清客或“篾片”。
应伯爵是清客,是“篾片”,是陪人玩乐的帮闲。贾府的一群小姐、奶奶和丫鬟,也是这样看刘老老的。在第四十回,鸳鸯说:“天天咱们说外头老爷们:吃酒吃饭,都有个凑趣儿的,拿他取笑儿。咱们今儿也得了个女清客了。”[1](P488)鸳鸯称刘老老为“女清客”,是对二进贾府的刘老老的定位。
“女清客”刘老老没读过什么书,却生来有些见识,谈吐风趣:“刘老老吃了茶,便把些乡村中所见所闻的事情说给贾母听,贾母越发得了趣味”,“彼时宝玉姐妹们也都在这里坐着,他们何曾听见过这些话,自觉比那些瞽目先生说的书还好听”[1](P477-478)。为了讨贾母等人喜欢,刘老老任凭凤姐、鸳鸯捉弄,不仅一点儿不恼,居然还懂得主动配合,故意说些呆话,或者自嘲。贾母让刘老老戴花,凤姐就“把一盘子花,横三竖四的插了一头”,引得贾母和众人“笑的了不得”。刘老老不失时机地自嘲说:“我这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今儿这样体面起来!”“我虽老了,年轻时也风流,爱个花儿粉儿的,今儿索性作个老风流!”[1](P484)刘老老的“清客”角色,扮演得十分到位。
一般说来,“清客”的人品都不大靠得住。《金瓶梅》中的应伯爵,在西门庆纵欲身亡之后,转眼就投靠了他人,还把西门家的内幕泄漏给新主子,以换取好处。读过《金瓶梅》的人,也许会拿应伯爵来套刘老老。而《红楼梦》却郑重地提醒读者:那个一进贾府时怯生生的刘老老,那个二进贾府时被视为清客的刘老老,当她三进贾府时,却是一个令人敬重的侠客——一个始终记得别人的恩情,并且寻找机会来回报的人。
刘老老的知恩图报与贾雨村的忘恩负义真有天壤之别。贾府败落的时候,贾雨村千方百计掩盖他与贾府的关系,而刘老老口口声声说的都是贾府对她女婿一家的恩德。她三进贾府,一见面就指着青儿对凤姐说:“我们若不仗着姑奶奶”,“他的老子娘都要饿死了。如今虽说是庄家人苦,家里也挣了好几亩地,又打了一眼井,种些菜蔬瓜果。一年卖的钱也不少,尽够他们嚼吃的了。这两年,姑奶奶还时常给些衣服布匹,在我们村里算过得的了”[1](P1451)。一个总是感念别人恩德的人,饮水思源,虽然不一定有报答的能力,但报答的愿望是一直放在心上的。如刘老老所说,他们一家,总是牵挂着贾府的兴衰与哀乐。
刘老老也许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她居然可以真的给贾府实实在在的帮助,而不只是有心无力。贾府败落后,骨肉相残,巧姐的几个“狠舅奸兄”,拟把她卖给外藩王爷做妃子。情急之中,幸亏刘老老设计,将她救往乡下。刘老老的智谋,来自于她听说过的民间曲艺,与一个乡村老妇的身份高度吻合。而她的知恩仗义,不计风险,则让读者对这个乡村老妇刮目相看。贾雨村饱读诗书,却只知为个人的得失盘算。刘老老以一介村妇,却仗义行侠,风骨铮铮。也许,侠行义举,本来就是中国民间的美德。刘老老在让读者刮目相看的同时,也让读者对那些读书不多的人刮目相看。
贾雨村和刘老老对贾府的回报,当然是一种个人行为,却引发了社会生活的显著变动。贾雨村促成了贾府的被抄,加速了贾府的衰败,使其跌入出卖田产的境地:“贾琏无计可施,想到那亲戚里头,薛姨妈家已败,王子腾已死,余者亲戚虽有,俱是不能照应的,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将地亩暂卖数千金,作为监中使费。贾琏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见主家势败,也便趁此弄鬼,并将东庄租税也就指名借用些。”[1](P1366)刘老老则改变了巧姐的命运,她的义举使巧姐避免了沦为骨肉相残的牺牲品,也使得巧姐有机会重回荣府,父女散而复聚,正所谓“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济村妇,巧得遇恩人”[1](P59)。在《红楼梦》中,馈赠和回报,不是简单的人情往来,而是承载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结语
馈赠方和受馈赠方,是依据经济往来情形划分出的两类人物。他们的人格,不因为是馈赠方就一定高贵,也不因为是受馈赠方就一定卑贱。《红楼梦》的馈赠书写,既着眼于馈赠一方,写出了不同的馈赠动机和馈赠方式,也着眼于接受馈赠的一方,写出了不同的回报动机和回报方式。而林林总总的馈赠和回报,不仅关联着复杂的人格类型和人际关系,也引发了社会场景的重组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其内容之深厚博大,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