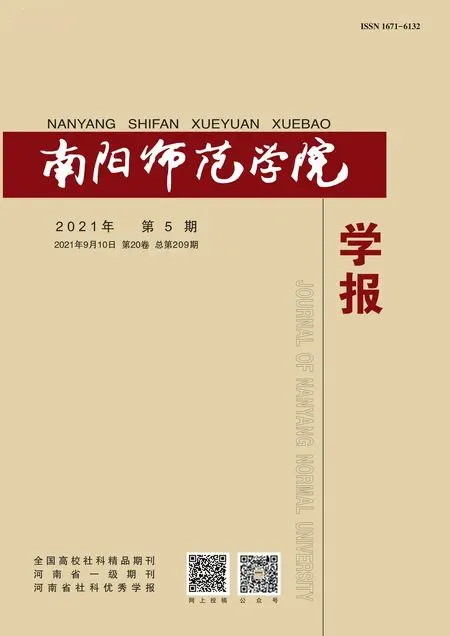再造传统:70余年来词论研究的演变与启示
付 优
(苏州大学 博物馆,江苏 苏州 215006)
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的发展,尤其是新世纪20余年来的发展,词论研究从新旧交融走向蓬勃兴盛,文献整理成果突出,理论方法逐渐更新,学术范式不断变革,形成了稳定成熟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格局。回顾与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词论研究的发展、演变和特点,对于全面审视词学学科的影响、把握词学研究的走向、推动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词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下,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被逐步强化,“重思想,轻艺术”的批评取向和“重豪放,轻婉约”的审美标准得以盛行;第二阶段系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末,随着社会文化氛围的复苏与繁荣,过分注重社会功能的词学批评标准得到反思与纠正,词学研究拨乱反正,呈现出复苏并初步繁荣的景象;第三阶段系21世纪初至今,互联网与大数据为词学研究与词学批评提供了新的工具与新的方法,而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介入又极大地扩展了词学批评的视野,词论研究进入了多样化的新时期。
一、阐释“主流”:探索时期(1949—1976)的词论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词学研究和词学批评受到“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思想上的人民性与阶级分析意识,方法上的“古为今用”和现实主义成为词学批评的主要标准。研究群体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作为词学批评的准绳,尝试以唯物史观来重新评价词作、词派与词史,由此形成了深具时代烙印的研究格局。在此过程中,人民性问题、豪放婉约之争是持续时间较长、产生影响较大的讨论。
(一)两次词学论争与二李词的评价问题
这一时期最早引起关注的是两次大规模的词学论争,即关于李煜词、李清照词评价问题的大讨论。
有关李煜词的论争源于1955年8月28日詹安泰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上发表的《答陈培治同志》一文。作为词学爱好者,陈培治不满詹安泰在《学习苏联,改进我们的古典文学教学》中对李煜《虞美人》词的阐释,寄送文章给《文学遗产》刊物,提出李煜“奢侈淫乐的生活是建筑在残酷地剥削人民的基础上的”,其作品“是含有毒素的”,不应当进入“古典文学抒情的教材”[1]。詹安泰则认为,“人民性并不是这么机械地理解”,“(李煜)亡国后所表露出来的怀念故国的思想感情和南唐的人民的思想感情还是有共通之点的”,同时指出,“从‘唯成份论’或者单纯的阶级观点出发,以及一切反历史主义的论点,都是不正确的,是我们应该引为鉴戒的”[2]。
两篇文章刊发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游国恩、启功、林庚、李长之、吴组缃、余冠英、俞平伯、钱锺书、刘大杰、沈尹默等著名学者和众多诗词爱好者纷纷加入论战,围绕“李煜前期词是否具有人民性”“李煜后期词是否体现爱国思想”“千百年来李煜词为什么受到读者喜爱”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中文院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古典文学组等研究机构接连组织关于李煜词评价问题的讨论会,相关讨论稿整理后由《文学遗产》刊发。据《文学遗产》编辑部《关于李煜词的讨论》记载,至1956年9月,编辑部陆续收到30余万字有关来稿[3]。由于对“人民性”的内涵理解差异较大,学者们对李煜前后两阶段的生活和词作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评价。
有关李清照词评价问题的论争源于1958年9月出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55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该书将易安词视为“北宋形式主义的逆流”,其词作“引导人民走进她所描绘的灰色的罗网,从而削弱人们的生活斗志” 。1959年4月至1960年6月,围绕“李清照词是否有社会意义”“李清照词是否有爱国主义情感”等问题,仅《文学遗产》就集中刊登了16篇讨论文章。部分讨论者认为,李清照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家庭妇女,“既不能算是爱国主义的诗人,又不能代表人民的情感”[4],其前期词作“并无多少社会意义”[5],后期词作也“是一种比较低沉和消极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是一种哀鸣和挽歌似的作品”[6]。盛静霞则在《论李清照》中提出,易安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很多流离失所的人的痛苦心情”,“我们可以惋惜她在词里的思想感情没有在诗里表现得健康,但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她后期词的艺术力量”[7]。相关讨论一直延续到1963年,胡光舟、王淑明、黄盛璋、夏承焘、唐圭璋、沈祖棻、程千帆等学者先后撰文,引导论争走向深入。其间,王汝弼谈道,李清照“并非驯服的封建家长制的俘虏,并非祸国殃民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应声虫”,片面否定清照前期闺阁词作,指摘其“没有涉及当时的政治斗争”[8]的看法是武断的。
这一时期,两次大规模词学论争引发了众多词学爱好者的热情,许多读者写信投寄给报社,主动参与到词学讨论之中。如1955年9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刘乾所撰《评王瑶先生论“词”》。刘乾认为,《文艺学习》1954年12月所刊王瑶《词》一文存在不少自相矛盾之处。刘乾质疑王瑶对词体的音乐性和思想性关系的认识,主张词作中的“冶荡之音”缘于“士大夫阶级把劳动人民的创造变了质”,是“灵魂空虚、生活苍白的寄生阶级所需要的适应”[9]。同年9月18日,王瑶在《光明日报》刊登《答刘乾同志论词》。王瑶的回应主要阐明两点:一是《词》一文乃是“为了对爱好文学的青年介绍一些文学知识而写的”,仅针对词的一般形式特点;二是“词本管弦冶荡之音”并非专指词的文字所表现的内容,而是传统对词的音乐特质的看法[10]。这些有关词作鉴赏、词体特质、词风审美的讨论,客观上增进了大众对词体特质的理解。
(二)“豪放派”“婉约派”的评价问题
1962年2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胡云翼《宋词选》,产生了极大社会影响。该书选录74位宋代词人的296首作品,历年总印数已达200万册以上,从通衢大邑走向僻地边城,“大学中文系师生几乎人手一册”[11],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流通最广的宋词选本。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云翼就编选有《抒情词选》《故事词选》《清代词选》等7部词选,积累了丰富的选词经验,对历代选本及其体例得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胡云翼在《试谈唐宋词的选注工作》中提出:“宋词里面豪放和婉约两派分别体现了阳刚、阴柔之美,就艺术风格说,二者各有胜境,可是我们宁愿更多地推荐豪放派……我们必须依据马列主义观点和政治与艺术相结合的标准来评选唐宋词……以期达到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的目的。”[12]《宋词选》注重词作的注释和串讲,推崇豪放派词人词作,正是对这一选词宗旨和审美取向的具体实践。
总体上看,《宋词选》一书呈现出强烈的重思想轻艺术、重豪放轻婉约的选评倾向。在《宋词选前言》中,胡云翼描述了词体在两宋的发展历程及著名词人的风格特征,提出“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在词里形成了一支波澜壮阔的主流”,“与之相反,代表南宋士大夫的消极思想和个人享乐思想,在词坛里形成另外一支逃避现实、偏重格律的逆流”。因此,该选本主要“以苏轼、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作为骨干,重点提倡并选录南宋爱国词人的优秀作品”[13]。
与此同时,俞平伯在《文学评论》发表了《唐宋词选前言》。该文系俞平伯为1962年编《唐宋词选》所撰序言的前两部分。但《唐宋词选》最初只印刷了300本试印本,传播不广,后经过俞氏多年增补,直到1979年10月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唐宋词选前言》提出,与过去词论家、评家、选家所称的词史“正变”观念不同,“花间”范式远远不够“正”,“苏、辛、漱玉一路,本为词的康庄大道,而非硗确小径”,呼吁推动词体回归“广深”的道路,“来表现更丰富的革命生活”[14]。该文提倡文体进化观,推崇苏、辛词作的历史与社会意义,与胡云翼《宋词选》的编选宗旨有共通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胡云翼《宋词选》对“婉约派”词人的贬抑,在当时已经出现不同意见。1962年,万云骏发表《词话论词的艺术性》,主张婉约派的词“以离别相思、伤春伤别为主要内容,一般带着浓厚的感伤主义色彩”,“其表现手法,有时比较曲折而深婉,仓卒之间,不易领会其佳处,因此在某些文学史或某些论文中,有估价偏低的现象”[15]。次年,王季思在《文艺报》发表《词的欣赏》,强调“婉约派总的看来成就不及豪放派,却更多地表现了词的特点……这特点是从晚唐到宋初在词的长期创作过程中形成的”[16],同样反对全盘否定“婉约派”的词学贡献。这些意见虽未能在当时的学术界中赢得广泛认同,但已为20世纪80年代有关词派二分法问题的讨论唱响先声。
(三)老一辈词学名家与词的声、韵、情问题讨论
现代词学家施议对曾绘制《二十世纪词学传承图》,大致依据词人生年为序,以20年为一代,将100年间活跃于词学领域的名家排班列队。其中,出生于1875年至1895年间的刘永济等11人,被划归为第二代词学名家,出生于1895年至1915年间的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张伯驹等20人,被划归入第三代词学名家,他们共同组成了百年词苑的中坚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主流文化思潮影响下,这批声誉卓著的老一辈词学家有的自觉尝试搬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展开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全面清算,也有的遭历次“反右”“反修”“锄毒草”的“整风运动”波及,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基本退出学术坛站。词学研究的发展蒙受了极大损失,甚至一度趋于沉寂。整体上看,在动荡波折的政治学术思想裹挟中,老一辈词学名家对词之起源发展的系统审视,对作家作品的阐释重评,对词学资料的汇集整理,依然为词学研究做出了许多贡献。
以词的声、韵、情问题为例,龙榆生、张伯驹、刘永济就分别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和心得。1957年,时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古典文学教授的龙榆生连续发表了《试谈辛弃疾词》《谈谈词的艺术特征》与《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等数篇论文。其中,《谈谈词的艺术特征》反对词话家拈出片语只言、强分诗词曲文体疆界的行为,主张了解词的艺术特征,“该从每个调子的声韵组织上去加以分析,该从每个句子的平仄四声和整体的平仄四声的配合上去加以分析”,否则“是很难把‘上不似诗,下不类曲’的界限划分清楚的”[17]。该文的写作宗旨原本是“提供一般爱好读词者的参考”,但文章强调重视词作在思想上的继承性和创造性、在形式上的音乐性和艺术性,对我们今日研究词的艺术特征依然裨益良多。
1961年,张伯驹将《丛碧词话》油印成册,分送寿康(周汝昌)、罗继祖等好友。此书当年印量稀少,直至1981年经《词学》第1辑排印刊载,方才得以传播开来。《丛碧词话》共计91则,起自李太白,终至况周颐,详细探讨了词体起源、词史盛衰、词韵考究、词作版本等诸多问题,折中众说,时得真解。《丛碧词话》反对常州词派之刻意求索、遮蔽本意,主张通过考索词的声、韵、情来推究词意。如论史达祖《双双燕》词,反对戈载“其韵庚、青杂入真、文,究为玉瑕珠类”的批评,指出“宋人词用庚、青杂真、文者甚多,南人无论,如梅溪汴人亦如此”,主张“宋人词用韵当自有其习惯,颇同于乱弹剧之十三辙”[18]。整体上,该词话提倡从考察词作的选字用韵出发,强化评词释词的声学视角。
值得注意的,还有部分老一辈词学名家在词集自序、词学书札与读词心得中所保存的词苑轶事与词学观念。例如, 1949年,刘永济在武汉大学撰写《刘永济词集自序》,文中谈到昔时况蕙风曾引其参与海上沤社之绿樱花、红杜鹃分咏,沤社盟主朱祖谋激赏其词作“能用方笔”[19]。又如,1956年龙榆生撰写《与吴则虞论碧山词书》,以吴氏所著《花外集斠笺》为引,论及碧山词的艺术价值和历代接受情况。又如,1963年夏承焘发表《月轮楼读词记》7则,主要记录读词、填词与教学中的点滴心得,如批评梅村《病中有感》“末二句与上文不贯,且作放倒语,与全词悔艾之情亦乖背”[20]。这些序言、书札与心得,不但具有一定的词学理论价值,而且也是考察当时词人交游、词社活动的宝贵资料。
此外,1955年《人生》杂志发表饶宗颐《人间词话平议》。饶宗颐认为,王国维《人间词话》取境界论词,“虽有得易简之趣,而不免伤于质直,与意内言外之旨,辄复相乖”。《人间词话平议》主要针对“‘境界’一词的渊源”“以‘隔’为病非笃论”“伸北宋黜南宋为偏激之论”[21]等九个问题进行考证辨析。该文是香港地区第一篇研究王国维词学的论文,对香港此后的《人间词话》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赓续“模范”:转折时期(1977—2000)的词论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文艺界打碎了前一阶段“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精神枷锁,驳倒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错误认识,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简单化、片面化甚至庸俗化的解读,文艺研究亦随之呈现出勃勃生机。研究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强化宏观研究的呼声,提倡通过对文学的特征研究、规律研究和比较研究,深入地阐明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同时,对“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新三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等西方自然科学方法的引入,一度使“方法热”风靡文艺研究界,推动了意象分析、原型批评、叙事学、接受美学等新观念、新方法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结合。
(一)反思词学论争,形成新认识
本阶段有关词学论争的反思肇始于对稼轩词历史地位的再评价。辛弃疾是20世纪最“热”、受关注最多的宋代词人。20世纪60年代,围绕辛弃疾所镇压的是“农民起义”还是“地主武装”问题,学术界展开过激烈论争。有学者提出,不应该将辛弃疾视为“一个有良心、有干才的地方官”,其人创建“飞虎军”、扑灭茶商军,实际是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起义而效劳的行为。70年代中期,在极“左”思潮催生的“批儒评法”运动中,辛弃疾又被塑造为“法家代表人物”,被利用来揭橥“儒法斗争”中的法家路线。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研究者再次批判辛弃疾效忠于南宋王朝,参与“镇压农民起义”,“毫不犹豫地站在他出身的官僚地主阶级立场上,表现是恶劣的,思想是反动的”[22]。该文引发了对辛弃疾爱国思想的思辨,严迪昌、吴恩培等分别撰文批驳,反对“以今衡古”,将无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强加于历史人物。
1978年,刘乃昌在《关于评价辛弃疾的几个问题》中,详细论述了辛弃疾是否“尊法反儒”、如何评价辛弃疾抗战词、怎样认识辛词抗战爱国思想三个问题。文章指出,辛弃疾“和法家思想没有多少瓜葛”,他的思想“一方面同当时许多士大夫一样表现了儒、佛、道三教合流归宗于儒的倾向,一方面又存有自发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进步因素”。辛弃疾的抗战词“深深地根植于抗战御敌的现实土壤之上”,其贡献“就在于集中地反映了民族矛盾问题,深刻、动人地歌唱了抗战恢复这一重大主题”[23]。该文在“儒法斗争”的余波震荡下,深入总结有关辛词评价问题的词学论争,较早倡言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合理剖析辛词,在当时发挥了扫清思想迷雾的积极作用。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探讨苏轼词风的主体特征为源头,词学界出现了有关宋词“婉约派”与“豪放派”之分的大讨论。这场论争的核心问题有二:一是宋词是否存在“婉约”与“豪放”二派;二是究竟该如何评价宋词“豪放派”。论争中反对者多主张宋词从未形成“婉约”“豪放”两种风格流派,机械的“二分法”不足以概括宋词的历史发展;赞成者则多主张“婉约”“豪放”是宋词内容题材与艺术手法的两种倾向,能够高度概括词史发展的不同趋势。1983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组织首届词学讨论会,将这场论争更进一步地推向全国。
在这场论争中,首先引起较大关注的是词的“派”与“体”之争。1980年初,施蛰存与周愣伽以通信的形式展开了激烈辩论,主要讨论宋词中的“婉约”与“豪放”究竟是作家个人风格(或曰“体”)的表现问题,还是集体流派(或曰“派”)的倾向问题。施蛰存认为,婉约与豪放只是词人思想感情所造成的作品风格,提出“稼轩有婉约,有豪放,其豪放之作,多民族革命情绪,东坡亦有婉约,有豪放,其豪放之作,皆政治上之愤慨”。施文还指出“宋人论词,初无二派之分”,只有“侧艳”与“雅词”之别,婉约、豪放不是对立面,尚存在既不婉约也不豪放者,并主张编词史不宜再用婉约、豪放二派之说。周愣伽认为,婉约、豪放自《诗经》以下就已分派:“汉魏风骨,气可凌云”,此为豪放之祖;“江左齐梁,职竞新丽”,此为婉约之祖。周文提出,婉约与豪放,既是词作的风格表现,又是词人的流派倾向[24]。施、周二人各执一端,以“俟世之公论”告结。
随着论争逐渐走向深入,部分学者尝试对苏词的性质问题、“豪放词”与“婉约词”的区分问题进行总结。1982年秋,吴世昌在日本讲学时,作了题为《有关词学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提出北宋词人没有“豪放派”,苏轼绝大多数词并不“豪放”,不能称为“豪放派”。该报告引起了较大反响,吴世昌归国后,即将之修改为《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一文发表。文中,他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出发,提出质疑:“我们至多也只能说,北宋有几首豪放词,怎么能说有一个‘豪放派’?如果真有这一派,试问有多少人组成?以谁为派主?写出了多少‘豪放’词、收印在什么集子里?”[25]同年,他又在《文史知识》发表《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进一步考辨了“豪放”“婉约”两个概念的运用,断言东坡从未开创“豪放”一派,没有“改变什么词坛风气”,强调“北宋的词人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派,也没有区别他的作品为‘豪放’‘婉约’两派”,“这种机械的划分法并不符合北宋词坛的实际,很难自圆其说”[26]。该文引出了曾枣庄、雷啸林等学者的质疑意见。
1984年,王水照跳出窠臼,综合众论,发表《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一文。文章梳理了“豪放”“婉约”的概念来由与指称嬗变过程,明确指出二者之分是词体的“变”与“正”的区别,“所谓豪放词派和婉约词派实际上成了革新词派和传统词派的代名词”。该文以苏轼在“词乐分离”“诗词合流”进程中对词体地位抬升的贡献为例,有力地论证了“豪放(革新)”词派的学术内涵。其后,刘秉忠发表《也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王兆鹏发表《对宋词研究中“婉约”“豪放”两分法的反思》,从不同角度深入总结了“婉约”与“豪放”论争。整体来说,这场大规模论争加深了研究者对词体特质的认识,深入推进了词学研究的发展。
(二)继承传统形式,催生新质素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学术研究环境的正常化、开放化,一批词坛硕学耆宿再放光芒。他们不但积极参与词学论争,重新梳理词学史上各种范畴、风格和流派,而且继承古典文学批评传统,尝试探寻点将录、词话等批评形式的现代价值,为新一代青年词人与词学家的成长创造了良好氛围。
1977年,钱仲联在苏州撰写完成《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从“不向彊村门下乞残膏剩馥”的立场出发,将“殁在光绪初元以后、生于宣统辛亥以前而今已谢世”之词人排序比附,以谭献为“托塔天王晁盖”,以朱祖谋为“天魁星呼保义宋江”,以王鹏运为“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以况周颐为“天机星智多星吴用”,以郑文焯为“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27],100年间词坛领袖人物,捃录罔遗。该文虽立论有主观局限之处,但集中体现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方法,为考察近百年来词人词作、地域流派与词学思想留下了广阔空间。
1983年,朱庸斋病逝于广州,陈永正、蔡国颂等弟子为他汇辑遗著,陆续编撰出版了《分春馆词话》《分春馆诗词集》等书稿。其中,《分春馆词话》是朱庸斋毕生作词心得和词学研究的结晶,其内容源自1971—1977年间朱庸斋致友人信札及1961—1963年间朱门弟子听课笔记中的论词零语,后经朱门弟子整理摘录汇编而成。全书共五卷:卷一为总论,通论词体源流衍变;卷二为词学常识与填词原则,包括论词调、词律、用字、对仗等内容;卷三至卷五分别评论清代及民国词、南宋至明代词、唐五代与北宋词。整体上看,《分春馆词话》论词标举“重、拙、大、深”,重视词中音律、结构、内容之“吃紧处”,对词作之风格意境、词集之得失长短、词派之源流正变,品评中肯切实,可称是当代广东词林中的代表性词学批评文献。
同一时期,词集编撰和出版重新走向兴盛。老一辈词学家在为新出版词集所撰序跋之中,尝试总结自身的词学师承、词苑交游与研究方法,引导中青年词人群体的创作。如夏承焘在1983年所撰《天风阁词集前言》中,详细追叙了自己一生的学词经历,自叙十四五岁初识《白香词谱》,以《如梦令》结句获赏于张震轩,青年师从林铁尊,参加瓯社社集,而立之年客居杭州,撰写数种词人年谱,抗战以后避难上海,参加午社活动,自评“早年妄意合稼轩、白石、遗山、碧山为一家,终仅差近蒋竹山而已”[28]。又如周汝昌在1984年为《张伯驹先生词集》所撰写序言中,追忆以别号“寿康”“李渔邨”为张伯驹《丛碧词》《春游词》《丛碧词话》作序跋的往事,回忆昔年参与展春园词社社集的旧谊,推崇伯驹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淳而不薄”,堪称真正的“词人之词”[29]。再如1998年,毛谷风、熊盛元合编平装修订本《海岳风华集》,收录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及海外的中青年诗词创作成果。周退密在上海为该书撰序,勉励当代中青年词人承继朱彊村、叶遐庵、卢冀野等前贤未竟之业,熔铸中外,调和古今,“自开新境,为词曲寻找一出路”[30]。霍松林亦在西安为该词集撰序,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词坛存在的若干弊病,鼓励年轻词人“尽取其法度、韵调及遣词、锤字、宅句、安章与夫言情、写景、叙事之经验技巧,为我所用,然后出其藩篱,于反映新时代、抒发新感情之创作实践中求变求新”[31]。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老一辈词学名家的词论撰述在继承古典批评旧形式的基础上,迎合总结词学创作经验、梳理词林师承交谊的时代需求,直面词苑创作现实问题与共同弊病,容纳着新内容,孕育着新质素。
(三)回顾百年词学,探寻新方法
自20世纪70年代末马兴荣率先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的词学研究成果起,一直到世纪之交,词学界出现了“回顾和反思”的热潮。以施议对、谢桃坊、杨海明、胡明、刘扬忠为代表的一批词论家摆脱了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文学遗产的负面影响,通过反思20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词学发展的阶段和成果,审视词学研究的现代价值与当下意义,探索着新的学术方向与研究范式。整体上看,词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30年中词学研究的成果与不足。马兴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词学研究在观点和方法上起了根本的变化,在资料的汇集整理上有了新的进展,在普及工作上也开始做了些工作”,但研究者片面理解“古为今用”,“按照今天狭隘的政治需要来选择、评价词人、词作”,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来,没有一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写的新词史”[32],使词学研究逐渐走向片面化。施议对则谈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词学研究出现了两个值得称述的变化,即“对于词体的认识,逐渐由外部转向内部”与“词的创作从地下转向地面”[33]。他认为,当代词仍存在严重的缺陷,“瓶”的问题(形式问题)、“酒”的问题(内容问题)与“装”的问题(表现方法问题),依然极大地限制着词体在当代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力。谢桃坊在《中国词学史》中着重反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30年以来,词学批评方法的僵化和庸俗化。他提出,在新的文化条件下,古典文学基础研究传统的“实证方法”应当“为最先进的方法所代替或加以改造”,才能科学地、历史地、深刻地阐释和评价词学的内部因素及其特殊规律。
二是反思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词学研究的成果与不足。20世纪80年代末,马兴荣撰写《十年来的词学研究》,主要阐释改革开放后第一个10年期间,词学研究成果增多,研究领域扩大,研究问题走向深入,研究方法不断更新,海内外词学交流逐渐繁荣。90年代中期,杨海明刊发《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一文,强调从“文革”结束至90年代中期的新时期,受嗜“柔”嗜“美”的文化心理影响,对词心、词体、词境、词风的探讨出现重大突破和超越,词学研究呈现“前所未见的开阔态势和活跃景象”[34]。随后,胡明在诠释与思考八九十年代来的词学研究时,强调“‘别是一家’的本色理论受到体制内集体无意识的推重”,“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与评价体系形成”,“清词研究成绩令人注目”,“三流、四流词人进入研究领域”,研究者纷纷撰写“普及赏析、辞书条目”,推动百年来的“词学积储得以全部释放”[35]。刘扬忠则主要回顾了改革开放后词史研究和编撰的成果,重点评述了断代词史与专题词史研究著作。他提出,转型时期的词史研究者“一改列传式修史者按作家作品的历时性排列叙述来构‘史’的单一模式”,参酌吸收了原型批评、意象研究、范式理论、结构主义等西方理论,“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创新,实现了词史撰著的多元化”[36]。
三是展望新世纪词学研究发展的新方向。20世纪末,胡明在阐述100年来词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成果时,曾设想词学理论建设与开拓的新路,包括加强对词体微观的体制内研究,强化对唐声诗与倚声填词的形式界限研究,提升对词体的产生机制研究,关注对五代两宋词人的生存状态与人文情志研究等。世纪之交的《文学遗产》组织的词学座谈中,词论家从不同的角度为新世纪的词学发展指引了新方向。钟振振提倡,今后的词学研究应当从“词作文献的整理,词人生平的考证”方面进行突破,因为“词人的生活年代不清楚,词史的进程也就无法真正弄清”。刘扬忠更关注研究者学术个性的凸显,主张把“确立研究者个体的学术个性和研究方向”与“加强对词史上的空白段明词和清词的整理与研究”同列为新时期词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目标。王兆鹏则认为,新的词学研究生长点,应该在词人年谱或年表的制作、词史个案问题的定量分析、词集版本目录的总体清理上。
综上可见,20世纪末的词论研究“回顾与反思”热,是三四十年代以来现代词学逐步成型的思想成果,也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词论研究曲折前进的经验反馈,还是世纪之交词学学科自我更新的客观需求。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已经认识到确定“学术传统的生成机制”与寻求“词论研究的范式转型”的重大意义,但对新世纪词学发展到底应“向何处去”,尚未形成大范围的共识。这一使命,需要留待新时期的词论研究来完成。
三、制造“新声”:新世纪词论研究的特点与展望
21世纪初至今,随着互联网与大数据的发展,新的分析工具、分析模型、技术手段和呈现方式,大幅度拓展了词学理论的研究视域,词论研究日益与数字人文技术的更新相结合,与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相结合,与海外词学研究的发展相结合,出现新变化、新趋势、新动向。从内容层面看,词论研究重心从唐宋向明清转移,研究视野从词人个体向群体扩展,研究热点向“传播—接受”模式偏斜。从形式层面看,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兼备,词论研究正在进入“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文献检索”向“数据分析”转变的关键时期。整体来说,不断成熟的新技术、新工具,不但改变了词学领域知识生产的原料选择,而且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词学领域知识生产成果的流通与消费形式。这一时期,词论研究值得关注的新成果、新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代词论文献整理成果丰硕
21世纪以来,在况周颐辑、王文濡增补《词话丛钞》和唐圭璋辑《词话丛编》[注]可参见况周颐辑、王文濡增补《词话丛钞》,1925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刊行,内辑清人词话10种。唐圭璋辑《词话丛编》,1934年由中华书局刊行,内辑历代词话60种。1986年唐圭璋又增补词话25种,合计85种,汇总由中华书局刊行。的基础上,学界陆续出现几种《词话丛编》补辑本:一是朱崇才编《词话丛编续编》五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收录《蓉渡词话》《锦瑟词话》等历代词话32部;二是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编》六册(中华书局,2013年),收录《倚声初集辑评》《山中白云词偶评》等历代词话67部;三是屈兴国编《词话丛编二编》五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收录宋吴曾《能改斋词话》、宋胡仔《苕溪渔隐词话》等历代词话48部。三种补辑本体例浩大,内容多为从词集、词选的批注评点中摘录汇辑而成的词话,其中不乏唐老未及寓目的稀见本词话,但三书有不少篇目重复,且都没有编制索引,使用起来时有不便之处。
与此同时,诸多学者爬梳剔抉,分时代补辑了大量词话著作,如张璋等编纂有《历代词话》与《历代词话续编》各两册(大象出版社,2002年、2005年);邓子勉编有《宋金元词话全编》三册(凤凰出版社,2008年)与《明词话全编》八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孙克强主编有《唐宋人词话》《金元明人词话》《清人词话》三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与《历代闺秀词话》四册(凤凰出版社,2019年),另与杨传庆、和希林合作编有《民国词话丛编》八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刘梦芙编校有《近现代词话丛编》(黄山书社,2009年);和希林、杨传庆编有《辑校民国词话三十种》(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黄霖则主持全面梳理了民国时期的稿本、抄本、油印本、评点本、报刊连载本词话作品,即将出版《民国话体文学批评丛刊·词话卷》两册。
以论述词话缘起、特色、功用为核心内容的理论著作也逐渐涌现,其中系统性最强的是朱崇才所撰《词话学》(文津出版社,1995年)、《词话史》(中华书局,2006年)与《词话理论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三部专著各有侧重,分别阐释了词话的背景、基础与方法、词话的基本状况与表现形式、词话的历史发展和词话的各种理论范畴等问题。
此外,冯乾从清词别集、总集、选集中搜辑了大量序、跋、题识、凡例,编为《清词序跋汇编》四册(凤凰出版社,2013年),杨传庆搜辑清初至20世纪60年代词学书札695通,编为《词学书札萃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为研究词人生平、词坛交游、词籍编纂、词论争鸣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文献支撑。
(二)当代旧体词的价值得到重视
当代旧体诗词曾长期被排斥于主流文学之外,其创作与研究均呈现喑哑低沉之势。新世纪伊始,受益于中华诗词研究院、中华诗词学会、各地诗词组织及高等院校的大力推动,借助互联网新媒介传播平台,诗词创作开始从新旧对峙走向新旧共存、新旧互鉴,旧体诗词创作渐渐复苏并走向繁荣,甚至出现旧体诗词“写作热”现象。
同时,当代旧体诗词“入史”或“入教”问题、旧体诗词格律宽严问题、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词问题逐渐得到学界关注,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陈友康、马大勇等学者围绕20世纪旧体诗词的价值展开热议。有学者认为,从现代文学的思想性质、诗歌文体与文学语言, 旧体诗歌文体演变与自由诗体、现代旧体诗词与自由体诗歌, 诗歌传播与现当代文化语境等诸多方面来看,“现代文学史研究不把旧体诗词纳入文学史研究,既有历史的原因, 也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历史与现状的客观性发展的一种选择,体现了一种学院化的经典性文学史观,不存在‘压迫’‘拒绝’与‘悬置’的问题”[37]。
对此,大量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陈友康指出,首先需要理解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合理性, 有必要“重新厘定‘现代文学’的范畴, 用‘现代汉诗’这一概念来整合20世纪中国诗歌, 消弭新、旧诗词的对抗和对立”[38]。王兆鹏认为,当代旧体诗词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关注和研究旧体诗词,不仅是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开拓研究空间的需要,也是深化已有成果、求新求变的必然需求”[39]。词学研究与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结合,有益于帮助研究者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提升整个词学研究的学术品位和理论水平。李怡、陈思和与曹顺庆从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角度,重新阐释了旧体诗词进入现当代文学史的实践和理由,提出“传统诗词的创作在事实上已经是许多现当代作家、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是我们认识、理解这些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途径”[40]。马大勇则旗帜鲜明地表示,“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应该还在它是否可以入史的问题上再过多纠缠,而是进一步探讨现代旧体诗词如何入史、如何高水平的入史的问题的时候了”[41]。
综合来看,建立融通新旧雅俗的新的文学史观和价值体系,仍然是制约现当代旧体诗词高水平“入史”“入教”的关键短板。如果不解决理论建构不够成熟、研究成果仍待丰富等问题,“旧体诗词即便入史,也有可能成为现代文学史著中即而离、离而即的‘附骥式’存在”[42]。可喜的是,近年来,部分研究者和创作者开始尝试通过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探究制约旧体诗词当代传播的声韵问题,促进当代诗词的题材扩展、审美跨越和文体创新。例如,张海鸥总结了20世纪以来旧体词历次声韵改革的尝试,详细阐释了新旧韵并行、全用新韵废止旧韵、以词韵取代诗韵、恪守旧韵各种方案的利弊,提出适应和融洽新韵,才能“使旧体诗词的现代生存和未来发展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使旧体诗词“更易于成为所有汉语人群可以共同拥有的经典语言艺术”[43]。又如,当代诗人蔡世平提出,当代诗词的创作语言,必须有诗意的“当代性”,也就是“从语言到思想尽可能体现当代人的审美情趣”[44]。这实际上是要求当代诗词贴合时代潮流和现实情境,寻找到与当前社会文化同步发展的结合点。
(三)词体理论批评逐渐走向深入
21世纪以来,研究者们沿波讨源,在继承与梳理前人辨体、破体、尊体诸种异说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了词体起源论、词体体性论、词体革新论等问题的研究,探讨了词体在风格、文本、声律等层面的规范和定型,推动了整体性和长时段视域之中文体谱系的重构。
这一阶段,首先应当关注的是老一辈词学家的新成果。叶嘉莹(迦陵)自20世纪70年代末回国讲学后,陆续出版《迦陵论词丛稿》《唐宋词十七讲》《清词丛论》等著作,倡导以“兴发感动”论词。叶嘉莹提出,词具有“深远曲折耐人寻绎之意蕴”的“弱德之美”,而词体“主要的美感特质是一种兴发感动的力量”[45]。究其根本,“兴发感动”说主要关注词人的审美感知、词作的艺术构思与读者的欣赏评价三方面,尤其强调将词作的“精神伦理价值”而非词人的伦理道德品质作为评词标准。叶嘉莹数十年来深耕诗词阐释领域,凭借贯通古今、连接中西的审美体验为当代词学研究的转型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示范。此外,寇梦碧等词学名家通过编撰词集、汇编书札、题写序跋,不断总结自身的填词经验与词学活动,推崇“以稼轩之气,遣梦窗之辞”的词坛风尚,为新世纪初叶的词学研究保留了典雅的余韵。
与此同时,一批骨干词学研究者从词体特性与声律研究两个方面入手,撰著了大量具有开创性的词体研究论文,为亟待转型的词学界引入一湾“活水”,推动词体研究成为词学学科新的学术生长点。
一方面,学者们细致剖析了词体与诗、曲、文、小说、新体乐歌等各类文体的异同,考述还原了历代词人对词体特征的建构与演进,为词体特质研究的系统化、纵深化、完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孙克强着眼于唐宋词学史上对词体特性认识的理论标度,详细探究了欧阳炯《花间集叙》、李清照《词论》与沈义父《乐府指迷》分别如何准确把握词体发展的新变,高度概括特定时期词体的新特质。陈水云关注清代词学推尊词体的风气,曾以康熙年间为例,追溯了广陵、阳羡、浙西等词派对词之特质的辨析、对词之正变的论争,主张清初词学辨体与尊体之风为近代词学尊体观的最终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彭玉平以况周颐《蕙风词话》为中心,深入探讨了词体与古文、诗赋、小说等文体错综复杂的关系,论述“以诗比词”现象的缘由、实质及其影响,同时从词笔质直、不嫌说尽、词笔变化、曲笔传情、拙语真情等五个角度辨析“小说可通于词”之说的合理性。张宏生则着重关注19世纪末“诗界革命”中“词体的缺席”现象,详细辨析词体抒情本质与新生活、新语句、新境界的矛盾关系,指出“即使在词的诗化已经日渐成为趋势时, 词坛上坚持诗词之别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词在总体诗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46]。
另一方面,学者们积极推动对词乐、词调、词律、词韵、词唱法的研究,致力于全面、整体、动态地把握词体体制的独特性和音乐性,革新词体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词律领域,朱惠国深入研究了1940年前后发生在午社的“四声之争”,指出“其实质是民国时期以推崇梦窗词风为标志的词学观发展到这一时期面临困境,要求再次改变的一种表现,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47]。在词调领域,陈水云重点关注了明末清初词调“三分法”的出现、反响与意义,提出“它标志着中国词学由音乐谱时代进入到格律谱时代,改变了明代以后词选与词谱编刻的体例及其发展方向”[48]。在词谱领域,张宏生提出,在清初30年间,“以万树为代表的词学家总结明代词谱的得失,主要对《诗余图谱》和《啸余谱》进行批评,从格律形式上确立了词的创作规范”,“可以视为清初词风演进的一个重要标志”[49]。在词唱法领域,彭玉平通过对比论述民国时期詹安泰等词人所主张的“合声、情、乐为一体,最大限度地恢复宋词旧唱的面目”与叶恭绰、龙榆生等词人所提出的“融合中外音乐并借以配合长短不齐之诗,以新体乐歌来代替传统的词曲”[50]两种词体革新理论,提出韵文创作研究应坚守声文合一的原则。
整体观照,历经70余年的发展,词论研究从探索时期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为工具重审古典词学的当下价值,塑造词论研究的时代“主流”,走向转折时期尝试调和理论论争,从传统词学中赓续与催生新的路径,继而借助21世纪以来数字人文技术的飞跃,推动词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推动现当代旧体词“入史”“入教”的讨论,推动词体特征的探索与研究,同时也为学界带来了沉甸甸的压力。新的时期,词学研究如何整合传统资源,如何面对数字人文技术的挑战,如何吸收利用海外词学研究的成果,如何与地域、传播、家族、党争相结合,如何立足文本、贴合当代、面向世界、关怀现实,是每一位新世纪的词学研究者必须承担的学术责任和不能回避的时代命题。
——评陈水云教授新著《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