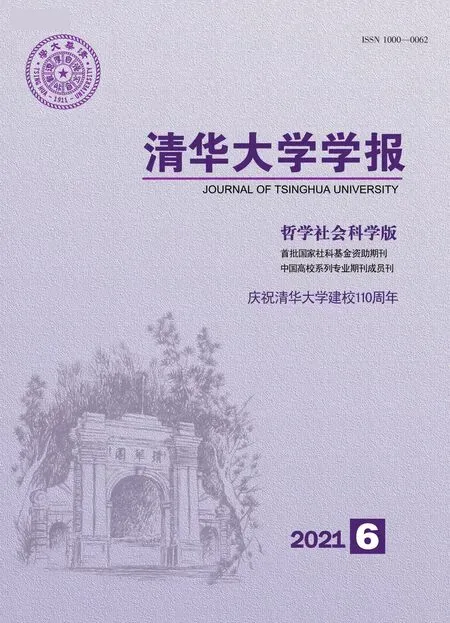先秦秦汉的“秦人”称谓与认同
刘志平
史党社在《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一书中从族群①“族群”是一个灵活而具有伸缩性的概念,既可指一个“民族”,也可指一个“民族”之下有区域差异性并具历史传承意义的各次级人群。不过,虽然“‘族群’这一词语具有了比‘民族’更加宽泛的含义。但是,这种宽泛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它限于人类群体具有历史传承意义的‘族类化’范畴,而非在现代社会中不断出现且日益增多并称为‘族’的社会文化群体”。见郝时远:《类族辨物:“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中西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97页。的角度探讨了“秦人”内涵的动态演进过程,②史党社:《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0—366页。给本文的探讨提供了较多有价值的启示。本文拟在其研究基础上,对先秦秦汉时期的“秦人”称谓进行系统的梳理,从当时的历史场景来考察“秦人”称谓是怎样存在于“自我以及其他族群的主观意识中”,③史党社:《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第260页。由“族群称谓”体现的“族群认同”是一种主观的自觉体认,这种主观的自觉体认包含“他称”(主观被认为)和“自称”(主观自认为)。一个族群称谓的“他称”和“自称”孰先孰后?王明珂以“羌人(羌族)”认同为例,认为“羌人(羌族)”之“他称”在其“自称”之前,且“自称”是在“他称”影响下产生的,而此“他称”往往是一个强势族群的主观认定,所谓“在‘羌族史’上,显然被称作‘羌’的人群只有由华夏那儿知道自身被称作‘羌’,而在族群生活中‘羌’成为一种认同与区分的社会现实之情况下,才在他们中产生‘羌’的族群认同”。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8页。王明珂用族群理论及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考察民族历史,往往有不同于传统民族史学者的独到见解,值得借鉴。受王明珂影响,史党社认为“秦人”这一称谓也是“他称”在前,“自称”在后,且“自称”也是在“他称”影响下产生的,而此“他称”也是一个强势族群的主观认定,所谓“‘秦人’族群认同的诞生,是由周王朝认定和‘识别’、‘秦人’所认同的”。见史党社:《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第289页。不过,对以现代民族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果去回溯比附中国先秦秦汉时期的族群称谓和族群认同,我们要谨慎对待。同时,我们不能否定客观文化特征在族群认同上的基础工具意义。并对“秦人”称谓与认同在先秦秦汉时期消长的历史轨迹进行详细探寻,以期为中国上古时期的族群认同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观察点,同时希望能为如何正确认识当今中国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提供一点历史启示。不当之处,尚祈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春秋时期的“秦人”称谓与认同
虽然在周孝王时,非子被封于“秦”,号为“秦嬴”,“秦人”的族群意识已开始产生,“秦人”已开始作为一个族群登上历史舞台,但其族群意识的增强是在历史情境性的整体性“秦人”称谓频繁出现后才得以体现的,而这种历史情境性的整体性“秦人”称谓本身要到秦成为诸侯国后的春秋时期才频繁出现。①史党社考论过西周金文中的“秦夷”和“秦人”问题,认为西周金文中的“秦人”“是殷遗而属东方,其地位比‘秦夷’为高,并与后者为一族,只是一族的上下层而已”;“商周以来东方范县之‘秦’地一直存在,并且当为《左传》等文献记载的春秋秦氏的由来。由此可证,在更早的西周时期,此处一直有一个以‘秦’为名号的族群的存在,这个族群无疑就是‘秦夷’、‘秦人’之类”;“‘秦人’应是东方秦氏的上层,而与西方孝王时代得名的秦人无关”。见史党社:《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第223页。笔者认可史党社的观点。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末尾言及“嬴姓”后分出很多“氏”,其中就有“秦氏”,而特别提到非子之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见《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1页。司马迁将非子之秦与“赵氏”联系在一起,而与“秦氏”隔离起来,这表明其中的“秦氏”属东方,非子这一支秦人与东方的秦氏无关。
春秋初期,凭借周王室的册命,秦成为诸侯国。“国家的力量介入了‘秦人’的形成过程。此时,除了嬴秦宗族之外,又有邽、冀那样的‘西戎’以及‘周余民’的加入,这些人士构成了‘秦人’的下层”。②史党社:《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第263—264页。而“秦人”这一称谓本身是在春秋时期多层次的族群认同背景下产生并被使用的,且具有一定的情境性,所以我们考察春秋时期的“秦人”称谓与认同,应考虑当时与此相关的族群称谓和族群认同的总体情况,且要注意其场景性。
检诸文献,“秦人”称谓在《春秋》经文中首次出现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秦与诸侯于此年有一次大会盟。③《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虽然对于此处“秦人”称谓有“班序最后,而称人”这样的理解,但其族称含义是不能否定的。其实,杨伯峻对“诸侯书某人”又有“此自是时代不同,称谓有异,无关所谓大义微言”的认识。若依从这样的理解,就更不能抹去“秦人”称谓的族称含义了。鲁僖公二十八年亦即秦穆公二十八年。《左传》所载秦与华夏诸侯最早的一次会盟是在秦穆公十五年,《左传·僖公十五年》:“十月,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50、67、366页。《春秋》经文是以鲁人口吻记述的,④此有很多例证,除了此处直称鲁公为“公”及此年中“杞伯姬来”的记载,还有《春秋·隐公元年》“祭伯来”、《春秋·桓公二年》“滕子来朝”、《春秋·庄公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春秋·闵公元年》“葬我君庄公”、《春秋·僖公二年》“葬我小君哀姜”、《春秋·哀公八年》“吴伐我”等记载(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450、8、83、156、256、280、1646页),不胜枚举。故此处“秦人”是鲁人对秦人的他称。而此时正是秦国势力得到显著增强并对东方各国构成一定威胁的秦穆公时代,大概源于此,此后《春秋》经文中多有鲁人口吻中的“秦人”称谓的出现,如《春秋·僖公二十九年》:“夏六月,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春秋·成公二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⑤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475、616、786页。
从以上记载我们还可看到,春秋时期鲁人所称呼的“秦人”同“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楚人”“巴人”“卫人”“郑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一样,都是以封国名号命名的人群集团称谓。而考虑到其血缘世袭的宗族性和地缘扩展的政治性,我们可知在具有浓厚宗法血缘色彩的嬴秦贵族所建立的政治体内,秦人上层精英所推行的政治、文化建设和族源历史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整个政治体内秦人的整体自我认同,这种认同又在与其他同样具有浓厚宗法血缘色彩的贵族所建立的政治体的交往与对抗中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其他政治体成员明确的“秦人”族别意识。①有学者指出:“秦人既是一个族群概念又是一个政治概念,在述及祖源记忆的问题时主要针对秦国公族而言,在大部分情况下,秦人是一个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政治群体。春秋时期之后,‘秦人’与‘秦国’在内涵上有高度的重合。”见彭丰文:《先秦两汉时期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0页。彭丰文将“族群”和“政治体”完全等同起来的观点虽有可商榷之处,但我们还是不能忽视政治体在族群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除了上述鲁人对“秦人”的他称,还有周人、晋人等其他族群对“秦人”的他称。②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475—1477页;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93页。此外,又有戎人对“秦人”的他称,《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
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洩,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貍所居,豺狼所噑。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貍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殽志也,岂敢离逷?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赋《青蝇》而退。③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005—1007页。有一点需作说明,即虽然《左传》一书成书于战国时期,“但许多材料却直接来自于春秋各国史官所记的原始资料”,特别是一些“记言材料”,“许多应为原始记录”。见王晖、贾俊侠:《先秦秦汉史史料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82—83页。所以《左传》中的材料尤其是“记言材料”,总体上是可以用来反映春秋时人的族群观念与春秋时的族群实态的。朱圣明认为从《左传》所载春秋时期参与现实政务的诸国君臣的话语中可看到春秋“华夷之辨”的现实。参见朱圣明:《华夷之间:秦汉时期族群的身份与认同》,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36页。这样的意见总体上也是可取的。
戎人驹支言及“秦人”和“晋人”,又明确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可见,在戎人眼里,“秦人”和“晋人”一样属于华夏。而晋人范宣子也言及“秦人”,且与“姜戎氏”对言,说明在晋人眼里,秦人并非戎人。
鲁僖公十五年,秦晋会盟,晋人言及“必报雠,宁事戎狄”,意即宁肯屈事戎狄而必报秦雠,也说明在晋人眼里,秦人并非戎狄。鲁成公十六年(前575),晋人范文子言及晋国曾经面对的四个强敌是“秦、狄、齐、楚”。可见在晋人眼里,秦与齐、楚一样,皆有别于狄。鲁僖公十一年,“扬、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秦、晋伐戎以救周”。鲁僖公二十二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④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66、882、338—339、394页。可见,秦人与晋人一样,皆非戎人。据此,我们能否认为春秋时期的秦人处于华夏之列,而非戎狄?要回答此问题,必须对春秋时期多层次的族群认同背景及“诸夏”指称的具体范围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族群认同上,春秋时期盛行“夷夏之辨”的思想观念。虽然对周人自称“有夏”之“夏”的含义可有“夏后氏之夏”“中原王权国家的符号”和“西土之人”之不同理解,⑤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4—32页。但对于春秋时期的“诸夏”“夏”“华夏”“中国”“诸华”“华”已成为与“蛮夷戎狄”相区分的政治文化实体和族群实体则是无可质疑的。《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①杨伯峻注:“中原诸侯,为互相亲近之国,不宜抛弃之。”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256页。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②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256页。管仲所言“诸夏”是与“戎狄”对立的,这应是春秋时期最外围的族群分界。③春秋时期,戎狄与华夏在空间上又是交错的。参见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28—358页。这还有很多其他例证,如《左传·襄公四年》记载:
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④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935—936页。
又如《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
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无慝,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诗》曰:‘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不能济河。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子其受之!”⑤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993—994页。
还如《左传·定公十年》记载:
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犂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⑥杨伯峻注:“杜《注》:‘莱人,齐所灭莱夷也。’”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577页。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⑦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577—1578页。
由上可知,晋人魏绛将“戎”与“华”对言,晋侯将“诸戎狄”与“诸华”对言,孔子将“裔”“夷”与“夏”“华”对言,足以说明“诸夏”或“诸华”与“蛮夷戎狄”的分界是春秋时期最外围的族群分界。
而从以上历史场景可明确判断出当时“诸夏”的部分所指,即齐、邢、晋、陈、鲁属“诸夏”,而楚、莱不在“诸夏”之列。鲁襄公二十六年(前547),蔡人声子言及“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也可见楚不在“诸夏”之列,“华夏”指郑、蔡等中原诸侯。《左传·襄公十三年》:“秋,楚共王卒。子囊谋谥。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大夫从之。”⑧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121、1002页。楚人虽然认为自己不是“蛮夷”,但是也不敢自诩为“诸夏”。
《左传·僖公十五年》:“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寻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可见,“徐”也不在“诸夏”之列。又《左传·哀公二十年》记载晋人楚隆之言曰:“吴犯间上国多矣,闻(越)君亲讨焉,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从,请入视之。”①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51、1716页。在晋人楚隆看来,吴、越皆非“诸夏”。《左传·成公七年》:“七年春,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②杨伯峻注:“中国,当时华夏各国之总称。”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832页。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弔者也夫!《诗》曰“不弔昊天,乱靡有定”,其此之谓乎!有上不弔,其谁不受乱?吾亡无日矣。’”③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832—833页。在鲁人眼里,吴人属“蛮夷”,不在“诸夏”之列。《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皥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皥、济而修礼、纾祸也。’”④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91—392页。杨伯峻认为原文“修祀”当作“修礼”,笔者从之。可见,任、宿、须句、颛臾不在“诸夏”之列,而邾人被成风视为与“夏”对立的“蛮夷”。《左传·昭公元年》:“祁午谓赵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晋。今令尹之不信,诸侯之所闻也。子弗戒,惧又如宋。子木之信称于诸侯,犹诈晋而驾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晋,晋之耻也。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诸侯,三合大夫,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⑤杨伯峻注:“东夏,华夏东方之国,实指齐。”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201页。可知在晋人祁午看来,秦既非“狄”,也非“夏”。
可见,春秋时期的“诸夏”或“诸华”,是指齐、鲁、晋、郑、陈、蔡、邢等中原诸侯,其与“蛮夷戎狄”构成当时现实观念中的族群分界。不过,这个时有确指的“诸夏”又被涵盖在以周王室为名义上的核心的封国体系内。
《左传·昭公十五年》:“十二月,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既葬,除丧,以文伯宴,樽以鲁壶。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文伯揖籍谈。对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王曰:‘……匡有戎狄⑥杨伯峻注:“谓其国境内有戎狄。”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372页。……抚征东夏。’”⑦杨伯峻注:“晋服齐、鲁、郑、宋诸国,皆在晋东,故云东夏。”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371—1372页。周景王所言“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与籍谈所言“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说明周王室仍是春秋时期诸侯封国体制名义上的核心。而周景王又言及“戎狄”和“东夏”,表明“夏”与“戎狄”有着明确的族群分界。
这个以周王室为名义上的核心的封国体系,可说是广义的“华夏”,其与“蛮夷戎狄”构成了最外围的族群分界。《左传·成公二年》:“晋侯使鞏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齐,而不使命卿镇抚王室,所使来抚余一人,而鞏伯实来,未有职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礼。余虽欲于鞏伯,其敢废旧典以忝叔父?夫齐,甥舅之国也,而大师之后也,宁不亦淫从其欲以怒叔父,抑岂不可谏诲?’士庄伯不能对。王使委于三吏,礼之如侯伯克敌使大夫告庆之礼。”⑧杨伯峻注:“不用献捷礼,而用告庆礼。告庆礼内容已不得而知。”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809—810页。而晋侯另两次“献捷”并未受到周王的拒绝,原因就是所献乃“狄俘”。⑨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765、768页。可见,诸侯向周王的“献捷”只针对“蛮夷戎狄”,由此足见以周王室为名义上的核心的封国体系与“蛮夷戎狄”之间确实形成了最外围的族群分界。
这个以周王室为名义上的核心的封国体系内部还存在着以姬周为核心的同姓与异姓之别。《左传·成公十六年》:“吕锜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战,射共王中目。王召养由基,与之两矢,使射吕锜,中项,伏弢。以一矢复命。”①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886—887页。“占梦者站在晋国的立场上,谓姬姓诸侯国为日,泛称异姓诸侯国为月,尊同姓贬异姓心理明显”。②谢乃和:《古代社会与政治——周代的政体及其变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0页。而这里的异姓诸侯国指楚国。嬴姓秦国当然也在异姓之列。《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③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497—498页。可见,先轸主张攻打秦国的理由之一就是秦伐其“同姓”。④秦所伐滑国乃晋同姓。鲁成公十三年,晋人在《绝秦书》中也明确说到秦“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⑤杨伯峻注:“郑、滑与晋同为姬姓,兄弟之国。”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862—863页。不过,秦、楚作为异姓诸侯国,地位要低于齐。《左传·昭公十二年》:“右尹子革夕,(楚灵)王见之,去冠、被,舍鞭,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⑥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339页。可见,齐作为“王舅”,地位高于楚。对于吴为姬周之后,虽然在春秋社会现实中已成为一种观念事实,⑦如《左传·襄公十二年》:“秋,吴子寿梦卒,(鲁)临于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是故鲁为诸姬,临于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于周公之庙。”鲁将吴视为同姓。又如《左传·昭公三十年》:“子西谏曰:‘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若好吴边疆,使柔服焉,犹懼其至。吾又强其雠,以重怒之,无乃不可乎!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光又甚文,将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将以为虐乎,使翦丧吴国而封大异姓乎,其抑亦将卒以祚吴乎,其终不远矣。我盍姑亿吾鬼神,而宁吾族姓,以待其归,将焉用自播扬焉?’”楚人认为吴为姬周之后。还如《左传·哀公十三年》:“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呼司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长幼必可知也。’对曰:‘请姑视之。’反,曰:‘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国胜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轻,不忍久,请少待之。’乃先晋人。”吴人也自认为是姬周之后,不过晋人仍将其视为“夷”。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996、1508、1677页。甚至影响到了司马迁,⑧在《史记》中,司马迁将《吴太伯世家》列为世家之首,并在最后说道:“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见《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1475页。但吴有时还是被视为“夷”,⑨除了《左传·哀公十三年》所载晋人仍将吴视为“夷”外,《左传·定公四年》载有楚人将吴视为蛮夷之言:“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场之患也。逮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左传·哀公十二年》还有“尚幼”的卫人子之将吴视为“夷”的记载。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548、1672页。在司马迁的脑海里仍留有深刻的“荆蛮”印记。有学者已经指出,吴为姬周之后是吴对姬周华夏的一种主观攀附,同时也是姬周华夏为了现实族群利益而作的主观认定。⑩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1—193页。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春秋时期的“华夷之辨”,除了政治因素(以周王为名义核心的封国体系)外,礼仪文化也是重要的因素。周公制礼作乐,创造出的一套礼仪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华夏族群区别于蛮夷族群的客观文化基础。关于这套礼仪文化,《左传》中有详细记载。⑪1景红艳:《〈春秋左传〉所见周代重大礼制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这种将礼仪文化水平的高低作为华夷区分标准的观念影响深远。当然,若落实到春秋社会的现实,情况是复杂的。这正如朱圣明所言:“固然,现实社会中‘蛮夷’与‘华夏’的确在文化礼仪、同周室政治关系上存在显著差别,然而,这种差别由来已久并在短时间内很难被改变,华夏同蛮夷的族群特征与界限也由此而趋向固化。此时,现实中的他们断然不会仅以某一行为、举动而被另视为‘夷狄’或者‘华夏’。”朱圣明进而指出:“现实社会中楚、秦等国向‘华夏’的转变也是通过文化变革及参与诸夏会盟等方式逐步进行的……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楚、秦由蛮夷变为华夏。中原蛮夷或为诸夏所并,或被驱逐到四边之地。诸夏之国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亦日渐趋同。华夷五方格局(华夏居中,蛮夷分处四方)、‘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局面得以真正成形。”①朱圣明:《华夷之间:秦汉时期族群的身份与认同》,第32、36—37页。这样的意见值得重视。
总之,在春秋时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②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672页。这个以周王室为名义上的核心的封国体系,是开放、包容、变动、多层次的,既包括“核心华夏”(既包含同姓,也包含异姓)——中原诸侯,③《春秋·庄公三十年》:“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齐人伐山戎。”《左传·庄公三十年》:“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246、247页。山戎“病燕”,燕得到齐鲁救援。可见北方的燕也在“核心华夏”之列。也包括“边缘华夏”(主要是异姓)——秦、楚、吴、越等诸侯。虽然随着“核心华夏”和“边缘华夏”对其外部“蛮夷戎狄”的政治吞噬和文化渍染以及“边缘华夏”华夏化程度的逐步加深,春秋时期的族群认同格局在逐步朝着新的方向演化,但“夷夏之辨”的总体族群认同格局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个以封国名号命名的“秦人”称谓也还没有凸显出它在当时族群认同格局中的显著地位,仍被笼罩在“夷夏之辨”的族群认同格局中。正因为这样,“秦人”处在异姓、边缘华夏的位置,即在“核心华夏”与“蛮夷戎狄”之间,是“大夷”,是“蛮夷诸侯”。④朱圣明:《华夷之间:秦汉时期族群的身份与认同》,第44—49页。从而在“秦人”的自我体认中,随着场景的变化产生时而自称“中国”,时而自称“戎夷”,⑤这在秦穆公身上有显著体现。《史记·秦本纪》:“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92页。在真正的“戎夷”面前,秦穆公自称秦国为“中国”。而《吕氏春秋·不苟论》记载:“秦缪公相百里奚,晋使叔虎、齐使东郭蹇如秦,公孙枝请见之。公曰:‘请见客,子之事欤?’对曰:‘非也。’‘相国使子乎?’对曰:‘不也。’公曰:‘然则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国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犹懼为诸侯笑。今子为非子之事,退,将论而罪。’”见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42—643页。在与晋、齐的交往中,秦穆公又自称秦国为“戎夷”。时而自认“非蛮非夏”的不同情况。⑥作于春秋中期的秦公簋、秦公钟铭文所记秦公(论者多认为是秦景公)之言有“保()氒(厥)秦,事(蛮)夏”的内容。另外,秦景公四年(前573)的残磬铭文也有“(肇)尃(敷)(蛮)夏,极(亟)事于秦,即服”的内容。见王辉、王伟编著:《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25、26、24页。可见,在没有客体在场时,秦公自认为秦国处在蛮夏之间。
二、战国及秦代的“秦人”称谓与认同
三家分晋结束了春秋时代,揭开了战国的序幕。⑦晁福林指出:“战国七雄对峙的局面是从三家分晋开始的……三家分晋乃是春秋与战国两个历史时期的分水岭。”见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第161—162页。到了战国时代,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以周王室为名义核心的封国体系已经瓦解。与此相应,春秋时期“核心华夏”和“边缘华夏”的族群区别也逐渐消失。①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写道:“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见《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2886页。可见,战国七雄都属华夏冠带之国,与匈奴构成新的外层族群分界。史党社对此也有精当的分析:“春秋以来,与华夏比邻的‘蛮夷戎狄’,逐渐被晋、齐、秦、楚等大国吞并,夷、夏在各种各样的接触中走向融合,自西周晚期以来对华夏造成极大威胁的‘戎祸’,也基本消弭。原来进入中原的戎、狄之类,不但本身融入‘华夏’之中,其土地也成了中原诸侯的版图。有实力的诸侯国如秦、齐、楚、魏、赵等,还向外扩展自己的领地,它们在这些地方设县立郡,建立塞徼,并把中原农业生产方式向更远的周边扩展。在这些国家内部,除了原来的‘蛮夷’被同化而融入华夏外,所谓‘蛮夷’的地理界限,已在更远的徼外。这些人群,对秦来说,就是羌、胡(如匈奴)等人群了。在这个情况下,春秋以来甚嚣尘上的‘夷夏’之辨,自然也归于沉寂……原来的诸侯国,由于外来威胁的消失,周天子的天下共主的地位的失去,因此原来的团结不再,都想出头称王,一切都变得须用实力说话。重要的是,这些活动都不需要假借王室或攘却‘戎狄’的名义进行了,有实力的诸侯如秦、齐等等都表现出为天下新主的强烈愿望。这个原因促使原来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华夏’也发生了变化,在大量融合‘蛮夷’的基础上,新的‘华夏’正在形成,这是后世‘汉人’的前身。中原主要的族群关系,也由原来的‘华夏’与‘蛮夷’的关系,变成了诸侯之间的关系。”见史党社:《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第320—321页。而“秦人”的内涵随着秦国政治体的不断膨胀也在不断扩展,②史党社:《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第264页。“秦人”在与其他政治体成员的交往与对抗中进一步强化了“我群”认同,而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其他政治体成员明确的“秦人”族别意识。这样,“秦人”与“非秦人”的族群区分逐渐得到凸显。以下将对此作具体分析。
虽然这一时期内涵不断扩展的“秦人”内部存在“‘故秦人’、‘蛮夷’(二者都属本土之民)、诸侯之民等等之间的差异和‘分裂’现象”,③史党社:《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第358页。但新的“秦人”作为与新的“齐人”“楚人”“燕人”“韩人”“赵人”“魏人”等相对出现的族群概念,已经表现出鲜明的“我者”与“他者”的新区分模式。
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是“秦人”族群认同的转折点。“商鞅变法以行政和法律的力量,厉行‘耕战’;郡县制的实行,可以使政治的力量到达秦领土内的各个角落”。这时,“在秦地生有名籍的人,就是‘秦人’”。④史党社:《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第322、358页。“秦人”就是“皆言商君之法”的秦国政治体成员。⑤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59页。不仅如此,商鞅还使秦人摆脱了“戎翟之教”的影响,改变了秦人“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及“男女无别”的民风民俗。⑥《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4页。当然,秦人在礼义道德水平上仍与齐、鲁有差距。荀子有言:“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从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见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2页。秦人不仅在华夏化的道路上有了质的发展,而且国力得到显著增强。秦孝公逐步实现了秦献公当年“东伐,复缪公之故地”的理想,改变了“诸侯卑秦”的局面。⑦《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2页。而随着秦国东进以统一天下的步伐逐渐加快,秦国成为山东六国共同的敌人,所谓“秦欲与山东为雠”。⑧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第772页。又《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去楚,因遂之韩,说韩王曰:‘……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见《史记》卷七○《张仪列传》,第2293页。事秦的魏人张仪将“秦人”“秦卒”分别与“山东之士”“山东之卒”对言,也可见“秦人”与“山东人”的对立。见王子今曾指出,秦在兼并战争中实行的“出其人”及“募徙”“赐爵”“赦罪人迁之”予以充实的移民方式,“可能体现新占领区居民与秦人之间极端敌对的情绪,以及因此导致的秦军政长官对新占领区居民的不信任心态”。见王子今:《秦兼并战争中的“出其人”政策——上古移民史的特例》,《文史哲》2015年第4期。而从族群认同的角度来看,这也体现了秦人具有区分“我者”和“他者”的族群观。山东诸国也逐渐形成与秦对立的联盟集团,如魏人公孙衍将“伐秦”的韩、赵、魏、燕、楚等国称作“中国”,与“秦”对举,所谓“中国为有事于秦”。⑨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第115页。这样,“秦人”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群体与其他政治群体之间由于资源利益的争夺,形成了“我者”与“他者”的判然两分。①如《史记·秦本纪》记载:“楚人反我江南。”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3页。罗志田也指出:“古人族类观念的生成发展,常常也由于现实的军事政治需要。古代族群间的竞争不仅是文化的,同时也是一种生存竞争。在此竞争时代,人我之别的意义首先是强调族群意识以维护群体内的凝聚力。”见罗志田:《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当然,“秦人”与“山东诸侯人”的尖锐对立,仍有从礼仪文化上区别华夷的深深印痕。如《史记·魏世家》载魏信陵君无忌之言曰:“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②《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第1857页。仍将秦人视同戎翟。而将秦人或秦国视为“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的虎狼,可说是山东诸侯人的共识。如楚昭雎在劝阻楚怀王赴秦时就说:“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③《史记》卷四○《楚世家》,第1728页。又如苏秦也说:“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④《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第2261页。还如游腾也说秦是“虎狼之国”。⑤《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第2308页。尉缭则对秦王嬴政有“少恩而虎狼心”的评价。⑥《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0页。这些都是在文化道德层面对秦人的歧视。不过,尽管如此,强势的秦人因政治军事上的优势而在族群的识别和认定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又因其一直未放弃文化上的努力,故其在客观上逐渐主导了华夏的历史进程。
梳理相关文献,“秦人”称谓不仅出自齐人、周人、魏人口中,也出自秦人自己口中。⑦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第386、423、788、110、229页;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15页。而关于战国晚期的“秦人”称谓与认同,还可从简牍资料中获取更多情境性微观个案信息。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中的“尸等捕盗疑购案”有相关简文:
当我没有事的时候,我一直站在窗口。我的窗口向东,我的门口朝西,我们的阳光永远那样充足,一直到未来我才知道,原来你们的门窗都是向南的。我的房子的南面是一堵墙,但我还一直嫌它太亮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方向,我只知道窗户要对着太平洋,这样我就是这个国家第一个吹到太平洋的风的人。在岛的另外一边也有房子,他们面向的也许是南海,也许是东海,但从颜色上来说,那更像黄海。但谁管它呢?因为当你从窗口跳下去,就能在太平洋里游泳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对海里发生了什么感兴趣。
廿(二十)五年六月丙辰朔己卯,南郡叚(假)守贾报州陵守绾、丞越:子(谳):求盗尸等捕秦男子治等四人、[四○简正]荆男子阆等十人,告群盗盗杀伤好等。治等秦人,邦亡;阆等荆人。来归羛(义),行到州陵,悔[四一简正]□□□□□□攻(?)盗(?),京州降为秦,乃杀好等。疑尺〔尸〕等购。●(谳)固有审矣。治等,审秦人殹(也),尸[四二简正]等当购金七两;阆等,其荆人殹(也),尸等当购金三两。它有〚律〛令。[四三简正]⑧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113—117页。
此案发生在秦攻楚的后期,具体来说是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二月十七日,①据李忠林在《秦至汉初(前246至前104)历法研究——以出土历简为中心》一文末尾所附“秦至汉初(前246—前104)朔闰表”,秦王政二十五年二月朔日为戊午。参见李忠林:《秦至汉初(前246至前104)历法研究——以出土历简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故秦王政二十五年二月甲戌即二月十七日。这很可能在秦取楚之“郢陈”及“淮南江北之地”后和秦“定荆江南地”之前。②《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二十五年,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虏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五月,天下大酺。”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4页。“京州”很可能是邻近南郡州陵县的江南某楚地。从此案中可看到,作为案件的当事人,治等四人明确说自己是逃亡至楚国的“秦人”,而阆等十人明确说自己是“荆邦人”,即“楚人”。可见,当时的普通民众具有显著的“秦人”和“荆人”(即“楚人”)的族群区分意识。而对于政治领属的即时变化能否引起族群归属与认定的变化,州陵县廷长官不能确定,故请求上级决断。南郡长官最终认定治等四人为“秦人”,阆等十人为“荆人”(即“楚人”)。由此可见,治等四人为“故秦人”,即使有逃亡楚国的经历,也被认定为“秦人”。而阆等十人为“故荆人”(即“故楚人”),即使其在政治领属上已属秦,仍被认定为“荆人”(即“楚人”)。当然,治等四人很可能属于已被秦统治50余年的“南郡特别是州陵县编户民”,③琴载元:《秦代南郡编户民的秦、楚身份认同问题》,见杨振红、邬文玲主编:《简帛研究(二○一五·秋冬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9页。已经被同化成“秦人”,故自认为与被认为是“秦人”。④对于南郡居民的自我族群归属观,琴载元指出:“南郡设置初期,其居民基本上由‘迁徙民’与‘楚遗民’构成,而50多年后,其后裔都在当地出生长大,就成为‘故秦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南郡民认为自己是‘楚人’的可能性比较小。”见琴载元:《秦代南郡编户民的秦、楚身份认同问题》,杨振红、邬文玲主编:《简帛研究(二○一五·秋冬卷)》,第91页。而阆等十人所居楚地京州此时才刚刚入秦,故还是自认为与被认为是“荆人”(即“楚人”),且被南郡长官认定为“荆人”的时间是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即在秦已完全灭楚之后。
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中的“多小未能与谋案”也有相关简文:
关于此案发生的时间“十二月戊午”,整理者认为是“秦王政二十二年十二月丙午朔十三日”。⑥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第143页。而琴载元认为“秦军进军庐谿的时间也有可能是秦攻略‘荆江南地’的时候,因此秦生俘‘多’与文书书写时期会晚一些,其下限应在秦王政二十五年秦最终平定‘荆江南地’以前”。⑦琴载元:《秦代南郡编户民的秦、楚身份认同问题》,见杨振红、邬文玲主编:《简帛研究(二○一五·秋冬卷)》,第91页。不管怎样,此案发生在战国晚期。“故(?)秦人邦亡荆者”的表述,⑧“故秦人”的称谓也出现于《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中。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80页。强调的是“秦人”认同,而与其对立的无疑就是“荆人”(“楚人”)。
形成年代大致在秦孝公至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有“者(诸)侯客”“使者(诸)侯”等相关简文,①高敏指出:“根据出土《秦律》的内容,我们可以初步判明:它既不是商鞅变法时期制定的《秦律》的原貌,也不是撰写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而是在商鞅《秦律》的基础上,经过从商鞅死后到秦昭王这段时期逐步累积而撰写成的《秦律》。”见高敏:《云梦秦简初探》,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4页。不过,据整理小组介绍,“《法律答问》所引用的某些律文的形成年代是很早的”,有些律文“很可能是商鞅时期制定的原文”。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说明”,第93页。又有将“秦人”与“它邦耐吏(客吏)”对言的简文,②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第135、136、142页。也可见战国后期秦人与山东诸侯人的严格区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国秦与臣服于秦的蛮夷之邦“臣邦”的关系中,秦自称为“夏”,③《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可(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第135页。且将“臣邦人”与秦女通婚而生的“子”称为“夏子”。④《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可(何)谓‘真’?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谓‘真’。可(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殹(也)。”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第135页。这个“秦(夏)”的概念,已包含了“臣邦”。具体地说,这个“‘夏’是表达以秦为中心的两个结合关系的概念。一个是对秦的政治臣属,另一个是由秦人父向子所传续的血统。前者通过臣邦君主,形成了使其属下的人们也间接地归属的政治架构;而后者则以下嫁的秦人女性为媒介,构筑了让秦女所生的‘臣邦人(夏的孩子)’也归属的血统架构”。而从“产它邦”之子不是“夏子”来看,此时秦人观念中的“夏”是将“它邦”(山东诸侯)排除在外的。这或许表明,春秋时期“夷夏之辨”的族群认同格局在战国时期被“秦人非秦人之辨”的族群认同格局取代后,秦人单方面对“夏”概念作了狭隘界定。当然,此时秦人的“夏”概念还是有“夷夏之辨”的痕迹,正所谓“秦律以中原诸侯与戎狄蛮夷的差异为前提,就在两者之上以本国为中心设定了‘夏’的结构。这是战国秦为统一‘秦’以外各种各样的人们所构筑的,是特殊的‘中华’论”。⑤渡边英幸撰,李力译:《秦律的“夏”与“臣邦”》,见杨一凡、寺田浩明主编:《日本学者中国法制史论著选·先秦秦汉卷》,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66—267页。但令人遗憾的是,“秦人非秦人之辨”的族群认同格局从战国时期一直延续到统一后的秦帝国时期,始终未形成最大范围的涵盖山东诸侯的“秦(夏)”认同。
“秦人”与“非秦人”的族群区分延续到秦统一之后,里耶秦简中的“秦人”称谓也是明证:
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辛巳,尉守蜀敢告之:大(太)守令曰:秦人□□□Ⅰ
侯中秦吏自捕取,岁上物数会九月朢(望)大(太)守府,毋有亦言。Ⅱ问之尉,毋当令者。敢告之。Ⅲ8-67+8-652
这里的“秦人”及“秦吏”称谓,出现在秦洞庭郡太守之“令”中,时间是在秦灭楚之后,而且此“令”应是下发到包括迁陵县在内的洞庭郡各县,表明在秦洞庭郡各县有“秦人”和“秦吏”之特殊群体,这或许可看作秦代有“秦人”和“非秦人”之区分的又一证据。而在旧属楚地的迁陵县,似又集中表现为“秦人”与“荆人”(即“楚人”)的区分。③出土于里耶古城K11的户籍简牍特别标注了户主的出身国籍名——“荆”。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203—208页。此外,里耶还出土有未记录户主出身国籍的户籍残简。尹在硕曾言及这两类户籍简牍,认为“像这样在户籍上记录‘荆’这一点是在秦王政二十五年,秦完全占领楚国以后,为区别新民与秦内地的故民,因此标记有显示其出身国名的‘荆’”,而没有记录出身国名的户籍“可能是秦内地,即,故秦地区移住到迁陵县的故秦人的户籍”。此外,里耶秦简还有“二人其一秦一人荆皆卒”的简文。尹在硕指出:“可将其释为‘两名兵卒中的一名是秦人,另一名是荆人’,推定两人为同一部队的兵卒,但其出身被严格地区分为‘秦’和‘荆’。此种区分是以记录有两者的出身是秦故民,或是旧楚新民的户籍为基础的。”见张春龙:《里耶秦简所见的户籍和人口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研究——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91—194页;尹在硕:《秦朝的“非秦人”认识与占领地支配》,第80、81页。当然,还应注意到里耶秦简9-1145、9-2300号简有关“濮人、杨人、臾人”的记载。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2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68、466页。所载“濮人”“杨人”“臾人”,应为南方的蛮夷族群。可见,在秦帝国的南方,有“秦人”和“荆人”的区分,又有“秦人”和“濮人”“杨人”“臾人”的区分,这个多层次的族群区分是以“秦人”为中心而展开的。
由秦末反秦起义时的“秦人”称谓,我们也可看到秦代“秦人”与“非秦人”的族群区分。《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及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啗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憙,秦军解,因大破之。”“秦人”“秦军”之称反映的应是当时的族群观念。《史记·高祖本纪》又记载:“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秦人”和“秦王”之称,体现的仍是当时的族群观念。与“秦人”拥戴刘邦不同,对于项羽,“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④《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61、362、365页。《史记·天官书》还记载:“项羽救钜鹿,枉矢西流,山东遂合从诸侯,西坑秦人,诛屠咸阳。”⑤《史记》卷二七《天官书》,第1348页。“山东诸侯”与“秦人”仍是当时对立的两大族群。
《汉纪·高祖皇帝纪》:“韩生说羽令都关中。羽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韩生曰:‘人谓楚人曰沐猴而冠,果然。’羽闻之,怒杀韩生。羽所过残贼,秦人失望。”⑥张烈点校:《两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7页。项羽不都关中秦地,而要归故乡楚地,又被韩生称为“楚人”,对秦人的极端残暴措施使“秦人失望”,足见当时“楚人”与“秦人”的势不两立。不过,楚人刘邦对“秦人”采取的是怀柔政策。同为楚人的刘邦和项羽,对“秦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这除了因为两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追求有高低之分,很可能还因为项羽是楚人贵族,而刘邦只是楚人的下层,项羽的亡国灭族记忆要比刘邦沉痛得多。①《史记·项羽本纪》:“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0页。而刘邦是“起细微”。见《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0页。这也很可能就是后来楚人刘邦建立汉帝国后不再强调“楚人”与“秦人”、“楚人”与“非楚人”之区别的重要原因。而这促成了更具包容性的“汉人”称谓的产生。②关于汉代的“汉人”称谓与“汉人”认同,参见刘志平:《汉代的“汉人”称谓与“汉人”认同》,《人文杂志》2018年第12期。
“秦人”与“非秦人”的族群区分甚至延续到楚汉相争时期。据《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彭城惨败后,刘邦退居荥阳,面对项羽麾下来势汹汹的“楚骑”,刘邦“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刘邦“欲拜之”,李必、骆甲说道:“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刘邦“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③《史记》卷九五《樊郦滕灌列传》,第2668页。李必、骆甲明确说自己是“故秦民”,担心自己不能为众军士信服,可见此时仍有“秦人”与“非秦人”之族别观念。不过,刘邦大胆重用“故秦民”,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刘邦对“秦人”采取了包容、怀柔的政策,这对融“秦人”于一更具包容性的族群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综上,自战国至秦代,“秦人”与“非秦人”的族群区分得到凸显,原来以姬周华夏为核心展开的“夷夏之辨”的多层次族群认同格局,被以“秦人”为核心展开的“秦人非秦人之辨”的多层次族群认同格局取代,且形成了狭隘的“秦(夏)”认同。“秦人”与“非秦人”的族群区分甚至延续到楚汉相争时期。
三、汉代的“秦人”及其他相关称谓
拥有悠久历史的“秦人”虽然随着以嬴秦贵族为核心的政治体的覆灭而在现实族群称谓的表达上失去了昔日的强势主导地位,但“秦人”称谓本身仍在汉代的现实族群称谓表达中留下了印记。
《史记·大宛列传》有这样的记载:“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所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④《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77页。此处“秦人”称谓出自汉武帝时汉人之口,而同时又言及“汉军”,可知此“秦人”应为秦时入西域之秦人后裔,他们在汉代仍被称为“秦人”。《汉书·匈奴传上》:“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⑤颜师古注:“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见《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83页。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遗汉粮也,卫律于是止,乃更谋归汉使不降者苏武、马宏等。”⑥《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82页。此处“秦人”称谓出自汉昭帝时匈奴人之口,也与“汉兵”对言,可知此“秦人”应为秦时入匈奴之秦人后裔,他们在汉代也被称为“秦人”。
发现于19世纪末的东汉桓帝永寿四年(158)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刻石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谷关”的铭文。关于其中“秦人”称谓,王国维认为是指“汉人”。⑦王国维:《刘平国治□谷关颂跋》,《观堂集林(附别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79、980页。而李铁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在汉朝建国三百余年后的刘平国时,再称汉为秦则是不可思议的事……像刘平国这样具有汉绶官阶的将军,决不至于秦汉不分,沿称汉民为秦人了。还有种情况值得注意,在焉耆龟兹出土的文献中有‘秦人’和‘秦海民’的称谓,联系当地关于秦海的种种神话传说看,可知当地居民就把自己作为秦海的后裔来看待。再从刻石中提到的六人姓名上分析,如当卑、万羌、阿羌者,也都是以族别为名,姓为汉姓,这正是受汉文化影响后,‘渐慕华夏之风’改为‘姓中国之姓’的缘来……秦人在东汉时乃指秦海以西居民而言,古龟兹离秦海仅四百里,当然也包括在这个范畴之内。”①李铁:《汉刘平国治关刻石小考》,《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可见,李铁认为铭文中的“秦人”指“秦海”以西受汉文化影响的西域民。初师宾又提出第三种不同的意见,他指出:“姓氏于种族、宗亲关系中最为紧要,如排除政治原因而改姓的可能,此六人多汉姓,似属于汉族的可能最大,因久居龟兹地方,故又习用‘当卑’、‘阿羌’等胡名。这种情形,恰与颜师古注吻合,可见秦时入胡并非凿空之谈。”②初师宾:《秦人、秦胡蠡测》,《考古》1983年第3期。认为铭文中的“秦人”为秦时入西域之秦人后裔,已受胡风影响,在东汉仍被称作“秦人”。③初师宾在此所言“汉族”是以后世的概念来述说的,按其意,即指“秦人”。其在此文中已明确说道:“书明为秦人,知与汉人已不可等同……这区别就是:一是秦时胡化的汉人,一是汉时汉人。”见初师宾:《秦人、秦胡蠡测》,《考古》1983年第3期。联系上下文,所谓“秦时胡化的汉人”,其本意当为“在汉代仍被称为‘秦人’的秦时入西域之秦人已胡化的后裔”。考虑到“在张骞之前,中原经过西北地方与外域的文化通路早已发挥着促进文化沟通、文化交流、文化融汇的历史作用”,“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的贵族墓中曾经出土中国丝织品。巴泽雷克5号墓出土有凤凰图案的刺绣和当地独一无二的四轮马车。车辆形制和刺绣风格都表明来自中国。在这一地区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的墓葬中,还出土了有典型关中文化风格的秦式铜镜。许多古希腊雕塑和陶器彩绘人像表现出所着衣服细薄透明,因而有人推测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为希腊上层社会所喜好”,④王子今:《前张骞的丝绸之路与西域史的匈奴时代》,《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笔者认可初师宾的意见。若这样,秦人西入西域,不仅自称为“秦人”,也被西域人称为“秦人”,其后裔直到东汉仍被称为“秦人”。而“秦海”及“秦海民”也很可能跟东方之“秦”及西入西域之“秦人”有关。⑤“秦海”之名首见于《后汉书·西域传》所载敦煌太守张珰的上书中,其文曰:“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李贤等注:“大秦国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见《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1、2913页。按李贤等注,秦海似指西海——地中海,源于“大秦国”之名。余太山遵从李贤等注,认为“‘秦海’似应指大秦所临之海,即今地中海”。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35页。清人王先谦早有不同看法,他指出:“大秦在海西,去北匈奴绝远,呼衍王不得展转其间……疑匈奴中别有秦海,再考。”见王先谦等撰:《后汉书集解: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435页上栏。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西域都护府”图中将“秦海”标注在焉耆附近。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65—66页。再考虑到李铁的介绍,即“在焉耆龟兹出土的文献中有‘秦人’和‘秦海民’的称谓,联系当地关于秦海的种种神话传说看,可知当地居民就把自己作为秦海的后裔来看待”。见李铁:《汉刘平国治关刻石小考》,《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秦海应在西域焉耆附近,“秦海”之“秦”很可能跟东方之“秦”有关,因为“大秦”之“秦”都跟东方之“秦”有关,所谓“罗马帝国规模盛大,有类中国,中亚人称中国为‘秦’,故称罗马为‘大秦’”。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第157页。可见,西入西域的秦人不仅将“秦人”称谓带到西域,还对西域的地理称名产生了影响。
与汉代“秦人”称谓相关的又有“秦虏”“秦骑”和“秦胡”称谓。居延新简E.P.T8:15号简载有“秦虏”称谓,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1页。李烨认为“这里的‘秦虏’,即是汉朝人对业已胡化的‘秦人’的称呼”。⑦李烨:《“秦胡”别释》,《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王子今认为“‘秦虏’之称谓指代,大致是与西北民族形成融合,在生产方式、生活礼俗诸方面与内地民族传统显现一定距离的原中原民众”。①王子今:《说“秦胡”、“秦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所谓“原中原民众”,应是指“秦人”,故其意见和李烨相似。肩水金关汉简73EJT1:158号简载有“秦骑”称谓,且与“胡骑”称谓并举。②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下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1页。关于汉代的“胡骑”,王子今有过详细探讨,认为“胡骑”是两汉对北方草原游牧族骑兵的通称,包含匈奴、乌桓、鲜卑、羌胡、杂种胡等少数族骑兵。③王子今:《两汉军队中的“胡骑”》,《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李烨也有相似意见:“‘胡’在两汉当是对以匈奴为主的北方和西域民族的泛称,‘属国胡骑’也应是由多部族所组成的,除了匈奴外,还杂有羌、月氏等诸多北方和西域民族。”那么与“胡骑”对举的“秦骑”,该如何定义?李烨的意见或许是可取的:“如果汉时确有世居胡地的‘秦人’存在,那么这些尚在匈奴统治下的‘秦人’是有可能随着匈奴等胡族的归附后继续生活于‘属国’之中的。而胡人和秦人之属同被汉朝政府编入骑兵部队自然也成为了可能。胡人骑兵被称为‘胡骑’,秦人骑兵自然也就可以称为‘秦骑’。”④李烨:《“秦胡”别释》,《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王子今也认为“‘秦骑’,应与‘秦人’称谓有关”。见王子今:《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79页。
对于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所载“秦胡”的认识,意见纷呈:第一种意见认为“秦胡”是汉化的胡人;第二种意见认为“秦胡”是指“秦”和“胡”,分别指汉族人和非汉族人;第三种意见认为“秦胡”是胡化的汉人;第四种意见认为“秦胡”即“支胡”,是塔里木盆地土人之称号;第五种意见认为“秦胡”是秦地之胡;第六种意见认为“秦胡”是降汉的匈奴人;第七种意见认为“秦胡”并不特指某个少数民族或某地少数民族,而是一种政治身份或法律身份,在这一身份之下,又有种落、地域之分,如卢水胡、湟中义从胡、支胡等,总谓之“秦胡”;⑤以上七种意见参见胡小鹏、安梅梅:《“秦胡”研究评说》,《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第八种意见认为“‘秦胡’应分开理解,‘秦’是对秦时亡入胡地的华夏遗民的称谓,‘胡’是对北方和西域外族的统称”;⑥李烨:《“秦胡”别释》,《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九种意见认为“‘秦胡’之‘秦’,已经与‘胡’形成极其密切的关系”,并将“秦胡”之“秦”理解为“与西北民族形成融合,在生产方式、生活礼俗诸方面与内地民族传统显现一定距离的原中原民众”。⑦王子今:《说“秦胡”、“秦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最后一种意见虽然看似未将“秦胡”作为一个民族称谓整体来看待,但在解释“秦胡”之“秦”的民族属性时,又无疑是将“胡”融入了“秦”,从而实际上是将“秦胡”作为一个民族称谓整体来看待的。其实,要理解“秦胡”的真正含义,我们还需回到“秦胡”在《后汉书》中出现的族群场景。据《后汉书·邓训列传》记载,汉章帝章和二年(88),包含“烧当种羌”“武威种羌”等在内的“诸羌”与包含“月氏胡”在内的“诸胡”之间存在矛盾。在以烧当种羌迷唐为首的“诸羌”“先欲胁月氏胡”的情况下,邓训否定了许多人“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的意见,“令开城及所居园门,悉驱群胡妻子内之,严兵守卫”,致使“羌掠无所得,又不敢逼诸胡,因即解去”。于是邓训得到“湟中诸胡”的拥戴,“其中少年勇者数百人”成为邓训的“义从”。之后又因邓训对羌人有德义之举,故一些羌人“自塞外来降”。于是,邓训“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唐”。⑧《后汉书》卷一六《邓训列传》,第609—610页。中华书局点校本将此处“秦胡”断开,不可取。实际上,中华书局点校本在其他出现“秦胡”的地方又未断开,如《后汉书·段颎列传》所载段颎“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见《后汉书》卷六五《段颎列传》,第2153页。可见,邓训“发湟中秦胡、羌兵”的背景是因其采取“以德怀之”的策略而得到湟中“诸胡”和“诸羌”的拥戴,“秦胡”应和“月氏胡”一样,也属湟中“诸胡”之一。《后汉书·董卓列传》所载董卓上书,也言及“湟中义从及秦胡兵”。⑨《后汉书》卷七二《董卓列传》,第2322页。看来,“湟中诸胡”确实包含“秦胡”。此外,由居延新简“建武六年甲渠言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简册”可知,东汉初的张掖属国也有“秦胡”。①居延新简E.P.F22:696、E.P.F22:42、E.P.F22:322、E.P.F22:43,此应为一完整简册,其中E.P.F22:42和E.P.F22:322应缀合。参见邢义田:《“秦胡”小议》,见氏著:《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0页。联系前面所述秦时入西域或匈奴之秦人后裔有胡化的情况,又考虑到“湟中”和“张掖属国”恰好都在秦境之外,将“秦胡”理解为秦时入秦之西部外域之秦人已胡化的后裔或许是可取的。
此外,我们还可看到西汉人仍被匈奴人称为“秦人”的情形。《汉书·西域传下》载汉武帝罪己诏曰:“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②颜师古注:“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见《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14页。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③《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13页。此处“秦人”称谓是军候弘所引匈奴人之言,这无疑显示了“秦”及“秦人”对匈奴的深刻影响。
总而言之,到了汉代,拥有悠久历史的“秦人”虽然随着以嬴秦贵族为核心的政治体的覆灭而在现实族群称谓的表达上失去了昔日的强势主导地位,但“秦人”称谓本身仍在汉代的现实族群称谓表达中留下了印记。秦时入居秦境外的秦人后裔在汉代被称为“秦人”“秦虏”或“秦胡”,而匈奴人在某些场景仍称西汉人为“秦人”。
四、余 论
“秦人”称谓与认同在先秦秦汉时期遵循着这样的历史轨迹:周孝王时,非子被封于“秦”,号为“秦嬴”,“秦人”的族群意识已开始产生,“秦人”已开始作为一个族群登上历史舞台,但在西周时期,“秦人”称谓与认同是隐而不显的。春秋时期,随着嬴秦贵族所建立的政治体的不断扩张,“秦人”称谓与认同逐步得到凸显,但仍被笼罩在以姬周华夏为核心展开的“夷夏之辨”的族群认同格局中。正因为这样,秦人处在异姓、边缘华夏的位置。自战国至秦代,嬴秦贵族所建立的政治体继续扩张,且在文化上基本完成了华夏化,在与其他同样具有浓厚宗法血缘色彩、且在文化上也基本完成了华夏化的政治体的资源利益争夺中,“秦人”和“非秦人”的族群区分得到凸显。这样,原来以姬周华夏为核心展开的“夷夏之辨”的多层次族群认同格局,被以“秦人”为核心展开的“秦人非秦人之辨”的多层次族群认同格局取代,且形成了狭隘的“秦(夏)”认同。楚汉相争以后,“秦人”与“非秦人”的现实族群区分由于帝国上层精英的重组及帝国政治名号的改变而退出历史舞台,但“秦人”称谓本身仍在汉代的现实族群称谓表达中留下了印记,如秦时入居秦境外的秦人后裔在汉代被称为“秦人”“秦虏”或“秦胡”,而匈奴人在某些场景仍称西汉人为“秦人”。
关于春秋战国及秦代的“秦人”称谓与认同,有两个关键点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华夏之大认同一直是“秦人”认同的大背景,这不仅体现为春秋时期“秦人”对融入华夏的不懈追求,也体现为战国及秦代“秦人”单方面对“夏”概念的狭隘界定。因为“秦人”单方面对“夏”概念的狭隘界定正体现了“秦人”强烈的华夏认同意识,而且对“夏”概念的这种狭隘界定并不能消弭含纳关东诸夏的华夏之大认同,只是此一华夏之大认同因秦人狭隘的东方政策以及汉初对这一政策的历史惯性延续而被隐藏在历史舞台背后,待至西汉中期,才走上历史舞台。而形成和维持此华夏之大认同的主要因素就是由共同使用以《易》《诗》《书》等经典文本为主要载体的“雅言雅字”④“雅言”,即“华夏共同语”;“雅字”,即“华夏标准字”,不仅指以“雅言”为基础形成的“字”,还指此“字”有共同的形构标准(即“正体字”)。关于此,参见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修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张中行:《文言和白话》,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7—28、37页;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2—53、64、76、79页。和共同践行一套虽有历时、共时之差异但文化精神内核始终不变的礼仪文化制度而形成的共同文化心性。①这里的文化心性,是指由习用共同的经典文本、使用共同的书面语言(文字)、共同践行一套虽有历时、共时之差异但文化精神内核始终不变的礼仪文化制度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特质与文化价值取向。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分裂与对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各区域文化的差异,但在以《易》《诗》《书》等经典文本为主要载体的“雅言雅字”的使用方面与礼仪文化的关注和建设方面并没有发生改变。这在先秦典籍中不乏记载,兹不赘举。此共同文化心性不但未因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军事的分裂而受影响,也未因秦始皇的“焚书”政策而受影响,其深层原因大概是《易》《诗》《书》并不是待所谓“儒家”兴起后才成为华夏经典的,礼仪文化也不是待所谓“儒家”兴起后才产生的,而是都有着更久远的历史文化起点。此后,共同习用的经典文本的扩展和礼仪文化的更加成熟系统化,更加固了华夏早已形成的共同文化心性。这是带有局限性的“秦人”认同在汉代消失后,更具开放包容性的“汉人”认同得以产生的重要文化原因。②有学者在分析“华夏有关异族群的知识建构”时指出:“匈奴、鲜卑、百越等一定也积累了丰富的有关自身以及华夏的知识,可惜因为缺乏文献记录,这些声音在历史中湮没了。除了西域流沙中偶尔残留的一些非汉字材料,唐代以前有关东亚的知识只能找到汉字写下的记录。自4世纪以下,北方一些原本非华夏的人群进入并占据中原,留下了很多文字记录,在南方也有相当多的非华夏土著开始用中文留下自己的声音。但是,使用汉字和汉语进行写作,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难以跳脱先秦秦汉以来定型的华夏文化传统。从思维和表达方式到具体的知识,先秦秦汉的文献是他们唯一可以学习、模仿、取材的对象,他们虽然为华夏传统注入了一些新的内容,但最终的结果是让他们自己越来越与华夏无法区分。”见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第115页。所强调的非华夏族群使用汉字和汉语进行写作对他们的思维、表达方式、具体知识的深刻影响,与笔者所说的由共同使用以《易》《诗》《书》等经典文本为主要载体的“雅言雅字”而形成的共同文化心性有相通之处。而赵汀阳更指出:“如果需要对中国文化给出一个最具特征性的描述,也许可以说,那是一个以汉字为主要载体,有核心基因而无边界的开放兼收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一直在生长过程中,历史上已经吸纳了众多文化的信息,在多种文化的互化过程中,制度、服饰、美术、音乐、饮食、工具、语音、习俗皆多有变化,唯有作为精神世界载体之汉字保持其超稳定性,而汉字承载着中国文化最为根本的基因。”见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24页。这个带有历史哲学性的表达,可以说触及了中国文化的深层本质。
其次,嬴秦贵族所建立的政治体的消长决定着“秦人”称谓与认同的隐没与凸显,即血缘和政治也成为构建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嬴秦贵族建立的政治体和其他贵族建立的长期与其对抗的政治体都有着久远的历史,这是“秦人”称谓与认同得以展开的客观历史情境基础,也是“秦人”认同必然在一定时期内带有局限性的客观原因。秦帝国历时的短暂及其狭隘的东方政策使得“秦人”认同的局限性永远留在历史的遗憾中。刘汉取代嬴秦,帝国政治体上层的激变性重组和帝国政治名号的改变,使“秦人”和“非秦人”的现实族群区分消失在新的帝国政治体中,这表明政治力量在“族群”认同构建中起着重要作用。刘汉继承嬴秦的帝国政治遗产,在政治整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并成功抵达理想的终点,同时又在对凝聚族群认同起重要作用的共同祖先及历史传说上作了成功的构建,③史党社认为同秦代上层精英相比,汉代上层精英在共同祖先的构建上要做得好些,即“把五帝奉为‘汉人’的祖先,使自我族群顺利地完成了从战国‘华夏’到‘汉人’构建的过渡。司马迁把《五帝本纪》列为《史记》之首,就是汉代人重视‘五帝’这个族群标志的体现”。见史党社:《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第360页。在宗法专制色彩浓厚的古代中国,上层精英对虚拟血缘的构建和强化,可以稀释到政治体内的各个阶层,而汉代正是这个重要构建初步完成并成功地稀释到各阶层的历史关键期。故在西汉中期形成了融政治、文化、血缘和族群于一体的“汉人(华夏)”认同。④刘志平:《汉代的“汉人”称谓与“汉人”认同》,《人文杂志》2018年第12期。
西汉中期形成的这种“汉人(华夏)”认同突破了战国秦及秦帝国“秦(夏)”认同与汉初“汉人”认同的局限,达到了族群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三者之间相对一致的稳固状态(这种稳固状态又带有开放包容性),这奠定了后世中国在族群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等方面向心内聚的坚实基础。以后每一次冲击和挑战,都带来了这种稳固状态的一次升华。这或许就是中国最核心、最本质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