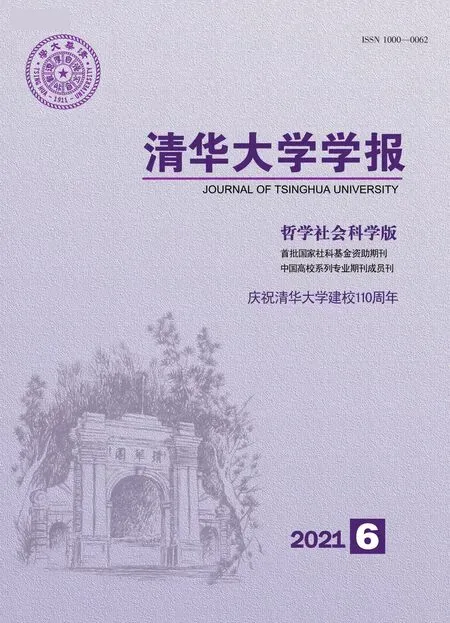从“盟府”到“杏坛”:先秦“书”类文献的生成、结集与流变
程 浩
“书”是由史官对君臣言论实时记录形成的档案整理而成,作为“政事之纪”的一类文献。①关于“书”类文献的定义及其范围限定,详见程浩:《“书”类文献辨析》,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8辑,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139—145页。这类文献在当时的功用在于“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天下”,②刘知几:《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页。即将帝王君公的治国理念敷闻天下、统一思想,③中国古代有着“言以化人”的传统,尤其强调政治演讲的思想教育功用。将今论古,我们今天开展“两学一做”活动中的“学系列讲话”,便很好地承袭了这种悠久传统,是以政治演讲生成的官方档案开展思想教育的鲜活示例。而流传到后世,则更多地起到了教化后嗣的作用。
本文所讨论的“书”类文献,其范畴不局限于传世《尚书》与《逸周书》中的篇目。就其“政事之纪”的属性与记言为主的特点而言,新见相近体裁的战国竹书以及西周金文中的长篇训诫、册命均可隶属此类。④《国语》一类的“语”类文献体裁也是记言,其与“书”类文献应该如何区分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对二者以时代进行划分:总体而言,被称为“书”的文献时代普遍较早,基本上属于夏、商、西周;而春秋以后的记言文献,则大多被称为“语”了。至于“书”与“语”之间的这种差别,或许与春秋战国时人对“三代”的尊隆有关。比如《墨子》常称引商周的“书”为“先王之书”,引述近人的话则称之为“古者有语”,这种现象说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古代圣王的作品“书”本就是有别于时人的言论“语”的。而《尚书》《逸周书》由于自身流传过程的复杂性,其中亦杂糅了一些比较特殊的篇目:如《禹贡》《克殷》《世俘》《作雒》等,内容虽然都来源有自,但并非君臣对话,前人早已称其“例不纯者”;①刘知几:《史通》,第4页。又如《尧典》《皋陶谟》《甘誓》《洪范》等篇,②关于《洪范》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向有争论,我们倾向于该篇主体部分的生成要晚于其所声称的商末周初。相关讨论,详见刘节:《洪范疏证》,见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88—403页;刘起釪:《〈洪范〉成书年代考》,《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杜勇:《〈洪范〉制作年代新探》,《人文杂志》1995年第3期。其成书显然晚于篇中所声称的时代,应是出自后人的构拟,可别作“泛‘书’类文献”。③我们知道,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曾兴起过一股仿写“书”类文献的风潮。《汉志》在著录先秦流传至汉的古书时,即常称某书为“依托”,指的就是这种托名仿写的现象。这些篇目中构拟的对话并非对历史现场的如实反映,因而不能与“书”等量齐观。考虑到其似“书”非“书”的特点,以及在当时就有被误认为“书”的情况存在,不妨以“泛‘书’类文献”称之。总而言之,《尚书》《逸周书》虽然被视作“书”类文献的合集,但由于其结集时间并不是太早、成书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其中既有作为商周时期历史记录的“书”类文献,同时也掺杂了春秋战国时期仿写的泛“书”类文献以及体裁不属于“书”的记事文献等。这些虽然都是真实的先秦文献,但其史料品质上的差异却是研究者不得不加以注意的。对于这些特殊的篇章,本文在考虑“书”类文献生成的过程时,暂时将其排除在外。④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书”类文献源流久远,即便是战国时代的人对其性质的认识也已经不见得特别准确,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一些战国时期的文献已称部分例不纯的篇目为“书”。但这种情况出现得并不是太多,或是由于不同时代对“书”的概念把握尺度也并不如一,同时也可能受了一些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对“书”类文献的划分,是应该遵循其本初的性质,还是信从后世被“污染”过的结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方面的论辩,可参见章宁《“书”类文献刍议》(《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1期)、李锐《清华简第九册〈成人〉篇为〈尚书〉类文献说》(《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2期)等文的综述。
作为“六经”之一,历代学者对《尚书》的研治可谓孜孜不倦,相关著述也是卷帙浩繁。但是在传统的《尚书》学中,关于“书”类文献源流的研究却并非主流。近代以来,由于新史学的传入对传统经学造成了极大冲击,《尚书》学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围绕着《尚书》成书、流传以及学术史的研究在学术界逐步展开。陈梦家、蒋善国、刘起釪、程元敏等先生均撰有《尚书》学史的专书,⑤陈梦家:《尚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刘起釪:《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程元敏:《尚书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对“书”类文献的性质、名义、体裁、源流等进行了全面总结,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就。
先哲时贤就“书”类文献源流研究做出的大量工作,几乎将相关研究推到了顶峰。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批简帛古书的出土,又为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新的可能。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中有多处引“书”、论“书”的内容,近年问世的清华简中更是发现了大量的“书”类文本,⑥目前公布的清华简中属于“书”类的篇目,至少有见于百篇《尚书》的《金縢》《尹诰》《傅说之命》《摄命》,见于《逸周书》的《程寤》《皇门》《祭公之顾命》以及文体绝类《尚书》的《尹至》《厚父》《封许之命》《四告》(仅限前两篇)等11种。至于《保训》《命训》《成人》等,盖出自后人拟托,应归为“泛‘书’类文献”。具体内容详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整理报告,本文以下引用清华简释文不再备注。较多地保留了这类文献的原始形态,使我们有了重新认识其成书过程的新契机。本文将结合新出土文献提供的线索以及古书中的相关记载,对“书”类文献在先秦时期的整理成篇、结集成书以及版本流变的过程进行尝试性的探索。
一、作为单篇的“书”的编纂与生成过程
熟悉古书通例的学者都知道,先秦以前古书以单篇流行者居多,⑦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5—268页。本文所讨论的“书”类文献本非一时之作,自当不会例外。“书”类文献的生成,必然经历了由原始材料整理成篇,再由单篇结集成书的过程。故而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将先集中讨论“书”类文献在篇这一形态下的一些基本情况。
(一)“书”类文献编纂的材料来源
“书”类文献最大的特点乃是以记言为主。大约写成于战国中晚期的郭店简《性自命出》篇,有一段对文献生成来源的描述,其云:
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①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79页。上博简《性情论》亦有此语,但与该篇基本没有差异。
简文的“有为言之”一句,阐明了“书”的记言性质。《汉书·艺文志》也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②班固:《汉书》卷三○《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左史”与“右史”的执掌虽然仍存争议,但“言为《尚书》”的说法基本是被接受了的。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即云:“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③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2页。认为“书”类文献就是从行政过程中的文书档案演变而来的。刘知几《史通》也说:“《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天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④刘知几:《史通》,第4页。其云《书》“本于号令”,乃是承认了“书”类文献编纂的材料来源就是君臣言论记录形成的档案文书。覆视传世《尚书》,其篇章也基本以记言为主。个别例外者,如《金縢》的后半篇记述了周公居东后的灾异。但这些内容总体来说时代较晚,很可能来源于后世的“层累”,并非“书”之原貌。⑤艾兰也认为:“传世《尚书》中的一些章节不含演讲,这些章节为数不多并相对较晚。”见艾兰:《何为〈书〉?》,《光明日报》2010年12月20日,第12版。
艾兰近年在分析“书”的起源时提出了一种假设,她说:“‘书’一开始是官员为了在正式仪式上代表君主或大臣讲话而事先准备的讲话稿”,并认为讲话的简册最终给了讲话的对象,而在皇家档案馆还有份副本。⑥艾兰:《论〈书〉与〈尚书〉的起源——基于新近出土竹简的视角》,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50—651页。实际上,将“书”篇与西周的册命金文联系起来,并认为册命是史官预先写就的观点,阐述得最为详尽的要数陈梦家。⑦陈梦家:《王若曰考》,见氏著:《尚书通论》,第143—166页。这种看法的主要依据在于,在册命铭文记载的命官仪式中,有一种物质形态的“册”,一般由王授权史官代宣。李峰穷尽式地分析了目前发现的册命金文,对这类“册”有了一个基本判断:
这个书面命令很可能事先已准备好,并在册命仪式开始前写在竹简上;内容有时详细记录了所授予职官的名称及实际的行政职责。大多数情况下,册命文件会由宣读者口头宣读出来。文件上面还详细列出一份长长的赏赐品清单,包括鬯酒、官服、玉器和车马等,有时甚至会有土地;赏赐物往往是以上几种物品的不同组合。⑧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12页。
这种记载任命官职、罗列赏赐物品的文书当然可能提前写就,并在册命仪式中由史官宣读后交给受命者留存。但是这个“册”里的文书是否就等同于铭文之后记载的“王曰”或“王若曰”引领的内容,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张怀通《“王若曰”新释》一文便反对将其等量齐观的做法,他认为二者“一是命书,即委任职务的文书,一是王就委任而作的讲话”。⑨张怀通:《“王若曰”新释》,《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任命文书当然可以由内史预先代拟,在仪式中颁发给受命者作为凭证;但王的讲话恐怕还是即兴为之,并由史官记录整理后成为一篇“书”。册命金文对册命仪式记述较为详尽,有的时候长篇铭文中史官宣读任命文书的过程与王就此作的讲话俱在。而经整理成为“书”类文献后,一般就对册命仪程一笔带过,或仅保留王的讲话了。①清华简的《摄命》篇即详细记录了王的讲话,而对册命仪程仅用最末一支简进行了简要描述。至于《封许之命》《文侯之命》等篇,则全然不见此类内容。最近又有学者以册命文体为例指出在西周时期有“王的口头讲话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以及“直接以文字的方式撰写王命”两种文本生成机制,并认为前者流行于西周初期,而后者在西周中期以后占主导地位。②李冠兰:《西周册命文体的文本生成》,《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在我们看来,这种调停似乎没有必要,因为二者本就是在一场册命中发挥着不同功用的两种文本,在文本生成机制方面也应视作共时关系。
陈梦家这种“书”由史官预先拟写的观点,放诸不同体裁的“书”类文献中进行检验,其■格更为显著。我们大家都知道,“书”类文献虽以记录王命为主,但以君臣对话为主题的篇目亦不在少数。比如《厚父》与《祭公》等篇,就分别为王与厚父以及王与祭公的问答。即便我们承认篇中“王曰”的内容存在史官草拟的可能,但厚父、祭公等人的大段回答却无论如何不会出自史官代笔。而且“书”由史官预先拟写的假设似乎也无法解释几乎每篇“书”中都会出现的“呜呼”等叹词以及“拜手稽首”等动作描写。因为如果“书”是事先写好的讲话稿的话,很难想象起草文稿的人会把语气词以及动作也提前写进去。③程元敏即云:“《尚书》载君主当时口语,号令天下,篇中多见语气词,如都、俞、於、惟、呜呼、猷……俱是直录发话者叹词。”见程元敏:《尚书学史》,第15—16页。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把“书”看作是史官对君臣讲话的实时记录或事后记载。④关于“书”究竟是本自现场记录抑或事先准备的讲话稿,还可以借鉴现代的秘书规范进行人类学的考察。我们知道,一般的领导讲话虽然都会提前拟好讲稿,但在实际发言过程中仍然会有很多自由发挥的成分在里面。为了忠实地体现领导讲话的原貌,一般正式出版发行的领导讲话单行本(如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都是在现场记录的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虽说在后期编辑过程中也可能会对提前准备好的讲稿进行参考,但现场记录才是其文本的直接来源,这一环节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史官制度起源甚早,君主的一言一行都有史官负责记录、存档与保管。如《汉志》即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⑤班固:《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15页。商代的史官名曰“作册”,见于卜辞与商代金文的即有“作册西”(《合集》5658)、“作册丰”(《集成》2711)与“作册般”(《集成》944)等。到了周代,不仅有见于《耆夜》的“作册逸”,还有了《酒诰》中的“太史友、内史友”,史官系统较商代更为丰富。
根据现在对商周职官制度的研究,史官作为重要的王官系统,其执掌范围不局限于记言记事等文书工作。比如金文中大史的地位就非常尊隆,相当于王的助手与顾问。⑥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页。但是对于内史、作册等基层史官而言,现场记录君王与臣下的对话仍是其重要职责。张怀通认为史官作现场记录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快速记录……二是由多个史官同时轮流记录,每个史官只记录一两句话,待讲话结束后将所作记录汇总起来,布政之辞中多次出现的‘王曰’或‘曰’就是每个史官在所记文字之前作的标记”,并引用了西方学者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结果来论证“轮流记录”存在的可能性。⑦张怀通:《“王若曰”新释》,《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我们认为以分组轮流记录的方式进行现场记录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因为讲话的内容本身很难预测与把握,在不进行沟通的情况下分工进行记录似乎难以达成。更有可能的还是由两名及以上的史官同时进行记录,事后再进行汇总与校雠,并进行必要的整理工作。至于张先生提出的“王曰”或“曰”,应该就是史官在后期整理过程中添加的表示转折的语词。
由于史官与“书”的这种密切关系,周代的“书”篇在全篇之末多有关于史官的记载。如《洛诰》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7页。 1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409页。《顾命》亦云:“太史秉书,由宾阶,御王册命”,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0页。都昭示了史官在王宣告政令时的重要作用以及之后整理文献的重要职责。最显豁的例子见于简本的《金縢》篇,其云:“周公乃纳其所为功自以代王之说于金縢之匮”,传本对应之处作“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这里的“说”与“册”所指就是前文中周公的祷词。这些祷告之辞经史官记录在竹简上,就变成了可以纳入金縢之匮的“说”与“册”。也正因如此,简本《金縢》自书的篇题便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
在国家运转与日常行政过程当中,由于君臣对话的场合、事由、对象各异,就会造成记言档案类型的不同。唐代孔颖达认为《尚书》是“因事立言,既无体例,随便为文”。③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17页。葛志毅通过对《尚书》中政令文件的分析,进一步指出:“《尚书》的文本体例形式,原是出于现实政治关系的需要而产生。”④葛志毅:《试据〈尚书〉体例论其编纂成书问题》,《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2期。换言之,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书”类文献内部体裁的差异,乃是由于其发生场合与产生原因的不同。传统《尚书》学根据百篇“书”的篇名将“书”类文献的体裁总结为“六体”“十例”,⑤“六体”说源自《书大序》:“先君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十例”为孔颖达《尚书正义》之说,其文云:“致言有本,名随其事,检其此体,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诰、七曰训、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使我们对“书”的分类有了大致的认识。但实际上大部分“书”的篇名都出自后人之手,并非该篇作成时所加,因此基于篇名的归纳在很大程度上难得其实。⑥宋人林之奇对这种方法早有批评,详见林之奇:《尚书全解》,见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儒藏》精华编第1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4页。陈梦家曾以内容为标准将传世《尚书》的篇目分为“诰命”“誓祷”“叙事”三类,⑦陈梦家:《尚书通论》,第312页。最近我们又根据出土文献的新启示在此基础上将其修正为“训诰”“册命”“誓祷”三类,⑧程浩:《从出土文献看〈尚书〉的体裁与分类》,《文艺评论》2017年第3期。基本上可以涵盖“书”类文献生成的材料来源。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划分,实际上也是为了与日常行政的行为类型相呼应。君臣间的一般对话形成“训诰”,这其中包括了君主对臣下的训示、臣子对君主的规劝以及二者的互相问对。古代君王重视以德宣教,如《盘庚》《大诰》《酒诰》等篇主要内容即为君主教训臣下。君可诰臣,臣亦可训君,《尹诰》《厚父》《立政》《祭公之顾命》等篇便为君向臣乞言或者臣子的主动规劝。在早期国家的治理结构中,分封与册命是基本的统治手段,而君主对臣下分封、命官过程中的言辞就形成了“册命”类的“书”。传世《尚书》中的《康诰》与《文侯之命》、清华简的《傅说之命》与《封许之命》即是此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君主在誓师、田猎、祭祀等重要仪式中发表的讲话,便是“誓祷”类“书”的来源。《牧誓》《费誓》《秦誓》以及《尹至》《金縢》《四告》等篇,其编纂材料的来源便是誓祷过程中对誓词、祷词的实时记录。
(二)档案文书的整理成篇与不断“层累”
史官在对君王的言论进行现场记录后,就形成了官方的档案文书。这些档案或“书于竹帛”,成为简册,藏于“盟府”之中。如《逸周书》的《尝麦》篇,篇末即云“太史乃藏之于盟府,以为岁典”。⑨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49页。《尚书·多士》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⑩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0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有的现场记录并不书写在竹帛之上,而是“镂于金石,琢于盘盂”,如《礼记·大学》引有《汤之盘铭》,又《逸周书·大聚》篇末载武王“乃召昆吾冶而铭之金版,藏府而朔之”,⑪就是以铜版为载体对这份档案进行了留存。此外,清华简的《封许之命》篇格式与册命金文非常相近,很多字形遗留了西周金文的写法,很可能就是由一篇青铜器铭文转写而来的。
对于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将言论记录形成的档案文书“藏之于盟府”并不是其最终目的。政治演讲生成的官方档案,除了在当时“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天下”,把时王的治国理念敷闻天下、统一思想外,还要满足后世之君以史鉴今以及垂训后代的政治需求。如《国语·周语下》云:“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①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98页。即是强调了“书”传遗子孙的功用。上博简的《武王践祚》篇记载了武王向师尚父问道,师尚父以“书”答之的故事:
武王问于师尚父,曰:“不知皇帝、颛顼、尧、舜之道在乎?意微丧不可得而睹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如欲观之,盍斋乎?将以书示。”武王斋三日,端服冕,逾堂阶,南面而立。师尚父曰:“夫先王之书,不与北面。”武王西面而行,矩折而南,东面而立。师尚父奉书,道书之言,曰……②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8—168页。释文采宽式,部分释读根据学界的意见进行了改释。
武王欲观览先王之书,不仅要先“斋三日,端服冕,逾堂阶”,还不能南面而立,足见周人对这类文献教育意义的重视程度。而正因如此,这些“藏之于盟府”的档案文件才会被整理编纂成“书”类文献,并流出王家秘府,为后人广为传诵。
虽然“书”类文献出自史官对君臣言论的记载,但现场记录形成的文书档案并不能直接与“书”类文献划等号。这些实时记录必然是经过了事后的整理与再加工的过程,才能成为一篇单独流传的“书”。可以想见的是,商周时期的贵族即使都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但其在行政过程中的即兴发言不经整理即可成为一篇严整的文本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更何况负责实时记录的史官即使经过了快速记录的训练,但囿于书写材料的限制,也很难做到完整无缺地记录一场仪式中所有的发言。因此,现场记录的工作可能是由两名以上的史官共同完成,并在事后再进行汇总与整理的。
以上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史官在完成了现场的实时记录后,事后还必须对当时形成的文本进行整理与加工。除了对发言者所用词句的疏通外,最常见的对文本整理的痕迹是引领语句或表示转折的“王曰”与“王若曰”等。如《康诰》除篇首介绍故事背景的一段外,正文中成王的发言即以“王若曰……王曰……王曰……王曰……王曰……王曰……又曰……王曰……王曰……王曰……王曰……王曰……王曰……王若曰”的形式进行分割。这样的处理应该是考虑到对发言的原始记录晦涩而冗长,如果不加入“王曰”表示转折,就很难读通、读懂。而所谓“王若曰”即“王如此说”,是史官在后期加工时所添加的标志,表示该篇为君王所说,史官所记。有学者认为“王若曰”与“王曰”等为史官代写册命时所书的特殊用语,在句中并没有表引领与转折的功能。这当然是由于其以“书”为事先拟写而非现场记录的预设所致。但此类说法似乎很难解释《尚书》的《康诰》以及清华简的《摄命》中多次出现的“又曰”的用法。如果说给“王曰”赋予特殊的意义尚可解释,但“又曰”表转折的用意则甚为明晰。由是观之,“书”类文献中的“王若曰”“王曰”“又曰”等仍当为史官对现场记录进行后期整理时所添加,其后所引领的并非事先书于简册的任命书。
另外一种情况是一篇中有两人或两人以上参与对话。如清华简的《祭公之顾命》,既载有穆王的“乞言”,也有祭公的“顾命”。③张怀通亦曾根据《祭公》篇分析过“书”类文献记录与生成的过程。张怀通:《清华简〈祭公〉解构》,见氏著:《〈逸周书〉新研》,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22—327页。针对这种情况,史官在整理该篇时就加入了“王若曰……祭公拜手稽首曰……王曰……王曰……王曰……公懋拜手稽首曰……曰……公曰……公曰……公曰……曰……公曰”等语,以区分其发语者。除了“王曰”“公曰”等表示发言者身份的词语,一些发言者的动作也会被加入到文本中,如《召诰》《洛诰》《立政》的“拜手稽首”以及《顾命》中的“再拜稽首”、《祭公之顾命》中的“王拜手稽首誉言,乃出”等。李山通过将此类词语与西周金文进行比对,指出整理加工的过程发生在西周中期。①李山:《〈尚书〉“商周书”的编纂年代》,《西北师大学报》2011年第6期。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这类最基本的润色加工最有可能还是由负责记录的史官在讲话结束的现场所作的“第一轮整理”。
君主言论的现场记录在经过史官的“第一轮整理”后,就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文本。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祭公之顾命》中穆王与祭公对《君奭》《顾命》等篇的引用,就会发现其与今传《尚书》中这些篇目的文句差距并不是很大。该篇的“兹迪袭学于文武之曼德”一句,是对《君奭》“兹迪彝教文王蔑德”的引用。②陈剑据清华简校订《君奭》文为“兹迪彝〈(袭)〉教(学)文王蔑德”。陈剑:《清华简与〈尚书〉字词合证零札》,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李学勤先生八十寿诞纪念论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213页。除了字词的近似之外,这两句话在两篇“书”中出现的语境也十分值得玩味。《君奭》篇为周公诰召公所作,此语即是周公训诫召公所说的话。而到了《祭公之顾命》,此句虽是穆王所述,但“兹迪袭学于文武之曼德”的主语乃是“祖周公暨祖召公”,赞美的仍是周公与召公的德行。此外《祭公之顾命》的“敢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王受之,惟武王大败之,成厥功”一句,《尚书》的《顾命》篇有一段表述与之极其近似:“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③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4页。这种现象提示我们或许在《祭公之顾命》所作之时,《君奭》《顾命》等篇已有较成熟的文本并为穆王、祭公等贵族所熟稔。只有这样,《祭公之顾命》对这两篇的引用才能与今所见文本如此一致。而《君奭》《顾命》作于成王之时,《祭公之顾命》成于穆王,相距不足百年。也就是说,上述篇目的主体即对话部分,应该在该篇发生的当时或不久后就已经整理成形了。
然而,由载笔史官所作的“第一轮整理”对充分发挥“书”类文献的教育功能是远远不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已经不甚明晰这些“书”作成的时代与故事背景。这就必须开展“第二轮整理”,为“书”篇添加一些故事背景与情节的描述。我们仍然以《康诰》为例,在“第一轮整理”时,载笔史官为该篇增加了“王若曰”与“王曰”等表示语义转折的词语,而到了“第二轮整理”,就在篇首增加了一段描述该篇发生的故事背景的话: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2页。
相同的处理方式亦见于《牧誓》: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2—183页。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9页。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⑦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7页。
以及清华简《皇门》:
惟正[月]庚午,公格在皇门。
清华简《傅说之命》的上篇,也多是对王得傅说故事的叙述。有学者据此怀疑其为该篇之“序”,①赵平安:《试析清华简〈说命〉的结构》,见氏著:《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续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67—269页。实际上它的情况应该与上述文句一样,是对“书”篇的“第二次整理”时所加。而这种为“书”篇增加情节描写的工作,很可能是出自该篇作成时或不久后史官的整理,毕竟现场的许多细节后人殊难知其详。有的时候史官的整理工作也并不包括此类内容。比如像《大诰》《酒诰》《无逸》《君奭》《立政》以及清华简的《祭公之顾命》等篇就是纯记言,没有经过“第二次整理”,这就说明为言论记录增加情节描写并不是史官整理文本时的必须步骤。
现场记录的档案文书经过两次整理后成为单篇的“书”,这一过程在清华简的《摄命》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摄命》或即《尚书》中失传已久的《囧命》,共有32支简,篇幅长达近千言,在“书”类文献中几乎无出其右者。该篇前31支简的内容全部是王对伯摄的训诫,由于讲话过于冗长,其语意多次出现转变、反复、跳跃。为了明晰层次、疏通条理,史官在对该篇的“第一轮整理”中大量添加了“王曰”“曰”“又曰”等以示折转。除了篇首领起全文的“王曰”外,全篇中“王曰”又出现了10次,表转折的“曰”以及“又曰”各出现2次与3次。有了这些分割标志的提示,后来的读者才能勉强把这篇“书”读通。
该篇的第32支简,根据简背的序号可知应与前31支相连,同属一篇当无疑问。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第31支简并没有写满,而是写了不到半支简就留白了,并且在该简的最末一字下还添加了一个绝止符号表示篇章完结。这说明在该篇的抄写者看来,第32支简的内容与前31支是相对独立的。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前31支简的内容全部是王的讲话,但是第32支简却全然不同,所描述的是时间、地点以及王对伯摄的册命仪程。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传世《尚书》的《洛诰》篇之末也是在王的讲话后描写了一系列仪节,其文云: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7页。
该篇与《摄命》如出一辙,也是先记载了王与大臣的对话,又描述了与之相关的背景与仪节。从《摄命》的抄写者将此类内容置于篇末,与王的讲话“区别对待”来看,这些时间、地点以及情节描写的内容,来源还应该是史官对“书”的“第二次整理”时所添加。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第二轮整理”的时间一般要晚于文本生成的时代,负责整理的史官也未必曾亲临现场,因此这些后添加的内容有的时候不见得一定准确。就比如清华简《四告》第二篇开篇的“曾孙禽父拜手稽首”等语应该就是“第二轮整理”的产物,但“禽父”是发言者的字,在神灵面前自称表字显然与上古的称名习惯不合。③程浩:《清华简〈四告〉的性质与结构》,《出土文献》2020年第3期。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大概就是后世史官在重新抄写、整理该篇时担心后人不能辨析作者身份,就根据自己的错误认识添加了“曾孙禽父”四字。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反过来印证了“书”的成篇一般都会经历后世二次整理的过程。
史官对旧有的档案进行“第二次整理”,有的时候还会将内容相近的若干篇进行合并。比如《尚书》的《多士》与《多方》,④陈梦家认为《多士》《多方》中的这种情况是由于两篇在成篇过程中互相参照附益(《尚书通论》,第163—164页),最近张怀通从体例角度进行了辨析。张怀通:《大克鼎与〈多方〉体例研究》,见王志东主编:《东夷文化论丛》第1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6—135页。每篇都分别记载了两次周公的训诰,而据学者研究,单篇所记两次诰命之间相隔的时间还有可能会非常的长。①张怀通:《〈多方〉两个“王若曰”发布的时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590,2020年6月28日。此外《召诰》《洛诰》两篇所载事语甚为杂乱,顾颉刚就怀疑“两诰之命经过周秦人的重编,把断篇残简合而为一,遂致其事参杂,其语凌乱”。②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6页。刁俊豪最近对《洛诰》的篇章结构有细致的分析,见刁俊豪:《再论〈尚书·洛诰〉篇章结构》,未刊稿。清华简《四告》中的第一篇,也载有周公在前后两天内进行的两次祭祷,全篇可由中间的“翌日”分割为两部分。③程浩:《清华简〈四告〉的性质与结构》。这些不同时间记录的档案,由于作诰者相同、思想内容互通,遂被负责二次整理的史官归为了一篇。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收入《尚书》的《金縢》等篇虽然都属于“书”类文献的范畴,但在其文本中却充斥着大量叙事的内容。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这些篇目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又遭到整理、增补,文本经过了不断的“层累”所致。就以简本与传本互见的《金縢》为例,根据内容可将其划分为“周公自以代王”“周公居东”“成王启金縢之匮”三章。其中“周公自以代王”章内容古奥,应该出自史官对周公祷词的记录,而且简本的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所指就是这一部分,证明了这一部分在全篇中的特殊地位。至于“周公居东”与“成王启金縢之匮”两章,内容多怪力乱神之语,因此前人早有怀疑。④苏轼:《东坡书传》卷一一《金縢》,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51页;于省吾:《双剑誃群经新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55页。我们通过分析这两部分“于”“於”二字的用法,同样得出了《金縢》前半篇为原始材料与核心内容,后半篇为后人所增的看法。⑤程浩:《清华简〈金縢〉性质与成篇辨证》,《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如果我们对《金縢》的成篇过程加以总结,大致会是这样一条路径:首先是周公的祷词由史官记录成册,原始记录形成的文本就是简文所说的周公纳于金縢之匮的“所为功自以代王之说”;其后,史官在仪式结束以后根据副本加以整理,藏之于“盟府”,是为“第一轮整理”;再后来有人对其进行了“第二轮整理”:添加了篇首“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迟”等故事背景以及周公与二公的对话,并描述了周公纳册于金縢之匮的行为。这样初步整理后的文本或既名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约在春秋至战国时期,后人根据世间流传的关于“周公居东”与“成王启金縢之匮”的传说作成第二、第三两章增补进此篇,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金縢》。
与《金縢》“层累”了篇中的后两章相比,清华简《四告》的情况则更为特别。根据我们的研究,四篇《四告》中的后两篇,乃是春秋战国时人根据前两篇附益而成的。⑥程浩:《清华简〈四告〉的性质与结构》。但是由于这两篇中完全没有原始的记录,全篇都出于假托,严格来说应该属于“作伪”而非“层累”了。
任何古书的流传都是在不断变化与发展的,“书”类文献的这些篇目也不能例外。但像《金縢》这种在流传过程中增添或改变了内容元素的篇目在“书”类文献中仍属少数,大部分“书”篇都只是在字词与章句方面发生了自然损伤与流变。
二、“书”的以类相存与结集“成书”
在上文中,我们对“书”类文献编纂成篇的过程以及其以篇为单位流传的情况进行了大致介绍。接下来,本文将着重论述作为一类文献的“书”由分散的单篇结集成文献意义上的书籍的过程,并尝试归纳“书”在以类相存的形态下流传与演变的规律。
(一)“书”类文献结集的过程
“书”在其作成的早期阶段应该是以篇为单位藏之“盟府”的,至于它是如何进入到大众阶层并结集成为知识分子广为传诵的一类文献的,过去的研究都很少有提及。陈梦家在《尚书通论》的“重版自叙”中感叹到:“我们若能较多的利用出土西周长篇铜器铭文和战国、汉代编简成册的书籍、簿录,或者可以从其体例中探索到《尚书》由若干单篇形成一书的过程。”①陈梦家:《尚书通论》,第3页。现如今我们有机会见到清华简中保存的战国时期“书”类文献的原貌,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中国古代社会在西周以前都是“学在王官”,“书”作为重要的官方档案长期由王朝的史官执掌。这种情况一般只有在改朝换代以及王室动乱时才会发生改变。《尚书·多士》载周革殷命后周公曾艳羡“惟殷先人,有册有典”,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0页。可以想见的是殷商灭国后这些原藏于商朝内府的档案最终都会被周王室所接管。③周公本人尤为重视“书”类文献,《墨子·贵义》赞其“朝读书百篇”,今传《尚书》之《周书》中亦有多篇为周公所作。过常宝更是认为,“‘书’类文献的载录和编纂,始于周公制礼作乐”(过常宝:《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38页),将西周王室对“书”类文献的收藏整理与周公紧密关联。然而好景不长,西周中晚期之后持续不断的政治动乱导致了藏在“盟府”的典籍也不断散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14页。在这条材料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随王子朝奔楚的大臣中有“尹氏固”。尹氏世代担任周王朝史官,掌握着王室的文书档案,因此他的出奔势必带走了大量的“周之典籍”。此外,《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⑤司马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85页。东周时期的史官家族司马氏适晋,也加速了王朝所藏典籍的向外传播。
除了动乱时的被动散佚外,王朝也会对典藏的“书”进行主动传播。如《周礼》规定外史不仅要“掌三皇五帝之书”,还要“掌达书名于四方”。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20页。《左传》定公四年载成王时期对鲁国的分封:
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⑦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34页。
王室对鲁公除了分土赐民外,还授予了一批器物,其中“典策”就是一种重要的赏赐。《史记·周本纪》云武王时“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⑧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26—127页。武王分赐给诸侯的“殷之器物”中,就很可能有周公所艳羡的殷先人之“册典”。此外,王在重要场合所作的诰命也应该会在事后抄送各诸侯国一份,以宣布王命、统一思想。《左传》定公四年载蔡、卫争歃血为盟之先后,宋国子鱼从中调停说:
晋文公为践土之盟,卫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犹先蔡。其载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视也。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35页。
子鱼讲践土之盟的载“书”藏在周府可以核验,而其本人又熟稔其文,可见至少在宋国也存有一份。而根据阎步克先生的分析,子鱼于此上提到的《伯禽》《康诰》《唐诰》《蔡仲之命》等篇,“应该也是既藏于‘周府’,同时又藏在各诸侯国之‘府’的”。⑩阎步克:《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见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页。
以上这些情况都导致了“书”类文献后来不再为王室所独有,诸侯国甚至民间也流散着为数不少的“书”篇,这就为“书”类文献的结集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大约在春秋时期,“学在王官”的状况被打破,学术文化逐渐开始下移。《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孔子的话:“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84页。随着周室日渐衰微,典籍档案不断散佚,“书”类文献的收藏与传习也逐渐由王室转移到了民间。
诸侯国在进行贵族的文化教育时,就往往把“书”作为一种重要的教本。《国语·楚语上》载楚庄王使士亶傅太子箴,士亶问于申叔时,答曰: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②徐元诰:《国语集解》,第485—486页。
申叔时提出的教育门类有很多,“书”教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教育方式。以先进的教育思想著称于世的孔子,对“六艺”的教化作用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礼记·经解》云: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③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09页。
孔子认为以“书”教人可以使之“疏通知远”,对于“书”的教育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古人看来,“书”类文献的另一重要功用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国语·周语上》载邵公语于厉王:“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可以看出史官与公卿、列士一样,有责任献盟府藏“书”以教诲天子听政。《国语·周语下》太子晋亦云:“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④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1、98页。对“先王之遗训”也就是“书”的“观废兴”作用可谓推崇备至。正因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阶层与知识分子就特别流行引用“书”类文献的内容来声张自己的学说。《论语·述而》既云孔子“雅言诗、书”,⑤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75页。《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赵衰赞美郤縠“说礼、乐而敦诗、书”,并说:“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22页。而先秦诸子之书中对“书”类文献的引用,更是不胜枚举。
正是出于对“书”类文献“观废兴”以及教化两方面作用的重视,时人便开始对传流于世的“书”类文献进行搜集与选编。过去的学者都把《尚书》的编定归功于孔子,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就说: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⑦司马迁:《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第1935—1936页。
孔子杏坛讲学,以“六艺”教授弟子,作为其中一项重要门类的“书”,也必然会有作为教材的选编本。
但是孔子以及儒家弟子所沿袭的“书”类文献的选编本,并不见得是当时唯一的“版本”。⑧“版本”这一概念晚出,在本文中借用为一种包含一定篇目的“书”类文献选编本,即通常所说的“本子”。从先秦文献对“书”类文献的引用情况来看,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家派使用的“版本”间篇目甚至文本往往都有较大差异。清华简的“书”中就有《尹至》《厚父》《封许之命》《四告》几篇从来不见于传世文献,也可以说是一种与儒家选编本平行的“版本”。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认为“书”类文献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了搜集与选编的过程并形成了各种“版本”,但它依然处在以类相存的形态,与后世作为典籍的“《书》”的概念仍然是不同的。这体现在这时的“书”仍然是开放性的,“书”类文献所结集的各“版本”间差异巨大,篇数与篇名也都不固定。
(二)影响篇目结集的因素
既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多种平行流传的“书”的“版本”,那么影响每种“版本”篇目入选与结集的因素又有哪些呢?如果我们对先秦各文献引“书”的篇目、传世《尚书》的篇目以及清华简中的“书”篇进行对比与归纳,会发现其至少会受到以下几点因素的影响:
第一,是“书”篇本身内容的重要性。
“书”类文献虽然每篇都是记录王言的重要载籍,但由于作“书”者、授“书”者、作“书”的场合与内容的不同,其重要性与受重视的程度也当有高下之分。《书纬·璿玑钤》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15页。纬书的说法虽不可尽信,但其云孔子选书的原则是“可以为世法者”,明确地指出了“书”篇本身内容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篇是否会被纳入后世流传的“书”类文献“版本”中。
从先秦古书对“书”类文献的称引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篇目被引用的次数较他篇而言要频繁得多。根据刘起釪的统计,“汉今文二十八篇在先秦称引最频繁,次数最多,可知这是当时广泛传习之本。伏生把它传授到汉代,就是由于它是习读之书”,其中“以《康诰》称引次数最多,达三十余次;其次《太誓》二十三次,《洪范》十九次;再次则《吕刑》、《尧典》各十六次”。②刘起釪:《尚书学史》,第62页。《康诰》《太誓》记载的是周朝建立之初先公先王的丰功伟业与训诫教诲,《洪范》《吕刑》两篇则集中体现了周代德主刑辅的治国之道,因此这些篇目都是时人非常重视并广为称道的。
从清华简保存的“书”类文献篇目中,也可以看出部分“书”篇的重要性。《金縢》篇述周公以身禳武王之疾,很好地彰显了周公忠君爱国的品质,十分符合当时人心目中的周公的形象,因而清华简与传世《尚书》两种“版本”都收入了此篇。清华简的《尹诰》篇是夏商之际的宝贵资料,该篇不仅见于百篇“书序”,《礼记·缁衣》还曾两次引用。还有见于清华简的《傅说之命》篇,虽然没有文本传世,但《国语》《孟子》《礼记》等文献进行了8次征引,可见该篇流传之广。
无论是为了教育后人而或以古鉴今,“书”类文献的各选编本都会将这些内容极其重要的篇目选编进去,成为各“版本”所共有的核心部分。
第二,与篇目本身的重要性相呼应的,是流传过程中的偶然性。
虽然内容是“书”篇传世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古书的流传过程往往并非绝对的“优胜劣汰”。许多内容极好的篇目,在流传过程中还是发生了散佚。就比如在先秦被引用了20多次的《太誓》,尽管在汉代还曾出现过,但在今传《尚书》中已经见不到了。还有清华简中的《厚父》一篇,内容是周武王向夏代后人厚父的乞言,该篇所体现的思想与周初的治国理念十分吻合,文辞也平易工整。这篇“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应当是很受重视的,《孟子》还曾对其进行了征引,但是它在后来的流传过程却意外地散失了,如果没有清华简的再次发现,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该篇的存在。
此外,今传《尚书》与《逸周书》的分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偶然性的存在。李学勤最早在介绍清华简的时候就已经指出,“这个简里没有《尚书》与《逸周书》的差别”。③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清华简的“书”类文献里,既有一般被认为是《尚书》的《金縢》《尹诰》《傅说之命》等,也有收入《逸周书》的《程寤》《皇门》与《祭公之顾命》。这些篇目内容都是王与大臣的训诰,在用简的规格方面也并无差别,④关于战国竹书的用简制度及其意义,见贾连翔:《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为中心》,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可见当时的人们仍然认为它们是一类“书”。《逸周书》大约是刘向等人根据汉代中秘所藏声称为周代的材料(有些并不是“书”类)整理、编选的,①陈梦家:《尚书通论》,第291页。所谓71篇就是由“百篇”之数减掉今文29篇得来的。虽然《逸周书》中的绝大多数篇目都时代偏晚,应出自后人构拟,但像《皇门》《祭公》等内容与思想各方面都绝不逊于《尚书》中的“周书”各篇。因此,哪些篇目后来被编入《尚书》,哪些又被归入《逸周书》,本来就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与篇目本身的内容性质并无太大关联。
第三,收藏与传播的地域也会影响“书”篇的选编。
作为维护分封制的一项重要举措,地方的诸侯国会收到王朝对本国的封赏册命之“书”以及王室下发的训诰类的“书”。除此之外,诸侯国自己也会作“书”、藏“书”。《左传》襄公十一年载晋悼公的话,称“国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51页。可见诸侯国亦有“盟府”,藏有“国之典”。《左传》就曾两引“郑书”:
“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襄公三十年)
“郑书”有之,“恶直丑正,实蕃有徒。”(昭公二十八年)③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13、2118页。
清华简的《郑武夫人规孺子》与《郑文公问太伯》两篇,虽然严格来讲属于“语”,但从体例上来看也有被混淆为“郑书”的可能。而《礼记》的《大学》篇还引有“楚书”:
“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75页。
清华简第9辑整理报告公布的《成人》篇,或即一篇佚失的“楚书”。这些本土的诸侯所作的“书”与来自王朝的“书”一起,共同构成了该地域“书”的“版本”的选编来源。
传世《尚书》收录的《费誓》与《秦誓》两篇,就明显是诸侯国的作品。过去的学者往往从“微言大义”的角度去解释这种现象,如伪孔传云:
诸侯之事而连帝王,孔子序《书》,以鲁有治戎征讨之备,秦有悔过自誓之戒,足为世法,故录以备王事,犹《诗》录商、鲁之颂。⑤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4页。
认为孔子将这两篇选入《尚书》,是看重了这两篇的教诫意义。邵雍则说:“夫子逆知天下之将并于秦”,⑥顾炎武:《日知录》,见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故编《书》存《秦誓》。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实际上,对《费誓》《秦誓》入选《尚书》的解释并不需要如此迂曲。大家都知道,今所见《尚书》为伏生所传,伏生本是济南人,又长年担任秦博士,在他传习的“书”类文献选编本中掺入了齐鲁系的《费誓》与秦系的《秦誓》似不足为奇。
这种“书”的选编受传播地域影响的情况也见于清华简,典型的例子就是《封许之命》篇。该篇是成王封吕丁于许的册命,虽然出自王命,但传播并不广泛,在古书中未见与该篇相关的只言片语。而且该篇的用字保留了许多较早的写法,有的甚至与西周时期的金文很像,这或可说明该篇被传抄的次数都是比较少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许国国小势微,与它有关的“书”自然不会受到广泛关注,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种具有很强地方性的“书”在别的区域不一定有机会见到。而该篇之所以被选编进清华简所在的楚地的“书”类文献“版本”,大概是由于许国长期是楚国附庸,灭国后其典藏的“书”也尽归楚人所有。
第四,与传“书”者的思想以及所属的家派也有一定关联。
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九流十家”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与学说,都会利用一些典籍作为讲学的教材与论说的依据。而各家由于主张的不同,在选编“书”的时候自然也都各有取舍与扬弃。
清人江声、孙星衍、王先谦,以及今人陈梦家、刘起釪与马士远等都曾对先秦文献对“书”的称引进行过辑录与统计。由于采取的标准各异,其统计结果也便不尽相同,但基本都能看出诸子所用“书”的版本与篇目的差异。刘起釪先生总结这种现象说:
当时的《书》篇在各家引用中出现的分歧很不小。由上面所引资料就看得很清楚,同一篇各家所引出基本相同点外,在文句方面大都出现很大歧异。例如《甘誓》,儒墨两家本子内容相同,文句的歧异却不小。又如同样是《仲虺之诰》的一段话,《荀子》和《吕氏春秋》所引即有不小出入。①刘起釪:《尚书学史》,第63—64页。
这些差异的形成有的是由于“版本”平行流传所致,有的则是传“书”者为了迎合自己的思想与主张而作的筛选与更改。因此,主观的人为因素也是我们在讨论“书”的选编问题时不得不考虑进去的。
三、先秦时期“书”类文献的“版本”与流派
受以上几点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域、不同家派对“书”篇的搜集与选编肯定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书”的“版本”一定会有很多。然而我们目前能够得见的,就只有传世《尚书》以及清华简两种“版本”。而且硕果仅存的这两种“版本”,与它们在当时的面貌相比也都已经残缺不全了。即便如此,将这两种选编本作为样本,仍可以一窥“书”类文献在先秦时期的流传情况。
(一)传世《尚书》与儒家
严格来讲,传世《尚书》的编定是入汉以后的事了,但在先秦也一定有一种“书”类文献选编本作为其来源。关于传世《尚书》的版本来源,过去都认为是由孔子所编次。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曾“序书传”,并将当时所见的“书”按照时代顺序“编次其事”,因而在他看来“故书传、礼记自孔氏”。②司马迁:《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第1936页。司马氏此论盖袭自汉代经说,言孔子事并不一定有确据。而后世儒者尊隆孔子,甚至认为《尚书》为孔子所作,恐怕就是盲目信从了。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孔子设科授徒,肯定选编了一种“版本”的“书”作为讲习的教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传世《尚书》的“版本”,不见得一定与孔子有直接的关联。在蒋善国看来,“就《尚书》各篇的编次看,汉代以来所传的《尚书》,也绝不是孔子所选定的”。③蒋善国:《尚书综述》,第13页。最直观的例子就是《论语》中孔子及门弟子对“书”的明确引用只有两处(《为政》《宪问》),而且都不见于今传《尚书》。④见于百篇者一处,即《泰伯》篇“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据《左传》昭公二十四年称引,为《太誓》之文。如果当时孔子已经编定了今传《尚书》的本子,很难想象《论语》对“书”的引用会绕开它。此外,传世《尚书》中的《尧典》《禹贡》等篇,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孔子当然是没见过的。至于传世《尚书》的“版本”把这些篇目编入,则应该是孔子以后的事情了。
虽然传世《尚书》非孔子手定,但其“版本”来源与孔子后学有关则几乎是学术界的公论。如刘起釪先生就认为:“流传到汉代的《书》,才是儒家传下来的。”⑤刘起釪:《尚书学史》,第12页。裘锡圭也说:“今传《尚书》和《礼记》各篇所引之《书》,都是儒家传本。”⑥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4辑,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14页。我们都知道,汉代所谓今古文的源头一为伏生,一为孔壁,伏生本是齐鲁儒者,孔壁则是孔子旧宅,因此无论今文还是古文都应该是儒家选编的“版本”。
《韩非子·显学》载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以孟、荀两派影响最大,而孟子与荀卿对“书”也都非常重视。根据刘起釪先生的统计,《孟子》一书引“书”共计38次,在诸子中仅次于《墨子》。①刘起釪:《先秦文献引用〈尚书〉篇数次数总表》,见氏著:《尚书学史》,第49—50页。这其中称说的篇名有《尧典》《汤誓》《伊训》《太甲》《太誓》《康诰》《武成》等,皆见于百篇“书序”。程元敏先生据此认为:“孟轲似已据一成书之集编本《尚书》”,②程元敏:《尚书学史》,第40页。已然洞悉了孟子所引的“书”与今传《尚书》间的密切关系。
与《孟子》情况类似的还有《荀子》,该书引“书”计28次,其中竟有16次见于今文《尚书》28篇者,余下的《太誓》《仲虺之诰》等也都是儒家选编“书”的核心篇目。可以看出,《荀子》引“书”依据的“版本”与汉代传授的《尚书》就已经很接近了。正因如此,蒋善国先生认为《尚书》的编次甚至都可能与荀子有很大关联。③蒋善国:《尚书综述》,第15—16页。
除了《孟子》《荀子》外,《礼记》中的大部分篇目一般也都被认为是儒者所作。其中的《缁衣》《表记》与《坊记》等篇都引有“书”,其引《太誓》《康诰》《君奭》《吕刑》《尹诰》《太甲》《说命》《君陈》《君牙》《祭公之顾命》等,不仅篇名基本不出于“百篇”,文句也基本可与传世《尚书》或《逸周书》对应。
此外郭店简的《成之闻之》一篇,从内容与思想上来看可能是战国时期子思孟子一派的作品。该篇引“书”有《大禹》《韶命》《君奭》《康诰》四篇,李学勤指出《大禹》即《大禹谟》,而《韶命》即《说命》。④李学勤:《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中国哲学》第20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页;李学勤:《试论楚简中的〈说命〉佚文》,《烟台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准此,则本篇所用亦不外乎“百篇”,可见当时儒家所选编的“书”与传世《尚书》基本上是比较接近的了。
综上所述,战国儒家一派的作品《孟子》《荀子》《礼记》与《成之闻之》等对“书”的引用无论是篇目还是文本都与所谓“百篇”以及今传《尚书》比较接近。孟、荀时期流行的儒家的“书”类文献选编本应该就是传世《尚书》的“版本”来源,但是经历了秦汉之际的禁毁,汉代流传的《尚书》已经残缺严重,无论是篇目还是篇数都与战国选本有了较大不同。
(二)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墨家
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虽然在公布之后就一直被学者与传世《尚书》联系起来,但两者篇目的差异与文本的不同提醒我们清华简与儒家的选编本在战国时期应该属于平行流传的两种“版本”。⑤对于这一点,学界早有认识,见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4辑,第14页。
首先,清华简“书”类文献的篇目与传世《尚书》大不相同。清华简中的“书”见于伏生今文28篇者,只有《金縢》一篇;《尹诰》即《咸有一德》,是鲁恭王坏孔壁增广的古文篇目;《傅说之命》《摄命》(或即《冏命》)在百篇“书序”中有著录;《程寤》《皇门》《祭公之顾命》在汉代属于《逸周书》;《尹至》《厚父》《封许之命》《四告》等篇则是前所未见的篇目。可见清华简的篇目与传世《尚书》重合很少。这其中当然有儒家选编本大多散佚的原因,而清华简所见的篇目也未必是该“版本”下葬时的全貌,因此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必然存在的。
其次,清华简“书”类文献的篇名与传世《尚书》也多有抵牾。百篇《尚书》有《说命》篇,清华简题作《傅说之命》;传世《尚书》中的《金縢》,清华简题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收入《逸周书》的《祭公》,《礼记·缁衣》称引与清华简篇题均作“祭公之顾命”。“书”之篇题的拟定乃是出于流传过程中区分篇目的需要,因而出自后世藏书者之手的可能性较大。各“版本”间同篇异名的现象,实际上最能体现出其内部差异。
再者,简本的部分文句与传世《尚书》或儒家典籍所引也有一定距离。比如清华简的《金縢》较《尚书》的本子少了许多文句。《孟子》《礼记》等儒家典籍对“书”的部分引用与清华简的文本也有明显不同。《孟子·梁惠王下》引“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①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5页。今据清华简知是《厚父》之文。但简文作“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之慝”,较《孟子》所引多了“设万邦”一句,“乱下民之慝”与“宠之四方有罪无罪”也有差距,可见孟子见到的《厚父》与简本略有不同。此外《礼记》的《缁衣》《学记》与《文王世子》等篇引《说命》,有许多条都不见于清华简的《傅说之命》。又如清华简《尹诰》“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遏其有民,亦惟厥众”一句,《礼记·缁衣》引作“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49页。其间虽有错字与通假字的纷扰,但不可否认的是两种“版本”确有不同。
由此可见,清华简“书”的“版本”与战国时期的儒家选本有着明显的差异,属于两种不同的“版本”。③刘光胜亦撰文申说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与《尚书》同源异流,分属于不同的文献系统。刘光胜:《同源异途: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儒家〈尚书〉系统的学术分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那么清华简中的这批“书”又是哪里来的呢?在我们看来,清华简的“书”类文献的结集与选编,除了楚国的地域性因素外,或许还受到了墨家对“书”之传授的影响。④这种看法最早为笔者在《古书成书研究再反思——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为中心》(《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但仅一笔带过,未进行详细阐述。最近读到刘成群《清华简与墨学管窥》(《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一文,亦有类似主张。
在战国诸子中,以儒、墨两家影响力最为卓著。而当时除了儒家传授“书”外,墨子及其门人对“书”也十分重视。《墨子·贵义》载:
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也。今若过之心者,数逆于精微,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而子何怪焉?”⑤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45页。
墨子外出游历,车中仍“载书甚多”,他还以“周公旦朝读书百篇”作为榜样。这里墨子车中载书当然不会全属“书”类文献,应该指的是一般意义的书籍。但是作为当时公共知识的核心,“书”类文献想必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子》一书对“书”也多有引据,根据刘起釪先生统计,《墨子》引“书”在战国诸子中最多,共引用了47次,涉及的篇目也有22篇。⑥刘起釪:《尚书学史》,第64页。然而《墨子》引“书”与今传《尚书》多有不同,罗根泽先生云其“非不见于今古文《尚书》,即与今古文《尚书》大异;与今古文《尚书》虽字句有异同,而大体无殊者止有三则,而此三则又止在《吕刑》一篇。故概括言之,即谓《墨子》所引《书》,与今古文《尚书》全殊,亦无不可也”,又言:“今孟、荀儒家书所引者,略同今本,墨家所引者,则悬殊太甚。”⑦罗根泽:《由〈墨子〉引经推测儒墨两家与经书之关系》,见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78—281页。例如《墨子》引今《甘誓》曰《禹誓》,引《太誓》也有《去发》《大明》《三代不国》等称,可见其篇目的定名和分合与今传《尚书》并不相同。而《礼记·缁衣》引《说命》作“惟口起羞”,与《尚同中》所引《术令》“唯口出好兴戎”在文句上也有所不同。由此可见,墨家对“书”的传授大概有自己的一种“版本”。
而我们之所以说清华简中的“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墨家的影响,则是由于二者在以下几方面的关联:
第一,墨家与清华简所在的楚地有较深的渊源。
清华简虽非科学发掘多得,但通过与包山简、郭店简等楚地出土的简册用字进行对比,基本可以将其认定为是楚国的文献。至于这批材料的时代,碳14测定的结果为公元前305±30年,专家鉴定会的意见也大致在战国中晚期。①李学勤:《清华简整理工作的第一年》,《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虽然墨子主要活动在战国初期,距清华简的年代尚有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但墨子的学说却是影响到整个战国时代的。墨子晚年长期居住在楚国,而根据《吕氏春秋》的记载,战国中期墨家的巨子孟胜也是为楚之阳城君守城而死。墨子死后“墨分为三”,南方之墨者屈将子、邓陵子为楚公族之后,苦获、已齿等贤达也俱是楚人。②孙诒让:《墨子传授考》,见氏著:《墨子间诂》,第706—722页。如此看来,墨家对楚国的影响可以说是延绵不断的。③关于墨学在楚地的传播,还可参见高华平:《“三墨”学说与楚国墨学》,《文史哲》2013年第5期。而《墨子·贵义》云:“子墨子南游于楚”,献“书”惠王,④《文选注》引《墨子》之文,见孙诒让:《墨子间诂》,第440页。则墨子不仅把他的学说带到楚国,还应该囊括了他所搜集选编的“书”。
关于墨家在楚地的影响以及传“书”的情况,还可以得到考古材料的充分印证。1956年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土的战国楚简中有一篇记载申徒狄与周公问对的竹书,⑤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我国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信阳长台关发掘一座战国大墓》,《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9期。经学者研究,知其即为《太平御览》所引《墨子》佚篇,当与墨家有着密切关联。⑥李学勤:《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见氏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27—333页;李零:《长台关楚简〈申徒狄〉研究》,见氏著:《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91—208页。无独有偶,安徽大学新近入藏的一篇战国楚简中,再次出现了这一篇的内容,⑦黄德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文物》2017年第9期。足见墨家学说在楚地传授之广泛。
第二,清华简“书”的“版本”对篇目的选取较合墨家的取向。
清华简中与商代相关的篇目较多,“书”类文献有《尹至》《尹诰》《傅说之命》三篇,不属于“书”的也有《赤之集汤之屋》《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等篇。其中仅述伊尹事的,就有《尹至》《尹诰》《赤之集汤之屋》《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五篇。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墨子》,《墨子》经常将汤与尧舜、文武并举,其《所染》《尚贤》《贵义》等篇亦屡言伊尹。⑧沈建华即已申说清华简中有关商汤与伊尹的篇目与《墨子·贵义》的关系,见沈建华:《清华简〈唐(汤)处于唐丘〉与〈墨子·贵义〉文本》,《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墨子是宋人的后代,又长期担任宋国大夫,而宋国本就是商代的后裔,故而墨子获得商代之“书”会有天然的便利,对商汤与伊尹也特别青睐。而正因如此,墨子在他的著述以及所编选的“书”中就会对商代的篇目更有倾向性。
第三,清华简的“书”不讳言鬼神,与墨家思想相合。
清华简《傅说之命》的上篇有佚仲氏生二牡豕的故事,甚为离奇古怪,《金縢》篇后半段还有天人感应的描写,这些都是与儒家的“不语怪力乱神”相冲突的。而墨家独言鬼神之明,墨子在《明鬼》篇中云:
故尚书(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则圣王务之。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⑨孙诒让:《墨子间诂》,第242页。
墨子还说:“一篇之书,语数鬼神之有。”可见在墨子看到的“书”的篇目中,讲鬼神之事的内容是很多的。而从清华简的这几篇“书”来看,这种情况也基本相符。
第四,墨家学派的一些基本思想,在清华简的其他篇目中亦有体现。
学界普遍认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十论”乃是墨家思想的核心。①杨义:《墨子还原》,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4页;Ian Johnston,The Mozi:A Compl ete Transl ation,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10,p.32。除了前文已经论述的“明鬼”之外,其他几种主张在清华简中也有一定的体现。例如“尚贤”,清华简中有一篇《良臣》列数历代贤能之臣,《邦家处位》篇亦专论如何选贤度能;又如“尚同”,清华简《尹诰》开篇便强调“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又如“非攻”,清华简《天下之道》亦主张以天下之道取代攻守之器;再如“节用”“节葬”,清华简《邦家之政》《治邦之道》等篇中也反复强调了此类观念。②负责《邦家之政》《治邦之道》两篇整理工作的李均明、刘国忠即认为其与墨家有关。见刘国忠:《清华简〈治邦之道〉初探》,《文物》2018年第9期;李均明:《清华简〈邦家之政〉的为政观》,《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在墨家思想与清华简文本之间有着如此多的内在联系,使我们不得不考虑清华简受到墨家思想传授影响的可能。
第五,《墨子》一书对“书”的引用也近于清华简。
《墨子·尚同中》引《术令》曰“唯口出好兴戎”,孙诒让指出此处《术命》即《说命》。而《礼记·缁衣》引《说命》此句作“惟口起羞”,与《墨子》略有不同。清华简《傅说之命》中此句作“惟口起戎出好”,与《墨子》所引仅有语序的差别,跟《缁衣》相比关系显然要更近一些。
综上所述,清华简的“书”类文献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墨家的影响,可能与墨家选编的“书”类文献在楚国的传授有关。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不认为清华简“书”的版本就等同于墨家的选编本。因为从《墨子》引书的篇目与文本来看,其与清华简的“书”类文献并不能密合。而且诚如我们在上文所说的,一种“版本”的“书”对篇目的选定要受地域、家派以及偶然性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对于清华简来说,墨家对“书”的传授只是其影响因子之一。
四、“书”类文献成书后的文本流变
“书”类文献的流传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即便是战国中晚期写定的清华简,距离这些“书”生成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至少数百年。因此,无论是清华简的“书”类文献还是传世的《尚书》《逸周书》,其文本在经历了无数次的传抄与整理后较作成时的原貌必然发生了极大的偏差与演变。
(一)文本流传过程中的自然演变
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总结所校《元典章》说:“凡得谬误一万二千余条,其间无心之误半,有心之误亦半。”③陈垣:《校勘学释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页。通过对《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三篇的简本与传本进行比勘,我们发现造成两者之间差异的原因亦有“无心”与“有心”两种。所谓“无心之误”,就是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由于简册散乱、文字漫漶以及转写时的失误等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自然演变,包括常见的脱、衍、乙、误等。
清华简三篇与传世文本的差异中,属于自然演变一类的,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1)脱简或漏字
古书往往以简册为载体,而用于简册编联的丝麻编绳又极易朽坏,故脱简现象在流传中比较常见。《汉书·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④班固:《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06页。可见脱简的现象早在汉代人整理“书”类文献时已经引起了注意。清华简虽久藏地下,历经墓中环境的腐蚀,但通过简背的编号来看,《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三篇保存状况基本良好,并没有整简脱失的现象。然而经过详细比勘,我们发现这几篇的祖本或者相对应的传世文本中或许曾发生过脱简。①具体论证见程浩:《古书成书研究再反思——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为中心》,《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
对比这三篇的简本与传本,单字的缺失更是不胜枚举。如简本《皇门》有一句“维媮德用”,意为巧黠之德是用。而此处传本作“维德是用”,清人孙诒让已疑:“‘德’上当有一字,而今本脱之,此上下文所言者皆恶德也。”②孙诒让:《周书斠补》,见氏著:《大戴礼记斠补》,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第116页。今据简本可知,此处确是脱了“媮”字。脱字的情况不仅发生在传本,简本中也不可避免。如传本《皇门》首句“维正月庚午”,简本作“惟正庚午”,显然是脱漏了“正月”的“月”字。
(2)字形讹误
由于底本中文字发生磨泐,或者传抄者认字水平的限制,对字形的误写与误识在传本中也有很多。这其中大部分是由于形体较为近似而传抄致讹。如简本《金縢》的“亲逆公”的“亲”字,在传本中误为“新”,二字的形体就极为接近。而《皇门》中的例子更多:“公格在皇门”的“在”字传本误为“左”;③孔晁注此处曰:“路寝左门曰皇门”,已经将“皇门”与“左门”联系起来,则“在”“左”之讹至少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发生了。“肆朕沈人”的“肆”字传本误为“建”;④清人段玉裁校传本《皇门》时,已指出“建”当为“肆”字之误。“今我譬小于大”的“今”字传本误为“命”;“王邦用宁”的“王邦”传本误为“四国”;⑤黄怀信指出:“上下文皆言王邦,此不应又言四国,今本‘四国’当是后人所改。”见黄怀信:《清华简〈皇门〉校读》,武汉大学简帛网,ht t p://www.bsm.or g.c n/show_ar t i cl e.php?i d=1414,2011年3月14日。“弗肯用”与“不肯惠听”的“肯”字在传本中分别误作“见”与“屑”;“休德以应”的“德”字在传本中误为“真”;“弇盖”的“弇”字在传本中误为“食”;“戎夫”的“夫”字在传本中误为“犬”;“媢夫”的“媢”字在传本中误为“媚”。⑥“弇盖”与“媢夫”之误,高邮王氏早已指出,实为先见之明。见王念孙:《读书杂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页。《祭公之顾命》篇自然也不会例外,如“汶予小子”的“汶”字被传本误写为“次”,⑦传本“次予小子”之说前人早有怀疑,魏源《书古微》云:“次字未详,疑为讹”,朱右曾校此句则径自删去“次”字,刘师培《周书补正》引或说云:“次当作汶,汶、闵同”,从简文来看是很正确的意见。诸说均见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924页。“由”字在传本中误写为“申”,有一个作否定副词的“不”在传本中还被写成了“丕”。上述这些字形有些从今天行用的字形来看没有太大关联,但是在古文中他们的形体都极为接近,很容易互相讹混。
以上这些变动,大部分是由于客观因素造成的,可以说都属于文献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演变。而另外有些现象虽出自人为,但却是时代大趋势所致,并非出自个人的主观意志,也可以归入此列。比如这三篇中大部分的第一人称代词“余”,在传本中都被改作了时代较晚“予”,个别的介词“于”在传本中也写成战国以后才普遍行用的“於”。这些变动未必出自刻意窜改,可能只是后人在转写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换作了习惯用字。
(二)后人在传抄与整理时的主观改动
与上述“无心之误”相对应的,是后人在传抄与整理古书时根据自己的认识和意愿对文本作的主观改动,即所谓“有心之误”。“书”类文献本非一时之作,整理与作成也非出自一人之手,再加上后世的不断传抄,尤其是“书同文”后的转写,使“书”类文献的文本中较多地掺入了后人作的改动。通过将传世的《金縢》《皇门》《祭公》三篇与简本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经后人改动的部分。按照改动的动因来区分,至少有以下几类:
(1)为避讳而改
中国古代有避讳的传统,著书为文都不得直书君名,必须用其他方法进行规避。后世虽有经书无需避讳的规定,但古书中的许多字形还是在流传过程中被讳改了。从清华简提供的原始文本来看,传世《尚书》《逸周书》中的很多篇目可能都在入汉以后被汉人改过讳字。比如三篇简本中的绝大多数的“邦”字,在传本中都改作“国”或“封”,有的甚至还被直接删去。而先秦时期常见的第一人称“朕”,在传本《皇门》中则被视作僭称而几乎删除殆尽。还有一则例子见于《金縢》。该篇周公对武王之称在简本为“元孙发”,而传本作“元孙某”。将“发”改作“某”,显然是避武王名讳。但是这则避讳的发生一定不会太早,因为《史记》所引仍作“元孙王发”,而且《程寤》《牧誓》等篇也并不讳武王名。
(2)为易读而改
“书”类文献源自对君王言论的现场记录,而有的篇目由于年代久远,读起来难免有“佶屈聱牙”之感。后人为了使原本艰涩的文本更容易读懂,往往会对“书”的文句进行改易。
如司马迁著《史记》在夏、商、周三代本纪中对“书”多有引用,有的甚至是全篇称引。但其文本与今古文《尚书》并不完全相同,很多是司马迁用汉代的语言训读后的结果。①关于司马迁《史记》引述《尚书》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最新的成果见马士远:《司马迁〈尚书〉学研究》,《齐鲁学刊》2013年第3期。这种现象在清华简以及传世的《金縢》《皇门》《祭公》中都可以见到,其简本与传本用词的不同很多都是因为用了训诂字。这些同义代换的词有的是由于“版本”不同所致,有的则可能是后人替换了当时常用的字。
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简本的《金縢》对人物称谓都作了特殊处理。如在篇首“既克商”前增“武王”,明确了该篇的时代与归属;将传本的“二公曰”增广为“二公告周公曰”,明确了此句的谓语为“周公”;篇名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明确有疾者为“周武王”而非楚国当地的“楚武王”。②对这种现象的分析,见刘国忠:《试析清华简〈金縢〉篇名中的称谓问题》,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简研究(第一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75—178页。凡此种种,都是传习清华简这批“书”的人为了避免读者误解,使文本更易读而进行的改易。
(3)为押韵而改
熟悉文学史的学者都知道,有周一代的文学特别是诗词之学高度发展繁荣,西周金文中就已经出现了用韵的现象,春秋战国时期的撰述更是经常追求押韵。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有些“书”的文本也会遭到传授者的改易,使之合乎审美并易于传诵。
李锐最早探讨了简本与传本《金縢》中祝辞的押韵现象,并将其韵脚标识如下:
今传本:
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质)。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真),以旦代某之身(真)。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真);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真)。乃命于帝庭(耕),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歌)。四方之民(真),罔不祗畏(微)。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真/耕),我先王亦永有依归(微)。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歌),我其以璧与珪(支),归俟尔命(真/耕);尔不许我(歌),我乃屏璧与珪(支)。
清华简:
尔元孙发也,遘害虐疾(质)。尔毋乃有服子之责在上,惟尔元孙发也,不若旦也,是佞若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真),命于帝庭(耕),溥有四方,以定尔子孙于下地(歌)。尔之许我(歌),我则晋璧与珪。尔不我许,我乃以璧与珪归(微)。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明显地体会到传本在押韵方面较简本要丰富得多、工整得多。而在李锐看来,传本更多用韵的情况乃是后人对文句进行调整后的结果。③李锐:《〈金縢〉初探》,《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4)为迎合思想取向而改
先秦时期对“书”的传授,很重要的两项功用就是“引《书》以赞治”与“顺《书》以造士”。①马士远:《周秦〈尚书〉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8—185页。各家派出于传播思想与教授门徒的需求,也会对“书”的文本进行删改,使之符合自己的学说。
按照传统的说法,孔子即曾删订“六经”。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可以举出“诗”的例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②司马迁:《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第1936—1937页。
在司马迁看来,孔子对“诗”的选编除了要“去其重”外,很重要一个标准就是要“可施于礼义”。前引《书纬》之文也说孔子选“书”的原则是“可以为世法者”,可见孔子在编次“书”时也会偏重于他所认为内容适宜的篇目。当然,这些仅代表汉朝人的看法,孔子之时的情况未必是这样,但后人为了迎合自己的思想学说对经文进行改易的情况是一定会有的。比如简本《金縢》对传本中涉及占卜文句统一进行了删改:传本第一章周公的祝辞中“乃卜三龟,一习吉”等40余字全然不见于简本;第三章成王启匮见书后所说的话中“其勿穆卜”一句也被删掉了。我们知道,周人信天道,事必占卜,而且从包山简等出土材料来看,祝祷的同时都是要进行占筮的。因此,这些对占卜的记载应如传本有之为确。简本对占卜事的删改,可能是由于简本《金縢》的传授者并不信占卜。
(5)误读后妄改
文本流传过程中,经常会有后人对文字未能正确识读而致误的现象。然而这种误读造成的后果往往是一连串的,因为后人在误识了一字后,还会根据自己的错误理解,对其上下文进行臆测与妄改。
这种情况在《金縢》《皇门》《祭公》每一篇中都有出现,而且体量并不在少数。比如简本《金縢》“王亦未逆公”的“逆”字,传本将其误为“诮”之后,又在其前添加了一个“敢”字,使此句变成了“王亦未敢诮公”,文意从“王也没有迎接周公”陡然急转成了“王也没敢责怪周公”。这一字之误不仅逼迫传本增字解经,对后文也有影响。简本下文载成王得知真相后云“余沈人亲逆公”,是说要亲自迎回周公。而传本为了弥补上文的错误,将其读为“朕小子新逆”,变成了“我刚刚即位登基”,简本的“王乃出逆公至郊”也更作“王出郊”,文意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主观改动,再加上传世本脱去了简本的“是岁也”三字,遂导致司马迁《史记》在引述《金縢》时将此篇割裂为两部分,甚至误以为成王启金縢之匮是周公卒后的事了。
由是观之,后世传“书”者的“整理”与主观改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书”类文献文本的流变。而且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传抄次数的增加会越来越显著,这点在传世文献对《程寤》的引用中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程寤》篇名虽见于《逸周书》,但文本早已亡佚。在清华简发现之前,只有一些汉晋时期的著作和唐宋类书保存了一部分佚文。有了清华简的战国文本之后,再以各本所共有的“太姒寤惊”故事进行对比,就很容易观察出其文本演变之脉络。
战国清华简《程寤》:
大姒梦见商廷惟棘,乃小子发取周廷梓,树于厥间,化为松柏棫柞。寤惊,告王。
晋张华《博物志》卷八:
大姒梦见商之庭产棘,乃小子发取周庭梓树,树之于阙闻〈间〉,梓化为松柏棫柞。觉惊,以告文王。①张华撰,范宁校正:《博物志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3页。
唐《艺文类聚》卷七九《梦》引《周书》:
大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太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于阙,梓化为松柏棫柞。寐觉,以告文王。②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55页。
宋《太平御览》卷五三三引《程寤》:
太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小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于阙间,化为松柏棫柞。惊,以告文王。③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418页。
我们可以看到晋代张华《博物志》引《程寤》之文“乃小子发”“觉惊”等语还比较接近简本,而到了唐宋类书《艺文类聚》与《太平御览》,与原始文本相比所作的改动就比较多了。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文献流传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的规律,那就是古书流传的时间越久,其文本的变异以及遭到窜改的程度也就会越来越高。
五、结 语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书”类文献在先秦时期的生成、结集与流变的过程作一概括:首先是在古书流传的基本单位“篇”这一层次。“书”类文献作成的材料来源是由史官对君王与臣下言论进行的现场记录。对话发生的场合与参与者的不同,就造成了“书”类文献内部体裁的差异。君臣间的一般对话形成“训诰”;君主对臣下的分封、命官与赏赐等形成“册命”;“誓祷”则是对誓师、田猎、祭祀等重要仪式中君主言辞的记录。这些记录或“书于竹帛”,或“镂于金石”,作为官方的档案文书被藏之于“盟府”。后来出于统治者以史鉴今以及垂训后代的政治需求,这些档案就被整理编纂成了文献。“书”类文献由档案文书编纂成篇,首先要经历的是史官现场记录后的第一轮整理与加工,对口语化的内容进行疏通,并添加表示引领语句或语气转折的“王曰”与“王若曰”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篇目还被加入了作成时代与故事背景的介绍,这是第二轮整理。至于《金縢》那样增多了两章的内容,则是流传过程中的“层累”了。
再者是“书”类文献结集成文献意义上的书籍之后的一些情况。“书”类文献在周代官学下移后流散到了民间。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与思想家出于声张自己的学说以及教育弟子的目的,对流散的“书”类文献进行了搜集与选编。而由于地域性、偶然性以及思想倾向的不同,各家收藏与传习的“书”的“版本”也就各不相同。我们现在看到的传世《尚书》,大约是由孟、荀时期流行的儒家选编本流传而来的。而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墨家对“书”的传授的影响。在“书”类文献的流传过程中,其文本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这其中既有脱、漏、乙、误等自然演变,也有后人出于避讳、押韵以及思想性等动因作的主观改动。而随着流传时间的增加,文本的变异与改动也就会越来越多。凡此种种,都是流变两千余年的“书”类文献所无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