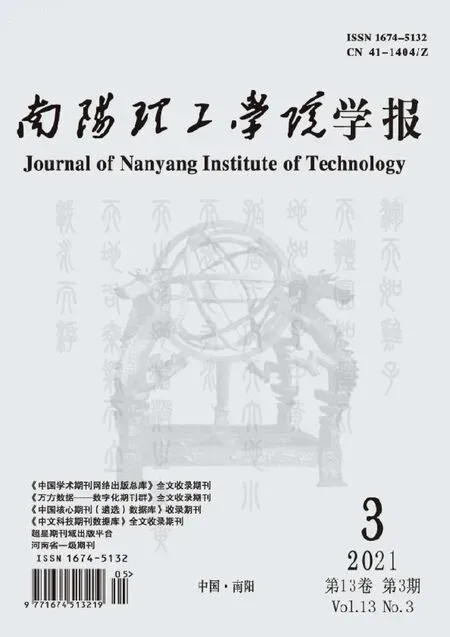施蛰存《善女人行品》的女性生存困境
刘瑞芳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00)
五四运动加快了社会观念的转型,两性婚姻观也随之发生重大调整,新的婚姻观不再以生育为目的,而是以爱情为核心组织婚姻生活。现代婚姻观的普及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避免会与传统婚姻观发生碰撞,致使一部分走出闺门、踏入婚姻的女性陷入了欲前进却不能的尴尬境地。施蛰存的《善女人行品》描写了11位女性沉重的婚姻生活,她们承受了不幸的婚姻,压抑着自己的欲望,缺乏独立的精神,为转型期女性的婚姻生活提供了一面自我审视的镜子。
一 婚姻的不幸
如果说幸福是婚姻的一种状态,不幸便是与之对立的另一种状态。婚姻成立后需要面对日常生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遭遇不幸。这涉及一个重要的却又经常被忽略的问题,日常生活的价值是什么?男人和女人对于这个问题的判断是不一样的,男性普遍认为女性应该扮演好“家庭妇女”的角色,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生活角色几乎占据了女性的全部,她们没有为自己而活的时间。刘半农在《南归杂话》中计算了妇女天天所做的事,从早上七点钟起身,料理小孩子的事情、买菜、做饭、洗碗、洗衣服等,一直到晚上,“到十点以后是呵欠催人快点睡罢”[1],而无论什么样的妇女,一经结婚生子,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一日三餐人人离不开又躲不掉,占据了一个人大半个人生,妻子作为家庭日常生活的主要承担者,其实是很伟大的。但男性看到的,就只是日渐衰老并且无趣的妻子,正如鲁迅《伤逝》所描写的,涓生很快厌倦了同居以后变得粗糙的子君。许多原本相爱的男女,在走进婚姻后,总会因为生活中的一些小事而发生争吵,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想要激情与安定兼得,但两者同时拥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莼羹》中妻子只是想尝到丈夫做的羮汤,却被屡屡推辞,两人还发生了争吵。《残秋的下弦月》中妻子卧病在床,整日处于悲观状态,新死的女儿埋葬在哪里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丈夫需要写一篇文章才能保证下星期的生活费,好像压死骆驼的每一根稻草都落在了这个家庭身上。《妻之生辰》中丈夫想为妻子买一个生日礼物,最后因为钱不够而作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金钱不是万能的,但它可以让基础变得更稳固,为生活奔波而忽略浪漫是普通人典型的生活状态,这更是显示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使婚姻的质量在降低。
即使婚姻是基于爱情的结合,但情感作为人的一种心理属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二十岁时喜欢的音乐或小说,到了三四十岁就觉得无聊了。爱情有时候也是这样,法律和伦理道德非但不能成为爱情的有效保护,反而会成为束缚和枷锁。婚后的琐事会把当初的爱情都消耗,如果爱情消失了,也许会出现“新”的情感关系,甚至会形成婚内出轨现象。《港内小景》中丈夫在妻子患病期间就出轨了。“他不能很细密地分析出自己对于妻不满意的种种因素,但是在思想和行为上,他们随时都会发生冲突。”[2]239妻子患病后,他觉得对于妻子只剩下服侍病人的义务,出轨了也没离开妻子,因为自己是一个“绅士”,这是典型的补偿心理。所有他对妻子的“好心”,都是为了减轻自己出轨的不安以达到心理平衡。《散步》中的丈夫认为婚后的妻子不爱他,在妻子因为家事及孩子多次拒绝出去散步后,与两位女性发生了不正当行为。这是因为婚后的琐事把妻子当初的浪漫消耗掉了,一旦爱情消失,延续婚姻的良药就没有了。当然不仅是男性,女性也会有出轨现象。《蝴蝶夫人》中蝴蝶夫人在受不了丈夫的迂腐与无视后,就出轨了。蝴蝶夫人和李约翰教授的结合是因为见面那一瞬间的神圣,但是婚后当这个神圣的女子变得俗气的时候,丈夫便开始厌倦。对于李约翰教授来说,妻子的过度花钱让他招架不住,而自己必须加班赚钱才能满足妻子,所以开始变得迂腐和木讷。但对于蝴蝶夫人来说,丈夫不但没有时间陪伴她,而且丈夫还那么无趣,于是便用花钱来打发自己的无聊时间。陈君哲教授与李约翰教授刚好相反,有情趣、有时间、有欢乐,蝴蝶夫人与其一拍即合。
这些人的婚姻充满了焦虑,跌入了困境,出轨成为饮鸩止渴的消极方法。无论是知足的妻子、不知足的蝴蝶夫人,还是失去浪漫的家庭主妇,都是整个出轨婚姻的牺牲品。妻子成为出轨丈夫降低愧疚感的一种工具,婚姻变成了爱情的坟墓,婚后的生活打磨掉了女性追求爱情的想法,并且得不到男性的理解。男性幻想中的另一半总是一些善女人,温柔贤惠、善解人意,他们渴望与这样的女性产生爱情。但当心目中的幻想被打破,也就伴随着另一个人的出现,女人也一样,当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也会找人来替代,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去释放焦虑,把问题推给对方。如果现代婚姻过于突出感情,忽视日常生活和道德法律的问题,就会使婚姻走向偏执的状态。爱情作为情感的一种特殊形式并非一成不变,但五四新文化提倡的爱情是作为稳定性因素来传播的,仿佛一旦产生爱情便会天长地久,这容易产生误导。真正的爱情必须与日常生活相融合,夫妻之间互相理解与扶持,爱情才能放射光芒。前述这些人物在日常生活的重压下迷失了方向,每一个人都在找一个出口,找一种刺激,来释放掉自己的欲望与压力。所以,出轨变成了逃避婚姻问题的方式,其实不过是走进了另一个围城。
二 欲望的压抑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引出了关于“生”与“欲”的讨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3],他认为欲望是生活的本质,得出生活、欲望、苦痛三者合一的人生观念。郁达夫的早期小说表现男性的欲望压抑和精神苦闷,塑造了无所适从的 “零余者”形象。丁玲批评男权社会对女性生活的压抑,《莎菲女士的日记》就表现了莎菲情感与欲望的冲突。施蛰存的《狮子座流星雨》《雾》《春阳》分别描写卓佩珊夫人对于孩子和文雅的男性的欲望、素贞对于婚姻的欲望、婵阿姨对于男子的欲望。但从她们为了满足欲望所做的事情造成的后果来看,并不能说明这些欲望是她们作为“人”的正当要求,而是未完全褪去的传统观念像一副沉重的镣铐,让她们把正当的欲望压抑在最底层。
《狮子座流星雨》中卓佩珊夫人希望有一个孩子,看了她认为最好的德国医生却无结果,听说看到狮子座流星雨可以怀孕的传言以后,就把床横在窗前等待着半夜的流星,以至于梦到流星变成怪星投在她身上。《雾》中自信漂亮又有文化的素贞,渴望与一个完美的男子拥有一段婚姻,在火车上遇到青年绅士陆士奎,觉得他完美至极,但当她知道他是一个戏子的时候,又对他厌恶至极。《春阳》中的婵阿姨为了金钱选择冥婚,做了财产的奴隶,但仍旧过着吝啬的生活,同时她也选择了孤独,饭店里的男人、银行的员工,都让她想入非非。
“中国自周代以来,宗法社会既已成立,聘娶形式视为当然,于是婚姻的目的遂以‘广家族繁子孙’为主”[4];儒家对于婚姻的解除所做的习惯性规定称为“七出”,“无子”为一出;《孟子·离娄上》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都是出于传宗接代的考虑而提出的。在传统观念中,支配婚姻的动机为生育,女性成为生育的工具。卓佩珊夫人的求子行为,反映出传统观念的残留意识,只有生出孩子才算是自己为婆家做了贡献,传统思想在她心里变成了一副重担,她时时刻刻都用这样的思想来提醒自己,只有孩子能让婚姻变得圆满。五四启蒙运动虽启迪了一部分人,但先进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渗透进女性的思想中,即使受过教育的女子,在她们的意识中也依旧受着传统的摆布。《雾》中素贞小姐虽受过教育,但仍然是一个守旧的人。她看到火车上女客人的旗袍袖子很短就觉得害羞,对于“自由恋爱,素贞小姐是一向反对的”[2]232,受过教育且经过五四新文化的启蒙,新女性应当具有新的人生观,但她却没有。而且当素贞知道她心目中的完美男子是一个戏子的时候,态度突然转变,认为他是“一个下贱的戏子”[2]236。小说结尾说“今天的雾真大,一点都看不清楚哪!”[2]237,素贞小姐看不清的,不仅戏子,还有她自己被传统思想压制的心灵。《春阳》中的婵阿姨“感觉到寂寞,但她再没有更大的勇气,牺牲现有的一切,以冲破这寂寞的氛围”[2]258,这样的“恪守妇道”,一守就是十三年,她无处释放也不敢释放,其实背后反映的正是性压抑所带来的寂寞。“节是丈夫死了绝不再嫁,也不私奔”[5],是传统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一副沉重的镣铐,它维护着家族礼教的专制统治。婵阿姨在传统女性贞节观的束缚下,在金钱和旧有道德的压抑下,只能在幻想中满足自己的欲望。在传统思想的压制下,婵阿姨非但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更是只能在幻想中来稍微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欲望会永远作为一根针,提醒着自己有多痛苦。
无论是卓佩珊夫人对于孩子、文雅的男性,还是素贞对于婚姻,或是婵阿姨对于男子的渴望,都体现了传统礼教对于女性的毒害。传统社会要求女性要有三从四德,几千年的文化早已深深刻在她们的头脑中。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了“女性”这个词语,标志着女性以独立的人的身份出现在社会上,但并不能覆盖全部女性,启蒙精神只在知识分子、学生当中广为流传,并没有渗入整个社会群体中,也没有唤醒普通的民众,更没有打破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伦理结构。这些善女人便成为了五四遗忘的对象,她们之所以“善”就是因为传统思想的束缚,善并没有带给她们任何好处,即使内心已经开始翻江倒海,但仍然规规矩矩,她们作为“人”的欲望被压制在了内心深处。“个人生活是决定于社会的,社会既然如此难以安定,则个人生活除了‘浮生偷活姑安之’,也不敢有奢侈的梦想”[6]。卓夫人、素贞、婵阿姨都在传统文化的束缚下活成了社会想要的样子,并且把自己的欲望深深地埋葬在心里。
三 独立的缺失
“社会性别”由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最早提出,主要观点表现为“女性”应具有顺从的美德,“男性”具有支配与控制的权利,当然,这本身就是一种男权文化的表现。男权文化存在于人们的基本生活中,常常被认为是约定成俗的。《雄鸡》中阿毛娘在丈夫死后受到婆婆的欺辱,既没有再嫁的权利,甚至和别的男性接触多了也不行,更别说逃离,最后发生了上吊的惨剧。《阿秀》中的阿秀,被自己的爹用850块钱卖了,却不被丈夫当人看,没有话语权,后来逃出去嫁给炳生,也只是从一个男权制家庭到了另一个男权制家庭,最后还发生了一场悲惨的闹剧。《特吕姑娘》中的秦贞娥小姐,为了让自己的工资上涨,利用自己的美色让男人在她的柜台消费。她们都是被男权家庭及社会欺压、支配的对象,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痛苦之中,无法逃离。阿秀像一个玩具,被两个男人玩得团团转,恰似张爱玲《连环套》中的霓喜,依赖着男人生存,从一个套子进入另一个套子,将自己锁了进去。无论是阿毛娘、阿秀,还是霓喜,最终从男人身上没得到什么,反而失去了自己所有的青春和希望。在传统文化中,女子是男子的附属品,三千年的妇女生活,早被宗法组织排挤到社会之外了,妇女总是被忘却的人,“除非有时要利用她们,有时要玩弄她们之外”[7],这些妇女是没什么重要性的,她们没有自己的地位,好像一定要依靠男人才能活下去。偏远农村中的家庭把所谓的“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表现到了极致,在丈夫死后,女人依然遭受着整个家庭的控制与伤害。《雄鸡》中的婆婆体现出了“仿父权”的统治,在她“熬成婆”后,便以同样的方法去对待弱小的媳妇。这种女性试图拥有“父权”一样的统治,女性奴役女性更是可怕。文中很多次描写看到婆婆后阿毛娘恐怖的眼神,可想而知她平时的生活多么悲惨。阿毛娘在丈夫死后,对于自己欲望的压抑,不仅是宗法父权对于女性的压制,更是女性对于自己道德上的压制。社会还没有脱离宗法的桎梏,贞操成为妇女自身的“宗教”,这样的悲惨还将继续下去。罗家伦提出“妇女解放的第二步就是妇女的职业解放”[8],但事实上,即使妇女有了人格,有了知识,不坐在家里成为附属品,出去工作,也依旧摆脱不了这种“奴隶”生活,她们一面未曾完全脱离家庭的枷锁,一面又做了工资的奴隶,也就是男性的“奴隶”。《特吕姑娘》中的秦贞娥小姐,她的原型是距今九十年前上海著名百货公司永安的“康克令皇后”谈雪卿,她在受到一些顾客的侮辱后选择了辞职,最后与一位男子结婚。经过改编,文中的秦贞娥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工作中被顾客吃豆腐,但为了自己的工资上涨只能隐忍,还是要靠这些男人吃饭,最后得到公司的告诫书,之后便是“永远是患着忧郁病似的了”[2]291。可以看出即使女性有了工作,依然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还是要依靠男性。
被婆婆欺负没有自己人格的阿毛娘、陷入男人套子中的阿秀、最后患了忧郁症的特吕姑娘,她们没有接受过“人”的教育,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人”,更别说想着去自我解放。她们的遭遇体现出了她们所在家庭、社会的男性中心意识,她们没有自己的选择权与独立意识,甚至不如《春阳》中的婵阿姨。米利特的《性政治》提到“男权制的主要机构是家庭,家庭即是反映大社会的一面镜子”[9],阿毛娘和阿秀的家庭生活,特吕姑娘最后的遭遇,都是男性压迫所造成的生命异化,依附于男性的传统女性,精神空虚与命运惨淡是确定的,每篇小说都弥漫着悲剧色彩,这些善女人成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善女人行品》是施蛰存的一部“女体习作绘画”[10],这些善女人的故事反映了女性婚姻的不幸、欲望的压抑和独立的缺乏。这些家庭中的琐事,从一个世俗的小窗口透视了新旧交替过程中女性的尴尬命运,对于思考婚姻生活是一面值得借鉴的明镜。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