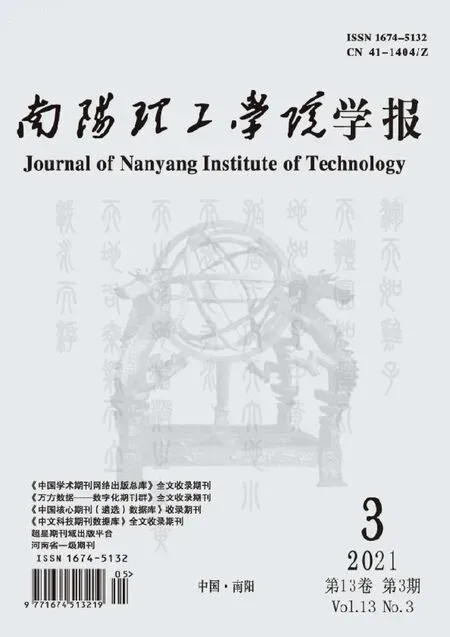“文化守成”与多元现代性追索:寻根小说再审视
张旭东
(南阳理工学院 传媒学院 河南 南阳 473004)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际、国内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寻根”思潮蔚然兴起,昭示了中国文学逐渐挣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具有了广阔而深远的文化视野,而其中成就最大的,无疑是“寻根小说”。 诚如吴秀明所言:“文学不仅是形象的艺术、情感的载体,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现象,它蕴含着时代社会或明晰或模糊或先进或滞后或平实或超越的种种精神走向。”[1]寻根小说也是如此,它是对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和民众精神的艺术显现和表达,如果把其纳入到当时开始逐渐壮大的“文化守成”思潮视域下去考察,则可发现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价值趋同。虽然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寻根”运动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但从广泛意义上看,其所确立的文化审美视角和精神价值指向却长久留存,并影响到后来的文学创作,值得我们从文化守成和多元现代性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和探究。
一 回归传统文化,追求本土文化身份认同
将寻根作家的理论主张与文化守成思想内涵相比较,二者相合之处甚多。其中,最明显和首要的是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回归,以及对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纵观几位代表性寻根作家的理论主张,可归纳其大致的逻辑理路:社会政治层面的种种变迁和沿革仅是表层,而更深层的,是“文化制约着人类”,影响和决定着人类的发展;具体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五四以来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上的激进态度割裂了民族文化的整体性,造成了“文化的断裂带”,所以目前文学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接续上这遗失了的传统文化,真正使中国文学“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阿城);文学是有根的,“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韩少功),所以要改变以往对传统文化的单纯批判态度,对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认识”;特别是在对待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方面,要对以往“唯西方是崇”的做法进行反思,确立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的“根”在东方,“东方有东方的文化”,中国文学要想真正地被世界认可,就必须“建树一种东方的新人格、新心态、新精神、新思维和审美的体系”(郑万隆)。这些理论主张归结到一点,实际上表达了要建构民族传统文化的“同一性”和“民族自我”的主体性这一文学需求和文学思考,是一种明显的民族文化认同话语。并且,这种对民族认同的表述,“并不是在单一的中国/西方的框架内展开的,而同时与‘新时期’/‘文革’这样的历史变革的诉求联系在一起”[2],其反思启蒙现代性的“文化守成”思想理路非常明显:他们试图通过“寻根”, 修补之前近十年的精神创伤,在满目疮痍的精神废墟上重铸东方民族的文化主体,从而开辟出民族前行的道路。
从具体的小说文本来看,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回归意向,最早在汪曾祺的系列小说里就有明显体现。虽然汪曾祺本人并不曾明确提出过“寻根”主张,但其小说文本中浓厚的文化蕴含以及向传统文化回归的主旨意向,可以说与寻根小说一脉相承。同乃师沈从文一样,汪曾祺的小说最着力的不是叙写时代之变,而是描画人生之常。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家们竞写时代变革的大潮下,他却注目于发掘自然人性美与追求民族品德重造,对既往的不曾污染的山川田野风情与纯朴的人际情感进行礼赞与缅怀,当然有些不合时宜。然而,正是他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历史无意识”,却以其深厚的审美意蕴引导了后来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当西方现代性日益显露出其不可克服的弊端时,这种文学创作就更激起了人们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汪曾祺的系列小说,无论是《受戒》《大淖记事》还是《异秉》《岁寒三友》等,到处都显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好因素的赞美与讴歌:儒家文化中的积极进取、忧患担当精神,适切的伦理秩序,和谐的人际关系;道家文化中的天人和谐、亲近自然、随性自适、旷达超脱等。作家通过对古朴而诗意的东方生活方式的精心描摹和深情回顾,营造了心目中理想的中国文化,真切地传达了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和认同。
此后阿城的“三王”系列、李杭育的“最后一个”系列等小说,可看作是对这一传统的自觉承续。《棋王》中的王一生,其最突出的文化人格是对世俗功利的超脱以及个人人格的独立自洁,这自然深受道家和禅宗文化的影响和塑造,他的从容散淡、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态度,那种用理智坚定地驾驭情感的东方智慧,无不体现出对传统文化中合理成分的继承;不仅如此,王一生的身上同时有着儒家文化的积极因子,比如其生命意志的强劲以及身处困境而不灭的对人生前途的积极进取和追求等。此外,像《树王》中的肖疙瘩、《孩子王》中的“我”和王福、《最后一个渔佬儿》中的福奎等人物形象,他们的人格精神中也无一不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精粹。“寻根”作家通过一系列类似主旨的创作,明确表达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对民族和国家的热爱,诚如有论者所说:“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是总体的、彼此相连的,它不只是信仰的、道德的、真实和勤奋的,同时还体现出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和民族国家的热爱。”[3]稍显例外的可能是韩少功,他的寻根小说代表作《爸爸爸》《女女女》接续的却是鲁迅以来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优根”没有寻到,却掘出了我们民众的“劣根”。其实,韩少功在这里也并不是对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彻底否定,而是期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审视和重新清理来让中华文化获取现代品格,从而更好地汇入世界文化发展主流,完成民族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重建价值系统和国民精神。况且,韩少功在创作这两篇小说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有尖锐的批判,但同时“也有同情甚至赞美”,如“对美丽自然、质朴民风、顽强的生命力,包括老人们在危机时舍己为人的自杀等”[4],都心存感激、由衷赞美。汪曾祺很早就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和传统文化脱节“是开国以后当代文学的一个缺陷”,因此,他的小说创作就是要“复活”与“转化”传统,“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5]。当然也可以说,汪曾祺的小说是“既古且今、中西兼容”,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完美结合。
应该指出的是,寻根作家这种对民族本土文化的认同和归依,并非盲目的复古,更不是机械的“倒退”,也不是极端的排外(至少从他们寻根的初衷看是如此),他们在对待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是非常清醒、通脱、辩证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并非一味大唱赞歌,同时也对其中的负面因素批判有加;对于西方文化,他们并非民族主义式的完全抵制和排斥,而是持一种开放和融汇的态度,也主张从西方文明中吸取有益的元素。他们渴望以“现代意识”去观照民族传统文化,寻找其中的优势和力量源泉,再通过对西方优秀文化因子的吸收,促进中国文化健康发展。所以,提倡寻根“并不是要复古,而是要清理、改造、利用各种文化资源,更好地向前走”[6],“准确地说,是在借传统改造外来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反观传统,解释传统,选择传统,通过调整传统的内部结构来创造一种更富有生命力的‘新中有旧’的‘传统’”[7]。许多论者对这种价值追求进行了充分肯定,如陈晓明指出:“‘寻根’当然不是简单的复古,不是保守的,它站在现代性的高度,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思考中国文化的命运,来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价值标向。它比那单纯的现代意识显得更加高瞻远瞩,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8]李欧梵也认为,“他们的寻‘根’不可能是一种怀旧的行为,而是一种想象性再造的积极的努力,以便重新赋予这些长期缺席的文化资源以生命力,作为重建一个更有意义的现实(在艺术层面上)的途径,作为消解有关革命史宏大寓言的神秘性的方式”[9]。其实,寻根作家自己对此也有清醒而辩证的认识,韩少功认为:“东方文化自然有很落后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他并且非常欣赏批评家单正平创造的一个词:创旧,认为“创旧”的过程就是“旧获新解”“旧为新用”的一个过程,“更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创旧’还在于人文价值方面的薪火承传。中国正在迅速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过程,正在经历实现现代化和反思现代性这双重的挤压,正在承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各方面的变化和震荡。……各种传统思想文化资源被重新激活并且被纳入作家们的视野也就是必然的”[10]。
二 反思启蒙现代性,张扬审美现代性
寻根小说和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主旨和文化价值倾向上另一契合的地方,在于主张以价值理性对抗工具理性,反思启蒙现代性造成的人性的疏离和异化,因而倡导审美现代性的制衡。寻根小说当然有对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启蒙主义式的批判,但与此同时,对重建一种极富感性、诗性、神性的“人文魅性”(孔范今语)文化的要求则更为迫切,期望以此对现代性的科学主义弊端予以补充与校正。如果说这一点在寻根文学的倡导之初还不太明显的话,则愈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模式的弊端愈益显露之时,表现得就越清晰。
对于一个前现代化国家来说,尽快实现现代化无疑是全民的理想,因此,“拨乱反正”后,作家也同许多人一样,对“现代化”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与渴望,并通过创作表达急切的呼声。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诸如道德迷失、人性异化等现代化的危机和弊端也开始逐渐显露,这让作家又不能不对其产生警惕、疑虑甚至排斥心态,虽然理性上他们都认识到这是现代化追求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情感上仍然对传统农业文明那种宁静、平和的生活方式缅怀有加,正是在这一矛盾心境下,一部分作家开始倡导文学“寻根”,以审美现代性的方式表达对技术理性偏颇的批判。这一点,正和文化守成主义的主张异曲同工:向“传统”复归,在过去与当下的比较中礼赞过去牧歌式的理想生活。而且这种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反思,又有着明显“超前”的“后现代性”色彩:“后现代性……,它倾向于‘恢复过去的文化’,试图‘找回已往的一切文化’,找回所有被摧毁了的东西。”[11]
反思和质疑启蒙现代性和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压抑以及对完整生命的切割,因而提出审美现代性的维度,这在小说文本中的具体表现有:对理性、科技等现代观念的犹疑和拒斥,对城市文明、市侩文化的批判;对传统不规范文化及乡土文明生活方式的礼赞;对“民间”的认同与皈依。在寻根作家眼中,以城市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化模式,到处充满了功利、算计,“唯实唯利”是崇,对人性造成了极大伤害和扭曲,而且,它的各种负面影响也开始逐渐蔓延于广大的乡村,对传统乡土伦理和文明造成冲击。痛感于现代文明的这种片面性,意识到原始生命力被抑制与阉割的深层危机,作家们开始满怀忧患地对城市文明带来的这种人际关系异化、人格人性扭曲、社会道德失范现象进行揭示,表达“对于拜金主义的批判,对于人格上委琐、蒙昧、造作、虚伪的厌恶,对于工业文明的异化以及城市综合征的警觉”;同时,作为弥补和制约,作家们着力于对乡村原始文明和自然的生命状态进行礼赞,呼唤元气淋漓的野性与强力,缅怀和谐、淳朴的人伦关系,“表现出对于自由脱俗、独立精神的向往,对于旺盛生命力以及勇敢、胆魄的赞叹,对于感性、感情、热血义气的推崇,对于原始自然景象的由衷欢悦”[12],力图以这种本真、素朴的人性以及明显理想化了的、保留在自然山水和乡土田园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来对抗工业文明、商品经济中唯利是图的庸俗市侩哲学,挽救当下人性的堕落。郑义、郑万隆、王安忆、李杭育、韩少功、贾平凹等作家的作品里对此有形象的表达。
贾平凹的小说《古堡》,写“现代”观念开始影响到古朴的村落,唤起了村民们对金钱的渴望和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理想的蓝图是明晰而诱人的:改革开放,治贫治愚,提高人的素质,然后形成良性循环,快速而健康地实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就像大城市来的导演对村长老大说的那样,“……多赚了钱,人的素质慢慢就起了变化,人变,什么事都好办”,“矿还要挖,但往后就要多注意怎样使村人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坚强自己”——一方面发展经济,一方面同时进行思想教育和素质提升,这当然是很好的想法。但似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农民们的经济水平的确是越来越高,可人的精神素质和道德品质却没见有同等程度的提升,反而一些传统美德和美好伦理在乡村逐渐消逝。带着深深的困惑和忧患,贾平凹在作品中开始更多地表达对以往美好乡村生活的缅怀,对乡村不良现状的批判。其他像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作家,他们笔下所塑造的主人公,“这些人物的刚烈、血性、自由精神以及对于财富的蔑视显示了另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是非西方的,前现代的,同时又包含了某些令人向往的自在境界。他们的存在即是对现代社会的斤斤计较、功利、投机和猥琐报以轻蔑的嘲笑”[12]。寻根作家正是通过对这种传统不规范文化及乡土文明生活方式的礼赞,来表达对这现代性压抑的不满与抵抗。
在对“民间”的认同上,寻根文学与文化守成思想也显现出了一致。它们都认为在现代文明的强势冲击下,传统文明几乎被荡涤一空,只在民间还稍有留存。关于文化守成主义的“民间”追求,艾恺说:“对乡村社会、乡民和中世纪(常常包括宗教在内)等的加以提升和歌颂,在浪漫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中几乎是无处不见的主题。”[13]而寻根作家也是一样,他们所寻找到的文化之根和繁华的都市没有关系,它们或存在于村庄田头、胡同里弄、海边江上和森林草原里,或见于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和风俗中。贾平凹在商州的山川、人物和习俗中找到了它,乌热尔图在大兴安岭森林中鄂温克人的身上找到了它,扎西达娃在藏族的神秘文化和异域风情中找到了它,李杭育则在葛川江上“最后”的渔佬儿那粗犷、豪放、硬朗、洒脱的个性中找到了它……比之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他们情感的天平明显偏向以天人和谐为生存准则的农业文明。他们在写作中开始自觉地把目光投向日常和民间,叙写那存在于民间的乡风民俗,礼赞那种朴素和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表达民间文化的富有活力、自由自在和生机勃勃。这种致力于“向后看”的书写策略,赓续的仍然是汪曾祺所开创的“怀旧模式”,即“以原始文化、民间文化作为感知基础,转化正统道德文化为生命动感文化,使民族的过去得以重新构成”[14]。
三 追求自然环境生态和人文精神生态的双重和谐
寻根文学和文化守成思想主张相契合的第三个层面,表现在对自然环境生态和人文精神生态双重和谐的追求上。这一点其实也是和对启蒙工具理性的反思批判相一致的,因为,在工具理性的价值观念下,人们对待自然万物采取的是一种功利的、算计式的态度,一种“一切为我所用”的无限制的索取态度,却缺少目的性的关怀,这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同时也招致了同样严重的精神危机,如道德滑坡、信仰沦丧、精神萎缩等。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许多作家开始思考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写出了《大林莽》《灵缇》《沙狐》《野人》等作品。寻根作家也较早就觉察到了这一点,与一般的书写自然的小说不同,他们不光描绘人与自然之间神秘的联系以及和谐共生的关系,更敏锐地意识到自然生态与人类文化之间有着内在而潜隐的联系,所以他们的创作更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反思和批判现代文化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强调“回归自然”,维持文化和生态的多样性,达到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双重和谐。这些作品包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以及阿城的《树王》等。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关注的是商州人虽略显原始但古朴自然、自由随性的诗意生活方式,担忧的是“历史的进步是否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社会朝现代化的推移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之风的萌发”等问题。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对现代工业文明破坏自然生态、戕害和谐的传统乡村伦理精神进行了有力的揭示和批判:主人公福奎,可看作是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牺牲品,他在轰轰烈烈的时代变革面前,不去迎头赶上,而是固守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以至于无鱼可打,成了可悲的“最后一个”。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无鱼可捕呢?一是现代人的滥捕过度,二是江河水的大面积污染。小说与其说在批评福奎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不如说是在呼唤一种健康和谐的生态环境。阿城的“三王”系列,其“主旋律是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和人情味”,它重新审视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目的是找寻人失落的本性,以及人的灵魂与外在世界和解的希望。其中,《棋王》推崇的是一种随性自然、淡泊超然的道家处世哲学;《孩子王》张扬的是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树王》则明显表达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人定胜天”的迷信神话的否定,以及对天人合一生命境界的崇尚等多重主题。作为“知识”和“科学”代表的红卫兵李立,信奉的是“人定胜天”,相信人类无穷的创造力量,在他看来,大规模的毁林垦荒正是人力控制自然的体现,但“树王”肖疙瘩怀着对森林的朴素感情,直觉上感到这样毁坏环境是有问题的,他要像看护自己生命一样地保住“树王”:“可这棵树要留下来,一个世界都砍光了,也要留下一棵,有个证明……证明老天爷干过的事。”李立对此的回答最引人深思:“人定胜天。老天爷开过田吗?没有,人开出来了,养活自己。老天爷炼过铁吗?没有,人炼出来了,造成工具,改造自然,当然包括你的老天爷。”这明显表达了阿城对人类肆意“征服”自然的质疑,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而主人公“树王”肖疙瘩身上那种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素朴而可贵的生态意识无疑寄寓了作家理想的价值追求。
毫无疑问,以城市化、工业化为根本特征的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因素,因此,寻根作家的生态思想是与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质疑和批判分不开的。正如韩少功敏锐指出的:“什么是生命呢?什么是人呢?人不能吃钢铁和水泥,更不能吃钞票,而只能通过植物和动物构成的食品,只能通过土地上的种植与养殖,与大自然进行能量的交流和置换。这就是最基本的生存,就是农业的意义,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以土地为母的原因。英文中culture指文化与文明,也指种植和养殖,显示出农业在往日文化与文明中的至尊身份和核心地位。那时候的人其实比我们洞明。总有那么一天,在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激荡之处,人们终究会猛醒过来,终究会明白绿遍天涯的大地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15]人们需要回归自然,建立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和谐关系。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寻根作家通过理论阐述和文本创作给出的答案是:返归传统文化,吸取古老自然观中有益的养分,如儒家的民胞物与、利用厚生,道家的天人和谐、顺应自然等,对西方那种戡天役物、无节制开发资源的自然观进行矫正;警惕“唯科学主义”,破除“人定胜天”的迷信神话和狂妄浅薄,重新思考天人关系,尊重自然,呵护生态。
四 余论
从“文化守成”的积极面向来考察,“寻根小说”的价值理念的确值得称赞,如它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转换性创造”的努力,对启蒙理性的反思性批判,对生态和谐的追索等,都充分彰显了其现代性的品格,而且提供了迥异于西方启蒙现代性的另一种文化现代性理路,彰显了现代性追求的多元性和动态性。但与此同时,在一些寻根小说中我们也能明显感觉出其价值理念层面的偏颇,而这也正是导致该思潮没能保持长久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在对待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上,缺乏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对于自身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认识不足、批判不够,态度暧昧,甚至对一些传统陋习表现出玩味乃至欣赏的态度,并且对民族性特征的认识“停留在某一静止的时刻,而不是将民族文化看作一个不断开放的,同世界上所有优秀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动态发展的结构”[16];其次是启蒙反思与批判上的“因噎废食”,认识不到人类的进步端赖于启蒙理性的健康发展,而是基于一种对“现代”的恐慌,盲目否定启蒙现代性的价值,所以其批判的尺度也就不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尺度,而是前现代的农业文明的尺度;再次,在处理民间性、地域性的古老文化习俗与现实生活、时代精神的关系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偏颇,主要表现在,只是用表层的地域文化的展示代替对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入挖掘,而且往往认为真正的生命的诗意只能存在于边远甚或蛮荒的乡野民间,从而“颠倒了社会实践主体与精神主体的关系,导致文学的审美、文化寻根同文学的社会、历史观照相悖离”[17]。
这些文本实践中所显示出来的价值理念的偏颇时刻提醒我们,寻根小说的这种“文化守成”的价值追求,如果缺乏清醒的现代意识的观照,稍有不慎就会堕入真正“保守”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