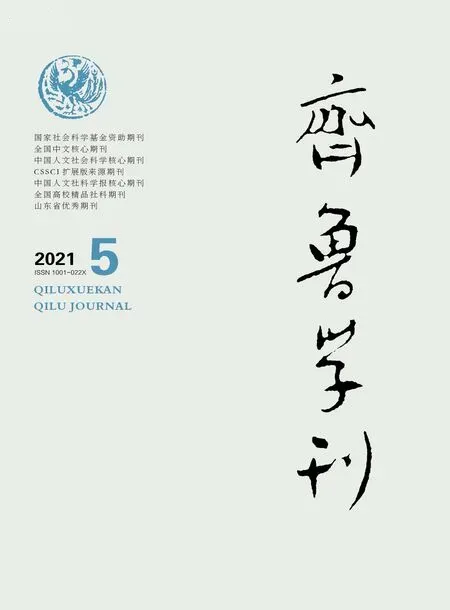关于后葛瑞汉时代文本分析的反思
刘笑敢 撰,刘雪飞 译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100875;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273165)
葛瑞汉是首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西方学者。1985年夏天,我在北京大学刚刚完成关于《庄子》文本及其哲学研究的博士论文时,曾将一本论文送给当时在北京大学任客座教授的杜维明教授。后来维明教授与我交谈时,他开口就说:“你的论文写得很好,你的做法和葛瑞汉一样,他也对《庄子》做了语言学上的分析。”这让我非常好奇。我的研究方法怎么可能和我从不知道的西方学者相类似呢?
1988年春天,在为期两年的哈佛访学之前,应孟旦(Donald Munro)教授的盛情邀约,我前往密歇根大学做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我在那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借阅葛瑞汉的书。我发现,他的庄子研究尽管和我有明显差异,但也的确存在某些相似之处。
翌年夏天,当我在夏威夷召开的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见到葛瑞汉本人时,我希望就庄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他进行探讨和交流。但出人意料的是,还未等我提及,他就表示他对庄子研究不再感兴趣。所以当时我们谈论了许多其他问题,未再涉及庄子。
虽然葛瑞汉未能直接回应我的愿望让我稍感失望,我还是很想了解他的方法和观点。通过个人的观察和学术上的考察我对他的学术风格和个人性情有了一些了解。在我看来,葛瑞汉岂止是位学者,他简直是一个天才。尽管天才也努力工作,但与众多研究者不同的是,天才所取得的独特成就更多地来自于自身的兴趣、天赋和活力。天才不大顾及或不严格遵循专业研究的常规做法,更无意于成为通常意义上的所谓专家。他们往往为满足自己极大的好奇心和兴趣而自由地发挥他们的才能。
葛瑞汉的确是个天才,至少从我的观察和了解来看是这样。他对诸多课题和文本都进行了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撰写了有关老子、庄子、列子、墨子和二程的专门论著,出版了《论道者》(DisputersoftheDao)、《晚唐诗选》(PoemsoftheLateTang)、《西湖诗选》(PoemsfromWestLake)等著作或译著。此外,他还出版了富有挑战性和思想性的其他著作,内容涉及更为广泛的哲学话题,包括《理性中的非理性》(UnreasonwithinReason),《价值、伦理和科学问题》(TheProblemofValue,Ethics,andScience),以及《理性与自发性》(ReasonandSpontaneity)等。他总是以其独创的文本分析、优雅的译文、对文本研究的独到见解、精彩的推理以及哲学的视域和洞见给学界同仁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如罗斯文(Henry Rosemont,Jr.)所言,葛瑞汉“既因其作为一名语言学家、语法学家和翻译家对中文文本研究的深度,同样也因其对这些文本哲学诠释的广度而闻名于学界”(1)参见[美]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为[美]哈罗德·罗斯(Harold D. Roth)编著的《葛瑞汉〈庄子·内篇〉研究导读》(A Companion to Angus C. Graham’s Chuang Tzu: the Inner Chapters)(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3年)所作序言,见该书第9页。。这也就难怪在我所编辑的《道家哲学研究伴侣》各章中他是唯一一位名字出现次数最多、援引率最高的学者(2)参见刘笑敢主编:《道家哲学研究伴侣》(Dao Companion to Daoist Philosophy),纽约和伦敦:斯普林格出版社,2015年。。
我深感荣幸的是,能受邀为葛瑞汉纪念专辑撰写纪念专文,他是伟大的学者和精神的鼓舞者。我相信,这本书不仅是对一位杰出学者的礼敬,而且也是一个展示其典范性研究和方法以供后学借鉴的平台。我的这篇论文将指出,在大师离世之后的时代,我们在进行文本分析时普遍存在着一些无意识的假设,这应该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这实际上是对文本分析中预设的一些基本假设的反思。其中有些假设尚未得到明确阐述,更不要说进一步的讨论了。古代墓葬中出土的诸多文本激发了我们的反思,这些文本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业已熟悉的关于中文文本的某些通行的认知和结论。这里的关键问题不仅是依据这些文本证据来改变和修正我们的立场,而是要重新审视数十年来导致我们错误立场的路径和方法。如果没有这些重要文本的出土,我们仍然会延续这种错误,并且忽略一些至关重要的认知盲区。我的反思将会触及葛瑞汉的研究,但不会局限于他个人的理路,因为我们之中的多数学者都有意无意地采用了与其相通的路径和方法。有的读者可能会认为本文意在持守传统认知,但这决不是我的初衷和目的。为任何立场辩护或论证,都不是本文的工作。应该做的远远超出了本文能够容纳的范围。本文的重心乃是方法论的回顾与反思,特别是要重新审视葛瑞汉与某些传统不同的学术立场,以及在这一立场支配下的论证中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性的假设。这些假设已经被最近的考古发现证明无效,从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3)我做文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各种类型的证据,并且为更合理的立场寻找新的证据。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可能无法讨论。当然,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学者们可以提出各种猜想,尽管我对此并无多少兴趣。对我有关《老》《庄》文本问题的讨论感兴趣的学者,可参阅《道家哲学研究伴侣》中的“道家有创始人吗?——关于《老子》的文本问题”以及“《庄子》的文本问题”,见该书第25 -45页、第129 -157页。。
以下就是我们在文本研究中应该重新考虑的四个无意识的假设:
1.现有文本和文献代表了历史上所有的全部文本和文献。
2.合理的推理和推测比不完善的历史文献记载更为可靠。
3.历史文本或历史记录要么被判定为真实可靠,要么就应该丢弃不用。
4.某些例证可用作总体性判断的证据。
假设1:现有文本就是古代文献的全部
这是现代文本分析,尤其是在认定作品年代问题时一种惯常的假设。以《老子》成书为例,钱穆(1895—1990)这位备受国人尊敬的一代儒宗,最早声称并坚持主张《老子》成书比《庄子》晚出[1]。他的立场曾一度被学界公认是20世纪30年代颇具影响力的“古史辨”运动的一部分,但他的观点很快就受到了梁启超(1873—1929)、胡适(1891—1962)以及其他学者的批评。抛开所有的争议、论辩和推断不谈,1993年郭店楚简本《老子》的发现最终证明《老子》成书不可能晚于《庄子》,因为考古学家将郭店楚墓下葬的年代断定为公元前278年,学界一般认为庄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而该墓主人拥有三组《老子》竹简。这一事实表明,当时已经流传着多个不同版本的《老子》,因此它们成书的时间就会比郭店本埋葬的时间早10到20年,而《老子》祖本的流传年代肯定还会更早。所以说,《老子》晚出于《庄子》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
钱穆的论述主要立足于他所谓的“思想线索”理论,这一理论大意是说,思想家的思想从早到晚是呈线性承继演进的。具体而言,钱穆提出了这样一种设定,即弟子思想的大致轮廓必定源自老师全面而详细的讲述。因此,《老子》这部仅有五千言的短文,一定是从《庄子》的长篇宏论中衍生、抽绎出来的。这种预设是很成问题的,因为相反的情况似乎更有可能,即宗师提供某种宏大思想观念的简要框架,追随者将其发展成精微的系统论说,就像孟子对孔子语录的开拓性阐发一样。钱穆的“思想线索”理论在英语学界影响甚微,此处不再赘述。
当我发现葛瑞汉采取了和钱穆相似的立场,且在他的力作《论道者》中,将有关老子的章节置于庄子之后时,我很是惊讶,甚至有些为他感到遗憾,因为钱穆的观点无疑是值得商榷的,而我原本以为葛瑞汉应该有更为合理的判断。实际上,葛瑞汉设计出了一套相对周全的策略。他没有提及钱穆的假设,却为其在老子断代问题上所持立场提供了更加复杂的理由。
葛瑞汉试图以其设想之策来解决持续争议将近一个世纪的问题。概而言之,他的假设不是基于正面证据的存在,而是建立在与其假设相矛盾的反面证据缺失的基础之上。葛瑞汉立论的主要依据是,既然《庄子》之前没有任何文本称引过《老子》,那么这就构成了《老子》成书很可能晚于《庄子》的“证据”。葛瑞汉声称,“由于《庄子》‘内篇’并无明显迹象和确切证据显示其对于《老子》的熟识,所以可权且将《老子》成书时间认定在《庄子》之后,尽管没有正面证据证明它的晚出”(4)[英]葛瑞汉(A. C. Graham):《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拉萨尔:欧朋·考特出版公司,1987年,第217 -218页。原英文引文中所有的韦氏拼音我一律将之替换为汉语拼音,并且将其中的重点语句做了标记。。
葛瑞汉的方法看起来似乎非常科学:一切都应以直接证据为依准。在缺乏直接证据,就是说在《庄子》之前的其他作品中尚未发现对于《老子》文本直接引述的情况下,葛瑞汉暂且将《老子》置于《庄子》之后,以此来适应对传统观点的挑战。但这不能不说是自相矛盾的:将《老子》置于《庄子》之后,这就背离了他似乎从一开始就遵循的证据原则,因为他承认“没有正面证据”能够支持他新的年代排序,而且《老子》书中也未见出自《庄子》的引文。
葛瑞汉的方法让我们不禁联想到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的做法。他曾主张《老子》是在汉初《淮南子》(约公元前141年)成书之后被伪造出来的。翟理斯依据的是,孔子、左丘明、孟子、庄子、荀子、《淮南子》以及司马迁从未见过或者声称见过《老子》文本(5)[英]赫尔伯特·翟理斯(Herbert A. Giles)在提及韩非子的作品时说道:“[《韩非子》一书]专门用两整篇来系统地‘解老’‘喻老’,从这两部分看,韩非子似乎在参照某种写成的文本。”参见翟理斯:《老子遗存》,《中国评论》1886年第14卷第5期,第231 -281页。。由此他提出了《老子》汉初伪造说。翟理斯的观点后来逐渐被遗忘,1973年马王堆帛书的出土最终使之被搁置。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和乙本比较确切的抄写年代分别可追溯到公元前195年和公元前169年之前,这无疑证实了翟理斯推理和论证的无效,但我们却很少从他的失败中汲取教训。葛瑞汉的假设不是基于肯定性证据,而是依据“缺少否定性证据”以及对传世文献的排除,由此来看,他实际借鉴和采用的是翟理斯的理路和方法。
翟理斯是一位富有经验和开创性的学者。从他的推理来看,他的论证似乎合乎逻辑,但他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他论证的缺陷究竟在何处?恐怕在于他的无意识的假设,即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接触到了古代全部可用文本。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的考古发现之前,很少有学者意识到古代90%的古籍已经佚失。时至今日,翟理斯的这种假设依然是多数学者的共识。因此,尽管一个人或许会极尽所能、极为细致地去检阅所有可及的文本,但他看到的仍可能只是古人所知的文本、记录和典籍中很少的一部分。不仅如此,翟理斯的文本推理还植根于其更为具体的特定假设,这些假设也同样为现代学者所认同,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翟理斯的推论都难以成立。这些假设是:
1.所有古代的文本和典籍都必须在其他文本和典籍中被记载、引用或提及。
2.所有这些其他文本和典籍也都必须幸存两千年以上,供现代学者使用。
3.只要我们看不到X,就有理由认为它从未存在过。
我通过举例来说明这些假设是不合理的。首先,假设我们手头有玛丽的记载,说苏珊写过一本书,但这本书从未被人引用过,也没有其他记载提及这本书。据此,我们并不能够断定苏珊没有写过这本书。其次,如果贝拉引用了苏珊的书,但苏珊和贝拉的书后来都佚失了,至今仍然无法找回,这并不足以证明玛丽的记载就是错误的,同时这本书不是由苏珊所写的根据也不够充分。第三,假如玛丽、切瑞和贝瑞三人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记述他们曾经看到或听说过苏珊的书,但现在我们无法获取到苏珊的书,因此也就没有充足的理由反驳玛丽、切瑞和贝瑞三人的记述,难以就此断言这本书的作者不是苏珊。
毕竟,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现在尚未发现X,就得出X在古代某个时间点之前从未存在过或者不可能存在的结论。更概括地讲,我们不能事先假定可供我们今天使用的典籍和文本就是古代著述的全部。因此,认为我们手头已经掌握了确定古代文本年代及其作者所必需的全部证据的无意识假设,是根本站不住脚的(6)我所认为的“证据缺失并不是没有证据”,是专门针对中文文本研究而言的。如果将其用作一般原则,则需作进一步讨论。例如,我们是否应该将没有有鬼证据的情况视为无鬼的证据。。这也是为什么基于现有书籍的逻辑推理而得出的结论最终可能会被考古发现证明是错误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没有学者正式提出过上述任何一种假设,但我们必须对中文文本分析中类似的推理背后那些潜在的假设保持警觉。因为即便是在最近几年,这样的假设在某些研究者的思想和方法中仍然根深蒂固(7)例如,2011年,朴仙境(Esther Klein)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关于《庄子》内篇包含了该书的核心和最早部分的传统认识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这些篇章可能是汉代学者选编的。她很少关注最近几十年出土的大量文本。她的结论类似于翟理斯和葛瑞汉,都是基于前文提到的假设。参见Esther Klein:《战国时代有〈内篇〉吗?〈庄子〉成书新证》,《通报》(Tong Pao) 2011年第96卷,第299 -369页。。研究中国早期思想的学者必须充分认识到,大量出土文本已一再证明这些假设在理据上的不足,任何基于这些假设的论争都是极其冒险的。翟理斯的方法可能适用于已经取得高度共识以及有足够证据和参照的某个特定的认识主体,但对于我们而言,古文献资料自身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无限的、难以尽知的领域:考古学家不可能发掘出所有的古书、记录和文献,但他们的发现会使我们驻足省思。建基于原有假设上的结论不仅根据不足,而且大多结论往往被新的发现证明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近几十年来,无论是已被史籍著录还是之前不为人知的著述,都有为数众多的帛书本和竹简本相继出土,它们的问世揭示出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中文文本仅占中国古代文献遗产的极小一部分。这其实也不足为怪,毕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的五十七部儒家著作,保存下来的仅有七部;三十七部道家著作,现存于世的仅有五部;十部法家著作,也只有两部幸存至今。更有甚者,近些年发掘出的90%的中文文本在传世的各种书目中均未见载录。
汉代历史学家当时能够见到比我们想象的更多的早期文本和记录。当然,他们也可能有失误,但他们不可能臆造历史人物和文献目录。新近出土的文献表明,汉代的历史文献记录比我们以往的认识要更加真实可靠。在参考文献资源方面,我们并不具备与他们争论古代作品真伪及其年代问题的优势,尽管我们的推理听起来似乎更具理论性、系统性和逻辑性(8)参阅刘笑敢为孟旦著《早期中国“人”的概念》(安娜堡: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01年)再版所作序言,见该书第ix -xxvi页。。
不仅如此,考古发现还表明,关于古代文本的一些传统观念应该得到修正。根据现代学者的推测,汉代文献中载录的许多书籍都被认为是伪书。但出土的简牍文本已经证明,其中的某些书籍在西汉之前就已广为流传,譬如《鹖冠子》《文子》《六韬》《尉缭子》以及《晏子》等等。
相较于不完善的历史记载,当代学者更倾向于相信“严谨的”推理。例如,钱穆曾对有关孙膑(约公元前380—公元前320年)所作《孙膑兵法》(9)根据相关的历史记载,孙膑与梁惠王大致生活在同一时期。和孙武(约公元前545—公元前470年)所作《孙子兵法》的历史记载,分别予以否认。因为《孙膑兵法》已经失传约两千年,钱穆就主张史上只有一部作者为孙膑而非孙武的《孙子兵法》,孙武不过是从孙膑故事中衍生出来的一个名字而已[2](P304-305)。然而,1972年山东临沂出土的《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的考古学发现表明,即使是大师级学者的推测也不如历史记载真实可靠。另一个例子与子思的作品有关。据早期文献记载,孔子之孙子思曾经有过一些著述,但后来失传了。学者们因此认为,子思当时可能并没有多少著述。但1993年郭店楚墓出土竹简中有关于“鲁穆公问子思子”的材料,这表明子思在当时可能是知名人物,且留下了自己的著作。诸如此类的例子说明,汉代史家的记载和著述是不能轻易否定的,“文本缺失”不能作为证明其自身从未存在的确凿证据,更不能成为有关文本年代问题的新理论或新假说构建的根据。我们必须意识到,怀疑性推理本身既没有提供新的证据,也没有提供坚实的知识基础[3](P140)。这是我们应当从考古发现中汲取的教训。
尽管我结合考古发现批评现代学界对于中国传统古籍的怀疑,但我并不认为“疑古”运动的精神完全错误,以至于要摒弃它的全部结论,转而相信所有古代文献记录。相反,我的意思是,我们确实应该为提高文本研究质量而改进我们的方法。这对该领域的良性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设2:合理的推断比残缺的历史文献记载更可靠
另一个无意识假设是,历史事实一定符合我们的逻辑推理和推想。这里的危险在于,合乎逻辑的推想有可能取代历史事实。仍以《老子》年代问题为例,当学者们强烈的怀疑使得他们抛开全部传统文献时,他们只能依据从存疑的文献记录中获取的一两条零碎信息来进行逻辑推理。
刘殿爵曾说,“我倾向于某种形式的《老子》最迟在公元前三世纪初就已经出现的推说”[3](P140)。刘殿爵坚称,司马迁“也难以搞清老子的身份。他明确表示老子与太史儋可能是同一个人,尽管后者生活在孔子去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3](P11)。这一观点也体现在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的著作中,阿瑟·韦利将司马迁的《老子传》描述成“一种承认撰写这样一篇传记没有任何史料依据的供状”[4](P108)。
刘殿爵误解了司马迁的语义:他轻忽了司马迁传记主体部分的肯定性叙述与其附记的两则传闻之间的区别。刘殿爵只侧重于两种传闻中的一种,却忽视了这一立场将比传统立场面临更大困境的事实。“明确表示”一词是刘殿爵用来支撑其解读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刘殿爵曲解了司马迁语义的关键点:“或曰儋(周太史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这显然并非刘殿爵所谓的“明确表示”。刘殿爵更没有进一步意识到,依照司马迁的记述,太史儋对秦国命运的预言与《老子》内容以及先秦汉代文献中反复提及的孔老会晤交流故事的主调均无关联。与司马迁的主体叙事相比,刘殿爵的假说与广泛意义上的历史文献有着更多的矛盾和冲突。
尽管如此,刘殿爵仍然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坦诚。他说,“我对老子的整体描述的确都是推测性的,但当能够确定的东西如此之少时,就不仅有推测的空间而且有推测的必要”[3](P132)。这里,我们必须澄清司马迁在老子身份、生活年代问题上不持有任何倾向这一普遍的、也可能错误的印象。
如果我们全面考察分析司马迁的《史记》就会发现,司马迁对老子生平问题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他并未受到附记中两则传闻的困扰。在《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对老子的身份和年代也并未怀疑;他保持了《老子传》主体部分的叙事方式,只字未提另外两则传闻。
此外,学者们考察《史记》七十列传的排列顺序后发现,这些传记基本上是根据首位传主的时代先后清晰有序地编排的。《老子传》位列第三,在管子之后,司马穰苴之前。管子曾经辅佐过齐桓公(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3年在位),因此远早于孔子。司马穰苴辅佐过齐景公(约公元前547年—公元前490年在位),齐景公曾问政于孔子,则司马穰苴与孔子当属同一时代人。司马迁将《老子传》排在管子之后、司马穰苴之前,表明他确信老子与孔子同时且略早于孔子。司马迁并没有将老子与战国晚期的太史儋混为一谈[5](P9)。
葛瑞汉对“子见老子”作了精彩的推想。在其《老聃传说的缘起》(TheOriginsoftheLegendofLaoDan)一文中,葛瑞汉提出了老子故事演进五阶段的构想[6](P111-124),展示了他专注于一个关键性文化叙事之历史演进所体现出来的天赋及生动的想象力。为了这项研究,葛瑞汉重新细致考查了关于孔、老关系传说的所有材料,但他对于儒家仪礼记载、道家寓言与历史性记录未作区别。葛瑞汉的目的不是要从这些材料中找出可能的真相,而是为了消除怀疑司马迁《老子传》传统的反证。他发现,“公元前4世纪以来,‘子见老子’是老子传说的核心以及唯一不变的元素”[6](P111)。由于诸多古文献提到“子见老子”,因此“子见老子”就成为传统认识的“核心”因素,以及消除司马迁叙事影响的最终障碍。葛瑞汉的重点是反驳道家创构“子见老子”故事的可能性;转而论证该故事是由儒家设计并为其所用的。以下即是作为葛瑞汉这篇长文结论的五阶段说:
第一阶段:出现了“儒家版的关于孔子向一位叫老聃的人问礼的逸事,老聃当时很可能以管理周朝档案而闻名”[6](P124)。这一逸事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流传,它可能是旧事忆述,也可能是称扬孔子谦逊好学的榜样故事。
这一观点是基于葛瑞汉通过苦心孤诣的文本分析及个人才识,以证明该会晤传说源自儒家传统而非道家历史。这种推测完全取决于儒道两家对立的背景。但汉代之前对两家进行系统区分的历史记载极为少见,甚至连“道家”这一术语也尚未出现(根据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文献,“道家”一词可能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创造)。
第二阶段:“约公元前300年,《庄子·内篇》采用与孔子同一时期的人物老聃作为‘庄学’(‘庄子主义’,Zhuangism)的代言人。”[6](P124)(10)[英]葛瑞汉:《中国哲学和哲学文献研究》,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24页。以下关于五阶段说的引文来自同一页码,注释从略。
但《庄子》书中并没有迹象表明老聃是“与孔子同一时期的人物”。“内篇”只有一处涉及老聃对孔子言论的间接评论,“外篇”和“杂篇”另有老子与孔子的七次对话。然而,所有这些对话都是明显的寓言,两个人物的形象并没有多少连贯性。孔子是《庄子》书中众多的“寓言人物”之一,他的身份或者是大师,或者是后学,有时甚至还兼具正反两种形象。孔子和老聃之间基本没有明确的关系。人们不应该试图从寓言中寻找历史真相。
第三阶段:“托名老聃的《老子》的出现,借重了其作为孔子老师的权威性。从这一点来看,老子代表了一种哲学倾向(‘老学’,‘老子主义’,Laoism)。”
葛瑞汉进一步推测说,“托名老聃”的《老子》的出现这一阶段,很可能发生在公元前240年左右。但参照公元前278年的郭店《老子》,这一时间显然过晚。葛瑞汉并且指出,《老子》之所以成为重要文本,是因为它出自老聃,而老聃则是曾教导过孔子的有声誉的人。这实际是一种无法证明的假设。
第四阶段:“老聃被认定是曾于公元前374年预言秦国崛起的周太史儋,出关西游和为关尹著书的故事同时产生。其目的是赢得秦国对《老子》的认可。”
葛瑞汉此处似乎是在表示,《老子》一书在某种意义上被归属于太史儋所作,作出如此归属的人,其意图是让秦国统治者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这个演变阶段恰与老子归隐中国西部腹地及其应关尹之请著述《老子》的故事传说相吻合。即使如此,将《老子》成功地推行到秦国似乎不太可能,因为《老子》明确提倡自然和谐与无为而治,强烈反对竞争和侵略战争。这些主张与秦国的战略和野心背道而驰。
再者,如果一个人仅仅依靠想象来解决复杂的历史问题,那么他就可能自由创作故事而无需任何证据。事实上,太史儋的言论思想与《老子》没有任何关系。葛瑞汉对孔老相会故事的关注,毕竟不同于有关《老子》作者故事的构想。人们仍然会追问,是谁首先写作《老子》的?葛瑞汉如果认为作者是太史儋,那么历史上太史儋的言行为何与《老子》的思想理念毫无关联?如果认为作者另有其人,那么太史儋为何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认可,而真正的作者却隐而不现?
第五阶段:“公元前206年之后,太史儋后人巧妙地将‘儋’改为‘聃’,以便使他们的祖先能得到汉朝的接纳而非之前秦的认可。因此有关太史儋的个人资料就成为司马迁撰写老聃传记的主要依托……由于老聃早于庄子,所以就被追溯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葛瑞汉“(太史儋的)个人资料……成为司马迁撰写老聃传记的主要依托”的推断,恐怕很难经得起推敲。它与司马迁传记原文语义不相符。果如葛瑞汉所言,司马迁又何必对此含糊其辞:“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7](P2142)老子隐居之后其身份变得神秘莫测,也就难以理解了。
我们知道,想象和推理在学术研究中是颇为重要和有效的,但它们却不是发现历史真相的唯一途径。关于任何人物或处境的推想,都必须找到确凿的证据,然后对其进行检验,最终由事实和文献加以证明。我们也清楚,学术进程和理性思维必须遵循逻辑规则。但我们必须牢记,任何复杂事件都不会沿着单一路径发展。现实世界中的事件也不会遵循着某人的逻辑推理而演进,特别是那些经过漫长历史时期形成的、涉及诸多人物和因素的事件,它们的发展演变更是如此。
马克·吐温曾说,“事实比小说更离奇,因为小说必须遵循可能性。事实则不然”(11)见http://www.twainquotes.com/Fiction.html.。马克吐温所言不虚。历史事实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而不留下清晰的演进轨迹。这里可以用一个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理学现象为例,来说明事实的复杂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指,被劫持的人质会对劫匪表现出共情(empathy)和同情(sympathy)的倾向,对劫持者抱有肯定的态度,有时甚至达到维护和认同的程度。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信息显示,大约8%的受害者会表现出这种症状,所以这种“不合逻辑”的现象可能影响事态发展和事件走向(12)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ockholm_syndrome.。因此,一般而言,尽管逻辑推理通常是有价值意义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也都是事实分析所必需的,但事实真相却不会按照逻辑推理而展开。
刘殿爵和葛瑞汉都试图在儒道两家对立的背景下解读孔老会晤。但有意思的是,刘殿爵推定是道家编造了这个故事,意在讥讽孔子[3](P130);而葛瑞汉则认为是儒家发明了这个传说,意在赞扬孔子虚心求教的谦恭有礼[6](P111-124)。对于同一个故事,两人得出的却是相反的结论,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出于猜测,而没有可资验证的实证根据。无论是刘殿爵还是葛瑞汉的解说都无法通过历史文献的检验。我们在先秦文献记录中,没有发现儒、道两大群体激烈论争的迹象,而“道家”这一术语这时也还未出现。
对于儒道两家对立这一现代假设,出土文献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反驳证据。在郭店简中,《老子》文本未见对儒家“仁”“义”的直接批判,而其中那些一般被视为早期儒家的文本,却不乏明显的道家理念。实际上,在宋代新儒学运动极力攻击佛道之前,几乎没有支持儒道两家公然对立论争的证据。
假设3:历史文本或记录要么可信,要么摒弃
许多学者对古代文本持有二元对立态度:它们必须真实可靠,否则就应弃之不用。即是说,如果一个文本按照某种特定标准被判定为不可信,那么它就不包含任何真相或价值,以至于不值得用于比较研究。这种态度如同法官对待证人:如果法官发现证人有谎言,那么证人所有的证词都应被视为不予采信的证据而予以驳回。尽管司马迁的史传难免讹误,但他显然不是故意说谎者。尽管其《老子传》也含有传闻的成分,但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从事的并非虚构工作。他对于老子的评论和描述,与《老子》一书的内容特点以及其它史籍对老子的记载大体一致。孔老相会、问礼于老子,不仅作为故事广为流传,而且作为正式的记载出现在当时的许多著述中。
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表明,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是建立在早期文献记载的基础之上的。司马迁记录了似乎难以置信的传说和传闻,因为这些都是他的亲身听闻,即使他不一定认同或有所存疑,他也希望在他那个时代做忠实的记录。例如,前文提到的那些有关老子的传说,司马迁就用“或曰”及“世莫知”这样的用语来标示。司马迁的《史记》也时或使用精彩的文学描写,这是由于在他那个时代,文学和历史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和区分(13)文学元素并非都是负面的。它们可能有助于理解和揭示历史的真相。即使是现代历史学家也会借助文学技巧。譬如,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和黄仁宇都曾运用故事叙事技巧及其文学天赋来撰写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这非但没有削弱他们作品的可信度,反而增强了他们对历史的解释力(从而使他们的作品成为畅销书)。。指出这一点并非为司马迁的失误而辩护,因为我们确实不能将他所有的记述都视为历史的真实。我们有必要参照其他时期的历史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现,来辨析司马迁《史记》各个部分的内容、风格和可信度。
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除了《史记》中的三条记述外,在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以及儒家著作《礼记》《韩诗外传》《孔子家语》《说苑》中也有相关的记录(14)《孔子家语》和《说苑》历来被认为是汉代后期的伪作。然而,1973年河北定县汉代早期墓葬出土的大批竹简,都包含有与这两部作品相同的段落。这说明这两部作品的内容来自先秦或汉初。。由于这些记录,我们很难将其完全忽略从而推定老子生活在孔子之后的某个阶段。当然,这些证据本身也不足以确定《老子》成书时间(15)在这一点上,我将略过《庄子》。如所周知,《庄子》一书虽然提到许多历史人物的名字,但它本身并不是一部历史著作。事实上,出于各种创作目的,该书对历史人物的援引自始至终都是任意的。。
我们如果仔细研读《礼记·曾子问》中有关孔子追忆老子的四段文字,将会有所启发。在二十世纪“疑古”运动的影响下,《礼记》曾被认为是可信度不高的汉代文本。但郭店简出土后,学术界逐渐认识到它包含着可靠史料,至少部分篇章保存了先秦时期的作品。在这四段文字中,孔子回顾了他与老子交流的主要话题——关于如何处理丧礼中具体问题的部分解释。这里,我们可以从对话的角度来感受一下他们会面的情境。其中一段记录是这样描述的:
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君去其国,大宰取群庙之主以从,礼也……’老聃云。”(16)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23 -524页;[英]理雅各(James Legge):《中国圣书:儒家文本》,新德里:Motilal Banarsidass出版社,1968年,第324 -325页。《礼记》英文依托理雅各本,并稍作改动。
另一段则写道:
曾子问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老聃)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吾闻诸老聃云。”(17)孙希旦:《礼记集解》,第545 -546页;[英]理雅各(James Legge):《中国圣书:儒家文本》,第338 -339页。
这两段文字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另外两段文字尽管涉及的是不同的礼仪细节,但叙事风格与此非常相似。所有这些引文都不禁让人联想到老子向孔子讲解丧礼的情景。我们从中看不出任何褒贬的迹象,也察觉不到记录者流露出的好恶倾向。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解读这些材料,我们就不能认同孔老相会仅仅是一个意在褒扬或贬抑某人而编造出来的故事。有意思且耐人寻味的是,《老子》中只有一处从肯定意义上提及礼,而且仅仅是对丧礼而言的(“战胜以丧礼处之”)[8](P155)。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显然,儒家文献中保存下来的这些有关丧礼情况及具体仪节的记载,与《庄子》中的孔老对话完全不同。《庄子》“外篇”中孔老两人的七次对话,是将孔子描述为主角或配角的众多寓言故事的组成部分。孔子在该书的不同章节中,被塑造为宣扬儒家或道家思想的最佳代言人。尽管在这些故事中,老子比孔子更胜一筹,但两人的对话是个人之间的问题交流、忠告、批评以及教导启发,而不是对立或冲突。
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一一考察《吕氏春秋》《说苑》《韩诗外传》以及《孔子家语》等著作中的相关事例。但概而言之,这些文献对孔老相会的记述至少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以司马迁《史记》的传记为代表,既记载历史,也介绍传说;第二种以《礼记·曾子问》的记录为代表,基本上是对某些礼仪仪节进行交流的直接忆述;第三种以《庄子》寓言为代表,基本与历史事实无关,尽管有时它们假托的是孔子与弟子颜回、子路等真实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历史文献纷繁复杂,我们不能将其一概肯定或否定。分析和鉴别对于从文献资料中充分获取历史信息是必要和有效的。
假设4:样本可作为综合判断的证据
葛瑞汉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庄子》文本的研究,他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庄子》“内篇”的作者极有可能就是庄子本人。这对研究《庄子》以及其他文本的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9](P3-4)。除了优雅的语言和独到的见解外,葛瑞汉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对于《庄子》内篇、“庄子学派”作品(23—27篇,32篇)以及该书其他篇章中的语言材料所做的详尽细致的比较工作。这一比较依据的是其在“内篇”中所发现的特殊的习语、哲学术语、人物姓名、一般术语以及具有特殊语法特征的短语。我相信其见解的说服力依赖于语言资料的整全性。葛瑞汉与我在《庄子》研究方面的不谋而合,说明了语言分析所能够达到的客观性,尽管我的比较和统计主要聚焦于三个哲学复合词(道德、性命、精神)以及《庄子》全书中具有明显相似语言特征的所有段落上(18)刘笑敢:《庄子篇章分类》,安阿伯: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94年;刘笑敢主编:《道家哲学研究伴侣》,纽约和伦敦:斯普林格出版社,2015年,第129 -157页。。有学者声称我的研究是对葛瑞汉的挑战,但我要指出的是,这不是也不可能是我的初衷,因为我研究《庄子》的时候,尚不知其人。
至于我们之间的不同,我同意哈罗德·罗斯(Harold D. Roth)的看法:
葛瑞汉的《庄子》研究最具原创性也最具争议性之处,或许是他对文本的重构。其重构包括:将他认为原本完整但由于文本损坏以及四世纪《庄子》注家郭象大幅度的改编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段落拼接回复到原处。[9](P186)
之所以说这是葛瑞汉最具争议性且不如他关于《庄子》内篇论证那样具有说服力,原因有三点:首先,《庄子》内、外、杂篇的划分是一种历史遗存。因此,现代语言学分析的结论仅仅是对该书传统编排总体可靠性的验证。其次,葛瑞汉用来比较文本不同部分的语言材料包括许多习语、术语和人名,这些习语、术语和人名也用于文本的所有部分。第三,不同篇章群【或篇章组,或篇章组合?】之间语言比较的结果要么是同,要么是异,这是确定的、清楚的。因此,这种比较的结果是客观的,不同解释的空间很小。
然而,葛瑞汉试图重新编排《庄子》,尤其是将外篇和杂篇的段落移“回”内篇,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方案。首先,他的重组缺少客观或历史的参照及依据。第二,他根据个人观察来判断某些段落的“相似性”,而没有确立明晰的“同”与“不同”的界线,因此,其他学者可能不会认同这种相似性。第三,这些主题和用语相似性背后的源起可能是多方面的:它们可能是弟子效仿的结果,或者是由于后来作者与先前作者兴趣巧合所致,所以它们并不一定能够表明其作者就是庄子。第四,《庄子》不是一部包含单一主题甚或风格一以贯之的散文集。它的主体部分是传说(神话)、寓言、论辩、叙事、散文、故事的汇集,因此,它没有结构脉络可以让我们据以找到缺口将遗失部分复原。毕竟,语言相似和主题相同的个例本身,不能成为严谨的文本分析的依据:它们不能充分证明总体的文本结构与某个作者的关联。样本,无论多么相似,都不足以用来判定整个章节的作者和结构。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葛瑞汉试图从《庄子》杂篇移出四个段落,以重构(内篇)第三篇引言段的尝试[6](P296-297)。这四个段落是,A:第二十五篇(51—54),B:第二十四篇(105—111),C:第三十二篇(50—52),以及D:第二十四篇(103—105)(19)[英]葛瑞汉:《中国哲学和哲学文献研究》,第 296 -301页。括号中的数字,是《庄子引得》(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特刊第二十号《庄子引得》 )中文文本标注的行位数。。最终葛瑞汉放弃了段落A的移动,因为他承认,“我对此没有多少把握”[9](P18)。他从第二十四篇选取了段落B和段落D进行重构,但是将其拆分并换位放置在第三十二篇段落C的前后(20)[英]葛瑞汉:《中国哲学和哲学文献研究》,第296页;葛瑞汉译:《庄子内篇》,印第安纳波利斯:哈克特出版社,2001年,第62 -63页。。我认为,在试图复原初始文本的过程中,葛瑞汉这种重编掺杂了太多的揣测,以至于大大偏离了原初文本。
葛瑞汉为他的重组而列举的“作为依据的相似性”(21)本段中文语句的英译及其解释,包括括号的使用,均出自葛瑞汉之手。主要有:(一)第三篇和第二十四篇的“有涯”和“无涯”;(二)第三篇的“殆”和第二十四篇的“殆”;(三)第二十四篇的“解”和第三篇的“解”;(四)第二十四篇的“恃其所不知”和第三十二篇的“恃其所见”;(五)第二十四篇的“神”“目”呼应,第三十二篇的“神”“明”(22)葛瑞汉将“神”“目”与“神”“明”分别解释为“目胜于神”(daemon preferred to eye)与“目力胜于神”(daemon preferred to eyesight)。这种断章取义是难以理解的。呼应[9](P18)。
以这五组语言相似性的比照来证明相关段落是单一作者的作品,证据是薄弱的。四个例子都是在各种语境中经常使用的常见词。第三个例子中的“解”字,在第三篇和第二十四篇中用法和涵义大相径庭。在第四个例子中,两个短语分别表示肯定和否定,且都与第三篇无关。因此,这些语言材料远不足以支持文本的重组。而且,即使从道理上说,表面的相似性也同样不足以断定这些段落是由同一作者所写,或者说原本出自同一篇较早的文章。此即我所谓的“样本论证的缺陷”[10](P36-40)。
然而,样本论证又是常用的,它在界定明确且属同一类型的资料范围内是有效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古代中国文本的界限类型划分是不很明确的,因此,认为零散的个例可以证明一个整体性结论或者否定某个具体判断的假定,是非常冒险的。它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着缺陷。样本通常只出现在少数情况下,它们无法得到严格的检验,因此援引它们而进行的推理从逻辑上讲是无效的。
例如,自清代以来,学者们根据某些术语和短语,认为《庄子》部分篇章写定于汉初。这一认识被广为接受,其支持者除了葛瑞汉之外也包括我的导师张岱年先生(1909—2004)。然而,很少有支撑性的样本和证据在严格的检视之下站得住脚。代表性的实例有“六经”“十二经”“三皇五帝”“素王”“宰相”“上仙”“白云帝乡”和“孔子西藏书于周室”。但是,即使经过严谨的语言学研究,也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这些术语和短语可以被确切地认定在汉代。而且,即便有学者指出这些术语确实在某些汉代文本中出现过,也仍然没有根据来证明它们不可能在更早时候被偶尔使用过。一些学者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假设:某个历史上首次被使用的词语或词组也应出现在同时代的其他许多文本中,否则,它就是伪造和后起的,是在它被广为接受的时代才出现的。
更为重要的是,全面的语言学考察显示,《庄子》中有涉及十四篇的三十段文字被《吕氏春秋》和《韩非子》所引用。这意味着《庄子》三十三篇有42%的篇目被先秦时期的作品引用过。这有力地说明了该书在秦朝之前就已经开始流传。很少有书籍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引用。有意思的是,被引用某些段落的这十四篇中,有三篇出自《内》七篇,有六篇出自《外》十五篇,有五篇出自《杂》十一篇。巧合的是,3:6:5接近于内、外、杂篇的7:15:11,换言之,被引用篇数与《庄子》三部分各自的总篇数在分布上的比例是大体吻合的[11](P50-61)。这是基于对所有语言材料的综合考察,而非仅仅依据某些样本。
参照江陵、阜阳出土的竹简本《庄子》,李学勤认为,《庄子》内篇为庄子自著,外篇和杂篇可能也是先秦时期的作品[12](P126-131)。竹简本《庄子》并非全本,因此其本身不能有力证明《庄子》的年代。但是,如果我们不排斥关于《庄子》的所有文献传统和现代研究,包括葛瑞汉的工作,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学勤的结论是正确的。这里,考古发现再次证明,样本论证是一种有风险且极易出错的方法。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例子来说明样本论证的局限。《老子》六十三章有言曰“报怨以德”,这是先秦文本一种特有的说法。有意思的是,《论语》中有一段直接反驳该句意的对话: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8](P42)
有人向孔子请教“以德报怨”,这说明“以德报怨”是孔子尚未讨论过的通行观念。在现存文本中,只有《老子》提倡“报怨以德”,根据我们之前所批评的文本分析的一般方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老子》引发了孔子的评论,这或许可以进一步作为《老子》作者与孔子是同一时代人的证据。但这种论证是有缺陷的。首先,支持性的例子极少;其次,我们无法排除当时或者更早的其他人也有同样观念的可能性,尽管承载这种观念的文本我们可能已经看不到了。一般而言,孤立的样本不足以支撑涉及整部作品的总体结论。
本文的反思主要依托的是考古资料。遗憾的是,葛瑞汉生前无从知晓《老子》竹简本乃至中国境内众多古代文本的发现(23)郭店楚简的整理本出版于1998年,那时葛瑞汉已经去世。。即便如此,葛瑞汉还是期待相关研究能够向前推进。他曾表示:“希望未来学界能够找到一种探讨他[庄子]的更为精到的方法。”[6](P284)笔者也希望这种反思能有助于寻找“一种更为精到的方法”,不仅可用于探讨《庄子》,而且还可以增进其他许多依托文本分析领域的研究(24)本研究得到了北京大学中国诠释学史项目(12&ZD109)部分资助。我也非常感谢克莱尔蒙特神学院特别是校长Jeffrey Kuan教授,2015年春他曾邀请我去讲学一个学期,在那里我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并完成了本文的初稿。。当然,以上反思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学术研究中不可以或不应该有任何的假设。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假设需要检验,特别是在能够获得新的知识和参照的情况下,譬如考古学家的发现。当然笔者也难免会有一些假设,这些假设本人已反复检验,并且愿意接受同仁进一步的审查,如果依据不足的话,笔者将予以修正或放弃。
(本文原为英文,中译本已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