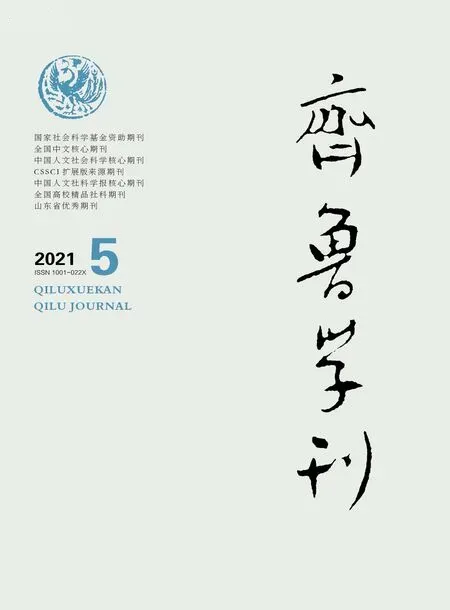狂妄的“朝圣者”
——关于萧军在延安的几个问题
宋剑华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萧军之所以能够蜚声文坛,并不是因为《八月的乡村》写得有多么好,而是因为鲁迅为《八月的乡村》所作的那篇“序”,赋予了他以超乎想象的莫大荣誉。从此以后,萧军虽然再也没有写出超越《八月的乡村》的文学作品,但对于他本人来说,一部《八月的乡村》就足够了,因为鲁迅已经“钦点”过,这是一部“显示着中国的一份或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的“好书”[1](第6卷,P296),而萧军则更是视其为一部“非凡的意义伟大的东西”[2](第18卷,P234),用他自己那毫不谦虚的话来说:“以《八月的乡村》给中国文坛和时代开了一个新起点,以我的艺术给了中国文坛的提高,使鲁迅先生见得后继者的欢喜。国际(尤其日本)因我的作品而使中国文艺提高了国际地位……《八月的乡村》引激了‘七七’抗战。”[2](第18卷,P526-527)他甚至还夸张地认为:“还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够这样密切地和现实配合像冲锋号那般的关系……对于眼前的小成绩我是鄙视的,虽然仅是这一点已不是任何人所能有的了。”[2](第18卷,P801)正是由于鲁迅对《八月的乡村》的推崇和赞誉,过度自我膨胀的萧军信心满满地把自己视为是“鲁迅精神”的传承人,而学界也默认他继承了鲁迅的“精神遗产和‘鲁迅大弟子’所带来的声誉和地位”[3]。但问题是:如果萧军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又一面“旗子”,那么,他为什么不在国统区同郭沫若、茅盾等大作家一争高下,而非要跋山涉水到偏僻的延安去发展自己的文学事业呢?为了解开这个历史谜团,我想结合《萧军日记》及其它历史资料,来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
萧军为什么选择到延安这一问题,曾使我倍感困扰、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萧军是一个我行我素、天马行空式的自由主义者,他那种唯我与自负、傲慢又狂妄的张扬个性,完全不可能融入延安的集体主义文艺群体,可他却偏偏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悖论逻辑呢?
长期以来,学界往往以一种教条思维,将萧军到延安的动机机械地等同于一般文艺青年的向往革命,认为他去延安的目的,就是要跟着共产党人干革命,进而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比如有人就曾这样说:“水流千转归大海,经历了千波万折,他终于正式投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了。这是他一生的重大抉择,他知道只有延安才是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所在。”[4](P144)但我个人并不认同这种说法,综观那厚厚的3本《萧军日记》,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他到延安显然是另有个人打算的,只不过是研究者自己没有发现而已。
鲁迅去世以后,失去了“保护伞”的萧军,因缺少作品的支撑而又唯我独尊,几乎把文坛上的人物都给得罪完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统计着我的仇人,几乎成了九面楚歌了:1,郭沫若系统。2,田汉系统。3,阳翰笙系统。4,国民党系统。5,成仿吾系统。6,周扬系统。7,萧三系统。8,山西阎锡山系统。9,茅盾系统。10,……好!我倒要看一看他们究竟能把我怎么样。”[2](第18卷,P360)既然“十面楚歌”已有“九面埋伏”,那么就只剩下了最后一条路可供选择,即只有到延安并借助于这一令知识分子向往的革命圣地,去重塑其“鲁迅大弟子”的光辉形象。对此,钱理群先生有一种说法:萧军之所以会选择到延安,是“因为不堪忍受国民党专制统治”,并因其对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有着特殊的“感情”,而将延安作为他“寻找精神的歇憩地”[5]。的确,萧军自己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哪里有民主自由我就在哪里,哪里没有我就走。”[2](第19卷,P677)不过,钱先生所要表达的意思,还是与萧军本人大相庭径的,因为他在诠释萧军的直率性格时,又人为地注入了一种暗示性因素,即:由于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萧军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如果不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有所“认同”,他也就不会萌生去延安的念头。另外,还有一种观点更是令人称奇,认为:萧军是冲着加入共产党才来到延安的,尽管萧军在延安经历了种种“痛苦”与“磨难”,没有实现他“入党”的迫切愿望,但是经过他孜孜不倦地思想追求,终于在1948年8月“被中央批准入党”;这位研究者进而还抱怨说:“1980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批准,做出萧军问题的复查结论,推翻了几十年来强加在萧军头上的种种罪名,但不知何因,萧军的党籍没有恢复。”[6]只要对萧军在延安的经历有所了解就不难判断,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有违历史的无稽之谈。
众所周知,萧军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他一旦选择了某种信仰,便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尤其是当萧军决心“要固执,执拗——静静地走自己决定的路”[2](第18卷,P13)的时候,他是绝不会违背自己的主观意志的。我仔细地浏览了《萧军日记》,发现萧军无论是来延安以前,还是到了延安以后,他一直都同共产党人的思想信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从未想过要加入党组织。这一点,萧军在“日记”中写得清清楚楚:
1937年8月4日:不要为偶发的一些现象耽误了自己既定的目标和方针……要革命,用自己的武器——文学——向根本的方向迈进。永久和政治保持平等的关系。[2](第18卷,P30-31)
1939年10月3日:放弃个人的自由,完全为别人而生活,在我是不可能。[2](第18卷,P114)
1940年10月8日:我爱我应该有的自由,我不愿意把这仅有的一点小自由也捐给了党
1941年7月28日:我不应该披起太硬的外壳,把自己包围起来啊!为了要了解,要改变这生活,我甚至想到加入共产党……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有任何锁链,那会毁灭了我自由突击的天才,蒙蔽了自己,为了一时政治目的会把我庸俗和主观化了。[2](第18卷,P488)
1942年6月22日:为了艺术的前途计,他们就是把死说活了,我也决不入党。[2](第18卷,P662)
不难理解,萧军到延安的真实目的,不可能是为了“革命”而去牺牲他所追求的“个人的自由”。萧军选择不加入党组织,与他本人的政治觉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他我行我素、桀骜不驯的性格有关。
应该指出,萧军虽然不愿入党,但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败,对于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抱有强烈的好感,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比如他在成都时,听到有人说共产党和八路军不抗日,便立刻拍案而起予以怒斥。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把“好感”理解为“信任”,两者在概念上的差异性是不能混淆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非常奇特的怪异现象:一生都声称要同共产党人保持距离的萧军,竟然曾有过两次“入党”的要求,学界认为这是萧军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而我认为萧军两次要求“入党”都不过是权宜之计。
萧军第一次要求“入党”,发生在1944年3月,当时萧军正因“王实味事件”受到延安文艺界的一致批判,他以要求“入党”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其实是为了从政治上保护自己。对萧军这次要求入党的背景,可以作更深入的历史考量。1943年10月29日,萧军因为“吃饭”问题同招待所的蔡主任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蔡主任批评萧军“搞特殊化”。结果心情本来就不好的萧军,竟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在故意使他难堪,一气之下立刻给王鹤寿和林伯渠写信,表示“实在不想再住机关,吃公家粮食”[2](第19卷,P248),并要求下乡去当农民,自己种地,自食其力。但仅仅过去了3个多月,过惯了舒适生活的萧军就顶不住了,他又连忙放下傲慢狂妄的文人架子,给林伯渠写信向“公家”借粮,并要求尽快回到延安城:“如果现在党或政府方面有需要我回去工作的必要,或为了任何原因愿意我回去,我是并不固执的,是可以回去的。”[2](第19卷,P305)过了不久,胡乔木到乡下检查工作,顺便看看萧军的生活情况。1944年3月3日的萧军“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下午出乎意外,乔木、王丕年和另外一个熟悉而不知名字的女人到我处来。我竟坦白地和他们谈了我回延安的目的——准备入党——他们当然是被一种不相信的感情惊异着。
我大致为他们解说了这过程:1,我自从到乡下以后,对于革命的真理又多了一面认识。2,中国革命需要更迫切的是什么。3,这是我应该入党的时机。[2](第19卷,P335-336)
在与胡乔木的交谈中,萧军表示:自己从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虽然到延安后感情上有“很多不舒服”,但理性上认同党的“给与贫穷人民土地、生活”的方针政策。与胡乔木会面之后,萧军很快回到延安城。对于萧军而言,他知道如果不说他要“入党”,胡乔木就不会管他回城的事情;对于胡乔木而言,虽然他不太相信萧军的话,但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不出所料,胡乔木等人的“惊异”是有道理的,回到延安城以后,萧军就再也不提“入党”之事了。
萧军第二次要求“入党”,是1948年在东北,用的是与延安“入党”同样的套路。当时,萧军因“文化报事件”正在被东北局“批判”和“封杀”,他预感到情况不妙,故赶紧打报告给东北局,说他准备加入中国共产党。据萧军1948年8月12日“日记”记载:
他(凯丰)和我谈,接到我那入党信后,即与东北局交换了意见,他们是同意的,接着打电报去中央,前几天才回电,据说因我思想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很浓厚,本不合党底要求,但因我一直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决定接受入党……[2](第20卷,P284)
准备接受萧军入党后,凯丰要他自己去找入党介绍人,萧军本来想找舒群,可是舒群却让他去找丁玲和凯丰,萧军发现他们都在兜圈子,没有一个人态度积极,所以干脆写了一封“告别书”,目的就是要“正式”表明自己“已放弃了做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打算”[2](第20卷,P371)。其实,东北局领导非常了解萧军的延安经历,故没有上他的当。
可以看到,萧军两次“入党”的时机都选得非常巧妙。萧军在延安自视为文化人的“保护者”,但实际上,以他一贯的傲慢狂妄的做派和为人,他在延安文化人中间是十分孤立的,他曾报怨自己身边没有朋友,感觉能做朋友的几个人也随时都可能变成敌人。因此,当受到批判和“封杀”的时候,他自感到孤立无援,要求“入党”而寻求保护,既是无奈之举,也是明智的策略。实际上,萧军刚到延安时并没有打算常住,只是想看看情况再说,以便给自己留条后路。从他的“日记”看来,他到延安后只待了几个月,就萌生了要离开的强烈念头,但因种种原因没有付诸行动。1940年9月8日,萧军曾决定去见毛泽东,一是向毛泽东“告别”,二是表明自己愿意“继续做共产党的友人”[2](第18卷,P298)。1941年7月,萧军似乎下定决心要离开延安,他7月15日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面谈,算是离开延安的“告别礼”。7月18日毛泽东约见萧军,两人相谈甚欢,萧军没有提离开延安的事。之后一段时间,毛泽东与萧军多次通信、面谈,萧军很受感动,他一再要离开延安与毛泽东“告别”,但却迟迟没有行动。实际上,与毛泽东的交往,使萧军在延安文化人群体中树立了“威信”,也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他与延安文坛的紧张关系,从而使他从“十面楚歌”而又“无地彷徨”的危机状态中有所解脱,这应该是萧军在离开延安问题上犹豫不决的重要原因。
二
萧军到延安既然不是为了参加“革命”,难道他仅仅是想要借助延安文坛去为自己扬名吗?我个人认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目的;他真正的野心,是要去“影响”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文化政策。这听起来有些言过其实,但读罢萧军“日记”就不难发现,他虽然在人格上狂妄自大,但在思想上却十分幼稚。
萧军到达延安以后,有一次曾在“日记”中写道:“我懂得共产党也懂得共产党人,但是它们并不懂得我啊!我是一个作家,我只有含着泪帮助它们生长。”[2](第18卷,P292)萧军为什么要“含着泪”去帮助共产党人?从“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出,萧军读过苏联小说《铁流》《毁灭》,他以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战士,个个都应像莱奋生、郭如鹤那样,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养,给人一种顶天立地的英雄印象。然而,来到延安以后,他发现这里的一切都与他的预期相去甚远,这令他感到有些沮丧。他在1940年9月7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今天下午四时许,我去统战部合作社买东西,回来路经山坡下,山上警卫营的兵士向下扔石头,我质问他们不肯承认,反下来一个四川口音的兵和我纠缠不清,不肯放我走,我要去见他们长官,他也不许见,我要见毛主席他说我不配,我要见洛甫他不准我上去,我要和他打架他也不肯,这完全是一种无赖的行径。”[2](第18卷,P297)还有一次他去乡政府办事,工作人员的办事风格有些粗鲁,于是他便认为乡上的干部“几乎全是流氓成分,鬼鬼祟祟,全无正气……吃着老百姓的公粮,而不给老百姓办事——这是可耻的啊”[2](第19卷,P330-331)。仅仅因为几个顽皮的八路军小战士,和几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乡村干部,萧军就对中国共产党人丧失了信心,认为:“这是个充满封建性的党,很少无产阶级气氛,它必须要进步,改造,否则就有要替代它的。”[2](第19卷,P101)这也未免太夸张了吧?中国现代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农民当然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的思想与行为难以一下子就摆脱农民的落后习气,这只能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地去加以克服。但萧军却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准要远高于延安的共产党人,因此他才会居高临下地评论道:“所谓科学的预见,科学的方法,共产主义的人生观、道德观……至少在目前的共产党还谈不到。他们还没有脱离农民的原始的自发性底存在。所好的,是它们在进步”[2](第19卷,P74)。作为鲁迅的“大弟子”,萧军似乎忘记了鲁迅先生的谆谆教诲:“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1](第10卷,P372)他只是以文学家的艺术想象,去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战士,当然会不无遗憾地发现发展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在“作风”“气魄”上的“农民性与小资产阶级性”的杂质。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要去除这些杂质“决不是短时期的事,恐怕还要经过内部峻烈的斗争”,同时还表示“我只有忍耐地等待或帮助他们生长罢”[2](第20卷,P445)。
萧军将鲁迅视为自己的“精神之父”,同时也在人格上将鲁迅视为完人,他把鲁迅列为与马克思、列宁、史(斯)大林一样的人物,并且自觉不自觉地以鲁迅为标准衡量延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领导者,结果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与对鲁迅的精神崇拜不同,萧军对毛泽东的看法很复杂:一方面,他在同毛泽东的通信和交谈中,感到他是一个“人性充足的人”“诚朴,人性纯厚,客观”[2](第18卷,P471-472);一方面,他又认为毛泽东不是“哲人”“学者”,是“单纯的政治家”[2](第18卷,P537),是“一个经验性的天才” [2](第19卷,P139),但“他自己对一切事物的思想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2](第19卷,P525)。这样比较之下,萧军想当然地认为毛泽东与马、列、史(斯)以及鲁迅之间还有差距,他因此而有意无意地试图以他所理解的“鲁迅精神”去“影响”和“感化”毛泽东。他不仅向毛泽东推荐《鲁迅全集》,而且每一次与毛泽东谈到鲁迅,他都要“像一个使徒那样传布先生的影响”[2](第18卷,P567),其真正目的是希望通过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巨大影响力,使“每个在延安在边区的党人和非党人,能够懂得鲁迅,继承鲁迅的精神”[2](第11卷,P429)。他甚至声称“将要并鲁迅和列宁为一人”[2](第18卷,P775)。其在思想上的幼稚和人格上的狂妄由此可见一斑。
萧军自诩为文学“天才”,但众所周知,他的文学天赋和成就,既比不上丁玲和艾青等人,也比不上萧红,对此他本人是非常清楚的,但这并不影响他的自负与清高。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除了一部不太成熟的《八月的乡村》,萧军的确再也拿不出别的像样的作品向人们去炫耀。因而,萧军聪明地打出了“鲁迅大弟子”这张牌,先是把同时代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排除在鲁迅的思想体系之外,认为“和鲁迅先生接近的人,还只有我还在这样健在着,战斗着……其余的大部飘萧了”[2](第18卷,P546),只剩下他一个合法的“继承人”,势必会使他与鲁迅之间形成这样一种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即:“若说鲁迅是中国文学的根干,我则应该是那花与果实,而且我也应该做这花和果实。”[2](第18卷,P216)他宣称:“在十年之内,我要使中国的文艺在世界上奠定他的光辉地位。”[2](第18卷,P217)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誓说:“我要在世界上做最好的作家!”[2](第18卷,P631)萧军之所以敢如此夸口,那是因为:“我自己估量自己:无论在生活经验上,文化艺术修养上,文学秉赋才能上,写作经验上,所得的成绩上,身体条件上——当然比起中国同时代的‘作家’们那全是要优越。”[2](第20卷,P532)故他根本就不去考虑自身的客观条件,自己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宏大计划:“我的任务:不独要使中国新文艺的堡垒建立的坚牢,而且要使世界各国受到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不独现在,而且要影响人类的将来。”[2](第18卷,P233)
萧军不仅在文学上信心满满,同时也在思想上跃跃欲试,比如他说:“我应该像成吉思罕或拿破仑那样,虽然以剑征服世界我无望了!但是我却要以笔去征服这世界!至少是中国。”[2](第18卷,P314)他觉得自己已经具备了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叱咤风云的巨大能力,用他那毫不客气的话来说就是:
我是新生的力量底代表者,中国鲁迅这转轴人底承继者,从对国家民族的意义上讲,没有作家能够和我相比的。我不独是这民族解放第一个点起鲜明火把的人,而且还是个战略指导者,我不愿在这里谦卑,我是这古老的伟大的民族一朵伟大的鲜花……我具备着马克思、列宁、鲁迅、托尔斯泰这些伟大人物的某部分品质,我有着一种释迦牟尼,耶稣,摩西,穆罕默德等人物对人类负责的精神。我将要慢慢完成这品质和精神。[2](第18卷,P568-569)
萧军这段话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在延安时期特殊的社会格局中,由于鲁迅的过早去世,造成了文化领导权的“空白”与“缺失”,应该由谁继承“鲁迅精神”,扛起“文化”这面大旗呢?恐怕只有他这位“鲁迅大弟子”最为合适。1946年3月底,萧军途经张家口去东北时,曾在张家口做过一次讲座,他发现:“我讲《鲁迅》时,多少蒙古人全来听了,他们称赞我,同时对于鲁迅引起了很大的兴味,那些青年们不知道毛泽东,朱德,却知道我和丁玲,他们有百分之四十几读过丁玲的《母亲》,百分之五十几读过《八月的乡村》。”[2](第19卷,P748)这一“发现”令萧军信心倍增,所以,他1948年到了东北以后,以为自己在文化思想上的影响力是超过一般的革命领导者的。因此,他与当地领导阶层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文化思想上领导权问题。他们是不甘心属于我,但又无力和我竞争,于是就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方法”[2](第20卷,P209)。萧军如此的狂妄而且偏执,其与延安文坛格格不入,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
萧军的傲慢与狂妄,说穿了就是他“新英雄主义”价值观的一种表现。萧军所倡导的“新英雄主义”,是指以“鲁迅精神”为主体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意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战斗即生活!这是我新英雄主义基本的信念。”[2](第18卷,P771)他的解释是:“新英雄主义——在中国以至世界是新一代人类以至将来人类所必须。它是马克思主义更新阶段的发展,它可以提取人类的精英,作为先锋队——这是此后阶级战斗中,战斗后,必然的产物。”[2](第19卷,P196-197)从“新英雄主义”这一认知基点出发,我认为萧军在王实味问题上的自我表现,绝非是“主持公道”或“仗义执言”那么简单,他是在借题发挥以彰显其“战斗”意志,进而向世人宣示他“卓尔不群”的独立人格。
萧军并不认识王实味,在延安也没有同他有过交往,他为什么要在王实味的问题上,固执地要引火烧身呢?直到读完了萧军“日记”,我才明白了这其中的奥秘。萧军到延安以后,由于太过傲慢与狂妄,延安文人对他都非常反感,甚至还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和蔑视态度。这无疑使想要称霸延安文坛的萧军,既感到恼火,又感到了危机。在他的“日记”中,包括胡乔木、丁玲、艾青、刘白羽等知名的文人都被他骂过。他不仅自己在心里“骂”这些人,而且还把这些人的“斑斑劣迹”写信向毛泽东作了反映。恰好毛泽东正因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问题,准备要召集一次文艺座谈会,于是他便让萧军帮他收集一些资料,以供他写“讲话”稿参考。从萧军“日记”中那些暗示性的文字来看,他向毛泽东提供的“反面”材料一定不会少,因为他期待着借助毛泽东在延安的崇高威望,去整治一下他在心里“骂”过的那些“仇人”。1942年5月2号,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第一次集会,萧军竟然认为这次座谈会的召开是由于他的“工作”而引发的,他异常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一时半去杨家岭办公厅参加由毛泽东,凯丰等召集的文艺座谈会。这还是延安从没有过的举动,这也是自己这二年来,间接直接工作出来的结果,我可以如此说。”[2](第18卷,P614)萧军本以为会议下面的议程,应该是他向毛泽东所反映的批判宗派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可是出乎他的意料,座谈会刚一结束,矛头却直接转向了对王实味的批判,这无疑使他大失所望。尤其当他看到周扬、陈荒煤、丁玲、艾青、何其芳等人的“恶劣”表演时,就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立刻站出来替王实味说话,提出王实味“主观上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何其芳等人“对于王实味批评的态度是不对的”[2](第18卷,P632)。他的发言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6月3日,周扬代表文艺界党组织找他谈话,不仅批评了他的“新英雄主义”思想,同时还质问他为什么不同共产党人站在一起。但萧军并没有理会周扬的口头警告,在6月4日的王实味批判会上,萧军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导致会场一度出现混乱。会后,中央研究院等8个团体及108人联名向萧军发出“抗议书”,希望他“好好反省一下”。6月7日,柯仲平、李又然等人都来劝萧军做出让步,但仍旧遭到了他的强硬拒绝。
萧军本来与“王实味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对于王实味这个人还十分反感。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人底‘质地’我不喜欢,浮狂而还自私,名士气太重,他的一些习气和气氛是我所难容的,——他‘不正’,邪气,鬼气很深”[2](第18卷,P808)。王实味曾主动找过萧军3次,而每一次萧军都对他提出过批评,特别是当王实味无端指责毛泽东等人的“享乐主义”时,萧军还马上给予反驳:“根据所能取所值这原则,毛泽东他们也应该要生活得好些……为了工作。并且据我所知,他们底生活并不比我们好过多少,那是朴素的,简单的。因为我和他们有过交往,也偶尔吃过饭。”[2](第18卷,P803)另外,萧军对于批判王实味,从内心深处是表示理解的,比如他说:“内部进行自我批评,外部宣传自己的功绩,现在的共产党的政策是对了。”[2](第18卷,P711-712)对于王实味的顽固不化,萧军也感到十分地担心:“我推测:如果将来战势紧张,王实味仍顽固不化,他们也许杀了他祭旗。”[2](第19卷,P169)由此可见,萧军在“王实味事件”中唱反调,无非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借机发泄。党组织对萧军是理解和爱护的,据萧军“日记”记载,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领导人陈云曾找萧军谈过话,他向萧军解释说:在批判王实味的群众大会上,有些人的发言可能会伤及到萧军个人的“面子”,希望他不要太介意。但萧军却对组织上的宽容和关怀不以为然,他在给陈云的信中固执地说:“对于此次‘不幸’事件,我底看法并不那样简单,它不是个人‘面子’问题,而是党与群众关系问题,党与他的朋友关系问题……也是我对共产党底观点和态度重新决定的问题。”[2](第18卷,P756)
萧军的不配合态度,已使他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膨胀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可他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后,毛泽东也不再纵容萧军,他表示:“萧军既然不顾大局,应开始对他抱冷淡态度,使其感到孤立,或有悔悟的希望。”[7]不幸的是,萧军不仅没有“悔悟”,却在相反的道路上执迷不悟、越走越远。他本以为可以借助延安文坛成就自己的一番大业,最终却因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成为了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萧军的人生悲剧,归根结底是他的人格悲剧。对于这一点,萧军晚年也是承认的,他说:“我青年时期,只知自己,不知有人,于人于事拙于处理方式方法,树敌颇多,伤人太重,因此招到任何攻击和打击,绝无怨尤之情,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蒺藜得蒺藜’是也。”[2](第16卷,P161)萧军明白是明白了,只是有点明白得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