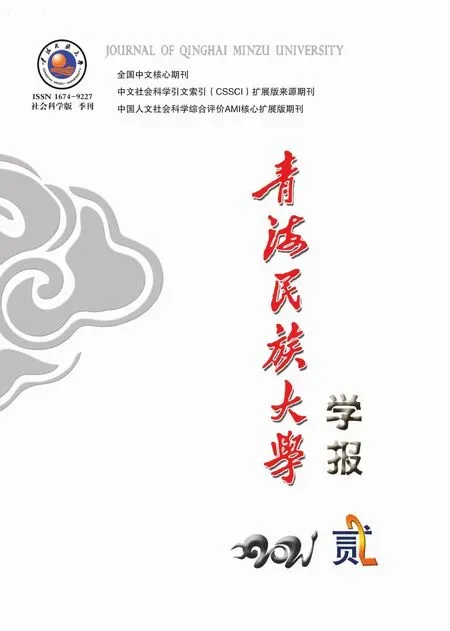中国民间生活中的防疫观念与抗病避灾的文化实践
邓 苗
(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引 言
这段时间,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肺炎疫情成为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一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场疫情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民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了重大而无法挽回的损失,包括政府、社区/村落、相关企业、非政府组织(NGO)、学术界和广大民众都深度参与疫情防控之中。对于疫情防控,以现代传染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理论为基础,政府施行全国动员,采取了许多严格的措施,从整体上来看,这些措施固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其对于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1]中国是一个瘟疫多发的国家,历史上发生多次重大瘟疫事件,[2]不论在医学的治疗上,还是在疫情的防控中,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3]这些防疫的经验、智慧与知识和民众的日常生活相结合,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行为方式而被世世代代地传承与应用。因此,从民间生活中的防疫观念、抗病避灾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经验出发,结合历史上应对瘟疫流行的举措和有关的中医治瘟知识,对中国民众的防疫抗疫避疫经验与知识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对于当前的新冠疫情防控大有裨益。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将长期以来在民间生活中传承下来的医药知识和养生知识运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自然的生活习惯和行为逻辑。这些知识从整体上来说由内而外形成了一个由个体、居所和社区社会所构成的三层防疫知识体系,这三层知识体系层层扩展又相互联系,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相结合,有效地保卫着民众的身体健康。
一、个体自身的洁净观念与防疫防病的行为习惯
保持个体自身的身体卫生并遵循一种健康的作息习惯是防止疫病的最基本内容,个体只有首先做好自身的防护,才能在根本上避免疾病和瘟疫的侵袭。
(一)作为守护之所的身体:个体的日常盥洗和沐浴
防疫防病首先要从个体自己的身体做起,因此,身体的清洁是最先需要注意的地方,虽然这方面跟个体自身的卫生观念直接联系在一起,但是,普通民众对此还是有一些共同的认知。日常盥洗主要包括晨昏洗手、洗脸和洗脚三个方面。
“洗手”作为一种生活习惯,其价值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保持勤洗手、仔细洗的习惯,特别是饭前便后洗手,对于抑制细菌、保持卫生具有重要的意义。民间有谚语曰:“饭前便后洗净手,细菌虫卵难进口。”古代文献中,人们用很多语汇来描述这一现象,包括“洗手”“澡手”“盥手”“洒手”“濯手”等。[4]我们日常用语中所说的盥洗的“盥”,其最初的含义就主要指洗手,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卷五上》中说:“盥,澡手也。”洗手不但要勤洗,而且要仔细洗,注意洗的方法。据东晋著名的佛教经典《摩诃僧祇律》记载:“若两手相楷摩者,即名不净,当更洗。”东汉佛典《佛说成具光明定意经》记载:“澡手洗浴,以力为施,勤而不厌。”唐代《续高僧传》记载:“必盥手及腕齐肘已。”
洗脸不但可以清洁面容,还能够以一种整齐干净的面貌将自己展示给他人。洗脸不光要洗面部,耳朵、脖子、鼻窝等部位也要顾及。民间谚语曰:“洗脸洗鼻窝,扫地扫黑角。”早在魏晋时期,在文学家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就已经出现了“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多次出现“洗手面”“傅面”的表述。[5]此外,在同时期的佛教经籍《增一阿含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也多次出现类似的表述。当然,在不同的使用语境中,虽然都是“洗脸”,但其含义可能稍有差异。嵇康笔下,“洗脸”就是指该词的本义,而在医家兼道人葛洪那里,洗脸除了表示其本义,还有一定的卫生保健之指,到了佛教经典当中,则增加了一定的宗教神圣色彩。
洗手、洗脸和洗脚都需要擦布,过去老百姓擦脸用布,又叫“擦脸布子”“手布子”,[6]近代以后随着纺织工艺的发展,人们开始用棉织毛巾。[7]不论洗手、洗脸还是洗脚,虽然也可以直接用净水,但是也有很多人用一定的除垢之物,以保证彻底洗净。历史上,中国民众洗手、洗脸用过米汁/米汤/淘米水、贝壳烧成的灰、皂荚、澡豆、[8]胰子等物,对此,中医典籍《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科学著作《考工记》和文人笔记小说《世说新语》《文昌杂录》《武林旧事》等著作都有记载。
洗脚与洗手、洗脸略有不同,除了单纯用净水洗脚,许多民众还注重进行足浴。足浴也称足疗,就是在洗脚水中加入特定的中药材,通过长时间的浸泡达到养生目的的洗脚方式。足疗作为一种防病、治病的方式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9]中国最早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就已经记载了全身的经络和穴位,以及经络、穴位与五脏六腑的关系,并且对通过按摩治疗疾病有大量的论述。《皇帝内经》所述的十二条全身经络有六条与足部直接相关,脚是足三阴经从足到胸的开始,又是足三阳经从头到脚的结束。足疗的原理就是通过一定温度的热水,使浸泡在水中的具有特定疗效的中药材充分发挥药性,同时通过热水刺激足底血液循环,采用特定的按摩手法按摩足底可以投射全身的穴位,[10]从而达到治病、保健、养生的目的。[11]另外,即使不加入中药材,用热水泡脚也是民众十分推崇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热水泡脚能够缓解疲乏,有助于睡眠。
如果说洗手、洗脸和洗脚是每日必做的身体清洁的话,那么洗头/洗发频率就稍微要低一点。当然,具体隔多长时间洗一次头因人而异。在现代社会,洗头跟洗手、洗脸类似,除了用净水,也需要必要的除垢之物。历史上,我国古人大多是将洗头当做一种治病的方式,因此洗头所用除垢之物实际上也有药用价值,这些除垢之物包括桑灰[12]、热泔[13](淘米水)、皂角或猪苓等。洗头跟洗手、洗脸也有差异之处,洗头的时间、环境不对,容易导致疾病。如陶弘景《养性延命录·杂诫忌让害祈善篇》中记载:“凡热泔洗头,冷水濯,成头风”“饱食勿沐发,沐发令人做头风。”巢元方等所著《诸病源候总论·卷二》记载:“新沐头未干,不可以卧,使头重身热,反得风则烦闷。”
沐浴的洗尘洁体、解乏养神和医疗保健功能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就得到了人们的充分认识。我国上古社会流传着“羲和浴日”“常羲浴月”的神话传说,在这些神话中,沐浴被上古先民赋予了重要的生活、生殖意义。[14]在民间生活中,沐浴一方面是一种日常的洁身行为,另一方面在三月三上巳节[15]、五月初五端午节、六月初六天祝节[16]等特殊节期,沐浴又被人们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内涵,与去灾避邪紧密联系在一起。沐浴的治病功能不但被普通民众所知晓,也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认同。据先秦时期的典籍《礼记·曲礼上》记载:“头有创则沐,身有病则浴。”在这里,沐和浴可以分别治疗头痛和身体的疾病。除此之外,沐浴在诞生、婚姻、丧葬等民间礼俗现场和佛道等宗教文化中,又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神秘的内涵。[17]很多时候,沐浴也并非单纯的用净水清洗,而需要肥皂乃至人们特意加入鲜花、药材,[18]从而使沐浴的治病功能、保健功能更加突出。从一般的清洁、解乏到具有特定意义的礼仪行为,[19]乃至民俗生活中的去灾避邪、养生保健,沐浴的防疫避疫功能不断深化,从而成为民俗生活中与洗手、洗脸、洗脚、洗发/洗头、熏香一脉相承的行为习惯和群体习俗。
(二)饮食起居: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
民众在饮食起居上的防疫观念主要体现在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两个方面。
在日常饮食中,多吃熟食,少吃生食,通过将生食加热使其品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同时,这种加热的过程也杀灭了其可能携带的病毒。在饮食的选择上,崇尚清淡、本味,[20]忌油腻、过分烹调,这就在无形中使过分烹饪可能带来的不健康因素消失于无形。与此相应,不吃陈腐变质的水果、剩饭剩菜,特别是放了一段时间的鱼虾等肉食也是民众在长期的生活中信奉的不二信条。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人就认识到了陈腐食物可能带来的疾病。《论语·乡党》曰:“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除此之外,民众在饮食方面还尤为注重杂食。杂食包含的内容很多,既包括粗粮和细粮,也包括蔬菜、水果、葱、蒜、姜,特别是蔬菜中的萝卜,民间认为有多重食疗价值,可以消积滞、化痰清热,还可以解毒利便。在日常饮食中,也不可吃得过饱,民间讲究“少食多餐”,使身体的能量摄入均衡化。
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注重茶的药用价值,历史上有很多著作对茶的医用功能有所记载。[21]唐代著名诗人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茶坞(其一)》中说:“俾饮之者除痟而去疠,虽疾医之不若也。”但是,喝茶也要讲究饮茶之道,不能空腹喝茶,因为这样可能会使人心悸、头晕、四肢无力、心神恍惚。以茶待客是中国民众几千年来的待客之道,形成了洋洋大观的茶文化。[22]
中国民间讲究食疗,注重通过改善饮食结构达到养生、防病、治病的目的,因此,日常饮食的食疗价值也为人们所推崇。在《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千金方》等著名古代医典中都有大量关于食疗的记载。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根据当地的出产和特产习俗合理搭配饮食宜忌以达到食疗的目的是比较普遍的做法。[23]这些以粥、酒、茶、槟榔、鼻烟等多种形式所构成的食疗文化是民众防疫防病的重要武器。[24]在本次新冠疫情防治中,食疗的地位也得到人们的认可,通过调节患者的饮食结构,增加患者饮食中萝卜、芦笋、蒲公英、薏米等食材,以达到开胃、利肺、安神、通便的治疗效果。[25]
在睡眠方面,民间也有许多讲究。首先,与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相适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天时、气候相配合,春夏时节早起晚睡,秋冬时节晚起早睡。在睡觉的场所上,忌讳睡在中堂中、石头上,因为这些地方要么风大,要么渗凉,容易导致寒气入体。而睡觉的时间,既不宜太少,也不宜太多。另外,在睡觉前,注意关门关窗以防止睡觉过程中天气突变,风雨入室。
生活起居方面,保持个人衣物和被褥的卫生、干燥也很重要。衣服鞋袜除了要经常换洗,避免生虱子之外,还要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拿到太阳底下晾晒,这样可以很好地杀毒除虫。
二、居住场所的防病避邪理念与卫生保健实践
对于疾病和瘟疫的防治,除了要做好个体的清洁卫生,居所环境的干净整洁也很重要,病毒、细菌、疫病能通过不整洁的居所环境侵袭到人体。这种居所环境包括自己家屋内部,也包括家屋所处的社区或村落大环境。
(一)传统风水观中的避邪防病理念
风水,是一种关于聚落区位选择的知识体系,[26]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八卦九宫等众多理论,[27]成为长期以来民间阴阳宅卜地选址、房屋内部结构布局的重要行动指南。如果我们抛开那些隐秘难证的部分,仅从卫生、防病避邪的角度出发进行审视,也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在传统风水观中,家屋的坐落位置、大门朝向、周围环境等对于家宅的兴旺发达十分重要,好的风水能够带来家庭的繁荣昌盛,而坏的风水则可能带来病邪、恶运。
在居所的选址上,风水理论认为房屋布局应该坐北朝南、依山傍水,虽然从主流风水学的理论来说,这种选址是为了体现前朱雀(夏),后玄武(冬),左青龙(春),右白虎(秋),从而可以实现山水相拱、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效果,[28]但同时,这种布局也可以避免冬天来自北方的寒冷之风,利于接纳春夏季节来自南方的暖风,[29]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寒风直吹对生活于居所中的人们的危害。房屋的宅基地要避免曾为废井或者附近有废井,因为废井周围大多较为潮湿,长久居住易患风湿病。[30]
在家屋的内部结构布局上,风水理论也有诸多讲究。家屋内部要构筑合理的排灌系统,使积水易流,同时要注意及时清理这些暗沟阴渠,防止杂物堵塞。要注意不能在庭院中形成积水,因为庭院中长期积水容易滋生蚊蝇,传播疾病。[31]
村落所处的位置也有许多风水方面的宜忌,包括其卜居、形局、水龙(龙脉)、构景、水口等。[32]特别是水口,即水流出入之口,对于村落极为重要,因为它是全村生活用水的来源和生活废水排出口,水源如果受到污染,全村人的生命健康将无法保证,如果生活污水不能及时排出就会滋生蚊蝇,进而产生病菌病毒。这一点在许多历史悠久的古村落尤为可见。如浙江楠溪江流域的芙蓉村、苍坡村、岩头村等古村落就有很多村规民约规定不得在溪流、沟渠下游建造猪棚牛圈,不得于日出之前在沟渠洗衣,水渠内不得放养鸭鹅等。[33]
在新房建成上梁的时候,民众特别注重举行隆重的上梁仪式,这种仪式不但可以阻止凶神恶煞侵犯房屋的祥瑞,还可以防止他人抢走或者扰动新房的“好运”,[34]从而使新房成为一家人希望和兴旺的开端与象征。
(二)居所的卫生实践
居所卫生首先要在房舍营建时将牲畜棚舍、厕所等容易产生污秽的场所尽量建在屋后、墙角或者僻静之处,[35]尽量与人们的活动场所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不但可以远离这类场所产生的恶臭气味,还可以避免因近距离接触带来的病菌。
在家宅的清扫方面,民间还有许多很重要的习俗。每天清晨早起洒扫庭院是许多农村家庭的良好习惯,整洁的庭院不仅能够给外人留下一个良好的视觉印象,还能使家庭成员神清气爽、精神饱满。经常清扫屋舍,保持室内的清洁卫生,特别是牲畜、家禽的圈舍,要及时除粪、清洗,厕所也要经常冲水,尤其在夏天,以免恶臭难闻。
腊月二十三是民间最重要的除尘扫除之日,民众称呼这一天为“辞灶日”,即辞别灶王爷,祈求灶王爷上天面见天帝之时多言好事。这一天全家发动,进行整个居所的大扫除,以迎接新的一年来临。
在春节期间,有的地方正月初六,有的地方是正月最末几天,许多地方流行一种“送穷”的习俗,主要内容就是清扫屋子,把杂物垃圾送到田野中烧掉,[36]一方面象征着旧的一年的“穷鬼”被送走,另一方面又预示着对过去的、旧的面貌的改变,迎接新的美好生活到来。
日常生活中的生活用品要勤于洗刷,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衣帽鞋袜、被单被褥等生活用品的洗刷,另一个是对锅碗瓢盆等厨房用品的洗刷。这两类物品也需要常洗多换。衣物经常换洗,特别是内衣常换勤洗能够减少细菌的产生,从而避免皮肤病的发生,有谚语曰“常洗衣裳常洗澡,常晒被褥疾病少。”厨房用品经常洗涤也能够及时清除灰尘、污渍和各种有害细菌,从而保证厨具的卫生,进而使得食物健康卫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厨房在夏天特别容易招致苍蝇聚集,经常清扫屋角旮旯,避免泔水、剩饭、变质的饭菜大量积留,锅碗瓢盆等厨具灶具的干净、干燥、不油腻可以很好地避免苍蝇聚集。
我国古人习惯使用熏炉燃烧沉香、檀香、麝香等物品,通过在室内燃烧这些香料,可以达到心神宁静、祛除秽气、防霉杀菌的作用。[37]而在民间生活中,许多女性喜欢佩戴香囊,香囊散发出的香味不但可以使人身心愉悦,还可以祛疫逐蚊,特别是在端午节,佩戴香囊已经成为一项全民性的节日习俗。现在,在中国许多地区还有在丧事结束之时,在家中焚烧艾叶、菖蒲等驱邪除疫的习俗,这也是焚香避疫习俗的一种残留。在本次新冠疫情防治中,中医药治疗通过焚烧艾叶、菖蒲或者佩戴用藿香、苍术、白芷等中草药制作的香囊[38]来抑菌、抗病毒的做法已经受到了广大中医专家的认可。[39]
除此之外,民间在居所卫生方面还十分注重及时除虫,采取各种措施对老鼠和蚊蝇及时投放药饵进行杀灭,从而避免这些生物可能带来的病毒。[40]
三、民俗宗教:以仪式的手段化解疾病/疫鬼
中国民众传统的疾病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鬼怪联系在一起的。在民众的传统认知中,疾病和鬼怪联系在一起,疾病来源于鬼怪。[41]在这种情况下,相当多的生理之病(内部生理器官损伤、衰竭等)和心理之病(心痛、胸闷气短、浑身无力、头疼、没精神等)融合在一起,或者说人们无从区分也并不感到有区分二者的必要。因此,生病之后,特别是那种并无直接或明显病因的以心理之病表现出来的生理之病,许多人第一时间不是去看真正的医生,而是去寻求神道的“指点”。神道通过做法降神、驱鬼逐疫找到“疾病的根源”,从而使民众获得“化解之道”。对于社区来说,通过定期举行驱鬼逐疫、送瘟神的仪式,将疫鬼逐出或者送出社区,从而使社区免受瘟疫的侵扰。在中国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医生是和巫师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称之为“巫医”。同时,道士、和尚这类宗教人士也大多懂得治病,或者说他们举行的各种仪式和诵经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治病,目的是为了将精神和生理处于痛苦之中的民众从水深火热当中解脱出来。因此,不仅专门的民俗信仰,如跳傩、送瘟神是为了治病、除疫,而且一般的民间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民众应对病厄的重要方式。
(一)跳傩:驱鬼逐疫的多维文化丛系
傩文化是一种包括傩观念、傩仪、傩戏、傩神信仰、傩舞、傩面具文化、傩堂、傩器、傩画、傩俗等内容在内的多维文化丛系。[42]在这一文化丛系中,傩仪和傩神信仰是其他文化形式发展的基础。[43]在傩祭和傩舞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傩戏和傩画等艺术形式,而傩面具、傩堂和傩俗等文化形式则是伴随着傩仪,或者说是作为傩仪和傩神信仰的一部分而产生的。驱鬼敬神、逐疫去邪、消灾纳吉是傩仪和傩神信仰的核心,[44]因此,也可以说,驱鬼逐疫是整个傩文化丛系的观念基础。
傩文化在中国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傩文化的主流是以官方礼仪的形式展现出来的。
商周时期,夏官司马下设的官职方相氏以狂夫(武士)四人,通过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将散播于人们居所四周的疾病和疫疠驱赶出社区。这一礼仪包含多种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索室殴疫,即进入屋内搜寻并殴打疫鬼,将其驱逐出家屋。[45]狂夫(武士)在施行这一礼仪的过程中,手上戴着用熊皮做成的头套比拟熊、脸上佩戴面目狰狞黄金四目的傩面具,[46]同时身上穿着黑色的衣服和红色的裤子,手执戈盾,呈现出一种恐怖、神秘、凶恶的面貌。毫无疑问,狂夫(武士)的这种打扮都是为了营造一种可怖的氛围,从而能够更好地对疫鬼造成惊吓,并最终将其驱赶出室外。除此之外,地官司徒下设的职位司救,秋官司寇下设的有庶氏、翦氏、赤犮氏、蝈氏、壶涿氏、蜡氏、野庐氏,以及祝官之长大祝、巫者之首司巫也都是有关驱疫逐疠的官职。
在这个时期,跳傩对于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跳傩的种类也比较多,包括春季的国傩、秋季的天子傩和冬季的大傩。
到了汉代,傩仪的内容更加丰富,仪式更加复杂,辅助的器物也更加多样化,桃弓、鼓等器物开始出现,大傩的日期提前到了“先腊一日”,即腊月初七。这些新出现的器物,无疑也都是为了避邪和惊吓疫鬼。到了后汉,民间避邪常用的桃梗、郁儡、苇菱也开始进入傩仪当中。汉代以后,傩文化的主流开始由以往宫廷操办的官傩变为民间举行的乡人傩,各地地方官也开始在自己的辖区举行傩仪。当傩文化的主流变为民间傩时,其所具有的娱乐因素就开始不断增加,但是行傩的文化核心并未发生改变,行傩仍然是为了逐疫驱鬼。同时,也正是从汉代开始,傩文化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到宋代以后,傩文化从以往的主要流传于北方地区进入南方,傩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开始成为一种多元的文化体系。
从明清开始,宫廷傩逐渐消失,傩文化成为一种彻底的民间文化,傩仪的形式更加多样,大量的地方神灵也开始进入傩神系统。[47]随着傩仪与民间文化更深刻地融合,原来的宫廷傩所具有的强烈的逐疫功能有所减弱,从傩仪当中产生了大量的具有地方色彩的傩戏。[48]当然,傩戏真正出现的时间可能在汉代,甚至可能在商周时期就已经伴随着神秘、恐怖的官傩而萌芽。
总的来说,虽然傩文化从俗入礼,又从礼入俗,经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所具有的驱疫逐鬼的功能在不断弱化,与各地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舞戏剧、民俗风情相结合而产生了更多的世俗化的娱乐成分,但是其所具有的逐疫驱鬼的文化内核是一贯的。
(二)瘟神信仰:应对瘟疫的地方性仪式体系
瘟神信仰就是以瘟神作为信仰对象所进行的以驱瘟逐疫为目的的民间信仰活动。它同跳傩的目的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跳傩作为一种文化丛系,在傩仪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前文所述的包括傩戏、傩舞、傩面具文化等在内的多种文化形式,而瘟神信仰则只有信仰仪式,并无其他次生文化形式。瘟神信仰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地方称之为“送瘟神”或“调瘟船”,[49]闽台地区则以“五帝信仰”而称之为“送王船”。同时,这种信仰形式在有的地方是以独立的瘟神信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有的地区则是与端午节的节俗结合在一起,成为端午节俗的一部分。瘟神的具体所指各地也是不同的,除了前述五帝或其他地方称为五瘟神、五圣之外,还有同样流传于闽台地区的王爷[50]、流传于浙江温州等地的温元帅温琼[51]、云南大理的白族本主大黑天神[52]、西藏地区的牛魔王[53]等。
瘟神信仰是民众将瘟疫这一具有较强传染性和较高病死率的病理现象人格化[54]或具象化[55]为具有强大的超能力,可以致人生病甚至死亡的神魔——疫鬼、瘟鬼、瘟神、疟鬼,从而通过各种仪式和信仰活动来祈祷瘟疫消退的社会现象。虽然这种方式并不能在医学上阻止瘟疫的社会传播,但是作为一种民众应对瘟疫的方式,其通过特定的仪式与符号体系,使地方社区在象征的意义上获得了对于疫鬼/瘟疫的驱离,将疫鬼/瘟疫阻隔在社区之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疫鬼/瘟疫对社区的威慑和影响,使得疫鬼/瘟疫可能带来的社会恐慌和社会失序消弭于无形。
民众的瘟神信仰受到中国传统的道教和佛教文化的重要影响。历史上,佛教和道教不但直接影响了民众瘟神观的形成,甚至直接参与了民间的驱瘟活动当中。[56]道教的《道要灵祇神鬼品经》辑录了十八品各类道书中的神鬼之言,其中一品就是瘟鬼。《太上洞渊辞瘟神咒妙经》《太上灵宝净明天尊说御殟经》《神霄断瘟大法》等都是有关瘟神的消灾延寿诵经必备。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医生同时也是著名的道人,如葛洪、孙思邈。道教治瘟一方面依靠中医知识,例如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另一方面也依靠道教的宗教仪式,通过服食丹药、神符,举行醮仪来驱瘟、治瘟。[57]
如果说早期的跳傩是通过可怖的面具、执戈的狂夫(武士)等场面营造一种强烈的威慑、惊吓的气氛从而将疫鬼驱赶、驱逐出社区的话,那么瘟神信仰则大多是乡民通过投(粮)食贿赂[58]、演戏酬神[59]等方式“恭送”瘟神或者载有瘟神的“瘟船”离开社区。[60]这其中些微的差异反映了宫廷、官府和民间对待同一种可畏之物的不同态度,对于民众来说,只能通过恭敬的演戏、巡游、投撒米豆来讨好瘟神,将其“送”出社区。而一旦瘟神离开人们居住的社区,则要迅速采取措施,使其“覆灭”以免重新进入社区对人们造成危害。[61]因此,在送瘟神的仪式中,恭敬的讨好和暴力的伤害是相辅相成的。
(三)作为“治”“病”方式的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的“治”病方式不同于医药的疾病治疗,医药的治疗是通过科学的检测或者体表特征、病理表现判断,从而直接或者间接获得患者生理损伤、失能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在生理上治疗疾病。而民间信仰的“治”“病”却是通过超自然的沟通将民众的现实需求(“病”)以至高无上的神灵之力予以满足(“治”)的“治病”方式。这样“治”病虽然缺乏科学的或生理的依据,却是能够解决民众心理之“病”或者灵魂之“病”的有效方式。当然,这种“治疗”也并非都能灵验,但是能够解决民众需求的最“合适”(经济、便利等)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在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根底深厚,“深入人心”。
从某种程度上讲,民间信仰的本质是治病,或者是为了治疗社会之“病”,或者是为了治疗个体之“病”。不论通过何种仪式,都是为了使民众和神灵沟通,从而解决现实生活中不足与缺失的问题。
从社区层面来说,许多民间信仰最重要的诉求之一就是祈求神灵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民众祈求国家无灾殃、天时利农事恰恰是以愿望的形式表达了对于灾祸、疫病的预防,而社区层面的巡游、仪式、神灵交往则是为了修复、强化由于时间的流逝所淡化的人与人、社区与社区之间的有机联系。
从个体层面来说,寻巫(医)问“药”是许多民众直接的信仰诉求,通过敬拜、祈求以及间接的以巫者为媒介与神灵之间的沟通,信众了解了关于自己身体之病的缘由,[62]从而有的放矢地采取对策,修复与神灵或鬼怪之间的关系。[63]即使民众是为了求财、求福、求姻缘、求平安,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为了寻“药”,因为人们生活中缺乏财运、福气和姻缘,以及对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的恐慌,所以通过对神灵的敬拜,以期获得神灵的青睐,从而得以治疗这种“疾病”。钟敬文先生在《医药的源起与民间信仰》一文中指出,在人类早期阶段,医术是和巫术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医术只不过是巫师的副业而已,医药源于民间信仰。[64]与原始信仰一脉相承的民间信仰自然也继承了巫术的这种医术性质。
四、节日与地方社会的防病避邪
节日在地方社会的民俗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许多重要的防疫防病习俗是依附于当地的节日的。这里所讲的节日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普遍性的全国性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和节气,另一种是当地的特色节日,例如神庙的庙会、宗族的祭日、新兴的文化节等。同时,许多并非在节日期间施行的防病习俗也构成了地方社会独特的防病避邪的知识体系。
(一)全国性节日与节气中的防疫防病习俗
由于中国的传统节日大多是来源于传统的节气,[65]因此,传统节日当中的防病习俗基本上是跟节气的改变相一致的。节气是古代中国人根据日月运行规律和随着日月运行而改变的自然物候所归纳的一套关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关系的学问。节气的基础是包括气候、物候在内的自然环境的整体变化,而这一系列变化直接影响了人们生存的地理环境,因此,应时而动、根据自然状况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成为民众自然而然的生活抉择。[66]这种根据生存环境所进行生活方式的调整恰恰就是民俗产生的基础之一。
在传统的节日系统中,包括除夕、大年初一、正月十五元宵节在内的春节系统、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清明节、五月初五端午节、六月初一半年节、六月六天祝节、七月七七夕节、七月半中元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九重阳节、冬至节、腊八节等节日都产生了大量与防病防疫有关的节日习俗,[67]特别是五月初五端午节,作为恶月中的恶日,端午的时令特征中充满了瘟毒、灾恶,同时,蛇、虫萌动,极易侵袭人体,因此人们在端午节俗中创造了大量的防病防灾的习俗。[68]这些习俗有相当一部分是食俗,如春节期间喝屠苏酒、二月二吃豆子、端午节喝雄黄酒和吃粽子,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包括洗刷、佩戴香囊、焚(熏)香、出游(走百病)、敬拜、晒衣、登高、泼水等在内的其他民俗事象。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共同构成了中国民众节日防病的知识体系和文化实践。
二十四节气作为一个整体,每一个节气都包括半个月时间,将一整年平均分为二十四个等份。在这些节气所涵盖的时间范围中,有的节气所涵盖的范围并没有形成固定的节日,但是不论是否形成节日,每一个节气段落,都有相应的习俗配合节令的变化。这些习俗当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为了防病防疫、养生保健的目的。[69]立春日的习俗之一咬春是制作春菜,而春菜当中的萝卜、五辛盘就具有很强的保健功能。雨水的节俗之一撞拜寄,也是为了通过拜干爹使小孩健康成长。惊蛰的习俗吃梨、扫虫、祭虎爷、敲梁震房是为了驱除害虫。谷雨的节俗杀五毒、走谷雨、洗“桃花水”都是为了防病祛灾。芒种的节俗煮梅是为了消夏,也有保健功能。夏至吃狗肉、戴枣花也都是为了抗寒、避邪。小暑吃黄鳝、吃藕,大暑送“大暑船”,立秋习俗插戴楸叶、贴秋膘、咬秋、吞服红豆、喝立秋水,处暑吃鸭子,白露吃龙眼、核桃、番薯,秋分吃秋菜,寒露吃芝麻,霜降吃柿子、用桑叶泡脚,立冬进补吃膏滋、倭瓜,大雪进补,大寒喝鸡汤、炖蹄髈,等等,都是从健康的角度出发而产生的与时令相符的民俗实践。
(二)地方社会防疫防病的独特实践
地方性节日当中的庙会和宗族祭日中的防疫防病大多是跟民间信仰中的避邪祛病联系在一起的。许多神庙在举行庙会的时候会在神庙门口向进入神庙的人们用柏树枝洒经过道士做法的“神水”,这实际上就是为了防病避邪,通过沾染“神水”将人们身上可能携带的邪祟排除在庙门之外。除此之外,在神庙的仪式活动中也有很多具有类似象征意义的仪式。在许多神庙仪式活动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抬着神像在社区的边界附近巡游,这种巡游实际上就是将一定的社区范围纳入神灵灵力的保佑当中,使人们免受其他恶神凶鬼的骚扰。
江苏和安徽一带农历四月初八的乌饭节,虽然是为了纪念孝子目连,但乌米饭同样也具祛风解毒、防止蚊虫叮咬的功能。在浙南的畲族地区,三月三作为一种民族节日,也制作食用乌米饭,也具有同样的防病功能。[70]温州地区在农历二月二吃芥菜饭,也是为了防止生疥疮,民间俗谚“二月二吃了芥菜饭不生疥疮”。
洗三是民间的一项重要的育儿习俗,其最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于通过为婴儿沐浴,洗涤其身上的污秽,免除未来成长过程中的灾难,许多人家在洗三的时候要请和尚过来做法,用佛教的法力为洗三的婴儿进行法力加持,都是为了婴儿的健康成长。
许多地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防疫防病习俗,这些习俗不一定是在节日期间进行,但同样构成了地方社会防疫防病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前述闽台地区的王爷信仰等瘟神信仰以及其他有关的民俗宗教、民俗事象[71]、民俗知识[72]等都是属于这一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