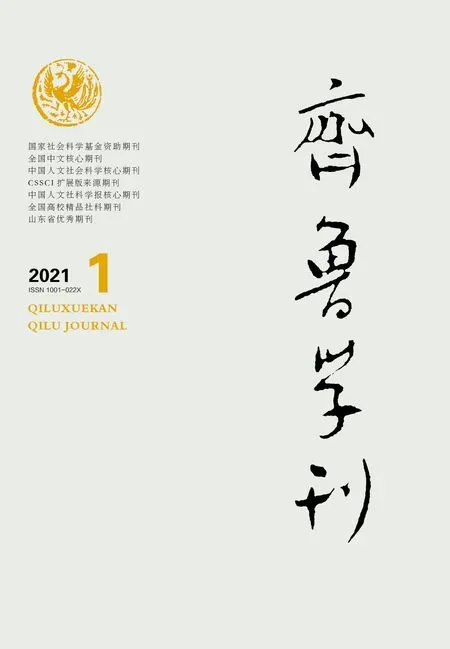两汉之际的外戚政治与赋学转捩
刘祥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两汉外戚政治笼罩一时,赋家大多与之有所关联。《文心雕龙·程器》:“扬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修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1](P719)刘勰论文人之疵,以党于外戚批评班固、马融;冯衍、杜笃也曾投靠阴氏、马氏。至于扬雄“少算”,范文澜注引《汉书·扬雄传》有关扬雄家贫的记载曰:“彦和谓其少算,岂指是与?”又引《颜氏家训》曰:“扬雄德败《美新》。”[1](P721)尚两存其说。陆侃如、牟世金则直接指出:“少算即讽其《美新》之失。”[2](P632)《美新》即扬雄为赞美王莽所作的《剧秦美新》,扬雄因为此文饱受争议。西汉外戚政治之于东汉,实开风气之先,且西汉因外戚篡权而亡,对两汉之际赋家的个人生存与辞赋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心雕龙·时序》:“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1](P673)明指西汉末年王莽喜好图谶对文学的影响延及东汉立国。研究外戚政治与辞赋的关系,对还原赋家生存情境、探究两汉之际赋学转变路径有其特殊意义。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尚少,故不揣浅陋,试加探析。
一、王政与王言:赋家与外戚的深层矛盾
汉代赋家多为文学侍从之臣,拥有郎官身份,积极参与现实政治,其大赋创作也有现实功用,客观上起到了代行王言的作用,与代行王政、侵蚀皇权的外戚政治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汉帝国内在组织架构留下的隐患,也是赋家追寻理想政治秩序、维护天子权威的体现,深刻影响了两汉辞赋创作与批评。
赋家代行王言与他们对辞赋源头与功用的认识有关。《汉书·艺文志》论荀子、屈原曰:“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3](P1756)概括出赋的三个特点:一、产生背景是被谗忧患;二、创作目的是以赋讽谏,揭示出赋作的强烈政治性与现实性;三、产生源头是《诗》,这不但与《两都赋序》的说法相呼应,也解释了汉代赋家以经义缘饰赋作的现象。源于《诗》,作赋以讽,兴于忧患为大部分赋作共有。其中尤以“诗源说”影响最大,《两都赋序》曰: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4](P1-3)
班固历数西汉辞赋的发展,指出汉赋发展与帝国文化建构的关系。他将武、宣之时设立乐府、赋家献赋与西周早期诗教相提并论,将其视为王朝政治兴盛的集中体现。而西周诗歌有其现实功用,据《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5](P11)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是为天子听政而作,后来演变为行人赋诗言志。刘熙载《艺概》:“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6](P445)汉赋与周诗在讽谏意旨上达成统一,如施补华《拟白香山赋赋》所说:“寄哀怨之深心,托规讽之微旨。”[7](P226)
《国语》中提及的“瞍赋”值得注意,瞍与瞽、矇在周代王朝政治中,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礼记·礼运》:“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8](P615)瞽、瞍、矇皆是目盲之人,乃“乐官也”[9](P730),有教育职能。《周礼·春官》言“瞽矇”行“九德六诗”之教,而据《礼记》可知教育国子仅是其职能之一,随侍君主左右,提供合理建议、规范君主行为更为重要,所谓“导其中和”[8](P615)。他们随君主而动,在庙、朝、学之外,形成王朝第四个政治中心。与之性质相似的巫、史,也是君王意志的延伸。陈梦家认为上古“王者自己虽然是政治领袖,仍为群巫首”[10];李泽厚也说:“自原始时代的‘家为巫史’转到‘绝地天通’之后,‘巫’成了‘君’(政治首领)的特权职能……即使其后分化出一整套巫、祝、卜、史的专业职官,但最大的‘巫’仍然是‘王’‘君’‘天子’。”[11](P6)则巫、史以及瞽、瞍、矇都是在王主导下的职能分化。王乃一切权力的根源,小国寡民的时代,王的职权高度统一,在后来的国家建制中,逐渐出现言权、事权分离,《礼记》所言庙、学与王之前后左右皆是言权的专职化,宗祝代王向祖先言说,三老代王向学子言说,巫、祝、卜、史代王向鬼神与天言说,瞽、侑代王向自我言说,言说的对象不同,代表的主体却是一致的,这些与文辞有关的专职人员都是代行王言,以补国政。
武帝朝赋家大多属于内朝官,他们随侍天子左右,献赋以讽、议论朝政,其职能与王之前后左右的巫、史之流,瞽、瞍之属相类。他们被颜师古称为“天子宾客”[3](P2776),大多担任郎中令统属的郎官、大夫、谒者等,钱穆曰:“是诸人者,或诵诗书,通儒术。或习申商,近刑名。或法纵横,效苏张。虽学术有不同,要皆驳杂不醇,而尽长于辞赋。盖皆文学之士也。武帝兼好此数人者,亦在其文学辞赋。”[12](P92)他们经常代王言说,辩论朝堂,“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3](P2775)。出使专对、宣谕王命,如严助晓谕淮南王,全是天子口吻。汉代赋家在赋中代行王言,正与其政治特性密不可分。
外戚在内朝制度建设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襄赞天子治理天下,分夺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官员的权力。《汉书·刘辅传》注引孟康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3](P3253)武帝时卫、霍分别被封大将军、骠骑将军,元狩四年(前119)武帝为二人初置大司马,冠将军之号,从此大司马一职与外戚势力密切关联。武帝临崩,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首开以外戚担任内朝将军辅政风气。据田旭东统计,西汉共22人担任大司马一职,其中16人为外戚[13],田氏所列非外戚者有张安世、韩增、师丹、韦赏、董贤、马宫等6人,其中董贤因其妹入宫为昭仪,亦可居外戚之列,实有17人。宣、成、哀三帝皆曾短期去将军于大司马,然而去掉将军号的大司马权力却丝毫未曾减弱,哀帝以董贤为大司马,欲传之以帝位;哀帝死后,元后以王莽为大司马,遂使他得以控制朝局,逐步篡政,都证明外戚任大司马一职对君主权力的侵蚀之大。
今按,“大司马”见于《周礼·夏官》:“大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制畿封国以正邦国,设仪辨位以等邦国,进贤兴功以作邦国,建牧立监以维邦国,制军诘禁以纠邦国,施贡分职以任邦国,简稽乡民以用邦国,均守平则以安邦国,比小事大以和邦国。”[14](P2280-2284)大司马掌握军政,颁布九法之书,所负责的九事皆为稳定邦国。孙诒让引《郑目录》云大司马“象夏所立之官。马者,武也,言为武者也。夏整齐万物,天子立司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诸侯,正天下,故曰统六师平邦国”[14](P2235)。大司马与天子共掌邦政,不可避免地分王之权,代行王政。其在汉代设立之初本为削弱外朝权力,而外戚担任大司马将军辅佐朝政局势的确立,反而进一步分割了王之事权。霍光左右昭帝、昌邑王、宣帝初期朝政二十多年,王氏父子兄弟于成帝朝作威作福,王莽擅行废立,最终取代汉朝,都与此职密切相关。
与赋家渊源颇深的太祝六辞、太师六教、大司乐乐教、矇瞍赋诵皆在春官宗伯,掌守礼职,代行王言;而为外戚专权服务的大司马一职,来自夏官司马,代王行政,遮蔽王权,二者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武、宣强盛君主主导下尚能联合,一旦君主仁弱,关系便迅速恶化。二者的区别在于,代行王言仍以“王”为中心,一切行动如在王前后左右的巫、史、矇、瞍,赋家言说是为了规范王的行动,进而让帝国运转更为有序,在西汉赋家笔下,这种秩序多表现为儒家政治理想。如《上林赋》赋末的崇儒描写,登明堂而朝诸侯,坐清庙而祭先祖,将整个帝国置于儒家理想政治秩序之中,从而实现“德隆于三皇,而功羡于五帝”[4](P378)。
代王行政,则以“政”为中心。政事是权力的具体体现,极易造成专权行为,损害以天子为中心的帝国政治。西汉外戚专权之所以引起赋家强烈反对,究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它破坏了赋家构建合理社会秩序的努力,引起社会动荡不安。成帝朝,最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是王氏专权朝廷与赵氏专宠后宫。专权朝廷,则损害天子威仪,破坏政治秩序。专宠后宫,大肆残杀皇嗣,则动摇国本,直接导致了外藩入继,帝王权威衰颓。前者如刘向《极谏外家封事》所言王氏外戚专权后果严重,造成政治混乱,朝政失序。至于后者,当时即有童谣“燕飞来,啄皇孙”讽刺赵飞燕姐妹残害皇嗣,《汉书·外戚传》录有解光的奏疏,对此事有详细论述。
扬雄《甘泉赋》也是在此背景下创作的,具有反对外戚政治与女色误国的双重意味。他作此赋目的是“微戒齐肃之事”[3](P3535),对女色抨击最为有力的地方有两处:一处如《汉书·扬雄传》所言讽刺赵昭仪不当在属车豹尾间,即不能进入天子的甘泉卤簿,参加甘泉祭祀活动[15];另外一处见于赋中的一段描写:“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卢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揽道德之精刚兮,侔神明与之为资。”李善注曰:“言既臻西极,故想王母而上寿,乃悟好色之败德,故屏除玉女而及宓妃,亦以此微谏也。”[4](P330)玉女、宓妃指女色无疑,而“西王母”或指王太后,乃扬雄对王氏家族过于强盛的潜在书写。扬雄在《甘泉赋》中批评外戚、女色,以求匡补国政,与其《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等赋一致,皆以构建合理的帝国政治秩序为旨归,力图讽谏,针砭时事,代行王言。
赋家、外戚之间代行王言与王政的区别,构成其内在的根本矛盾,致使二者之间的关系由武帝年间在强大君权下的联合,转为西汉后期二者的分离:赋家为了维护天子权威而与外戚奋起抗争,外戚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实行政治高压。面对掌控帝国权力的外戚政治,赋家生存空间被压缩,精神遭受压抑,反映到辞赋创作中,则使西汉后期辞赋从创作到批评都发生了重大转向,并深入影响了东汉一朝的赋学面貌。
二、骚怨与玄思:外戚政治影响下的赋学转向
外戚政治是西汉后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宋人黄震认为“汉世外戚之祸惨于匈奴”[16],赋家从生存状态到辞赋创作与批评都深受其影响。这种影响在辞赋创作中主要通过赋家的现实遭际而实现。在与外戚的冲突中,赋家在政治上遭受打压,以至最后王莽代汉,造成了赋家普遍的流离失所,这些都使他们远离朝堂,创作也从对校猎、郊祀等国家重大题材的关注转向行旅征途,从对外在国家政治建构转向个人情感表达,从对物态的堆叠铺陈转向对历史故事的沉思涵咏,其集中表现便是述行赋的出现。
外戚政治造成赋家征行的客观事实,成为早期述行赋创作的现实原因。具体影响有二:其一,外戚政治的昏暗成为述行赋创作的主要背景。外戚政治对赋家的这层影响,以政治贬谪与王莽代汉造成的兵祸为主。《遂初赋》的创作属于前者,由于长期受到外戚政治的压抑,刘歆的人生趋向发生转折,从与王凤等外戚对抗,转而投靠王莽。“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3](P1967)从此成为王莽一党,陷入王氏与傅、丁的争斗之中。哀帝初年刘歆出京,《汉书》本传以为是他移书太常博士招致执政大臣及诸儒怨恨,惧诛远走。然而徐华据《汉书·儒林传》详细分析建平二年(前5)刘歆出京时的政局变化,即傅、丁当权,诸儒多不在任,从而认为:“(刘歆)外放及徙任的最主要的原因乃哀帝政治立场的变化,后党得势后的打压,而非由于诸儒排挤。”[17]班彪《北征赋》则属于后者,创作背景是王莽代汉引起的大动乱使赋家失去了最为基本的人身保障,流离失所。
其二,外戚误国乱政成为赋家批判或者感慨的对象。刘歆《遂初赋》:“惟太阶之侈阔兮,机衡为之难运。惧魁杓之前后兮,遂隆集于河滨。”[18](P231)《春秋运斗枢》:“北斗七星弟一天枢,弟二璇,弟三机,弟四权,弟五玉衡,弟六开阳,弟七摇光,弟一至弟四为魁,弟五至弟七为杓,合为斗。”[19](P485-486)《春秋元命苞》:“常一不易,玉衡正,太阶平。”[4](P407)太阶乃三台星,喻指三公,明指三公不得其人,导致中央政治败坏。而建平二年(前5),傅太后上尊号,师丹、孔光相继被免,丁明为大司马卫将军,党于傅氏、丁氏的朱博为丞相、赵玄为御史大夫。《汉书·五行志》载此年朱、赵临拜,而有大声如钟鸣,李寻以为“人君不聪,为众所惑”[3](P1429)。刘歆于赋中接着哀悼衰周失权,批评晋平公不恤宗周,愤恨六卿专权于晋,实是感叹哀帝朝外戚当政、皇权不张,而诸侯宗室未能振拔。所谓“叔群既在皂隶兮,六卿兴而为桀”,乃以宗室贤臣自比,置身于权臣的对立面,对古代重用宗室的用人制度充满缅怀。其他如班彪《北征赋》曰:“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阨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4](P426)赋文开篇便以王莽代汉造成的大动乱为征行的缘起。刘、班二作皆以史实写时事,刘勰论曰:“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1](P615)他们对外戚政治的现实反映也杂用古代纪传,以古写今。
政治上的遭遇,使两汉之际的赋家情感体验多哀怨悲思,进而造成其作品关注中心与情感倾向的转移。武、宣盛世,赋家活跃于宫廷,受皇权左右,辞赋创作以帝王为潜在读者,关注重点在国家制度与人主娱乐,对个人情思着墨甚少。虽有董仲舒《士不遇赋》、东方朔《答客难》、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书写盛世不遇,但与外戚政治影响下的赋家创作普遍内转有别。西汉后期,外戚政治高压,造成赋家与皇权的疏离,赋家更多地审视个人遭遇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抒发怨愤,抨击时政。如扬雄《酒赋》以“常为国器,托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20](P154)的鸱夷比况外戚宦官等无德宵小,批评成帝用人不公,过于宠溺外戚,而忽略法度之士。正是在政衰俗怨的时代背景下,骚体赋强势回归,抒情小赋出现,班婕妤《自悼赋》即是一例,并且因其后妃的身份,使得此赋在外戚迭贵的环境中尤显独特。
骚体赋的复归与汉代屈原范式的确立大有关联。西汉后期士人推重屈原,是因为屈原被馋人隔绝与他们被外戚政治压迫有着历史相似性。屈原行廉志洁可与“日月争光”[21](P2994),竭诚尽忠以事君,却遭谗言所谤,于是作《离骚》以抒怨,他的伟大人格成为汉代赋家在困境中的有力支撑。成帝朝,王凤兄弟相继为大司马,许、班、赵、李诸家外戚入侍帷幄,赵飞燕姐妹专宠后宫,《汉书·楚元王传》载:“(刘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3](P1966)他在此政治背景下创作《九叹》,乃有感而发。林纾认为:“贾谊、刘向作《惜誓》《九叹》,皆有所感,故声悲而韵亦长。”[22](P49)刘向身为宗室,深以屈原自比,通过对屈原及其作品的阐释,坚定修身自持、忠君藐俗的决心。如《逢纷》开篇道:“灵怀其不吾知兮,灵怀其不吾闻。就灵怀之皇祖兮,愬灵怀之鬼神。灵怀曾不吾与兮,即听夫人之谀辞。”[23](P285)主上信谗不寤,正是刘向与外戚、宦官斗争的真实写照,蕴含了无尽的悲哀与愤懑。
扬雄也极为推崇屈原,周必大《题赵遯可文卷》曰:“扬雄有言‘事辞称则经’,此为屈原发也。自国风、雅、颂之后,能庶几于此者,其《离骚》乎!”[24](P542)他作《反离骚》,表面上是反《离骚》之辞,表达“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的人生态度,实则是借此抒发对屈原的同情与对现实的不满:“图累承彼洪族兮,又览累之昌辞,带钩矩而佩衡兮,履欃枪以为綦……灵修既信椒、兰之唼佞兮,吾累忽焉而不蚤睹?”[20](P161-162)言辞之间对西汉末世深切担忧、对外戚专权强烈不满。扬雄的《解嘲》与外戚专政也直接相关,《序》曰:“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20](P175)外戚及其依附者占据朝廷,而扬雄守正自修却被嘲笑,可见《解嘲》的创作,正是激于外戚政治的肆虐。
此外,扬雄赋论也在外戚政治影响下,从早年模拟相如作四大赋,转而晚年悔赋,从此“汉赋艺术进入一变革期,在创作上,扬雄向楚骚复归和小赋的出现意味了这点;在理论上,扬雄受自身多变思想和忧患意识的影响,其创作心理和思维结构处于穷变之中,而汉代文学正以此穷变为过渡,显示了由西汉而东汉的发展轨迹”[25](P204)。西汉后期,惩于帝王昏聩与外戚擅政,赋论多重讽喻,如《诗赋略后序》批评枚、马大赋“没其风喻之义”[3](P1756),扬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3](P3575)。而到了东汉前期,班固《两都赋序》在“抒下情”与“宣上德”之间,明显更偏重后者。所以刘熙载《赋概》说:“屈兼言志、讽谏,马、扬则讽谏为多,至于班、张则揄扬之意胜,讽谏之义鲜矣。”[6](P446)这种变化与王莽代汉、变革引起的大变动相一致。吕思勉《秦汉史》曰:“中国之文化,有一大转变,在乎两汉之间。自西汉以前,言治者多对社会政治,竭力攻击。东汉以后,此等议论,渐不复闻。”[26](P174)整个社会的讽谏精神普遍失落。
外戚政治造成的赋家身体流离、情感哀怨,不仅使辞赋体式、情感指向以及理论批评发生变化,并且深刻影响了赋家的人生趋向。与两汉之际明哲保身的士人风气相应,道家思想备受青睐。扬雄《解嘲》曰:“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默,守德之宅。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20](P191)典出《老子》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王弼注:“以虚静观其反复。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27](P35)万物并作,当以虚静观之。扬雄发展了老子的致虚守静思想,玄默自守,静观世事变化,优游于道德之境。他的《太玄赋》也说:“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20](P138)越演越烈的外戚政治不但造成赋家思想的内转,也让他们在观察外在世界时,更为清醒与深刻。老子、扬雄式的守静观世,使得赋家逐渐认清社会现实,并在两汉之际,掀起了一股反思之风,尤以对天命、王命的反思与礼制社会的建构最为明显。
三、天命与王命:赋家对外戚政治的反思与自赎
王命与天命乃一个问题的两面,天授之于王为“天命”,王得之则为“王命”,二者都笼罩在西汉后期的儒学话语之中。福柯说:“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权力的眼睛》)杰拉德认为福柯意在表明:“现代性完全是规训性的,主体注定摆脱不了话语,也因此无法摆脱权力。”[28](P204)胡学常将这种话语机制运用到汉赋阐释中:“汉赋话语与经学话语乃是同步发生……经学权力赋予汉赋话语以价值,倘若想要保持这种价值,则汉赋话语务必心甘情愿地置身于这种合乎经义的合法性规范之下,处于经学权力网络的绝对控制之下。”[29](P32)他指出了经学权力对于赋学的重要意义。
自武帝独尊儒术至元、成时期儒生政治确立,经学话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忠君又是其核心。然而当王莽篡汉之时,士人群体砥砺名节、奋争高蹈者却并不多见。顾炎武《日知录》云:“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30](P752)所谓“大义”,即君臣大义。从这一现象至少透漏出三个问题:第一,外戚政治割裂或者淡化了君主与士人的关系,导致与专制皇权紧密结合的经学权力实现受阻。第二,西汉后期的经学话语并非仅仅忠君这么简单,而是涵纳了诸如五行终始说与灾异祥瑞思想等异质文化,儒生心中有一个比忠于现实君主更为高远、持久的政治理想。王莽充分利用这种政治理想,通过复古以革新,引导了人心思变的社会趋势。第三,影响儒生行为的并非只有经学权力,两汉之际外戚政治的黑暗、士人生存状态的恶劣,促使道家话语复归,隐遁思想、避祸态度具备相当规模,儒道并重成为当时流行的思想模式。
以上三点,在汉、新易代之际,尤以日益严密的五行学说以及大量出现的符命、谶纬为重要。谶纬起于哀、平,张衡、刘勰、孔颖达、顾颉刚诸家皆有明论。王夫之《读通鉴论》曰:“宣元之季,士大夫以鄙夫之心,挟儒术以饰其贪玩。故莽自以为周公,则周公矣;自以为舜,则舜矣……而且经术之变,溢为五行灾祥之说。”[31](P122)王莽以周公自居,以恢复儒家传统为己任,士人闻风响应。他又利用刘歆等人的“五行相生”说替代“五行相克”说,为皇位禅让作准备。依照这种学说,汉承尧后为火德,王莽为舜后得土德,由火生土,因此由新代汉是天命所归。《汉书·王莽传》中献符瑞者比比皆是,反映到文学中,便是扬雄名作《剧秦美新》。
《美新》历来颇受非议。徐师曾评之曰“遗秽”(《文体明辨序说》),张溥目之为“谀文”(《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所论皆有失公允。扬雄此作有其现实基础,是对王莽新政的真实反映[32]。吕思勉《秦汉史》:“新莽之所行,盖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其成其败,其责皆当由抱此等见解者共负之,非莽一人所能尸其功罪也。”[26](P174-175)阎步克也认为汉儒一直在寻找一种纯正的“王道”,而王莽改革正是这股力量发展的结果[33](P385)。今观《美新》列举秦政、汉政、新政三种政治模式,批评秦政暴虐,以为汉政对秦政有所因袭:“帝典阙而不补,王纲弛而未张。道极数殚,闇忽不还。”而将王莽“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胤殷、周之失业,绍唐、虞之绝风”作为理想政治的代表,从政治上的优越性来论证王莽“受命于天”。《美新》运用了大量符命对王莽政权的合法性加以论证:“逮至大新受命,上帝还资,后土顾怀,玄符灵契,黄瑞涌出。”[4](P2152)此后,对符命的书写与重构,构成了扬雄以后赋家对外戚政治的第一重反思:谁能获得天命?
两汉之际天下逐鹿,争夺天命至关重要。公孙述相信“帝王有命”,又听取李熊“天命无常,百姓与能”[34](P535)的观点,大肆渲染祥瑞、符命,以至于光武专门投书辩论,可见在王莽营造的神学氛围里,社会心理皆被天命营造所控制。班彪之所以作《王命论》便是“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文中说:“刘氏承尧之祚……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3](P4208)班彪从汉承尧后、火德赤符、累世积业、应天顺民诸方面,论证汉德之盛,几乎可以作为光武中兴的理论总纲,也搭建了后世赋家思考“王命”的总框架。杜笃《论都赋》:“天命有圣,托之大汉。大汉开基,高祖有勋。斩白蛇,屯黑云。蹈沧海,跨昆仑。”[35](P1102)以为天命选择了高祖。崔骃《反都赋》:“汉历中绝,京师为墟。光武受命,始迁洛都。”[35](P1102)则说光武接受了天命。无论是建国,还是迁都,都是天命所归。班固《典引》更是盛赞汉德:“矧夫赫赫圣汉,巍巍唐基,泝测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后宣二祖之重光,袭四宗之缉熙。”[4](P2162)在天命书写之外,《典引》承续《长杨赋》,对祖宗之德大加赞扬。至《东都赋》,对王莽的清算与对东汉的颂扬均达到新的高度:“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乃致命乎圣皇。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应若兴云。”[4](P29-30)赋文以王莽之乱与光武之治作对比,以明天命所在,王莽之废乃是“天人致诛”,光武之立则是“继天而作”。正是这种对比延伸到赋家对外戚政治的第二重反思:王莽因何失败?
王莽以外戚身份夺权而失败,受到正统史家严厉斥责。《汉书·王莽传赞》将之比于“桀、纣”,而“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3](P4194)!班固所论带有政治偏见,所言空洞,未中肯綮。相对而言,乃父班彪的论述较为细致:“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外内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而同辞。”[3](P4207)他指出王氏之所以能代汉,是凭借其外戚身份,由上而下以禅让的形式取得政权,并未伤及万民;而王莽之所以失败,思汉之风之所以重起,也是因为王莽自据高位,未能施恩于民,自固于下。“不根于民”之论,与桓谭《新论》“失百姓心”[36](P9)的说法相似。《新论》又曰:“王翁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致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36](P13)桓谭亲历莽世,所论更为公允。王莽一心效古,而不切实际,更兼不择将、重刑、虐死诸弊,所以败灭。
两汉之际,士人备尝乱离,充满矛盾与彷徨。班彪《北征赋》对大汉流连再三,高呼“惟太宗之荡荡兮,岂曩秦之所图”[4](P429),拥有浓烈的情感倾向与尖锐的政治见解。浦铣评此赋“妙在有议论,有断制”[37](P401)。在东汉初年赋作中,王莽篡汉、汉历中绝乃是普遍的集体记忆,多数赋作将之作为东汉创建的背景,如傅毅《洛都赋》“世祖受命而弭乱”[35](P1103)。至张衡《东京赋》,对王莽篡汉的惨痛记忆尚未止息:“巨猾间舋,窃弄神器。历载三六,偷安天位。于时蒸民,罔敢或贰。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龙飞白水,凤翔参墟。”张衡比前人客观的地方在于,他认识到王莽统治的威重,百姓不敢叛离。李善曰:“言是时众民无敢有二心于莽者。”并释光武之“忿”曰:“疾王莽威重如此也。”[4](P101-102)东汉赋中的王莽更多地是作为大汉盛德的反面铺垫,尚未触及外戚政治的根本,也就使得这些反思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固然是由于辞赋体裁所限,同时也与东汉赋家以颂扬为主的基调有关。对王莽的大力批判,隐含着东汉赋家的第三重思考:何为美政?
社会环境主宰了个人生存状态,加之士风柔惰,使得一代士人步履维艰、深蒙困苦,崔篆《慰志赋》便反映了赋家在两汉之际艰难的人生选择。赋中一面痛陈:“六柄制于家门兮,王纲漼以陵迟。黎、共奋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睹嫚臧而乘釁兮,窃神器之万机。”将王莽夺权定性为“窃”。一面赞扬:“皇再命而绍恤兮,乃云眷乎建武。运欃枪以电扫兮,清六合之土宇。圣德滂以横被兮,黎庶恺以鼓舞。”[34](P1705-1706)以汉再受命作为论述根本,而将光武圣德作为叙述重点。思汉叙述是当时赋家自我救赎的重要方式,他们反复申说汉德,大力赞扬新建立的东汉王朝,将之作为美政的代表。
处于光武朝的冯衍、崔篆、班彪等人曾陷入易代纷扰之中,虽大力赞美东汉王朝,却未能真正融入当时的社会秩序。后来杜笃论西都之优,仍是站在西汉王朝的立场发表意见,缺少反思、内省之意。到明、章之后,东汉立国日见规模,大量礼乐造作活动鼓舞士心,王莽之祸逐渐淡化,成为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同时,东汉王朝吸纳了王莽改制的部分内容,构建起更具有可行性的礼制社会。此时新一代赋家班固、傅毅、崔骃之流,皆拥有生逢盛世的自豪感。《论衡·须颂》所言最为明晰:“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38](P855)班固之颂国德并非如其前辈单单强调天命所归,也不是像他的同僚崔骃在《达旨》中笼统描述治世,而是如其《两都赋序》所言:“极众人之眩曜,折以今之法度。”[4](P3)而法度又集中体现在《东都赋》对永平之治的铺陈上,班固依次叙述巡狩、蒐狩、会盟等典礼,又叙述倡节俭、劝农桑等惠政,赋末言及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制,致力于揭示汉德所由。
班固的写法在《二京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艺文类聚》载张衡见班固《两都赋》“薄而陋之,故更造焉”[35](P1098),这是有意与之争胜,其礼制描述也确实更胜一筹。比如张衡在描写宫殿时说:“奢未及侈,俭而不陋,规遵王度,动中得趣。于是观礼,礼举仪具。经始勿亟,成之不日。犹谓为之者劳,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4](P105-106)比之班固“奢不可踰,俭不能侈”[4](P32)的八字概括,更为详尽。张衡对朝觐、郊祀、籍田、大射、大傩、巡行等诸般礼制皆极力铺排,且注重顺天法道,各种典礼描写均与帝国典制及阴阳哲学相合。《东京赋》末西京客感叹“而今而后,乃知大汉之德馨,咸在于此”[4](P134),透漏出张衡此赋的创作宗旨,是对汉德的颂扬,也是对社会新秩序的建构。西京客的恍然大悟,标志着东汉士人彻底走出了西汉败亡、王莽篡政的阴影。值得注意的是,张衡描绘以明、章盛世为代表的汉德,又是从新的历史语境出发,而以回忆的姿态展开,在构筑大汉图景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盛世的失落与消沉。属于东汉的末世即将来临,盛衰兴亡的悖论在大赋叙述之中展露无遗。
反思的三个层面,由瓦解到建构,由反思到自赎,反映了两汉之际赋家面对政治危机所做的种种努力。外戚政治打破了稳固的统治秩序,赋家便利用儒家话语,逐渐建构起新的评价标准与理想范式,通过比较亡秦、西汉、新莽、东汉四个不同的政权,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政治经验,而最终在大汉继周的叙述中,归复到儒生理想中的礼制社会,将国家各项政治纳入合乎礼仪的轨道之中。
结语
代行王政与代行王言之别,根植于王朝官僚体系的设置与内在运转机制,是外戚与赋家之间不可调和的一组矛盾。随着西汉后期外戚政治愈演愈烈,以至政权更迭,赋家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政治失意与个人生存危机迫使赋家远离朝廷,改变了围绕朝廷重大题材书写的习惯,述行赋产生、骚赋复归、赋写玄思等赋学现象皆与之有关。儒学话语是两汉之际赋家书写外戚政治所依凭的重要理论工具,他们反复思索天命与王命的命题,无论是扬雄的《美新》,还是东汉赋作中充满张力的新、汉对比,都是为了争夺统治的合法性。东汉赋家反思王莽之乱,分为多个层次、多个阶段,从冯衍、崔篆等努力融入新王朝,到班固、崔骃、傅毅等利用新、汉对比来颂汉德,再到张衡《二京赋》利用王朝礼制建设完全战胜王莽政权,前代外戚政治遗留的惨痛经历似乎已经得到清理。然自章帝起,东汉社会又形成了新的外戚政治,章、和之际女主临朝、将军辅政的局面重又出现,并成为皇位更迭时的常态,后来随着宦官干政的掺入,社会局势进一步混乱。东汉中期以后,皇权、外戚、宦官、士人、宗室等各种社会力量进行角逐,又对东汉文士的生存与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