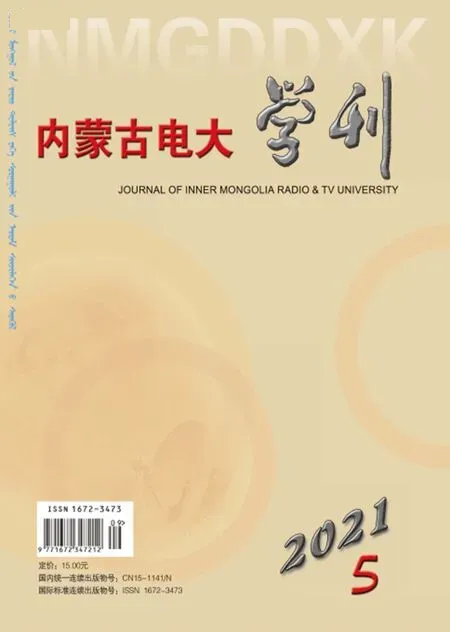“一带一路”视阈下草原文学创作的文化自觉
李俊红
(内蒙古河套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 巴彦淖尔 015000)
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文艺座谈会时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草原文学处在新时代的世界语境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纵深和世界加快交流融合变化的大格局之中,讲述精彩草原故事、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展示自身的独特个性。“加强与国内外各民族文学的交流交融、相互激发、学习借鉴,是草原文学发展道路中的必然选择,也是草原文学作家实现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1]
早在1997年,费孝通先生就提出“文化自觉”概念,从对“根”的找寻与继承上、对“真”的批判与发展上、对发展趋向的规律把握与持续指引上,深刻阐述了文化自觉的内涵。他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实现文化自觉的精练概括。费孝通先生强调:“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2]
为适应全国文化蓬勃发展的大势,草原文化在党委政府支持下,作家们面对波澜壮阔的生活创作出大量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学精品,让新时代的草原文学焕发出新的活力,这些作品引领草原文学快速发展,在国内外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真正在多元文化的世界文学里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草原文学作家的创作,基于对文化地位作用有深刻全面的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有坚定正确的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的进程有时代担当。面对时代的课题,草原和草原上生活的人们一直都在密切关注和融入时代的发展变化,他们在不断地抉择、适应和创新。
一、在“根”的继续找寻中折射出民族文化的自信和对传统的热爱和继承
新中国成立以来,草原文学经历了从萌发到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草原文学作家群形成、发展、壮大和趋向成熟的过程。历代草原作家们都以繁荣发展草原文学为己任,通过自己的作品将草原的面貌、草原的生活、草原上的人们、草原上的牛羊和草原上的万物百态展现给读者。老一代的文学家纳·赛音朝克图、周戈、云照光、巴·布林贝赫、额尔敦陶克陶、曹都毕力格、宝音达来、超克图纳仁、朋斯克、杜古尔苏荣等人的文学作品,如:《沙原,我的故乡》《挺立起来的农民》《像泉水般涌出的欢乐》《血案》《鱼水情》《圆圆的山峰》《牧民之歌》《七月一日》《蒙古杏花》《国旗颂》《爱国妇女白依玛》《翻身后的两位老人》等讴歌党、讴歌新中国、讴歌草原新生活,抒发强烈的时代和革命精神,散发着浓郁芬芳的草原气息。玛拉沁夫、扎拉嘎胡、安柯钦夫、敖德斯尔、照日格巴图、钢普日布、其木德道尔吉、哈·丹碧扎拉桑、斯仁道尔吉等一批草原文学作家更是将具有新颖 “草原风味”的作品奉献给了广大读者。
跨入新世纪,在广袤草原沃土的滋养下,草原文学在艺术和创作的探索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批中青年作家和新草原文学作品先后涌现。影响力和文学品味都有了更大的提升。比如萨仁托娅创作了长篇小说《静静的艾敏河》和长篇纪实文学《草原之子廷·巴特尔》,这两部作品获得2003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萨娜的中短篇小说集《你脸上有把刀》荣获了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包丽英的长篇小说《纵马天下——我的祖先成吉思汗》荣获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此外,一大批诗歌、散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比如长篇历史散文《蒙古密码》 (特·官布扎布)、诗集《九十九只黑山羊》 (博·宝音贺什格)、 诗集《白云的故乡》 (阿古拉泰)、散文集《裂痕》 (乌仁高娃)等。
纵观草原文学的创作成果,其表现手法一般都是对草原、蓝天、白云进行景观化的书写,对草原轰轰烈烈的生活进行图像化的叙述。在草原文学民族性的“根”的深入挖掘和展示方面略显不足。而近年来新涌现出来的一些文学作品则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细腻,在创新中注重传统,在创新中突破传统,显现出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和充分热爱。[3]
2017年蒙古族作家刘利华的长篇巨著《长生天》问世,这部文学力作一经发表便引起读者的巨大反响。相比较以前的文学作品,这部小说更具有蒙古民族的民俗性和对原生态传统的广泛挖掘。具体表现为投入大量笔墨正面或侧面描写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思维模式,以及口口相传的口头文学、独具蒙古民族智慧的民间技艺、传统技艺。“这些传统浸润于蒙古民族的血脉之中,虽经历几十代人生活的更迭,依然在他们精神家园里息息相通,是蒙古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民族魂魄。”[4]P89
《长生天》对蒙古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的叙述描写非常细腻,把蒙古人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婚丧嫁娶、战争祭祀的场景描写得生动形象、细致入微,给人以面对面交谈娓娓道来的感觉,这些细节的描写恰是作者对民族生活的深入了解和对民族传统的深沉爱意的体现。不是蒙古民族的作家写不出来,没有对蒙古民族文化和历史有透彻地了解也不能完全品味到其中浓浓的意蕴。《长生天》使用了大量蒙古谚语和民歌来表达蒙古族口头文学的生动性。书中大量使用 “人要心强,树要皮硬”“与其流泪,莫如攥拳”“男子汉岂能无名而死”等蒙古族古谚语和民歌歌词。还有许多充满民族特色的语言,比如“眼里有火,骨头里有精髓” “断了腿也要爬,烂了脖子也要拉”等,用踩烂多少张骆驼皮来形容人数的多少,以草的枯荣表示时间的年轮,以及哈敦、安答、舌头、伴当、黑骨头等等独特的民族语言。有些甚至是抢救和挖掘整理出来的,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表达和场景的再现,使得这些民族文化中极具韵味的语言为读者知悉并重新流传。
2019年1月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蒙古铁蹄马》是蒙古族作家天热创作的一部力作,是近年来草原文学创作的优秀成果之一,作为内蒙古作协“草原文学重点创作工程”的重点项目被推出。与《长生天》的创作理念极其相似,小说同样大量使用和展现了蒙古民族在草原游牧生活中的日常交流语言,频繁使用蒙古民间传统的谚语、警句以及蒙古民歌中诗一样的语句,“散发着奶酪香味的文学语言,色彩浓郁,回味悠长,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5]
二、在“真”的不懈追求中展示出坚强的民族性格和对真善美一如既往的向往
草原文学作家们徜徉于广袤无垠的草原,深情回望与草原一路走来的金戈铁马的流金岁月,怀着对人间一切美好事物的无限向往,发自内心为出身于这个民族而感到自豪。他们自豪于祖先开疆拓土创造的丰功伟绩;自豪于历代先贤建立政权、治国理政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自豪于在游牧生活中长期形成的豁达乐观、粗犷豪爽、大步行走、高声歌唱、大碗饮酒、大块吃肉的风俗民情;自豪于敬畏自然、顺应规律,尊崇草原、热爱大地的悠悠牧歌般的自在生活;自豪于优秀儿女不畏牺牲,奋力为完成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的铿锵足迹;更自豪于一次次风云际会的历史进程中与汉民族和其他民族融合交流,与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书写中华民族的辉煌和灿烂。
草原文学所秉持的 “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创作理念,成为草原作家们源源不断的创作力量和源泉。 他们用文学照亮历史,对英雄深情歌颂,表现出昂扬向上的民族的精神风貌和审美追求。[6]比如冯苓植的《元史演绎系列》,包丽英的《纵马天下》《蒙古帝国》,萨仁托娅的《静静的艾敏河》和《国家的孩子》,阿云嘎的《满巴扎仓》,满全的《飞鸟集——一段天边的浪漫故事》等等。
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题材也是当前草原文学创作的重点。70后作家赵耀东的长篇小说《寻仇记》以抗日战争为创作背景,以哥哥寻找失散的弟弟为情节主线,叙述了他们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在国难深重的战争岁月里人生道路的选择。“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作品《远去的战马》讲述了草原上一支优秀的骑兵部队,历经伪满时期自发抗战,到抗战胜利后接受共产党的改编,成为一支不畏牺牲、英勇杀敌的解放军骑兵部队,参加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远去的战马》成功塑造了一批蒙古族骑兵勇士的生动鲜明的形象,他们热爱草原、尊重自然、信守诺言、忠诚国家、珍惜友情,读来让人感慨万千、荡气回肠,是草原文学弘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优秀代表作品。《蒙古铁蹄马》描写中日甲午海战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此背景下,蒙古族弘吉剌部所发生的以马为主线的跌宕起伏的故事。小说反映了中国积贫积弱特定历史时期蒙古高原的政治风云变幻和蒙古民族为民族解放和人类正义事业不怕牺牲、奋起抗争的坚强民族性格。达斡尔族女作家鄂阿娜的长篇小说《以父之名》是草原文学民族解放题材的又一力作,小说巧妙地以达斡尔族母语的表达方式,充满激情和感染力,讲述了达斡尔族青年讷克宝的故事。小说对达斡尔民族的族源、历史、宗教信仰都有详尽的描述,对达斡尔人在西伯利亚等地与沙皇俄国的不息抗争、浴血奋战的光辉事迹,以及在乾隆年间被西迁戍边,保家卫国都进行了追溯和描写,凸显出了达斡尔族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和英勇顽强、热爱祖国的民族特质。
立足于“真”,对英雄人物客观全面地刻画也是新时期草原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比如《长生天》不仅塑造了成吉思汗坚如磐石的顽强意志、海纳百川的恢宏性格、揽天下人才为我所用的宏大气魄,塑造了他能正确处理恩怨,有理有节、有情有义、张弛有度的一代领袖风范。而且在正面描写之外,也不隐讳他杀弟、气母、疑子的人物性格,这使成吉思汗的个性更加立体化,表现出了人物的真实。
三、在时代大潮中坚持清醒独立的思考和义无反顾的时代担当
草原文学写作的基本取向是草原生存状态变化的直接反映,也是作家价值观和审美观的直接体现。进入21世纪以来,草原文学的创作不仅仅局限在对草原、蓝天、白云及悠适生活的描写,更多的是跟随草原日新月异变化的现实,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对人与自然、对草原未来的思索和凝视是当代草原作家关注的重点,几乎每一部草原文学作品都和读者在互动思考草原与自然生态的问题,并将保护他们心中神圣的家园作为义不容辞的职责。张秉毅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装点此河山——鄂尔多斯生态报告》记叙了鄂尔多斯草原历史上的生态变迁,详尽总结了新时期以来草原恢复生态的显著成就。从这部书中,我们感受到了曾经美丽的草原,也感受到了人类开发破坏导致草原千疮百孔,用一张张强烈对比的画面表现出人类所付出的惨重代价。面对这样的草原,草原上蒙汉各族儿女主动担当起草原生态回黄转绿的时代使命,最终实现了家园绿色梦。 高朵芬的长篇诗集《一抹蓝》是“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的一部重点作品。诗集以广阔的内蒙古高原为创作背景,作者从哲学思考的角度细腻描摹了内蒙古高原人与自然相依共存、和谐共生的关系,通过抒写民族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自然地理,彰显内蒙古高原上的人们崇尚自然、崇尚文明的人文情怀。生于内蒙古科尔沁的蒙古族作家郭雪波在当下生态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他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日益恶化的草原生态,他的创作过程是一种很有使命感的深度写作。不断定位、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的《大漠魂》《狼孩》《沙狐》《银狐》等十余部作品对草原生态恶化的根源进行了多维度表现和反思,赋予了人与自然的社会内涵和生存哲学的阐释,这些作品从灵魂深处叩问人类生存的基本价值,透过草原生态日益恶化的现象探究其根本,从而唤醒人们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意识。
除了文学作家的呼吁与关注之外,学术界对于当代草原文学的生态担当和研究也一直在持续,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比如渠成成的《新时期草原小说的生态意识研究》、坎钦道尔吉的《生态文化视阈中的“草原文学”——谈新世纪“草原文学”之一种可能》等等,都对当代草原文学生态主题的写作给予了全面的梳理和研究,草原作家从文学创作的学术和理论层面对书写生态给予支持。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草原文学加强与域外民族文学的交流,以草原文化的开放、进取与包容孕育的文化自信,建设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草原文学,积极参与世界文学对话也是草原作家的创作自觉。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理德曼写了一本书《世界是平的》,他认为互联网等新的信息科技,产生全球化的新的趋平化时代。它有更大的潜能促发文化的“差异性”与“多元性”,多元的地方(民族)文化会越来越全球化。[7]草原文学与中原文学一方面具有原生性与独立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体现出互动发展,具有融合性和共生性的特点,作为一种文学形态,这种融合性和多元化正是草原文学进行自我丰富的一种必要元素。草原文学也一直处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和场域中,身处世界格局变化之中,草原文学的作家们和世界其他民族的作家一样,既书写着民族性的文学作品,也书写着世界性的文学作品,既要讲好草原故事,也要讲好世界故事。
80后蒙古族作家萨娜致力于研究“阅读透视多样文化”探讨中外文化交流,领略民族文学魅力,她的小说《彳亍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内蒙古中生代作家海勒根那的《到哪儿去,黑马》《父亲鱼游而去》《骑马周游世界》《一只羊》等作品,对处在剧烈变动时代下的草原给予了密切关注,在多重文明与文化的场域中寻找自我。这些作品揭示的人与自身、人与人的关系,引起国内外众多读者的关注。另外艾平、鲍尔吉·原野等散文作家善于用广角和长镜头来描述人与草原、人与草原上万物的关系,进而上升为人与自然的哲学思考,这些文学作品都在人类互融互通的交流背景下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