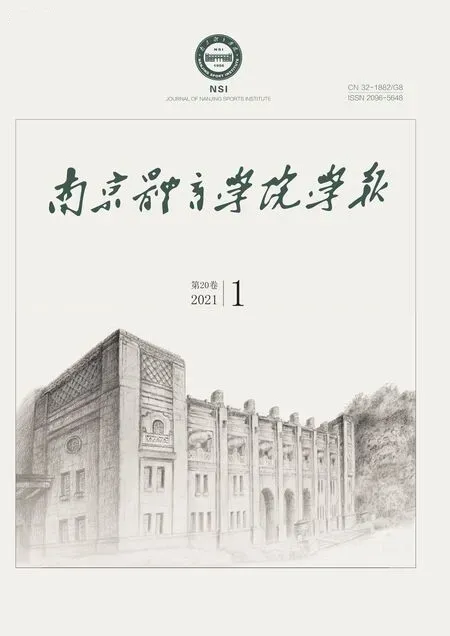新中国体育电影的发展、突破与文化建构
赵 聪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433)
如同艺术一样,体育也是人类跨国界、跨语言、跨种族自由沟通的一种重要方式。体育电影是电影艺术对体育题材的表现形式,以体育为媒介对国家精神、民族意识和个人意志的弘扬与传播,将体育精神与国家、种族、社会等宏大主题融于一体,赋予电影作品以最为广泛的普世价值,进而对观众产生强烈激励作用。体育事业作为20世纪国家发展的重要内容,为体育电影创作提供了支持,为其类型化发展做了充分准备。20 世纪70 年代之后,美国体育事业迅猛发展,带来了体育电影创作热潮,在随后的几十年,好莱坞推出了多部产生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推动了体育电影类型化发展,并使之成为奥斯卡奖项关注的重要题材。随着世界电影新浪潮从欧美走向亚洲,印度、日本、中国、韩国等国均加大对该题材的挖掘,尤其是2016年上映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2019年上映的俄罗斯电影《绝杀慕尼黑》,再次激发起观众对体育电影的关注。
在世界电影的影响下,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体育电影涌现了《水上春秋》《女篮五号》《沙鸥》《少林足球》《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攀登者》等优秀作品,塑造了大批体育人物形象,反映不同时代社会责任和体育人的自我追求,既努力与世界电影并轨,又清晰展示了中国体育电影的民族特质。但与诸多获得奥斯卡奖的体育电影相比,其艺术性还有待于提高,尤其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的统领下,电影艺术应如何通过体育题材建构民族主体性、建构新时代民族意志和国家精神,亟待电影人的反思和创作上的突围。
1 作为类型片的体育电影
世界电影发展初期,首先展示的是电影的记录功能。美国的贝奥格拉夫(又译为比沃格拉夫)电影公司采用早期电影拍摄方法拍摄了本地体育队的画面,用于吸引当地的电影观众[1]。20 世纪20、30 年代,体育题材广泛进入美国电影;1931 年,获得第五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最佳原创故事奖的《舐犊情深》首开拳击电影先河,讲述了一个比赛失利后沉迷于赌博和狂欢的前重量级拳击冠军在7岁儿子亲情的感召下重整旗鼓的故事,故事将拳击融于人性的温暖与信任,深深打动了观众。但这一时期的体育电影并没有和黑帮片、战争片、歌舞片、喜剧片、恐怖片、西部片一样成为重要的电影类型。
1961 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就任青年健康委员会主席,并在《运动》杂志上发表著名文章《软弱的美国人》,文章指出,鼓励民众参加体育活动并提高他们的体质水平永远是美国的基本政策[2],同时随着美国消除黑人歧视的政策化导向、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世界政治在体育赛事上角逐、电视媒体开始大量地进行体育赛事和体育节目的播出等,多种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了美国体育竞技(专业和业余)的全面兴盛,为美国体育电影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20世纪70 年代,美国的体育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和电影艺术不断创新的内在要求共同为体育电影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电影人开始着力打造具有时代精神的体育电影明星,通过明星传播体育精神,塑造新的国家形象。同时,种族斗争、阶级冲突、民众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命运的反抗等重要的文化主题也与体育题材深度融合,从而使该题材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1976年,以草根拳手为主题拍摄的《洛奇》,以100万美元的成本,取得了2.25 亿美元的票房,在美国引发了体育电影热、拳击运动热。1979 年,同样以拳击为题材拍摄的《愤怒的公牛》再次获得世界电影的认可,与《洛奇》一起至今被视为全球体育影视作品的巅峰之作。影片强烈的体育精神感召了大批怀揣梦想的美国青年人投身到拳击事业、体育事业,让美国在20 世纪80、90年代的体育事业和体育电影均进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美式橄榄球、冰球、拳击等高强度的运动项目是美国体育电影的主体项目,也成为电影关注和反映的主要内容,先后出现了《最长的一码》(橄榄球)、《光辉岁月》(橄榄球)、《冰上奇迹》(冰球)、《百万金臂》(棒球)等一大批优秀体育电影,也精彩呈现并促进了美国人在竞争对抗的体育运动中表现出的强烈的冒险意识和勇于追求梦想的共同性格特征和文化特质,同时,使体育电影成为名副其实的类型片。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美国体育电影承袭前一时期的主题和风格,进一步挖掘体育故事、体育精神,通过好莱坞精心制作予以呈现,如《心灵投手》(2002,棒球)、《奔腾年代》(2003,赛马)、《弱点》(2009,橄榄球)、《点球成金》《我,花样女王》(2018,花样滑冰)、《奎迪:英雄再起》(2019,拳击)等影片,继承好莱坞电影固有的经典叙事风格,同时进一步融入白人与黑人的种族问题、面临现实与梦想之间巨大差距时的勇敢选择、敢于挑战传统偏见、坚持梦想永不服输、亲情与友情交织的梦想之路等,在社会冲突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人与社会的真善美。《弱点》中白人安妮·陶西跨越了黑白人种的障碍,看到了黑人孤儿奥赫身上闪光的品质,收留他、培养他、成就他,最后也成就了她自己,故事本身已经超越了常见的种族歧视,将这一主题上升为对美、善、尊严和价值的追求。《点球成金》中的比恩作为一名职业球队总经理,特立独行、敢于冒险、有个性、有思想,但同时又有他自身的弱点,不敢到赛场看球,不敢正视比赛,最终在助手的帮助下,他克服怯懦、勇于革新,实现了自我突破。在平凡的人身上发现可贵的品质,追求真正的平等、自由、美、善和勇敢,以之化解人类所有仇恨、争端和执念,从对抗走向和谐,从竞争、对抗、矛盾冲突上升为人类更高层面的情感需求,即爱、自由与平等,这是电影立意的根本性创新,更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
在美国体育电影的影响下,20 世纪90 年代以后,日本、印度影视作品均非常重视这一题材。日本出品了大量具有世界影响的体育题材电视动画,如《灌篮高手》《足球小将》《棒球英豪》等,虽然不是电影作品,但对体育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2002 年,印度体育电影《印度往事》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奖,同时被美国《时代》杂志列入25部杰出世界体育电影的名单。2016年,印度上映宝莱坞体育电影7 部,所涉及的体育项目包括摔跤、拳击、板球、曲棍球和马拉松,以摔跤为主题的《摔跤吧!爸爸》将国家荣誉、民族事业、个人理想与女性命运以及社会偏见、腐败现实相互融汇,严肃思考了女性命运,通过电影展示、思考社会广泛存在的女性社会问题。2017 年上映的俄罗斯电影《绝杀慕尼黑》以其独特的电影结构,利用大篇幅完整展示了整个比赛所有的得分情况,描述了当时苏联内部严重的政治问题、民族问题、社会问题,以及复杂的世界冷战格局与冲突,将教练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家庭之间的抉择、球员们在伤病与政治压力下的个体意识和团队精神等主题统摄于爱国主义、顽强拼博的体育精神的大主题之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像效果和社会影响。
这些作品与好莱坞作品交相辉映,使近年的体育电影成为持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艺术典型。
2 中国体育电影的发展与突破
在西方现代体育概念输入中国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多种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射箭、蹴鞠、马术、角力等,这些项目在古代分属于军事或娱乐项目。晚清时期,随着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侵入,体育作为西方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洋务运动的推动下,首先在学校和军队进行推广。洋务派的开拓者们首先在新式课程中引入西方体操以增强学员体质,在军队则表现为兵操。1895 年,北京的教会学校渐次开设棒球、网球、足球等西方现代体育项目课程,继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体操和篮球。至民国初期,北洋政府成立了较早的体育专科学校,并在亚洲各种运动会的推动下,中国体育开始与世界体育接轨。
20世纪是中国体育事业长足发展的时期。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军事长期处于劣势,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成为前半个世纪的政治主题,应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也因日本人对中国“东亚病夫”的歧视性称谓,这一时期的体育事业有一定的发展,但终因时局混乱、战争频发而受到较大限制。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国家体育事业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事业被纳入国家建设事业而载入国家根本大法,从法律上确认其重要性;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事业与中国经济腾飞相得益彰而得到快速发展,20 世纪末中国已成为体育大国。21世纪,习近平指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体育强国梦作为中国梦的一个重要方面,体育代表着青春、健康、活力,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坚定自信,奋力拼搏,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更好发挥举国体制作用,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提高其为国争光能力,让体育为社会提供强大正能量。经过70多年的努力,新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体育电影也成为新中国电影的重要拍摄题材,先后有130 多部体育电影被推出,涉及排球、篮球、足球、田径、体操、摔跤、游泳、跳水、滑冰、武术、帆船、赛车等多个项目。这些作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展现了不同时期中国的时代风貌、社会特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强烈的艺术性,是坚持社会主义创作原则的重要作品。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新中国各个领域的管理都更加突出政治性和阶级性,文艺界也不例外。刚刚起步的中国电影以开创新时代、新气象为创作导向,在政治性、阶级性和艺术性结合的基础上,重点突出政治性。1952 年6 月20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全面引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3]。在此背景下,1956年,《两个小足球队》首开新中国体育电影的先河,校园题材、足球主题、场景的时尚化、角色设置的多元化以及独具民族特色的歌舞元素,均使该片洋溢着青春之光、时尚之美。1957 年,谢晋执导的影片《女篮五号》是国内第一部体育题材彩色故事片,虽然艺术性略显稚气,但人物、台词具有清晰的时代感,蓬勃青春激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1959年,新中国十周年献礼作品《冰上姐妹》和《水上春秋》均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切实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十年间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体育人才的全面培养。《水上春秋》无论是在政治性还是艺术性上都有更好表现,故事生动,人物鲜活,在新旧中国体育事业的对照中突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以及两代体育人为国争光的理想追求,加之拍摄剪辑技术提高、人物对话生动、叙事结构巧妙,该片较同时期作品更具艺术创新性。但从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中国体育电影存在着主题单一、政治说教色彩浓重、演员动作程式化、镜语陈旧呆板、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等问题。
20 世纪70 年代末至80 年代末,中国开始从创伤中走向全面恢复,体育电影在体育事业的恢复中开始探索新的方向。《乳飞燕》(1979,体操)、《排球之花》(1980)、《沙鸥》(1981,排球)、《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1,围棋)、《高中锋,矮教练》(篮球,1985)、《帆板姑娘》(1985,帆板)等,立足于新时期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以强烈的爱国主义、艰苦奋斗、决不放弃的体育精神为主要表现内容,展示了时代、命运、人生的坎坷和体育人对中国体育事业的信心及坚守。具有代表性的电影《沙鸥》突破之前体育电影,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冲突的僵化设置,而是以悲剧形式反映了十年动乱给个人、国家带来的灾难性创伤,大量使用长镜头拍摄,以纪实性手法追求和表现艺术真实。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拍摄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是中日复交后联合摄制的第一部影片。影片真实地反映了日本侵华战争影响下中日两个家庭30 年历史变迁和沧桑命运,强烈的悲剧性增加了电影的艺术性。这些基于对历史伤痕的文化反思在主题上有所深化,艺术性也有所加强,政治说教色彩有所减弱,电影程式化痕迹依然存在,尤其是赛事设置简单化,故事重于赛事的主观处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破坏了叙事真实性。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腾飞,消费主义思潮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社会思潮,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有学者对消费自由做出了解释:“从理论上讲,只要有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就可以消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消费者与生产者比较起来处于主导地位。这种主导性表现在生产者的生产行为要依照消费者的喜好来进行,而消费者喜好的主要判断标准就是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从后果上看,消费主义倡导的个人消费自由无疑会给社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奢侈消费、竞争消费、符号消费等无止境的消费行为给整个人类发展带来了道德、社会和环境问题。”[4]这一时期的影视作品均渗透着消费主义的感性形象,以隐蔽的形式掩盖了阶级性,在追求艺术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消费主义特征。1990 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了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第11届亚运会,盛大赛事激发了中国民众的体育热情,也激发了体育电影人的创作热情。《千里寻梦》(1991,田径)以新的时代为背景,将故事设置为大陆和香港两地,为体育题材添加了绑匪、枪战、私生女等商业元素。以20 世纪90年代中期的北京为背景,《赢家》并没有将重点放在残疾人运动员的职业生涯,而是更多地关注他们作为一个都市平凡人的情感世界,在人逐渐被“物化”的时代背景中,赞扬爱情和男性的阳刚之美,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对社会文化的反思。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通常被称为“奥运时代”,突出了奥运主题对这十年体育电影创作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以奥运为契机的体育电影在2007—2009 年形成了创作热潮。自2000 年至2010 年,电影人共创作了35部不同主题的体育电影,集中为2007 年7 部,2008 年11 部,涉及篮球、足球、排球、滑冰、游泳、羽毛球、武术等多个体育项目,也涌现出《女帅男兵》《女足九号》《少林足球》《闪光的羽毛》《大灌篮》《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破冰》等优秀作品。《女帅男兵》(2000,篮球)试图对类型电影进行大胆尝试,《少林足球》也充分地融入商业元素,延续了周星驰电影一贯的喜剧风格,幽默搞笑中加入精彩的武打情节,以爱和梦想为主题,以“功夫+体育”的独特表现形式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效果,成为该类型的一个经典。之后,《大灌篮》无疑是对《少林足球》“体育+功夫”模式的借鉴,虽然票房和口碑上并没有出色表现,但该作品抓住了观众的内在需求,以周杰伦的高人气加上功夫绝学和竞技体育的完美结合,以极具美学的画面冲击了电影市场。这一时期的体育电影开始走出宏大的国家政治叙事和集体主义精神,关注个体、关注生命价值,这一重大转向明显受到整个文化研究的影响,也是21世纪中国电影逐渐摆脱商业炒作回归艺术本体的表现。
艺术回归这一命题在2011—2020年间的体育电影中有了更为深刻的表现。在这十年里,体育电影创作总量达到51部,为历史之最。《极速天使》《翻滚吧!阿信》《许海峰的枪》《激战》《破风》《我是马布里》《飞驰人生》《羞羞的铁拳》等作品从技术、主题、叙事、结构、画面等方面形成新的突破,由《夺冠》《攀登者》《李娜》《中国女排》等作品将对个体的尊重和对民族利益的尊重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新的叙事风格。《极速天使》《翻滚吧!阿信》两部同年上映的小成本电影,虽然叙事不够流畅,故事逻辑性不足,但前者对极速运动高超的拍摄技术和后者的画面美感都极具欣赏性。《许海峰的枪》《李娜》《攀登者》都是以著名的体育明星、真实事件为拍摄对象,讲述他们的个人追求、坎坷职业道路和爱国主义情怀。《我是马布里》也属同类作品,讲述一个外国籍球员对中国的深厚情感。《夺冠》作为《我和我的祖国》中的一个小故事,通过一个平凡的孩子讲述了民众对祖国的深情。这是中国体育电影的一个重大变化,从宏大的国家叙事转向对个体的关注,从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到突出刻画运动员平凡而伟大的自我追求、战胜命运、挑战困难的勇气和毅力,从重要历史人物转向平凡的人民群众,这种转向既反映出中国电影的重大变化,也反映出社会整体文化的导向性变化。此外,电影人物立体化、格调丰富化、叙事主题化,都展现了新世纪中国体育电影的发展水平与实力。
我国电影业经过70多年的发展,中国体育电影以独特的角度和面貌表现着历史变迁和时代变化,电影的技术发展、人才培养、产业成熟、观众成长都在改变着电影的基本面貌。但是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中国体育电影无论是题材本身的挖掘还是类型化都没有在艺术审美的层面上表现出其独特价值,不仅体现在人物思想深度挖掘不够导致形象不够丰富,主题单一无变化导致观众对该题材没有观影期待,叙事不清晰导致故事逻辑的不合理,影响电影的艺术品质,对集体主义、荣誉、自我牺牲的过分强调,使作品与当下的大众审美相脱离,对具有民族品格的影像内容缺少表现从而失去民族性特征等问题,使中国体育电影仍然需要从目前的困境中突围和重建。
3 中国体育电影的文化建构
21 世纪,体育成为社会热词,国家层面的政策性支持,全媒体环境下中国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体育赛事的多角度、多层面报道与转播,数量更多、专业更强的观众,国家的富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自身健康的关注成为新的流行时尚,使中国电影逐渐摆脱消费主义思潮的负面影响。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开始重建中国电影文化审美体系,体育电影适应时代要求,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呈现国家精神、体现民族品质的作品更加刻不容缓。
3.1 体育电影的现代化发展
在整个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国电影无不以美国好莱坞电影为基本范式和发展模式,在美国电影的强力引导下走向电影现代化。中国电影也不例外,近一百年来的电影发展史,是中国民族电影全力创新发展的历史,也是向西方电影学习、借鉴、模仿的历史,电影语言、电影审美、电影技术与技巧、电影叙事、美国的制片厂制度、经典好莱坞电影风格、欧洲电影美学、苏联蒙太奇电影学派等,无不是电影人的学习手册。因此,中国电影的发展必然要以世界化、现代化发展为前提,追求世界电影共有的艺术内涵,挖掘具有世界性、现代性、人类普适性的电影主题,展示电影作为无国界艺术的本质特征,这既是体育电影的时代命题,也是中国电影的时代命题。
3.2 中国体育电影的民族性建构
中国电影自其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寻求民族、国家主体身份的认同[5],为世界电影奉献了诸多经典作品。但是,真正的民族化是开放的民族化、创造性的民族化,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特征的艺术形式、审美风格转变为世界艺术的民族化,是与世界电影交流的民族化,而不是故步自封、自我欣赏、自我冲锋的民族化,也不是为了取悦西方人的审美而丑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化,更不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置于西方社会环境中无所适从的民族化。日本电影之所以保持了非常好的民族性,是因为自诞生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电影都以时代剧(古装剧)为主要内容,而民众对于日本本土文化的喜爱也成为电影保持民族化特色的推动力。历经半个世纪,日本电影在黑泽明、沟口健二、小津安二郎以及动画制作大师手冢治虫、宫崎峻、大友克洋、押井守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创造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族化电影,尤其是武士片、艺伎片和动画片。与之相比,20 世纪中国文化系统多次受到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曾经整个社会的西化倾向以及对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摒弃和破坏,使我国民众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价值比较中出现了整体性的误判,导致中国电影民族化之路显得尤为艰难。
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极其丰厚,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东方哲学,独特而神奇的武术文化和武侠精神,从北方到南方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化,从西部沙漠的粗犷神秘到东部沿海都市的浪漫时尚,都有着强烈的中国气质和民族风格。电影作为塑造国家形象的艺术形式、传播民族文化的有效手段,始终以民族差异化成为国家文化传播的有力武器。美国的《花木兰》《功夫熊猫》使用了大量的中国元素,但这些中国符号并没有表达中国文化的意味,而是承载着美国人的思想和价值。因此,发掘中国元素、中国符号是体育电影表现民族性特征的重要手段。姚明不仅是一位NBA球星,他更是中国体育人走向世界的代表,是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对外传播的窗口;刘翔在田径场上取得的成就,是整个亚洲人、黄种人的骄傲,他理所应当地成了不朽的传奇;李娜在世界网球史上的成就,不仅仅证明了她个人的体育成就,更是中国人、中国女性向世界表达话语权的特殊标志。除了他们,还有中国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体操、游泳、田径各个体育领域的优秀运动员,在国际运动场上,他们每个人都是民族和国家的代表,都值得被电影艺术记录和呈现。因此,中国体育电影的民族化建构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相关联,着眼于民族文化特征,建构清晰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将中国的体育、中国人的体育和他们的体育精神以更具世界水平的电影技术和艺术呈现出来,塑造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
3.3 提升中国体育电影的艺术审美
有评论者提出,体育电影因其运动镜头较多,拍摄难度大,投资成本大,投资回报率低,导致产出较少,这种认识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共识。但实际上,美国好莱坞电影投资中,体育影视产业已日趋成熟,与其他类型电影相比,投资成本较低但收益颇高,所以很多大牌导演和影星都非常热衷执导和参演体育电影。近20年,最具有知名度的低投入高回报美国体育电影是《百万宝贝》(成本0.3亿,票房2.32亿)、《弱点》(成本0.29亿,票房3.06亿)、《空中大灌篮》(成本0.9亿,票房2.5亿)、《点球成金》(成本0.5亿,票房1.1亿)。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更是以0.1 亿美金的成本收获了12亿美金的全球票房。事实证明,投资并不是决定体育电影发展的根源性问题,体育电影的发展主要取决于艺术审美。优秀的体育电影其艺术品质和创作者的艺术审美追求必然要高于观众的审美水平,并且要在艺术与现实相结合的维度上打动受众,既不是政策的传声筒,也不是生活的原貌;既是普遍的,又是独特的;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才能够打动人、感动人。尤其是体育电影视觉表达利用镜头运动与画面剪辑的动与静、力与美,演员气质与特殊的运动要求,日常化情感与体育运动的特质,要体现出独特的运动审美与艺术审美的结合,符合现实逻辑、叙事逻辑、艺术逻辑。体育精神包含更快、更高、更强的运动哲学,以及团结、协作、平等、进取、包容的价值观念……吃透体育精神,平衡自我价值与国家荣誉之间的关系,是体育电影实现既接地气又有情怀的关键点[6]。运动哲学、体育精神、自我价值、国家荣誉如何在艺术审美中得到和谐、完美地呈现,需要电影人提高文化自觉,提高时代使命感,提高艺术感受力,提高与世界电影对话的能力。
3.4 中国体育题材微电影的创新
2009 年之前,通常将时长较短的电影称为电影短片,因其商业价值不高,又与广告性质完全不同,并没有受到电影界的重视。2009 年,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连续剧和网络短片应运而生,并在当年出现了被称为微电影标志性作品《一触即发》,时长90秒,场面宏大、制作精良,引起业界关注。之后,随着自媒体的迅猛发展,应新媒体平台传播需求出现了大量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息状态下观看,故事情节完整、制作周期短、投资规模小的电影作品,形成了微电影创作、传播新的体系。融媒体的发展,促使微电影行业出现了“微电影+”的新业态,也被称为网络大电影。以体育为题材的微电影创作在新的电影浪潮中不断有佳作呈现,如《另一种温暖》《吊车尾的逆袭》《无敌波》《我是球迷》《永不独行》《穿越心际》《为爱奔跑》《军人的荣耀》等。尽管体育题材微电影还没有产生具有强烈社会影响的作品,但微电影已经成为电影创作的一种主流形式,这种趋势为体育题材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空间,必将引起电影创作者的重视。
中国体育电影70多年的发展史见证了新中国的成长,也见证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它以艺术的形式和独特的审美内涵记录、讲述、塑造了我国特有的体育人、体育精神、体育梦想和国家追求。21世纪的新技术、新思想、新时代已经促使体育电影从固有的艺术和技术的桎梏中突围而出,经过理性的文化反思,站在世界的艺术舞台上。期冀中具有现代化风格、民族性特征和鲜明民族气质的中国体育故事,既是平凡的体育人追梦路上的人生故事,也是承载着新的体育精神、国家形象和国家精神的中国故事。
——评《休闲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