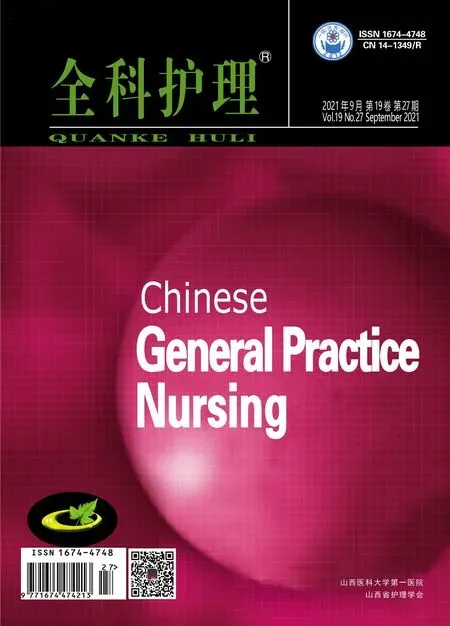认知行为疗法用于癌症复发恐惧的研究现状
苏小凤,王 瑾,王 云,仲 琳,韩继明
癌症病程进展及其复杂合并症状群是阻碍人们健康的重要单一障碍,不过随着肿瘤筛查、诊疗的不断发展,病人的总体生存趋势明显提高[1]。但由于疾病本身,加之治疗过程中病人所负荷的躯体症状和承受的巨大身心压力,致使其无法形成对于癌症病征的正确认知,诱发其内心的强烈恐惧感。癌症复发恐惧(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FCR)是肿瘤病人常见心理适应不良症状,严重影响病人的生存质量。而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为这一临床难题的攻克提供了新思路。因此,现对CBT用于FCR的研究现状予以归类总结,以期为FCR的临床护理实践提供一定的可行性依据。
1 相关理论概述
1.1 CBT的概念及起源 CBT是由美国贝克博士于1955年提出的[2]。它主要通过改变思维、信念和行为来改变不良认知,从而达到消除不良情绪和不良行为的目的。CBT主要包括认知疗法(CT)和行为疗法(BT)。认知治疗起源于信息加工模型理论,它认为事物的认知影响且决定了人的行为和情绪[3],心理障碍的产生不是由应激事件或不良刺激导致的直接结果,而是通过扭曲或错误思维的情况下进行认知加工来产生影响的。所以,通过纠正个体的不理智观念,帮助病人构建一套具有逻辑性和自助性的信念,进而能减轻或者消除病人的不良情绪。
行为疗法以学习心理学(条件反射理论、应激理论)为基础,其最初灵感来自Watson和Skinner等实验家,他们都认为个体的行为是通过学习而得的,避免去考虑不可观察到的精神状态[4],并且可以通过适当的奖惩来规范病人的行为,从而起到减少不良行为的目的[5]。
目前关于认知行为疗法主要有3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分别是艾力斯的理性情绪理论(REBT)、贝克的认知治疗理论(CT)和梅钦鲍姆的自我指导训练(SIT)等。艾力斯认为不理智或不正确的想法、观念是出现情感障碍或异常行为的重要原因,所以他提出了有名的“ABCDE”理论,即通过引导个体建立有效的理性观念或合适的情感行为以代替非理智信念,异常情感和行为的过程[6]。贝克认为人的情绪和行为变化与认知具有密切的联系,通过改变不恰当的认知方式,可以起到改善情绪和行为的目的[7]。梅钦鲍姆认为消极的内部语言是产生和影响行为障碍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通过纠正负面的内部语言,用正面的、积极的自我对话可达到纠正异常行为或者心理障碍的目的[8]。
1.2 FCR的概述 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觉对FCR的概念进行了界定。Bell等[9]认为FCR是癌症幸存者对原发部位癌症的复发、进展或转移产生恐惧的心理。而Cohee等[10]将其定义为个体对未来癌症可能复发的恐惧程度。其中Bell等[9]对癌症复发恐惧的定义在临床应用中最为广泛。FCR是一个从正常的应激反应到出现某些临床症状的持续变化的过程。通常低水平的FCR可以被认为是对癌症的一种正常和暂时的情绪反应,它可以帮助病人对疾病复发保持警惕,鼓励他们采取更健康的行为[11]。但疾病的初诊、癌症筛查与传统医学治疗以及深入的肿瘤创新治疗(如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会给病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疾病促发心理压力及负性情绪,反之情绪困扰加剧疾病的进展,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同理,癌症复发的恐惧感会加重病人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这种消极情绪不仅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而且在负性心理作用下也难以充分发挥化疗药物的疗效。同时,这也是药物不良反应率上升的重要诱因,它将进一步影响病人的身心健康[12]。另外,晚期或复发性癌症病人往往有抗肿瘤治疗经验,对化疗充满恐惧[13]。通常这些病人会过于关注身体症状的变化,如过度警觉、过度检查、过度追求舒适,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14]。同时,病人也可能会出现功能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焦虑症状,如恐慌、冥想以及心理幸福感下降等症状[15]。恐惧对病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病人长期或过度恐惧,将严重降低病人对疾病治疗的依从性,也会增加医疗费用[16]。
2 CBT的应用
2.1 CBT用于FCR干预的机制 CBT强调关注“目标”“当下”和“正在影响你生活的事”,而并不关注事件背后的动机以及无意识的心理冲突[17]。通过记录事件-情绪-生理反应,改变认知模式,从而实现消除负面情绪和不良行为的目的。CBT是认知理论和行为疗法的结合,但两者并非简单的相加。在实践过程中CBT不仅涉及认知矫正干预,且根据服务对象的具体情况进行行为干预。在二者的相互促进下实现了问题解决和服务效果的可持续性[18]。CBT认为治疗的关键是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纠正服务对象的非理性信念,促进行为情感的改变。CBT可通过提高认知和自我效能来降低FCR和医疗费用。
2.2 CBT的实施方法 认知疗法包括识别自动思维、识别认知性错误、真实性检验、去中心化、焦虑或者抑郁水平监测等技术方法。识别自动思维指的是帮助病人发现不良情绪发生前存在的非理性思维,并教会他们自动识别消极思维的过程[19],其技巧包括提问、自我示范或模仿。对儿童来说,他们经常使用语言、文字或象征性的表达(游戏、舞蹈、唱歌、艺术、思维日记、角色扮演)等方式开展。识别认知性错误是通过记录病人在不同情绪情境下的自动思维,分析他们在概念和抽象上的常见错误,进而帮助他们识别自己的认知错误。此外,儿童病人主要存在主观推断、选择性概括、偏激思维等认知错误[20]。真实性检验指的是将病人的自动思维和认知错误视为一种假设,使其在特定情境下对假设进行验证,使其意识到原有概念的不合理性,进而诱导其自觉改进的过程,它是认知治疗的核心[21]。行为治疗技术包括系统脱敏、厌恶疗法、冲击治疗、阳性强化、生物反馈、放松技术等[22]。放松训练包括渐进式肌肉放松、静坐、呼吸放松、想象放松等。放松训练是一种自我调节的训练方式,它可以帮助病人从身体放松到促进全身身心放松、抵抗心理应激和交感神经兴奋引起的神经反应,达到消除紧张、强身健体、消除疾病的目的[23]。渐进式肌肉松弛法是一种常见的放松训练方法,也是儿童病人常用的放松训练方法。其操作步骤是:病人根据指示交替收缩或放松骨骼肌群,体验肌肉的紧张和放松程度,自觉感受四肢和躯干的紧绷、重量和温度,达到放松的效果。
3 CBT应用于FCR干预的临床效果
CBT已被广泛研究并用于许多精神性疾病[24-25](如抑郁症、焦虑症等)和非精神疾病[26](如慢性疲劳、综合征失眠、偏头痛等)的干预治疗。而对肿瘤病人的FCR国外也已有许多学者证实了其有益效果。但CBT作为辅助治疗之一应用于癌症病人FCR症状干预时,并不能完全取代其他非药物心理干预疗法或是药物疗法。Milbury等[27]将其结合其他心理干预疗法用于FCR的症状治疗,其研究发现呼吸放松干预结合心理教育和认知行为疗法可以缓解病人的负面情绪,降低癌症复发恐惧的发生率。而Kexin等[28]对174例癌症病人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认知行为治疗干预。结果显示,认知行为疗法干预可以降低疾病进展阶段癌症病人的病情复发恐惧感。这一研究结果与Chan等[29]的研究发现一致,即病人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改变适应不良疾病的药物和用药信念,可以减轻癌症病人对癌症复发的恐惧感。并且Van Helmondt等[30]专门针对454例乳腺癌病人实施在线CBT自助干预措施,干预内容包括FCR心理教育、行动计划、放松和寻求保障。得出的研究结果表明,干预组病人的FCR显著降低,同时其生活质量状况也得到了改善,这一干预研究说明该方法能用于降低病人的FCR水平,可以考虑推广到整个癌症人群中。此前Van de Wal等[31]针对不同癌种人群进行了研究,其通过对52例高复发恐惧症(乳腺癌、前列腺癌、直肠癌)病人实施5期面对面CBT和3阶段在线或电话干预,结果显示干预组病人恐惧感水平和生活质量优于对照组。以上研究表明认知行为疗法有助于降低癌症复发恐惧感。
CBT在国内起步相对较晚,2009年至今中国先后成立了中华医学会CBT协作组、中国心理学会CBT学组、中国心理卫生协会CBT专委会和中国医师协会CBT工作组4个专业组织,共同组成“中国CBT专业组织”,CBT专业组织成立的浪潮推动了认知行为疗法在我国的发展。黄霜等[32]就针对癌症病人的恐惧疾病进展、风险察觉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结果显示乐观面对疾病、积极接受治疗的病人FCR水平较低,能更好地应对疾病风险。且研究者认为,CBT还有助于病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和负性情绪的改善,而通过情绪疏导转移了病人对疾病的关注,神经与肌肉的放松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病人的恐惧水平[32]。而赵毛妮等[33]应用认知存在团体干预针对肺癌化疗病人进行了研究,通过将认知行为疗法与积极应对策略相结合的方式指导病人改变不良认知,达到消除不良情绪和行为的目的,同时能帮助病人积极应对和获取社会支持。研究结果表明,在接受了6次认知-存在团体干预(CE)后病人FCR水平有明显下降趋势。杜妍等[34]也运用了类似的干预方案进行了随机对照试验,在研究中将104例卵巢癌化疗病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2例。对照组病人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病人接受认知-存在团体干预,结果干预后观察组病人的无助/无望、焦虑、消极应对方式、肿瘤复发恐惧感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积极态度、积极应对方式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因此,该研究认为认知存在团体干预可以增强卵巢癌化疗病人的心理适应能力,使病人保持积极的应对方式,减少对肿瘤复发的恐惧感。此外,程春燕[35]采用抛硬币法将病人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进行6周、每周1次、每次45~60 min的干预。对照组仅接受1次淋巴瘤知识讲座,后续接受常规护理。有研究表明,与常规护理相比,减轻非霍奇金淋巴瘤病人恐惧症进展的认知行为干预方案能有效缓解恐惧症的进展,提高病人的希望水平,对提高生活质量有积极作用。
尽管以上诸多临床试验表明认知行为疗法应用于癌症复发恐惧中的有效性,但也有研究证实,CBT并没有显示出比其他类型的社会心理干预措施始终如一的优势[36]。其结果差异可能与研究设置的基线水平、纳入的样本量、研究对象的差异或不同的干预方式有关。如Milbury等[27]以联合干预的方式针对肾细胞癌病人的FCR进行了干预且取得了有益效果。未来的研究重点应放在更多的实证研究上,以进一步明确CBT用于FCR的实际效用。
4 小结
随着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临床护理关注的重点不仅是疾病,而且病人的身心状况也需引起重视。FCR作为影响带瘤生存病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制约因素,理应成为关注的重中之重。此外,现代心身医学研究表明,75%的疾病与心理压力有关[37]。但当前国内关于CBT用于FCR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将CBT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或辅助技术应用到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中,仍然还有许多问题待商榷。比如,干预的适用人群还需要检验、干预的适用症状仍要进一步明确等。因此,我国需要根据国情制定最适宜癌症病人的CBT干预策略,以此助力于病人FCR的减轻,继之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