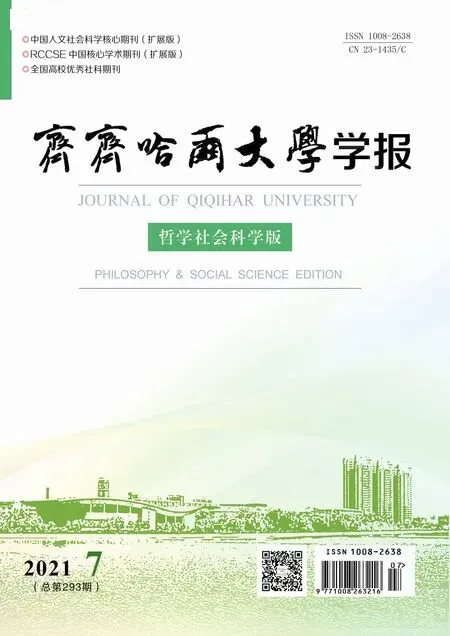科学、历史与文化
——“后李约瑟时代”文化相对主义析论
郝新鸿,闫国疆
(1.新疆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2.新疆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重建的时代主题,如何立足于自身传统,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乃至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多元思路,是今天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使命。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方法论自觉,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亦需要从前置性的方法论层面去总结、反思与创新。相对于真实发生的科学的历史,科学史的书写是一种史学重建,它往往预设了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文化”等基本问题的回答,而这些预设既受到彼时学术思潮的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学史研究的方法、策略与视角。被称为20世纪学术里程碑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工作,及后李约瑟时代那些意义深远的编史学变化,使中国科学史研究超出了“中国”与“科学”的范围,涉及到科学观念、历史叙事、文明进程等一系列编史学问题。
李约瑟之后,以美国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通过反思李约瑟“百川归海”普遍主义的一元科学观,批判用现代科学解释过去的辉格史风格,主张以当时文化传统和期自身标准对科学进行理解,倾向于一种相对主义的、多元的科学观。这种科学史研究主张领略中国科学的“河岸风光”,探讨中国文明之河中的知识之水是如何在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土壤中产生并得到滋养的,[1]表现为一种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编史诉求。情境主义编史学策略是对目的论主导下辉格史传统的当代回应,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在“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下,文化人类学要求研究者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native’s point of view)去看待其文化,主张对文化的“理解”,而非“评价”。以席文为代表的科学史研究,常常结合人类学、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视角,采取一种全方位的反辉格史的研究立场,拓展出利益、性别、地域等多重内部视角,探讨当时科学家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重建“那时”的人们是如何理解自己的实践和概念的,而不是现代文本作者应怎样评价他们的工作。[2]9这种立场将中国科学解读为中国特有社会文化的建构物,并将合理性分配给各种“本土知识体系”,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被解构,构成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科技强国的新时代,对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科学观的方法论根源、理论困境和现实危害,迫切需要我们在学理上给予深入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刻反思与批判,以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方法论支撑。
一、反辉格的选择:情境主义
后李约瑟时代的文化相对主义科学观在史学实践中是通过情境主义编史策略实现的。在社会建构论框架下,多种研究路径从社会、文化、性别、种族等“内部视角”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反辉格的历史解释,科学被放在文化情境中进行考察,并由它所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所标记。然而,这种情境主义并非是多语境要素的实践互动,而是凸显了社会文化这一单一情境,其基本取向是社会建构论。
(一)审视情境中的科学
席文在1970年代就提出,要基于中国本土语境对相关内容进行理解,清理出本土的基本概念。他主张对过去的情况做一种整体的考量,“审视情境(context)中的科学”[3],而不是李约瑟那种独立于其社会和历史根源的、普遍的、价值无涉的现代科学。[4]507
席文在2002年与劳埃德(G.E.R. Lloyd)合著的《道与名:早期中国和希腊的科学和医学》一书中提出的“文化整体”(Cultural Manifolds)方法论便是情境主义编史学的一种自觉尝试,也对传统科学史观追求超越历史的抽象概念的纠偏。“文化整体”试图“不分前台和背景”[5],考察一个给定问题所发生其中的那种文化所相关的“所有维度”,包括理念、社会关系、经济、宗教、政治、亲属关系等,同时也涵盖了把这些方面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相互作用关系。[6]在《道与名》中,席文将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和科学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与文化情境中,从宇宙观、社会、制度等方面进行考量:“人们是如何谋生的,他们与权威结构的关系如何,什么维系着他们做着相同的工作,他们如何交流自己所理解的东西,他们使用的概念和假设是什么。”[2]3
曾经撰写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农业分册的美国科学史家白馥兰(Francesca Bray)也持有一种与席文类似的情境主义编史立场。她反对把中国的科技从自身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认为古代科学是与那些产生它们的社会目标、价值、意义结合在一起的,主张探讨科技体系在具体境域中的含义,以深入研究“另一种世界”的构造。[7]8-11另一位美国科学史家费侠莉(Charlotte Furth)也对情境主义的编史立场积极呼应,赞赏席文用中国本土文化的概念框架及其制造者的文化假设来解释中国古代科学,认为这种内在论的策略为相对主义运用另一种认识论方法开辟了道路,同时也鼓励她从女性主义的路径践行这种情境主义。[8]2
(二)文化规定科学划界
与情境主义相适应的是,席文对“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基于一种人类学的文化判断。在席文看来,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殊的抽象概念,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因为使用了截然不同的概念和知识体系,从而导致了它们有各自的文化边界。古代和现代、希腊和中国都有各自的一套基本概念,它们只在自身的文化中是普遍有效的。以医学为例,两种文化中的人不会患完全相同的疾病,如果假定任何地方的患病经验都一样,就会犯严重的历史错误。[9]
席文提倡人类学的科学定义,将科学放在其自身的文化系统中考察。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由“阴阳、五行”等基本概念构成的知识结构非常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知识结构,当选用这种人类学标准来看待科学的时候,中国的科学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便获得了独特性,与古希腊或中世纪欧洲的科学思想具有同样的独特性。[10]pxviii而对于中国民间的巫术治疗,即使它们看上去不科学,但也应采用神、鬼、祖先组成的天官系统这样的人类学标准对其有效性进行合理解释。席文补充道,一个给定文化中的科学的领域是由那些普遍概念的应用来决定的,虽然它们可以被再提炼、再阐释,并由更特殊的概念进行补充,但对各种经验领域,文化则被选作关于划界的内在和外在的理由来界定它们。[10]pxviii正如埃岑加(Aant Elzinga)所分析的,席文对科学史研究的前提是,“文化因素决定了科学的划界,或换言之,不同科学分支的一般概念亦由文化因素决定。”[4]577
(三)科学史研究的“内部视角”
人类学取向的科学史研究关注地方性知识,强调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看待其文化。这在理论空间上为反辉格史立场拓展了视野。在西方的科学研究的社会建构论框架中,“当地人”的视角拓展出社会、性别、种族等内涵,这在方法论上产生了强调不同情境的“地方性路径”(local approach):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研究对象置于社会情境中,为反辉格史观打开了以社会利益作为历史解释的新向度;后殖民主义在欧洲科学之外重新确立编史基础,强调以“弱者的生活为思考的出发点”;女性主义则以女性视角揭露社会性别的建构过程,批判并拒绝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代科学框架,并常与后殖民主义结合,继而主张一种“边缘人的立场”。这些地方性路径从不同的研究路径为反辉格史打开了利益、性别、种族等多种“内部视角”,建构出历史人物的“自我理解”。
后李约瑟时代,以席文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积极使用社会学、人类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路径和相关方法对中国科学进行研究。席文积极倡导年轻一代的学者学习和使用属下研究(subaltern studies)、人种志、话语分析和其他路径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而不要纠结于这些方法的优缺点。[12]24他本人对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中国的医学、天文学、数学等进行分析,费侠莉从女性的边缘立场出发,以社会性别为基本范畴,对中国医学进行社会学重建,白馥兰则拒斥殖民主义的“辉格史家”以西方科学为标准所书写的“大叙事”[7]6,反对“五四视角”下的“女性受害论”,采取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视角对中国与妇女相关技术进行了“本地人”的解读,认为中国的妇女并没有被动地遭到迫害,而是作为主动的参与者将自己整合进了社会秩序之中。这些不同取向的情境主义编史学都采用不同的“内部视角”,强调社会文化维度,突出了中国科学的情境特征,成为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鲜明特征。
二、科学史研究中的文化相对主义
后李约瑟时代,席文、费侠莉、白馥兰等科学史家在社会建构论的框架内,通过利益、性别、种族等多种路径践行情境主义编史学,将科学约束在其地方性的传统和自身标准中,中国科学成为特定社会政治的建构物,面对中国内部不同文化系统的差异性,选择各自的文化作为解释资源,使科学的合理性多元化,进而走向文化相对主义的科学观。
(一)社会建构论的史学立场
对席文而言,情境主义是通过“文化整体”的运用而实现的。通过考察古代科学的资助雇佣模式,席文指认了研究者在利益导向下的动机,以及自然和政治作为工具性资源的相互利用。他认为,中国古代研究者在制造知识时渗透进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即为了获得资助维持生计,他们努力将知识内容与统治者保持统一。在这种利益模式的分析下,社会和政治便构成了古代思想家制造科学知识的工具性资源——《黄帝内经素问》《九章算术注》通过采用政治观念以获得权威的认可;《神农本草》利用政治模式作为修辞手段表达正统的合法性;《周髀算经》的“天圆地方”暗含政治意味,《九章算术》的内容与政治的关系是“含糊暧昧”的;气、阴阳、五行、道的思想是对制度和盛行的价值做出回应的结果。在这种分析中,中国官僚制度下的政治生活导向“主宰”甚至“垄断”了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分子的生活始终绕着君主的一极旋转,中国古代科学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的建构物。这种社会建构论的倾向导致“文化整体”并非真正的“整体”,而是最终指向了社会纬度,中国古代科学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的建构物,构成了社会建构论编史学的中国版本。
事实上,席文主张的是一种多维取向的社会建构论,人类学、女性主义等路径都有所体现,带有鲜明的社会建构论倾向。以医学为例,这种社会建构论的问题意识是:“性别、族群、社会阶级的不同,是如何影响健康、疾病及治疗的。”[12]22尤其是,为了形成一种对中国健康护理充分全面的理解,席文认为,应对建立在社会和种族特征基础上的不平等的治疗进行更多的研究,以性别视角为例,妇女所特有的疾病不仅是生理学上的内容,而且还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是对于低下身份的反常和正常的分类。[12]29正是在这种社会建构论的纲领下,席文对费侠莉等人的工作给予了认同。[12]23
费侠莉秉承了西方女性主义对性别的社会建构的基本观点,将女性及性别问题纳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深入到中医学知识和实践的内部进行考察。在《繁盛之荫——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一书中,费侠莉将中医置于中国社会父权制的语境下,不仅将中医身体观做了政治上和性别上的解读,还对医学话语做出了社会性别的分析。她认为,《内经》的身体观实际上蕴含了一种性别政治:人位于三维和谐的世界(天、地、人),用通俗的话来说,代表了以男性为主宰的世界。[8]50同时,宋代妇科提出了妇女以血为统帅的理论,女性由于兼有生殖的功能而被认为是虚弱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母性,强化了“黄帝的身体”中对男性至上的认同。她总结道,虽然身体存在基本的物质功能,但它本身并不能被认为是客观实在。这样的理论导向落实在中医史的研究中,则导致中医赖以存在的哲学——阴阳学说的解构,中医成为父权制社会建构的产物。费侠莉这一著作成为在后现代影响下的社会建构论对中国传统科学的一次代表性的操练。
白馥兰则融合了人类学方法、女性主义视角和后殖民的批判路径,在《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一书中,讨论了一组自宋至清代对性别有着建构作用的技术——建筑、纺织和生育。白馥兰凸显了家居空间的文化和政治纬度,将中国的房屋建筑看成是“编成密码的父权制”的文本;将纺织技术视为规训妇女的统治工具;作为妇科医学核心内容的自然生育力和调经理论所暗示的母性角色的双重性,为一夫多妻制和收养制提供了医学辩护,使它们成为正当的社会性生育手段。基于此,白馥兰使用“本地人”的内部合理性标准指出,宋至清代,妻子在丈夫纳妾、收养时常常扮演着非常活跃的角色,中医遗传理论和家庭伦理道德支持了一夫多妻制,这允许地位高的妇女可以正当地占有下层妇女的孩子而获得社会后代。[7]277,285在白馥兰看来,一系列与妇女有关的技术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建构物,是负载了意识形态的物质表达。
(二)多元科学的多元“合理性”
人类学中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常常与对多元文化的认可联系在一起。在文化人类学家看来,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本土文化框架,文化因多元性和多样性获得了复数的形式。当席文批判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以多元的、地方化的科学观取代一元的、普遍的科学观时,不仅“科学”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其边界也被拓展,形成了多元的科学观。以医学为例,席文认为,虽然现代生物学界定的身体在每个地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样的,但处于每个社会甚至每个亚文化中的人们对他们自己的身体和其他人的身体,以及他们的病痛所抱有的看法却是不相同的。[12]29
席文的多元文化的科学观一方面是指各种文明的多元文化,即各种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另一方面则是指对前者的继续细化和分化,即在同一种文化中存在的众多可选择的科学方案。前者在理论上为后者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对于前者,“文化整体”将科学安放在每一个文化单元中进行研究,以了解不同的文化情形如何把观念和社会制度导入了不同的发展方向,[5]这种宏观的多元文化科学观构成了他所谓的科学史的比较研究。对于后者,针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领域,席文进一步将研究单元细化,认为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这样的研究单位根本无法容纳巨大的多样性。[12]26-27对此,他一方面他呼吁应该增加地域纬度的地方性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从社会文化的纬度,试图将中国社会中的精英与大众、城市与农村、汉族与非汉族等各种层次的文化纳入进来,尤其关注当地非精英的文化传统。
以医学为例,席文吸收了人类学中的“医学多元论”,认为医学存在着多样性,且这种多样性之间具有平等地位。他对精英医学与大众医学的区分使医学史研究内容不仅限于经典医学,还包括更多替代性的传统和实践,诸如巫术、铃医、法术等大众医学。在席文看来,“科学”和“迷信”并不是彼此专有的两个领域。[12]28他通过借鉴人类学中对“仪式”的研究,分析了巫术作为大众医学的疗效。席文认为,古代中国人感觉身体异常时,通常会认为是鬼神附体,治疗方式是请法师做法驱赶鬼神,因为人们相信法师有控制鬼神的权威。“不论这种控制是否是客观事实,这都无关紧要,反正人们信它。这种信念往往比药物更有效。”[9]对这种信念的解释,席文选择了与精英医学完全不同的一套灵魂社会的理论框架,认为这是这种大众文化自身的价值评价系统,由此,法师做法驱鬼获得了合理性。后李约瑟时代,面对不同文化在认识论上的多样性和不协调性,席文等持有多元文化科学观的学者选择各自的文化作为解释资源,将合理性分配给各种“本土知识体系”,传统思想史方法所依赖的合理性标准不再适用。
三、问题与反思
文化相对主义科学观对文化相对性、多元性的承认与尊重具有积极意义,这种史学实践在后李约瑟时代打开了新的研究空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消极意义来说,过分强调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向度,过度推崇情境主义编史路径,将对科学的理解锁定在单一的社会文化因素上,忽视了不同要素在科学实践中的互动生成,不仅颠覆了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对科学观乃至文化观也存在着潜在的不利影响。
(一)以论代史:科学及其历史失去独特生命
文化相对主义科学观的下的历史研究,将中国古代学置于中国文化社会的情境中,认为科技是社会性的和地方性的,并总是政治性的,将文化、社会作为单一的普遍性解释,因而科学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被动产物,中国的文化决定着中国的科学,规定了中国科学的身份与界线,科学成为社会文化的表达物,甚至成为“文化傀儡”,失去自己独特的生命。而这样的文化系统常常被看作是始终如一的、已经完成了的、拒绝改变的,这容易导致一种在科学观上的文化保守主义。
后李约瑟时代,席文的发问方式是:“为什么这些社会制造了他们所从事的那种科学。”[2]251社会建构论成为以席文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种模式,即将中国古代科学看作是在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把文化、社会作为单一的普遍性解释因素,具体的历史情节被同化为一般的图式,历史则变成社会利益或其他因素持久发挥作用的一系列例证,始终重复着同样的故事,[13]导致“时间无所作为,历史徒劳无功”,[14]走向了“以论代史”的困境。同时,这种历史叙事使具有专属性质的科学消弭在巨大的文化图像中,科学史被同化为一般历史,[15]科学史完全附属于人类社会史,亦丧失了自己独特的生命。
(二)突出边界:导致文化分水岭
后李约瑟时代的文化相对主义科学观的总体特征是对文化边界的强调和突出,包括不同文化之间、过去和现在之间由文化边界所造就的区别。在对文化分水岭的强调中,“我们”与“他们”成了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群。
就时间维度而言,过于坚持古今文化边界而放弃了与现代科学技术沟通的可能,从而走向一种由时间纬度所分割的文化单元,中国传统科学便失去了与现代科学比较参证的可能,基于本土知识的当代创新更是无从谈起。就空间维度而言,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边界使科学成为被各自文化所标划的独立单元,以席文等为代表的新史学进路由于对情境知识的过度强调,在对李约瑟“欧洲中心论”进行批判的同时,又陷入了封闭文化单元,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被过度放大,中西比较研究的工作实则重申了文化间的差异,西方和非西方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假想的分水岭,换言之,后李约瑟时代,以席文为代表的情境主义的科学史研究仍然没有摆脱“中国和西方是两个不同的社群”这一基本预设。[4]600
当然,本文绝不否认地方性知识与多元文化的重要价值,相反,地方性的丰富资源和多元的可能性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本文赞同这样的观点,“一切文化都是相对的,但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立场是错误的。一切文化都有终极关怀和终极价值,但文化普遍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立场也是不对的。”[16]对本土知识的确认和多元文化的尊重不应成为支持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的理论依据。多元文化的科学观对科学的多元价值的确认,恰恰是走向普遍的基本要求。李约瑟之后,情境主义编史学过度使用,不仅造成科学陷入各自的文明单元中,且由于各种文明中的科学具有同等的合理性,使得普遍性的科学纲领成为不可能。这不仅限制了我们对客观的物质世界的认识与把握,同时还会使根据地域外知识来批判性地评价地域内传统关系和意义的工作失效。[17]
(三)超越二分法:走向文化的互动与交融
1990年代社会建构论通过理论内省,超越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框架,在自我批判中逐渐走向了科学实践。拉图尔认为,二元论的现代性框架不仅造成了人类与非人类的分裂,还造成了西方和非西方、现代和前现代之间的对立。在他提出的三种对称性中,第二种是广义对称性原则,第三种便是指在西方与他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先验区分。[18]103-104他指出,现代制度下存在“两大分界”,一是自然与社会文化的分界,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分界,前者是内在的分界,它导致了后者——外在的分界。这是因为前者使现代人认为自己能够认识到自然与文化、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差别,而前现代式的自然和社会是交叠在一起的混沌状态,前现代和现代之间便产生了鸿沟,“我们”与“他们”之间出现了巨大差异,[18]113由此出现了主张不同文化间不可通约的文化相对主义。而根据广义对称性原则,并不存在纯粹的社会或自然,二者是科学实践中共生性的文化因素,处于一种交杂的状态。现代人和前现代人、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并不存在无法超越的文化边界。广义对称性原则打破了传统自然、社会二分框架下自然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的两难困境,否认了不同文化之间,包括西方与非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所谓的文化分水岭,这为批判和超越文化相对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国际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学界的后殖民理论在批判性吸收拉图尔上述思想的基础上,从地方性的复杂运动角度出发,把科学理解为一系列混杂的地方性的异质性活动,主张地方性和全球性互动的分析框架,挑战了地方性与全球性、西方与东方的传统二元论。按照这种观点,地方性的身份在知识的全球运作中不断被塑造与创造,它已成为一种杂合体,兼具本土与全球的特征,地方性知识从封闭的文化情境走向了全球流动的实践生成。[19]这些洞见与科学史研究中的反思形成了呼应。科学史家斯科德(James A. Secord)在1993年便提倡一种科学的“大图景”,2004年更是鉴于科学史研究中“被困在情境中的地方性科学”,提出了“传送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Transit)的理念,呼吁科学史应了解更多知识流通的形式和地方性背景中的使用,尤其是传送过程中的物质形式。[15]当代STS学界,在后SSK、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众多不同的研究路径中,超越传统二分框架的共同努力使得科学史的分析单位从单一的“科学”、“技术”或“社会”转向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综合体”,即“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旨在表达科学、技术或社会的祛中心的交杂状态和实践特征,摆脱了历史解释的预成论和还原论,走向一种生成本体论。这些都为后李约瑟时代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超越传统与现代、地方性与全球性、本土与西方、多元与一元、精英与大众的文化相对主义迷雾,探索综合性的研究方案以及当代中国科学文化的重建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启示。在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应从中国自身的科学传统出发,借鉴实践生成的科学观和科学史立场,寻求能真正把握中国科学的实践内涵与历史发展的方法论路径,进而由科学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达到中国传统科学现代重建的文化自觉。
——博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