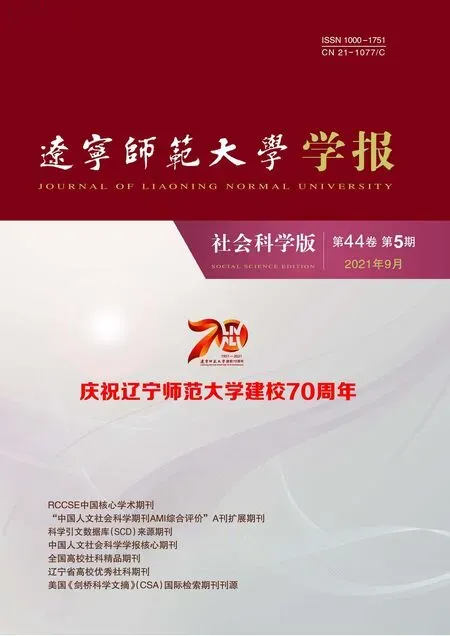莱蒙托夫诗歌中的天使形象
贺 梵, 谢 周
(1.华北电力大学 英语系,河北 保定071003;2.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400715)
天使(ангел)作为一个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形象,在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诗歌作品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俄罗斯东正教中的天使形象出自《圣经》,他们是耶和华的使者,遵照他的命令保护信徒,而《圣经》中甚至没有对天使的外貌进行详细描述。由于11—17世纪的古俄罗斯文学深受东正教的影响,故而这一时期的天使形象总与宗教相关联。18世纪初,天使形象开始变得更为世俗化,诗人们常常将君王、女性和孩童比作天使。例如,罗蒙诺索夫以天使赞颂俄罗斯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称她为“我们和平岁月的天使”(Ангел мирных наших лет)[1]207、“我们美好的和平天使”(наш Ангел мира красный)[1]80、“和平的天使”(Ангел мира)[1]238等。18世纪中期,天使被用以形容美好的女性和纯洁的儿童,比如卡拉姆辛称少女丽莎为天使(ангел красотою, ангел нравом и душою)[2],在他的诗歌《拉伊莎》中,拉伊莎也称呼自己的情人为天使;杰尔查文的诗歌中,天使被用来形容古罗马女神福尔图娜(О кроткий ангел во плоти)[3]26、美丽的新娘(как ангел хороша)[3]309等一系列女性形象。而到19世纪初的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阶段,天使形象则包含了更多的象征含义。
莱蒙托夫作为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不但继承了以往俄罗斯文学的天使传统,同时也大大发展了天使形象,使其诗歌中的天使蕴含了诗人丰富的感情与深刻的哲思,为后世俄罗斯文学中的天使、恶魔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性、神性、魔性等文学主题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丰富的养分。
一、天使——爱情
将宗教传统中的男性天使与现实中的女性联系起来并非俄罗斯的固有传统,直到18世纪俄罗斯诗人们才开始频繁用天使指代美好的女性形象,这一传统到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得以确立。尽管普希金也曾以天使来称呼国家的君主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ом, грозным ангелом)[4],然而他作品中绝大部分的“天使”——如“我的天使”(ангел мой)[5]——都是用来称呼美好的女性或抒情主人公的情人。值得一提的是,普希金的“女性天使”频繁出现在其叙事诗中,给诗歌增添了浪漫主义色彩。在《沙皇尼基塔和他的四十个女儿》中,普希金将美丽的公主们喻为“天国的天使”(сорок ангелов небесных)[6]134;《新郎》中女主人公娜塔莎的父亲称呼自己的女儿为“我的天使”(ангел мой)[6]269。对莱蒙托夫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也曾以天使形容女性,他在《致伊莱扎》中写道,“女人是天使,而婚姻是恶魔”(Though women are angels, yet wedlock’s the devil)[7],从而将天使与爱情直接联系在一起。
莱蒙托夫继承了普希金的传统,在他的诗歌中“天使”同样不再指代君主,取而代之的是拥有美丽外表的女性。莱蒙托夫将天使与女性、爱情紧紧相连;甚至可以说,天使在某种程度上已化作爱情的拟人形态。莱蒙托夫在《塔拉玛》中塑造了一个外表艳丽、内心狠毒的女王,并以天使形容其外表(Прекрасна как ангел небесный)[8]202,以魔鬼形容其内心(Как демон коварна и зла)[9]202,将天使与魔鬼、美与恶、爱与死的反差表现得极为强烈。在《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中,诗人将自己的爱人称为天使,并且写道,他的爱人将因为他的爱情而获得不朽的生命[9]178,其中表现了诗人对爱情的态度。永生是神圣和理想化的,莱蒙托夫意识到凡人的肉体无法长久,而附着在肉身之上的精神与灵魂却可以永恒。在年轻诗人的心里,一份炙热的爱情可以让有限的肉体趋向无限的永恒。莱蒙托夫在《假如造物主想斥责我们》中,更是直接将爱情比作“温情的天使”(как ангел нежный)[9]222,它可以拯救惆怅的心灵。诗人相信,爱情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灵魂,可以让精神达到永恒。《骠骑兵》里,诗人以天使指代骠骑兵的爱人[8]71,但实际上,这个天使不仅仅是具体的爱人,更是爱情本身,抚慰着骠骑兵无处可归的灵魂和光辉外表下空虚的内心。除此之外,莱蒙托夫的天使不仅用于称呼女性爱人,天使也可以是情郎和孩子,比如在1832年的《抒情叙事诗》中,犹太姑娘将自己的情人也称为“我俊美的天使”(Мой ангел прекрасный)[8]68,而在《哥萨克摇篮曲》中,母亲又称自己的孩子为天使[8]141。在莱蒙托夫的诗歌世界中,孩提阶段是一段美妙神奇的时期,童年总是与善良、光明和美联系在一起,因为无邪、无罪的孩子像天使一样纯洁[10]。
莱蒙托夫的女性天使形象与普希金和拜伦作品中的“天使”有着较大的差异。首先,在莱蒙托夫的诗歌中,天使常常指代现实生活中诗人钟情的某位具体女性,而非一个仅仅借抒情主人公之口呼出的虚构形象。诗人不单单突出了她们的外表美,还强调其内在美。在诗人1831年创作的诗歌《我见过幸福的影子;但是我》中,他将娜塔莉亚·伊万诺娃称为“痛苦的天使”(ангел казни)和“纯真的天使”(чистый ангел)[9]225,以天使赞颂爱情,又以天使表现爱人的纯真美。诗人一方面沉醉于对她的欣赏与爱慕之中,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承受着爱而不得的痛苦。1832年,莱蒙托夫与伊万诺娃已经分道扬镳,在《致……》一诗中,即使诗人背负着爱人对他的不理解与冷漠,但正如诗人所说,相互遗忘是困难的,他仍然称她为天使[8]22,表现出了莱蒙托夫对爱情的悲观绝望与内心深处仍会被触动的深情。莱蒙托夫与伊万诺娃的失败恋情使他对爱情产生了怀疑,即使在他与瓦尔瓦拉·洛普欣娜初生情愫后,他仍然对爱情的结局抱有质疑。诗人在《听我说,或许,当我们离开》中赞美了爱人,说她“会成天使”,而他自己将会“成恶魔”(Ты ангелом будешь, я демоном стану)[8]40,用天使与恶魔的对比表现出他内心的矛盾与无法克制的对爱情的向往。《致……》(1831)一诗原来是莱蒙托夫写给一个爱过他的女性的,但是他加以改动,将诗歌纳入长诗《恶魔》,献给自己的爱人洛普欣娜,其诗句“因为你简直是位天使”(Ты слишком ангел для того)[9]216中的天使如同形容伊万诺娃的“纯真的天使”一样,所指不再是爱人与天使相似的美丽外表,而是她们与天使相似的美德,使诗人不能自持地向她们表露出爱意。
莱蒙托夫的此类天使形象也被研究者称为“人间的天使”,其中最典型的形象就是莱蒙托夫的小说《瓦吉姆》中与魔鬼式主人公瓦吉姆相对应的善良美丽的奥尔加[11]。莱蒙托夫将奥尔加身上的外在美与内在美集合起来,通过对这一形象的理想化、象征化,使其成为“魔鬼”瓦吉姆难以接近的“天使”。
二、天使——守护人
随着19世纪初俄罗斯哲学继续发展,在包括莱蒙托夫曾就读过的莫斯科大学等众多大学中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哲学精神的教授,他们在当时的俄罗斯年轻人身上种下了哲学的种子。然而,不论当时俄罗斯社会中潜流的神秘主义,还是来自德国的舶来品谢林的自然哲学,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东正教思想也顺理成章地通过哲学的思触融入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创作中,再加上诗人们从出生起便生活在浓郁的东正教氛围里,因此,莱蒙托夫及其同时代作家们,无一不深受东正教思想的影响。莱蒙托夫没有把天使仅仅视为一个虚幻的艺术形象,而是将其纳入客观存在的真实世界[12],所以我们在分析莱蒙托夫诗歌中的天使形象时,也不应忽视其固有的宗教意涵。
在东正教传统中,天使的职责除却传达耶和华的旨意之外,也有保护信徒的责任。《圣经》记载,天使常常奉命保护虔诚的信徒,如天使在索多玛灭城之际保护罗德,而圣徒彼得也专有天使保护。也正因为如此,天使常常与守护者联系在一起,天使的“守护”职责正是俄罗斯的诗人们将国家的君主誉为天使的原因。俄罗斯东正教徒相信,每一个受洗的信徒都有自己的守护天使(ангел хранитель),他们既保护信徒免受伤害,也指引信徒的灵魂,使他们不会误入歧途。莱蒙托夫的守护天使正是他的名字“米哈伊尔”的来源——天使长米迦勒[13]158。在他的诗歌中,盘桓于天地之间的守护天使成了最常见的意象之一,他们不仅保护尘世间的众生的肉身,也给他们的心灵带来慰藉,成为指引人们走向安宁与幸福的引路人。对于莱蒙托夫而言,天使就是真正的天国使者,是诗人信念中真实存在的灵魂守护者。
与普希金一样,莱蒙托夫也有一首名为《天使》的抒情诗。虽然普希金的《天使》创作较早,但莱蒙托夫却没有简单沿袭普希金“天使与魔鬼”的主题,可以说《天使》这首诗是莱蒙托夫早期创作的独立表达。莱蒙托夫的《天使》创作于1831年,诗人的母亲早逝,而父亲也在这一年10月去世,并且诗人当时还陷入了与伊万诺娃的感情纠葛,这一切都使诗人体会到了深深的独孤感,促使其在人生的低谷寻求灵魂的拯救,并为其创作《天使》一诗提供了契机[14]。在该诗中,莱蒙托夫刻意将天使放置在一个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处于临界点的位置上:诗中的天使飞翔于天地之间,午夜之时,天国与尘世之间,怀抱着一个即将从天国来到人世的稚子的灵魂,吟唱着一首由天上传向人间的圣歌。在这首诗中,天使作为天、地两个空间的联结者,以歌声的方式将人世和天堂直接联系起来,为灵魂带来安宁,让这首歌永远伴随着这个即将被凡尘惊扰的灵魂,使他不致忘记天国的永恒,换言之,天使正是“年轻的灵魂”的指引者。
在莱蒙托夫笔下,来自天国的灵魂是无罪的、幸福的,他真挚地赞美天国;人间则充满了悲伤和眼泪,灵魂在这里饱受痛苦。天使是连接天国与人间的上帝使者,他的“歌声”则是天国福音的载体。对诗人来说,天国不是归处,而是来处,是灵魂的故土,是诗人的精神故乡,因而天使留存在灵魂心中的歌声会一直陪伴着这颗灵魂流浪于人世,并在其死后为其指引回归天国的路。年轻诗人认为,从人世间的痛苦中解脱的方式是倾听天使的声音,也就是遵从对上帝和东正教的信仰,天使的歌声可以指引人们在喧嚣的尘世中获得安宁。《天使》一诗中“飞翔”是天使最重要的状态,因为就诗歌内容而言,全诗都建立在天使携带灵魂从天国飞到人间的过程之上;从深层含义上来说,正是天使的飞翔,使得天与地、神与人之间有了连接。另外,《天使》的结构形式也表现出了天使飞翔的姿态,以诗歌第一节为例:
По небу/ полуно/чи ангел/ летел,
И тиху/ю песню/ он пел,
И месяц,/ и звезды,/ и тучи/ толпой
Внимали/ той песне/ святой[9]230.
可以看到,莱蒙托夫使用了四音步抑扬抑格与三音步抑扬抑格交错的四行诗诗节格式。抑扬抑格张弛有度,舒缓悦耳,不仅为诗歌增加了音乐美和神秘性,其音步长短交错的特殊结构仿佛天使振翅一般,也在视觉上增加了诗歌的画面美和空灵之感。
诗人1837年创作的《祈祷》中的天使也起着守护天使的作用。《祈祷》是莱蒙托夫后期的一首宗教主题的抒情诗,相比于《天使》,作者此时的宗教哲学思想更为成熟。该诗歌创作于诗人昔日的爱人洛普欣娜另嫁他人之后,莱蒙托夫将这首诗寄送她的姐姐,在诗中向圣母为昔日爱人而祈祷,饱含着作者对她深厚的感情与衷心的祝愿。诗歌中的尘世与《天使》中所描绘的一致,是冷漠孤独的,而爱人的灵魂是美好善良的,应当得到幸福,因此他希望圣母可以将她托付给“最好的天使”——也就是“冷漠尘世中热情的保护人”——直至她生命结束。《祈祷》中的天使不仅在少女弥留之际引导她前往天国,同时也在她在世的时候给予保护,让她得到幸福,因此与《天使》一诗中一样,《祈祷》中的天使也充当着天与地、天国与凡间、上帝与人之间交流的媒介。如果说《天使》中莱蒙托夫需要反复强调天使对灵魂的关切来缓解内心的痛苦,他心中对于通过信仰获得心灵慰藉还有一丝疑虑,那么在《祈祷》中诗人已经不再有任何怀疑,他虔诚地通过祈祷这种与天国沟通的方式为曾经的爱人祈福,诚挚地希望有一位天使能够从生到死守护她的肉身与灵魂。对于莱蒙托夫来说,上帝与天国是遥远而真切的寄托,而天使作为二者与人间的联结人,正是近在诗人身边的灵魂保护者。
三、天使——死亡
提到天使,就不能不谈及莱蒙托夫诗歌中一类特殊的天使——死亡天使。《圣经》中的天使会带走离世的人的灵魂,成为亡魂的指路人。死亡天使虽然与守护天使在生死上对立,但是二者却并无善恶之分。死亡天使的形象也常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拜伦诗歌《死亡天使》(AngelofDeath)事实上所指就是死神,而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诗歌中的死亡天使则是上帝派来带走灵魂的使者,在亡者的国度继续指引着背负罪恶的灵魂。死亡作为莱蒙托夫抒情诗中的重要主题,也是诗人从少年时期就反复思考的哲学问题,因而死亡天使也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莱蒙托夫的诗歌作品中。
莱蒙托夫早期的抒情诗《夜之一》和《死(在绚丽多姿的幻想抚慰下)》都受到了拜伦《黑暗》(darkness)和《梦》(Thedream)的影响,以梦的形式展开叙述,但是在内容上与拜伦的作品有较大的区别。在两首诗中,莱蒙托夫描绘了亡灵面对死亡的过程。《夜之一》的抒情主人公发现自己死亡后,灵魂首先陷入恐惧,随后感到迷茫与矛盾,之后他遇到了天使。在天使的引领下,灵魂由混沌回到人世,看到了肉身灭亡的可怕景象。莱蒙托夫认为肉体与灵魂可以相互剥离,死亡以后灭亡的也只是肉体,灵魂可以以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肉体的腐败,从而肉体成了灵魂的他者——一位“最后的、唯一的朋友”。诗人通过描绘介于明暗之间的混沌,将生与死的世界进行了分割:这首抒情诗整体色调阴沉,唯有天使光辉明亮,他的形象与昏暗的死后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表现出了天使的神圣与超然。年轻诗人对于死亡自然是恐惧的,但是恐惧之外仍有宽慰——那就是天使和天使所在的天国。天使告诉诗人的灵魂,他负担着罪恶,应当在人世中生活、赎罪、祈祷,这与东正教的赎罪思想是一致的。看到了肉体的销蚀,诗人认识到,人世间轻浮的欢愉是短暂空虚的,他想要追求永恒的幸福(блаженство),而获得这种幸福的方式他却不得而知,这种矛盾让诗人痛苦,进而让他想要诅咒上天。天使建议亡者的灵魂去祈祷,而在东正教中祈祷是人与上帝沟通的途径,想得到真正的幸福就一定要坚定对上帝的信仰,唯有如此才可以脱离凡世的痛苦,获得永恒。如果说《天使》中的天使指引的是一条由天国来到人间的生的道路,那么《夜之一》中的死亡天使则恰恰相反,他所指引的是从人间回到天国的途径,两首诗共同构建了一条灵魂来自天国故地,降临人世,而最终又回归天国的道路。
《死(在绚丽多姿的幻想抚慰下)》则是对《夜之一》的改写,莱蒙托夫在其中保留了关于肉体腐败的描写,但在此基础上也进行了修改:指引灵魂的天使被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命运之签”(жребий),相应地,命运之签也没有给予灵魂指引,只是单纯地让他回到人世。两首诗在对死亡的思考上也有较大区别:在《夜之一》中,诗人在天使的指引下对人间的欢愉、爱情予以反思,思考如何获得永恒;而在《死(在绚丽多姿的幻想抚慰下)》中,虽然没有了天使这一角色,抒情主人公仍然平静地接受了死亡,但是在看到自己腐烂的身体时,他还是难以克制内心的起伏以至于突然惊醒。由此可见,在《死(在绚丽多姿的幻想抚慰下)》一诗的反衬下,《夜之一》中“死亡天使”的形象更加得以突显,正是这位称职的亡者指引者,引导抒情主人公对死亡进行深入思考。
四、天使——恶魔
莱蒙托夫在其早期的长诗《死亡天使》中,记述了天使成为“恶魔”的变化过程。俄罗斯文学中关于天使与恶魔的转变的描述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以前,《编年史》中将恶的源头归于曾经是天使但堕落成魔的魔鬼,这些堕天使的随从“小魔鬼”们(бесы)会以天使的外形出现,遵从魔鬼的命令在人间散布邪恶。古俄罗斯文学中善恶处于绝对的对立,上帝、天使和圣人是善的来源,而魔鬼在上帝的默许之下在善恶交战中考验着人们对上帝的信仰。
与东正教传统不同,《死亡天使》中的天使抛却了善,转变成“恶魔”,并非因为其自身对上帝力量与地位的质疑,而是具有更为世俗的原因——人类自身的欲念。长诗《死亡天使》中的天使本应履行死亡天使的职责,带走死去的阿达,但是因为受到她和佐雷姆的爱情的感动而与少女合二为一,令阿达起死回生。死亡天使行为的动机很特别:他想要深入人类的内心世界,探求人类灵魂的本质[15]。然而,平静的生活注定无法让佐雷姆满足,他仍然希望追求人间争斗的荣耀,却在战争中丧命。阿达在战场上找到了濒死的爱人,但即使在死前,佐雷姆仍没有因当初的决定而感到后悔,始终难以抛却建功立业所带来的刺激感,无法拒绝荣耀的诱惑。死亡天使因此对人类的爱情和追求感到失望,他感到人们不能珍视宝贵的爱情和平静的生活,反而去追求短暂而虚伪的荣誉,因此失去了对他们的信心,不再以善良、博爱的眼光去看待尘世中人,反而具备了轻视、仇恨的恶魔特点,成了凶恶的“死亡天使”(但是他并未反抗上帝,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恶魔)。莱蒙托夫将天使转变为“恶魔”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人类自身的缺陷,这种态度也反映了诗人对人性的不信任,而这种对人性的怀疑同时也贯穿了作者的多部作品。
长诗《阿兹莱厄》描绘了另一个死亡天使的形象。虽然阿兹莱厄的原型是伊斯兰教的死亡天使亚兹拉尔,但在长诗中他既非天使也非恶魔,反而更像一个人世间的“多余人”,虽然内心充满了才能但却无处施展,于是他怀疑一切,自怨自艾。阿兹莱厄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因为内心的空虚而诅咒上帝,被从天国放逐,不生不死,永远盘桓于人世和天堂之间,永远无法获得解脱。相比于《死亡天使》中的天使,阿兹莱厄更具备凡人的特质:他被迫与爱人分离并非因为凡人难以克服的死亡,而仅仅是因为少女母亲的意志,他就失去了唯一的一次爱情。失恋之后他无计可施,也只是顺从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再次陷入痛苦与不得救赎之中。除却诅咒上帝、被驱逐出天堂以外,我们很难将这样一个软弱、忧郁的阿兹莱厄归入恶魔的行列。
与上述两首长诗不同,莱蒙托夫在其后创作的长诗《恶魔》中,则描绘了一个更具恶魔特点的“堕天使”形象。《恶魔》的主人公虽然继承了上述两首诗中死亡天使的特点,但是又与两者有明显的差别。恶魔曾经是司智的天使,背离了上帝选择作恶,却又在遇到塔玛拉以后主动向她所代表的善靠近,当她死后恶魔再次选择与上帝派来带走塔玛拉的天使争夺她的灵魂,试图用恶的力量撼动善,但最终失败了。相比于阿兹莱厄的无所作为,恶魔更具有反叛精神,并且将这种不甘和抗争践行在他的行动之中,这让他与“多余人”阿兹莱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恶魔在本质上与阿兹莱厄区分开来。虽然《恶魔》中的堕天使也表现出了怀疑、阴险、恶毒等典型魔鬼的特点,但天使美好的一面仍然保存在恶魔的灵魂中——恶魔尽管憎恶善、美和爱,但他对于它们却有着无法自持的认同和趋近;恶魔始终怀念天国的时光,对美丽的塔码拉一见钟情,甚至于“改恶从善”,为爱情“祈祷”,想要回到天国重新做一个天使,恢复对上帝的信仰。与其说是塔拉玛改变了恶魔,不如说是身为美的化身的塔玛拉唤醒了隐藏在恶魔身上的“天使特征”。换言之,恶魔并非纯恶,他只是被恶掩盖的善,是在诗人创设的极端环境下从恶中发掘出的天然的善。但是诗人不肯原谅他,恶魔的悲剧在他背离上帝的一刻就已经注定:塔玛拉作为唯一可以拯救他的爱人,却死于他因为背叛上帝而被惩罚的有毒的吻,恶魔没有获得解脱,转瞬即逝的爱恋只能让他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
在我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莱蒙托夫创作中的宗教因素长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学界往往更加关注其创作中的社会历史因素,例如顾蕴璞先生在分析长诗《恶魔》时,对读者从宗教文化视角看待恶魔与上帝的冲突提出了质疑,认为比起“宗教生活”,诗歌更符合朴素的“政治生活”以及人民善恶观的秩序[16]。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在19世纪的俄罗斯,无论贵族还是普通民众,绝大部分人在道德观念上都遵循东正教教义,即使是俄罗斯民族的爱国精神,同样也建立在对上帝信仰的基础上。莱蒙托夫与同时代的俄罗斯人民一样,其是非观、善恶观都深深植根于东正教传统。根据俄罗斯当代莱蒙托夫研究者伊·亚·季谢廖娃的研究,莱蒙托夫的爱国情怀是与东正教思想紧密联系的:罗马帝国灭亡后,俄罗斯人将俄罗斯的土地视为新罗马和俄罗斯民族的“应许之地”,将莫斯科视为新的圣城耶路撒冷,莱蒙托夫在早期散文《莫斯科全景》中更是直接将克里姆林宫比作一座祭坛。拿破仑在莱蒙托夫的时代被视为反基督者,1812年卫国战争不仅是反抗法国侵略者的战争,更是一场卫道的战争[13]124。可以说,东正教对俄罗斯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即使到了20世纪,高尔基笔下的人物也不可避免着晕染着东正教的色彩[17]。因此,我们今日回首反观19世纪上半叶莱蒙托夫的创作,就会发现,以东正教的天使长、拜占庭的守护天使与战斗天使米迦勒之名命名的米哈伊尔·莱蒙托夫,不可避免地投身到了保护俄罗斯与东正教的使命中。另外,季谢廖娃在将长诗《恶魔》与莱蒙托夫的《天使》《每当黄澄澄的田野泛起麦浪》对比时指出,恶魔的不生不死与上帝的永恒具有天壤之别,“恶魔”的永恒不过是一种肉身与灵魂双重死亡的状态。恶魔向塔玛拉承诺时,他可以允诺的只有“人间的一切”,而人间的一切都必然会凋腐,因此上帝所能赐予凡人的永恒,恶魔却不可能给予塔玛拉[18]。由此可知,在《恶魔》一诗中,尽管莱蒙托夫为恶魔增添了诸多美德,但上帝作为绝对高于恶魔的存在,仍然是诗人心中的绝对主宰。诗人对恶魔的态度体现在了长诗的结局中——他亲手了结了恶魔的愿望,让恶魔付出了背叛上帝的代价,并再次陷入万劫不复之中。
五、结 语
在莱蒙托夫笔下,除了早年《我的恶魔》中的恶魔形象之外,其余作品中的恶魔都被诗人明确标注了“天使”的来历;诗人描绘了同一角色作为天使和魔鬼时的不同形象,甚至还解释了他们成为堕天使的原因。虽然诗人笔下的恶魔受到了普希金、拜伦等人作品中的恶魔形象的影响,但是莱蒙托夫并未把恶魔定义为单纯的邪恶者和反叛者,而是怀着怜悯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天使的烙印,为恶魔的反思和救赎留下了伏笔。莱蒙托夫诗歌中的恶魔是世俗化的,具备人的特点以及弱点,这让诗人对恶魔有着复杂的态度:一方面,其笔下的恶魔继承了文学传统中背离上帝、追求自由、叛逆不羁的特点;另一方面,诗人又在恶魔的灵魂里保留了对美的追求、对善的向往、对爱的渴望以及对天国与上帝不可分割的联系,使天使的形象融合到恶魔之中。
天使的形象作为莱蒙托夫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诗歌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来自基督教传统的形象,俄罗斯文学中的天使形象从古罗斯时期开始逐渐充盈并在19世纪具备了世俗化的特点,莱蒙托夫时期它们已不再被用以形容君王,而是常常用来赞誉美好的女性、纯洁的婴孩以及爱人。基于东正教信仰,莱蒙托夫笔下的天使不仅是尘世中灵魂的保护者,还承担着连接天国与人间、上帝与人的联结者的责任,并在死后指引灵魂去往天国。另外,莱蒙托夫还将天使善的一面融入自己作品里恶魔的形象中,使恶魔不仅更具人的特点,也表达了作者对于善恶关系的深层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