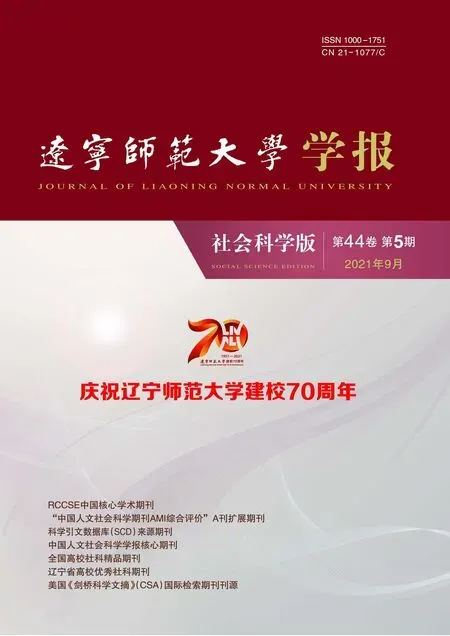论新性灵主义诗观及其中西诗学渊源
朱坤领, 冯倾城
(1.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2. 澳门大学 人文学院,澳门 999078)
龚刚从古今中外的诗学中汲取营养,立足于七剑诗群(他本人为其中的论剑)的创作实践,创立新性灵主义诗观,修正明清性灵派对天性的过度强调,提出关于性灵的核心主张,不断地对其发展、完善。迄今基本框架已成,内涵也已初具规模,并已自觉地指导七剑诗群的创作和诗学建设。本文将探讨新性灵主义诗观的学理脉络和价值及其中西诗学渊源。
一、新性灵主义诗观
(一)新性灵主义的要义
“新性灵主义”一词首次提出是在2017年前后。龚刚在《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性灵派——论徐志摩的诗学思想与诗论风格》一文中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两个方面对徐志摩展开研究,认为“他既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灵派,也是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性灵派”[1]。徐志摩强调诗歌是性灵的抒发,可谓继承了“性灵派”的衣钵,并融合了中西诗学的双重影响。思辨深度(即哲性)不仅是文学批评的要求,也是文学创作的要求,成为之后新性灵主义诗观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本文较早提出“新性灵派”一词,以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和评论为载体,对性灵做了详细研究和阐述,可谓新性灵主义的理论奠基之作。
之后不久,龚刚正式提出“新性灵主义”,对其进行了更加详尽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阐述。何为新性灵主义?他在《七剑诗选》里提出了基本主张:“①闪电没有抓住你的手,就不要写诗;②写诗需要审美启蒙,突破线性思维;③自由诗是以气驭剑,不以声韵胜,而以气韵胜,虽短短数行,亦需奇气关注。”[2]285龚刚进而提出新性灵主义歌诀:“独抒性灵/四袁所倡/厚学深悟/为吾所宗/智以驭情/气韵为先/一跃而起/轻轻落下。”他又对歌诀做了进一步的概说:“新性灵主义诗学源于创作、批评、翻译实践的心得,包括四个方面:1.诗歌本体论。其要义为:诗性智慧,瞬间照亮;2.诗歌创作论。其要义为:一跃而起,轻轻落下;3.诗歌批评观。其要义为:灵心慧悟,片言居要;4.诗歌翻译观。其要义为: 神与意会,妙合无垠[2]244。
诗歌的本体论、创作论、批评观和翻译观是新性灵主义的四个主要方面,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作为创作倾向,新性灵主义崇尚顿悟、哲思和对生命的照亮;作为批评倾向,它崇尚融会贯通基础上的慧悟、妙悟。作为一种翻译倾向,它崇尚融汇中西语言和文化的妙合。总之,诗歌活动是天赋基础上的后天修炼之所得。本文着重探讨其中的诗歌本体论和创作论。
新性灵主义是相对于明清性灵派而言的,它“新”在何处?龚刚归纳如下三点:“1.不认为性灵纯为自然本性(natural disposition)。……性灵者,厚学深悟而天机自达之谓也。”“2.肯定虚实相生、以简驭繁是诗性智慧,肯定诗人要有柏拉图所说的灵魂的视力。”“3.主张冷抒情,而不是纵情使气。……无理而自有理,悟在无形中。”[2]283-284
新性灵主义主张冷抒情、虚实相生,推崇陌生化理论,核心观念是“闪电没有抓住你的手,就不要写诗”[2]1,也即是,诗歌创作是性灵与生命体验、感悟的结合;好诗是诗人(气质、性情、情感、哲思等)、诗性(境界、诗语、意象等)和灵感(顿悟、情思、思考或外界事物对心灵的强烈碰撞)的最佳结合。龚刚归纳到:“什么是新性灵主义诗风?简言之,就是性情抒发与哲性感悟的结合。”也即是,新性灵诗包含缺一不可、相互交融的两个要素:一是性情或情感抒发,二是哲思、反思或批判。只有这样的诗,才不仅有审美价值,更能产生“闪电式的照亮”[2]1。
新性灵主义主张诗歌创作应“突破线性思维”[2]285,即突破理性逻辑和时间顺序,让诗随性而出。这是不少人不能充分把握的常识,也是诗有别于各散文文体的本质特征。结构主义思想家托多罗夫即指出不按因果关系的逻辑和时间顺序,而按空间顺序组织的作品,“习惯上不被称为‘叙事’;所涉及的结构类型,在过去时间里,在诗歌方面比在散文方面更为普遍。”[3]
(二)从明清性灵派到新性灵主义的性灵论
“性灵”概念在中国古典文论里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总体而言性灵主要指人的心灵或天性,其外在表现是性情或情性。
在南朝,刘勰认为人是“性灵所钟”[4],即人天生有灵性。钟嵘强调诗歌“摇荡情性”[5],即诗的功能是抒情。二人所谓的性灵和情性,开了后世性灵说的滥觞。唐宋文论也强调性灵和情性。司空图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6]皎然云:“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7]严羽云:“诗者,吟咏情性也。”[8]
明代的李贽提出了童心说,强调性灵,写童心便是写真心,抒发真性情:“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其立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9]的矛头直指理学的虚伪和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蹈袭。
童心说直接影响了公安派的性灵说。其代表人物袁宏道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10]165三袁反对儒家的诗教传统和前、后七子的拟古不化,主张抒发真性情,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他们对自然天性的绝对化处理和消极避世的倾向也导致创作主题的狭窄和内容的浮浅。
及至清代,袁枚发展了性灵论:“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11]他对公安派的性灵说做了修正[12],他所谓的“性灵”,性意为性情,灵意为才华,没有局限于人的天性,而是包含了后天学养和修炼的成分,但以天赋为主,后天为次。因此,他的立论没有充分重视后天的重要性。
广义的明清性灵派,以公安三袁和袁枚为代表。性灵说既是他们的创见,也是他们的硬伤。一方面,作为理学和泥古沿袭的对立面,性灵说的提出革新了诗歌创作的内容和主题,丰富了诗学理论。另一方面,天赋秉性固然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前提,但是他们过于强调之,却忽视或低估了更为重要的一点:后天的积淀和参悟。
新性灵主义对明清性灵说给予传承与创新,继承其核心概念“性灵”,并痛改前说,对性灵进行更合理且与时俱进的重新界定,注入与现代生活、审美和诗学相协调的要素。龚刚如是解释新旧性灵主义的区别,作为旧性灵主义代表的明清性灵派虽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却终究要受格律、声韵束缚,新性灵派主要以现代汉语写自由诗,不仅不拘格套,还不拘格律、声韵,且注入了现代人的主体性意识。这就是新旧性灵派的简明区分。现代诗人在写现代诗时,没必要考虑格律和声韵的条条框框;应以现代人的主体意识书写现代生活,方能与时俱进,写出符合现代审美的好诗。归根结底,诗歌和诗学的现代性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如果说袁枚的“性灵”包含了部分后天的学养和修炼,那么龚刚则把这个要素大幅提升,重新做了界定:“性灵者,厚学深悟而天机自达之谓也。”[2]283“天机”是先天的性情和禀赋,“厚学深悟”是后天的学养、涵养和体验;前者是或然,后者是化为必然的根本条件。换言之,天性只是基础,必须经由后天的蕴蓄和感悟,性灵方能发乎于外。
龚刚并未止于此,他进一步立论:新性灵主义诗学认为,所谓性灵,不仅是自然本性,也不仅是性情,或性之情,也不同于西方美学所谓灵感,而是兼含性情与智性的个性之灵。新性灵主义诗学同时认为,性灵是生长着的,因而是可以后天修炼、培育的,钱锺书所谓“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即是揭示了性灵的可生长性。
性灵“兼含性情与智性”,具备此特征的诗即是新性灵主义诗,也属于现代哲性诗和文人诗的范畴。新性灵派的主体是七剑诗群(论剑龚刚、问剑杨卫东、花剑李磊、断剑罗国胜、柔剑张小平、灵剑薛武、霜剑朱坤领),他们的诗便是现代文人诗,将另文详论。“具有可生长性”是龚刚本段论述的关键词,强调诗人诗艺和诗性的不断进步,其途径便是后天的历练和感悟。
“个性之灵”强调诗人应有不同的个性,以顺应丰富多彩的世界和诗意的要求。个性不同,即便是同题写作,不同诗人营造的诗意也是不同的。以七剑诗群为例,七人的学养和诗歌理念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又性情和诗风各异,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笔者(为七剑之霜剑)做了如下的概括:
写雪,也同样能够体现七剑不同的性情和诗风。论剑的雪空灵:“却听到了/雪花跌落湖水的声音”(《老照片(外二首)》之《闻江南降雪感赋》);问剑的雪意象感强烈:“词语和雪花自由飘落”(《与那些陈旧的人对话》之四:给策兰);花剑的雪感伤:“白雪覆盖田野,空洞的乡村/我们还要乡愁有什么用”(《乡愁与哀愁——悼念余光中先生》);断剑的雪意象唯美而忧伤:“飘着月色时也飘着雪花”(《无题·少年游系列》之十);柔剑的雪是浪漫的精灵:“在雪的遐想中/飞升”(《精灵》);灵剑的雪充满思辨:“我说我们可以卖火柴/擦燃的刹那可以照亮诗歌的小女孩”(《醉雪》,未选入本书);霜剑的雪唯美而温馨:“北风抚古筝/万户掌灯密云彤/雪舞满天星”(《暮雪》)[2]285-286。
龚刚的上述论点可以解释文学作品产生的内在机理。由先天性情和禀赋所产生的作品(如骆宾王的《咏鹅》和亚历山大·蒲伯的《孤独颂》)并非没有,但数量极少。绝大多数作品是厚学深悟,而后天机自达。例如李白的《将进酒》,如果没有他对人生短暂、不如意的感悟,又怎能把狂放的天性和人生的悲剧性写得如此具有哲性?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如果没有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和思考,又怎能写出脍炙人口的《未选之路》?即便是极少数天赋之作,也有后天的因素。骆宾王假如在生活中从未见过鹅,又如何能在七岁写出《咏鹅》?蒲伯十二岁时对生死已有深刻感悟而作的《孤独颂》,也因他身体残疾在伦敦受人耻笑,从而厌恶城市生活,向往生死皆无人知的乡间隐逸生活。
二、新性灵主义的中国现代诗学渊源:五四新诗以降
(一)五四新诗
五四新诗是旨在颠覆传统文化、建设现代文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指从1917年初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到20世纪20年代初之探索初期的诗歌。胡适力主摈弃文言文和格律诗,转向白话文和自由诗,在《文学改良刍议》里提出不模仿古人、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八事”,成为初期新诗的纲领。
需要指出的是新诗与白话诗不能混为一谈。汪剑钊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区别:“新诗之‘新’最重要的还是其中贯穿了一种自由精神,对人性和美的再认识和价值重估。”[13]自由的精神,对人性和审美的再认识,成为此后百年中国新诗一以贯之的追求。
从诗学的角度看,中国新诗从一开始便走上了一条歧路。意识形态议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也使新诗承载了过多的非诗负担,损害了诗质和诗美。胡适提出的“八事”主张以及他初期的新诗创作都具有先天不足的弊病。且看五四新诗领袖胡适最初的一首新诗,发表于1918年《新青年》4卷1号上的《一念》: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这首诗是勉为其名的,只是白话散文辅以押韵,并借用了西诗的分行;思维浅显,过于口语化,缺乏打动人心的诗意。可以说五四新诗“走出了一条既不中也不西的艰难之路:西方的诗歌只学了个皮毛,却把自家延续千年的、美轮美奂的诗歌传统差不多丢了个干净。惜哉!”[14]
胡适并非真正的诗人,初期的新诗只能勉为其名,他的“八事”纰漏众多,并未构建真正的诗学,因此他是中国新诗并不算成功的领导者。这与西方现代诗的建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新性灵主义是对五四新诗的传承与创新,一方面继承、发扬它的自由精神对现代人性和审美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思它口语化、线性思维和诗意肤浅等方面的弊病以及诗学建设方面的不足。龚刚进而提出自己的诗观以期修正胡适等先驱的不足,填补中国新诗理论的空白,为当代和未来的新诗(本文里的新诗指现代诗)创作提出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理论主张。
(二)从新月派到朦胧诗
20世纪20年代,新月派开始反思五四新诗诗艺粗陋、语言散文化的弊端,提倡形式的新格律化和内容的理性节制情感。闻一多提出了 “三美”主张,即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辞藻)和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即具有新格律。可以说新月派是中国新诗诗学探索真正意义上的开始。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象征派师法法国象征主义的暗示、对比、联想等手法。李金发深受波德莱尔的影响,思路跳跃性大,使用一系列“恶之花”风格的意象(如污血、枯骨、寒夜等)表达丑陋、死亡、畸形等主题,抒发凄苦的情感。《弃妇》便具有这样的特征:“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长染在游鸦之羽,/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静听舟子之歌。”
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使用现代意象,注重象征性、荒诞性、意识流、意义的含混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卞之琳的《断章》言简意赅。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表达了现代的爱国情:“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20世纪40年代,九叶派主张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现代诗,成就突出,影响深远。穆旦的《赞美》使古老的中国农民具有了现代审美意义。
其后,现代诗渐被边缘化,直到朦胧诗群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出现。朦胧诗学习西方现代诗歌,使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营造含蓄、多义、朦胧的诗意。“拒绝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指令写作,而回到真实的情感和体验,表达在脚下土地发生漂移时的困惑、惊恐、抗争的情绪和心理,这在‘文革’初始的诗歌写作中,无疑具有强烈的叛逆性质。”[15]例如,北岛的《回答》书写内心的冷峻:“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顾城的《一代人》则抒发了对光明的追寻:“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朦胧诗接续了五四新诗、象征派、现代派、九叶派等的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促成了新时期文学的质变。
总之,五四新诗、象征派、现代派、九叶派、朦胧诗等不断探索、学习、借鉴,促使现代诗在古老中国的土地上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地逐步发展起来。尽管还很难说成熟,但奠基和开拓之功不可磨灭。新性灵主义以学习和反思的姿态把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现代诗性元素吸收、融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和七剑诗群的创作实践。换言之,新性灵主义的诗学主张是对自五四新诗以降诗学和诗歌创作的传承与创新,舍弃、修正其所短,继承、发展其所长。
尤其需要指出朦胧诗是距离当代最近的主要诗歌潮流,新性灵派从中受益匪浅,但同时也认识到朦胧诗尽管人才济济,杰作众多,但兴盛的时间过短,诗艺也有缺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缺少系统、有力的理论体系的支撑,也没有形成实体流派的强大合力。这在某种意义上促使龚刚酝酿新性灵主义理论,旨在把诗歌创作和诗学建设同步推进,并促使新性灵派的主体七剑诗群形成强大的群体合力。
三、新性灵主义的西方现代诗学渊源:从意象派到意象东突西进的演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里意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总体上意指人的主观心理,象指客观物象,意象指意中之象,即能够在人内心产生反应或对应的物象。陈希详尽考察了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文论里的演进,从《周易》“象”的概念,到西汉王冲首次把“意”和“象”组成一个词,再到刘勰(“窥意象而运斤”)、司空图(“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以降的演化。他认为:“意象本意是‘意中之象’,显示了中国诗学交感寄兴的审美方式和‘离形得似’、注重神韵的审美追求。”他也探讨了西方意象论的发展轨迹,从柏拉图(“事物的影像或形象”)到康德(“想象力所形成的形象”),到克罗齐(“意象是直觉表现论的中介”),再到庞德(“一刹那思想和感情的复合体”),得出结论:“总体趋势是从客观趋向主观,从表象转为内心关照和直觉。”[16]
发端于1908年、终结于1917年的美国意象派运动以克罗齐、伯格森的直觉主义美学为依托,师法古希腊、古罗马诗歌的简练,以及现代法国印象主义诗歌的标新立异,尤其是汲取中日古典诗歌独有的意象和凝练的诗语。意象派创始人庞德受到中国(和日本)古典诗歌的启发,主张提取基于直觉、具有本质特征的意象,直接客观地呈现事物,为日益刻板、说教的西方诗歌注入新鲜血液。1912年庞德首次使用意象派的名称。
经过庞德等人改造的、重形似的意象已经大异于中国重神似、轻形似的传统审美观,可以称为现代意象。1913年下半年从美国东方学家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sa,1853-1908)遗孀那里获得的一摞笔记和手稿使庞德首次了解到日本能剧、中国古典诗歌和书面文字里意象的力量。意象派主张的意象经历了从图像到意义的重大转变。他们还主张弃明喻而取隐喻,吻合了现代诗学的发展趋势。尽管意象派存在的时间短暂,理论也并不系统,但它引进的“意象”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成为现代诗歌和诗学的核心元素。意象派及其后续者成功创作了不少现代意象诗。例如庞德的《在地铁车站》中的主要意象花瓣与面庞具有关联性,产生了丰富的诗意和意义。
龚刚汲取并发展了意象派的长处,其新性灵主义的主张与意象派的上述原则有诸多相通之处。他在吸收和借鉴意象派现代性的基础上,进行了性灵化的发展。我们可以逐一对应他在上述六点上与意象派的异同:1.龚刚主张日常语言入诗,他本人的诗歌创作即是如此;但是,与意象派主张“最精确的词”不同,他主张现代诗语的多义性。2.他主张现代诗应营造内在的节奏,“不以声韵胜,而以气韵胜”[2]285,但也主张适度的声韵和平仄。3.他强调诗歌“是与现实的交锋,也是对现实的照亮”[2]1,主张现代生活入诗,题材和主题应与时俱进。4.他主张诗歌须有灵魂的内核,有实感,反对空洞无物。5.他的观点与意象派“坚实而清晰的诗歌”的主张差别较大,强调多重所指乃至不确指,这正是性灵的体现。6.他主张“以精短诗行涵盖一种精神,一个时代甚至一部历史”[2]1,即诗歌的内核应凝聚在凝练的诗语之中。
作为西方现代诗核心元素的现代意象以及整个西方现代诗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创作和诗学建设。从五四新诗、象征派、现代派、九叶派到朦胧诗及其之后的各现代诗歌流派莫不如是,这已成为公认的事实。这其中也包括了七剑诗群的创作和诗学主张;如上所述,龚刚的主张与意象派的主张便有许多相通之处,体现了新性灵主义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精神实质。
四、结 语
本文探讨了新性灵主义诗观的要义及其中西诗学渊源,新性灵主义既从中国古典和现代的诗歌和诗学里汲取营养,又接受西方现代诗歌和诗学的财富,打破古今中外诗学的界限,强调对古今中外诗学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凡有价值的理论和观点皆可吸纳或改造,为我所用。在中国诗学渊源方面,新性灵主义吸收古典诗学的精华,对明清性灵派给予传承与创新,对性灵做出更合理和与时俱进的界定,并师法五四新诗以来现代诗的创作和诗论。在西方诗学渊源方面,新性灵主义侧重学习、借鉴美国意象派的主要原则主张,使用现代意象写作现代诗。
新性灵主义作为新兴的诗歌理论,注重“厚学深悟而天机自达”的性灵、从心而出并包含哲思的诗歌创作、“智以驭情/气韵为先”的诗性语言、“瞬间照亮”的诗意和诗性智慧。新性灵主义的框架和内容已具雏形,并仍在不断补充、完善,已经成为新性灵派之主体——七剑诗派的主要理论方向和创作指南,必将发展成为完整、独特的诗学理论体系,对中国现代的诗歌创作和诗学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