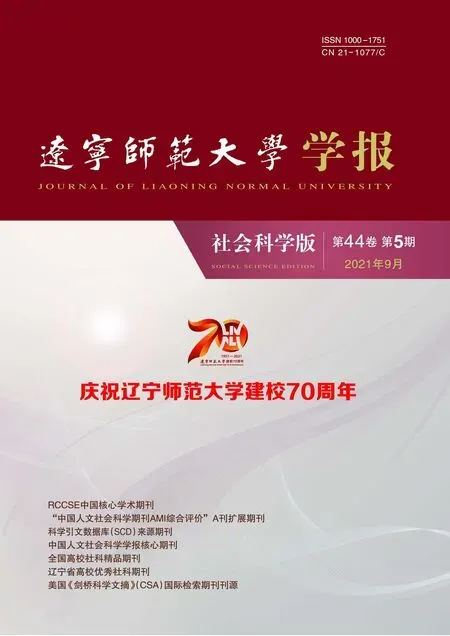论“汉语欧化史”
刁 晏 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在中国文学语言的研究中,有人提出了以下这样的问题:中国自身的古白话是何时开始转化为欧化的白话的?而给出的答案是要归功于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认为是他们创作了最早的欧化白话文[1]。这样,从西方传教士到晚清白话文运动,再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就构成了一条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展线索[2]。至于“欧化白话文”的起点,有人定在了明末清初[3],如果这样算起的话,那么,汉语欧化已经有近500年的历史了。
不过,相对于文学界,汉语学界的欧化研究则要“保守”得多,基本仍以“五四”以来的白话文欧化或欧化白话文为研究对象,因为很多人的认识是“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活动开创了汉语欧化进程的先河”[4],而这一“传统”的形成与维持,主要因为以下这样根深蒂固认识的普遍存在:“自从‘五四’倡导白话文以来,汉语所受欧美语言的影响太多了。现代汉语,尤其是普通话书面语,是已被西方语言、西方标点符号渗透和改造了许多的语言。”[5]
无论着眼于文学界大大向前延伸的近500年,还是立足于语言学界划定的100年,总之“欧化”与汉语相生相伴已经有不短,甚至可以说很长的时间了,在这一过程中造成了汉语既有面貌的极大改观,并由此而广受关注,进而成为汉语研究中一个持续时间长达百年的专门领域。那么,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我们现在是否可以提出“汉语欧化史”这一概念,进而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欧化研究分支领域,以与欧化的共时研究形成合理的二元分布?我们认为,这一提法既有现实需求,也有事实依据与理论基础,因而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本文即就此展开初步的讨论。
一、汉语欧化史的提出依据
事实上,至少早在20年前,史学界就有人提出了“欧化史”概念[6],而我们也于2019年正式提出了“汉语欧化史”[7],只是限于篇幅以及并非文章重点所在,所以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证。因此,本文算是旧话重提,首先讨论汉语欧化史的提出依据和已有基础。
(一)汉语欧化史的认识基础
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事实上,绝对的不变是不存在的;语言的任何部分都会发生变化。每个时期都相应地有或大或小的演化。这种演化在速度上和强度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无损于原则本身。语言的长河川流不息,是缓流还是急流,那是次要的考虑。”[8]这里虽然是就整个语言立论,但是,在我们的语言即现代汉语的长河中,自然包括“欧化形式”这一部分,所以,上述表述可以作为我们提出汉语欧化史的认识基础。其实,类似的表述在名家的经典论著中十分常见,如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萨丕尔这样写道:“每一个词,每个语法成分,每一种说法,每一种声音和重音,都是一个慢慢变化着的结构,由看不见的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沿流模铸着,这正是语言的生命。”[9]如果说这是着眼于具体语言项目的话,那么中国社会语言学家程祥徽则是立足于宏观的认识:“语言的生命如同放大了的人生,每时每刻都在变迁,永远保持运动的形态。”[10]
人们讨论语言的发展性,并不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现象或特点提出来,而主要是为了说明或强调对其加以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比如索绪尔就特别强调历时的语言研究,并提出了“共时与历时”这一对概念及研究范畴,被后人誉为对现代语言学的重要贡献之一。
具体到汉语欧化,也有一些观点和表述可以直接作为建立汉语欧化史的认识基础。比如,何九盈指出:“现代书面语的发展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欧化的过程。”[11]44这里把欧化作为一个“过程”,并与现代书面语的发展相关联,自然是着眼并立足于前者的发展性;而赵晓阳则对这一过程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发展建立现代白话的过程,也就是古白话逐渐欧化的过程,是将原来觉得‘不顺’的新式白话也逐渐变‘顺’的过程。”[12]很显然,这里的“不顺”与“顺”,既是汉语用户的改造使然,也包含着其对欧化态度及接受程度的改变,同时更是欧化现象历时发展变化的结果,而这样的认识无疑比上引何说深入了一步。周光庆、刘玮结合汉语的发展,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讨论:“事实上,八十年来,‘我们的语言’总在不停地‘欧化’——纠正,进一步‘欧化’——再一次纠正;‘欧化’了有必要‘欧化’的,纠正了过分‘欧化’的。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我们的语言’有了不断的变化,得到了不断的发展。”[13]这里把“我们的语言”即欧化的汉语纳入不停的“欧化→去欧化→再欧化→再去欧化”发展过程中,从总体上概括了汉语欧化的历时发展演变模式和路径;而思果则着眼于更长的历史阶段,从另外的角度阐述了同样的认识:“不良的新鲜说法大都遭到淘汰,这要归功于多数人都有头脑。另一方面,有些生硬的洋话,经过时间这个熨斗熨来熨去,也渐渐变得自然了。三十年前特异的说法因为一再为人采用,已经成了‘土产’,再过一两代也许给人视为陈腐。”[14]这里不仅立足于过去与现在,还把视线引向将来,即“再过一两代”以后的发展,而我们认为,这也是汉语欧化史观的应有之义。
以下一段表述,把欧化研究引向一个新的领域,其实质也是指向了欧化史的研究:“重读这些时隔半个多世纪的文字(按,指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六章‘欧化的语法’),使我们在这里至少想到了两个问题:1.王力上述的现代汉语欧化现象如今已不再使我们产生异质的感觉了,这些欧化语言已成了我们语言中的血液。2.依照王力上述观点,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系统地研究一下当代汉语的‘欧化现象’。”[15]这里把欧化现象按“现代汉语”和“当代汉语”进行区分,而这在我们看来,不仅表现出史的见解和认识,而且已经是在进行史的阶段划分了。其实,早在此前就有人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了汉语欧化进程及历史的阶段划分:朱自清把白话文的欧化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模仿欧化语法,一般人行文时,往往有牵强不过的词汇,读起来感觉非常别扭;第二个时期则注意到欧化的方法,如徐志摩的文章就是代表这个时期的成功作品[16]。
总体而言,在已有研究中,类似以上这样可以直接归为汉语欧化史认识基础的观点还不多见,而比较常见的,是立足于当下的相关表述,从中依然可以认识到汉语欧化现象的历时性,以及建立汉语欧化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比如,作为语言学家兼作家,戴昭明用极富文学色彩的语言,描绘了这样一幅情景:“我们今天涵泳在与近代汉语相比早已面目全非的当代汉语的汪洋大海中,只觉得弥漫周身的全是汉语之水,除非经过精细的专门研究已不能一一确指其中哪些来自黄河长江,哪些来自恒河印度河,哪些来自泰晤士河、莱茵河或密西西比河了。”[17]文学界的相关表述如:“现代白话的确是‘中西结婚’生产的混血儿,成分复杂,欧化的血缘是难免的。”[18]
可以想见,当今汉语的上述现实特点,自然并非一时形成,而必然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而这也就是汉语欧化的历史。在汉语学界的具体研究中,类似的表述时能见到,以下再摘引两段:
近三十年来,在祖国语文的表达方式和方法上,起了重大影响的,是翻译作品和翻译文章。在十几岁到五十几岁的人中,凡是能写文章的,他们所写的文章,或多或少都受有翻译文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要继续扩大和深入下去。这是因为接触翻译文章和翻译作品,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曾经是和将要是我们生活中的常事[19]。
事实上今天的汉语里,来源于外国语的影响而我们逐渐不大觉察的东西,已经相当多了。比较长的句子,比较多的修饰语,比较多的联合成分,特别是运用虚词连接的联合成分,比较多的被动句,这一切都或多或少是受了西洋语言的影响才广泛应用起来的。这类欧化句法,一般是先由翻译作品介绍进来,逐渐影响了一部分人的写作,写作再影响了口语[20]。
总之,即使是立足于已有的认识,无论是就整体性的“语言”还是局部性的“欧化”现象而言,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可以作为汉语欧化史的重要理论支柱。
(二)汉语欧化史的事实基础
我们在最近完成的一篇论文(1)该文名为《欧化及其研究的新思考:写在汉语欧化研究百年之际》,发表于《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中,呼吁在汉语欧化研究中建立起历时观,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整体的欧化历时观,即把欧化作为一个整体现象,来观察和分析其在汉语中从“泊来”到生存发展,或者是遭到淘汰的过程;二是局部的欧化历时观,指的是在众多的欧化领域或方面中对某一领域或方面历时发展变化的认识;三是具体现象的欧化历时观,认为各种各样的一切欧化形式都有其发展过程,从研究的角度来说,都应该了解甚至还原它们的历史。
下面,我们就分别从这三个方面,来讨论汉语欧化史的事实基础问题。
首先看整体性的欧化发展变化事实。通过以上的一些引用,读者就可以对此有所认识,而以下的表述则主要是立足于欧化的整体发展。周红民指出,“无论是翻译内部,还是翻译外部,都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汉语在与异族语言的碰撞中一直在变化,在吸纳新的质素,在不断淘洗,不断锻炼,不断更新,我们也需要这一变化去承载、去表现不断变化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21]王飞认为,20世纪30年代掀起的“大众语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矫正滥用过分使用欧化、日语句法的文腔和洋调。“大众语运动”在欧化语法结构特征基础上吸收了本土中国大众的口语、俗语,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了白话文过分“欧化”“日化”的弊端,但是有些势力强大的“欧化语”至今顽存于现代汉语中,影响日益恶劣[22]。
影响是否“恶劣”,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另外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以上两段论述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都直指一个与“欧化”相对的概念:“去欧化”。邵莉、王克非首先立足于翻译语言提出了这一概念,指的是欧化形式使用频率下降,使用范围缩小,或是在用法上更趋近汉语传统规范等现象[23],而郝锐则立足于整个欧化语言,着眼于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欧化形式的系列“收缩”表现,对此做过具体的讨论[24]。
我们认为,抓住“欧化-去欧化”这一作用与反作用交替或交错进行的事实,对整个汉语欧化及其历史发展变迁大致就可以“思过半”了。巴金曾经说过:“有一个时期我的文字欧化得厉害,我翻译过几本外国书,没有把外国文变成很好的中国话,倒学会了用中国字写外国文。……在翻译上用惯了,自然会影响写作。……幸好我有个不断修改自己文章的习惯,我的文章才有进步。最近我编辑自己的《文集》,我还在过去的作品中找到不少欧化的句子。我自然要把它们修改或者删去。”[25]美国语言学家Kubler对巴金作品的欧化及去欧化表现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以长篇小说《家》1933年的初版和1957年的修订版为对象,对二者之间词法、句法两个方面的异同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对比[26],为上引巴金的话提供了一系列绝好的例证。例如,初版的《家》中一共有272个被动句,而修订版中删除、省略或改为主动句的就多达116个(2)被动句欧化是汉语欧化研究中的“老节目”,人们普遍的认识是由于受欧化影响,汉语被动句的使用频率大大提高,使用范围也有所扩展。所以,修订版对初版的删改,正是去欧化的具体表现。。
以下再看局部性的欧化发展变化事实。近年来,人们对汉语欧化内容及范围的认识日趋广泛,如张彤指出,“‘欧化’可以概括近代以来汉语与欧洲语言接触产生的文字、词汇、语法、语体等方面的变异,汉语欧化现象曾以诸如‘拉丁化’‘拼音化’‘外来词’‘欧化语法’等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27]早在此前,王力就把现代书写和印刷中字的顺序、行列的顺序、文章的分段、每段的开始,以及引语、注释、夹注、序言、例言、目录、附录、参考书目、索引等,都归入欧化行列[28]334-396。在这样的认识下,汉语以“要素”或“领域”等划分的局部性欧化事实无疑是非常多的。大致言之,上述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其从无到有或从有到无、从少到多或从多到少、从不稳定到稳定或从稳定到不稳定等的发展变化,而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局部性欧化发展事实。
例如,在外来词语的研究中,很多人都谈到先音译后意译的发展过程(如“水门汀→水泥”“维他命→维生素”),就是对其历时发展规律的揭示。邵莉基于历时翻译语料库,考察了1918—1936 年间鲁迅小说译作中的词汇欧化现象,对欧化特征显著的代词、量词、介词、连词,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描写和分析其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的变化趋势。调查结果显示,以上四类词均存在明显的欧化现象,且欧化强度与形态发生了历时变化:后期译作中代词、量词、介词使用频率增加,表明欧化趋势持续增强,但连词使用频率下降、介词“当”的连词化用法消失又揭示了与欧化相反的变化趋势。文章的结论是:“鲁迅的‘欧化’语言观与时代语言风潮相呼应,其译作语言中的欧化现象,是译者也是时代的风格标记。对鲁迅译作中句法欧化现象的历时考察,揭示了译作语言的动态发展,从微观层面反映了现代汉语演变的轨迹。”[29]我们认为,这样的研究非常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属于汉语欧化史的具体研究了。
最后看具体欧化现象发展变化的事实。这里针对的是那些数量巨大的作为“个体”的欧化现象,比如一个具体的词,某一种句法格式,某一种修辞方式,某一个读音,甚至于某一个标点符号,等等,它们中往往都包含着欧化现象发展变化的部分事实。比如,有人指出,“马克思”一名的音译,我国先后出现过10个不同的书写变体:麦咯士、马陆科斯、马尔克、马儿克、马可思、马克司、马尔格时、马克斯、马格斯、马克思;列宁于1897年被流放的“舒申斯克村”也曾被译作12个不同的形式[30]。以上10个人名和12个地名,自然不可能同时显现或退隐,而总要有一个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变化的过程,而这就是历史,就是这两个专有名词的欧化史。梳理革命导师译名等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过程及具体的时间节点等,不仅具有汉语欧化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史等,也有其意义和价值。
以下我们再举一个语法方面的例子:
(1)他是一个画家,住在一条老闻着鱼腥的小街底头一所老屋子的顶上一个A字式的尖楼阁里。(徐志摩译《巴黎的鳞爪》)(3)转引自刘珍振、桂林《从“的”字滥用看翻译中的汉语西化问题》,《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3年第5期。
这里主要涉及一个屡遭非议的“恶性欧化”现象,即滥用结构助词“的”,曾被概括为“的的不休”[31]。时至今日,这样的现象已经较少见到,所以有人才就此例作出以下评议:“徐译之佶屈聱牙着实令一代又一代热爱他的诗文的中国读者始则瞠目结舌,继而顿足叹息,好端端一位极有才华的诗人竟然沦为如此蹩脚的翻译匠!”[32]
其实,类似用例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各类文本中相当常见,例如:
(2)凡是一个哲学家,都有他的一定的主张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3.23)
(3)我常说清代的汉学,是朱熹的格物的工夫加上了王守仁的良知的精神。费若便是一个很好的例。(《晨报·副刊》1921.10.17)
除“的”外,徐译例句中的“底”很大程度上也是欧化的产物,按当时的“规则”,“的”用于一般定语和中心语之间,而“底”则用于领属性的定语与中心语之间[33],所以,这一时期结构助词欧化表现的准确表述应该是“的、底不休”。然而,这样的“底”现在早已不用,所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在“底(de)”条下注为“旧同的(4)转引自刘珍振、桂林《从“的”字滥用看翻译中的汉语西化问题》,《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3年第5期。”,即一般的结构助词。这一“底”的用例再如:
(4)他们底自然律和分别什么是自然的底观察,是由动物界中与人不大相干的一部分产生出来的,至于那多过与人类似生活的动物他们可未观察得到啊。(《晨报·副刊》1922.5.6)
按,此例中“底”两次出现,其中第二次是与“的”共现并用。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样的形式陌生化程度极高,而可接受程度极低,但是在早期现代汉语中却并不鲜见。再如:
(5)而事实上却是由袁世凯耍了一套王莽到赵匡胤耍厌了的底老把戏,请溥仪退位。(《语丝》1925.1.5)
像“的底”连用这样的形式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无疑是历时变化所致,而它本身也提供了一个汉语欧化史的实例。
有人曾以“‘欧化’语言的演变”为题,从实证角度,以翻译“欧化”语言发展四个时期的具体译例来验证其百年来的演变历程。文章结尾更是直接提出了 “‘欧化’语言的发展史”[34]。这里虽然是就翻译语言立题,语言事实及论证也稍嫌简略,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整个汉语欧化史的部分事实和相关思想。
二、汉语欧化史的意义和价值
在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欧化的思想与实践与之伴随始终,并且后者作为前者的一个最重要影响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百年汉语的基本面貌、精神和走向[7]。正因如此,100年来,“欧化”不仅成为汉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并且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支研究领域。郭鸿杰对现代汉语欧化研究的状况和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梳理,在此基础上也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共时的平面研究多,历时的综合研究少”[35];成嘉露对20世纪40年代至今70多年来的汉语欧化语法研究,从概念的界定、性质的判定、现象的考察、欧化的特点及理论的探讨五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文章也提出了相关研究的五点不足,其中第二点是“大部分研究者没有明确的语源意识,没有认真考究语法成分的始源,没有将新兴的语法现象和复兴的语法现象区分开来”,第三点中包括“共时的平面研究较多,历时的综合研究较少”,第五点是“研究者基本上以五四以来现代汉语作为研究对象,对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过渡阶段——清末民初这一阶段缺乏应有的关注”[36]。
以上对欧化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概括都很客观,也很准确,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因于研究者欧化历时观的缺失,同时也从反面说明建立汉语欧化史的必要性,甚至是迫切性。
我们认为,在语言研究中,对于任何一个方面或一项内容而言,共时与历时的结合都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所以,我们不仅要对汉语欧化现象进行共时平面的深入研究,同时还应立足于历时平面,研究它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发掘其背后蕴含的规律,进行理论的升华与阐发,而这无疑就是汉语欧化史的主要研究内容。
总体而言,建立汉语欧化史的意义与价值巨大,以下我们分别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一)汉语欧化史的实践意义和价值
这里指的是汉语欧化史对于具体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和说明。
第一,对汉语欧化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如上所述,当今的汉语欧化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而其中属于历时或与历时有关的占了很大一部分,也就是说,还远未形成以上所说的共时与历时并举的两翼模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早在20世纪40 年代,朱自清在给王力《中国现代语法》所作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中国语的欧化或现代化已经二十六年,该有人清算一番,指出这条路子那些地方走通了,那些地方走不通,好教写作的人知道努力的方向,大家共同创造‘文学的国语’。”[28]12多年以后,还有人就此继续发声:“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大力改造汉语书面语言为己任,曾经在短时间内创造了一种夹杂着大量外文单词、汉语音译人名、地名的欧化文体,成为一时之尚,事过境迁,那个时代的文本,为后代的读者究竟留下多少在语言上堪称典范的佳作,值得认真甄别。”[37]
这种立足于当下,跟欧化之初或其某一阶段的对比考察与分析,无疑是汉语欧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它本身对于欧化史的知识建构,无论是从整体上对于汉语欧化之路,还是具体对某一或某些欧化形式的发展变化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汉语欧化史的研究还能够纠正一些业已存在的片面或不正确认识,从而提高欧化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比如,关于欧化起点,除了本文开头所说有人定在明末清初,以及“五四”时期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认识,例如:
汉语“欧化”现象的产生可以追溯至300多年前,而真正的大规模显现则应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科技和思想文化大规模涌入中国开始,而其最直接的载体就是翻译作品的大量出现[38]。
汉语的欧化现象是鸦片战争以来英汉语言接触的产物[39]。
汉语自19世纪末开始走上漫长的欧化之路,在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汉语欧化痕迹均十分明显[40]。
这里的300年前、鸦片战争和19世纪末,显然是三个不同的时间节点。
再如,有些讨论欧化现象的论著,可能范围过宽,即把有些不一定属于欧化的现象也纳入其中,特别是在语法研究方面。崔山佳就此指出:“欧化现象被扩大化了,把好多本来应该属于汉语固有的语法现象,硬是套上了欧化的印记。”[41]上述问题的造成原因之一,还是历时因素的缺失。如果能结合汉语的历史及现实以及该形式的产生过程和实际使用情况,仔细考镜源流,多方求证,应该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和认识。
此外,除了白话文的欧化外,在近代以来中国的书面语言体系中,还长期存在文言文的欧化问题,典型的文本如梁启超的“新民体”,林纾的翻译小说,以及章士钊的“逻辑文”,它们以及其他更多相近的文本形式共同构成了“欧化文言”[42]。站在今天的立场和角度,欧化文言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有其完整的发生、发展以及式微过程[43],相应地,我们不仅应该有“欧化白话史”,也还应该有“欧化文言史”,而后者理应成为欧化历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认为,随着欧化史概念的提出,以及具体研究的开展,欧化文言及其发展演变的历时研究也会提上日程。
总之,客观地说,汉语欧化史的研究基础还非常薄弱,甚至还存在一些死角。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一些相关成果,几乎都是一些零星的讨论,或者是作为附带内容的偶然涉及,既不具备基本的规模,更难成完整的体系,甚至还有一些片面或不正确的认识,而这也正说明汉语欧化史的建立不仅在一定,甚至很大程度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同时也展示了这一研究的广阔发展空间和前景。
第二,对现代汉语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早在近30年前的1992年,笔者首次提出应该对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演变进行独立、系统的研究[44],差不多过了10年,在积累了一定的相关研究成果和知识后,我们把这一研究提炼、升华为“现代汉语史”[45]。20年来,我们的几乎所有研究都围绕现代汉语史进行,最新的一项成果是由笔者担任首席专家的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汉语发展演变数据平台建设与研究”。目前,该项目已经顺利结项,最终成果(共9部专著)也已列入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名单,将于2021年年内出版。
其实,即使仅仅根据以上所引的部分观点和表述,我们也能够认识到,当今的语言即现代汉语普通话已与欧化融为一体,甚至难分彼此,所以谈现代汉语的发展离不开欧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无论进行共时层面还是历时层面的研究,都离不开欧化史的观照与参与。关于这一点,邹嘉彦、游汝杰明确指出:“‘语言接触’是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其最常见的结果是词汇的互相借用,也可能造成语音成分和语法成分的互相渗透,从而改变语言的语音结构和句法结构。‘语言接触’是语言或方言演变的原动力之一,所以,研究语言接触是研究语言演变的重要途径。”[46]李如龙也就此谈道,“古往今来,语言接触普遍存在,因而自变与他变是长期并存的两种语言的演变。他变通过自变起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研究自变是重要的,但不能不研究他变。语言接触的研究对历史语言学是不可或缺的补充。”[47]
我们在研究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在有些时候和有些情况下,研究某一或某些欧化形式从产生到发展演变的过程,本身就属于现代汉语史的研究,而反过来也是一样。比如,汉语的传统造词法以句法造词为主,而进入现代汉语阶段以后,词法造词现象日益普遍,并且成为相当能产的造词方式,由此而构成了一大批各类词族,如“-性、-化、-者、-员、-体”等。如果细加梳理,这些用于构词的准词缀或类词缀,多是由于欧化因素的影响而活跃起来,而它们在现代汉语的不同阶段,活跃程度也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极富“史”的内涵。
再如,早期现代汉语中,数序助词“们”有时可以用于指人名词以外的其他名词,表示“复数”,黎锦熙、刘世儒认为这是欧化用法[48]。例如:
(6)现在流行的古镜们,出自塚中者居多,原是殉葬品。(鲁迅《看镜有感》)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去欧化”的浪潮中[24],这一用法逐渐退隐,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又开始“复显”,并且与早期现代汉语相比使用频率更高、范围更大[49]400-412。例如:
(7)昨天京城的大街小巷还是皇冠、奥迪、桑塔纳们的天下,今天黑压压灰溜溜的车流忽然间被明快黄黑色白色调理得有了生机。(《中国青年报》1992.2.19)
(8)我伫立在书架前,看着整齐排列的书们,仿佛听到了书的呼唤。(《人民日报》2004.7.15)
时至今日,还不断有新例产生,表明这一形式依然具有活力。例如:
(9)信用卡积分权益大缩水 如何与花呗们“短兵相接”?(《国际金融报》2020.7.20)
(10)资本的抢入无疑让教育行业成为今年最受瞩目的领域之一。百亿资金的加持下,教育机构们纷纷发力营销。(人民网2020.12.30)
按:以上二例中,前例是一篇报道的标题,正文中说明,这里的“花呗们”指的是花呗、任性付、白条等代表性消费贷产品;后例除了“教育机构们”,同文的标题及正文中还用到“机构们”。
其实,欧化史的相关研究,不仅对于现代汉语史而言非常重要,有时对于现代汉语的本体及应用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这里讨论的“们”,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各类工具书以及一些论著,在提及这一用法时,多视之为修辞现象,比如吕叔湘就认为,“指物名词后边加‘们’,是拟人的用法,多见于文学作品。”[50]就早期以及当下的大量用例而言,这样的概括和表述应该还有进一步斟酌的必要与空间。
(二)汉语欧化史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对于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或一项成熟的研究而言,不能没有理论的追求。就汉语欧化史而言,自然也是如此,所以它的建立自然也有理论方面的诉求,而这也就使其具有了理论意义和价值。
郭鸿杰指出:“欧化研究将对国内外有志于从事弱势语言受到强势英语影响的对比研究的同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在各种语言接触背景下,语言变化表现出的共性和差异。此外,该领域的研究还将为语言变化、社会语言学、对比语言学、汉语的演变、英语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大陆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等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利用价值。”[35]这虽然主要是立足于共时而言的,但是如果把视角转移到历时方面,以上表述基本仍能成立。
以下,我们从两个方面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语言接触学理论。汉语欧化现象是语言接触的产物,因此属于接触语言学的研究范畴。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接触语言学的研究,大致都是在共时或泛时层面进行的,其基本原因,就在于认为语言接触通常通过借用而导致演变的发生,但语言接触本身不是演变[51]。其实,即使就“最短”的时间算,即认为汉语欧化始于“五四”时期,那么在这一百年间,英语对汉语持续施加影响,导致后者不断地变化,甚至产生一些阶段性的特点,比如其在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表现是词汇系统的丰富、字母化现象日益凸显、英语外来词的语素化和源自英语的类词缀导致多音节新词族的增加以及某些词语意义的变化[52]。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汉英之间的语言接触不可能是按同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持续而下,而是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条件下有所变化,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使用状况和特点。关于这一点,李如龙指出,“语言接触的过程总是由浅层到深层、由量变到质变、由局部到系统。”[47]这无疑已经充分肯定了语言接触的动态性与历时性,而伍铁平则更是进一步强调:“要撰写这部专著(引者按,指语言接触学研究),必须追溯语言接触的历史。”[53]
汉语学界立足于欧化的语言接触讨论,多集中在其方式及结果上,如直接接触对口语的影响,间接接触对书面语的影响,等等。而时至今日,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语言接触形式:网络语言接触。有人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网络语言接触会更加深入,语言变异程度也将进一步加深[54]。可以设想,不同的语言接触方式,必然会带来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结果,并有可能造成“传统”认识的某些改变,而这些无疑都可以而且应该归入历时的范畴。
另外,再就一些具体的研究而言,也指向语言接触的历时性或动态性。比如高万云、赵鹍指出:“语言接触始于‘言’,终于‘语’,又用于‘言’。就是说,语言接触存在于具体的言语交际活动中,长期的双言接触必然使接触的两种语言系统有所改变,而改变了的语言系统又应用于新的言语交际。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修辞因素是语言接触的一个重要动因,只有重视这一动因,语言接触研究才算是完备的。”所以,“对语言接触的研究自然也应该借助动态的修辞学方法,这样才可以全面揭示语言接触的运行机制,也可以弥补其他视角研究的缺陷。”[55]再如,宇璐、潘海英认为,基于语言模因理论,语言间的相互接触即为不同语言模因复合体在作用场中相互影响作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用场中的各要素对语言模因复合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产生了动态的影响和制约[56]。
总之,汉语欧化史的建立,有助于从历时及动态角度观察和认识汉语跟其他语言的接触事实、过程及发展变化,从而把语言接触学引向历时、引向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
二是汉语欧化本身的理论内涵,以下我们结合前边几次提到的“去欧化”进行讨论和说明。我们的基本认识是,“去欧化”是一个既有实际研究意义又有理论价值的问题,其在汉语欧化发展及其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把现代汉语史划分为三个阶段(5)从1919年算起,这三个阶段分别是1919-1949年、1949-1978年、1978年至今。,就总体的倾向性而言,大致经历了欧化(第一阶段)→去欧化(第二阶段)→再度欧化(第三阶段)的发展变化过程,而每个阶段内部,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全部或部分的交替。例如,邵莉、王克非这样描述20世纪30年代的去欧化倾向及其表现:“时代背景决定了翻译的价值与功用以及大众对‘欧化’的态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众语运动集中体现了对‘欧化’的反思,方言等语言资源的吸纳削弱了欧化形式,去欧化也因此成为新的语言风向。”[23]如果要证明以上所引内容,无疑涉及大量的语言事实,需要从共时及历时的角度进行细致的梳理。以前的认识显然不够,相关的事实研究多有缺失,更谈不上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和价值了。
然而,围绕作为历时过程的去欧化,确实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理论思考。何九盈认为,不论怎么“欧化”,汉语总还是汉语[11]6;而朱恒也有类似的认识:“欧化是现代汉语改造、优化的重要推动力,但现代汉语的本质仍然是汉语,而不是被欧化了的外语。”[57]这种观点引发的问题和思考是:汉语是什么?为什么无论怎样欧化也改变不了它的基本属性?这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或方式,怎样做到的?其背后有什么内在的规律,其决定因素是什么?以下两段话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述问题。
虽然,汉语欧化整体上是必要的和积极的,它对改变旧白话长期以来的粗糙、含糊、直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翻译语体对汉语毕竟是异质的,与汉语有很多扞格不入之处。因此,中西语言碰撞交汇之后,必然经历一个整合与融汇的过程[58]。
一方面,欧化作为一种外力,影响着汉语从词汇、到语法、再到篇章的方方面面;而与此同时,汉语自身的规律也在不停地规约着欧化的种种语言变化,吸纳可以吸纳的,排斥不能融入的,这两种力量的角逐最终决定了汉语欧化既是可能的,同样也是有限度的。现代汉语建立的过程也正是欧化的词汇和语法接受种种考验,试图融入汉语系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汉语言的特点、汉民族心理和汉民族的文化规约着欧化的种种现象,只有符合汉语习惯和汉民族文化心理的欧化才能够最终成为汉语的一部分[59]14。
如果说,以上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欧化与去欧化这一矛盾运动的原因,那么除此之外,仅就去欧化问题,我们还可以提出许多问题,并引发一些理论性的思考:比如汉语欧化的限度是什么,其边界在哪里?何为“善性”欧化,何为“恶性”欧化,其判定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去欧化的方式有哪些,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如果再进一步延伸,比如按有人的观点,把汉语的第一次欧化定在东汉以后由于佛教文献的翻译造成的汉语诸多变化[60],那就可以想见,其必然也伴有一个去欧化的过程,那么,与现代汉语的去欧化相比,二者之间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应对其如何认识?总之,无论从语言接触及语言接触学角度,还是从历史语言学以及演化语言学的角度,上述思考都会带来一些新的理论内涵。
三、汉语欧化史的研究内容
我们对汉语欧化取其“广义”:其一是来源范围并非仅限于欧洲或印欧语言对汉语的影响,而是大致等同于“外化”,即汉语受外国语言影响而产生的变化及其发展等;其二是内容范围基本取一个“最大值”,即指汉语受外国语言影响的所有一切方面;其三是其资源范围既包括真正外来的部分,同时也包括受外来因素影响而被“激活”的汉语旧有形式等[35],甚至有可能还包括以上二者结合而形成的中间物(6)以往谈及这个问题时,人们很少从语言资源的角度切入,并且通常只围绕“他源”和“自源”这两者来进行。我们认为,综合观之,汉语欧化就是对不同民族语言资源的再利用。另外,除他源和自源外,很可能还有二者结合而生成的“第三者”,或者叫“中间地带”。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意译词,特别是为数不多的音、意兼译词,与其纠缠或纠结于其是否属于外来词,不如换一个思路,把它们作为“纯”外来词与“纯”汉语词的中间物。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有挑战性,值得进一步探究。。
下面,就在上述范围内讨论汉语欧化史的研究内容。
有人认为,汉语吸收了符合中国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词汇和结构,这个欧化过程往往以“翻译腔”开始,到语言的本土化与语法化结束[4]。这里对汉语欧化作了从起点到终点的简单描述,其实如果着眼于完整的欧化历史及其发展过程,头绪会更多、情况会更加复杂。以下我们着眼于欧化的“时态”,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讨论和说明。
(一)“完成时”研究
这是主要立足于“前端”并着眼欧化全过程的研究,凡业已进入汉语的所有外来形式,或者是汉语原有形式由于受外来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各种变化,均包括在内。具体而言,大致包括以下两个观察与研究角度,而由此就带来了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其一,是欧化现象本身的角度。立足于此,大致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已经“固化”为汉语基本形式的欧化现象,比如大量的外来词语,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一般来讲、据我所知”等话语标记形式[59]169;二是一度存在并使用,后来已经或基本退隐的欧化形式及用法,比如上文所说表示领属关系的结构助词“底”,以及“马克思”音译形式的不同书写变体等。我们认为,对于史的研究而言,相对于一直作为客观存在的欧化形式或用法,那些一度存在而后来退隐的形式或用法更值得重视,研究难度也更大,因而更具挑战性。在一般的认识及研究中,人们往往更加重视“有”,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无”,由此就造成了后者研究的相对空缺。其实,研究从有到无,不仅要发现并抓住相关现象,还需要对其退隐原因等进行分析和解释,而这就有可能使研究者获得观察汉语欧化现象及发展的“另一只眼睛”,进而弥补单纯对“有”的研究之不足。
其二,是欧化载体的角度。这里主要指某一或某些译本及创作中的欧化现象研究,这样的现象都具有已然性,因此属于比较典型的“完成时”。比如,鲁迅后来的小说、杂文和译作,多用“日本新名词”和日本句式[61],而这作为一种已然的“历史”现象,自然应该纳入欧化史的考察范围,如上文提到的邵莉的研究[29],以及邵莉和王克非的研究[23];此外再如Kubler对巴金《家》不同时期欧化与去欧化情况及其表现的对比研究[26]41-135。在这方面,张芹芹、徐剑的研究无论就语料选取还是所得结论而言都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本身几乎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史”的考察与呈现。文中指出:“通过《傲慢与偏见》在不同时期的21个全译本语料库,试图探讨众译本句法规范的历时变迁。平均句长、关联复句、直接引语及特殊句型是研究的重点。数据显示,第一时期的译本更加接近源语的文本特征;第二时期大部分数据都呈现出和第一时期相反的趋势,体现出更加贴近目标语的文本特征;第三时期数据则大都处于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之间,说明本时期译本兼有源语和目标语的共同特征,但总体上呈现出更加向源语靠拢的倾向。”[62]此外,以单一文本为对象的,如对丁韪良翻译《官话约翰福音书》的考察[63]。以往的研究中,针对“人”或“作品”而进行的专题性欧化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基础比较薄弱,而我们认为,汉语欧化史既是汉语中各种欧化现象发生、演进的历史,同时也是不同时期不同的人探索、尝试以及实践的历史,而后者均以作品或文本的形式呈现,不同时代的不同文本大致构成了一个历时的连续存在,所以应该而且能够成为欧化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进行时”研究
这是着眼于“后端”,特别是“当下”,对正在发展变化之中的欧化形式的即时性研究。著名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特别强调语言“正在进行的变化(chang in progress)”,因为可以通过观察研究当代语言中正在进行的变化来解释过去已经完成的变化,寻找共时变异中存在的历时变化证据,以及预测现在的语言变化的可能方向[64]。在相关研究中,有人已经注意到欧化的当下性以及持续性,比如朱冠明指出,“近代以来汉语同西方语言(以及日语)又一次大规模的接触,更是给汉语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影响,这种接触和影响目前仍在持续进行当中。”[65]笔者的研究方向之一是当代汉语词汇、语法等的发展变化,因此对上述“仍在持续进行当中”的诸多欧化现象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比如,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人们较多谈及外来或受外来影响的词缀及类词缀。赵艳平指出,语言接触影响汉语词缀的方式有三种:一是语素的词缀用法从罕见偶发到频繁使用,二是词缀的使用范围扩大,三是词根语素增加类词缀的新义项[66]。沈光浩、何林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汉语类词缀不断增多,派生式新词语大量涌现,语言接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动因。语言接触对于汉语派生构词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外来音节语素化后演变为类词缀,外来类词缀的引进,促使汉语原有词类词缀化等[67]。举例来说,与英语“cool”相对应的“酷”在当代汉语中极为常用,既可单独使用,也经常用于构词。有人曾经对一组说“酷”的文章进行归纳,一共得到46个不同义项[68],可见其使用频率之高、范围之广。这些当然并非一时形成,而是一段时间内“累积”(即历时发展)的结果。另外,我们看到,由“酷”构成的词语还在继续增加,而这也就是说它的发展过程仍在进行之中。比如,“拽酷”(有时也作“酷拽”)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才在网络世界产生及使用的。
以下再举一个更近的例子。来自英语“involution”的“内卷化”,经历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音节缩略过程,即“内卷化→内卷→卷”。“内卷”在2020年使用频率非常高,因而进入《咬文嚼字》杂志编辑部发布的2020年度十大流行语榜单,而在这一过程中,它又向单音节方向发展,既可以单用也可以用于构成组合单位,目前主要在网络世界使用。比如,江都在线2021年1月6日在网上发表《太卷了什么梗?卷王、卷是什么意思梗》,文中说道:“昨天在脉脉上看到一个人吐槽说985/211毕业的人参加工作后都‘太能卷’,都是‘卷王’,实际这个‘卷’是由‘内卷’衍生出来的一个词,意思是‘内部竞争激烈’,再延伸一点就是形容这些人‘事事都要做到最优秀,以便把同事给压下去、比下去’。”总之,这里不但有词形的变化,同时还伴有词义的发展,这就是外来词语在当代汉语中的“进行时”。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它们非常值得关注。对欧化现象在当下语境中的鲜活使用及其发展进行实时性的跟踪研究,与传统的欧化研究有所不同,但却是欧化史研究的应有之义。
总之,时至今日,汉语欧化的进程还在持续,这也就是说,“汉语欧化史”依然还在延伸与发展,而这就是我们倡导“进行时”研究的认识和事实基础。
(三)“起始时”研究
这是立足于欧化“起点”的研究,强调对其来源及产生过程、原因等进行观察、分析,对其初始阶段的形式及用法等进行描写。我们认为,对于史的建构来说,这一研究非常重要。在当代汉语的欧化研究中,有人提出了“新欧化”概念,认为相较于早期汉语欧化,尤其是“五四”时期以来的欧化思潮与汉语欧化现象,在新时代视野下,汉语欧化有了新发展,产生了很多区别于早期欧化的新特征,如产生大量的字母词语以及“-化”“-型”“-性”词族等[69]。虽然上述概念只是立足于词汇角度提出的,但是我们认为它对于汉语欧化,特别是汉语欧化史研究具有极大的意义和价值,而这些新欧化现象本身也为“起始时”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语言事实。
粗略地划分,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基于传统语料的调查研究。这大致属于追根溯源,即对某一欧化形式或用法起始阶段的状况进行调查、描写、分析与呈现,这应该是欧化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以往对此注意不够,具体表现一是对很多欧化形式并未真正追究其来龙去脉,二是有些涉及起源等的讨论往往比较简单,如只是列出一个大致的时间,而少有对其具体来源及过程等的细致追溯。
其二,基于互联网历时或实时语料的调查研究。由此,可以对一些处于起始阶段的新形式和新用法进行即时性、跟踪式的研究,观察其从产生到发展的全过程。有人指出,在网络时代,新生语言现象通常都是产生于并首先传播于网络世界,而借助于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它们都可以准确回溯,找到其最初的源头,并且时间可以精确到秒[70]。我们就此总结、提出了“秒时代”概念,具体所指,就是三个可以“精确到秒”:一是对新语言现象产生时间的确定,二是对语言现象发展变化的每一个重要时间节点的确定,三是对一些语言现象产生与发展过程的回溯与“复盘”(7)对“秒时代”这个概念的内涵及其意义和价值,笔者在《机遇与挑战:论当代汉语中的外来因素及其影响》一文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该文将于近期刊于香港的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在秒时代,汉语欧化现象精确、精细的“起始时”研究成为现实的可能,而由此也给汉语欧化史研究带来新的内容,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如果不过分计较“新”的时效性,那么也可以稍微扩大一点范围,把产生时间不太久的一些欧化现象也归入此类。比如“是时候+VP”现象,一般认为产生于21世纪初,现在对其来源已经比较清楚,即由“仿译”英语的“It’s time to…”句式而来,但是其到底属于书面语还是口语形式(也就是说,是直接语言接触还是间接接触的产物),却有争论[65],而这也就是说,该形式的“起始时”研究还有一定的空间。
另外,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该形式并非普通话直接借入,而是经过了“英语→华语→普通话”过程。我们就《人民日报》所作的调查显示,第一个比较典型成熟的用例见于2002年,有明显的香港背景,而脱离“外来”背景的最早用例见于2004年。在海外华语中,该形式的使用时间明显早于此时,比如以下一例:
(11)是时候离开了!即使这份工原本适合你,但你发展得太快,这份工再赶不上你了。(新加坡《联合早报》1994.3.25)
至于具体是由哪一个华语子社区最先引进该形式,以及它再由怎样的方式和渠道进入普通话社区,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研究(8)当代汉语中的不少新欧化现象都有一个这样的过程,以前的研究对这一点注意得不够。。
(四)“将来时”研究
这是面向“未来”,着眼于“预测”的研究。前引拉波夫的观点已经提及语言预测问题,而苏金智也提出对连续体中语言变体的变化方向进行科学预测判断,他认为语言接触中普遍存在语言演变的连续体,由此可以对不同阶段的不同形式进行定位,也可以用于预测[71]。其他的相关表述也偶能见到,如胡开宝指出:“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字母词的借用会导致汉语语调发生变化,因为这些外来词的发音与其他汉语词汇不同。但是,汉语语音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外语的影响?受到影响的具体层面是什么?这种影响的具体方式和内在动因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非常有趣且具挑战性,显然应引起语言学界的关注。”[72]彭晓则就词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当代汉语中外源性、自源性词缀的共时活跃是否预示着派生式构词模式将转型为汉语的优势构词模式,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73]我们认为,对上述以及其他类似问题的关注或进一步的观察,就属于“将来时”研究的内容,而这样的内容并不少见。
笔者在《现代汉语史》一书的“外来词”一章中,用一节篇幅讨论“外来词的发展趋势”,就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一次预测,具体包括外来词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引进的周期会越来越短、字母词在外来词中会占更大的比例,以及更多的外来词可能在使用中产生新的发展变化等[49]284-289。
前边我们提到,“是时候+VP”现象有可能是经由华语区间接借入,该形式在华语区的使用数量更多,且比普通话复杂,而其原因是借入时间更长、使用更多,因而发展得更加充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通过华语中的使用情况,来预测该形式在普通话区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以下是马来西亚华语中的几个用例:
(12)也许政府是时候,利用现今建筑业过剩的资源,来大力推进廉价屋的发展。(光华网2016.9.9)
(13)他今日发文告说,如今的马华失去了执政权,接下来也可能面对更严峻的挑战,因此是时候“瘦身”。(光华网2018.10.4)
(14)不过,麦家廉认为目前不是时候让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中国领导人会面。(光华网2019.1.24)
就现在的使用情况来看,普通话中“是时候+VP”通常要带“了”,另外VP一般不太复杂,但也不趋向以“光杆”形式出现,而以上几例与此不同:例(12)VP比较复杂,VP前出现停顿;例(13)VP取光杆形式,而例(14)取否定形式。这样,如果以华语为参照,那么普通话“是时候+VP”形式显然还有不小的发展空间,而参照其他很多类似情形,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下一步有可能会朝着与华语趋同的方向发展。
四、结 语
本文立足于历时研究,提出“汉语欧化史”这一概念,并从提出依据、意义和价值以及研究内容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和说明。
总体而言,汉语欧化史既有认识基础,更有事实基础,而二者合一,就构成了它的提出依据;欧化史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它的提出可以在这两个方面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并带来新的元素与活力。至于欧化史的具体研究,我们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并进行了分割式的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四方面内容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比如“完成时”自然也有它的起始点,而截取“进行时”的前端,那就是“起始时”的研究了。所以,上述划分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方便叙述和说明,而具体的研究,则极可能是结合在一起的。不过,我们认为,在起始阶段,细致一些的划分可能更有利于进行相对细致与深入的研究。
按一般的认识,汉语欧化是长达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大规模、持续性的语言接触,其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远超一般的语言接触,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了解、认识近现代汉语的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之一[7]。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欧化现象几经起伏,它与中国社会共变,其本身也可以作为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另一方面,就其自身而言,作为一个持续不断的中外语言大规模接触的样本,汉语欧化的内涵极为丰富,其复杂多样的语言形式、丰富多彩的发展变化事项,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规律,都亟待发掘和总结。
另外,语言接触还在不断、持续地进行,而社会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为它增加了新的内容,比如前边谈到的网络语言接触,作为一种新技术及社会生活条件下的语言接触新类型,与当代汉语诸多新欧化现象的产生关系密切。
我们认为,汉语欧化史是值得花大气力进行深入研究的历史,现在,是提出它并进行全面研究的时候了。汉语欧化史与一般的语言史或语言的要素史(前者如汉语史,后者如汉语词汇史)不同,它不是基于传统认识所作的划分,而是立足于历时,着眼于中外语言接触对汉语产生的影响及具体表现,以及整个发展过程,它涵盖了语言及其应用的方方面面,因此是内涵非常丰富、同时也是非常独特的语言史。对汉语欧化史的建构,可以分为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前者大致是在上述近500年/300年/100年的时间范围内(本文即是立足于此),而后者则是把时间延伸到更为久远的过去。上文已经提及,有人把汉魏以后佛教文献翻译所带来的梵文(属于印欧语系)对传统汉语的影响认作汉语的第一次欧化,而中间还有蒙古语以及满语与汉语的两次较大规模接触[60,65]。这样,再加上近现代以来的汉语欧化,基本就构成了一部完整、丰富的汉外语言接触史,而这或许会成为我们建构汉语欧化史的下一步目标。